在酒楼上研究综述.docx
《在酒楼上研究综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酒楼上研究综述.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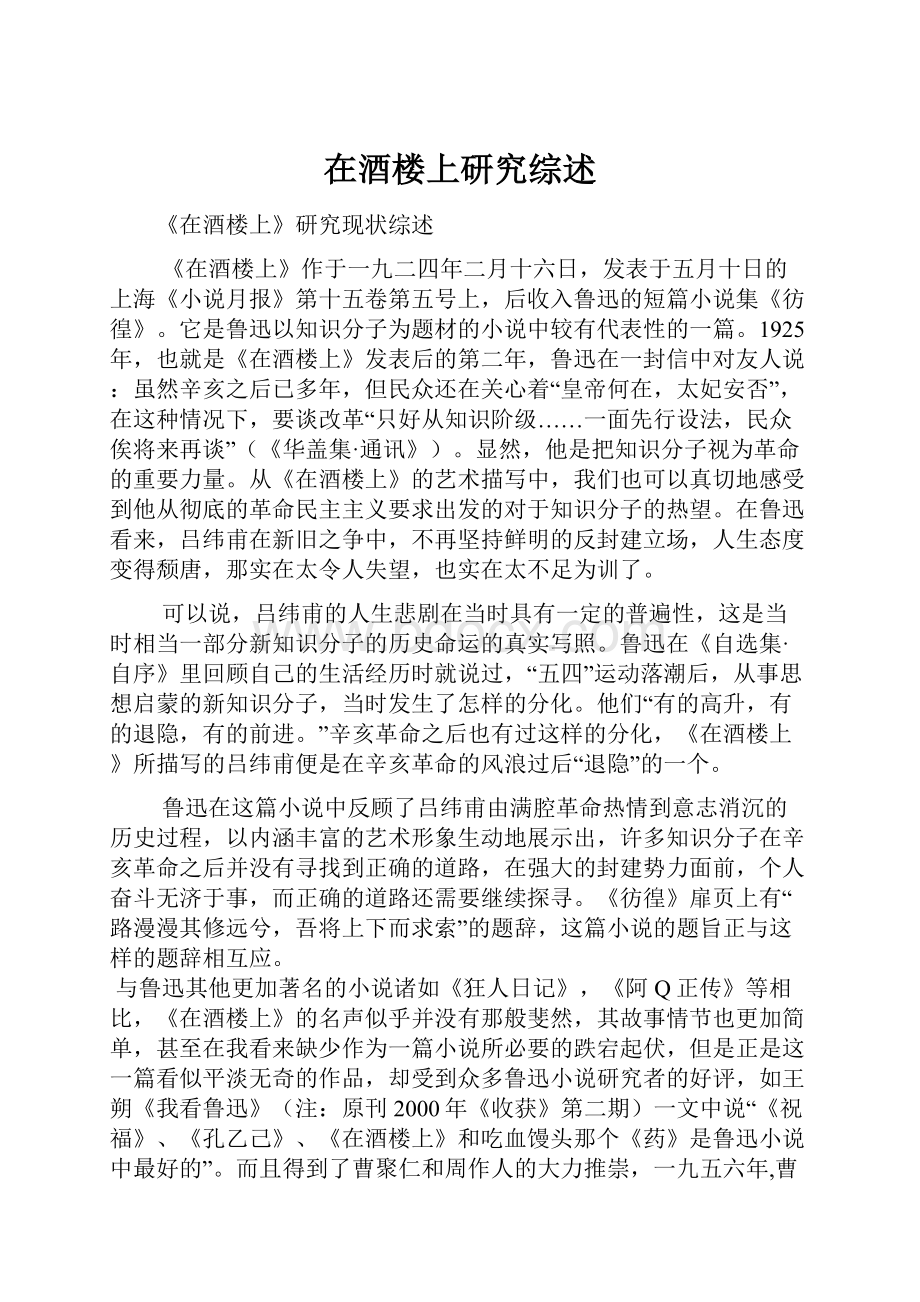
在酒楼上研究综述
《在酒楼上》研究现状综述
《在酒楼上》作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发表于五月十日的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号上,后收入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彷徨》。
它是鲁迅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
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
显然,他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从《在酒楼上》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热望。
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太不足为训了。
可以说,吕纬甫的人生悲剧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里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就说过,“五四”运动落潮后,从事思想启蒙的新知识分子,当时发生了怎样的分化。
他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辛亥革命之后也有过这样的分化,《在酒楼上》所描写的吕纬甫便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浪过后“退隐”的一个。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反顾了吕纬甫由满腔革命热情到意志消沉的历史过程,以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许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寻找到正确的道路,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个人奋斗无济于事,而正确的道路还需要继续探寻。
《彷徨》扉页上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题辞,这篇小说的题旨正与这样的题辞相互应。
与鲁迅其他更加著名的小说诸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相比,《在酒楼上》的名声似乎并没有那般斐然,其故事情节也更加简单,甚至在我看来缺少作为一篇小说所必要的跌宕起伏,但是正是这一篇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却受到众多鲁迅小说研究者的好评,如王朔《我看鲁迅》(注:
原刊2000年《收获》第二期)一文中说“《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吃血馒头那个《药》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
而且得到了曹聚仁和周作人的大力推崇,一九五六年,曹聚仁北上访问时已七十二岁的周作人,谈到了鲁迅的作品。
曹聚仁表示自己最喜欢的是《在酒楼上》,周作人同意曹聚仁的看法,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被钱理群认为是鲁迅艺术水准最高的“诗化小说”之一。
(注:
钱理群:
《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在酒楼上》也被汉学家夏志清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誉为《彷徨》集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四部作品之一”,而鲁迅在回答“在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你喜欢哪一篇”的提问时,举出的总是《孔乙己》,理由是因为写得“从容不迫”。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孔乙己》之外,写得最为“从容不迫”的,就是《在酒楼上》。
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对《在酒楼上》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的特点关于它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历史性的较多来考察,在九十年代以前,人们一直是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来评价《在酒楼上》这部作品的。
在这一立场上,传统文学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酒楼上》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性,以及社会势力的强大,从而总结了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历史教训。
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在重写文学史的新的视域下,借鉴英美“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细读的方法,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吕纬甫所讲述的两个故事中。
下面,就此篇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究的结果做一综述。
一、“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在酒楼上》的确可以说是最富“鲁迅气氛”的一篇小说。
鲁迅小说的创作基调“忧愤深广”,在这里得到了艺术的诠释。
这与五四时期的激进、热情、感伤不同,表现为深沉蕴藉,透露出一种“苦的寂寞”,流露出内心的绝望与苍凉,我们把鲁迅小说的这种特点称之为“鲁迅气氛”。
(参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鲁迅气氛”在小说《在酒楼上》的表现具体与小说的下列特点相关:
1、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小说的开放性和多重阐释性;2、小说表现的作者心灵深处的冲突;3、回忆的心态。
(回忆是现实的救赎方式,标志着现实生活的缺失,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慰藉和心灵的归宿感。
)这篇小说无论是对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探讨的独特构思,还是对人物灵魂揭示的深刻,对写景状物的精当与细腻,均极富鲁迅的才情和风骨。
1956年,时在香港办报的曹聚仁到北京访问周作人,一见面就谈起鲁迅的小说。
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表示欣然同意,他说,我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参看曹聚仁:
《与周启明先生》。
周作人的评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鲁迅小说的很好的视角。
所谓“气氛”,周作人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气味”;在《〈杂拌儿之二〉序》里,他这样写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
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
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气,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
因此,我理解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
而谈到鲁迅的精神气质就不能不注意到鲁迅和他的故乡浙东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骨、魏晋风度的精神联系。
这就提示我们:
要从鲁迅小说与魏晋文人、魏晋文学与玄学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鲁迅气氛”的问题。
在这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的,是王瑶先生在20 世纪50年代写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他发现了《在酒楼上》、《孤独者》和魏晋风度、魏晋风骨的内在联系。
王瑶先生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的魏连殳的塑造,跟鲁迅对魏晋时代的某些人物的看法有类似之处。
他强调吕纬甫性格中的那种颓唐、消沉,他的嗜酒和随遇而安,都类似于刘伶;而魏连殳则具有一种稽康、阮籍似的孤愤的情感。
(注:
钱理群:
“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
《在酒楼上》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叙述的,但叙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作品的主人公。
可是这个“我”又不是简单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独立的角色。
不但对作品的环境氛围和抒情基调承担着极大的作用,而且自身就融入到小说情节中,和主人公构成对话关系,甚至成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对偶式人物。
“他们似乎是一对有着独特心灵感应的孪生人,虽各各不同,又密切相关,骨头连筋。
”(汪晖《反抗绝望》第3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究其实,这种对偶式主人公,都各自是作者鲁迅内心的两个侧面,他们的对话背后,正隐藏着20年代中期鲁迅内心深处的冲突。
据周作人回忆,《在酒楼上》写到的为小兄弟迁坟的情节,取自作者自己的经历。
对照鲁迅的经验和感受,那么,我们也会觉得吕纬甫内心那种对于母亲、对于传统道德的妥协,那种面对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所形成的颓唐而又自责的心态,也是鲁迅曾经有过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酒楼上》的叙事特点是将鲁迅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化成两个人物―――两个孪生兄弟式的人物,一部分以单纯独白的主观的方式呈现,另一部分则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
这种独特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者自身经验过的许多矛盾以及绝望、悲苦的心态,是鲁迅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尝试。
这在鲁迅小说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这种将矛盾着的自己一分为二地转化为两个艺术形象的方法,我们认为是最具有“鲁迅气氛”的。
二、“我”和吕纬甫关系研究
学术界对《在酒楼上》的潜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分析:
1、“认为吕纬甫是鲁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而小说叙述者‘我’则更多地代表了鲁迅的立场,‘我’对吕纬甫在“五四”落潮期的‘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颓废状态采取的是审视和批判的态度。
而吕纬甫也在见证着自己当年的革命热情的同路人——叙述者‘我’的面前表现出一种自省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在小说中坚持的是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吕纬甫的声音是作者力图压抑甚至摆脱的声音。
”
2、“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吕纬甫身上是有鲁迅的影子的,吕纬甫的声音可能比小说叙述者‘我’更代表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
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
‘我’与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内在的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
这种辩难性正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在小说中文本层面的印证。
”(注:
钱理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在酒楼上》中,尽管“我”主要讲述的是吕纬甫的故事,但是作者同时对“我”也倾注了别样的关切。
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我”的身份背景和心理状态: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家乡,就到了离家三十里,当年曾经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教员的S城。
“深冬雪后,风景凄清”,在“懒散和怀旧的心绪”中,“我”独上一家以前熟识的叫一石居的小酒楼。
小说这时描绘了楼下废园中老梅斗雪的风景,进而引入了对“我”的心理描写:
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
小说很自然地从叙事过渡到心绪,羁旅之愁的刻绘为接下来与吕纬甫的相逢奠定了心理期待。
而上述对叙事者的勾勒,一方面使“我”构成了小说中独立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则为与吕纬甫的邂逅和对话提供了必要的前理解。
叙事者“我”与吕纬甫接下来的邂逅构成了一种情境,进而生成了潜在的对话性。
这种对话性主要还不是指小说中我和吕纬甫的对话,两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一下子突然相逢,肯定有寒暄,这种寒暄当然称不上复调意义上的对话性。
而且,在小说中,叙事者与吕纬甫的寒暄很快就变成了吕纬甫的独白。
这时“我”的作用在表面上看只是把吕纬甫的独白串联起来,体现的是纯粹的叙述功能。
由此,《在酒楼上》变成了由“我”叙述出来的吕纬甫所讲述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他千里迢迢回故乡为三岁就死去的小弟弟掘墓迁坟的故事;一个是他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给母亲当年邻居的女孩子顺姑送剪绒花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
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唐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的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
我们猜测,《在酒楼上》有可能是鲁迅最个人化的一篇小说,吕纬甫所做的两件事可能是鲁迅所真正激赏的带有鲜明鲁迅特征的事情,让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光芒。
”(注: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
林毓生研究《在酒楼上》认为吕纬甫完全是作者鲁迅。
小说中的吕纬甫表现出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林毓生由此推断说:
“鲁迅自己一生中也从未在理智和道德上违反这种传统价值,因为他就是小说中的吕纬甫。
”(注: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35页,179页,246页,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三、反传统与传统认同的冲突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教授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提到:
“《在酒楼上》在创作方法上,把严格的现实性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细微的心理解剖,自我解剖结合了起来。
”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吕纬甫和“我”都有鲁迅自己的影像,甚至可以说是鲁迅内心深处两种思想倾向的沟通和争斗。
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如为小弟迁葬等,都是鲁迅亲身经历过的。
有着与吕纬甫相近的生活经历的鲁迅,势必与之有着相似的内心感受和思想倾向,吕纬甫所感到的痛楚,也便是鲁迅的痛楚。
因此,从吕纬甫对旧势力的妥协与屈从中也可看出鲁迅在他特定的处境与思想状况下,存在着不得不妥协的一面。
作为战士,叛逆者和“真正的猛士”的鲁迅,是决绝、坚定,甚至于激进、极端的,但是作为一个同样承袭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的知识分子,一个“从旧垒中来”的“中间物”,鲁迅又有着脆弱甚至是妥协的一面。
《在酒楼上》曾经备受海外学者的关注,譬如林毓生和李欧梵都集中讨论过吕纬甫的内在声音表现出的更复杂的意识,进而探讨鲁迅思想意识的复杂性。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林毓生把鲁迅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显示的层次,或者说是有意识层次,鲁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即属于这种显示的层次。
第二个是隐示的层次,是虽然有意识但鲁迅没有明言的层次。
第三个是下意识的层次(注:
下意识层次林毓生没有多谈,但是他认为谁想要了解鲁迅的下意识,就应该去读《野草》。
通过《野草》了解鲁迅的下意识,这一点在今天差不多已经是鲁迅研究界的一种共识。
)。
林毓生富有启示意义的是他谈论鲁迅意识的前两个层次——显示的层次和隐示的层次——的冲突。
在显示的层次上,鲁迅表现出的是彻底的激烈的反传统,但是在隐示的层次上,却表现出“献身于中国知识和道德的某些传统价值”(注: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35页,179页,246页,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用林毓生更通俗的说法是一种“念旧”,即对传统价值的热情。
这就在鲁迅的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张。
讨论这种紧张关系是很吸引人的,因为林毓生认为,这种紧张不是形式上或者逻辑上的矛盾。
林毓生认为,研究鲁迅如何应对这种紧张,对于了解鲁迅复杂的意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他的做法是通过细读《在酒楼上》讨论这个问题的。
林毓生和李欧梵都十分看重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提供的证据,即《在酒楼上》中的迁坟的故事和送剪绒花的故事“都是著者自己的”。
李欧梵由此认为“在主人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叙述中,潜藏着鲁迅生活的许多真实插曲”,“甚而在某个情节中,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成了鲁迅自身的投影,他们的对话纯然是戏剧性的作者本人的内心独自”(注:
李欧梵:
《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乐黛云主编:
《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90页,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林毓生也据此进行推断,认为鲁迅借助吕纬甫的故事来表现自己的意识,因此可以把小说中吕纬甫和叙事者“我”的对话,看成是鲁迅在他自己心中所进行的交谈。
换句话说,“我”与吕纬甫都反映着鲁迅的思想,而吕纬甫所表现出来的“念旧”,正是鲁迅的复杂意识的隐示的层面。
吕纬甫的矛盾在于他曾经是个到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的反传统的斗士,因此,他所做的迁坟之类的事情与他的曾经有过的革命信仰是冲突的。
吕纬甫的这种冲突在林毓生看来当然也正是鲁迅的冲突,它体现出的是反传统和传统的认同之间的冲突。
我们以往习惯于把鲁迅反传统和“怀旧”的冲突看作是情感和理智的矛盾,即在情感上眷恋中国的过去而在知识上信奉西方的价值。
比如汉学家赖文森也是用这种模式来解释这种鲁迅式的紧张和矛盾的,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所谓“历史”和“价值”的二分法。
但是林毓生对这种二分法却有所质疑,他认为用历史与价值的二分解释鲁迅的冲突是不顾具体历史根源的复杂性的一种僵硬解释,因为鲁迅意识中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间,而在于思想和道德的同一范畴之内。
换句话说,鲁迅的反传统和认同传统,都是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注: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35页,179页,246页,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而不涉及情感领域的问题,它是价值和理性的同一层面的问题,因而它是不可解决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即传统在鲁迅这里完全构成了两个对立的命题。
一个命题是:
传统是必须抛弃的,它引发的正是五四的文化逻辑:
彻底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姿态;而另一个命题则是:
传统是应该继承的,用林毓生的话来说,“中国传统的完整秩序业已崩溃,但它的某些成分未必就丧失其同一性和影响力”。
这是两个对立的命题,所以它是无解的。
也许在今天会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无解?
我们完全可以扬弃坏的传统,继承好的传统,对传统完全可以一分为二。
我认为这是对待传统的一种理想化态度,不符合五四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逻辑。
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那样,鲁迅意识的冲突“是20世纪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象征”,这种危机在当时的绝大多数激进主义者看来正是传统的整体性危机,它在五四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形成的是一种整体观思想模式,不可能寻求一个多元论的解决冲突的方法。
林毓生称,因而在鲁迅的思想中无法产生可供选择的分析范畴,所以鲁迅的意识的危机仍然没有缓解,而中国文化的危机则必须借助于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最终解决。
但这就意味着把传统的价值无差别地全盘抹杀,就像在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传统一下子又都成了好的东西一样,都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结果。
(注:
吴晓东:
《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四、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与深刻意义
鲁迅创作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所以取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观察与表现的视角也是独特的,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在酒楼上》的情节结构模式属于“离去——归来——再离去”,透过情节结构模看到鲁迅独特的眼光,除社会批评所达至的意义,其中内蕴着“反抗绝望”的哲学和生命体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开掘了在黑暗的现实中摸索光明和希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的深”,同时在谋篇布局和艺术技巧的运用方面也显示了高超的成就。
从《在酒楼上》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创作过程中对材料进行了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穿插的手法,丰富了情节,使他的短篇小说,能够“在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
在这篇小说里,几处景物的穿插描写尤其为小说增添了亮色,每一处景物都是一个耐人咀嚼的象征意象,凝聚着鲁迅对人生和时代的思考。
例如,他以“啧痕斑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霉苔”,无精打采的“铅色的天空”来渲染荒凉破败的气氛,烘托出人物疏懒悲凉的心绪;又以“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株的繁花”,“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的如火”,来表达绝望中仍不放弃希望,在苦闷中仍要坚持抗争的思想感情。
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中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小说的纽带,不论是政治革命研究范式还是思想革命研究范式,都没能从内部提供鲁迅小说作为完整的文学统一体所必须具备的统一的基调和由此产生的语气氛围,也没能求寻到任何一部艺术史诗固有的内在精神线索及其对作品的基本感情背景和美学风格的制约作用。
汪晖认为,这两个方面显然不决定于现实本身,而决定于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感受,也就是说,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
前述的两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重在考察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在小说中的体现,虽也注意到鲁迅某种精神状态对某些具体作品的影响,但其意识重心还是以一些外在于鲁迅的普泛性概念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为理论试金石,测试它们在鲁迅小说中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这样,鲁迅小说作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展现必然具有的贯穿始终的精神发展线索却被忽略了。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切入分析鲁迅小说,恰恰是为了说明作家的主观精神结构的内在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自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对于过渡时代的中国的全部复杂性的精神承担,鲁迅的小说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双重的复杂性。
通过这一番疏理,汪晖自然将鲁迅小说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转移到主体意识方面。
汪晖用“历史中间物”这个概念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的主体意识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
中间物意识既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动荡和碰撞中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的主体意识,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矛盾的心灵折光。
把鲁迅小说放在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封闭社会走向世界文明的总体文化背景上,就可以看出,它展示的正是历史中间物对传统社会以及自我与这一社会的撕拉牵扯盘根错节的搏斗过程。
从狂人的恐惧和发现,到夏瑜的奋斗和悲哀,到N先生的失望和愤激,到吕纬甫的颓唐和自责,到疯子的幽愤和决绝,到魏连殳的孤独和复仇,到涓生的绝处逢生的希望和绝望,构成了鲁迅小说的一条清晰的内在感情线索。
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以及《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祝福》等作品中的“我”所构成的形象体系共同体现着历史中间物的主要精神特征:
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对“死”(代表着过去、绝望、衰亡的世界)和“生”(代表着未来、希望、觉醒的世界)的人生命题的关注;以乐观主义为根本的“悲观主义”和认识。
这些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初体现者的觉醒知识分子,却无法成为这一进程的胜利的体现者——这正是中间物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
中间物意识奠定了鲁迅小说总基调:
这是一曲回荡在苍茫时分的黎明之歌,从暗夜中走来的忧郁的歌者用悲怆、凄楚、嘲讽的沉浊嗓音迎接着正在诞生的光明。
作为小说创作主体的鲁迅,以向旧生活诀别的方式走向新时代,这当中不仅有深刻严峻的审判和热烈真诚的欢欣,而且同时还有对自身命运的思索,以及由此产生的既崇高又痛苦的深沉的悲剧感。
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凸现生来的是,鲁迅这个独特的文学主体对凝聚着众多社会历史矛盾的中间物意识的自觉而又深刻的感受。
圆形故事形态:
《在酒楼上》中的“我”,在毫无酒楼气的酒楼上百无聊赖地喝着闷酒,巧遇昔日同窗吕纬甫,颓唐的吕纬甫幽幽地诉说自己经历的无聊事,他所诉说的“迁葬”和“送花”两件事在作品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不表明这两件事在整篇小说的故事构成中有多么的重要,其实将“迁葬”和“送花”换成另外的无聊事,并不妨害主人公的结局,因为主人公的命运几乎在他还未出场的浓郁的伤感气息中就已铸就,他的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圆”原本就无所谓起点与终点,就如吕纬甫无可奈何喟叹的那样:
“我在少年时,看见峰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
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
这里起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
吕纬甫的故事是停滞而不发展的,那些无聊事实实在在都是他经历的,可对他而言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孤独者》那“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呈现出的圆形故事形态是《在酒楼上》中“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另一种体现。
(注:
叶世祥《鲁迅小说的故事形态》原刊《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复调的诗学:
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着眼,更应引起重视的恰恰是叙事者“我”。
由于“我”的存在,吕纬甫讲述的故事便被置于叙事者再度讲述的更大的叙事框架中。
吕纬甫的故事便成为以“我”为中介的故事。
一方面吕纬甫的故事经过了叙事者“我”的再度转述,另一方面,“我”同时也充当了一个审视者的角色,吕纬甫的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注: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
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性一方面表现为小说的叙述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价值观意义上的对话,小说的更深层的语义正由这种关涉价值观的对话关系显示。
而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的潜在的对话,最终可以看作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
“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的两种声音在对话,在争辩,在冲突,而且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
前引李欧梵的话称“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成了鲁迅自身的投影,他们的对话纯然是戏剧性的作者本人的内心独白”,李欧梵和林毓生强调的都是叙事者“我”与吕纬甫的同一性,而小说的对话性本身指向的更是差异性,就是说,当鲁迅可能认同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