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诗词杂想之一4豪放与婉约.docx
《读毛泽东诗词杂想之一4豪放与婉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读毛泽东诗词杂想之一4豪放与婉约.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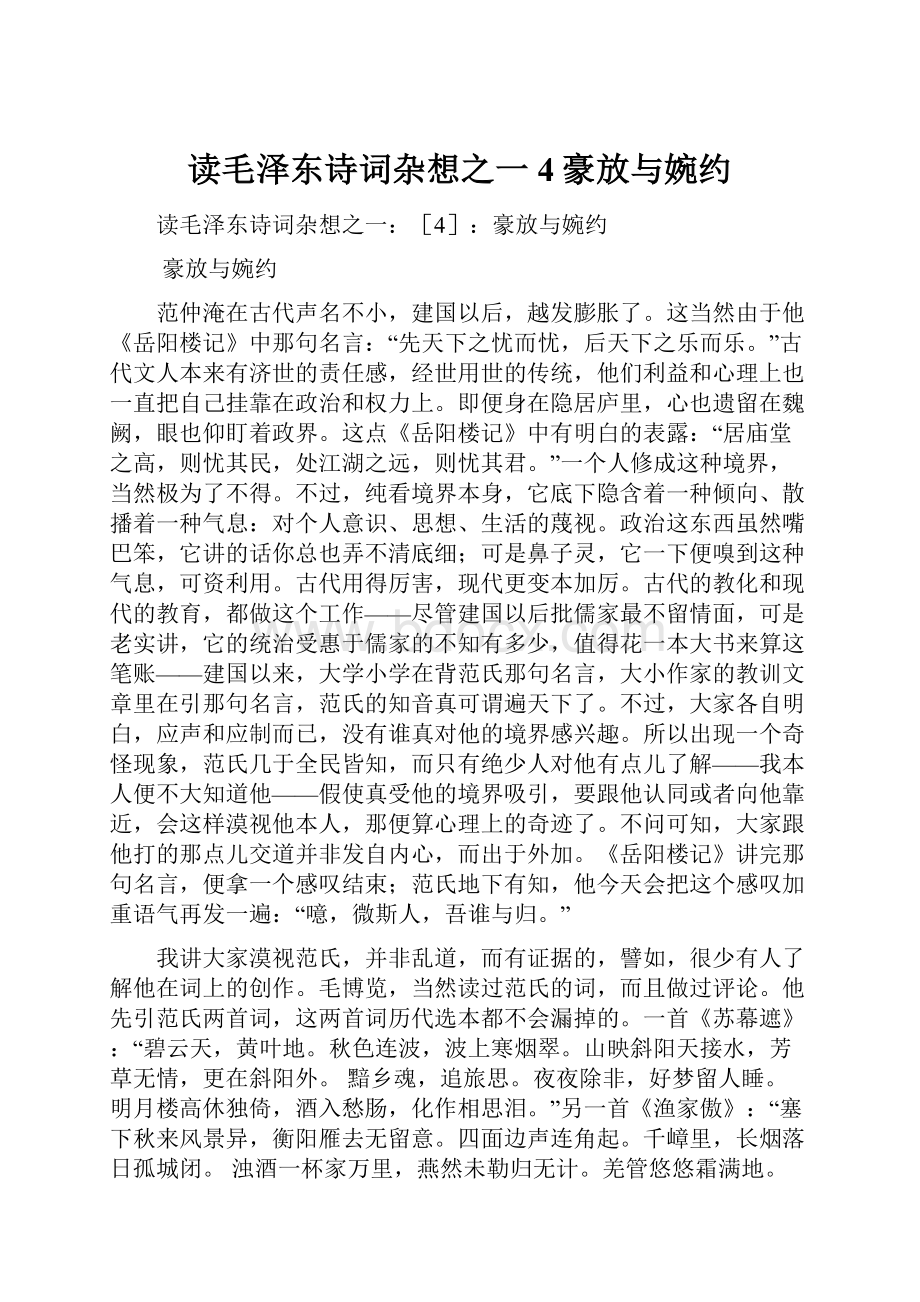
读毛泽东诗词杂想之一4豪放与婉约
读毛泽东诗词杂想之一:
[4]:
豪放与婉约
豪放与婉约
范仲淹在古代声名不小,建国以后,越发膨胀了。
这当然由于他《岳阳楼记》中那句名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古代文人本来有济世的责任感,经世用世的传统,他们利益和心理上也一直把自己挂靠在政治和权力上。
即便身在隐居庐里,心也遗留在魏阙,眼也仰盯着政界。
这点《岳阳楼记》中有明白的表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个人修成这种境界,当然极为了不得。
不过,纯看境界本身,它底下隐含着一种倾向、散播着一种气息:
对个人意识、思想、生活的蔑视。
政治这东西虽然嘴巴笨,它讲的话你总也弄不清底细;可是鼻子灵,它一下便嗅到这种气息,可资利用。
古代用得厉害,现代更变本加厉。
古代的教化和现代的教育,都做这个工作——尽管建国以后批儒家最不留情面,可是老实讲,它的统治受惠于儒家的不知有多少,值得花一本大书来算这笔账——建国以来,大学小学在背范氏那句名言,大小作家的教训文章里在引那句名言,范氏的知音真可谓遍天下了。
不过,大家各自明白,应声和应制而已,没有谁真对他的境界感兴趣。
所以出现一个奇怪现象,范氏几于全民皆知,而只有绝少人对他有点儿了解——我本人便不大知道他——假使真受他的境界吸引,要跟他认同或者向他靠近,会这样漠视他本人,那便算心理上的奇迹了。
不问可知,大家跟他打的那点儿交道并非发自内心,而出于外加。
《岳阳楼记》讲完那句名言,便拿一个感叹结束;范氏地下有知,他今天会把这个感叹加重语气再发一遍: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
我讲大家漠视范氏,并非乱道,而有证据的,譬如,很少有人了解他在词上的创作。
毛博览,当然读过范氏的词,而且做过评论。
他先引范氏两首词,这两首词历代选本都不会漏掉的。
一首《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另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是这位被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被西夏畏称为“小范老子”的范文正公守边时写的,据说并不止一首,都以“塞下秋来”起头,可惜其余的没有传下来。
毛对这两首词发表议论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
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
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
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
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者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
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
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
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从末一句看来,毛并不像普通家庭那样,直接跟妻子和女儿对面,一边闲谈一边交流,把范词拿出来朗读或者传观;他把这通感想写下来,然后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转交;就好像批公文似的,写下“请转某某同志一阅。
”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有点儿特别。
我想起一则逸闻。
英国不知哪位女王去敲她丈夫的房门,丈夫问是谁,她答“英国女王”;丈夫不理她,再问是谁,她答自己的名字,丈夫还不理;最终她柔和地说:
“你的妻子”,门才得开。
也许跟干一切行当一样,元首当久了也会形成职业病。
我不知毛的妻儿收到这样经外人转交的家庭公文时有何感受。
这是题外话。
在这篇公文里,毛把词分为两派,并且透露自己偏向豪放。
拿婉约与豪放来分别古代词的风格倾向,当然有它的方便,但是它太不精细了。
词史上那么多风格各相区别的作家,是不易简单地把两顶大帽子全体罩盖的,因为各家的脑袋规格、形状都颇为不同。
只谈豪放婉约,有些像李逵不分青红皂白的抡板斧“排头砍去”了。
古代批评家并不这么笼统,毛自己也有领会,他觉得范氏那两首词便介于两者之间——不过,仍要归它们入婉约,好成就那个二分法。
实际上,范氏《苏幕遮》上片已经很有豪放派风度,《渔家傲》通篇几乎已不存婉约气息。
毛说“基本上仍属婉约”,而不讲基本上已属豪放,看来他听惯后代豪放派声嘶力竭的喊嗓子,给豪放派定的调门比较高。
历来豪放派的溯源,除《花间集》里一丝半点写塞上的作品——比如毛文锡《甘州遍》——便数到范氏这首《渔家傲》。
范氏那时候,豪放派还没有眉目,欧阳修词学观念较为正统,所以讥笑《渔家傲》为“穷塞主之辞”。
这个评语大概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严正的斥责,而像朋友间的互相调笑,不过,观念的区别一目了然。
可是,欧阳修自己的好些作品,比如《采桑子·西湖念语》那组名词,虽调门不高,也决非“婉约”二字讲得尽或者讲得准的。
《朝中措·平山堂》更谈不上婉约,而俊快、豪爽、洒脱。
王国维《人间词话》引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两句,称赞道:
“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直接把“豪放”一词来品目欧阳修。
论者还常讲欧阳修“疏隽开子瞻”,疏隽大概不易讲成婉约,子瞻在我们心目中婉约的印象也决不会太重。
范氏是个特别的作家,他似乎无意以文学名家,可是文、词都有名作。
他能开豪放的先河,唱出豪放那第一声——我没有算上毛文锡——也许正因为他无意为词,因而不大注意词的规矩,心理、笔路承担的传统负荷要弱得多;他写作时,也便能更自由地把笔直追自己的经历、感受。
非专业人员总享有法外治权的;当然,在以笔达意的训练上,他绝对的专业水准。
词论家向来对范氏注意不够,也许他存词太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吓唬人。
他婉约的方面,“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两句,以后写同类情景、用相近笔法的篇什,都没有能超过他。
“酒未到,先成泪”比他自己先前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更进一解。
李清照名句说: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脱胎于范词,而多了些机趣、流动,可是论情感的诚挚,还隔一尘。
眉头和心头都是愁爱去的地方,范氏好像说:
愁要来,眉头和心头都害怕,忙不迭地闪避,把愁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可是终躲不过。
范氏写景,已经纯是豪放派气象,而不像《花间》和柳永,偶有一篇、一二笔阔大。
前边引到《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他的《御街行》:
“珍珠簾卷玉楼空,天谈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虽然并不鼓努作气,景象的雄阔,瞎子也看得见。
他有一首词似乎从没有人提到。
《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
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词里发议论、搬事典、甚至用口语,都该列为创辟之作,从前并没有人在词里这样胡来过。
这点且不详论,只看它的风格,尤其神似苏辛一脉好些二流作品;假使把它收到辛弃疾的集子里,我看没有人会把它剔出来。
也便是说,豪放派好些艰辛探索后的模式,他老早便轻巧地弄过了。
豪放派见了他,应该爽然若失,好比孙猴子翻斤斗云去天柱边洒了尿后,忽然发现只到了如来佛的手指边。
范氏只存下来五首词,两首算得正牌的豪放词,另两首写景早抢了豪放派的先,剩下来那首也决不软媚,可以收入《东坡乐府》的。
只把他豪放词的比例看作五分之二,我凭印象估计,东坡的豪放词未见得超过这个标准。
范氏吃亏在词太少,背后也没一群跟随者起哄,所以开宗立派的荣誉给东坡混走了。
豪放派的发明权我们争不回来,可是,假如我们不势利,至少得把豪放词的发明权注册在范氏身上。
他早就写出成熟的豪放词,东坡已落第二乘。
也许有人要讲,我这个说法也足够势利,为什么豪放词的版权不能判给名气更小、更不起眼的毛文锡?
我觉得毛文锡那一篇只是偶然之作,出于意外,他整个风调、其余作品里连一点豪放的兆头也没有;不比范氏,豪放是他的老习惯,尽管未见得是有意为之。
当然,我这个回答,意见不同者会当为狡辩。
划分婉约派最大的失误是李煜。
他被推为婉约派的大家,可是细读他的词,感慨之深、格局之大、尤其是抒情方式上的奔放、直率,都决非婉约家数——我知道讲李煜奔放直率,别人要跟我吵架的,可是目前先不回嘴——而且,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整个词史里都没有人能够梦见。
王国维对他推崇,极有见地。
词论家的思想、眼光,大半局限在文学、社会学里,缺乏对生命的哲学领悟——这也像是先秦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弱项——而王国维颇有哲学气质,并且下过功夫。
他自己做词,也有哲学意蕴。
他在《人间词话》里比较李煜和宋徽宗两个亡国之主:
“宋道君皇帝亦略似之。
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同样的亡国,而道君皇帝只局限在个人的身世之感,李煜却能把这个感受拔高到全人类的共同境遇。
我自觉领会得到王氏写“释迦、基督”四字时,是什么在触动他。
李后主把“流逝”这个意象写得后人没有措手的余地,透辟地概括出人类的恒常情感、一致命运;无论个人的具体遭际怎样,跟他一谈,都会觉到同病相怜。
这样,他便从具体的情景中超越出来,好比灵魂比肉体的枷锁中出窍,升到了哲学以至宗教的层次。
人类生活无非同时间的一场战争,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得在时间里才可能获取;我们想要保留现有的一切,也得经过时间的批准;可是时间极其刁难,老是板面不同意。
我们的欲望总在向时间乞讨,而时间不但不施舍,反而向我们抢劫。
它把我们曾有的抢走,丢进失去里,把今天抢走,掷向过去里,它甚至把我们的岁月抢走,而且永不归还。
最终,它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欲望本身也夺去,把生命扔进死亡,像扔片垃圾到垃圾箱,一点儿不怜惜。
这场战争里,我们从头便预定了是个失败者——在永恒的时间里,我们只是被它流逝者,我们的过去、所有给它流逝,连我们自己也给它流逝。
李后主讲: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些词直接触动我前边发的那些感叹,简直不消过渡的。
一个对我那段感叹没有明确意识的人,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触动更微茫难辨,处在更含糊隐晦的层面上罢了。
李后主是中国人,当然知道孔夫子站在河边的感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他又佞佛,佛家所谓“无常”,他也不会陌生。
这些无非只是“流逝”的另外版本。
亡国之后,旧日繁华一去不返,家国也一去不归,他的领会之深,我们常人想象不来。
可是,我们毫不奇怪他的词把“水”作为中心意象,他的名句全都在写水,因为水是“流逝”最为经典、最为恰切的象征。
便连“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里,名义上写草,明眼人也一眼辨得出它的意象实际依然是水,“更行更远”,冉冉而去,老不止息,不是水是什么?
欧阳修眼毒,早剥掉这句的面具,看出真面来了;他改写后主更行更远的离恨时,便把春草置换为春水: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
就我所见,王国维之后,只有叶嘉莹先生阐发过李后主的哲学境界。
龙榆生先生是我感激的前辈学人,因为他那本《唐宋名家词选》一直是我的基本读物。
我对他不了解,不过,有些迹象表明,他似乎也不大留意词里的哲学境界,他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里,就不选王国维“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一类作品。
即便最粗线条地把词分为豪放婉约两大块,李煜也圈不进婉约里去,而塞进豪放里来呢,恐怕豪放派那些正主儿也要视他为异类,挤他出去。
这是李后主的幸运,因为无论划归哪边,他的意义都要受损。
他身上的特质,使他把豪放婉约两派一齐推远了,显出他跟两派同样话不投机;实际上,那个对立与他了不相干,描述不了他最重大的品格。
假使不说他超出两派之上,至少得说他越出两派之外。
我承认自己对他有偏见似的偏爱。
毛把词分为两派,对古代众多作家未必适用,对他自己倒是顶配套的。
他的词像个爽快人、直性子,没有那么多细腻的微妙的东西需要照顾,咱们也痛痛快快把他算为豪放派便成了。
他自述不废婉约,也是实情,他现存最早的两首词可以作证。
[1]《虞美人·枕上》基本情调是婉约的,里边尽是婉约派的陈词滥调;然而局部地方用了一个受豪放派宠爱的意象:
“江海翻波浪”,来比方“愁”的激烈、巨大,给人的感觉,不很谐和。
《贺新郎·别友》试图把豪放与婉约调合起来,它安排了相别时婉约泊的悲伤,又讲到分别是为了革命的大事业,拿豪放派的笔墨描写了想象中的这场斗争,再期望两人比翼双飞。
这样,在一个情景里,有逻辑合情理地展示了由婉约到豪放的心境变化。
《枕上》那首,毛自己在《致李淑一》信中承认写得不好;《别友》那首,我们也觉得未见得太好。
两词都是写给杨开慧的。
贾宝玉讲“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恋爱这样感情也是水做的骨肉,它性子柔软,非常女性化。
毛词后来没有恋爱题材,否则,也许他会再次“不废婉约。
”
[1]我把毛那两首词抄在下边,免得我一个人空口讲白话:
《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贺新郎·别友》(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难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重过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