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docx
《《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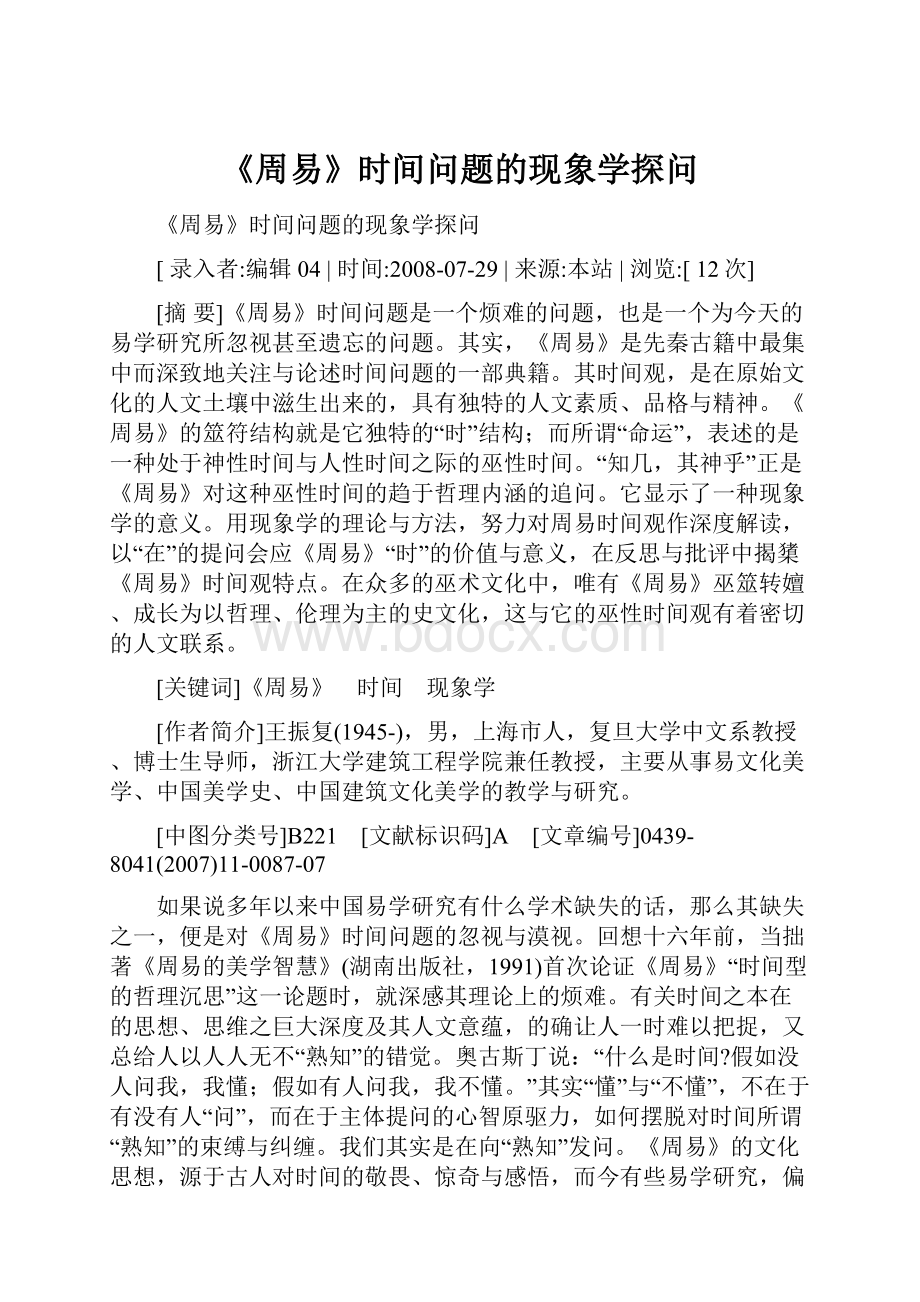
《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
《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
[录入者:
编辑04| 时间:
2008-07-29|来源:
本站|浏览:
[12次]
[摘要]《周易》时间问题是一个烦难的问题,也是一个为今天的易学研究所忽视甚至遗忘的问题。
其实,《周易》是先秦古籍中最集中而深致地关注与论述时间问题的一部典籍。
其时间观,是在原始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
《周易》的筮符结构就是它独特的“时”结构;而所谓“命运”,表述的是一种处于神性时间与人性时间之际的巫性时间。
“知几,其神乎”正是《周易》对这种巫性时间的趋于哲理内涵的追问。
它显示了一种现象学的意义。
用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努力对周易时间观作深度解读,以“在”的提问会应《周易》“时”的价值与意义,在反思与批评中揭橥《周易》时间观特点。
在众多的巫术文化中,唯有《周易》巫筮转嬗、成长为以哲理、伦理为主的史文化,这与它的巫性时间观有着密切的人文联系。
[关键词]《周易》 时间 现象学
[作者简介]王振复(1945-),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兼任教授,主要从事易文化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建筑文化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87-07
如果说多年以来中国易学研究有什么学术缺失的话,那么其缺失之一,便是对《周易》时间问题的忽视与漠视。
回想十六年前,当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湖南出版社,1991)首次论证《周易》“时间型的哲理沉思”这一论题时,就深感其理论上的烦难。
有关时间之本在的思想、思维之巨大深度及其人文意蕴,的确让人一时难以把捉,又总给人以人人无不“熟知”的错觉。
奥古斯丁说:
“什么是时间?
假如没人问我,我懂;假如有人问我,我不懂。
”其实“懂”与“不懂”,不在于有没有人“问”,而在于主体提问的心智原驱力,如何摆脱对时间所谓“熟知”的束缚与纠缠。
我们其实是在向“熟知”发问。
《周易》的文化思想,源于古人对时间的敬畏、惊奇与感悟,而今有些易学研究,偏偏“遗忘”如此重要的时间难题,这不免令人沮丧。
我们是多么不幸地茫然生活在时间的“黑暗”之中。
命运:
巫性时间
在通行本《周易》中,时间这个概念,一律被准确地称之为“时”。
没有哪一部中华先秦古籍,如此集中而深致地关注与论述时(时间)问题。
《易传》论乾卦,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其“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变通者,趣(引者注:
趋)时者也”;说坤卦“承天而时行”,君子仿效,“待时而动”。
《易传》又释大有卦: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言随卦“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称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大过卦时应“大过”,则运必有反,故日:
“大过之时大矣哉”;坎卦示喻重重险陷,“险之时用大矣哉”;遯卦表征人生之退避,此当“与时行也”,“遯之时义大矣哉”;睽卦喻乖背之理及因时而运化,所谓“睽之时用大矣哉”;损卦言减损之道,故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之论。
而革卦“革之时义大矣哉”,又“动静不失其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至于蹇卦、解卦、骺卦与艮卦等等的卦义解读,均不离“时间”主题。
凡此则雄辩地证明,《周易》对于“时”问题何其关注、执著。
这里,《易传》所言“时成”、“四时”、“趣时”、“时行”、“待时”、“随时”、“时变”、“时用”、“时义”以及“与时偕行”、“与时消息”等等,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时间意识?
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曾经指出:
“‘时’在这里最显在的意义是指天文学上的时令、四时;其次是指巫学意义上的人的时运、命运;而最深层的意蕴,是属于文化哲学层次上的时机、时势,是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中最独有的时间观念和时间哲学。
”这一论述大致可以成立。
欠周之处在于,《易传》时代,中华尚无成熟意义的“天文学”与“时间哲学”,《易传》所处的战国中后期之天文学与时间哲学意识,主要融渗于阴阳五行之说以及历算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意识、理念之中。
《易传》成篇,几与通行本《老子》、《孟子》、《庄子》同时。
此时作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其文化重心,正处于从原始巫文化向史文化即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文化形态的转嬗之中。
《易传》是表述这一文化转嬗的重要文本。
学界有人以为,《尚书·尧典》是论述“时间”观的最早文本。
但《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之“时”,仅为时令之义,并无人文哲学意蕴,而且,《尚书·尧典》的成书年代难以确考,学界一般以为在周、秦之际。
《庄子》一书的“时”意识与观念,除了指时令、时刻等义以外,其中最具哲学等意义的论述,是其《盗跖》篇所言“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以及“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等等。
一种葱郁的生命时间意识跃然纸上。
陈世襄在论说“诗的时间的诞生”这一问题时,认为屈子《离骚》之前,中华古代关于哲学、美学与诗学的时间概念与观念并未正式登上历史,人文舞台。
考虑到前述比如《庄子》关于生命时间问题的有关阐说与觉悟这一点,此见未确是可以肯定的。
比较而言,通行本《周易》的“时”意识,主要是在原始巫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
首先,整部《周易》六十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以及乾“用九”、坤“用六”两条文辞,大凡都是巫筮记录。
本经作为“占筮之书”,通篇讲的是吉凶休咎、趋吉避凶,讲人的命运。
这实际上是讲一个字,即命理意义的“时”。
所谓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之类,都应在这个“时”字上。
正如魏王弼《周易略例》云:
“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
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
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
” 其次,这种巫筮、命理的“时”意识,浸透于《周易》卦爻筮符系统之中。
简约地说,《周易》象数即筮符系统是一种中华古代典型的“时”结构。
第一,从每卦六爻爻位之动态分析,从初、二、三、四、五到上位,是一时间运变历程,从上经第一乾卦、下经第一咸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演化,尤可以得到确切而有力的证明。
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到上九“亢龙,有悔”、咸卦从初六“咸其拇”到上六“咸其辅颊舌”之爻位的上升,来象喻人之命运吉凶互变的运化过程。
第二,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均由下、上两个八卦所构成,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的方位,都以空间位置的变动来象示时间的变化。
比如“后天八卦”的方位,坎卦为北为水为冬,阴气极盛而衰,阳气始生之时;震卦为东为木为春,阳气渐长之时;离卦为南为火为夏,阳气极盛而衰,阴气始生之时;兑卦为西为金为秋,阴气渐长之时。
这后天(文王)八卦方位的四正卦,是自然四时运行的卦筮模式,而其四隅卦即东北艮、东南巽、西南坤与西北乾,都喻示相应时位的过渡。
第三,六十四卦每 [摘要]《周易》时间问题是一个烦难的问题,也是一个为今天的易学研究所忽视甚至遗忘的问题。
其实,《周易》是先秦古籍中最集中而深致地关注与论述时间问题的一部典籍。
其时间观,是在原始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
《周易》的筮符结构就是它独特的“时”结构;而所谓“命运”,表述的是一种处于神性时间与人性时间之际的巫性时间。
“知几,其神乎”正是《周易》对这种巫性时间的趋于哲理内涵的追问。
它显示了一种现象学的意义。
用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努力对周易时间观作深度解读,以“在”的提问会应《周易》“时”的价值与意义,在反思与批评中揭橥《周易》时间观特点。
在众多的巫术文化中,唯有《周易》巫筮转嬗、成长为以哲理、伦理为主的史文化,这与它的巫性时间观有着密切的人文联系。
[关键词]《周易》 时间 现象学 [作者简介]王振复(1945-),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兼任教授,主要从事易文化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建筑文化美学的教学与 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87-07 如果说多年以来中国易学研究有什么学术缺失的话,那么其缺失之一,便是对《周易》时间问题的忽视与漠视。
回想十六年前,当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湖南出版社,1991)首次论证《周易》“时间型的哲理沉思”这一论题时,就深感其理论上的烦难。
有关时间之本在的思想、思维之巨大深度及其人文意蕴,的确让人一时难以把捉,又总给人以人人无不“熟知”的错觉。
奥古斯丁说:
“什么是时间?
假如没人问我,我懂;假如有人问我,我不懂。
”其实“懂”与“不懂”,不在于有没有人“问”,而在于主体提问的心智原驱力,如何摆脱对时间所谓“熟知”的束缚与纠缠。
我们其实是在向“熟知”发问。
《周易》的文化思想,源于古人对时间的敬畏、惊奇与感悟,而今有些易学研究,偏偏“遗忘”如此重要的时间难题,这不免令人沮丧。
我们是多么不幸地茫然生活在时间的“黑暗”之中。
命运:
巫性时间 在通行本《周易》中,时间这个概念,一律被准确地称之为“时”。
没有哪一部中华先秦古籍,如此集中而深致地关注与论述时(时间)问题。
《易传》论乾卦,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其“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变通者,趣(引者注:
趋)时者也”;说坤卦“承天而时行”,君子仿效,“待时而动”。
《易传》又释大有卦: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言随卦“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称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大过卦时应“大过”,则运必有反,故日:
“大过之时大矣哉”;坎卦示喻重重险陷,“险之时用大矣哉”;遯卦表征人生之退避,此当“与时行也”,“遯之时义大矣哉”;睽卦喻乖背之理及因时而运化,所谓“睽之时用大矣哉”;损卦言减损之道,故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之论。
而革卦“革之时义大矣哉”,又“动静不失其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至于蹇卦、解卦、骺卦与艮卦等等的卦义解读,均不离“时间”主题。
凡此则雄辩地证明,《周易》对于“时”问题何其关注、执著。
这里,《易传》所言“时成”、“四时”、“趣时”、“时行”、“待时”、“随时”、“时变”、“时用”、“时义”以及“与时偕行”、“与时消息”等等,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时间意识?
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曾经指出:
“‘时’在这里最显在的意义是指天文学上的时令、四时;其次是指巫学意义上的人的时运、命运;而最深层的意蕴,是属于文化哲学层次上的时机、时势,是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中最独有的时间观念和时间哲学。
”这一论述大致可以成立。
欠周之处在于,《易传》时代,中华尚无成熟意义的“天文学”与“时间哲学”,《易传》所处的战国中后期之天文学与时间哲学意识,主要融渗于阴阳五行之说以及历算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意识、理念之中。
《易传》成篇,几与通行本《老子》、《孟子》、《庄子》同时。
此时作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其文化重心,正处于从原始巫文化向史文化即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文化形态的转嬗之中。
《易传》是表述这一文化转嬗的重要文本。
学界有人以为,《尚书·尧典》是论述“时间”观的最早文本。
但《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之“时”,仅为时令之义,并无人文哲学意蕴,而且,《尚书·尧典》的成书年代难以确考,学界一般以为在周、秦之际。
《庄子》一书的“时”意识与观念,除了指时令、时刻等义以外,其中最具哲学等意义的论述,是其《盗跖》篇所言“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以及“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等等。
一种葱郁的生命时间意识跃然纸上。
陈世襄在论说“诗的时间的诞生”这一问题时,认为屈子《离骚》之前,中华古代关于哲学、美学与诗学的时间概念与观念并未正式登上历史,人文舞台。
考虑到前述比如《庄子》关于生命时间问题的有关阐说与觉悟这一点,此见未确是可以肯定的。
比较而言,通行本《周易》的“时”意识,主要是在原始巫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
首先,整部《周易》六十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以及乾“用九”、坤“用六”两条文辞,大凡都是巫筮记录。
本经作为“占筮之书”,通篇讲的是吉凶休咎、趋吉避凶,讲人的命运。
这实际上是讲一个字,即命理意义的“时”。
所谓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之类,都应在这个“时”字上。
正如魏王弼《周易略例》云:
“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
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
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
” 其次,这种巫筮、命理的“时”意识,浸透于《周易》卦爻筮符系统之中。
简约地说,《周易》象数即筮符系统是一种中华古代典型的“时”结构。
第一,从每卦六爻爻位之动态分析,从初、二、三、四、五到上位,是一时间运变历程,从上经第一乾卦、下经第一咸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演化,尤可以得到确切而有力的证明。
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到上九“亢龙,有悔”、咸卦从初六“咸其拇”到上六“咸其辅颊舌”之爻位的上升,来象喻人之命运吉凶互变的运化过程。
第二,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均由下、上两个八卦所构成,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的方位,都以空间位置的变动来象示时间的变化。
比如“后天八卦”的方位,坎卦为北为水为冬,阴气极盛而衰,阳气始生之时;震卦为东为木为春,阳气渐长之时;离卦为南为火为夏,阳气极盛而衰,阴气始生之时;兑卦为西为金为秋,阴气渐长之时。
这后天(文王)八卦方位的四正卦,是自然四时运行的卦筮模式,而其四隅卦即东北艮、东南巽、西南坤与西北乾,都喻示相应时位的过渡。
第三,六十四卦每卦以二、五爻位为中位。
如果某卦阴爻居于第二爻位或阳爻居于第五爻位、因阴遇偶位、阳遇奇位,便是“得中”(“得正”)之爻,往往为吉。
如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讼卦九五“讼,元吉”等爻,都是“得中”、吉利之爻,这在《周易》巫筮文化学上,称为“时中”,即“中”得其“时”。
当然,有些卦的爻符,虽并非“得中”,而筮符也往往“吉利”,如睽卦九二之阳爻居阴、解卦六五之阴爻居阳,由于两者分别处于下卦、上卦之中位,而其巫筮结果为“吉”。
第四,从十二消息卦来分析,以十二卦分主一年四时十二月,象征阴消阳息、阳息阴消、盛衰互变,周而复始的“时”之运化:
这十二消息卦从复卦一阳始息于下、临卦二阳息、泰卦三阳息、大壮卦四阳息、夫卦五阳息、乾卦六阳息到骺卦一阴始消于下、涯卦二阴消、否卦三阴消、观卦四阴消、剥卦五阴消、坤卦六阴消,以及坤卦之后,一切又从复卦开始,是巫文化意义上的循环往复、四时更迭,体现出古人与原始天文、历算文化相联系的“时”意识。
总之,正如王弼《周易略例》所言:
“夫卦者,时也。
爻者,适时之变者也。
”此乃深谙易理真谛之论。
无疑,易理之原始、本在的人文意义,在乎“命运”。
命者,令也,上天、先天之指令,命乃先天所定。
就人之个体生命而言,其所属种族、民族、时代、家族、基因、性别、血型、肤色、长相等等,都是前定的,早在其父母结合之“时”已被决定。
这便是所谓“命里注定”。
运指后天,指人之后天所遭遇、创造的种种机会、机缘。
后天的人生经历、习得、修养、道路,是在先天“命”之基础上的人生运化与运作。
无论先天的“命”,还是后天的“运”,都是一个“时”问题。
从时间文化学角度分析,人类之“命”即先天时间、自然时间、物理时间;人类之“运”,指与“命”相对应的后天时间、人文时间、心理时间。
先天、自然与物理时间本身运化无穷,是“绝对权威”。
人类的无穷认识与实践活动,可以改变空间意义上的一切存在,但人类决不可能改变先天、自然与物理时间于一丝一毫。
宇宙间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摧毁这种时间及其运行。
《阿闼婆吠陀》有云:
“时间征服了世界。
它上升着,成了至尊之神。
”时间是“上帝”。
这当然不等于说,人类在这“上帝”面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
这种先天时间的“绝对”,恰恰为人类提供了实现无限之后天、人文与心理时间的“场”(field),人类对其自身及其世界的改造,是先天、自然、物理即“上帝”时间的现实实现。
人类可以将先天、自然与物理时间思性兼诗性地“带上前来”,使其“当下”即“是”。
这便是笔者关于人类之“命”、“运”关系的基本理解。
这里,“命”,可称为神性时间;“运”,则指人性时间。
《周易》巫筮文化的时间意识,处于神、人即神性时间与人性时间之际,笔者将其称为巫性时间。
作为在神、人之际所发生、进行的一场文化“对话”方式,巫性时间观具有五大文化要素。
(一)人类所面临的自然难题总是无以彻底解决,人类永远无力克服、超越先天、自然、物理时间的“绝对”,这也便是前述所谓“命里注定”。
(二)人类在崇拜“命”即神性时间的前提下,同时自我崇拜人自身的“灵力”而相信自己可以在“巫”文化领域解决自然与社会的一切难题。
(三)迷信于神人、物我、物物之际的神秘感应,此即“巫”意义上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亦即《周易》所谓的“气”与“咸”(感)。
(四)尽管《周易》巫筮文化的逻辑原点,是处于神、人之际的巫性时间,然而其文化目的却指望、落实于人性时间即人之世俗理想,是神秘地借助所谓神灵、神力以达到人的目的,因而其文化品格是“降神”而非“拜神”,这也便是巫术文化与宗教文化之品格的区别。
(五)《周易》巫筮文化作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谓“伪技艺”,作为一种笔者所言“倒错的实践”,却在非理性文化的阴影之下,显示出“实用理性”、“前理性”、“前科学”、“潜主体”的一点人文觉悟与灵明。
巫性时间的文化精神,半是天意半是人力;半是糊涂半是清醒; 半是崇拜半是审美。
“知几”:
“时间”地提问 问题不仅在于《周易》筮符、文辞系统即卦爻符号、卦爻辞如此精彩地表喻人类命运即巫性时间的人文真谛,而且重要的是,《周易》象数及其筮辞,还是中华古人关于时间、关于时间哲思的一种提问方式。
所谓“时”意识,不仅指时间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人文思维意义上,是“时间”地怀疑、思考与体悟人及其世界.一种“时间优先”地看待与处理世界的理念与方法。
作为西方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称现象学“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这里,暂且搁置“作为方法的现象学”与“作为哲学的现象学”两种含义的同异及其联系这一烦难问题,仅就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而言,它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人文“视域”与“思维态度”。
面对人自身及其世界,当古希腊的哲人主要从“物质”、从“原子”思考问题,认为“‘存在’着的东西,它唯一的性质就是占据空间”之时,古代东方的“圣贤”却极富智慧地以《周易》六十四卦这一巫筮符号系统,占验人事吉凶,叩问时间问题的历史、人文之门。
正如前文所一再引述的,《易传》所谓“随时之义大矣哉”,“险之时用大矣哉”等等所论述的“大”,甲骨文写作“穴”(一期“合集”一二七○四、一九七七三)。
此“大”之本义,《说文》云,“故大像人形”。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说,“像人正立之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称,“古汉字用成年男子的图形‘ 表示(大)”。
古人以为,“成年男子”是人的生命之“根”,故“大”像“成年男子”这一本义,后来就转义为哲学意义上的“本原”、“本始”《易传》“大哉乾元”之“大”,亦具此义。
因而,《易传》屡次所述说的卦之“时义”、“时用”、“大矣哉”的“大”,有本原、本始的哲理意义.这可以看作《易传》对时间哲理之本涵的一种追问。
那么,这种追问有些什么特点?
其一,现象学所谓“现象”,某种意义上指心灵属性即人的内在“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意向性”循“象”的“显现”。
这立刻使笔者联想到《易传》关于“象”的那个著名命题:
“见乃谓之象”。
这里,见,现也。
此“象”是“见”(现)于“心”的。
它直接便是心灵即“意向”本身。
因此,尽管在言词表达上,《易传》言“象”而不言“意象”,而作为这两个词所指涉的心灵现实,其实是一样的,象即意象;意象即象。
无意之象,无象之意,都是不可设想的。
因此,也可以将“意象”(象)称之为“现象”。
其二,象、意象与“意向性”的“意向”作为“时间”,作为“存在”是否可能?
当亨利·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称人的心灵意识即对实在的体验即“延展性”(Duration),是一种“真正的时间”之时,则意味着西方哲学开启了时间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柏格森从人的心灵意识的“延展性”,即从心灵意识运动的“延展”这一“现象”,用似乎有些“怪异”、却是深邃的目光,找到了一种“看世界”的方法。
这让世人兴奋与惊讶不已。
可是这种类似于“意向性”说的“象”的内在运演与理论建构,早在中华古代,大致经过从殷、周到战国这漫长岁月,就被充分地关注与思考。
“象”是体现于《周易》文本之独异的中华文化及其思维的“原素”。
它在原始巫筮文化中,是一种属于巫性时间的心灵迷氛;在尔后的史文化即中华政治教化及其人生哲理文化中,又体现为人性时间的“实用理性”。
两者共同的人文基元,因其所关注的并非构成世界之“物质”本身(空间),而是自然与人文、社会无数人事之间的动态联系即大化流行(变),所以,时间作为基元,无可逃避、无可选择。
易者,时也。
易即时。
时乃易之魂。
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古今中外的巫术文化种类数不胜数,惟有中华古代的《周易》巫筮,才能转嬗、成长为以哲理、伦理为主的史文化,作为人文时间、心理时间,发现、建构了一种“看世界”的恒新的人文视域。
易象及其人文转嬗与柏格森的“意向性结构”相类、相通,“它显现并展示了时间性的存在”。
其三,这种时间性即“意向性”,即人之意识运动的时间矢性,被柏格森时间哲学观的后继者与发扬者海德格尔称之为:
“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
”人类所经历、正在经历与必将经历的时间历程,从不间断,是一个“曾在”、“当前”(当下)与“将来”三维“统一”的矢性时间。
“曾在”,过去了的“当前”与“将来”,它已经不“在”;“将来”,必将实现为“当前”、且必以“曾在”为归宿;而“当前”,仅是由“将来”转化为“曾在”的一个瞬间。
它瞬息万变.借用佛学的话来说,叫做“刹那生灭”。
这“当前”,在历史学意义上可以设定与度量,指某一时段;在时间哲学意义上,它不可度量。
用庄子之言,可称为“倏、忽”而已.如“白驹过隙”。
它实际指处于“曾在”与“将来”之间的一种契机。
人是一种善于瞻前、顾后的“文化动物”。
瞻前者,向往也、理想也;顾后者,回忆也、回归于传统也。
以为只要将“曾在”、“将来”攥在手里,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人总是“慢待”“当前”,总是对“当前”忘乎所以。
这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叫做“时间遗忘”。
笔者将这种“时间遗忘”,称之为无可救药的“人性的弱点”。
然而就时间哲学而言,无论对“曾在”的回忆与留恋,还是对“将来”的向往与憧憬,两者都在“当下”“照面”,这便是所谓“时间到‘时’”。
“曾在”与“将来”,因来到“当下”即“到‘时’”而“存在”。
这种“存在”,作为具有“弱点”之“人性”显现的人性时间,恰恰是不完美、不圆满的,否则,便是神性时间了。
这种瞻前、顾后的时间观,在《周易》中表现得很是鲜明,人们可以从《易传》所言诸如“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以及“小往大来”、“大往小来”等论述中理解一二。
其四,既然知“来”、察“往”的《周易》巫筮使“时间到‘时”’,那么再次“登场”的,便是“此在”。
我们不能说“此在”的意思是“存在”于“此”,而是“此在”“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是’的那个存在。
”“有待去‘是’”’,即“当下”“在场”或再度“出场”,这是现象学、时间哲学思想的关捩点。
《周易》巫筮的人文思维与思想,同样尤为注重于“当下”时间。
全部巫筮操作即所谓“十八变”、“作法”的关键,是通过“大衍之数”的运演(算卦),唤醒吉兆、凶兆于“当下”。
这里所谓“兆”,稍纵即逝,它便是时间历程之中的“当下”。
这便是《易传》所谓“见”(现)、所谓“ ”,从而依所“见”之“ ”,来推断人事吉凶,察往知来。
《易传》有云,“知畿,其神乎”。
又说,“唯畿也,故能成天下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