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结婚.docx
《傻瓜结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傻瓜结婚.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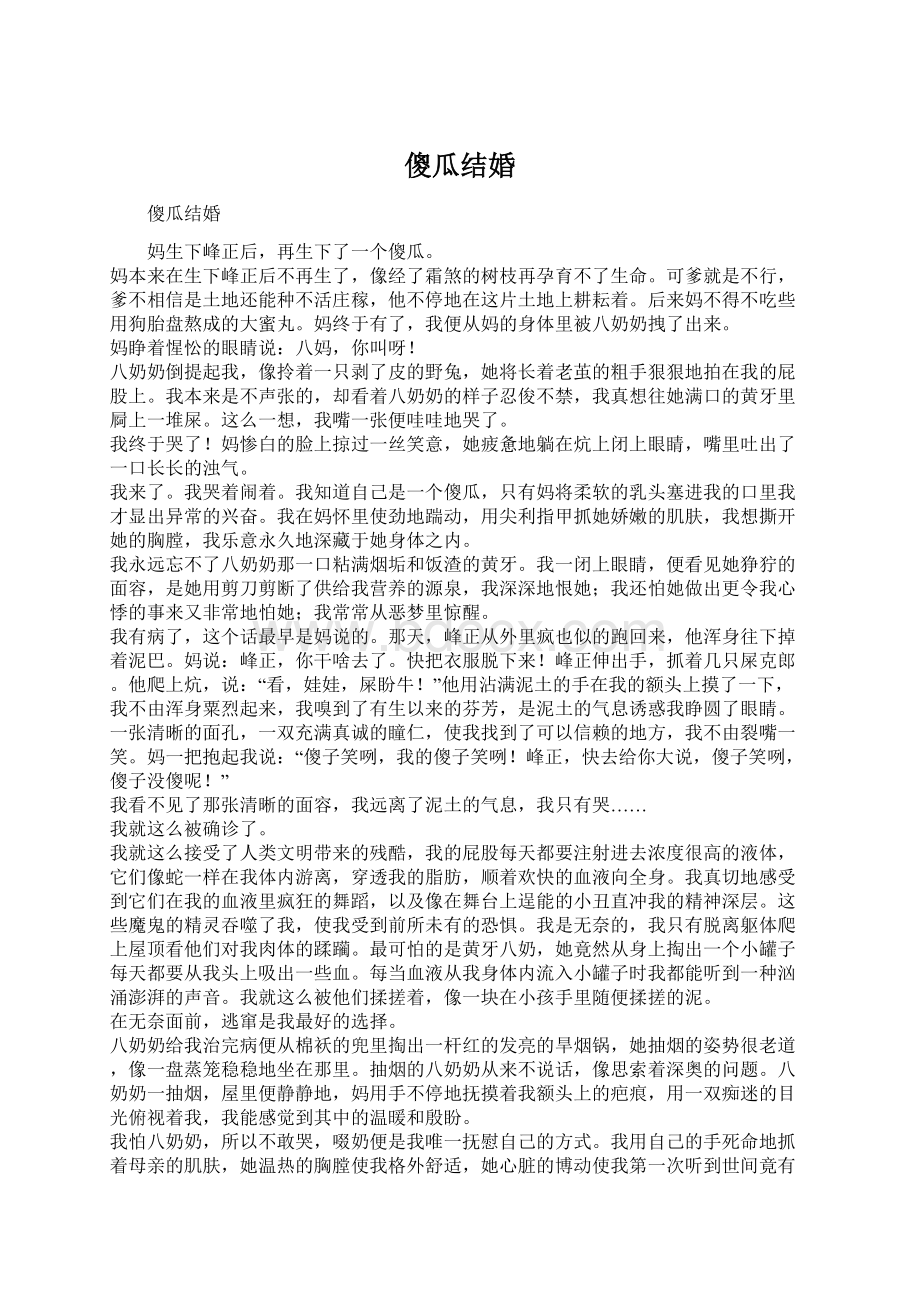
傻瓜结婚
傻瓜结婚
妈生下峰正后,再生下了一个傻瓜。
妈本来在生下峰正后不再生了,像经了霜煞的树枝再孕育不了生命。
可爹就是不行,爹不相信是土地还能种不活庄稼,他不停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着。
后来妈不得不吃些用狗胎盘熬成的大蜜丸。
妈终于有了,我便从妈的身体里被八奶奶拽了出来。
妈睁着惺忪的眼睛说:
八妈,你叫呀!
八奶奶倒提起我,像拎着一只剥了皮的野兔,她将长着老茧的粗手狠狠地拍在我的屁股上。
我本来是不声张的,却看着八奶奶的样子忍俊不禁,我真想往她满口的黄牙里屙上一堆屎。
这么一想,我嘴一张便哇哇地哭了。
我终于哭了!
妈惨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她疲惫地躺在炕上闭上眼睛,嘴里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浊气。
我来了。
我哭着闹着。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傻瓜,只有妈将柔软的乳头塞进我的口里我才显出异常的兴奋。
我在妈怀里使劲地踹动,用尖利指甲抓她娇嫩的肌肤,我想撕开她的胸膛,我乐意永久地深藏于她身体之内。
我永远忘不了八奶奶那一口粘满烟垢和饭渣的黄牙。
我一闭上眼睛,便看见她狰狞的面容,是她用剪刀剪断了供给我营养的源泉,我深深地恨她;我还怕她做出更令我心悸的事来又非常地怕她;我常常从恶梦里惊醒。
我有病了,这个话最早是妈说的。
那天,峰正从外里疯也似的跑回来,他浑身往下掉着泥巴。
妈说:
峰正,你干啥去了。
快把衣服脱下来!
峰正伸出手,抓着几只屎克郎。
他爬上炕,说:
“看,娃娃,屎盼牛!
”他用沾满泥土的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一下,我不由浑身粟烈起来,我嗅到了有生以来的芬芳,是泥土的气息诱惑我睁圆了眼睛。
一张清晰的面孔,一双充满真诚的瞳仁,使我找到了可以信赖的地方,我不由裂嘴一笑。
妈一把抱起我说:
“傻子笑咧,我的傻子笑咧!
峰正,快去给你大说,傻子笑咧,傻子没傻呢!
”
我看不见了那张清晰的面容,我远离了泥土的气息,我只有哭……
我就这么被确诊了。
我就这么接受了人类文明带来的残酷,我的屁股每天都要注射进去浓度很高的液体,它们像蛇一样在我体内游离,穿透我的脂肪,顺着欢快的血液向全身。
我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在我的血液里疯狂的舞蹈,以及像在舞台上逞能的小丑直冲我的精神深层。
这些魔鬼的精灵吞噬了我,使我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是无奈的,我只有脱离躯体爬上屋顶看他们对我肉体的蹂躏。
最可怕的是黄牙八奶,她竟然从身上掏出一个小罐子每天都要从我头上吸出一些血。
每当血液从我身体内流入小罐子时我都能听到一种汹涌澎湃的声音。
我就这么被他们揉搓着,像一块在小孩手里随便揉搓的泥。
在无奈面前,逃窜是我最好的选择。
八奶奶给我治完病便从棉袄的兜里掏出一杆红的发亮的旱烟锅,她抽烟的姿势很老道,像一盘蒸笼稳稳地坐在那里。
抽烟的八奶奶从来不说话,像思索着深奥的问题。
八奶奶一抽烟,屋里便静静地,妈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额头上的疤痕,用一双痴迷的目光俯视着我,我能感觉到其中的温暖和殷盼。
我怕八奶奶,所以不敢哭,啜奶便是我唯一抚慰自己的方式。
我用自己的手死命地抓着母亲的肌肤,她温热的胸膛使我格外舒适,她心脏的博动使我第一次听到世间竟有这么欢快的音乐。
八奶奶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有一天我看见八奶奶不再抽烟了,手里的拐杖代替了她的旱烟锅。
她坐在炕头上,用一束浑浊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听到她喉咙里微弱的气息正做最后的挣扎。
她忽然伸出自己满是褶皱的手在我头上轻轻摩搓,一滴冰凉的眼泪滴在我的嘴唇上,咸咸的,一股泥土气息涌灌了我的全身。
八奶奶不再可怕了,她只能用自己的舌头舐着脱完牙齿的牙床。
八奶奶走了,她给了我勇气后走了。
二
八奶奶走的那天我忽然站了起来。
我站起来那一刻妈正跪在地上的枯草中哭八奶奶,她们十几个女人嚎啕大哭。
我正爬在草上打滚,这忽出其来的一片哭声使我浑身一震,我急忙抓住妈的衣襟。
这一抓,我就从地上站立了起来。
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妈声音里倏忽闪过了一丝颤动,她一把拉过我的双手,能使我更好的站直自己的身体。
我再没有听到她的哭声,豆大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那泪珠都闪烁着银色光芒。
她抱着我回了家。
她拖着我的双手让我在炕上走个够。
她一会儿拉着我的左手,一会儿又拉着我的右手,有时把我的双手撑了开来让我像鸟一样去飞翔。
我扑倒在炕上她便使劲地喊:
起来!
她一会儿笑着,一会儿哭着,一会儿仰卧在炕上抖我的双手。
她的眼睛始终湿润着,她的眼角始终闪着晶莹的泪光。
八奶奶在我眼前的消失使我终于将地球踩到了脚下。
我迅猛地健全自己的骨骼和肉体,半夜我听到自己的躯体在豁然作响,好多次我都从悬崖里坠落下来,空中的惊惧和恐慌常常把我从恶梦中推醒。
我摸着自己额头的汗珠,听见妈帮我从地上捡起掉下去的枕头,我感受到自己躯体一天天变的僵硬。
有一种液体在我身体内不停地冲撞着,我努力使自己平静。
有时候我不得不在门前的小路上、草丛里、河岸边奔跑,我常常捡起一块土坷垃,使劲甩向觅食的鸟群,它们振翅高飞,在蓝天下白云间我不停寻找它们掠过的身影。
我最爱在苜蓿地里与峰正追逐,他总能抓几只翕动着翅膀的蝴蝶。
蝴蝶身上美丽的花纹让我俩不能扼止自己对于捕捉它们的欲望。
有时,峰正拉过我,让我和他一起躺在苜蓿地里潮湿的泥土上,我喜欢泥土的腥味,他总是抓一把土往我的脖子里灌,土粒贴着我的肌肤滑过我的胸膛、小腹、小鸡鸡,顺着我的腿落在地上。
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土地里早冒出来的一样,我也变成一株苜宿花在田地里张望。
在清爽的阳光下,我在风中轻轻摇摆。
后来我妈便教我说话。
我妈说:
叫妈。
妈!
我妈说:
叫大。
大!
我妈说:
你要学会叫哥哥呀!
哥哥!
我又看见我妈眼里闪动的泪花,可我妈不再把我抱在怀里,她最多只摸摸我的头。
我妈摸我头时很轻,像抚顺我头上粘满泥垢的头发。
她抚摸过我头后总说:
唤唤,去玩吧。
我就这么叫唤唤。
我先叫妈,后叫大,再叫哥哥,我就这么学会了说话。
然而我不喜欢说话,因为说话很费劲。
我一说话他们都竖起耳朵在听,他们的专注使我变得非常尴尬,特别是他们都把目光集中于我,我的身体便似乎夹在崖洼的缝隙之中,我的呼吸显得异常困难,我便紧张,我的心似乎被他们分别拉向四面八方,所以我不说话。
但峰正例外,他抓住一个蝴蝶一只地钻牛总要拿给我,他用小线绳系住它们的小爪子让我牵着,他只看在惊恐中逃命的小东西,从不痴痴地看我,我便在他面前说话,和他一起大喊大叫。
峰正总能带给我一些新鲜,总能让我感受到我们村庄竟然这么大。
峰正说:
我们去河里抓癞呱子吧!
我总觉得自己成了峰正小小的尾巴。
他喜欢在太阳光下脱个精溜子,将汗衫提在手里向河边奔去,我便跟在后面看个稀奇。
峰正说:
悄悄,你不悄悄癞呱子吃你呢!
峰正钻进水里,后腿一蹬一蹬。
我也脱光了衣服钻进了水里。
我看见清清的水面荡开一
圈圈波纹,像风吹过的苜蓿地时飘来的花香。
我闭上眼睛躺在河水之中,我又回到了我妈的怀里,我整个儿躯体向塞进了早晨的太阳之中。
我的双腿在水里轻轻摆动,似乎一丝丝一缕缕充实包围了我的躯体。
我在水里慢慢游动。
我俯下身子,用两手摁着河底的淤泥。
我又嗅到了曾经的乳香我又重新投入了我妈的胸膛。
在水里我突然浑身没有了感觉,我整个儿地融化了,像做了一场轻盈的梦。
我听见水流骤然撕裂的声音。
我看见一个人影在岸对面恍动。
峰正从水里一把拎出了我,他眼里流出从来没有过的惊恐,他像一只受了惊吓的鸟拽着我撒腿就跑。
我回过头,我看见自己汗衫在岸边的水草上轻轻地飘。
我说:
汗衫!
汗衫是啥,老回回来咧!
我说:
啥是个老回回?
和癞呱子一样,吃人呢!
三
我要跟着峰正去学校了。
大说:
瓜子念个啥书?
念些书人就灵咧!
妈说。
我妈给了我一个花书包。
我妈给我花书包时将书包挎在我的肩膀上,她顺手捋了捋我的衣服说:
还像!
我感觉我妈远离了我,她似乎越来越像八奶奶。
她在我面前很少说话,有时看见我的表情还不如看见我们院子拴着的那只大白狗。
我妈在家里只剩下我和她时她宁肯去和大白狗说话也不和我说话。
我妈说:
大白狗啊,你咋知道摇尾巴呢?
我家的大白狗一见我妈便跳起来用爪子抓脖子上的绳,看见我妈手里的脸盆,就在地上跳舞。
它懂得我妈说话的意思,而我不懂。
我知道我妈和大白狗说话时她心里很难过。
其实我看到我妈对大白狗热情时心里也很难过。
我问自己:
我怎么连狗都不如呢?
连狗都不如呢?
我妈说过书念上些就灵咧!
我这个傻子便拼命念书。
老师说:
春风吹,天气暖……我便说:
春风吹,天气暖……
在家里我妈说:
你学了个啥?
我说:
春风吹天气暖!
在哪达呢?
我说:
在老师嘴里呢!
瓜子!
在书上呢!
我妈一直纠正着我,特别是她看不见大白狗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她心里不难过的时候。
我妈心里不难过的时候我心里更难过。
我总认为我妈把我当成了院子里的大白狗,而我却不如拴着绳子的大白狗。
我心里难过时我便念书,我念:
春风吹,天气暖……我心里就很舒坦。
在学校我知道了手除了能搓绳、端盆、拴狗还能用来写字。
可我就是不会写字。
不会写字就得人教。
老师说:
妮子,你去教他吧!
就这么我靠近妮子。
妮子手把手教我。
她爬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划:
春—
妮子的手和我的手在我的作业本上乱七八糟涂些铅笔的墨痕。
她的一声声发音,是一口口热气吹进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胀胀的,像灌满了声音痒痒的。
妮子没有什么气息,虽然她那么紧的靠近我,虽然我拼命的感觉着。
然而妮子却让我信赖让我勤奋学习,因为妮子从不骂我。
学校里的同学都叫我瓜唤唤愣唤唤。
妮子从来不这么叫还说;唤唤最听话,我妈说老实才可靠呢。
于是在学校里我为妮子而活着。
我按她的要求拼命地学习,拼命地学着说话。
我总希望拿出最好的东西给她。
而我最好的只有油馍馍。
我一直等着我妈给我做油馍馍。
我妈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做油馍馍,我只有盼着,盼着。
妮子成了班长。
成了班长的妮子常常站在讲台上说话,我看见妮子忽然长高了一截。
妮子说话时薛子太就起哄。
薛子太起哄时便喊:
妮子,你妈个鸡巴。
妮子便与薛子太在一起厮打。
妮子说我要告老师,薛子太便耷拉下头不再骂她。
这时候我看见妮子走上讲台,她扭过头瞪了薛子太一眼。
薛子太埋下头边念书边说:
我要考过你我要当班长,你以为你比谁尿的高,你以为你本事有多大……
妮子与薛子太较上了劲。
他们俩凡事都比,我为妮子捏着一把汗。
妮子说薛子太骂我,他老说我没有他尿的高。
妮子中午教完我的课文这么给我说。
我说:
薛子太骂你我揙他,他说你没有他尿的高我就给你教。
我们来到麦地里。
麦子长的很高,我俩藏在麦地里的阳光下。
我记起了我妈给我烙的油馍馍。
我怎么出来时忘了拿,我想着盼着等我妈给我烙了油馍馍,我怎么就忘了拿给妮子呢?
我说:
妮子,我忘了给你拿油馍馍。
我妈说我不能吃汉民馍馍。
妮子睁着睛睛看我,我看见妮子眼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我,那个我躲在一片麦地里,麦子都垂下了头。
麦子长势很高。
我和妮子在起伏的麦浪里潜藏,真的我很紧张。
我和薛子太比过谁尿的高,和全班都比过,可我不怕。
现在我怕了。
我为什么在妮子面前怕了呢?
我暗暗地给自己使劲,我努力使自己镇静,然而我心里软软的,我尿不胀,可不争气的是我的尿道松松的,我的尿尿在向外款款的流。
我看了一眼妮子,妮子正在用无知的目光也看着我。
她的牙正咬在自己的下嘴唇上。
她是否和我一样,正在努力使劲憋着?
我不知道。
我揪了几个麦穗放在手掌里一搓,饱满的麦粒在我手掌里滚动。
好大的麦颗子呀!
妮子惊叹了。
我看见了妮子脸上荡漾着喜悦,她从我手里拿了去,她把麦颗子放在嘴里嚼。
我重新揪了一些麦穗放在手里搓。
妮子从我手里又拿去了一粒放在手掌里。
她怎么拿了一粒呢?
我看见那麦颗子在她手掌了滚动了三下停了下来,那是一个丰满的裂着缝隙的麦颗子。
你说麦颗子是几个?
妮子眨了一下眼睛。
当然是一个!
不,是两个!
你看是连在一起的圆圆的两个。
我没有反驳,我不会反驳。
我浑身的肌肉这时候绷紧了。
我对妮子说,我们来吧!
我对妮子说:
其实很简单,你捏住头头,一使劲一松,就尿高了。
我说:
你脱吧!
妮子说:
有人吗?
我说:
没有!
妮子说:
我羞。
你把眼睛闭上就不羞了。
风轻轻地吹动了麦地。
一只蚂蚁从我脚后跟爬上去在我的脊椎骨里游走。
我剥开了妮子,我像剥洋芋一样剥开了妮子。
我看见妮子大腿的肌肉在轻轻的抖动。
我用手碰了一下她的那儿。
我惊诧了!
。
我说:
咋不像,昨不像……。
不像啥?
妮子闭着眼睛,声音似乎从麦地深处传了出来。
咋不像我的……是一个,咋像个麦颗子……是两个……
四
我妈推开了我,她彻底的推开了我。
她说去那屋和峰正睡吧,你哥回来咧。
峰正坐在地上,我只好蹴在他的身旁。
我现在不敢说话,一张嘴就挨上我妈的巴掌。
她说,越长越个愣松咧,不会说话就不咧说。
我却控制不了自己,便一直挨我妈的巴掌。
她一伸手,我腮帮子就响上一下。
我大坐在炕沿上,抽着峰正带回的纸烟。
平时我大只抽旱烟,遇上有人给他递纸烟,他忙跪起来推辞:
旱烟习惯!
旱烟习惯!
现在我大抽纸烟不说旱烟习惯。
他狠狠地吸上一口,似乎吸到了脚后跟上,吐出来只剩淡淡的一丝雾气。
回来咧就去你二大、三大家看看。
我大给峰正说。
峰正走了。
我大继续抽烟。
他拿着烟对我妈说:
现在国家能的很,给女人尻子上垫卫生纸也给烟尻子上垫上了卫生纸。
我大对着纸烟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傻笑。
妈打了大一条帚说:
你嘴里胡骚个啥呢!
我说:
女人尻子上咋垫卫生纸着呢?
妈便跑过打我。
她一巴掌甩在我脸上,又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瓜子嘴烫的啥!
瓜子嘴里胡烫的啥……
一股热热的东西从我嘴里流出来,我用手紧紧捂着。
大吼着:
女人尻子上淌血着呢!
大很少发火,但家里的人都怕大,包括我妈。
大一吼妈便坐在凳子上不吱声。
但我不怕大,大从来不打我,也从来不骂,只有时对着我一声不吭,吧嗒吧嗒的抽烟,像一头反刍的老牛。
我看见妈放在炕头的卫生纸,我摸了摸嘴角流下来的血,我拿了一张,垫在我的嘴上。
妈走了过来。
我听见了妈的脚步声从她坐的那儿向我走来。
我脊梁里凉凉的,我的脸在粟烈。
我怕妈,我怕妈有时候出我意料的巴掌甩过来。
妈把我拉了个转身,抽掉了我垫在嘴角的卫生纸,她给我递了条毛条。
我看见她眼睛里亮亮地滚出了两滴眼泪,我听到她喉头里一丝轻微的叹息。
妈说:
咋给我施了瓜子,老天咋给我施了瓜子——唉!
……女人的血脏用卫生纸,你嘴里的血用毛巾!
我接过妈递给我的毛巾,心里一下陡然一动,鼻子便酸酸,一滴眼泪从我胀胀的眼眶里流了下来。
我不爱哭泣。
因为我从没见过我大流泪。
我是我大的儿所以我也不哭泣。
然而在我妈给我递毛巾时我却流下了眼泪。
我确实不想哭,但不争气的眼泪却流了下来。
现在我的脸不疼了,我却流下了眼泪。
人的眼泪啊怪怪的。
峰正从门外走了进来。
峰正说你咋咧。
我不敢看峰正,我的脸烧的厉害。
喂,流血了,嘴咋咧?
峰正捏了一张卫生纸递过来,但我却不敢接。
峰正拉着我去睡觉。
峰正总是很了解我,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离开大和妈的屋子,我的心情一下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峰正在屋里不睡觉,却看照片。
我也爬在他的旁边,看他一张一张地翻。
有些像片他也看背面,背面写着字。
我认出一些,但大部分还是看不懂。
有一张照片,他反过来覆过去的看。
那是一张双人照片,是峰正和一个女生照的。
在一个城市的花园里,花园里有多彩的灯光,还有喷泉,泉水的颜色是黄红绿相间。
我拿过来细看,那个女子是山秀,竟然是山秀——妮子的姐姐。
峰正和她坐在花园的栏杆上,山秀在前,峰正在后,山秀的腿向前伸着,峰正在她身后蹲着,峰正将双手搭在山秀的肩上。
他们俩的目光都在看我,都露着甜甜的笑。
我心里舒坦极了,也对着他们笑,峰正和山秀在一起真的很好看,他们笑的那样真切,那样的令人心里感到温暖。
我傻傻地看着,似乎听见峰正和山秀给我说着什么,却听不清,好像什么都说,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别傻看了,毕业时随便照的,峰正说。
我问:
什么是毕业?
哦……就是离开学校吧,我现在不去学校了,就是毕了业。
比如你再有一年便不去现在的学校了,就是小学毕业了。
峰正又给我解释了一遍。
可我就是听不明白。
我干吗要毕业呢?
我要一直在学校,我毕业了妮子毕业了,我到哪儿见她去。
短短的假期使我对妮子望眼欲穿。
我记起了在下午想妮子时,去了河边,妮子的家就在河的那边。
我知道她有时也会来河边洗衣服,可我怎么就一直没有碰到过呢?
但到了河边,我就忘了妮子。
我看见河水清清地流向远方,我想它们去了哪里,那河上飘的树叶草根都走向了哪里,我就跟着它跑,可走了很远很远它们还一直在流,我不敢去了。
就又回来。
我便躺在河岸的草上地上听河水哗哗的流。
有时它们像敲锣有时像打鼓,更多时我感觉有一群精灵在河水里嬉戏,一起在欢歌。
我就是这样爱小河,我一想妮子就想起了小河……
快去睡吧!
峰正看着发呆的我说。
我很听峰正的话,可我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
屋里的灯光映在峰正红膛膛的脸上,他一直爬在桌子上写着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我梦见了峰正和山秀的那张像片,只是我也在里面。
我看着他俩冲着我笑,跟我说了许多话,那话是用心说的。
忽然他俩身后的花园变成了一块苜蓿地,苜蓿长的很高,在墨绿的枝上挑着猩红的花,我在苜蓿地边追逐着,可我一下了找不到了他们俩,我心里非常紧张。
在他俩坐过的地方却盘着两条巨蛇。
有一只蛇的眼睛特别明亮。
我心里喊:
它不是峰正变的,不是峰正变的。
我又觉得峰正和山秀已经被它们吃掉了。
我这么一想,那蛇就向我扑了过来,张开了血盆大口,它的牙齿像竖着刀尖……峰正—峰正—我使劲喊……
我摸了摸,峰正在炕上,他的手很热,他没有被我的喊声惊醒,只习惯地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五
我的梦应验了。
那天,我们家来了许多人。
从不出家的长胡子五爷和九爷也来了,坐在炕上抽旱烟。
几个与大平辈的伯伯叔叔都来了。
他们都不说话,他们似乎一个个成了哑巴。
我看着峰正,他坐在门槛上,将头勾的很低。
我觉得整个屋子里阴森森的,大家都变成泥人。
我站在九爷身后的炕沿边,我的腿在发抖,我真的有些怕,
妈端来了饭。
大先给五爷端了一碗。
五爷说我不吃,我吃咧。
五爷不吃饭,大家都不端碗。
五爷又装了一锅烟,他把烟嘴用脱的没几个牙的牙齿咬住,一滴口水滴到了炕上。
九爷从他手里接过了旱烟锅,说:
吃一点吧!
少吃一点,你不吃娃娃们都不吃。
五爷用眼睛扫了一眼峰正,那眼光是一束令人发悸寒气。
他接过了我大重新捧给他的碗,用眼睛瞧了瞧碗里饭,说:
我吃不了这么多!
吃不了这么多!
九爷说:
吃着看吧,吃着看吧。
九爷边说边给五爷碗里调盐。
送走了五爷他们,大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大站在地上耷拉下脸,他看着我妈的眼睛,半晌,他忽然吼:
峰正呢?
峰正不见了。
天已经黑了,峰正去了哪儿?
妈一把拽过我,说:
唤唤,快走!
妈把我的手抓的生疼。
我没想到她的劲儿这么大。
我和妈在河岸上奔跑。
妈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我没有惊恐,我只有好奇。
和我俩一起跑的还有脱了绳的大白狗,它的尾巴在月光下随着跳跃的身体晃动,它欢快的样子就像与我和妈做游戏。
我妈拉住了我。
我俩和大白狗站在了河边,我听见了河水哗哗的流,我又想到水面上的落叶要飘到哪里,这流水声总让我沉迷。
在我俩前面就是一块苜蓿地,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的清晰,却又笼罩着一层神秘。
随着清风吹来,我闻到了苜蓿的花香和苜蓿草的气息。
一块苜蓿地,就这块平时熟视无睹的苜蓿地,在夜色下使我感到陌生。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它就是出现在我梦里的苜蓿地。
峰正在里面?
山秀在里面?
他们是不是像照片里的那样坐在一起?
我努力回忆着那个可怕的梦。
妈站在河边说你悄悄去,悄悄……
我顺着苜蓿地的边缘走了过去,我对苜蓿地很熟悉,但我努力回忆着那个梦,希望想起他俩在梦中相拥而坐的地方。
夜风吹着我的脸,大白狗跟在我的身边。
一株一株的苜蓿在风中摇曳着,我心里面白茫茫的一片。
我首先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唏嘘声,从深深的苜蓿地里传来。
我猫下了腰,我扭了一下头,我的右耳忽然伸长了,我仔细听着他们说话。
这会儿我已经听清了有一个男的是峰正,那女的肯定是山秀。
我遵循着自己的梦。
我很紧张,我躲进了苜蓿地。
谁?
峰正从苜蓿地里站了起来,我看不见他的面孔,但他的声音太像我大的声音。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我是不是该站起来了。
我都要快站起来了,但好像有一只手按着我的肩膀让我蹲下。
我听见大白狗吱吱地叫了一声,峰正俯下声。
他把大白狗的头抱在了怀里。
我听大白狗又吱吱的叫了两声。
山秀也从苜蓿站了起来,她还用手拍了拍身上的土。
他们是要走了,他俩要回去了?
峰正放下了大白狗和山秀向前走。
他俩又坐了下来。
我透过苜蓿的缝隙,我借助皎洁的月光,看见山秀像大白狗那样扑向了峰正,峰正也像抱大白狗那样抱住山秀。
我浑身火一样烫,我窒息的要命。
更可怕的是一株苜蓿花在我眼前一摆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只听到他俩沉重的喘息声。
我揉了揉眼睛,我重新看见了他们。
峰正抱着山秀从我的眼睛里倒了下去,倒了下去……我再看不见他们,只看见了一大片苜蓿也随着倒了下去,我听到它们的枝杆在痛苦的呻吟……
我从苜蓿地里溜了出来拼命往家跑。
大白狗也好像灼伤了眼睛跟在我身后狂奔。
我脑海里空蒙蒙一片,我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
我像看见了救星一样看见了我妈。
她正在河岸边焦虑地徘徊。
我说:
峰正……峰正将山秀……山秀压在了身下……在苜蓿地里……他打山秀呢,你快去看。
我拉妈。
妈一把卡住我的脖子把我往回拖。
我拼命说:
打死了,你快去看!
妈不知那儿来的劲,卡住我的脖子把我往回拖。
六
我已经好几年不上学了。
大说:
瓜子么回来算咧,能念个啥眯眼。
我便回来了。
虽然我离开学校极不情愿,但既然大说了我就只好回来。
回到家里我只有放牛。
放牛成了我的归宿。
远离了学校,使我深谙了放牛的乐趣。
整日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一边听老牛用嘴唇啃草一边看蓝蓝的天空。
偶尔天空飘过一朵云都令人感觉非常生动,它们像山、像石、像奔马、像飞龙……形态万千,变化多端。
有时天空上有鸟飞过,它们或一只独行,或两只相伴,有时一大片让你似乎和它们一起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这时我便站起来学着小时候的样子,撑开自己的双臂,从山上向山下跑,我就成了一只在阳光下飞翔的鸟。
牛温和的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当然不像我五爷,有点像九爷。
九爷有时也放牛,他放牛时便和牛一样在山上反刍。
这时管牛就成了他的事,我便在山坡上无拘无束。
然而,我却思念妮子。
思念妮子是我离开学校唯一难过的事。
听说她也不念书了,可我没有机会碰见她。
真的我想见见她,只是想见见她。
妮子的家就在河对面的山旮旯里,被山隔住了她和我的视线,使我们相互望不见。
但有时候我却能从吹来的微风中嗅到她的气息,是多年前在教室里手把手教我写字时的那种闻不到气息的气息。
我知道她离我很近,只是我们无缘相见。
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这个机会。
只要有风吹,我便要等。
我终于等到了妮子。
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天空里没有一丝云,太阳在天空站着不走,似乎要和人对眼。
没有一丝风吹过,连爱在阳光底下爬走的小虫也躲进了草下的洞穴里。
我躺在被阳光晒过的草地上,像是煨过的热炕舒服极了。
我用帽子捂住脸,睡在老牛的身边。
老牛卧着,它已经吃饱了,反刍着肚子里的香甜的草。
有一个声音在唤我,但我不能动弹。
我又听到:
唤唤,唤唤——
这个人拿掉了盖在我头上的帽子,站在我的身边。
她竟然是妮子,她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旁!
妮子啊妮子,我亲亲的妮子!
我日夜想念的妮子。
我在妮子面前不是个傻瓜,可我却变成了个结巴。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我就这么站起身用眼睛痴痴的盯着她。
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又听到她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老实才能可靠。
妮子啊妮子……
妮子靠近了我。
她竟然变的如此丰满,我嗅到了属于她的气息。
她像许多年教我写字一样抓起了我的手。
我像峰正抱山秀那样抱住了妮子,我听见沉重的喘息声。
我没有敢睁开眼睛。
妮子将一个软软的东西弄进了我的嘴里,我开始有些头晕目眩。
我浑身似乎闪电般的炸开了花。
妮子把啥东西弄进了我的嘴里?
我却睁不开眼睛,我只能任那东西不停的在我嘴搅动。
妮子你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抱着妮子在阳光晒过的草地上融化了。
一切都失去了真实,变的缥缈起来。
妮子的胸膛显的格外宽广,我回到了童年,回到我妈的怀抱。
我什么都感受不到,只感受到妮子剧烈的心跳。
妮子……我瞌睡……
睡吧!
你睡吧!
我沉沉地睡着了。
我醒来时我的身边已经没有了妮子。
我在河岸边的草地上努力寻找。
阳光依然在草地上朗照。
没有人看见我和妮子在一起,没有人能看见妮子离开我去哪里?
可有太阳嘛!
太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