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docx
《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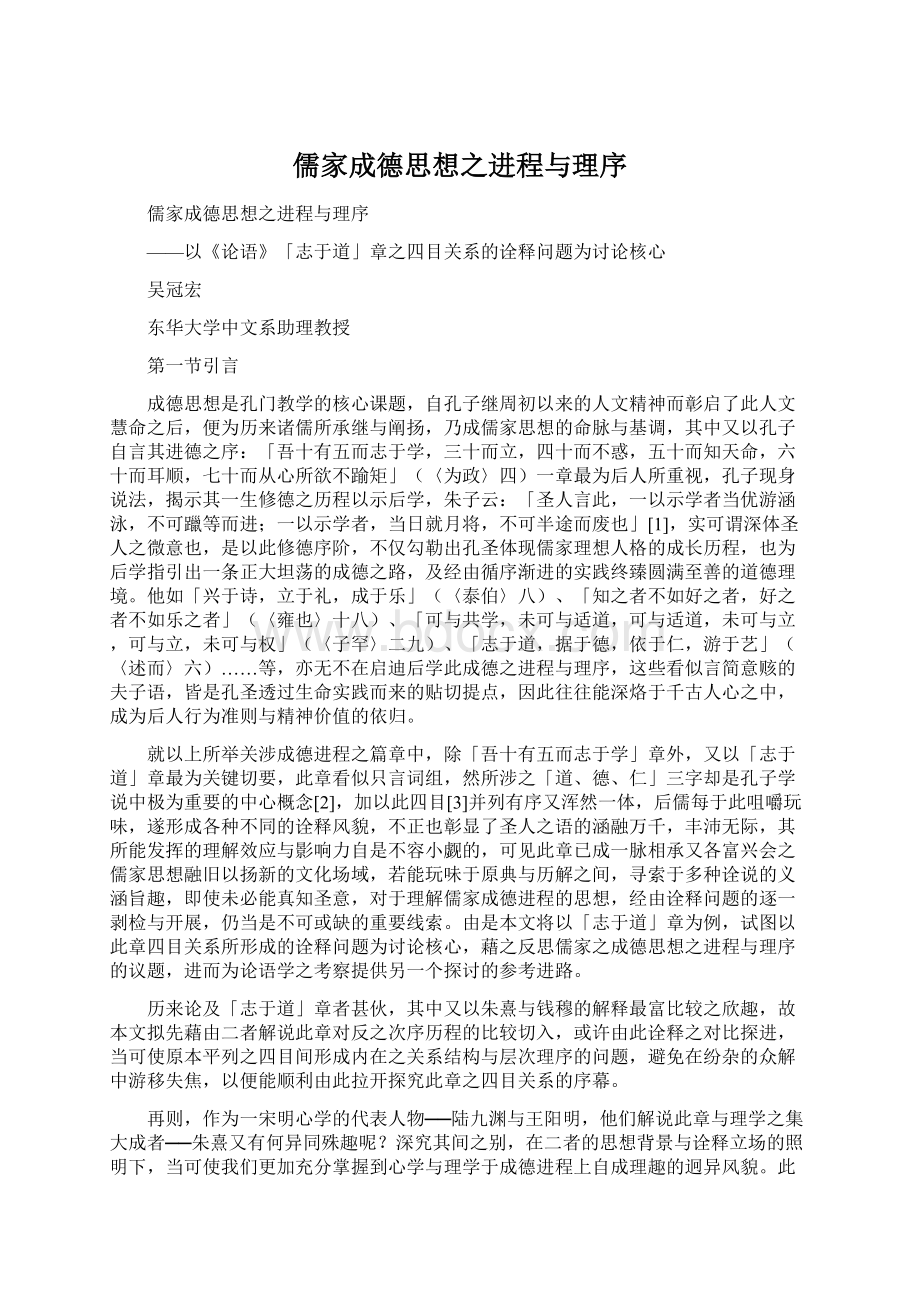
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
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
——以《论语》「志于道」章之四目关系的诠释问题为讨论核心
吴冠宏
东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第一节引言
成德思想是孔门教学的核心课题,自孔子继周初以来的人文精神而彰启了此人文慧命之后,便为历来诸儒所承继与阐扬,乃成儒家思想的命脉与基调,其中又以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四)一章最为后人所重视,孔子现身说法,揭示其一生修德之历程以示后学,朱子云:
「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一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1],实可谓深体圣人之微意也,是以此修德序阶,不仅勾勒出孔圣体现儒家理想人格的成长历程,也为后学指引出一条正大坦荡的成德之路,及经由循序渐进的实践终臻圆满至善的道德理境。
他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十八)、「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二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六)……等,亦无不在启迪后学此成德之进程与理序,这些看似言简意赅的夫子语,皆是孔圣透过生命实践而来的贴切提点,因此往往能深烙于千古人心之中,成为后人行为准则与精神价值的依归。
就以上所举关涉成德进程之篇章中,除「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外,又以「志于道」章最为关键切要,此章看似只言词组,然所涉之「道、德、仁」三字却是孔子学说中极为重要的中心概念[2],加以此四目[3]并列有序又浑然一体,后儒每于此咀嚼玩味,遂形成各种不同的诠释风貌,不正也彰显了圣人之语的涵融万千,丰沛无际,其所能发挥的理解效应与影响力自是不容小觑的,可见此章已成一脉相承又各富兴会之儒家思想融旧以扬新的文化场域,若能玩味于原典与历解之间,寻索于多种诠说的义涵旨趣,即使未必能真知圣意,对于理解儒家成德进程的思想,经由诠释问题的逐一剥检与开展,仍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线索。
由是本文将以「志于道」章为例,试图以此章四目关系所形成的诠释问题为讨论核心,藉之反思儒家之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的议题,进而为论语学之考察提供另一个探讨的参考进路。
历来论及「志于道」章者甚伙,其中又以朱熹与钱穆的解释最富比较之欣趣,故本文拟先藉由二者解说此章对反之次序历程的比较切入,或许由此诠释之对比探进,当可使原本平列之四目间形成内在之关系结构与层次理序的问题,避免在纷杂的众解中游移失焦,以便能顺利由此拉开探究此章之四目关系的序幕。
再则,作为一宋明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与王阳明,他们解说此章与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又有何异同殊趣呢?
深究其间之别,在二者的思想背景与诠释立场的照明下,当可使我们更加充分掌握到心学与理学于成德进程上自成理趣的迥异风貌。
此外,王船山从朱注「志于道」章寻索到「游艺」先后与否的理解争议,故本文拟进一步探寻「志道据德依仁」与「游艺」之间先后关系的问题症结,以进一步定位「游于艺」于此四目中的角色,并在此关系模式中揭示此章与时俱进又得以历久弥新的文化力量。
第二节朱熹与钱穆对此章诠释之比较
朱熹之《四书集注》对中国人理解《论语》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近人钱穆尤服膺朱熹之学问,章条理析之《朱子新学案》,对阐发朱学贡献良多[4],但钱穆对朱注却未必全盘接收,对此章提出截然对反的理解即为显例,今先将二说罗列于下以论之:
1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
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
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闲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朱熹)[5]。
2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
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而说之,庶有尚于孔门教学之顺序(钱穆)[6]。
由此可见朱子顺解四目为为学次第,钱穆却主张逆转四目说之才是孔门教学顺序,钱穆所释当是克就朱熹而来,两者皆重「先后之序」,却意见相左如是,个中原委值得玩味。
大体上朱熹的说法较为后人所接受,然而亦有学者与钱穆之见相近[7],尤其是他一反常论却又能自成理序的解读方式,使此章跳脱了理所当然的顺解模式,由之也凸显了理解此章之四目关系的合理位序问题,可见钱穆的说法仍有值得注意之处。
若依朱熹之解「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可知,「志道」之所以为先,「志」字实为关键,在〈里仁〉第九章亦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说法,认为士当从自然欲求中跳脱出来,如是道德生命方有开展的可能,可见「志于道」即代表向道仁心之开启,进而依此顺序一路展开,从朱注「本末」、「轻重」、「先后」、「内外」字眼的提点可知,朱解之先后实是建立在依本而末、由重而轻、由内而外的立场,乃是契会儒家「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二)的精神而来,因此虽在践履的过程中有先后之序,但其终极的理想却是「本末兼该,内外交养」的,朱注从「志于道」一路解开,注意到「据德」(不失)与「依仁」(常用)于道德境界之层次上的区隔,也照顾到「游于艺」之「游」(从容)与「艺」(小物)两个面向,此注文不仅具有骈偶的修辞之美[8],也充分展现出朱注严谨精要的风格。
朱子所论精当有据,钱穆何以觉得并不妥当?
而主张逆转此四项之排列以说之呢?
观钱穆有云:
1游于艺之学,乃以事与物为学之对象。
依于仁之学,乃以人与事为学之对象。
据于德之学,则以一己之心性内德为学之对象。
而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则为志于道。
志于道之学,乃以兼通并包以上之三学,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物与事与人与己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此即所谓道也。
[9]
2游艺依仁之学,皆下学也,知据德志道,则上达矣。
上达即在下学中,学者当从此细细参入,乃悟孔门之所谓一贯。
[10]
可见钱穆一则将此四目分为「事与物」、「人与事」、「一己之心性内德」、「兼容并包此三者」四个层级,而且依此分殊,道乃最高,统括前三者,乃是着眼于「道」、「德」、「仁」、「艺」四字的轻重位阶,掌握为学当由浅而深之循序渐进的原则,遂将四目全然收摄于「学」而成为学的对象;二则他分四目为下学(游艺、依仁)与上达(据德、志道),而四者之间「有其相通,亦有其层累」,此当本「下学而上达」(〈宪问〉三七)的精神而来,遂云依此乃可得孔子博文而一贯之深旨。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将「仁」与「艺」皆归为「下学」,学习的对象即是「事与物」及「人与事」等诸种事务,具体言之乃为扫洒应对进退及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等事,钱穆当是以为若能于日常生活上磨炼,在典籍中涵养,然后方有上达之学可言,所谓其间有相通与层累,即是要人在下学中悟道,在下学中砥砺其德,实践有得进而能臻道境,如此有德而能体道,则可使仁艺之学更臻深透圆熟,下学而上达遂能交互长养而境界愈高,使人事物皆得其位,皆尽其能,乃成一礼乐化成的和谐人文世界。
实则钱穆不仅提出此迥异于朱注的说法,更进一步语重心长地克就朱解所形成的宋学背景探究朱注之因由:
程朱所以必于此章为如是曲说者亦有故。
一则程朱论学,以志道据德为本而当先,以依仁游艺为末而在后,于孔门博文约礼下学一段不免忽过。
…宋儒所言,不免窥其高而忽略其基址,与夫其建构之层累曲折矣。
…故学必重于多见多闻,而宋儒必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为二,又轻视见闻之知,教人直从事于德性之知以为学,故必首重据德与志道,而不知当先从事夫下学,先从事于游艺依仁之学以渐求其上达,而渐企及于据德与志道之学焉。
…而宋儒必以人欲释下达,于是天理在君子,人欲属小人,志学则必志于据德志道,而俨若与游艺依仁之学显然有上下截之判,更不见其互通层累之一贯,此实宋学之失也。
[11]
由此可知,钱穆以为程朱之学弊在轻下学而重上达,以致形成两者之对立,使下学与上达成为人欲与天理的对立,成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对立,人遂务虚而无实学,造成宋儒高蹈义理轻忽实学之风。
清儒黄式三于《论语后案》中亦有相类之意见:
周官之法,教万民以艺,养国子以艺…士固有滞于艺而不闻道者,要未有不通于艺而遽高语道德者,此实学之所出也。
…学者高言志道据德依仁,而不亟亟于礼,能不违道贼德而大远乎仁也邪?
…后人以冥语为仁,以虚无为道,以清净为德,离训诂文字而言理义,弊遂至于此,君子博学无方,六艺之学皆宜遍历以知之。
故曰游于艺。
[12]
黄氏所言虽不是着眼于理解此章四目的关系次序,但已指出历解偏重「志道据德依仁」而未能注意到「游艺」的缺失,因而强调「游于艺」的迫切重要性。
钱穆之见亦在反省「以冥悟为仁,以虚无为道,以清静为德」之弊而来。
唯朱熹为宋儒中颇务实学者,深恐后学蹈虚骛高,与象山之心学强调立其大本而偏重心性之论有别,从他引程子之语: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以大者远者,非传以小近,而后不教以远大也」进而主张「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13]可知,朱子所秉持之精神实未悖钱说之意,何以集其心血力作的《论语集注》,注此为学之吃紧的章节,却「似未为允」[14]而有此一失?
不禁启人疑窦。
实则钱穆于《论语新解》中曾依「小学」与「大学」分论此章之序:
本章所举四端,孔门教学之条目。
惟其次第轻重之间,则犹有说者。
就小学言,先教书数,即游于艺。
继教以孝弟礼让,乃及洒扫应对之节,即依于仁。
自此以往,始知有德可据,有道可志。
惟就大学言,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
求道而有得,斯为德。
仁者心德之大全,盖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
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
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
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
若教学者以从入之门,仍当先艺,使知实习,有真才。
继学仁,使有美行。
再望其有德,使其自反而知有真实心性可据。
然后再望其能明道行道。
苟单一先提志道大题目,使学者失其依据,无所游泳,亦其病。
然则本章所举之四条目,其先后轻重之间,正贵教学学者之善为审处。
颜渊称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固难定其刻板之次序。
[15]
钱穆以为若就大学而言,当从志道而据德而依仁乃至游艺,可见他理解此章实已注意到传统大人之学的说法,后并以「无刻板之次序」解之,以为「固难定其刻板之次序」。
但整体而言似仍较倾向依循「小学」教学者以从入之门,仍当由「艺」而始的立场,故云:
「苟单一先提志道大题目,使学者失其依据,无所游泳,亦其病」,其归返实学而力摆宋学之失的立意赫然可见。
据此可知,钱穆之见就次第轻重间其实有两个面向,「大学」意谓以修德为主,「小学」则以日常生活之实践为主,钱穆以为若无生活上典籍上知识上的学习,何能真对修德大道有所体会明白?
所以以小学为入门之要,而后方有大学之学,这种说明其实与朱子并无二意。
但是笔者以为钱穆对此章就小学言的解说若仅从「道─德─仁─艺」四目以观,则未必有失,唯观此章于「道─德─仁─艺」之外,尚有「志─据─依─游」四字,钱穆就小学言的解说则将之皆统合于「学」,似未能全然照顾到用此四字的意涵,毕竟《论语》用词极为俭约精切,虽不必字字计较拘泥,但全章仅十二个字,不当无顾「志─据─依─游」四字,而且前引之朱注乃是顺钱穆文称引之材料而来,实仅及朱注此章之「外注」的部分,「内注」的部分则对「志」、「据」、「依」、「游」四字亦多有阐释:
志者,心之所之之谓。
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
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
据者,执守之意。
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
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违之谓。
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
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
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
[16]
就「志─据─依─游」四字之诠说而言,朱注颇能照顾到四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意义上即存在着由紧而松的发展层次,后四目承此而来,可视为道德实践中从启志持守至依顺从容的境界进程。
朱子这种站在注疏家的立场,配合对象「道─德─仁─艺」的存在,进而注意到「志」、「据」、「依」、「游」四字的用意,虽早在何晏《论语集解》及皇侃《论语义疏》时即着力于此[17],但何晏(魏初)与皇侃(南朝)处儒衰道盛之际,玄理倡行,每以道家思想来诠说儒理,在尚虚背实的时风下,以「无形」(不可体)、「有形」(有成形)区隔「道」与「德」,又主张「仁劣于德」,并认为艺「不足据依,故曰游」,可见两者对于「道─德─仁─艺」四目,皆是立基于「以虚无之道德为宗为本」的思维脉络下,遂有明显的轻重高下优劣之分判,故虽能措意于「志─据─依─游」的义涵,然而就掌握此章的义旨而言,终是有所偏颇的。
反观朱熹言「道」,既强调其乃「大本」之所在,又主张「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使之能由虚返实,回到人伦日用之常;至于「艺」一则落实于「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的面向立说,又点出其乃「至理所寓」,在此诠说下,「道」与「艺」遂能一体通贯、互有涵摄,毕竟若过于强调「道」之虚时易沦为「清虚之论」,但如果过于强调「艺」之实时,也极易沦为仅务小物技艺的末流,朱解之妙即在区隔两者之不同外又能得所会通,进而发挥本末兼该、虚实并融的理解效应。
综而言之,朱子乃是并观「志据依游」与「道德仁艺」而诠说之,遂发展出「志道─据德─依仁」与「游艺」两者内外交养的成德体系,并且志道据德依仁三者的发展关系亦有愈趋精密之意。
而钱穆则将「仁」归属下学,与「艺」成为入德之最先初阶,自与朱子所言迥异,而朱子主张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遗,亦与钱穆主张当从事下学方有上达之可言有实践理序上的差异。
在此我们发觉最大的分殊应在对「仁」的定位上,朱子视「仁」为成德最高境界;而钱穆则重在人之学上,即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人情事务,此当从「礼」而来,可说当归属于六艺之「礼乐射御」的范畴,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所熟习的一套生活与政治文化的美仪,夫子由此而悟出「仁」,遂将「仁」视为创造礼乐文化的精髓所在,而钱穆在此似乎归「礼」为「仁」,由是「仁」与「艺」的范畴有所重迭,是以以「仁」属「下学」,就「仁」于孔子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层次位阶而言,实有值得商榷检讨之处。
综而言之,钱穆阐析此章虽颇能另辟理趣,自成一说,但未必即能就此反对朱注;尤其是本着批评宋学之眼光探此朱注之意,又据此检讨宋学之弊,不免有藉题发挥之嫌。
而朱注能同时兼顾到「志─据─依─游」的先后之序及「道─德─仁─艺」的轻重之伦两个面向,自是比钱穆就小学言的角度仅偏于「道─德─仁─艺」的轻重之伦面向着力更为周全。
若依钱穆之见,朱熹以「志于道」为先乃宋明儒的通病,而言「自儒学大统言,宋明儒终自与先秦儒有不同,不仅陆王为然,即程朱亦无不然」[18],实则立论每与朱熹相对的陆、王对于此章之理解亦有别于朱熹,未可妄加等同,加以对观比较之或可一窥两派成德进程之思想的殊趣。
第三节朱熹与陆、王诠释「志于道」章之比较
陆象山与王阳明,他们对此关键篇章又当如何诠说阐发,与朱熹所释有何不同,首先例举陆象山之意见,象山有云:
1志道,据德,依仁,学者之大端。
[19]
2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尽。
[20]
象山并没有如朱子般批注经典,而每以语录、书信的型态留下他的意见,因此这两则与朱子有系统而细密的解释并不相同,但是仍可见象山对于「志于道」章整体的意见。
由第一则可知,象山对此四目,独漏「游艺」,而以前三者为「学者之大端」;次则将道德仁涵括在「道」之下,志道据德依仁遂以「主于道」涵括之,皆属修德,此四目遂变成「道」与「艺」即「修德」与「习艺」这两种关系。
修德意谓着充扩本心,即事明理,以心印道,使心即是道之展现,这种充扩己心合于大道的过程,浩然之气充塞于宇宙之间的气魄,正是文化创生的力量,也是象山最觉珍贵的东西,因此他教人以「辨志」、「立志」为先[21],使弟子向正道修德而行,如此开发一个人的潜能,必能增强学习技艺的能力,因此主于道,艺也随之可游,但是主于艺,却会因己心之不开拓,使欲望炽旺,遂导致道艺两伤的境地,可见象山所解正是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告子上〉十五)的发挥。
朱熹对于道与艺,虽亦有本末轻重之判[22],但他实未如心学家般将「志于道」标举到涵盖一切的地步,反而戒心于仅着重在「志于道」的缺失,而十分强调志于道后当于「据于德」与「依于仁」处持续精进:
先生问正淳:
「曾闻陆子寿『志于道』之说否?
」
正淳谓:
「子寿先令人立志。
」[23]
曰:
「只做立志,便虚了,圣人之说不如此,直是有用力处。
且如孝于亲,忠于君,信于朋友之类,便是道。
所谓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于己也。
及其行之尽于孝,尽于忠,尽于信,有以自得于己,则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
如此,然后可据。
然只志道据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间断了,二者皆不能有。
却须『据于德』后,而又『依于仁』」。
[24]
朱子在此针对象山兄弟主张的立志为先之说法,提出了他的质疑,显然朱子以志为「心之所之」之意,只是知道当往何处行去而已,而学者更重要的却在知之而后行的践履工夫,因此唯有据德依仁工夫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在朱子的主张下,志道据德依仁是一渐至精密的修德工夫与境界,他清楚明言了三者之间的差异,与象山以「道」涵言三者有极大的差异。
象山所言精简,却常发人深省,他直承孟子之学而来,以为「先立乎其大者」、「明得此理,即是主宰」、「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主张能立其本,则一切俱足,无稍缺欠,故其教人以「辨志」为先,以为当务之急在立其大本大根,而「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可见他的「辨志」,并不只是知道一个方向而已,其「辨志」便是不断自我开发的实践过程,是以由辨志而来的主于道之工夫进程即为一种无法分割的整体,诚如孟子所说的「由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梁惠王上〉六),故于志道据德依仁,自然没有必要再详加分割说明。
但于朱子却担心学者初闻辨志,即无着力之处,只能从光影中求便是浪费生命,故须细加分辨,因而十分强调「志道→据德→依仁」层层转进的发展关系。
再看阳明的主张:
问志于道一章,(王阳明)先生曰:
「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
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
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
」[25]
阳明在此直言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也就是从志道至游艺四者即是一事四个阶段,因此再以盖房子为例,从起念、规划至整体完成,整件事便是盖房子,虽有步骤进程的不同重点,却皆涵于盖房子之一事之中,不能本末倒置,缺一则不得成屋,故视「志于道」一句为可以涵盖以下三句的关键眼目,「志于道」一以贯之,来统摄「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尤戒心于脱离「志道」之「游艺」,以为若此便无本根,何枝叶花实之想?
亦不能将术艺发挥至极致,如此只能成为一平常之匠字辈的人物而已,故将术艺纳入整体修德的范畴,认为是一种「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的修德工夫,与象山「道」、「艺」相对而言的说法又不一样,可见阳明较象山分析说明地更为细致,但与象山相同的是皆视此四目为一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发展历程,只要真切从生命中来的,发动了自身的仁性,一切道德实践便是自然涌出,毫无欠缺,故象山曾云「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亲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26],我们具备了感知的能力,因此只要明心见性,孝弟的行为便是如此的自然具足,何尝是外在要求而来的德性?
是以阳明说「工夫自住不得」,若能真知,必有真行,即知即行,知行合之,不如此行便心有不安,阳明一本其亲切易晓的施教风格,故其诠说「志于道」,以盖屋为例,能近取譬,使后学当下受用,何等明朗通透,他不契于朱子格物之说,遂自家悟得「致良知」本领,故其施教反对逐外穷理,尤重本源根芽,寻绎于《论语》以观,孔子亦以为其学不在「多学而识之」的层面,宜从「一以贯之」之道得其精髓[27],即在区隔二者之间的本末,欲人莫殉末以忘本,就轻而舍重。
可见陆、王所以有此诠说,除了遥承孔孟一以贯之及立其大本的精神之外,亦与他们深体为学支离芜杂之失遂将一切收摄于本心的立场有关。
至于朱熹实未能苟同于心学家过于强调「志于道」的说法,以为「未知而有志于求道,也是志」,要在能续之以「据德依仁」,使之从实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进而功夫渐熟渐精,若更细密分之,则「志道」为向学之初阶,要在定其方向,与据德依仁于工夫境界之层次上相续转进终是有别:
1正卿问:
「志道、据德、依仁」
曰:
「德,是自家心下得这个道理,如欲为忠而得其所以忠,如欲为孝而得其所以孝。
到得『依于仁』,则又不同。
依仁,则是此理常存于心,日用之间常常存在。
据德、依仁,虽有等级,不比志道与据德、依仁,全是两截。
志只是心之所之,与有所据、有所依不同也。
」[28]
2据德,是因事发见底;依仁,是本体不可须臾离底。
据德,如着衣吃饭;依仁,如鼻之呼吸气。
[29]
据此可知,朱子与陆、王于此章的分歧即在「志」之解释,朱子以为志只是心上之一念,而陆、王则以为有志必已涵行方能称之为志,真知必已有生命真切的经历,没有真实的感动是不能有志出现的,相形之下,朱子在这一点上显得比陆、王宽松,只要是来书院听讲的初学者便可说是志于道了。
在此脉络下,朱子将志道、据德、依仁分截出粗细二阶段,即志道只是入门,而据德依仁方能有成绩可见,如此「志道→据德→依仁」乃为一由外返内、由客返主的成德历程,故朱子云:
「志于道,犹是两件事」、「志于道,方是要去做」、「道者,人之所共由,只是统举理而言」;直至「据德」的阶段,是出自自心之自主性的道德行为表现,故云:
「德是自家心下得这个道理」,并常依客观事件或外在环境及相关人事物而表现出超乎私欲、行其所当行的道德行为,即是据德;至「依仁」的阶段,更进而在自心中无时无刻不论何种境遇,仁心源源流出,无所稍息,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五),可说已成为如呼吸般自然且必要的立身条件了。
因此,朱子乃云:
「德是道之实,仁是德之心」,层层翻进,统而言之,乃为一「由客返主」、「从粗入精」的成德进路,如此是将陆、王之主于道与辨志之最优位降格,而着重于工夫较细密的践履之上。
根据以上朱熹与陆、王之说法的分歧可知,心学家重在彰显「志于道」的充分绝对性,由其践道工夫立其大本与知行合一的脉络下,故能以「志道」涵盖以下三者;朱熹则十分强调「志道据德依仁」环环相扣、循序精进的发展关系。
心学派每标举出若无志道所形成的游艺之失[30],而朱熹则对过于着力在「志于道」遂失之于虚的毛病心存警戒,在此充分展现了朱子渐修与陆、王顿悟臻道之修德路数的不同,而此四目之间的内在关系亦因心学与理学各有侧重的修德体会遂形成相异的理解进路。
第四节从朱熹到王船山─以「志于道」章之意见为考察
本文第二节因顺着钱穆的论述,对于「志于道」章之四目关系的讨论,不免局限于顺解之序(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与逆解之序(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两种对反型态。
第三节言及陆、王之说法时,则已逐渐转向以「志道据德依仁」为「修德」及以「游艺」为「习艺」两种面向。
实则朱熹亦曾以「『志于道』至『依于仁』,是从粗入精;自『依于仁』至『游于艺』,是自本兼末」[31]说明四目间即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关系,检视朱子诠说的「游于艺」于此四目中的确有别于「志道据德依仁」之三合为一的关系,因此如能掌握「游于艺」在此四目中的角色扮演,对于理解「志于道」章之义涵当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针对「游于艺」与前三者之间的先后关系所形成的疑解过程即曾展现于《朱子语录》中:
1子升问:
「上三句皆有次序,至于艺,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后否?
」
曰:
「艺是小学工夫。
若说先后,则艺为先,而三者为后。
若说本末,则三者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