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例子2.docx
《学术史例子2.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学术史例子2.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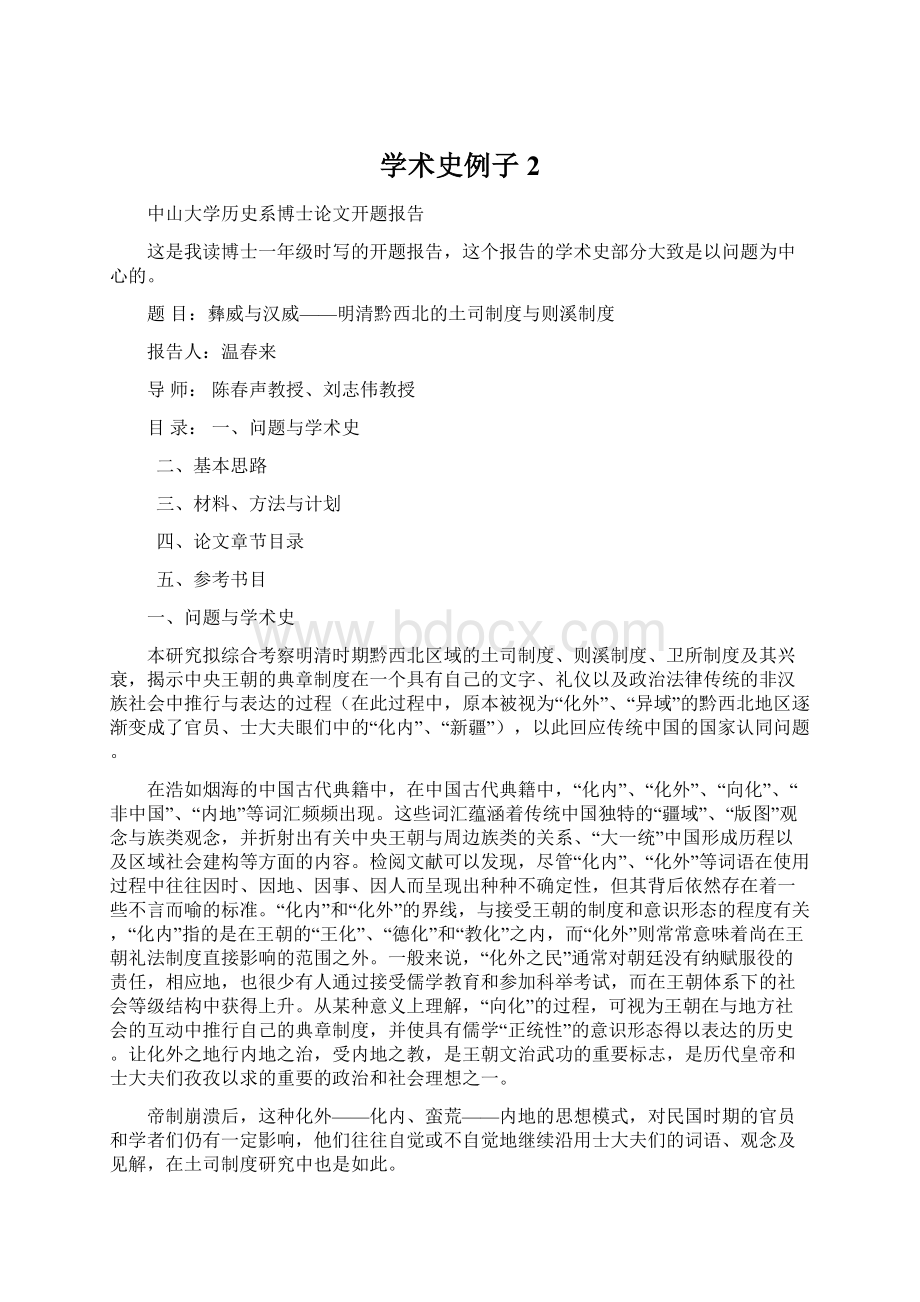
学术史例子2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这是我读博士一年级时写的开题报告,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题目:
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
报告人:
温春来
导师:
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
目录:
一、问题与学术史
二、基本思路
三、材料、方法与计划
四、论文章节目录
五、参考书目
一、问题与学术史
本研究拟综合考察明清时期黔西北区域的土司制度、则溪制度、卫所制度及其兴衰,揭示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本被视为“化外”、“异域”的黔西北地区逐渐变成了官员、士大夫眼们中的“化内”、“新疆”),以此回应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化内”、“化外”、“向化”、“非中国”、“内地”等词汇频频出现。
这些词汇蕴涵着传统中国独特的“疆域”、“版图”观念与族类观念,并折射出有关中央王朝与周边族类的关系、“大一统”中国形成历程以及区域社会建构等方面的内容。
检阅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化内”、“化外”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但其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言而喻的标准。
“化内”和“化外”的界线,与接受王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有关,“化内”指的是在王朝的“王化”、“德化”和“教化”之内,而“化外”则常常意味着尚在王朝礼法制度直接影响的范围之外。
一般来说,“化外之民”通常对朝廷没有纳赋服役的责任,相应地,也很少有人通过接受儒学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而在王朝体系下的社会等级结构中获得上升。
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向化”的过程,可视为王朝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推行自己的典章制度,并使具有儒学“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得以表达的历史。
让化外之地行内地之治,受内地之教,是王朝文治武功的重要标志,是历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之一。
帝制崩溃后,这种化外——化内、蛮荒——内地的思想模式,对民国时期的官员和学者们仍有一定影响,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沿用士大夫们的词语、观念及见解,在土司制度研究中也是如此。
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背景之一是民族学在中国逐步兴起。
加之内忧外患,时局艰危,开发边疆、改进边政等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们的目光。
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应予以废除或削弱,要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使边疆趋向“内域化”。
凌纯声指出:
“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
……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
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
”有的学者视改土归流为“内地”化运动,佘贻泽称:
“永乐八年(公元1410)思州、思南两宣慰使为乱,平定之,乃改为思州、思南、镇远、铜仁、石阡、乌罗、新化、黎平八府,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是为贵州成为内地之始。
”
抱着使边政与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许多学者希望从古代治边策略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他们关注历代王朝的土司政策沿革,呈现出重视制度史研究的取向,其有关成果,是考察南方族类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础。
1936年,佘贻泽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等论文,1947年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该书系土司研究的首部专著,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省对土司的态度等,并总结了明清两代土司政策的利弊得失,最后提出建议,呼吁从交通与移民入手解决土司问题。
作者的研究涵盖全国土司,在厘清制度的内容及其沿革方面,堪称当时的代表之作。
但作者对文献的了解不足,以致该书存有较多的舛讹与片面之处。
凌纯声的研究亦侧重于制度层面,如土司起源、土官品衔、袭职情况等,并已经注意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1949年以后,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模式成为中国大陆土司研究中主流的分析架构,对土司社会的性质、经济基础、阶级分化等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
不过,重视制度史研究的传统仍有影响,1958年,江应樑出版《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一书,在辨析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土官与土司的差异、来历、族系、贡赋情况与羁縻制的特征以及明代在云南设置大量土职的原因等,描述了土官和土司的分布区域及其疆界的变动情况,最后对滇省土官、土司进行全面统计,列举了各种品衔的三百多家土职。
1980年代,吴永章出版了《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南方民族政策史,作者从秦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施政方针说明土司制度的渊源,论述土司制度发展及衰微的过程,并对土司制度下的贡赋、人口、兵役、土地制度及文化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作者认为:
“在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过程大致是:
渊源于秦、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不断得到充实;正式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和清初;清雍正改土归流后,则逐渐衰微。
”1992年出版的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是一部在资料的耙梳和整理方面用力较多的著作,作者继承其在1988年出版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的思路与方法,统计了元明清时期设于全国十个省区的2,569家土司,并考订了其地望、族属、世系以及相关的重要事件等。
迄今为止的土司研究,在制度的考辨方面用力较多,初步勾勒了历代中央王朝向南方“蛮夷”地区拓展的图象,但对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王朝与地方社会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地方社会变革的动态而又充满矛盾的实际场景揭示不多,对所谓“蛮夷”社会固有制度和文化的实际形态及其潜在且可能更为深刻的影响关注不够。
作者以为,若能将王朝制度的变化与国家的礼仪和意识形态在区域社会表达的过程结合起来考察,将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特质、国家认同和文化整合等问题的认识。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人类学家借用Redfield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架构,“找到了他们研究的焦点”,以此架构分析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政治和文化都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的内在机制。
这种二分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小传统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
1965年,华德英(Ward,BarbaraElsie)提出了动态的、多重迭合的“意识模型”(ConsciousModel),按她的描述,意识模型可分为三种:
一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及文化制度的构想,即自制模型,这种模型因环境差异而各不相同;此外还有针对其它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而建立的各式各样的“局内观察者模型”;尽管上述两种模型千变万化,但中国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模型,这是对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它提供了评估何谓中国方式的标准,该模型所强调的内容,各个“自制模型”均较为遵守,而它所不涉及的方面,各“自制模型”均有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发挥的自由。
华德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延续性以及变异性的解释,不仅超越了大、小传统的二分法,也超越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功能论架构。
差不多同时,施坚雅(WilliamSkinner)参照中心地学说,发展出市场等级以及区域划分的模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的整合问题提出解释。
那么,大一统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是怎样在具体的时空领域推行开来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国祈发表《清季台湾的政治及近代化——开山抚番与建省(1875—1894)》和《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两篇论文,提出并阐述了“内地化”理论。
这一理论在某些方面令人联想起传统士大夫们“化外——内地”的思考模式。
作者认为,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番民的汉化、宗族的发展、神祗信仰的统一、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居民融合、行政体制的完善、文教的推广等一系列“内地化”运动,台湾逐渐由“移垦社会”变成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
这一理论涉及汉人、高山族、平埔族等多种族群,这些族群内部关系复杂,其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变迁呈现多样面相,相互间的互动更是千姿百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内地化”理论失之松懈。
除此之外,对土著民在历史变迁中所起作用的忽略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缺陷。
后来许多关于台湾的研究对此已有所修正,如陈秋坤注意到,国家力量的渗入并没有在岸里社建立起同内地一样的官僚制度和保甲体制,而是导致通事和部落组织的官僚化。
其实,与其说王朝制度和礼仪的推广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动,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过程。
有研究表明,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府通过列入王朝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官府认可的神明;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王朝祀典或官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
前者如天后,天后最初只是福建莆田县湄洲的一个普通地方神祗,但自北宋到清中叶,她不断得到朝廷的敕封和提升,成为了在南中国沿海极其显赫的神灵。
在这种使神明标准化(StandardizingtheGods)的过程中,国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介入了地方,民间信仰由此呈现出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交叉重迭的文化意义。
而珠江三角洲民间社会崇拜的北帝,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北帝崇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传布,并形成为一种地方传统的过程,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在文化上进一步整合到大传统之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标准化的神明信仰地方化过程”。
但是,王朝祀典中的庙宇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完成民间化,潮州樟林地方的乡民对官方神庙和地方神庙的不同心理体验(“份”的微妙感觉)以及两种庙宇的不同命运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过,“传统的政治力量消退以后‘官方庙宇’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观念在乡民的信仰意识中无关紧要。
实际上华南乡村社庙的出现,正是明王朝在乡村地区推行里甲制度,在里甲中建立“社祭”制度变化的结果,理想化的‘国家’的‘原形’,始终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
科大卫(DavidFaure)与刘志伟对宗族的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国家的制度和礼仪在区域社会得以实现的历史。
他们认为宗族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属制度,更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
明代以前是僧、道和巫觋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中有着广泛和深刻影响的时代,但自北宋以来士大夫们已经开始积极运用理学所规范的礼教去改造地方的风俗,向佛、道、巫的正统挑战,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取代以神祗为中心的地方组织,但却在乡村礼仪方面取得了成功,国家与社会的这种互动与妥协形成了华南地区广为常见的所谓宗族组织,这一深刻的变迁意味着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结合,边缘地区由此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的秩序中。
科大卫(DavidFaure)等学者还提出,区域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这种文化视角取向以及对历时性的关注,超越了囿于具体地域的观念,发展了施坚雅的区域理论。
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启发良多。
笔者希望,对明清时期黔西北区域独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能够补充和发展学界对中央王朝与“边缘地区”关系的认识。
首先,黔西北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地区,并且统治该地区的原住民(彝族)至少在宋代就开始使用自己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以自己的文字书写的文献,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宗教、文学、文艺批评、哲学观念、政治权力等。
这些文献提供了与汉文文献不同的关于本地历史的解释,使我们有可能在丰富的汉、彝史籍的比较中,结合田野调查所得去重构中央王朝和周边族类最初接触的情形,特别是尽量从原住民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情景。
其次,原居住在黔西北的族类拥有自己的文字、文献、礼仪、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制度,并非简单的初民社会。
掌握着文字的布摩与慕史们用吟诵或著述的方式传扬祖先的伟业,赞颂他们创下的美好制度,以张扬本族的威荣()。
这使后来的研究者有机会体验和了解黔西北社会固有的传统,并探讨这种传统与中央王朝传统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彝威()与汉威()的交织,以及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在“边缘”地区的表达,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地域社会的历史建构。
又次,因为黔西北区域固有的传统有迹可寻,使现代的研究者有可能超越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点四方”的思考模式,以所研究的区域为中心来进行探讨。
在这个过程中,以下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相对于士大夫们的“化内”、“化外”观念,彝族统治者和一般原住民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外部世界的?
当彝制崩溃、彝威消解、汉礼盛行之时,不同身份的彝民有过怎样的心理体验和因应举措?
笔者深信,黔西北区域所蕴涵着的复杂历史信息,使我们在把握“化内”、“化外”、“羁縻”、“内地”、“新疆”等词汇时,有可能从更多的角度(特别是从原住民和当地原有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从而更深刻且更有平衡感地揭示这些词汇所蕴涵着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等方面的复杂内容。
较之于民族国家、族群等产生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概念,上述源于中国本土的词汇,若能被置于较长时期的地域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加以理解,对建立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或许会有所启示。
从对这些词汇的历史性解释与分析入手,以则溪制度、土司制度、卫所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本文力图重构一幅黔西北地区从荒服异域到王朝“新疆”的历史图景。
关于各种制度“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遂得演进”的讨论,笔者从陈寅恪的精深研究中受益非浅。
陈先生关于唐代财政制度渐次“江南地方化”与“河西地方化”的洞见,更让笔者领悟到国家制度与地方制度之间往往难做简单的二元划分。
即便是周边族类“固有”的制度,与中央王朝的制度有时亦非全无关涉,例如有的士大夫已发现周边族类的制度和礼仪有合于先秦古礼之处,并用“礼失而求诸野”来解释。
关于黔西北地区的历史,胡庆钧、方国瑜、史继忠等学者已经做过相当深入的探讨,他们大致以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为分析架构,对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生产关系等进行了有影响力的论述。
此外,马学良、杨成志、马长寿、江应樑、刘尧汉、方国瑜、郝瑞(StevanHarrell)、樱井隆彦等中、外学者对彝族的研究同样给笔者诸多启发,本文在具体的讨论中将较多引证以上各位学者的相关成果,此不赘述。
二、基本思路
本文所讨论的黔西北区域,界临川、滇两省,包括今天贵州省的毕节地区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
该区域位于贵州省地势最高的黔西高原,崇山竣岭、峰峦起伏,地势极为险要,境内虽有六冲河、三岔河等河流,但大都源自乱山丛中,地险水浅,难通舟楫。
该区域气候高寒,山多田少,土壤贫瘠,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和马铃薯,生活贫困而又人口密集。
历史上,黔西北曾分属于乌撒()阿哲(,汉语称水西)两个彝族支系统治,由此而划分成乌撒与水西两个部分,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乌撒大致相当于毕节地区的赫章县及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
水西则包括毕节地区的大方、黔西、织金、金沙、纳雍五县以及毕节市的一部分,还有六盘水市的水城县、六枝县等。
但是,在明代崇祯三年(1630)以前,阿哲支系尚统治着鸭池河以东、三岔河以南的“水外”地区,即今天贵阳市辖下的清镇市、修文县以及安顺地区的平坝、普定等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因此,为着讨论的需要,本文有时将涉及到这些相关地域。
乌撒、水西虽属不同的彝族支系,但境土毗连,在历史上有着相似的制度与风俗,效忠元朝、归顺明朝、建立土司制度的时间也大体同步,且自清代改流后便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域,然而令笔者惊异的是,两个地区在田野调查中却呈现出种种令人深思的差异。
乌撒地区不但设有民族自治县——威宁,更重要的是还保存着彝、汉典籍中所记载的种种传统,比如家支制度、黑、白彝之分、大量布摩(彝族社会中的祭师)世家的存在等等,而水西地区并无民族自治县的设置,有些民族乡,如大方县普底彝族白族苗族自治乡的彝族甚至坦然承认自己已经彻底“汉化”,他们不识彝文,讲的是西南官话,从不穿彝装,几乎忘记了本民族的节日,行走在普底街上,完全没有身处民族自治乡的感觉。
当问起黑彝、白彝的情况时,大方县志办主任赵江先生告诉我:
“我们这里没有,你要到威宁去看。
”
因材料的缺如,笔直目前尚不能真正揭示乌撒与水西的不同发展历程。
但将两个地区视为同一区域似应首先交待。
就联系的紧密性和发展的一致性而言,水西与永宁(今四川叙永),乌撒与沾益(今云南宣威)、镇雄、芒部(今云南昭通)似乎更值得放在一起考虑。
但笔者将水西与乌撒视为一体的理由,不仅仅是它们地理相连且属于同一行政单位,也不仅仅是它们曾经有着相似的制度与风俗,笔者认为,划分学术研究的区域时不应过分拘泥于行政隶属是否相同、情况是否相类、发展是否相似等成见,而应根据问题来设定,从此角度看,乌撒与水西的相异及其对传统的更多保留,刚好提供了一个从“蛮夷”社会向“化内”社会过渡的完整序列,能够更好地回答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希望联系社会经济变迁,从制度和礼仪两个方面入手,探讨探讨周边族类走向“化内”的复杂历程。
沿着土司研究的传统,笔者将进一步厘清制度的沿革,对前人忽略或论证失当之处,尽力探讨明白,对地方社会固有的制度,力求有所揭示,至于制度变化的社会场景,更当予以展现和分析。
明代黔西北的政治制度,是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的结合,体现了蛮夷地区的制度与中央王朝的等级品官制的互动,清初这一独特的政治制度完全崩溃,流官制、里甲制取而代之,制度的嬗变开启了礼仪和意识形态演变的新方向,与这些变化相伴而来的,是经济方式的更替,人群身份的变更,“蛮夷”社会逐渐被整合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其脉络大致如下:
黔西北僻居天未,溪谷险阻,历来被视作夷蛮荒服之域。
该地族类繁多,据汉文献的记载,有黑倮倮、白倮倮、仲家、花苗、蔡家、侬家、仡佬、六额子、羿子等等,其中黑倮倮居统治地位。
这些族类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以产良马著称,至少在宋代便开始用马同内地交换物品,农作物则以荞麦为主。
黑倮倮统辖黔西北的历史相当久远,据说在三国时期便建立了国家。
首领们把辖土划分成若干个“则溪”,交给宗亲们管理,水西与水外共有十三个则溪,乌撒有九个则溪。
则溪的职能有二:
一是管兵马,二是管粮草,是一种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合而为一的制度。
在黑彝贵族的则溪制度下面,一些族类又有自己的制度,如苗族的理老寨老制、六色六巴制等。
但彝族是唯一拥有文字的族类,其传承和使用者是“布摩”与“慕史”。
前者系彝族社会中的祭师,经师,主要掌祭祀和占卜,而慕史的职能主要是在婚娶、外交等场合用朗诵、歌唱、辩论等形式宣讲历史、天文、哲学等知识。
今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已经翻译出版了大批彝文古籍,而更多的彝书尚在搜集、整理中。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黔西北或弃之不顾,或稍加羁縻,“终不能约之就法度”。
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体现在时断时续的朝贡上。
元代经过反复征讨,终于在此地设置起顺元路、乌撒军民总管府和亦溪不薛总管府等行政机构,并通过朝贡、任命职官、笼络土酋等措施进一步确立了中央的权威。
元廷还分封宗室为梁王,世镇云南,加强了对西南诸部落的控驭,乌撒因地近云南之故,可能受其影响较深。
而水西酋长阿画对元廷的效忠及其所享有的前所未有的隆恩,似亦表明元王朝羁縻政策的某种成效。
明代“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征讨与怀柔双管齐下,在没有里甲、没有科举的黔西北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以控驭诸夷,包括屯卫制度、赋役制度、土兵征调制度、朝贡制度、承袭制度、流官监控制度等,不过,在这些外来制度的包围中,黔西北的则溪制度依然卓有成效地运行着。
明王朝还注重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例如规定承袭土官必须经过国子监等机构的培训,在土司地区兴办儒学等等。
通过这些措施,明王朝对土司的羁縻更加全面而深入。
卫所的设立和移民的进入还在贵州地区移植了一种文化,这正是贵州科举的兴起以及许多地区岁时节令、风俗习惯“等同内地”的原因。
不过,朱明建国伊始,水西和乌撒便显示出了对新政权的不同态度。
早在洪武五年(1372)正月,水西首领霭翠就赴京朝贡,归顺明廷,朱元璋厚加赏赐,令其“世袭贵州宣慰使如故”。
霭翠去逝前后,其妻奢香开通川黔道路、立龙场九驿,送其子入国子监,从此水西首领兼用汉姓——安姓,并且或一年一贡,或三年一贡,恪遵定制,每有土著叛乱,更是“征剿必赖水西”。
另一方面,土司阶层倾慕诗书并接受一些正统文化观念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许多土司几乎可以称得上家学渊源,水西安氏虽然没有象水东宋氏一样诗人辈出,但是从各代土司的姓氏、名号上,从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对谪臣王阳明的尊重和礼遇上,从一些碑刻所反映出的仁和忠的观念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地方与王朝的文化价值观相互触动、并行不悖的图景。
至于安氏辖下的“水外”地区,更是“与卫人错居,近亦颇为汉俗”,“居田野者以耕织为业。
”,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相对而言,乌撒和中央一直保持着较大程度的疏离。
乌撒的内附,要等到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大张挞伐之后,并且屡服屡叛,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才改乌撒为军民土府,隶四川布政司。
迟至成化年间,其首领才采用汉姓——亦姓安,而朝贡衍期乃至缺贡等现象,时有发生。
至于奉诏征讨、学习汉文化等情况,几乎不见记载。
乌撒与水西的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水西安氏在西南地区的显赫势力以及明廷对两个地区的不同态度。
鸭池河水自南向北,将安氏的两片辖土——水西与水外连结起来,广袤千里,几占贵州行省的一半,连省城都成了土司驻地,称为“宣慰司城”。
安氏则是当时全国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被赐以“贵州宣慰使”之职,其所领族类能征惯战,素以强悍著称,周边部落往往仰其鼻息,受其号令。
可以说,水西的叛服与否,关系到明代整个贵州乃至川滇湖粤数省的安定。
正如朱元璋所说:
“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而不能守。
”因此他一度打算用十万大军平定水西,以安西南。
从此角度看,相对于乌撒,水西的效忠对明王朝或许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明王朝对水西的控驭远较乌撒严密,并且不断蚕食其土地,消解土司势力,以求改羁縻为化内。
手段方面则是恩威并施,明初朱元璋“诏霭翠位于各宣慰之上”,奢香去逝时朱元璋又遣使致祭,封其为顺德夫人,明廷还对每任土司赐予金带,至于征伐、贡献有功时,更是不吝封赏。
但羁縻政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实行土司制度目的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进行直接统治。
综观明代西南边疆史,虽然不乏土著向卫所屯地扩张的情形,但从总体上看,有明一代,改土归流的措施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其中尤以贵州的改流进程较为全面和彻底。
早在颖川侯傅友德征滇之前,朱元璋已旨令在宣慰司城(今贵阳)设立贵州卫,以后又添设贵州前卫,剥夺了安氏对该城的独占权,并且规定宣慰使必须在省城办公,无事不得擅还水西,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和监视。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廷借位居川湖交界、控扼入滇东路的田姓两大土司内斗之机,改土归流,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设八府二县,建贵州行省,直接管辖水西土司。
弘治以降,随着程番设府、迁治贵阳、新贵建县等一系列行政建置的变更,水东宋氏及安氏的水外六目地逐渐受到明廷的蚕食。
万历中期,播州改流,关于怎样处置安氏的辩论长期不断。
迨至天启初年,水西、乌撒、永宁联手起事,明王朝费百万饷银,动四省兵力,卒十年之功,终于戡定动乱,在乌撒导致了统治权力的变更,而水西安氏则被迫接受“贬秩、削水外六目”,“开毕节九驿”等条件,其势力被压缩至大方、比喇一带,水外六目地则设置了镇西、敷勇等屯卫,终明之世,变化不大。
顺治十五(1658)年清兵入黔,水西宣慰安坤归附。
五年后,吴三桂制造“安坤事件”,以安氏联络明朝旧将反清为由,率兵平定水西和乌撒,在其原有则溪制的基础上设立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是为清政府的“新疆”,而则溪制则进一步被改造成里甲制和保甲制,这意味着延续了数百年的贡赋制度被新的户籍赋役制度所取代,中央王朝与水西地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
改流后,以农耕为主导的经济方式代替了畜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经济方式(此过程在明中期已经开始),玉米、马铃薯的传入为人口的急剧增长提供了可能。
在清政府矿业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