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docx
《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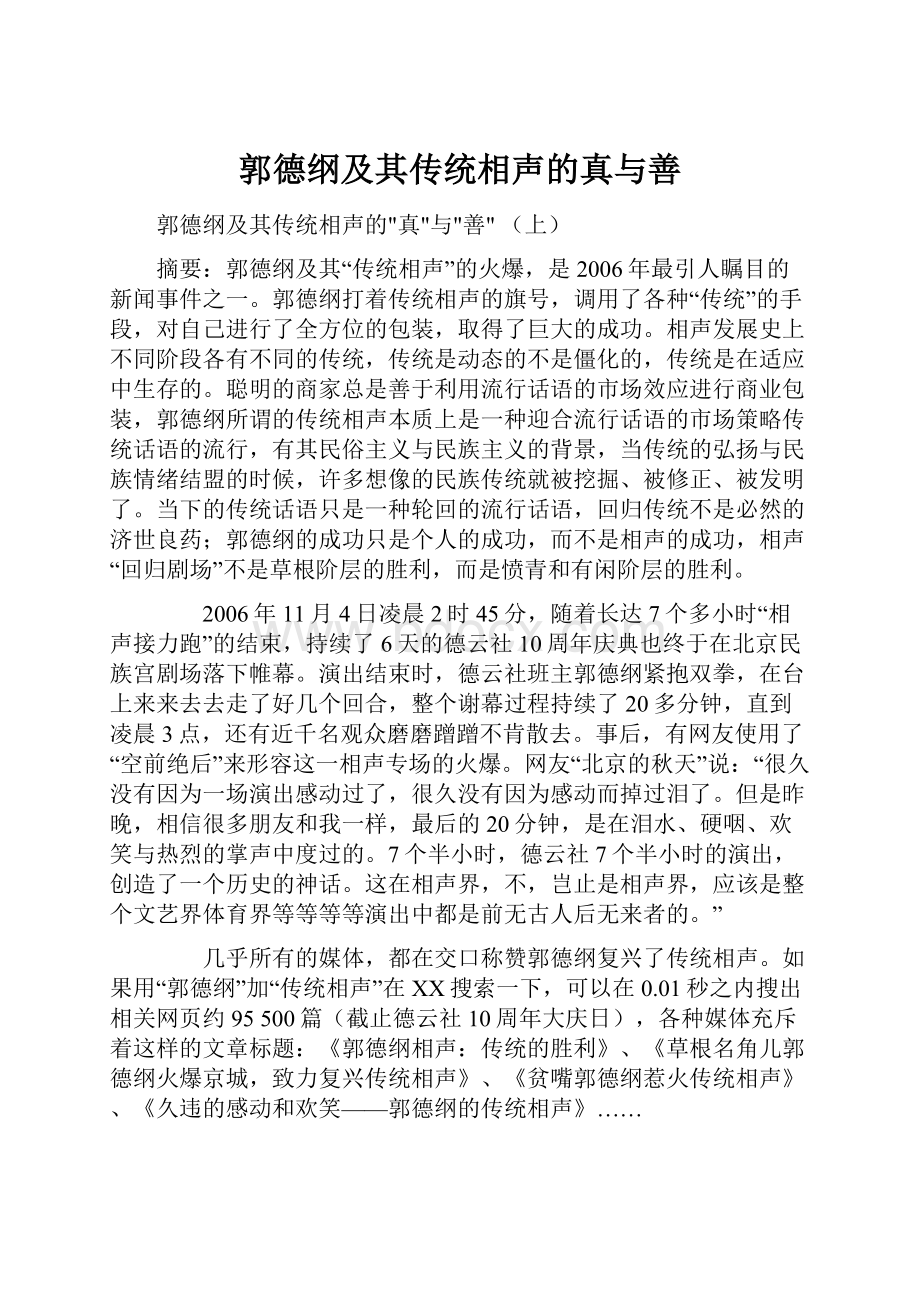
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
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上)
摘要:
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火爆,是2006年最引人瞩目的新闻事件之一。
郭德纲打着传统相声的旗号,调用了各种“传统”的手段,对自己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相声发展史上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的传统,传统是动态的不是僵化的,传统是在适应中生存的。
聪明的商家总是善于利用流行话语的市场效应进行商业包装,郭德纲所谓的传统相声本质上是一种迎合流行话语的市场策略传统话语的流行,有其民俗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背景,当传统的弘扬与民族情绪结盟的时候,许多想像的民族传统就被挖掘、被修正、被发明了。
当下的传统话语只是一种轮回的流行话语,回归传统不是必然的济世良药;郭德纲的成功只是个人的成功,而不是相声的成功,相声“回归剧场”不是草根阶层的胜利,而是愤青和有闲阶层的胜利。
2006年11月4日凌晨2时45分,随着长达7个多小时“相声接力跑”的结束,持续了6天的德云社10周年庆典也终于在北京民族宫剧场落下帷幕。
演出结束时,德云社班主郭德纲紧抱双拳,在台上来来去去走了好几个回合,整个谢幕过程持续了20多分钟,直到凌晨3点,还有近千名观众磨磨蹭蹭不肯散去。
事后,有网友使用了“空前绝后”来形容这一相声专场的火爆。
网友“北京的秋天”说:
“很久没有因为一场演出感动过了,很久没有因为感动而掉过泪了。
但是昨晚,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最后的20分钟,是在泪水、硬咽、欢笑与热烈的掌声中度过的。
7个半小时,德云社7个半小时的演出,创造了一个历史的神话。
这在相声界,不,岂止是相声界,应该是整个文艺界体育界等等等等演出中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交口称赞郭德纲复兴了传统相声。
如果用“郭德纲”加“传统相声”在XX搜索一下,可以在0.01秒之内搜出相关网页约95500篇(截止德云社10周年大庆日),各种媒体充斥着这样的文章标题:
《郭德纲相声:
传统的胜利》、《草根名角儿郭德纲火爆京城,致力复兴传统相声》、《贫嘴郭德纲惹火传统相声》、《久违的感动和欢笑——郭德纲的传统相声》……
任何存在,都是多种“必然因素”作用之下的“偶然现象”。
分析郭德纲的走红,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比如“歌颂相声”与“教育相声”等主流相声的没落,“草根文化”的崛起、审美风潮的转向、郭德纲本人的不懈努力及其相声基本功的扎实、郭德纲营销策略的成功,等等。
应该说,每一种分析都有其道理,正如一辆汽车之所以能跑起来,既使用了发动机,也使用了连动装置,还使用了轴承与车轮。
本文所讨论的是,郭德纲如何巧妙地利用“传统”这一方兴未艾的主流话语,为自己的剧场相声争取主流地位。
一、“从前”与“现在”的PK
2006年的中秋节,有一条原创自刘宗迪的“短信”在手机用户中广为流传:
中秋节了,别忘了给孩子们
讲讲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候天还是蓝的
水也是绿的
庄稼是长在地里的
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
耗子还是怕猫的
法庭是讲理的
结婚是要先谈恋爱的
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
药是可以治病的
医生是救死扶伤的……
这是一首非常漂亮的浪漫主义现代诗。
诗中先验地预设了一对“从前”和“现在”的矛盾。
“从前”是传统的、浪漫的、美丽的,而“现在”则是浮躁的、世俗的、丑陋的。
这种预设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传统”。
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不是今天才生产出来的新概念。
借助“从前”来发泄对于“现在”的不满,是从孔老夫子以来就屡试不爽的针贬时弊的重要手段。
如此推算下来,尧舜以降,人心每况愈下,社会日益恶化,一路恶化到今天,世界应该早成一堆烂泥了。
当郭德纲高举着“传统相声”这面大旗的时候,他显然使用了“颂古非今”的策略来结盟大众。
郭德纲的代表作《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有这么一段:
有人说了:
抛弃传统相声。
这就值左右开弓一千四百个大嘴巴!
(观众笑声)真的。
(观众鼓掌)
有相声大腕儿说过:
“我们宁要不完善的新,也不要完善的旧。
”这是糊涂。
无知者无畏。
由打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这么多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边能够构成包袱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摆在这了,你无论说什么笑话,这里边能给你找出来,你用的是这个方法,你用的是那个方法。
有现成的你不用,你非得抛开了,单凭你一个人,你干得过一百多年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
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好比说厨师炒菜,你可以发明新的菜,但最起码你得知道什么叫炒勺哪个叫漏勺,你拿着痰桶炒菜说是革新,那他娘的谁敢吃啊?
(观众笑声/喝彩/掌声)
这样一批无知的相声演员,无能的艺术家们,应该对今天相声尴尬的处境负最大的责任!
不是我咬牙切齿声嘶力竭,我愿意相声好!
《茶馆》里有这么句话:
“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
”我同样用这句话:
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
——我爱他,谁爱我啊?
(观众喝彩/鼓掌)
这话说得很精彩,也很有煽动性。
可是,同样这些话如果放在20年前,恐怕更多是讥讽而不是掌声。
大众的价值观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着的,在那个举国上下汹涌着改革浪潮的年代,谁要是翻唱传统的颂歌,同时还想获得满堂喝彩,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的新鲜劲己经过去,当今社会的思想潮流己经转向了对传统的怀念。
那些荒诞岁月中的陈词滥调、旋律古板的革命老歌尚且被当作时髦小曲翻唱如新,更何况传统相声这种“体现了民族文化草根性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郭德纲选择了以“传统”作为自己的营销策略。
他高举“传统”的大旗,身披“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坚韧铠甲,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英勇姿态,毅然决然地向主流相声界提出了挑战。
他以一种反主流、反权威的草根姿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源自传统的、来自民间的“正宗相声”监护人。
这一“非著名”的、“传统”的草根形象热烈地迎合了时代的主流话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借助于“从前”的号召力,郭德纲周围迅速聚集起一个庞大的“钢丝”(郭德纲fans的自称)群。
二、相声界族谱
既然要拿“从前”与“现在”进行PK,那还是从“从前”说起吧,看看“从前”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相声传统。
许多学者考证相声乃是由宋代“像生”发展而来,经历了“像生—像声—相声”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些学者则因为宋代前己经有了些许曲艺表演,因而“把唐代与六代都归入相声的萌芽期”;还有些学者追得更远,认为相声源自于东汉时期具有诙谐调笑性质的“偶语”。
这种无边界的溯源考证大多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可以滥用这种“相关性”作为学术溯源的出发点,我还可以把相声起源追溯到人类开始张口说话的史前社会,这比前述学者的考证结果都要早得多。
如果相声史真有如学者们所说的那么久远,从汉唐的长安到两宋的开封和杭州,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和辐射,相声早该流播全国了。
可事实上,直到民国结束,相声艺人的主要活动领域只是在京津两地的下层集市。
其他城市如南京、济南、重庆等地,个别娱乐场所零星有相声表演,表演者也大都是从北京天桥流落出去的相声艺人。
正是因为市场太小、圈子太小,所以竞争特别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而更需要严格的行业潜规则,由此显得相声行业的江湖气特别重。
相声界把东方朔尊为自己的祖师爷,并以祖师爷的名义互相约束。
“解放前的相声界对师承辈份非常看重,没有拜过师的演员在行内被叫做‘海青’,这和梨园界里不允许没有正式师承的演员搭班唱戏是一样的。
解放后,曲艺行经历了诸多变革,但拜师收徒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下来,甚至还有不少‘组织上’安排拜师收徒的先例。
”
侯宝林以降的相声演员们,作为党和政府的艺术家,都很忌讳在公众场合流露业内的江湖气息;而郭德纲则以“传统”和“草根性”为标榜,所以他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处处表现其特“爷们”的江湖气,说起自己的学生时,张口闭口称“孩子”,对上则一律以“爷”以“奶”来称呼,至于砸挂(取笑)同行、当着空码儿(外行)湍春(说行话),那更是家常便饭。
京津两地相声界,上上下下几乎全部笼罩在门派和师承的关系网络之中。
我们可以随机抽取若干相声大腕,看看他们的师承关系(名字后的数字为辈数):
(1)郭德纲7—侯耀文6—赵宝琛5—焦寿海4—范瑞亭3—富有根2—朱绍文1。
(或:
郭德纲7—杨志刚6—白全福5—于俊波4—焦德海3—徐有禄2—朱绍文1)。
(2)姜昆、冯巩、笑林7—马季6—侯宝林5—朱阔泉4—焦德海3—徐有禄2—朱绍文1。
(3)巩汉林7—唐杰忠6—刘宝瑞5—张寿臣4—焦德海3—徐有禄2—朱绍文1
(4)李金斗7—赵振铎6—王长发5—赵霭如4—卢德俊3—徐有禄2—朱绍文1。
(5)牛群6—常宝华5—马三立4—周德山3—范有缘2—朱绍文1。
可以看出,当今相声界各色红人,无论风格如何各异,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追溯到朱绍文这个习惯被人称作“穷不怕”的相声大师门下。
朱绍文是半路出家,在从事相声这一行业之前,并没有上承前辈的技艺。
据说与朱绍文同时还有阿彦涛、沈春和两人与朱齐名,但这两人也是朱绍文的“代拉师弟”,与朱绍文名为兄弟,实为师徒。
由此可见,朱绍文就是相声界的开山祖师。
不管朱绍文前面有过多少相声艺人,也不管那些艺人有过什么天才的创造,他们既没有留下任何文本,也没有留下任何传人,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己经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大漠之中了。
有,也等于无。
如果我们把相声发展史看作一条长河,那么,即使从前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河(如传说中的张三禄之流),河水到了朱绍文这里也己经断流了。
现在的河水,正是朱绍文这口泉眼里流出来的。
传统只能从朱绍文开始谈起。
三、传统的源头
朱绍文(一说朱少文)生平没有正史记载,全凭口口相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前朱绍文时代有没有相声表演活动,但至少没有成为一个行业。
传说朱绍文(约1829—1903)祖籍浙江,幼年曾学唱京剧丑角,后来改为架子花脸,擅长编写武戏,主要靠演戏、教戏维持生计,走上相声表演这条道路也是事出偶然。
一说因为咸丰皇帝去世,曾勒令天下100天内不许演戏、动乐,戏园子关了门,朱绍文生活无着,就来到天桥一带撂地卖艺,改演剧为说唱滑稽故事。
一说因为朱绍文唱京剧时喜欢自作主张,加添一些台词,虽然很得观众喝彩,但受到了同行的排挤,因愤而改行,卖艺于长安市上。
天桥是当时一个繁华的平民市场,三教九流云集。
朱绍文随身只带一把笤帚、一副竹板、一袋白沙。
他用白沙往地上撒出几个数尺大字,以此占领地盘。
一边撒字一边唱着太平歌词,一切科浑笑话也均由字义上生发,令人拍案叫绝。
如此逐渐吸引听众,看看人差不多了,便开始讲古论今,嬉笑怒骂,直到甩出几个响亮的“包袱”,才在观众的笑声中伸手要钱。
朱绍文最早是自说自唱,后来收了徒弟就开始搞点配合,两人一捧一逗,互相问答,逐渐演变成今天常见的对口相声。
传说朱绍文因为相声说得好,得到恭亲王奕诉的召见,“恭亲王十分赞赏,拨给他一份钱粮。
蒙古族罗王也很赏识朱绍文的技艺,聘他每天进王府献艺,按月发给钱粮。
后来,朱绍文用积蓄买了房屋,定居在地安门外毡子房”。
草根艺人一旦领上了国家工资,就等于从精神上被招安了。
再后来,传说朱绍文领着一班天桥艺人,在慈禧太后的60岁寿辰上紧做文章。
慈禧太后一时高兴,信口封了他们一个“天桥八大怪”的名头。
这班草根艺人得此口彩欣喜若狂,把慈禧的一句随口的玩笑话当作了无上荣耀,成天挂在嘴上,代代相传。
借助统治者以获取话语权力,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避免的俗套。
朱绍文和他的追随者当然也不例外。
也许“慈禧之封”只是一段虚构的“传闻”,无论是真是假,这些草根艺人借助了慈禧之封的传说,以哄抬自己的行业身份是无疑的。
据相声界内部传说,作为主事者,朱绍文得了一个“天桥八大怪之首”的名头(其他行业的天桥艺人一般不会把朱排在首位)。
这一传说大大地提升了朱绍文的江湖地位,为他建立相声行业奠定了必要的话语权威。
有关朱绍文的传说也许本来只是一种行业内部的、有目的的、“类型化”的虚拟叙事,但是,通过把传说附会在朱绍文这样一个真实的“专名”之上,传说的真实性就通过专名的使用而形成业内的普遍认知。
朱绍文之后,据说还曾有一对以“怪”著称的“老少万人迷”。
老万人迷李广义,据说长相丑陋怪异,表演时喜欢惟妙惟肖地摹拟妇女纳鞋、贴饼子、抱孩子以及梳头、洗脸、擦脂粉等日常生活的动作,能说会唱,有点类似今天的赵本山。
其孙小万人迷李德钖的名气更大,甚至被有些相声艺人称作“空前绝后的宗师”。
此外,以口技著称的早期相声艺人则有“百鸟张”和“人人乐”,他们都很擅长摹拟各种声音,口技卓绝。
1949年以前,相声界人数少,影响也不大,极少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
今天意义上的“相声”一词,是到1908年才偶一闪现在英敛之的《也是集续编》中:
北京供人消遣之杂技,如昆戈两腔,西皮二簧,说评书,唱时调种种之外,更有一种名曰相声者,实滑稽传中特别人才也。
其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声,摹拟仿效,加以讥评,以供笑乐,此所谓相声也。
英敛之无疑是把相声当作罕见的新鲜事物来介绍的,由此可见相声的知名度之低。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京津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人知道还有一门叫做相声的曲艺种类。
据赵景深回忆:
“解放前我在编《俗文学》和《通俗文学》时,所收到的稿件,涉及相声史的几乎没有。
尽管有同道研究弹词、大鼓、子弟书、宝卷、单弦……但是,没有一个人,一篇文章是研究相声的。
”
四、传统的涅槃
早期的相声艺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低层艺人,他们撂地卖艺的谋生方式决定了相声的文明层次。
为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相声艺人的穿戴言行往往以“搞怪”为胜,表演时常常骂大街、说下流段子、拿乱伦说事、嘲笑农民和外地人,甚至当众脱裤子,什么都有。
有时为了收取银钱,艺人们咒骂听众:
“您若看完扭脸就走,给人群撞个大窟窿,拆了我的生意,那可是奔丧心急,想抢孝帽子戴。
”
因为荤腥话太多,解放前的相声一般是没有妇女听的。
相声几乎就是“低级趣味”的代名词。
“至40年代末,由于曲目质量的低劣加之艺人在台上常信口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言语,致使学校向学生宣布禁听相声,相声居然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
1949年,曾有一批相声艺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他们的相声主要是说给大陆赴台的军人听。
1950年代,一些艺人曾经试图通过广播和娱乐场所把相声推向民间,但是很不成功。
1960年代以后,相声艺人纷纷转行,到1980年代初,台湾基本己经没有相声了。
可见,在新的历史地理环境下,传统不经涅槃,便成了死亡的传统。
那么,大陆的相声又是如何在1950年代摇身一变为红遍全国、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曲种呢?
这里而当然有政治的原因。
1949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低层技艺自然也就升格为“人民艺术”,这是大前提。
另外,还得从老舍和侯宝林说起。
1949年底,“低级趣味”的相声能否适应“人民艺术”的要求,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这时,老舍从美国回来了。
侯宝林、侯一尘等人打听到老舍住在北京饭店,马上就邀约一批有志于相声改革的艺人前往拜会。
老舍给了他们很大的精神鼓励,建议“把骂大街、贫嘴废话去掉,加上些新内容、新知识,既有教育意义,还有笑料,大家照样受欢迎”。
老舍是个北京通,从小就爱听相声,有时还偶尔客串,在朋友圈中表演一下。
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改本子”的任务,带动了其他一批知名教授和文化人加入到相声改革的行列中来。
侯宝林等人大受鼓舞,立即结伙成立了一个“相声改进小组”,抛弃了“下九流”的自卑心理,反复强化“人民演员”的身份认同,每天用一个小时进行识字等扫盲学习,切磋技艺。
同时成立“相声大会”,保障收入,边演边学。
他们以老舍为号召,主动迎合政治需求,进行改旧编新,取得很好的效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机关、团体、学校等纷纷邀请他们演出。
1952年,侯宝林等人又提议成立了“北京市曲艺工作团”。
他们为了扩大影响、改变形象,接收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年轻艺员,并向各书店接洽出版相声集子,积极加入到政府的各项宣传活动中,频频曝光于各主流媒体。
在老舍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界的鼓吹下,几年之间,相声表演就己经渗透到了全国各地,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曲艺种类,并孽生了一大批业余的相声队伍。
相声传统在1950年代得以涅槃。
这一时期,老舍是相声界的精神领袖,而侯宝林则是一位出色的经营大师,涅槃新生的领头人。
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中)五、传统的转型
早期相声是综艺型曲艺种类,大部分艺人都是从别的行业转行进入相声界。
艺人们出身不一,身份驳杂,各自的喜好与绝活也大相径庭,他们传下来的相声形式也就很不一样,有人擅长身体表演,有人擅长口技,有人擅长弹唱,有人擅长逗哏搞笑,没有统一的演出标准。
1951年,老舍在《谈相声的改造》中,把他在民国时期听过的相声分成了四类:
1.贯活类,即一口气说完的长段子。
2.口技类,即表现艺人口技特长的段子。
3.书史类,即利用书史改编的段子。
4.逗笑类,即纯粹逗笑的段子。
1963年,根据新的形势,老舍在一次相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相声分成了五类:
1.纯粹逗哏的。
2.纯粹技巧表演的。
3.讽刺相声。
4.歌颂相声。
5.化装相声。
“歌颂相声”此时还处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在一些年轻演员的新段子中,而且还曾受到一些老艺人的反对。
1960年代把歌颂相声推向高潮并使之成为相声主流,马季功莫大焉。
马季是典型的新中国新艺员,他是从业余相声起步的,1956年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在侯宝林等人的指导下进入专业领域。
马季聪明、文化水平高、觉悟也高。
相对于那些民国时期的老艺人,马季具有更强的理论和创作水平。
他创作和演出了大量的歌颂相声,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时代英雄人物为主题的相声新局面。
老舍是鼓励马季扬长避短、改革创新的,他这样说马季:
“在业务上,我们希望他勤学苦练,更结实一些。
比如说:
侯宝林先生在相声段子中学唱的京戏与地方戏,不仅照样儿唱出来,而且极有韵味。
他对戏曲下功夫钻研过,能够入弦上板。
我不知道马季下过这么大的功夫没有。
他若是仅以摹仿侯老师为能事,那就不易青出于蓝,超过老师去。
”
当相声以讽刺作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时候,只能用来抨击旧社会旧思想,或者表现小市民生活,谁也不敢用它来讽刺新社会新思想,因而其表现生活的面就受到了限制,与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与期望一也有一定的距离。
马季歌颂相声的出现,适逢其时,很好地迎合了这种要求与期望。
歌颂相声一旦在争议中站稳脚跟,迅速全面介入“社会主义新生活”,并逐渐占据相声主流成为社会主义相声的新传统。
从1960年开始,侯宝林、马季等人先后到中南海紫光阁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说了数百段相声。
国家领导的肯定和赞赏,极大地刺激了相声艺术在1960年代的大发展。
同时赋予了相声更大的社会责任。
继歌颂相声之后,“教育相声”应时而生。
周恩来就曾亲自要求马季创作一部相声,教育那些在球场内不守秩序和纪律的不文明观众,在比赛前播放。
1960年代,普通观众的文化水平非常有限,受教育渠道少,借助相声这种通俗的文艺手段来教育民众,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毋需论证。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相声又被定位为人民艺术,人民艺术自然要反映直接的人民思想,所以相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自然会比别的艺术形态更直接。
虽然1980年代的新相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也曾一度获得过观众的喜爱,但是电子传媒时代的相声己经身不由己了,它要接受来自另一电子终端的种种意识形态的监督。
相声适应性地变得淡乎寡味了。
相对于当年侯宝林时代的危机,现在的相声不是太“俗”,而是太“雅”。
到郭德纲学成出道的时候,正碰上相声再次陷入低谷。
他多郁闷呀,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学成出道,相声却没有人要了!
所以郭德纲把相声中的“歌颂”和“教育”当成了扼杀相声的罪魁祸首,他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义愤填膺地说道:
非得让相声教育人?
非得每段都有教育意义?
我不服!
知道么?
(观众喝彩/掌声)让人受教育的形式太多了!
放了相声吧!
饶了它吧!
它也没害任何人,就让它给大伙带来点快乐,我觉得很好啦己经!
不用这么苛求。
是不是?
六、“英雄叙事传统”中的郭德纲自传
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方显英雄本色,此所谓乱世出英雄。
相声的再度低迷为成就郭德纲的英雄事业提供了契机。
英雄形象该如何塑造呢?
金庸常常借用史诗英雄的叙事模式,按“特异诞生—苦难童年—名师授业—迅速成长—得到神奇助手—成功求婚—血洗冤仇—建功立业”的程序来安排英雄命运。
郭德纲也是这样做的。
郭德纲自传体小说《我叫郭德纲》中,那个少年郭德纲的成长模式,活脱脱就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英雄少年,除了缺少“成功求婚”的环节,其余叙述从情节结构到场景设置、人际关系、江湖守则,基本遵循着英雄命运的程式。
为了更彻底地把自己描绘成“草根英雄”,与英雄传统做到无缝接轨,郭德纲在自传中不厌其烦地细细诉说着自己打少年以来,如何在传统的氛围中“历经寒暑,洒尽汗水,尝尽个中滋味,复辗转于梨园,工文丑、工铜锤”,如何在天津各曲艺领域遍访名师尽得所长,如何拜把子认干亲,如何遭逢陷害失败受挫,如何发奋图强坚持不懈,最终六国封相大获成功。
郭德纲在自传写作中,有意识地选择使用了旧式交际话语,在旧式人际关系模式中叙述自己的学艺生涯。
比如,他这样描绘自己的学徒生活:
每天一般是这样,早上先买张报纸带去,进门时伺候老爷子起床,倒痰桶收拾屋子,给老爷子沏茶,一切忙完了,就要说活了。
本来是学评书,可第一段先学的是相声《五行诗》,这也许就注定了我早晚要说相声。
老爷子说是用《五行诗》来给我砸基础,说身上动作。
整个活里各种人物可不少,岳飞岳云吕布貂禅董卓西门庆武大郎……为《五行诗》我可受了罪了,比划金锤时一手一个酒瓶子,金枪是用毛巾捋,学董卓撩袍时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唉,那是夏天啊。
艰难的少年时代之后,是辛酸的江湖阅历。
郭德纲描绘自己在北京的潦倒经历时说,有一天剧场散了夜场,没赶上公共汽车,又没钱打车,只好从木樨园步行回大兴:
走到西红门的时候,哎呀,那个黑呀,桥底下也黑,当时的大桥光走车不走人。
还不能往下边走——都是大车,万一把你撞死呢?
只能扶着栏杆在边上走,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就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自己念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当时觉,这是好事儿,这是日后我吹嘘的资本啊。
对这段历史郭德纲曾经自咏为“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我们知道,直到1980年代,港台的娱乐业都还在沿用这种“苦难叙事’,进行造星运动。
其实,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多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郭德纲需要吸引的,并不是那些真正了解传统的、有过更苦难阅历的老男人。
这种英雄叙事传统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
无数钢丝的同情和悲怆在阅读中被唤醒,引发强烈的共鸣。
他们用激烈的言辞在博客的跟贴中对郭德纲表示了自己的敬仰、爱慕,为郭德纲的遭遇抱不平,甚至对他表忠心。
一位自称爱上了郭德纲的女钢丝说:
“郭德纲的走红,他的相声,他的功力,只是一部分因素,更多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胆识和勇气,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路,不屈服,不馅媚,不虚伪,不放弃。
”
更为夸张的是,郭德纲居然使用了“圣诞叙事”的传统来进行自我包装。
中国是个谶纬神话非常发达的国家。
在圣诞叙事中,大凡伟人出世,总是会有神异降临以为先兆。
比如《拾遗记》记载“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亘天而下,来附微在之房,因而生夫子。
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来,以沐浴微在”。
《史记》记载刘邦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刘邦出世之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
《我叫郭德纲》则是这样描绘郭德纲神奇出生的:
据说出生之前父亲曾做了两个梦,一个是梦见父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