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制与解放之间.docx
《法律规制与解放之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法律规制与解放之间.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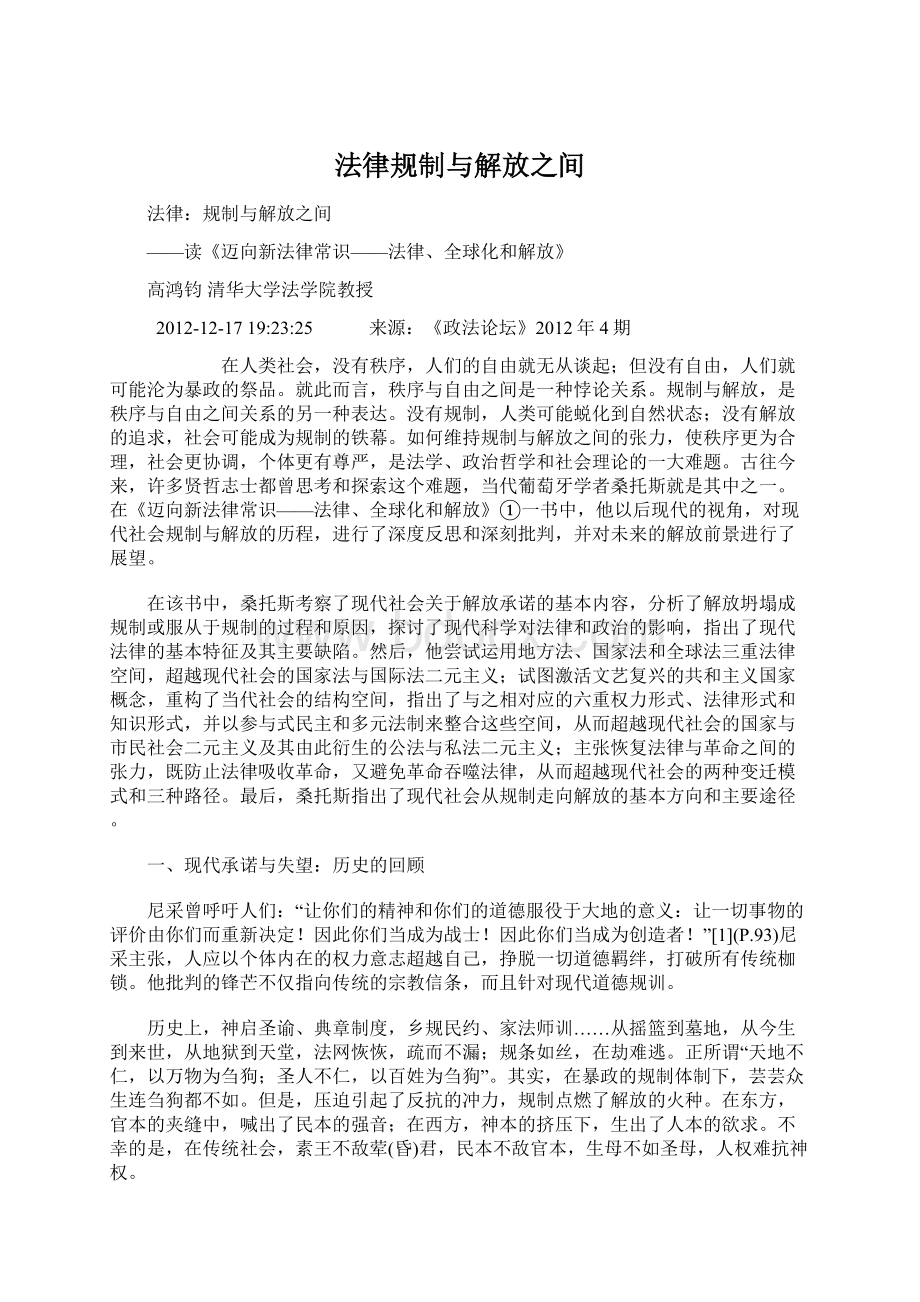
法律规制与解放之间
法律:
规制与解放之间
——读《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
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2-12-1719:
23:
25 来源:
《政法论坛》2012年4期
在人类社会,没有秩序,人们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但没有自由,人们就可能沦为暴政的祭品。
就此而言,秩序与自由之间是一种悖论关系。
规制与解放,是秩序与自由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表达。
没有规制,人类可能蜕化到自然状态;没有解放的追求,社会可能成为规制的铁幕。
如何维持规制与解放之间的张力,使秩序更为合理,社会更协调,个体更有尊严,是法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一大难题。
古往今来,许多贤哲志士都曾思考和探索这个难题,当代葡萄牙学者桑托斯就是其中之一。
在《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①一书中,他以后现代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规制与解放的历程,进行了深度反思和深刻批判,并对未来的解放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该书中,桑托斯考察了现代社会关于解放承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解放坍塌成规制或服从于规制的过程和原因,探讨了现代科学对法律和政治的影响,指出了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缺陷。
然后,他尝试运用地方法、国家法和全球法三重法律空间,超越现代社会的国家法与国际法二元主义;试图激活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国家概念,重构了当代社会的结构空间,指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六重权力形式、法律形式和知识形式,并以参与式民主和多元法制来整合这些空间,从而超越现代社会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主义及其由此衍生的公法与私法二元主义;主张恢复法律与革命之间的张力,既防止法律吸收革命,又避免革命吞噬法律,从而超越现代社会的两种变迁模式和三种路径。
最后,桑托斯指出了现代社会从规制走向解放的基本方向和主要途径。
一、现代承诺与失望:
历史的回顾
尼采曾呼吁人们:
“让你们的精神和你们的道德服役于大地的意义:
让一切事物的评价由你们而重新决定!
因此你们当成为战士!
因此你们当成为创造者!
”[1](P.93)尼采主张,人应以个体内在的权力意志超越自己,挣脱一切道德羁绊,打破所有传统枷锁。
他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传统的宗教信条,而且针对现代道德规训。
历史上,神启圣谕、典章制度,乡规民约、家法师训……从摇篮到墓地,从今生到来世,从地狱到天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规条如丝,在劫难逃。
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其实,在暴政的规制体制下,芸芸众生连刍狗都不如。
但是,压迫引起了反抗的冲力,规制点燃了解放的火种。
在东方,官本的夹缝中,喊出了民本的强音;在西方,神本的挤压下,生出了人本的欲求。
不幸的是,在传统社会,素王不敌荤(昏)君,民本不敌官本,生母不如圣母,人权难抗神权。
西方的文艺复兴,吹响了现代解放的多重号角。
人们不再敬畏神性、屈从权威和压制欲望,而开始张扬人性之力,主张民主之治,讴歌肉体之美,顺应欲望之需。
随后,现代社会带着四项解放承诺隆重登场:
平等、自由、和平与控制自然[2](P.9-11)。
为了实现这些美好的承诺,现代解放的三大支柱,也就是韦伯所概括的三大理性逻辑,随即得以确立:
科学和技术的认知工具理性,伦理和法律的道德实践理性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表现理性[2](P.4)。
在现代性的三大支柱中,理性成为统驭一切的源代码,而科技理性成为了万流归宗的新上帝。
政治科学化与理性化,虽然获得了新的正当性基础,却打造出科技官僚的铁笼,致使政府变成了衙门,选举变成了选主,公仆变成了主人;法律科学化和理性化,虽然增加了确定性,却结出了法律形式主义的苦果,法律运作无视内在精神和情境差异;生活世界科学化和理性化,虽然祛除了各种灵魅、斩断了家族羁绊,却导致了目的理性宰制生活常识,生产范式统驭生活范式,效率、权力和金钱奴役心性;文学艺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虽然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和御用的宿命,却陷入了标准化和形式化的误区,艺术的个性化、多元性和想象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简言之,科技理性主宰的现代化,并没有兑现原初承诺。
特权制不平等变成了契约式不平等,尽管后者具有形式平等的外观;集权制不自由变成了分散式不自由,尽管后者具有个人选择的面向。
现代化没有带来和平,科技理性却为军备竞赛和世界大战推波助澜。
现代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主要目的并非合理利用自然,摆脱宿命,而是为了更强有力地征服和控制同类。
人类对于由此而带来的全球性生态风险和自然灾难,或者无暇顾及,或者由于人类控制自然能力过度而预见此种后果的能力不足,结果是“现代科学并没有根除与前现代性相关联的风险,没有消除不透明性、暴力和无知,而是以一种超越现代的形式重新创造了它们”[2](P.13)。
桑托斯认为,为了兑现现代的解放承诺,西方现代的政治哲学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探索现代秩序的基本原则。
在各种关于现代秩序原则的学说中,三种秩序原则成为了主导范式,它们是国家原则、共同体原则和市场原则。
在上述三种秩序原则中,第一种秩序原则的设计师是霍布斯,代码是秩序,基础是政府与人民之约,区分是战争/和平,要旨是人权完全服从主权,核心是国家;第二种秩序原则的设计师是卢梭,代码是平等,区分是平等/特权,基础是人民之约,要旨是人权与主权同构,核心是共同体;第三种范式的设计师是洛克,代码是自由,区分是自由/专制,基础是人民之约和政府与人民之约,要旨是一般人权转让给政府,基本人权公民保留,核心是市场。
桑托斯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的不同时期,上述秩序原则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之相应,社会基本结构、民主和法律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价值取向[2](P.36-48)。
桑托斯认为,现代社会源自西方,恰与资本主义相耦合。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和去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
它们大体对应于自由放任时期、福利国家时期以及后福利国家或新自由主义时期。
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为了放任自由和强化竞争,主导秩序原则是市场原则,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
民主以代议制为特色,完全服从于市场的需要。
法律的特征是科学化和实证化,从而具有了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的气质;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法律主要维护消极自由。
这个阶段的结局是解放坍塌成规制。
在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控市场,矫正社会不平等,防止社会冲突演变成阶级冲突,政府出场进行干预,因而主导范式是市场原则与国家原则并驾齐驱。
在社会结构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线开始弥合。
民主扩大了参与范围,工人阶级开始参与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福利制度的实施减少了社会不平等,缓和了阶级冲突;法律的实质化打破了公法与私法的严格界域,法律的能动主义占据上风,由此导致了法律的再政治化。
这一时期,虽然共同体原则得到了加强,但其仍然服从于市场和国家的控制;法律的政治性虽然得到了重新确认,但这种政治性源自政府的导控,缺乏民主的基础;工人阶级的民主虽然得到加强,但仍然服从于资本主义体制。
从总体上看,在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重启了解放之维,但远不是解放与规制的真正结合与良性互动,而是“解放事业对于规制事业的完全服从”[2](P.75)。
在第三个阶段,由于福利国家模式导致了国家原则与市场原则相冲突,行政权的膨胀带来了新专制主义的危险,实质化和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的法律,带有家长主义的气质,其合法性严重不足。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便开始转向。
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市场原则具有了主导地位,国家原则相对弱化。
去规制化、私有化和契约化意味着,国家从市场和社会中抽身而退,国家与市民社会再度分离,公法与私法之间再次划界,民主受到市场大潮的冲击。
这似乎是对第一阶段的回归,但与其有诸多区别。
第一,这个阶段与全球化相耦合,因而强化市场原则和弱化国家原则,对于处在世界体系不同位置的各国,明显具有不同的后果:
核心国家原本国家权力十分强大,这对它们来说不过是“胖人减肥”;而对于某些控制能力本来就很弱的边缘国家来说,这几乎意味着“瘦人减肥”,对秩序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弱化,乃至失序。
第二,在法律上,这个阶段是司法主导的法治,核心国家把这种司法治理模式予以全球化。
第三,这个阶段全球化的去规制化,导致了全球化的竞争失序;对于跨国公司等全球性组织,国家法鞭长莫及,而国家或全球治理的管制措施也显得软弱无力。
因而,这个阶段的危险是规制面临坍塌之险。
一旦失序,解放与规制就会双重瓦解,同归于尽[2](P.75)。
桑托斯认为,在上述三个阶段,现代解放的承诺之所以没有得到兑现,主要原因有三个。
(1)科学主义的泛化及其早期科学范式的自身存有缺陷。
在他看来,国家科学化和法律科学化,导致了对共同体经验常识的排斥,而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及其规律中无法推导和建构出正当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同时,现代早期的以确定性和线性为特征的科学范式,不具有普适性,当代科学的发展揭示出与之相反的一些现象和法则。
(2)国家主义及其国家法霸权。
桑托斯认为,国家主义是对现代社会复杂结构的化约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因为在现代国家之上,一直存在世界体系,在国家之下,始终存在其他权力结构。
因此,国家主义及其法律霸权是对其他权力结构的排斥,其结果是国家失去了同其他权力结构维持互动和互补的机会。
同样,法律的国家化,导致了国家法的独占和霸权,由此排斥了实际存在的其他法律形式,也失去了与它们保持互动和互补的机会。
国家巨无霸为市场保驾护航,但对于社会共同体,则挥动着主权的“金箍棒”,系起法律的“混天绫”,征服了不同社群,宰制了生活世界。
由此,个体的心性成了国家理性的祭品,日常生活成了国家意志专政的对象,经验常识成了国家科技横扫的尘埃,社群精神成了国家学说占领的阵地,民歌乡曲成为了国家颂辞传播的载体。
(3)现代社会除了过分科学化之外,还过分市场化。
过分市场化导致了经济主宰政治,效率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平等变成了平等的经济博弈,自由变成了自由的策略设局。
相形之下,民主则显得势单力薄,人权感到声音微弱。
至于正义,只能在诗性的愤怒和侠士的壮举中,偶尔灵光一现,几如天上的流星;而美德也似久旱中的几滴甘雨,不过是道德世界的一剂心灵鸡汤。
②
在桑托斯看来,凡此种种都似乎表明,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把人对人的统治,转成人对物的管理,从而带来人性的解放,而是强化了人对人的控制,甚至导致了物对人的支配。
市场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而是把人类带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代议制民主没有实现公民当家作主,而是公民定期选主,然后由精英为民做主。
法律没有带来公平正义,而是成为自由市场博弈之则,官僚体制运转之器,以及政治国家驭民之具。
一言以蔽之,现代化的最初承诺并没有兑现,解放的理想坍塌成规制的现实。
毫无疑问,桑托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颇具冲击力。
但他显然忽略了以下几点:
人文主义对现代性的期许过高,解放的承诺在短期内无法完全兑现;现代科学对于人类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的改进,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市场也具有积极效应,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增加了消费者选择的空间;现代国家的统一和主权至上,有助于维护国内秩序和整合复杂的社会结构;现代法律对于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
简言之,在秩序与自由的冲突中,在规制与解放的张力中,他忽视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自由与解放的成就。
二、超越法的现代性:
三重法律空间与六种法律形式
自从世界时间统一于西方时间,全球的“空间脱域”[3](P.4-32)就成为这种共时性的结果之一。
由此,任何一阵地方“蛛丝”的微动,都会引起全球“蛛网”的共振;羁縻已久的物欲一旦释放出来,以市场为动力的经济就挣脱了宗教之神、道德之网和政治之缰的束缚,“脱嵌”而出,由此,“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4](P.65)。
它不惟凌驾于社群之上,甚至绑架了国家,疯狂扩张,必欲把全球建构成“市场帝国”。
然而,只有民族国家模式开始转型,冷战格局走向终结,经济全球化才真正吹响了“集结号”。
经济全球化摧枯拉朽,席卷世界。
跨国商人与本土强权联手,把“羊吃人”巧妙地升级到“厂吃人”和“房吃人”的版本。
在金钱的威力下,山楂树变成了摇钱树,投名状披上了黄金甲,“鸡的屁”胜过鸡的蛋,华尔街压倒了华盛顿。
男方女方,非诚勿扰,不过是现场交易的“甲方乙方”;搜狐搜狗,没完没了,不过是网上猎获“金姬银姬”。
全球化骤然降临,核心国家欢呼“千年王国”的到来,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向世界宣布“历史的终结”的“福音”。
边缘族群则作为被共识者纷纷签约,由此告别了自然状态,告别了乡土伊甸园,成为了市民社会的新盲流,都市红灯区老流氓的后备役。
边缘国家的动物也纷纷失去栖息之地,在文明与不满的冲突中,住进了人类社会的动物庄园。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法的独霸局面已受到严厉挑战,国家之上的跨国法和全球法开始形成,而国家之下的地方法或社群法重新发力,并溢出国界而在全球之网上发出声音,产生共鸣。
在桑托斯看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多元主义时代已然到来。
然而,法律全球化并不是自由的序曲和解放的福音:
无论是全球化的地方主义,还是地方化的全球主义,都是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无论是高强度的法律全球化还是低强度的法律全球化,都近乎全球法律的美国化。
各国法律在全球的地位,取决于本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边缘国家是全球法律的输入者,核心国家是全球法律的输出者,而半边缘国家则介乎两者之间。
一个国家法律现代化的路径以及该法在法系上的归属,也决定其在法律全球化中的位置。
由此说来,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发展,再次面临着现代之初的命运,只是被迫接受西方法律的情势有所改变:
殖民化的强迫接受变成了全球化的被动移植。
当然,与殖民化时代不同,新一轮法律全球化发生了重大变化:
持枪军人换成了持股商人,老牌传教士换成了新式律师,主宰者由欧洲的专制“教皇”,变成了美国的自由“女神”。
然而,这个过程开始不久,就出现西方所始料未及的吊诡,第三世界以举国之力打造国际都市,崛地而起的七星大厦和一望无际的世纪大道,成为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风景线,使老牌世界帝国的白宫和红场相形见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核心国家首都的流浪人群和“占领”大军,如同大观园里的刘姥姥,成为嵌在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流动景观[2](第3、5章)。
桑托斯认为,国家法与国际法的二元划分,是对真实“世界地图”的扭曲。
当代世界存在三重法律空间,即地方法、国家法和全球法。
不幸的是,国家法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唯一之法,而国际法不过作为国家法在领土以外的延伸。
针对晚近全球法的发展,桑托斯指出了七种主要类型,并分析了它们特征。
它们是:
(1)民族国家治理的全球法;
(2)以欧盟法为典型的跨国法;(3)伴随资本全球化和跨国公司而形成的新商人法;(4)由于移民全球化而产生的移民法;(5)经历殖民统治历史的原住民法;(6)以国际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次级世界主义(subalterncosmopolitanism)之法;(7)全球公域中生长出的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人类法。
在他看来,上述七种全球法中,判断其是属于霸权主义的全球法还是反霸权主义的全球法,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看它们的形成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二是看它们所代表的利益是核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是压迫者和排斥者还是被压迫者和被排斥者,以及是局部统治集团还是全人类。
[2](第5章)他对于全球法的考察和分析,全面、系统、敏锐并富有洞见。
桑托斯反霸权主义的立场,维护世界弱者权益的情怀,以及追求解放的世界主义精神,贯穿于他著作的字里行间。
桑托斯还主张,在现代社会和法律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应承认三重法律空间,而且应使它们互动,激活不同法律空间中的解放因素,抵制和反转其中的规制因素。
他把“帕萨嘎达法”作为地方法的理想类型,与作为国家法典型的城市“柏油法”形成鲜明对照。
“帕萨嘎达法”是城市贫民区之法,代表的是受压迫者和受排斥者的利益,其中包含着法律中的解放因素。
桑托斯回顾了西方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历程。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法治的范式分别是立法主导模式、行政主导模式和司法主导模式。
他承认,司法主导的治理模式具有许多优势,例如有助于把纠纷的解决个别化、分散化和程序化,有助于化解政治对抗和阶级冲突;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有助于超越道德和伦理的价值之争;有助于冷却社会公众的情绪。
司法治理的基本逻辑是社会问题权利化,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司法化,司法问题程序化。
在他看来,这种“司法共和国”[2](P.393)的司法治理进路,虽然有助于人权的宪法化和宪法的司法化,但对于追求解放的目标而言,则远远不够,因而“并不优先考虑司法斗争”[2](P.23)。
因为这种法治模式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仍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二元主义的产物,仍遵循法律去政治化的进路,仍没有把法律置于充分的民主基础之上。
此外,这种模式仅仅承认一维结构空间,即国家权力、市民社会和国家法[2](第6章)。
桑托斯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六重结构空间,即家务、工作、市场、社区、市民和世界空间,与之相应的有六重权力形式、法律形式和知识形式。
在家务空间中,权力形式是家父,法律形式是家内法,知识形式是家庭主义;在工作空间,权力形式是剥削,法律形式是生产法,知识形式是生产主义;在市场空间,权力形式是消费身份,法律形式是交易法,知识形式是消费主义;在社区空间,权力形式是不平等的区别,法律形式是社区法,知识形式是地方性知识;在市民空间,权力形式是统治,法律形式是国家法,知识形式是民族主义与公民文化;在世界空间,权力形式是不平等的交易,法律形式是世界体系法,知识形式是科学关于普遍进步的预设和由此预设而支配的全球文化。
在桑托斯看来,在上述权力形式中,不惟国家权力是政治权力,其他五种权力也具有政治性质,将它们去政治化只不过是一种掩盖策略;在上述法律形式中,不惟国家法具有法律性质,其他五种法律形式都具有法律功能,把它们去法律化也是一种虚饰策略;在上述知识形式中,不惟官方知识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其他知识也渗透着意识形态,将它们去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迷惑策略。
这些策略的意图在于,表明“权力集合体中的统治、法律集合体中的国家法和认识论集合体中的科学”[2](P.510),各自在现代社会中取得了中心地位,且它们三位一体,打造出现代社会权力、法律和知识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形象。
同时,这些策略也意在将市民空间的“政治的化约转化为一种政治常识,将国家法律的化约转化为一种法律常识,将科学的化约转化为一种认识论常识”[2](P.510)。
由此,其他权力、法律和知识形式就被排除在“常识”之外,而任何对“常识”的反对都显得有悖常理,因而变得极其困难。
桑托斯认为,上述策略的一个附带效应是,那些更专制的权力、法律和知识形式就逃脱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视野之外。
就法律而言,由于国家法毕竟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基础,因而总体上比其他法律形式较少专制因素。
当然,有些非国家性质的法律形式,源自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来自社群互动中的修辞性对话与商谈,在气质上与暴力和官僚制之法截然对立,因而其中潜藏着某些反规制和反霸权的解放潜能。
他主张,现代社会应承认各种法律形式,进而实现多元法制交叠互动,即走向他所谓的“居间法制”(interlegality)。
③在他看来,这种法制模式的典型是“帕萨嘎达法”。
它的特色是社区法与国家法相交叠,前者适用于民商事务,后者适用于刑事领域。
桑托斯更看重其中的社区法。
它的主要特质是采取社区内部视角,具有可接近性、参与性以及调解性等特征,因而具有灵活、快捷、成本低廉等优点。
他虽然意识到“帕萨嘎达”贫民区,并不代表田园诗般的和偕世界,而是工业化野蛮征地之结果。
但却暗示,就法律的结构性要素而言,这种地方法趋向于说服和商谈性的修辞,因而优于职业化、形式性和难以接近的国家法,因为后者包含着更多暴力和官僚制要素。
他认为,这种基于常识的法律实践具有解放的潜能,可以对国家法施加影响,抵制和改变其中的规制性因素[2](第4章)。
桑托斯注意到,在政治领域,现代西方的主要民主范式是代议制民主。
他认为,核心国家中的福利措施,缓和了阶级对立;代议制民主的改进,增强了政治的合法性。
尽管这些改革“暗示了解放的理想化约为现实的比例均衡,暗示了原则性的选择化约为暂时性的妥协”[2](P.58),但毕竟包括了趋向于平等和民主的解放诉求,并意味着“改革战胜了革命”。
关于后一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2](P.58)就是典型例证。
在桑托斯看来,社会福利的资源逐渐减少,无法满足民众不断增加的福利诉求;民主化仅限于公民社会空间,而没有触及其他结构空间,故而上述两种改革思路难以持续。
因此,西方在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巨大危机之时,不得不放弃这种模式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
在这个阶段,原先的福利分配制度被经济效率的考量所压倒,逐渐扩大的民主参与机制被自由市场的竞争所淹没[2](P.63-64)。
他承认,在人类历史上,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国家首次不再成为一家一姓独占的私产,或一党一派独据的领地,而真正成为了具有公共性的公民国家。
但他同时认为,宪政要获得充分的民主基础,必须把代议制民主转向参与式民主。
参与式民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公民选举精英和实行民主代议制,还重视公民直接参与民主的实践。
在这种参与式民主中,公民通过互动协商和说理论辩,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并作出决定。
他特别强调指出,西方和非西方国家要走出现代性困境,就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针对市场而言,民主必须处于优先地位;就民主自身而言,参与式民主应优先于代议制民主。
与许多后现代多元主义者不同,桑托斯没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多元价值观,而是确认并维护人类的普世价值。
他特别强调人权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和普适性,主张人类法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必须以人权作为基础。
他虽然认为西方人权观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因而反对把西方人权理论和实践全球化,但并未由此而走向相对主义人权论。
他强调指出,作为反抗规制的利器和解放的精神追求,普遍人权尽管受到了市场原则的压制,但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发展。
在国际层面,人权作为全球解放对话的代码,是一种政治世界语;在国内层面,国家既是人权的保护者,也是人权的侵犯者[2](P.358)。
因此,需要确认人权对主权的优先性,国家主权不应以侵犯人权作为维护统治的代价。
他主张通过跨文化对话来建构世界的普遍人权,然后将其全球化,用以反对全球的霸权主义和地方的专制主义,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捍卫人类的个体尊严。
在权利体系和内容上,他主张财产权不应导向占有性个人主义,而应有助于社会团结;权利应赋予自然和后代,强调人类对自然及其后代的责任与义务;民主自决权应得到强化,公民应享有对抗性人权,即公民对体制的激扰权(destabilizationright)④;创制权利之权应得到确认和拓展,由此公民可以随时实现权利的自我赋予。
他的权利主张中,不仅吸收了绿党的生态观,还明显融入了当代生命政治学与权利政治学的一些晚近思考。
桑托斯对于现代政治和法律缺陷的批判,深刻而切中要害。
他指出的补救途径或替代机制,也颇具启发意义。
但社会学的视角使他偏爱多元、边缘和事实之维,而对于统一、中心以及规范之维抱有抵触情绪。
他在提倡参与式民主时,没有虑及这种民主运行的巨大成本,也忽视了这种民主需要公民具备个人美德和献身公共事务的精神,同时也低估了公民分化的异议风险。
涉及法制模式,他关于不同权力空间和法律空间实现互动的建议,对于改变国家法的霸权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法、国家法和全球法,一直处在互动过程之中。
但就结构空间而言,他在批评福柯规训论的同时,陷入了另一种误区,认为家规、厂纪以及市场的非正式交易惯例,都具有法律的性质。
这种社会学视角的宽泛法律观,混淆了法律与非法律界限,而这与他推崇非正式的社区司法和调解模式密切关联。
此外,他认为“帕萨嘎达法”的上述特点构成了“解放性的法律实践”[2](P.194),因而颇为推崇并意欲拓展这种实践。
这不仅流露出他对边缘人群的同情,而且反映出社会学家对小型群体和自发秩序的职业偏爱。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