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docx
《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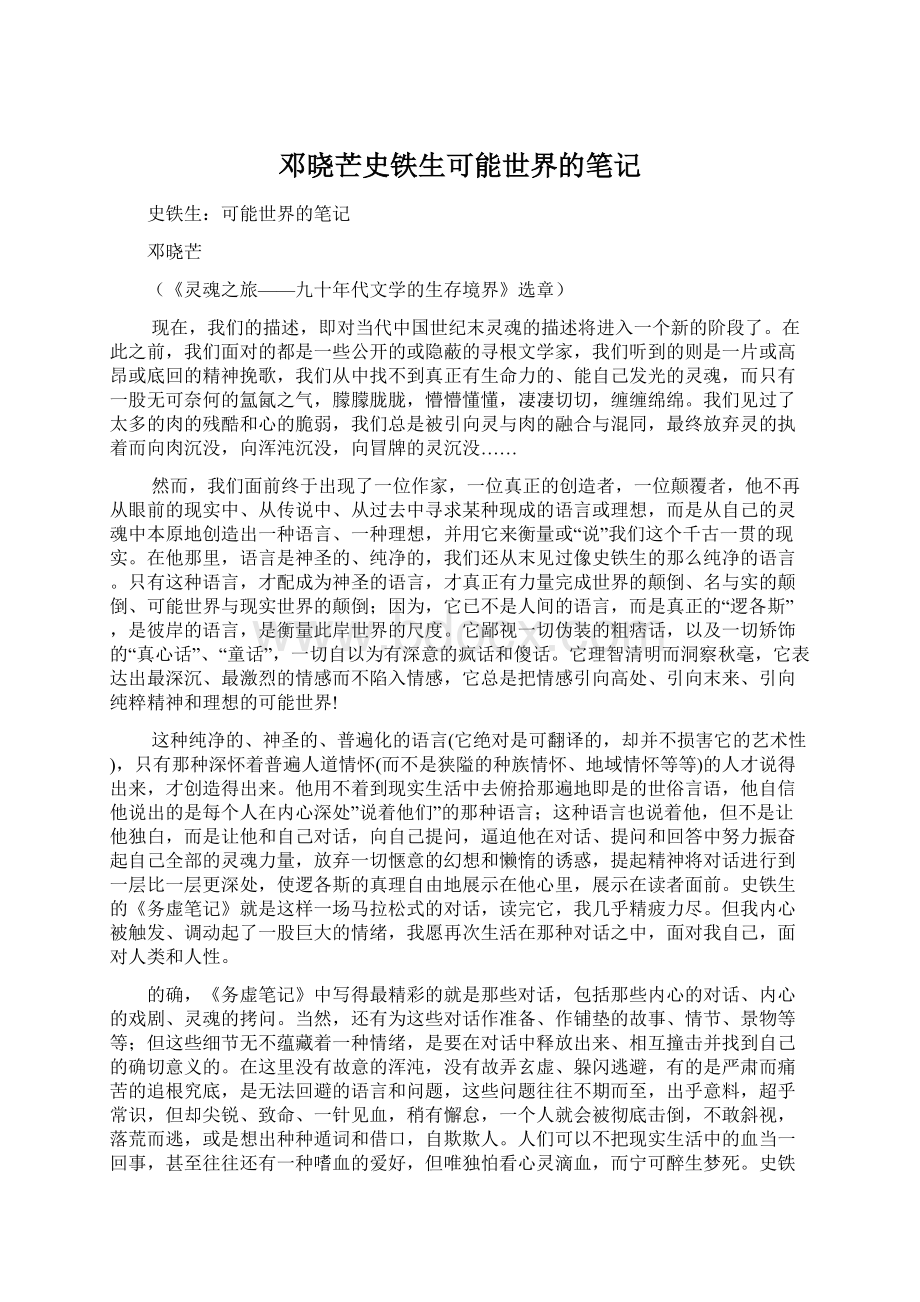
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
史铁生:
可能世界的笔记
邓晓芒
(《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选章)
现在,我们的描述,即对当代中国世纪末灵魂的描述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在此之前,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些公开的或隐蔽的寻根文学家,我们听到的则是一片或高昂或底回的精神挽歌,我们从中找不到真正有生命力的、能自己发光的灵魂,而只有一股无可奈何的氲氤之气,朦朦胧胧,懵懵懂懂,凄凄切切,缠缠绵绵。
我们见过了太多的肉的残酷和心的脆弱,我们总是被引向灵与肉的融合与混同,最终放弃灵的执着而向肉沉没,向浑沌沉没,向冒牌的灵沉没……
然而,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
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末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
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量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
它鄙视一切伪装的粗痞话,以及一切矫饰的“真心话”、“童话”,一切自以为有深意的疯话和傻话。
它理智清明而洞察秋毫,它表达出最深沉、最激烈的情感而不陷入情感,它总是把情感引向高处、引向末来、引向纯粹精神和理想的可能世界!
这种纯净的、神圣的、普遍化的语言(它绝对是可翻译的,却并不损害它的艺术性),只有那种深怀着普遍人道情怀(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情怀、地域情怀等等)的人才说得出来,才创造得出来。
他用不着到现实生活中去俯拾那遍地即是的世俗言语,他自信他说出的是每个人在内心深处”说着他们”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也说着他,但不是让他独白,而是让他和自己对话,向自己提问,逼迫他在对话、提问和回答中努力振奋起自己全部的灵魂力量,放弃一切惬意的幻想和懒惰的诱惑,提起精神将对话进行到一层比一层更深处,使逻各斯的真理自由地展示在他心里,展示在读者面前。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就是这样一场马拉松式的对话,读完它,我几乎精疲力尽。
但我内心被触发、调动起了一股巨大的情绪,我愿再次生活在那种对话之中,面对我自己,面对人类和人性。
的确,《务虚笔记》中写得最精彩的就是那些对话,包括那些内心的对话、内心的戏剧、灵魂的拷问。
当然,还有为这些对话作准备、作铺垫的故事、情节、景物等等;但这些细节无不蕴藏着一种情绪,是要在对话中释放出来、相互撞击并找到自己的确切意义的。
在这里没有故意的浑沌,没有故弄玄虚、躲闪逃避,有的是严肃而痛苦的追根究底,是无法回避的语言和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期而至,出乎意料,超乎常识,但却尖锐、致命、一针见血,稍有懈怠,一个人就会被彻底击倒,不敢斜视,落荒而逃,或是想出种种遁词和借口,自欺欺人。
人们可以不把现实生活中的血当一回事,甚至往往还有一种嗜血的爱好,但唯独怕看心灵滴血,而宁可醉生梦死。
史铁生不怕这个,他用一种普遍化的、谁都能懂的、因而谁都无法回避、谁都没有借口逃开的语言,刺穿了人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把人鞭策到他的“自我”面前,令他苦恼、惊惧,无地自容。
作者明明知道最终答案是没有的,灵魂永远不可能得到“安妥”(除非死),“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但正如鲁迅的《过客》一样,他只能踏向前去,义无反顾。
(一)
上面一章曾经谈到,“上帝是谁”的问题实质上是“我是谁”的问题,因为是“我”在需要或探求一个上帝;莫言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兴趣在自己的写作中认真探讨“我是谁”的问题,他们充其量只能假定一个上帝(或真主),或由别人恩赐给他们一个上帝,而无法去展示、去探求、去理解什么是上帝。
只有在史铁生这里,上帝的问题才立足于“我”的问题,而“我”的问题则被推到了极致,被推到了主体、作者、写作者本身的一个“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第10页)
而正由于这个“我”是一个写作者,所以上述悖论便直接转化成了一个“语言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第9—10页)
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指出过,王朔在潇洒地通知读者“我又要撒谎了”时,他是自以为绝对真诚的,他没有意识到语言本身的悖论。
在第五章中,我们也曾揭示了韩少功在“栀子花茉莉花”式的真假难辨中的尴尬处境。
更不用说那些一往情深、对自己的写作状态缺乏反思的作家了。
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史铁生这样,在意识到“我”的悖论和“解释学循环”的同时,勇敢地投身于这个痛苦的、钻心的循环,将自己一层一层地撕裂和扬弃,从一个又一个美好的、醉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奋力跳出,看出它的虚假,将它们一一击碎,即使只留下绝对的虚空也在所不惜。
因为这恰好表明,作者不相信有绝对的虚空,他相信毁灭即孕育着新生: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
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
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
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
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
(第5页)
这显然是一种信仰。
你可以说这就是对上帝全在或无处不在的信仰,但根本说来,这是对自己的“此在”的直接信仰,即一种明证的“被给予性”,是对自己生命本性的一种直接体验的真实性。
只有最强有力的人,才有这种坚定的自信,而只有彻底孤独、唯一地思考着自己的存在的人,才拥有这种力量。
所以我们在史铁生那里,虽然处处看到上帝的启示和命运的恶作剧,看到人的软弱如同芦苇,然而我们看不到人的乞求,看不到作者的怯懦和惶恐。
我们看到一个个人物在悖论中挣扎,并由于悖论而挣扎,看到他们努力着走向自己的毁灭,或为了自己的毁灭而拼命努力着。
但我们在荒诞之中感到了人格的强大,即使最脆弱、最无奈的,也透现出一种强大,因为他们的严肃、认真,因为他们的苦难,因为他们对苦难的意识。
《务虚笔记》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幸福的,然而,正是在深深的痛苦中,他们悟出了:
“一个美丽的位置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位置,它不排除苦难,它只排除平庸”,“那必不能是一个心血枯焦却被轻描淡写的位置”(第597页,又见第73页)。
美丽的位置,或幸福的位置,真正说来就是超出平庸而建构起人的可能性的位置。
平庸只不过是现实罢了;而现实往往是丑陋的。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位置提高到现实之上,为某种美丽的理想而追求、而苦恼、而受难时,他便获得了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或者说,他便把自己造就为一个真正的人。
人就是他自己造就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可能性。
只有在可能性中,一切悖论才迎刃而解。
悖论总是现实的,就是说,导致现实的冲突的。
在单纯现实中,悖论是不可解的,人与人,人与自己,现在与过去、与未来都不相通。
然而在可能性中,一切都是通透的。
正因为人是可能性,才会有共通的人性、人道,才会有共通的语言,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凡是想仅仅通过现实性来做到这一点的人,凡是想借助于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复到植物和婴儿或天然的赤诚本心来沟通人与他人的人,都必将消灭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
我们在寻根文学家(或挽歌文学家)那里多次证实了这一点。
但在史铁生这里,可能性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点。
它首先体现为“童年之门”: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第46—47页)。
“会”吗?
“不会”吗?
中文没有虚拟式,但虚拟的语气已经表达出来了。
“会”,这就是可能性。
动物没有“会”,动物的“会”是人为它们设想的;人则有“会”,而且“会有”两个可能的、永不相交的“世界”,也许是无数个不相交的世界。
但“童年之门”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栋美丽的、饱含诸多可能性(各个不同的“门”)的房子。
但不要依赖它!
童年只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童年之所以是童年,就在于它从虚无中给人提供了各种存在的可能性。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
结束于‘我’”(第55页)。
在这个生命的起点上,借助于“我”的行动,“上帝的人间戏剧继续编写下去,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第53页)。
唯一不可能的是退回到起点,退回到童年,回到虚无。
因为虚无的意义并不是虚无,它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是作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才有意义。
虚无是存在的可能性,儿童是成人的可能性,如此而已。
所以作者从“可能”(如果、或者、比如、抑或、也许、可以是、也可能、说不定……)开始他的写作,并由同一个“童年之门”(美丽幽静的房子)引出他的诸多人物:
“我”、画家Z、医生F、诗人L、政治家WR、残疾人C,以及他们的恋人O、N、T、X,这些人物都是可以混淆、相通的,许多语言或对话都可以互换;但由于他们走进了不同的“童年之门”,他们在普遍语言的基础上逐步展示了他们内心极其不同的个别言语结构,凸现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而由于这些个性是由共同的语言砖瓦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们有一种本质上的人性的沟通。
人与人当然还是不可通约的(他们走进了不同的“门”),但可以在极深处相逢;相逢之后仍然不可通约,但却可以理解和言说:
我不必成为你,也不必赞同你;但我知道,我如果进了你那个“门”,我也就会是你。
尽管如此,我现在并不是你,我是我,你是你。
我与你的这种分离不是人们想拆除就可以拆除的,它是我和你从小所建立起来的人格构架;我和你的沟通也不是靠回复到天真,而是靠向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可能世界的超越。
然而,每一个“我”都毕竟是从那个共同的“童年之门”走进这个世界中来的。
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就具有一种不可逆性,而最初是现实的东西后来成了梦境,却一直以“现实”的模样存在于梦境之中。
这种梦中的现实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
中国当代一切“寻根”精神都是这一诱惑的明证,而在这部小说中,女教师O便是这一诱惑的最典型的牺牲品。
孩子的梦是正常的,每个孩子都在祈盼着从母亲的怀抱里获得关怀、温情和快乐,尽管随着孩子的长大,这种快乐会(也许过早地)被剥夺、褪色,成为一种甜蜜却又伤感的回忆,但这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是,“O在其有生之年,却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第57页)。
她直到死都是一个“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第58页)。
其实,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务虚笔记》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他们太执着于梦中的现实而放弃了现实的梦想,也就是太执着于已不可能了的可能性(童年、过去),而闭眼不看真实的可能性(未来),正如那个受委屈的男孩“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第57页)一样。
因此,他们的悲剧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些悲剧通常都发生在他们的青春期,即从孩子进入成人和成熟的过渡时期。
他们以孩子的心态追求各自的爱情,他们爱情的破灭是那么凄艳美丽,他们只是逐渐地、通过付出一生的代价才明白这种悲剧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
整部《务虚笔记》记录的就是现代中国人的青春发育史,它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正在于标志着中国人终于凭借一种成熟的语言跨入了并确立了他们的青春思想,而扬弃和摆脱了幼儿的无辜、无助和未成年状态。
这一充满悲剧的苦难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层次:
最基本的层次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灰线,即女教师O与政治家WR、画家Z的两次恋爱(如果不算她与前夫的那次失败的婚姻的话)。
就O来说,这是纯情爱情的典范,连它的结局都是传统的,但其中已蕴含着绝对非传统的意义。
其次是作为对比出现的两对恋人:
医生F与女导演N,以及诗人L和他的恋人。
前一对仍是传统的,但从头至尾表现的是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及从传统失语桎梏中突围的努力;后一对则是“反传统”的,但仍无法脱离传统臼巢,诗人的千言万语都成了废话,最终归于沉默。
再就是两对比较次要的、但同样深刻的情人:
X和残疾人C,Z的叔叔和成为叛徒的女人,然后加上T和HJ(Z的同父异母弟弟)、T(或N)的父母、Z(或WR)的母亲与亡夫以及“我”在“写作之夜”的独白和自叙。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相当的理智和耐心才能理得清。
作者似乎在考验读者:
一个连这些人物关系都弄不清楚的人,休想清楚地把握书中的观念和哲学意义。
史铁生在当代作家中是哲学素养最高的作家,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务虚笔记》之中。
这使得他这部书决不可能用一般消遣和欣赏的态度来读,而必须用全部的灵魂和心力去认真对待。
(二)
该书的故事是从“死亡序幕”开始的,即画家的妻子O服毒自杀,引出了O与Z的颇费猜详的关系,引入了Z在儿时的“童年之门”、也是好几个主要人物的童年之门。
这个开端是意味深长的。
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此在”是一种“先行到死”的存在者,即人能以死为目标和终点来筹划自己为一有意义的过程。
女教师O虽然并非一开始就由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来筹划自己的一生,而是守护着自己童年的理想,毫无筹划地忍受着命运的苛待;然而,只有当她最终把死亡作为一种生命的计划来筹划并自由地实施出来时,她的整个人生的意义才第一次被照亮了。
她向世人也向自己表明,她终生守护的那个纯情的理想不能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是个残酷的、无情的、撕裂温情的东西;她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假装天真幼稚地守护下去了。
于是她以自己还算年轻的生命,作为牺牲,献给了这个童年理想的自我冲突。
O的童年,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女孩子,她的天真、单纯、善良、正直的天性和良好的家庭教养,都使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善意。
当出身于农村的少年WR第一次到她家里来玩的时候,她表现出的那种童真的喜悦能使每个大人都被打动,如果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也许还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读着这些地方,总感到作者一边写,一边在含泪地微笑。
他实在是描写这种儿童语言和儿童情趣的顶尖高手(可参看第208—211页,又参看第50—51页)。
而当他写到O与WR的青春初恋时,那些优美、羞涩、柔情的对话(仅仅是对话!
)更是如同一场净化心灵、净化整个世界的甘霖。
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在恳求中,允诺中,婉拒中,在互相的惊异、叹赏和沉默中,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那心房的颤动像音乐一样,和着窗外的细雨声在悄悄弹拨。
这是大自然的神秘,也是心灵的奇迹。
能用如此纯净的语言、特别是女孩子的语言这样生动地描述初恋的神秘激动的作家,除了史铁生再没有第二个了。
我仿佛看到他含泪的眼和颤抖的笔,但这次不是微笑,而是虔诚(可参看第219—223页)。
美丽的初恋事实上是永恒的,就像那只白色鸟(这一意象贯穿全书)。
一个人要从这种虔诚中超拔出来也是极其困难的。
不,我说的是“超拔”,而不是“放弃”。
人类永远不能放弃的是青春的激情,永远不应忘怀的是初恋的纯真,这种瞬间闪耀出来的理想光辉,正是照亮人们人生旅途中漫漫长夜的火把,值得人们为之献身。
然而,只有见过并忍受过了太多苦难的人,才有力量一面保持着对青春的虔诚,同时又超拔到一种大悲悯大智慧的精神境界,对上帝或命运将这一对恋人强行拆散的那双巨手表示理解。
青春的激情是超时空的,自从有人类以来,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都会在身体发育的一定阶段获得这一大自然的慷慨赠品。
但只有通过青春激情进入一种独立人格并摆脱了未成年(被监护)状态的人,才能将这一赠品雕刻成人类最美好的艺术品——光辉灿烂的爱情,才能使它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神圣的内驱力。
但O与WR并没有达到这种自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没有这一说,他们只是一种传统的“青梅竹马”的关系,他们把青春激情儿童化了。
没有人提醒他们,也没有人教给他们:
能够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起码标志(马克思也说,根据男女之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
可以放弃一切,但永远不能放弃爱。
爱既不是纯真的本心(童心)的守护,也不是可以牺牲的幼稚的错误,爱是追求的“力量”。
无力的爱不是爱。
当WR由于“思想犯罪”而被发配到边疆去时,他们的这种青春的激情就被彻底地否定了。
确实,我们不能说WR已经不爱O了。
即使12年后WR回来并拒绝了O的爱时,也不能这样说。
然而,当WR登上西行的列车时,他们的爱就已经被牺牲掉了,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
O仍然执着地要求WR记住她的地址,WR却知道,童年式的两小无猜的爱是一去不回了,从那一天起,他“长大”了。
所以当O说“我肯定能把新地址告诉你”时,他的回答是:
“不过我不会把我的地址告诉你”(第227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WR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所理解的爱正如O所理解的一样,也是儿童式的纯真,这种爱没有上升为成年人的成熟的热力,是无法承受社会生活的暴风骤雨的。
所以他作为一个长大了的成人,十分明智地切断了一切青春的幻想,他自认为、并且确实也是为了他所爱的人“好”,这是符合我们通常世俗道德的高尚行为。
但这一切是建立在对青春和爱情的贬低之上的。
被贬低了的爱,作为少年时代的幼稚和孩子的梦幻,在残酷现实面前是那么无力甚至不值一提,只有永远停留在“美丽梦境”中的孩子如O,才会执着于它,那悲剧是必然的。
直到他们十多年后重逢,O才逐渐明白:
“当她在漫长的昨天期盼着与WR重逢之时,漫长的昨天正在把WR引向别处”(第334页),即引向一个成人的、政治化了的、无爱的人间。
WR在大西北劳改地,确实懂得了很多事理。
首先他懂得了孩子式的激情(也包括他的初恋)的徒劳无用。
“童话是没有说完的谎言”(第337页)。
其次,他懂得了“只有权力,能够真正做成一点儿什么事”(335页),他要抓住我们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把柄。
最后,他树立起了自己人生的目的,或者说理想,就是不再有任何人像他一样被“送到世界的隔壁去”,与这个世界隔绝起来。
这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所唯一可能有的道德信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抱负”。
于是他从大西北回来后,决心从政。
经过了生活的磨炼,他当然懂得了政治的肮脏;但他决心投身于肮脏的权力斗争。
为此他拼命攻击灵魂的圣洁,而为“灵魂的穷人”辩护,自认为是这些穷人的拯救者和代言人。
他的这一套的确非常适合于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抱负”听起来也比那种小家子气的个人情感要更加博大恢宏,具有牢不可破的价值基础。
这实际上也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的现代体现。
可是,正当他滔滔不绝地宣讲自己的政治哲学并所向披靡的时候,冷不防“我”向他提到了O,并质问他:
“你真的是不爱她了吗?
”他立刻楞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第341页)。
他毕竟看过许多外国书,读过《牛虻》,他无法欺骗自己的心。
但他仍然想用理智(天理)来克制自己的情感(人欲):
“我只是想,怎么才能,不把任何人,尤其是不把那个看见皇帝光着屁股的孩子,送到世界的隔壁去。
其他的事都随他去吧,我什么都可以忘记,什么都可以不要,什么骂名都可以承担……”
“我”则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伪善:
“这么说你才是一个圣洁的人,对吗?
”他不承认。
但他越是不承认,越是标榜自己将来会“遗臭万年”,就越是说明他与他所攻击的那些“圣洁的人”、精神贵族没有两样,甚至比那些人更加“圣洁”。
因为“遗臭万年”在他那里被作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伟大牺牲。
他牺牲了“个人的”荣誉和爱情而结了一门政治婚姻,为的是更有权力来拯求人民,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水平无与伦比!
他骨子里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卑鄙,他深思熟虑地想过:
“我是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是不是必须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是不是敢于作一个被人斥骂为‘无情无义’的人?
”(第336页)他一直是一个诚实而大胆的青年,现在还是;他的伪善决不是性格上的,而是观念上和文化上的。
我们这个文化要求每一个想要成为人的人首先成为非人,要求每一个想要救别人的人首先扼杀自己;而结果是,每个人既不能成为人,也不能拯救别人,因为一个扼杀了自己的非人到头来什么也干不成,只能成为政治的工具。
但我们的文化却许诺说:
天将降大任于你,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当然不是说,要你泯灭良知,心狠手辣;但一个人一旦把自己当作“天命”的纯粹工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一切冠冕堂皇的“抱负”就都成了空头支票。
所以WR必然会在他的仕途中遇上一个无法解脱的悖论:
“如果你被贬谪,你就无法推行你的政见;你若放弃你的政见呢,你要那升迁又有什么用处?
”(第553页)他中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圈套,这时好像才真正从“世界隔壁”回到了人间,从他那井井有条的逻辑理性中感到了某种说不出的悲哀和荒诞。
WR后来和长得很像O的女导演N私通,他是把通奸作为爱情的代用品,把N作为O的替身。
他吃够了诚实的苦头,发誓不再“允诺什么”。
他知道自己已堕落为一个无耻的骗子,但他仍然自欺欺人地为自己保留下最后一点“诚实”,即他把自己的堕落作为一面警示牌,去维护人间的道德: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有什么人像我一样,因为我他们不会再像我一样……”(第560页)他,这个诚实而大胆的人,终于没有勇气正视自己本性中最终的虚伪、根本的恶,却无论如何要把这种恶理解为善的工具,把自己的人格理解为天命的工具,哪怕是多么可怜的工具!
WR在某种程度上与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有些类似,他们都诚实而深刻,都吃够了政治文化的苦头,都为了投身于这个政治文化并改造它而抛弃了爱情(爱情在他们都相当于一件珍贵的收藏品,可用来交换更贵重的东西),最后又都以婚外恋和性乱作为心理缺损的补偿,却仍然将这种堕落标榜为救世或警世的道德手段。
他们都从少年的真诚一步步无可救药地迈入了伪善。
不同的是,张贤亮无条件地认同和美化他的人物章永璘,包括章永璘的动摇、困惑、软弱和伪善,并为之辩护;史铁生却以批判的态度超越了WR,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WR内心的矛盾之症结。
在这里,没有任何自宽自解、自我原谅,更没有自怜、自恋和自我欣赏,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悖论的冷静的观察、分析,及对这种政治文化借WR之手扼杀青春、摧残爱情的深深痛惜。
更重要的是,史铁生没有把这场悲剧单纯归结为外在命运,而是深入到人物内在的心灵结构,即他们(WR与O)双方对爱情的理解的幼稚性、不成熟性,这注定使一方(WR)为了成人的事业(政治、仕途经济)而牺牲甚至践踏爱情,成为政治文化的帮凶,使另一方(O)成为幼稚无辜的孩子、独守空闺的“怨女”。
也可以说,张贤亮是在回忆中写作(张炜也说:
“写作说到底更多的是回忆”,见《九月寓言》第359页),他立足于现实,所以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现实并没有给他提供对或错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
反之,史铁生则是在可能世界中写作,他立足于可能性,不断地走向可能性。
他并不“塑造”他的人物,“我经过他们而已”,他们只是“我的一种心绪”,“我的心路”(第347页)。
他说:
“我不认为只有我身临其境的事情才是我的经历……,我相信想象、希望、思考和迷惑都是我的经历。
梦也是一种经历,而且效果相同。
”“因为它们在那儿纺织雕铸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
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第348页)。
换言之,张贤亮(还有张炜、贾平凹、王朔、顾城等等)是在展示自我,标榜自我,唯独史铁生是在可能世界中“寻找自我”。
他并不预先知道自我是谁,本心是什么,他只是把人们自以为是本心的东西摆出来、展示出来,然后批判它,超越它,“经过”它。
他的人物“成为我的生命的诸多部分”(第347页),他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但只有经历过所有的人物,即“诸多部分”的“总和”,才是他的“我”。
然而他既然是他的每一部分,他又如何能预先知道这些部分的“总和”呢?
哥德尔定理说,“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第84页)。
所以他不能满足于、停驻于任何一个部分,他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去努力寻求那全体的完成了的自我。
这才是他实现出来的自由和自信。
于是,在女教师O这条线上,史铁生首先是O,然后是WR,他超越了O的幼稚而变得成熟甚至过于成熟(老练);然后又超越了WR,揭示出WR的所谓老练在政治权力场中是多么幼稚可笑,于是进到了Z,一种少年老成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仍执着于儿童时代的印象,但已较之O高了一个层次。
这三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