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村落形态略论.docx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唐村落形态略论.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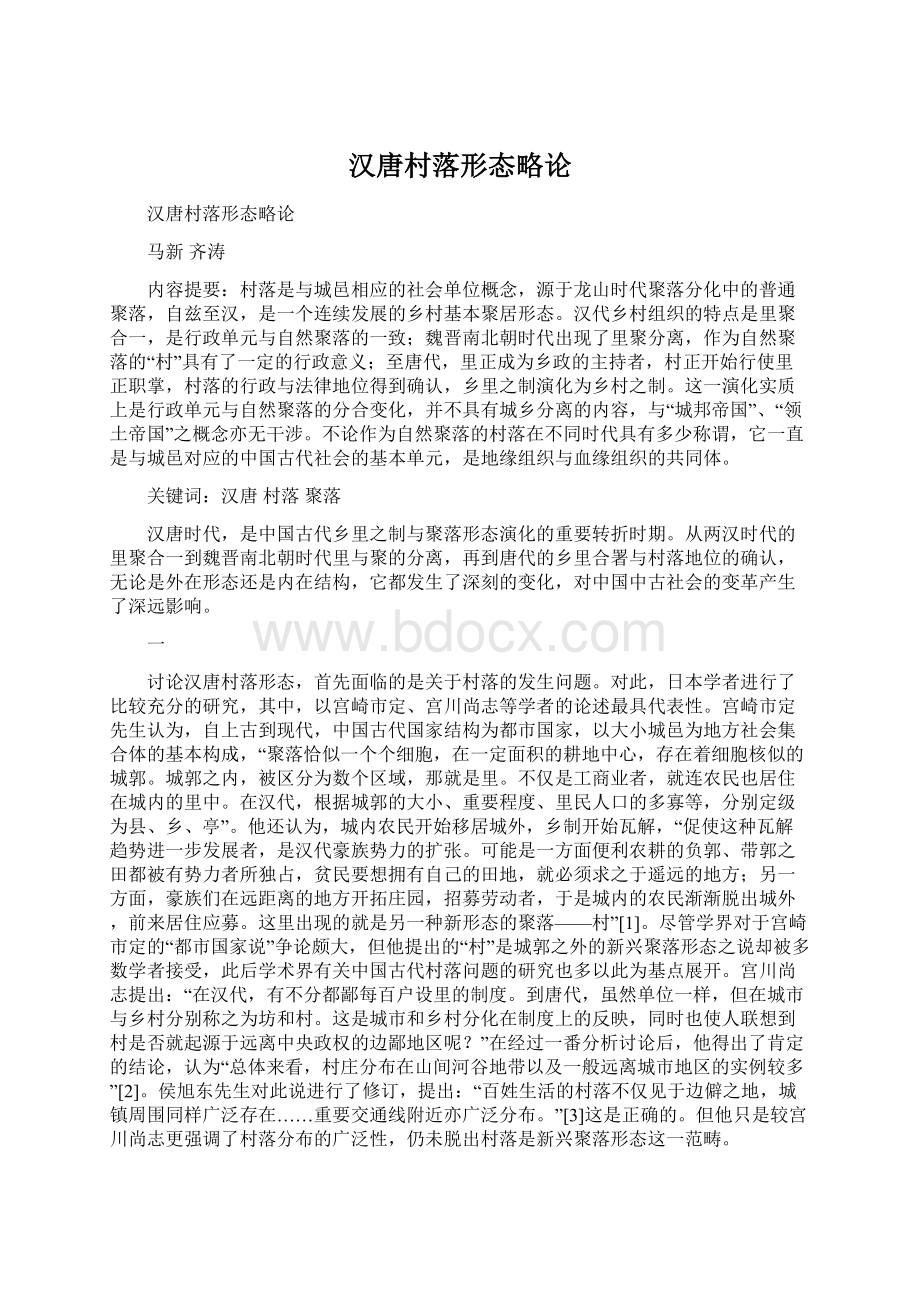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马新齐涛
内容提要: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
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
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
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关键词:
汉唐村落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
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
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
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
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
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
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
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
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1]。
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
宫川尚志提出:
“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
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
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
”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2]。
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
“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
”[3]这是正确的。
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
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
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
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
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
《史记•五帝本纪》曰:
“一年而所居成聚。
”《说文解字》释“聚”曰:
“聚,会也。
从乑,取声,邑落云聚。
”段注云:
“邑落,谓邑中村落。
”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
“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广雅》曰:
“落,谓村居也。
”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
《史记•酷吏列传》:
“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
”裴驷集解引徐广曰:
“一作‘落’。
古‘村落’字亦作‘格’。
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
”司马贞索隐:
“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
如《论衡•书虚》所云:
“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
乡、亭、聚、里,皆有号名。
”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
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
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
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
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
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
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
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
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
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
“(宣帝)遂下诏曰:
‘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
’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
”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
《汉书•戾太子传》曰:
“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
”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
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
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4],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
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列为表1如下:
表1马王堆出土《驻军图》所见里户表
里名
户数
里名
户数
上蛇里
二十三户
乘阳里
十七户
?
里
三十户
□里
□六户
□里
□十户
垣里
八十一户
纟可
五十三户
?
里
三十五户
淄里
十三户
路里
四十三户
虑里
三十五户
?
里
五十七户
波里
十七户
资里
十二户
沙里
四十三户
龙里
百八户
智里
六十八户
蛇下里
四十七户
□□里
□十四户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
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
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
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
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
《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宴《异闻记》“村口”一词。
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
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
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
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5]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
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
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
[6]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
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二
前已述及,汉代乡村社会的特点是里聚合一,也就是乡村基层行政单位与自然村落的大致重合,这导致了时人及后人论及此事时,往往只知有里,不知聚落,这是汉代社会所特有的状况。
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汉代里聚合一的乡村组织模式便面临着重大的变动,其突出表现是里与聚开始分离,作为自然的聚落的村落开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域与组织意义。
长沙走马楼所出土的三国吴简中,赋税户籍简达12700余枚,就已发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所整理的简牍资料看,共出现了完整的里名47个,完整的丘名443个,平均每里要对应9个左右的丘。
[7]统计一下里与丘出现时的相关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与里有关的资料,几乎都是户口登记方面的内容;而与丘有关的资料,则是缴纳赋税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如陈颜在9156简中的记录是“宜阳里户公人乘陈颜年五十六真吏”,属户籍登记;在4891简中的记录则是“嘉禾二年十月廿八日新城丘州吏陈颜……付仓吏”,是缴纳赋税的记录。
又如,雷宜在8446号简中的记录是“平阳里户人公乘雷宜年卌八苦腹心病”,也是户籍登记;而在6271简中的记录是“人南乡让何丘雷宜二年一匹三丈……”[8],为缴纳赋税的记录。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里仍是基本的乡村管理单位,是户籍与人口管理的基本单位;丘作为自然聚落,其数量已大大超出了里,而且也开始被作为重要的地域记录单位。
将此与西汉《驻军图》中所标明的里聚合一相比较,此时里与聚的分离显而易见。
需要指出的是,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对自然聚落的泛称还是以“村”为多,兼有其他称谓。
因此,与里、聚的分离相联系,“聚”这一概念开始被“村”或其他概念所代替,而且成为完整的地域概念。
《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的一段记载可以佐证“聚”与“村”的嬗代:
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余聚。
张守节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亦言:
“聚,谓村落也。
”将村落正式使用为地域概念,当始自《三国志》。
如《魏志•郑浑传》云:
“(郑浑)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林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
人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
”本书《高句丽传》亦言:
“毋丘俭讨句丽……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
”此后,“村落”作为地域概念渐为普及,成为魏晋南北朝乡村居民的基本居住与生活单位的泛称。
当然,这一时期“村”虽然已成为完整的地域概念,但并未取代同样作为地域概念的“里”的作用,只不过两者在这一意义上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
在当时的文献记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里与村虽然同样都可以作为地域概念,但在使用时却有细微的差别,这可以验证前述吴简中对里、丘的不同记录。
一般来说,在比较正式地记录谱系籍贯时,多田“里”不用“村”;而在记录当时居住地时,则多用村名。
如《南史•齐本纪上》记齐太阻高皇帝云:
“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
”《陈书•高祖纪上》记陈高祖武皇帝云:
“吴兴长城下若里人。
”这是以“里”表示籍贯者。
又如,《法苑珠林•冥祥记》云:
“宋刘龄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法,于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
”《宋书•孝义•蒋恭传》:
“州议之曰:
‘……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
’勒县遣之,还复民伍。
”《北史•来护儿传》载来护儿:
“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场,数见军旅,护儿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
”《南齐书•张敬儿传》亦言:
“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住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
”这是以“村”表示居住地者。
另外,在表达行政意义时,也多用里。
如《宋书•自序》云:
“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村)。
”本书《孝义•潘综传》云:
“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
”《北史•李灵传附李德饶传》记道,因德饶至孝,纳言杨达“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
在这里,村与里的关系一目了然。
由“村”与“里”用法的这种细微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分离消长关系。
据里的组织功能的变动,可将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即三国西晋时代。
这一阶段,仍有较为完整的乡里之设,里与聚只是实现了外在形式的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丘”与“村”等只是具有了赋税征收等事务的记录单位,或者说只是被官方认可了其地域单位的概念,还未见到类似于组织功能的记载,乡里仍是基本的组织单位。
后一阶段即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
这一阶段,村落组织功能的进展可分为南、北两途。
南朝虽然乡里之制仍存,但其村落开始接收里的一部分组织功能,渐有行政意义;北朝虽然乡里之制荡然,但三长制的设立使得村落没有像南朝那样开启其行政意义的转化。
南朝时期,开始设置村一级的管理机构,被称作“村司”。
村司人员的构成主要有村长、路都等人。
如《南齐书•海陵王纪》记延兴元年冬十月诏曰:
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忧为烦,抑亦苞苴是育。
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
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中华书局校点本《南齐书》未将“村长”与“路都”断开;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则认为村长、路都、防城、直县都是村司的构成人员。
[9]但细读上下文句,可以看出两说均不妥。
海陵王的这篇诏书是要贯彻轻徭便民的主张,所以,先讲到“汉务轻徭,在休息之典”,又讲到“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
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最后讲到“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若防城、直县都是官名,那么本句文字便没有了谓语,“为剧尤深”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村长、路都不予断开,也让人难以理解本句文义。
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应当是:
诸县使村长、路都(率人)赴县防卫值勤,为剧尤深。
村长当然是一村之首,路都何司,不详。
若望文生义,应当是负责管理村陌道路以及村内治安者。
除村长、路都外,村耆、村老在村落中也起着较大作用。
如《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萧子良遣官“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
在东晋南朝时代,村的行政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
《晋书•刘超传》记道:
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
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
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
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
刘超“作大函,村别付之”,与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应当是同一性质。
《宋书•自序》言“边蛮畏服,皆纳赋调,有数村狡猾,亮悉诛之”。
这里讲的是边境之事,足见以村纳税在南宋时已很普遍。
《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子良上书,也说政府的征调是以村为单位进行。
其文曰:
前台使督逋切调,恒闻相望于道。
及臣至郡,亦殊不疏。
凡此辈使人……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
但令朱鼓裁完,铍槊微具,顾眄左右,叱咤自专。
擿宗断族,排轻斥重……其次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征村切里,俄刻十催。
四乡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狱。
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
第二,村具有基本的治安管理职能,且是连坐的基本单位。
两汉时代,里是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里以下又有什伍。
东晋南朝时代对村的管理,继承了两汉对里内居民管理的内核,一村之内,也实行什伍相连。
不过,与前代不同的是,前代什伍连坐往往殃及里人,以至于“一人有罪,州里惊骇”。
而这一时期什伍连坐则往往波及同村,“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
这在刘宋时已比较普遍。
《宋书•谢方明传》记云:
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
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
《南史•郭祖深传》记梁朝的情况也是如此。
梁武帝时,郭氏曾上言,指出梁朝建立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甚至有战死疆场,而被主将列为叛逃者,再向其家中或村伍征调,使用的也是连坐法。
郭氏上言还说:
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
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
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
上述一村之内什伍的管理,恐怕是村长、路都的主要职责。
另外,村长、村耆可能还负责一村的教化与对村民的督察。
虽然他们并不具备司法权,但可以通过舆论的或其他什么手段行使这一职责。
《宋书•谢方明传》的一段记载也非常典型。
传称方明为南郡相时,年末,放狱中所有囚犯回家,约定正月初三返回。
到期时,除两名重囚犯外,全部返回。
对这两名重囚犯,方明也未马上讨捕,其中一人是因酒醉误期,二天后返回;另一人则十日不至,其传写道:
“囚逡巡墟里,不能自归,乡村责让之,率领将送,遂竟无逃亡者。
”
第三,村是基本的社会事务单位。
在东晋南朝时代,举凡流亡人口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多以村为单位进行。
如《陈书•宣帝纪》载陈宣帝在太建二年曾下诏,要求州郡以良田废村,安置流民。
诏云:
“顷年江介襁负相随,崎岖归化……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
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
”在这种经济事务中,村司、村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梁书•武帝纪中》记梁武帝天监十七年曾下诏安抚流亡,诏称:
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
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
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
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
第四,村有时还成为分封单位。
《宋书•夷蛮传》记道,宋顺帝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
与南方不同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北方,包括巴蜀地区,由于战乱与少数民族内迁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包括行政、军事、经济多种功能的坞壁,使相当一部分的自然聚落淹没在了坞壁的阴影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聚落与行政编制的合一。
但遗憾的是,这种合一是非常条件下的合一,不是乡村社会自然进程的结果。
北魏孝文帝时所实行的三长制,在废止宗主督护的同时,又将北方乡村社会中的行政编制与自然聚落剥离开来。
被剥离后的行政编制,一直是三级的三长制;被剥离后的自然聚落,则是散布于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村落。
在北朝的历史变迁中,这些村落也不断发生着不同往昔的变化,其自身功能也有所发展。
当然,因为有官方设置的三长制在,村落自身功能的进展,较之东晋南朝要逊色得多。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言,北朝以村落为单位的政府行为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旌彰、优赐。
《北史•李灵传附李德饶传》记道,德饶性至孝,“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庐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为孝敬村”。
《魏书•李元护传》载:
“元护为齐州,经拜旧墓,巡省故宅,飨赐村老,莫不欣畅。
”《北史•魏本纪五》曾记孝武帝逃难至湖城王思村,“有王思村人以麦饭壶浆献帝,帝甘之,复一村十年”。
这是以村为单位的优赐。
二是兴学。
如《北史•高祐传》,高祐在太和中即曾建议“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
三是以村为单位实行连坐。
《周书•明帝纪》曾记明帝诏曰:
“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
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并宜放还。
”
这一现象表明,北朝作为政府行政编制的三长与作为自然聚落的村,依然是南、北两途,尚未像南朝那样出现合而为一的趋势。
唐代的乡里组织上承北朝之三长制、南朝之乡里村落制,较前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乡长与乡正的消失,里正直接向县衙负责,成为实际上的乡政处理者;前代里正的职掌则交由村正行使,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
唐初尚有乡正之设,《旧唐书•太宗纪》所载《武德令》中就曾乡正、里正并提,此后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整顿乡里之制,未再见乡长之设。
开元二十五年《大唐令》规定道:
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
每里置正一人。
(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
)掌按比户口,课殖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
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
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
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10]
其他诸典籍记载与《通典》所记大同小异,而且都简于《通典》。
此后,唐代的乡村组织基本未脱出这一框架。
从该规定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但只是每里置里正一人,未有乡官之设。
从唐王朝县乡行政运转的有关资料看,县衙向乡所行文贴都是直接交里正办理。
王梵志诗云:
“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有事检案追,出帖付里正。
”[11]杜牧在《与汴州从事书》中也曾讲到州县文帖的运转:
“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
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着。
”[12]这都说明了里正对县衙文帖之承接。
该规定讲到里正的职责是“按比户口,课殖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
这实际上都是乡政所掌。
就按比户口言,唐代户籍之编核是“乡成于县,县成于州”[13]。
一乡之户籍是由里正直接报县。
吐鲁番一。
三号墓曾出土有贞观十八年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14],格式如下:
(前缺)
合当乡新旧
一十二百
六□新附
三百册四杂任、卫士、老小、三疾等
二百八十七百丁.见输
二百八十六旧
□人新附
……
户、口、新、旧、老、小、良、贱、见输、白丁,并皆依旧,后若漏妄,连累之人,依法(受)罪,谨牒
贞观十八年三月日里正阴曹曹牒
里正李
里
从这一户口帐看,诸里正对于一乡户籍负有全责,这样,里正就要在上报的牒文末尾署名,保证造籍时没有漏妄之弊。
从唐朝有关律令看,若户口出现漏妄之弊,里正是首当其冲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就检查非违看,里正也是直接行使乡政。
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
“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
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
各离之。
”因此,对在本乡之外活动的人员,如军士等人,娶妻纳妾之时,便要原居乡之里正出具证明。
《大谷文书》[15]二八三九号是这样一件牒文。
录如下:
洪闰乡敦煌乡
合当折冲、果毅、别奏、典、傔及士兵以上,
牒:
被责当乡有前件等色,娶妻妄者,并仰通送者。
谨依检括,当乡元无此色人,娶妻妄可显,谨牒。
长安四年二月廿日里正王定牒
敦煌乡里正董靖
这份文书是洪闰乡向敦煌乡之牒文,出牒人是里正王定,收牒人是里正董靖,正因为他们行使的是乡政,所以才不必言“某里里正”,而是径言“某乡里正”,或径言“里正”。
总而言之,里正是唐代一乡最高长官,执掌一乡之政,管理各个村正。
所以,王梵志诗言:
“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管户无五百,雷同一概看。
”[16]正因如此,唐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