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正在消失的文明》.docx
《《留住正在消失的文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留住正在消失的文明》.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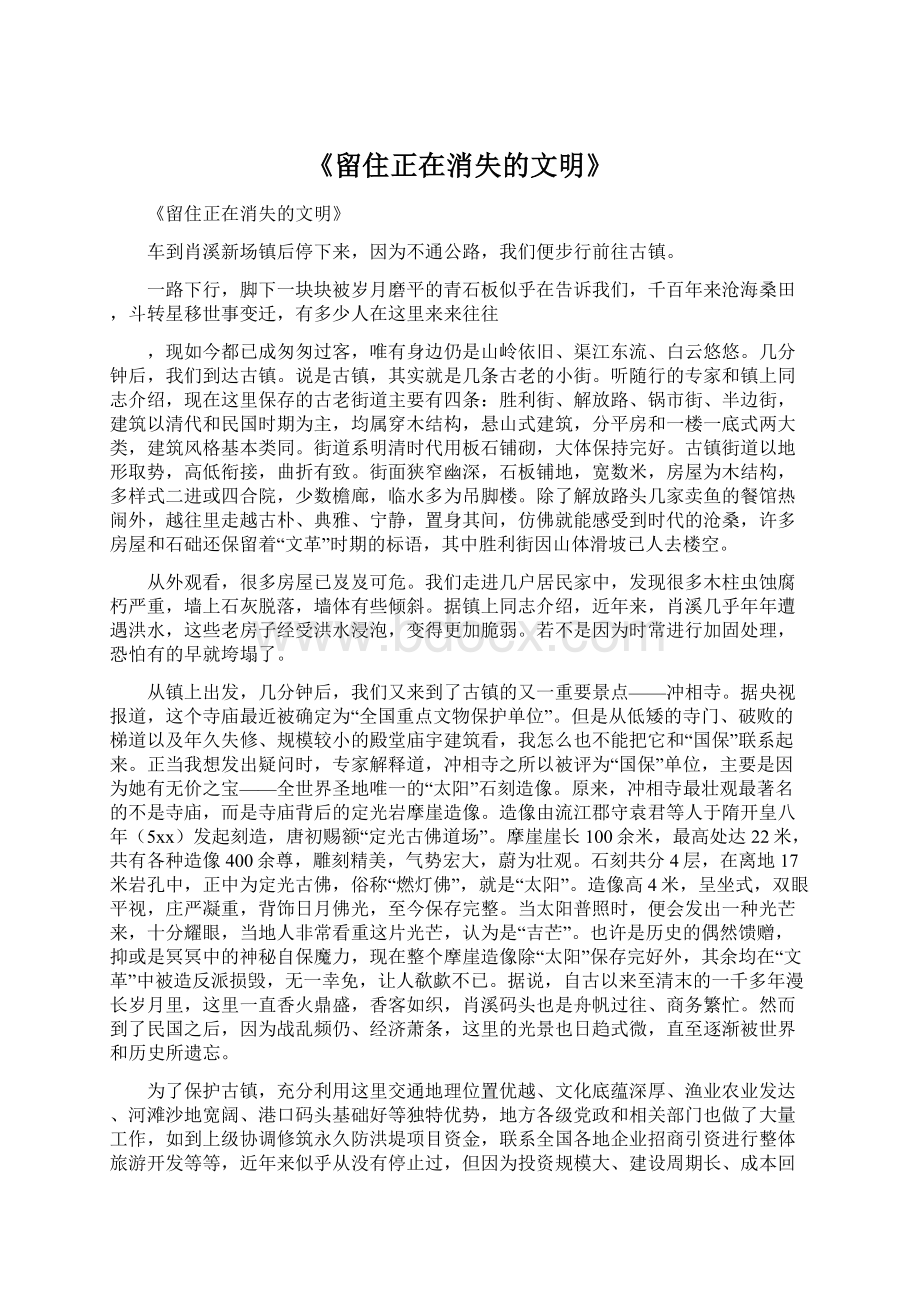
《留住正在消失的文明》
《留住正在消失的文明》
车到肖溪新场镇后停下来,因为不通公路,我们便步行前往古镇。
一路下行,脚下一块块被岁月磨平的青石板似乎在告诉我们,千百年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有多少人在这里来来往往
,现如今都已成匆匆过客,唯有身边仍是山岭依旧、渠江东流、白云悠悠。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古镇。
说是古镇,其实就是几条古老的小街。
听随行的专家和镇上同志介绍,现在这里保存的古老街道主要有四条:
胜利街、解放路、锅市街、半边街,建筑以清代和民国时期为主,均属穿木结构,悬山式建筑,分平房和一楼一底式两大类,建筑风格基本类同。
街道系明清时代用板石铺砌,大体保持完好。
古镇街道以地形取势,高低衔接,曲折有致。
街面狭窄幽深,石板铺地,宽数米,房屋为木结构,多样式二进或四合院,少数檐廊,临水多为吊脚楼。
除了解放路头几家卖鱼的餐馆热闹外,越往里走越古朴、典雅、宁静,置身其间,仿佛就能感受到时代的沧桑,许多房屋和石础还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其中胜利街因山体滑坡已人去楼空。
从外观看,很多房屋已岌岌可危。
我们走进几户居民家中,发现很多木柱虫蚀腐朽严重,墙上石灰脱落,墙体有些倾斜。
据镇上同志介绍,近年来,肖溪几乎年年遭遇洪水,这些老房子经受洪水浸泡,变得更加脆弱。
若不是因为时常进行加固处理,恐怕有的早就垮塌了。
从镇上出发,几分钟后,我们又来到了古镇的又一重要景点——冲相寺。
据央视报道,这个寺庙最近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从低矮的寺门、破败的梯道以及年久失修、规模较小的殿堂庙宇建筑看,我怎么也不能把它和“国保”联系起来。
正当我想发出疑问时,专家解释道,冲相寺之所以被评为“国保”单位,主要是因为她有无价之宝——全世界圣地唯一的“太阳”石刻造像。
原来,冲相寺最壮观最著名的不是寺庙,而是寺庙背后的定光岩摩崖造像。
造像由流江郡守袁君等人于隋开皇八年(5xx)发起刻造,唐初赐额“定光古佛道场”。
摩崖崖长100余米,最高处达22米,共有各种造像400余尊,雕刻精美,气势宏大,蔚为壮观。
石刻共分4层,在离地17米岩孔中,正中为定光古佛,俗称“燃灯佛”,就是“太阳”。
造像高4米,呈坐式,双眼平视,庄严凝重,背饰日月佛光,至今保存完整。
当太阳普照时,便会发出一种光芒来,十分耀眼,当地人非常看重这片光芒,认为是“吉芒”。
也许是历史的偶然馈赠,抑或是冥冥中的神秘自保魔力,现在整个摩崖造像除“太阳”保存完好外,其余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损毁,无一幸免,让人欷歔不已。
据说,自古以来至清末的一千多年漫长岁月里,这里一直香火鼎盛,香客如织,肖溪码头也是舟帆过往、商务繁忙。
然而到了民国之后,因为战乱频仍、经济萧条,这里的光景也日趋式微,直至逐渐被世界和历史所遗忘。
为了保护古镇,充分利用这里交通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渔业农业发达、河滩沙地宽阔、港口码头基础好等独特优势,地方各级党政和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到上级协调修筑永久防洪堤项目资金,联系全国各地企业招商引资进行整体旅游开发等等,近年来似乎从没有停止过,但因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成本回收较为缓慢等原因,有些企业虽有合作意向,但也一直未能拍板正式开发。
就这样,千年古镇和古寺等了一年又一年,一直等到今天……
从肖溪回来后,我们又去了华蓥市永兴镇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xx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安丙墓。
看到墓中南宋时期精美绝伦的石刻艺术,我们无不叹为观止。
但看到墓园至今仍呈当年原始发现状态尚未得到科学开发,文物现场保护尚处于“安保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的尴尬现状时,我们又感慨万千……
在广安和岳池城区,我们还顺道拜谒了两座屹立数百载的古代白塔,它们虽然贵为“国保”、“省保”,但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维修和保护,已经是遍体鳞伤、杂草丛生、岌岌可危。
真担心有一天它们禁不住风雨雷电,像当年杭州的雷峰塔一样轰然倒掉。
如果真有这么一倒,那倒掉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座塔了,而是一段珍贵的历史、一种典雅的文明、一个远去的时代、一片淳朴的民心。
到时花再多的金钱和精力去修复,恐怕也永远无法还原当初的模样……
在回来的路上,我仿佛听到一个悠远而宏大的声音在耳边萦绕,久久不曾离去——救救肖溪、救救安丙墓、救救白塔……
第二篇:
祠堂正在消失祠堂正在消失
经济观察报记者韩雨亭福州市乌龙江畔胪雷村陈氏祠堂,迄今已有730年历史,在当地拥有显赫地位。
陈氏家族奉行耕读传家,历经九世,人丁兴旺,走出无数知名“乡贤”。
当代最著名者应属数学家陈景润。
不过,这个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正四面楚歌,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危险,现在它已是一座被废墟围困的孤楼。
“也就一年的时间,记忆中的童年没有了。
”年轻村民陈少辉呆立在陈氏祠堂前,说话声音低沉,走路时也尽量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那些摆设在祠堂里的先祖。
眼前是一个让陈氏族人不忍直视的画面,曾经绿树掩映的秀丽乡村风貌荡然无存。
祠堂四周,全是大规模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垃圾遍地,废弃的砖瓦和枯黄的老树,大祠堂不远处本来是一条河涌,可是后来村里几乎所有的河涌都被填了,修路建房,曾经清澈见底的溪流如今变成了臭水沟,让人不胜唏嘘。
不过,让陈少辉略感安慰的是,废墟中的陈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往日风采,飞檐翘角、耸峙壁立的青砖大墙前,端坐着一对石狮,昂然雄踞。
抬头望,门墙顶部的青石上镂刻着泥塑浮雕,彩绘着历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书日本明治大学博士陈昌瑞先生题写的“胪峰陈氏祠堂”,显著位置摆放着陈氏家族的名人先贤的牌匾,他们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荣耀。
尽管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几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陈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
“祠堂是村里的灵魂,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
”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曾经分散各地的村民正在动员起来,以合力保卫祠堂。
保卫祠堂
作为闽中望族,胪雷村陈氏家族一直保留着良好的耕读传统。
据统计,明、清两代中试秀才、举人和进士者共有46人。
近现代也是名人辈出,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曾任民国政府海军部长的陈绍宽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xx年回到胪雷村省亲,也最先进入该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陈氏族人的骄傲资本。
从胪雷村走到台湾的名人也举不胜举,协助梅贻琦在台创办并继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后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丞城;xx年从台湾去美国在洛杉矶创办《国际日报》的陈韬。
即便当今,该村里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侨乡,旅外华侨遍布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目前这座占地约4亩规模恢弘的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
作为涉台、涉侨建筑物,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修缮。
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作为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和文化纽带,祠堂在北方地区几已消失殆尽,但在南方地区却得以存留。
陈氏祠堂更是一直有着强大的吸附力和号召力。
最好例证是每年为村里老人庆祝拗九节而在祠堂举办的“千叟宴”,该传统已经坚持了32年。
“千叟宴”场面极其壮观,祠堂门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径1米的大锅,百名厨师齐刷刷手拿铁勺,左右开弓,为几千名老人炒菜做饭,200张圆桌摆满了祠堂的各个角落。
戏台也是见证,每年都有数场闽剧在此上演,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来观赏。
“站得到处都是人。
”胪雷村祠堂管理委员会会长陈正宝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最辉煌时,每月戏班都会带着鼓、钹,到这个舞台表演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这个由锣鼓、丝竹和演员唱腔组成的乡村记忆,是这个村子传统的一部分。
“福州好多闽剧演员最喜欢在这里演戏,因为我们祠堂戏台最大,现在没办法演了。
”陈正宝说这句话时,骄傲中难掩落寞。
的确,曾经华丽的戏台如今沾染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繁华落尽,犹如胪雷村命运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福州火车南站的兴建和使用,经过几轮的大拆大建,这座历史文化名村被夷为平地,村民四处散居,元气大伤。
在浩荡的拆迁中,陈景润的故居也未能幸免,目前,这位蜚声世界的数学家在村里留下的足迹唯有陈氏祠堂。
此前在拆迁胪雷村时,福州市当地政府反复承诺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几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陈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的危机。
“这个祠堂是村里的灵魂,祖祖辈辈传下来,历代祖先牌位都在里面,当年修建祠堂就是为教育下一代。
以前拆我们的私宅倒好说,但现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们肯定不会答应。
”胪雷村老人会会长陈秀光对经济观察报说。
“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
”陈秀光说。
曾经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开始重新集结,同时村委会、祠堂管委会、老人会和部分村民之间形成价值共识和利益共同体,以此合力打一场祠堂“保卫战”。
与时间赛跑对陈秀光而言,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对手是强大的行政和商业力量,决心保卫祠堂的只有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数十年来,村里的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
过去几年,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又使村民进城的步伐加快,城市周边乡村拆迁与反拆迁的对峙不断上演。
如今,又轮到了胪雷村。
84岁的陈依明告诉经济观察报,“拆迁都搞了七八年。
”这位胪雷村最早的支部书记,如今正像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准备为陈氏祠堂的命运奔走。
胪雷村人对拆迁的抵抗曾让政府被迫做出让步。
不过胪雷村被拆迁后,村民散居各地,传统乡村的人际结构被改变。
更现实的是,年轻人都忙着挣钱,无暇顾及村务,“昔日团结的村庄变成一片散沙”。
陈氏祠堂的风险也日渐临近,村民们却浑然不知。
xx年11月份,福州本土的房地产公司——阳光城集团以39.1亿元竞得福州火车南站附近300亩地,这其中就包括陈氏祠堂。
在村民们看来,政府既然已经承诺,就不可能拆祠堂。
“从现在情况上看,政府违背了承诺,已经悄然更改了用途。
”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教授林怡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她是介入福建祠堂保护的重要学术界人士。
学者们卷入到这场祠堂保护运动完全是意外。
xx年4月15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一行数人,调研考察陈绍宽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陈氏祠堂。
眼前的一切让几位学者“十分难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废墟。
祠堂附近拥有百年历史的陈景润祖居也片瓦无存,此前政府曾承诺保护。
陈绍宽故居虽然保住了,但它孤零零立在大马路对面,和村庄分离开了。
陪同考察的村干部忧心忡忡地告诉几位学者。
“我们现在很担心祠堂能不能保得住,听说把我们整个村庄都卖给阳光房地产公司了。
”
目前,村民都不知道祠堂命运如何,传闻是祠堂也被卖了,要在村外围盖个新祠堂。
胪雷村没人答应把祠堂卖掉,前几年政府答应不会拆祠堂,但现在村庄都被拆成了废墟,政府也没派任何人员给村里讲祠堂怎么办。
外界传闻让村委干部寝食难安,他们委托学者到上级部门一探究竟。
“如果政府瞒着我们村民把我们祠堂给卖了,全村百姓绝不会答应。
”一位村委干部说。
接下来的两天,几位学者与阳光城集团取得了联系,得到明确答复:
“政府已经把祠堂连同村庄卖给了公司,但拆迁由政府负责,不关阳光的事,作为公司无权限干预。
”林怡和几位学者将此讯息转告胪雷村干部,他们万分惊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希望学者帮助向上级部门反映。
4月18日,学者们鉴于陈氏祠堂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于是将村民诉求形成文字,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并电话、短信联系仓山区政府主要领导、文物局领导等,建议紧急处置该事件,以免引发严重后果。
这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
4月20日,被拆迁后散居在外的胪雷村委、村党支部、村老人会主要人员冒雨回到胪雷祠堂集中,商讨这件事。
村两委和村老人会联合盖章,请求学者尽快把有关报告帮助送到上级领导手中。
未知的结局
4月21日,几位学者再次设法将村民诉求呈送仓山区、福州市主要领导。
并从仓山区得到回复,“会尽快与福州有关规划部门沟通反映。
”随后,学者又借机会将有关陈氏祠堂的调研报告呈送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
不过,区、市两级政府的回复并不乐观。
仓山区主要领导回复称:
学者们反映情况与事实基本相符,但规划是福州市有关部门在做,拆迁工期已经被耽搁,区里也耽搁不起,最迟不能拖过5月10日,如果近期上级领导没有新的批示,只好“对不起了”。
福州市委有关领导则回复学者们:
“下周请专家对祠堂再做调研论证:
是否涉台和是否是文物,然后再做决定。
”次日,学者再次致电区、市文物局领导,请求:
“如果召开专家论证会,有关教授应到场。
”
在城市建设中,文物部门的弱势,让几位学者意识到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文物论证上很不现实。
也许从涉台文物和两岸关系角度,或许会有一线希望。
4月29日,几位学者将村民有关保护祠堂的诉求反映至台盟省委、台盟中央领导,台盟领导高度重视,请学者们立即将该祠堂资料呈送福建省文物局和福州市文物局领导。
此事开始引起福建省、福州市文物局重视,于当天下午派市、区文物干部到祠堂现场调查,发现该祠堂主体结构依然存有陈绍宽1947年亲自设计修缮的部分。
学者们奔走的同时,胪雷村也开始行动。
村里一些年轻人暂时停掉了自己在城里的工作,加入到这场祠堂保卫战当中,祠堂寄托了乡土社会中他们的精神归属。
“这里的大树、祠堂和清澈的溪水,就是我在这里的全部童年记忆,哪怕他后来做生意,我在城里买了房,但都经常会回到村里,住上两天。
”一位年轻人说。
听说祠堂面临拆迁,他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奔走呼号,目前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给前来探访的学者及媒体记者开车。
村民开始成立分工明细的临时保卫祠堂小组,有人负责筹措经费;有人负责将情况汇报给海内外陈氏家族嫡亲和后人;也有人负责向前来调研者介绍陈氏宗祠的历史渊源和典故;还有人负责将祠堂重新打理得干干净净,让观者感受到宗祠文化的肃穆。
同时,还有人日夜巡逻看守,防止“意外火灾”。
保卫小组一方面要保卫祠堂,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激烈冲突。
多位保卫小组成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发现村里已经“潜流暗涌”。
这也正是学者们担心所在。
林怡表示,“作为学者,我们将努力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尽快与村民沟通,希望事态能够朝着政府与村民双赢的结局发展。
”
不过,目前看来政府更改规划已经十分困难。
同时政府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另外找一块地,政府出资1300万元,重新盖一个新的陈氏祠堂。
在学者和村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诚意的解决方案,首先论价值,仅祠堂土建就不止1000多万,更不要讲四亩的土地了。
最核心的是,当地政府只将“物”列入评价体系,忽略了祠堂作为家族传承的风俗和文化价值。
“以前祖宗选地方都是有看风水的,几百年的风水和牌位,都不是乱放乱挂的,每次重修都要举行慎重的仪式,怎么能说拆就拆。
”一位村民说。
残酷的“乡愁”
胪雷村祠堂面临拆迁只是福州城市扩张的一个缩影。
今年,福州正在力求变成中国东南沿海又一座“超级城市”,计划到2020年,福州市中心城区城镇人口将达到400万,市域总人口为890万人。
城市疯狂的扩张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拆大建,正让传统乡村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随着乡村消失的还包括承载了村庄传统和习俗的祠堂。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泓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愁,全都拆没了。
祠堂在今天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重要,尤其对于现代化社会。
”
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他在去年和今年福建省“两会”上均提出要保护乡村祠堂。
在他看来,保护祠堂就是留住乡愁,传统村落中很重要就是群居的家族生存方式,家族最重要的就是祠堂。
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正在被日益重视。
在全国范围内约97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80%左右来自乡村。
在学者们看来,如果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保留祠堂、老屋这种传统文化符号,可能是城市建设最理想的未来。
不过在现行的“以土地换资金”的改造逻辑下,这样的图景或许只是想象。
乡土社会祠堂和城市建设矛盾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和保护祠堂相比,豪华酒店、高档社区才能让城市更有面子。
如何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及中央提出的保护好祖国的青山绿水,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的要求,显然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即便中央三令五申,依然无法阻止一些地方政府的“造城”冲动。
为更有利于进行土地统筹、推动城镇化运动,福州市政府成立了“福州市土地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任由福州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不过在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看来,“这场宣称为改造乡村面貌的城镇化运动,却在执行过程中和主旨背道而驰,从目前看来,地方政府仍然希望用土地财政带来新的一波增长。
但是这种用粗暴的行政和商业力量斩断了传统乡村的人文结构,为未来的矛盾冲突埋下隐患。
”
尽管宗祠在乡村社会实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低,作为宗族也渐渐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但在王利平看来,祠堂文化之所以绵延千年,肯定有它的价值。
既为地方基层治理中,提供了维持社会稳定的“缓冲”地带;也为传统的延续提供了载体,很多家族成员的精神和人格教育都在祠堂里那些先贤的故事当中无形的完成了。
而如果地方政府为了眼前利益拆掉祠堂,意味着动了家族的精神“奶酪”。
事实也正如此,当胪雷村准备用学者上书保卫祠堂时,距离五公里左右的浦下村刘氏祠堂此刻也正“四面楚歌”,村民们也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祠堂保卫战。
刘氏祠堂历史迄今600多年,1480年左右建成,目前供奉了1100尊祖宗的神宗牌位。
历代都有重修,现在这座祠堂是xx年刘氏家族筹资数百万元修缮的,所谓重修,只是把破碎了的材料进行更新,因为祠堂要保留历史传统,故此地基始终未变,所有规格款式都是按过去的保留下来。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幅闽中水乡景色,祠堂、老屋、江水、榕树„„谁也没想到一年后这里就变成了孤立无援的“城中村”,犹如镶嵌在高楼大厦之中。
大面积的湿地被填埋,一栋栋高耸的“江景房”拔地而起。
那种神速让村民猝不及防,快到几头奶牛都来不及杀,躺卧在大榕树下无草可吃。
仓山浦下村有划龙舟的传统,村里每年都要举行划龙舟比赛,该村龙舟队已经连续几年摘得福州市龙舟赛桂冠。
听闻刘氏祠堂即将面临拆迁,村民们纷纷群情激昂。
浦下村刘氏宗祠老人会会长刘光安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我们不怕政府派人来,大家沟通下,让他们了解民意,就怕他们不来。
”
作为老人会会长,他深切体会到祠堂对于社会稳定的价值,他说那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哪怕从村里走出去的暴徒,或者地痞流氓,只要来到祠堂,都会对族长们规规矩矩,不敢轻举妄动。
”他说。
他认为。
“祠堂本身就具有教育及共建和谐社会功能,作为政府,应该帮助我们管好、保护好传统祠堂才对,而不是随便一声令下就拆了。
”
第三篇:
消失在城里诗歌消失在城里
在街道的岔口
突然色盲了
瞬间迷惘红黄绿的变幻
不知道怎样寻觅
就这样消失在城里
隐匿在街外街
隐匿在楼外楼
隐匿在紧锁的绣门
喧哗的地方最易无声
熙攘的路人最易无形
遣风追逐一路芳踪
拨响街角楼边的琴弦
当风掠过之后
时间的小雨就如约而来
抹去一段段忧伤轻轻
不留下丝丝印痕
第四篇:
消失在市区的小铁路消失在市区的小铁路
(xx-01-2117:
23:
08)转载文化▼
标签:
分类:
我喜欢
消失在市区的小铁路
11月19日上午,铁路居民小区院门口,几幢高楼投下凉而薄的阴影,阴影之外,是冬日的阳光,有几位老人在晒太阳。
周围的人步履匆匆,没有人在意这些老人的喜怒哀乐,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济源曾经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
当时,进到这个院子里,就意味着稳定而丰厚的收入,“在铁路部门上班”,要比当干部要光荣得多。
现在,除了小区院门前一个小小的门牌号以外,再也找不到一点和铁路有关的东西。
曾经的繁华和热闹都归于尘土。
如果打的到这里来,许多出租车司机都会问一声:
“哦,就是豫光集团大门口附近吧。
”
自从小铁路彻底被拆除之后,它在年轻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而对于三四十岁以上的济源人来说,小火车的汽笛声永远是人生中永不磨灭的印记。
曾经的苦乐年华
以前,济源曾经盛传过一段顺口溜,叫《济源十大怪》。
“愚公移山山还在,泱泱济渎不通海。
荆条根儿作梁材,老城东门朝北开。
西滩能把水比败,臭(溴)水路牌街边栽。
火车没有汽车快,男女老少话带把。
打听清楚才恋爱,娘咦声声不见外。
”这“火车没有汽车快”,说的是济源市区曾经的一道风景线。
所谓小火车,其实是一条窄轨铁路,总站在济源西关,北通克井,向东到梨林分开,一条经沁阳通往温县,一条向南通往孟州。
“那小火车老慢慢,一小时跑不了三四十公里,不过,真不少拉东西。
没有小火车前,拉煤拉石头啥的,全是凭人力拉的。
”张联齐说。
张联齐的家在济水大街和南街交叉口的东北角,他家的老宅就在铁路边上,曾经被租用为小火车的售票处。
在他的心目中,小火车是济源老百姓的功臣,把人们从拉煤的苦力中解救了出来。
“往年比现在再冷点的时候,我们就得上克井拉煤了,那可真受罪。
”提起小火车,济源的老一辈人最先想起来的,就是拉煤。
“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
家人忙,我都顶大人用。
天冷的时候,一个生产队里的小伙计们就约好,一起去克井拉煤。
”张联齐说。
那时候,每次拉煤最少会叫上四五个人,因为拉煤的路上有两处大坡,别说十几岁的孩子,就是大人拉车上坡也很吃力。
他们到了坡下,就相互帮着把车推上坡,然后一起排队等煤。
“那时候可不是你拿钱就能买到的,得排队。
下午去,一般要排一个晚上。
书上写的寒风刺骨,现在的人哪知道那是啥滋味啊。
当时的人也没啥穿,到了后半夜,真要把人冻死。
人们就拾些柴火在路边烧,可是前面暖和后背还是刺骨冷,转过身烤烤背,前面又冻得受不了。
咋睡。
哪里敢睡啊,前面的车一动,自己就得赶紧往前跟一下,不然就有人插队。
每次拉煤,都有因为插队打架的。
运气好的时候,头天下午去,第二天上午吃饭时能赶回家。
人多的时候,第二天晚上黑天半夜才能回来。
”
张联齐说着说着,激动起来。
11月下旬,天已经有了寒意,他和小孙子穿着棉衣在自家的小楼前玩耍,两只鹦鹉在相互梳理着羽毛。
他曾经所受的苦难在夕阳投下的余晖中,了无踪影。
“这可不是胡说的,我也去拉过呢。
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子上下学还得家长接送,我们那时候,小闺女也是顶一个大人干活。
车上带铺盖。
拿点干粮就走了,因为家里一件多余的厚衣服都没有。
那时候的人也结实,也没冻出病来。
”郑兰英笑着说。
她也是南街的老户,当年城里的小女孩一点儿也不金贵。
“就是。
好天还能烧火取暖,好过点儿。
有时晴天去的,到了地儿下起雨来。
人都穷,没有伞,大家就在雨地里冻着,浑身湿透。
路不是柏油路,是石子路,坑坑洼洼的。
那种感受,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体会不到。
”张联齐说。
这样的遭遇,以前在铁路部门工作过的人体会更深。
“济源人还好些,外县的,每家一来就是俩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儿,车上带着铺盖,兜里装着硬馍。
有的拉一车煤来回得跑四五天,而且越是路远越不敢拉多,最多只拉500斤,不然光走路人都受不了。
天黑了,走不动了,就找个地方睡下。
一路上也没饭店,条件好点的,到了济源县城住到起火店里,睡一夜,买点热水泡馍吃或自己做点饭。
有个孟县的老头带着孙子拉着平车,跑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到了煤矿,自己装了一车煤,然后倒下再也没起来。
”曾任济源铁路公司经理的李体亮说。
“温县的。
对,就是温县的。
那时候拉煤多难啊。
人太受罪了。
”济源铁路公司老职工苗爱玲说。
这件事当时曾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拉煤难、拉煤苦的滋味,在当时有多少人没有经历过。
“唉呀,我是15岁来济源拉煤的,村里一起来了3个人,拉了500斤煤,回家的时候,家人接到了柏香。
我到崇义是一步路也走不动了,就想坐在地上不起来——那是啥路。
坑坑洼洼的石子路算好的了,有的路上泥是泥,大坑是大坑,真是拉不动。
”老家在孟州市的李占功说。
他后来也成了济源铁路公司的一名职工。
由于拉煤太艰难,人们平常都舍不得烧煤,也就在春节前后用一阵子,其他时候都是拾柴烧火做饭、取暖的。
“小铁路修到西关时,你不知道村里的人有多高兴,大家都说,这下可不用上克井受那份罪了。
”张联齐说。
“铁路修到温县、沁阳、孟县时,你不知道人们有多激动,火车两边站满了人,夹道欢迎。
那场面,要是拍下来,肯定是好片子,都不需要导演。
人们高兴的那股劲儿,全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