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docx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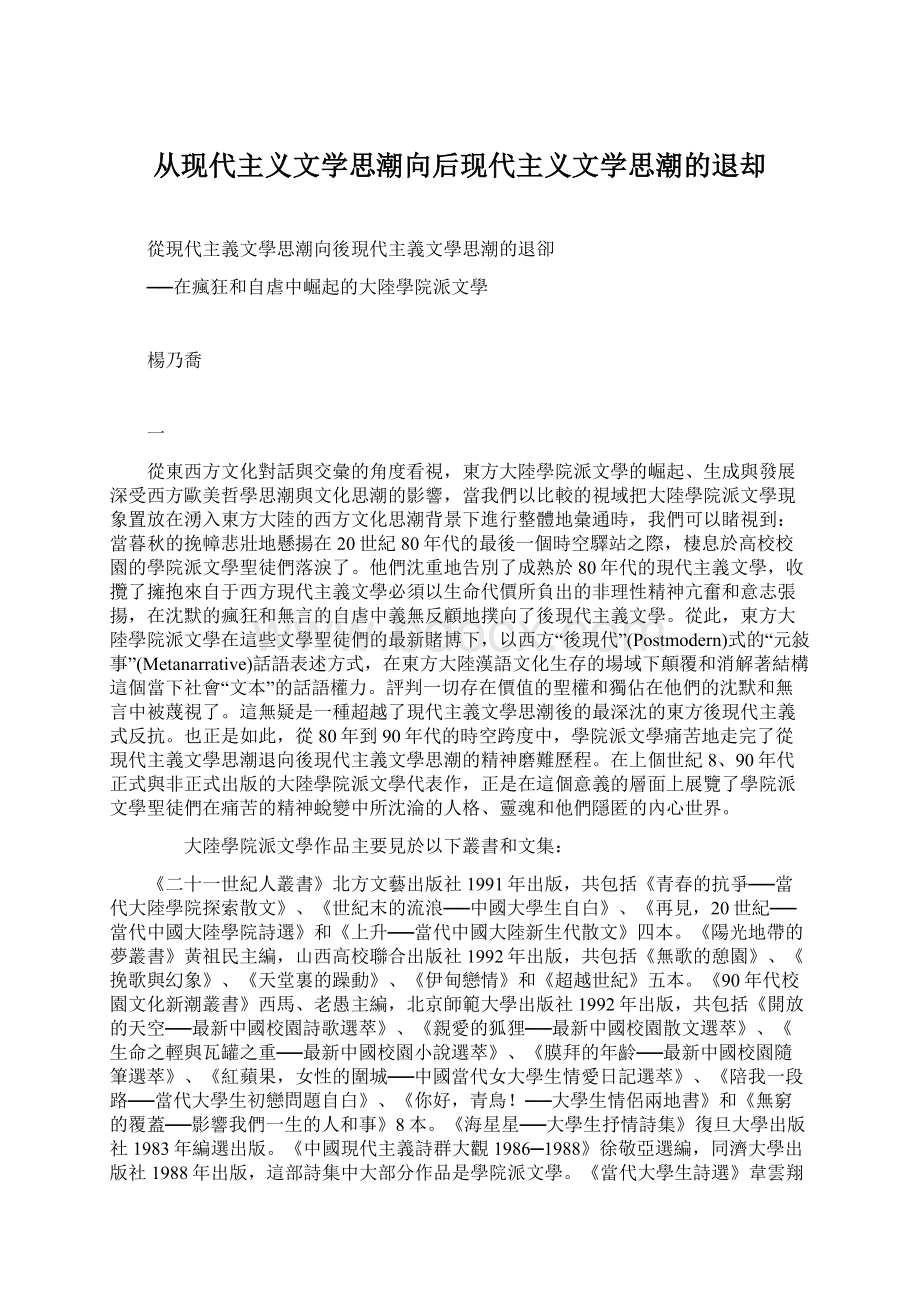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
從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向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退卻
──在瘋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陸學院派文學
楊乃喬
一
從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交彙的角度看視,東方大陸學院派文學的崛起、生成與發展深受西方歐美哲學思潮與文化思潮的影響,當我們以比較的視域把大陸學院派文學現象置放在湧入東方大陸的西方文化思潮背景下進行整體地彙通時,我們可以睹視到:
當暮秋的挽幛悲壯地懸揚在20世紀80年代的最後一個時空驛站之際,棲息於高校校園的學院派文學聖徒們落淚了。
他們沈重地告別了成熟於8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收攬了擁抱來自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必須以生命代價所負出的非理性精神亢奮和意志張揚,在沈默的瘋狂和無言的自虐中義無反顧地撲向了後現代主義文學。
從此,東方大陸學院派文學在這些文學聖徒們的最新賭博下,以西方“後現代”(Postmodern)式的“元敍事”(Metanarrative)話語表述方式,在東方大陸漢語文化生存的場域下顛覆和消解著結構這個當下社會“文本”的話語權力。
評判一切存在價值的聖權和獨佔在他們的沈默和無言中被蔑視了。
這無疑是一種超越了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後的最深沈的東方後現代主義式反抗。
也正是如此,從80年到90年代的時空跨度中,學院派文學痛苦地走完了從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退向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精神磨難歷程。
在上個世紀8、90年代正式與非正式出版的大陸學院派文學代表作,正是在這個意義的層面上展覽了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在痛苦的精神蛻變中所沈淪的人格、靈魂和他們隱匿的內心世界。
大陸學院派文學作品主要見於以下叢書和文集:
《二十一世紀人叢書》北方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包括《青春的抗爭──當代大陸學院探索散文》、《世紀末的流浪──中國大學生自白》、《再見,20世紀──當代中國大陸學院詩選》和《上升──當代中國大陸新生代散文》四本。
《陽光地帶的夢叢書》黃祖民主編,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2年出版,共包括《無歌的憩園》、《挽歌與幻象》、《天堂裏的躁動》、《伊甸戀情》和《超越世紀》五本。
《90年代校園文化新潮叢書》西馬、老愚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共包括《開放的天空──最新中國校園詩歌選萃》、《親愛的狐狸──最新中國校園散文選萃》、《生命之輕與瓦罐之重──最新中國校園小說選萃》、《膜拜的年齡──最新中國校園隨筆選萃》、《紅蘋果,女性的圍城──中國當代女大學生情愛日記選萃》、《陪我一段路──當代大學生初戀問題自白》、《你好,青鳥!
──大學生情侶兩地書》和《無窮的覆蓋──影響我們一生的人和事》8本。
《海星星──大學生抒情詩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編選出版。
《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徐敬亞選編,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這部詩集中大部分作品是學院派文學。
《當代大學生詩選》韋雲翔、岑玉珍編,廣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中國當代校園詩人詩選》馬朝陽編選,北京師範大學五四文學社印(非正式出版)。
《學院詩選》于水主編,中國人民大學詩社1986年出版(非正式出版)。
《八十年代校園詩人抒情詩選──多夢時節》潘洗塵主編,1986年出版(非正式出版)。
《走出荒原》馬朝陽編選,北京師範大學五四文學社1988年出版(非正式出版)。
絕大多數學院派文學作品是以油印本或手抄本這種非正式出版物在大陸高校校園傳閱,其中一些精英作品被有識者結集出版,當然還有許多優秀作品沒有被結集出版,這個工程有待於今後努力完成。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給出一個設問,什麽是學院派文學?
這也是當代文學思潮在80年代的終結期遺留給我們的歷史性設問。
而對“學院派文學”這個概念的界定及其之所以産生和怎樣生存的理論闡釋,任何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教科書都表現出闡釋理論的先天性不足。
因爲,學院派文學是被棲息於高校校園的文學聖徒們在東西方文化的話對與融合中作爲反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和後現代主義文學)推向8、90年代文壇的。
它們是以顛覆正統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方法和審美價值爲自我生存的詩意性文化方式。
它們的存在就是對教科書的蔑視。
學院派文學是在8、90年代於東方大陸高校校園文化母體中孤獨出的一脈文學思潮,這脈文學思潮深受西方哲學思潮與文化思潮的影響,學院派文學的創作主體都是咀嚼過高校校園文化的欣樂和苦澀的天之驕子;學院派文學的題材周延了兩個方面,一方面其透視了在校園文化母體中孕育的男女大學生們的文化心理,儘管這種文化心理可能是他們蓄意爲情造境所呈奉的虛假文明和真誠醜陋,另一方面其又涉獵了這些受過校園文化洗禮的文學聖徒們用自已的審美價值標準和道德價值標準讀解、評判校園文化的題材;學院派文學的主題在這些大學生的激情灼燒和精神窒悶中表現出一種深沈而自虐的無主題變奏,因爲,精神的流浪使學院派文學聖徒們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他們命中注定要浪迹思想的天涯,他們無法、也不願尋找精神的終極家園歸宿,也正是精神流浪的無所皈依,鑄造了學院派文學聖徒們的思想在無中心散點放射狀態中呈現出的未確定性(Unspecialization),無主題就是這些文學聖徒們在學院派文學作品文本中熱烈擁抱的主題,正如石磊在《我的大學》一詩中道白:
“揣著五顔六色的渴望第一次遠遊來到這所城市大學/一大堆日子淹沒在無主題變奏曲中/聽書館一萬個聲音重復著世界人生/你一頭撞碎了薩特弗洛伊德們的喋喋不休。
”
這就是我們給出的關於“學院派文學”這一概念的基本界定。
學院派文學的自覺崛起以80年代劉索拉描寫中央音樂學院大學生生活的《你別無選擇》爲歷史界標,其起勢就以生命的非理性衝動顛覆著痛苦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尋根文學的理性沈思;因此,學院派文學一崛起於80年代當代文壇,就以現代主義文學的顛狂勢態搖旗呐喊。
同時,學院派文學的崛起也宣告了大陸80年代當代文壇現代主義文學走向了主潮。
從此,學院派文學在西方歐陸哲學思潮與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也開始了它在東方大陸從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向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退卻的痛苦歷程。
讓我們的思考先駐足于學院派文學的前奏──學院派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從這裏啓開我們的思路。
毫無疑問,80年代大陸現代主義文學作爲一種思潮是從高校校園率先走向社會的。
而撕開8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幃幕的肇事者也正是那批涉世淺薄且故作城府深沈的男女大學生。
他們大都是取勝於激烈的高考競爭,從中學直接跨進高等院校大門的佼佼者:
“我們每人都是一座小心翼翼的火山/鬱積著無數熱情的火焰……長這麽大我們學到些什麽/考試、考試、考試──然後補考/我們是考大的/並且以後還要考!
”他們所擁有的幸運也正在於他們涉世未深的淺薄。
他們沒有充分地投入過社會,從學校到學校的直線性旅程就是他們的人生閱曆;因此,他們對歷史和社會充滿了距離感和陌生感。
也正是這種涉世未深的淺薄使他們在精神和思想上,從來就不願意背負歷史和社會的積澱所威壓給人們的東方本土傳統文化負重感。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在精神上都是赤身裸體和通體透明的自我。
美國後現代主義批評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曾給出過一種關於現代性身份的定義: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己,我在選擇和行動中創造我自己。
這種身份變化是我們自身現代性的標記。
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成爲認知和身份之源泉的是經驗,而不是傳統、權威、天啓的神諭抑或理性。
經驗是自我的巨大源泉,並且與各種他者的自我相對抗……把自已的經驗作爲檢驗真理的標準……”學院派文學聖徒們的文化心理就是這樣契合於丹尼爾·貝爾所言說的文化心理的現代性,一切盡如索姆所描敘的那樣:
“他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人。
”所謂“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人”,也就是在人格與思想上沒有被界定。
索姆在《與非門》中讓王征穩坐柏拉圖的“理式床”脫俗地高叫:
“我就喜歡這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就是西方歐陸現代哲學所倡導的人類生命的“未確定性”。
也正是這種生命的“可能性”和“未確定性”作爲文化思潮從西方歐美語境跨向東方大陸高校校園,誘惑著他們在社會和文化的空缺中自由、徹底地品嘗生命,像渴望閱讀詩歌一樣渴望讀盡社會和人生就是他們企盼的期望。
在這個意義上,淺薄恰恰構成了他們走向深沈的絕對可能性。
但是,他們跋涉出高考的泥沼步入高校校園所收攬的第一感覺,就像徐江在《青春》中所言說的那樣:
“當時大學裏流行著這麽一句口頭禪: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他們剛剛逃避了高考那種異化人格的束縛,又墜入另一個更高層次的、更文明的束縛人格的學術文化圈。
嚴格管理的准軍事化學院生活規則讓這些男女大學生們在24小時內得到的豐碩收穫,只是忘我地圍繞著一個中心周而復始:
勤奮睡覺,刻苦學習。
他們剛進校時最大收穫就是在“不許”爲開頭的命令下所建立起來的恐懼感。
自從孔子退而作“六經”創設學府而授業以來的兩千年,中國學術文化和學術文明的積澱使歷代的國學、太學、官學和高等學堂呈現出威嚴的學術文化壓抑感。
徐江在《青春》中對90歲高齡的大學捕捉到的最初印象就是:
“從暮色裏一望,陰沈莊嚴的教學樓真有點像一個略嫌嚴厲的老學者”,幾幢新樓“那不過是老學者們舊式中山裝上的幾隻新口袋而已。
一兩幢新樓是改變不了一座學院多年來形成的那種內在的氣質的。
”在這裏,學術猙獰著一位老者的威嚴面孔循循教誨著每一位學子,學術文化成爲神力無邊的法器,誰也逃不出它布下的那種神聖的恐怖和威嚴的陰影。
但是,這些青年學子的年齡指數決定了他們生命的律動跳躍在每一根神經的末稍,對他們來說,“只要有了肉,就有了火”。
青春的欲火燃燒著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就在於他們還從來沒有找到過自我。
因此,他們的未確定性人格在一切可能性中拒絕來自于大陸東方傳統學術文化的確定性(Specializtion)人格塑造。
“尋找自我”成爲他們生命存在的第一要義。
也正是如此,橡子帶著青春的野性闖入大學後的全方位感受就是“像一頭被安置在動物園裏的野獸一樣,又像被移栽到皇家園林的野生植物,不勝其寵,憂鬱、孤寂”。
自我失落了。
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總是以沈積的道德理性在確定性中成立自已的威嚴,以使得生命在文化的絕對命令中服從一切,這就是一種文明,而學術使道德理性在確定性中沈積的文明更加神聖化了。
在這裏,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在人格的未確定性和文化的確定性之間確形成了尖銳的衝突。
學術文化結構的老化和教授隊伍年齡的老化,已成爲80年代那些高齡名牌院校的老年文化病。
徐江在求知的希望中徹底地失望了:
“上課時我發現,與文學有關的幾門課實質上並沒有教會我一些什麽。
文學概論課實質上是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的翻版,古典文學則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寫作學教師的欣賞過於古怪,搞得大家全都昏頭昏腦。
有一次他竟然把一篇拙劣的抄襲魯迅風格的散文稱爲他見過的最好的文章,招來同學們許多不滿。
”在極度的失望中感慨“聽課所得幾近於零”是徐江不失高校學子風度的溫文爾雅的評價。
野舟在《發光的事物:
一個獨白》中則把評價推向了現代主義文學的詩意性調侃:
“第一次坐在我的稚氣未消的大學同窗之中,我們接受一個成年人的訓誡。
我所見的那個成年人有一隻肥厚的舌頭,它在那扇同樣肥厚的唇門裏爲戒律和美德熱烈地蠕動。
這是一次有趣的佈道:
一個笨拙的短衣神甫帶著濃重的關東口音面對一群爲自己的夢想弄得很矜持的羔羊。
我忘不了那枚沒有骨骼、跳動在陳辭濫調中的舌頭。
還有我們這群沒有骨骼、馴服的羔羊,宛如一幅匠人的月夜圖,陰柔而模糊的一輪半月在茫茫黑夜鑲嵌的白雲中運行。
”小說中的敍述話語鋪染著濃厚的西方現代派文化思潮的情緒。
實際上,徐江和野舟言說了這樣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80年代人文科學領域的陣地前沿,學術和教學都患有老年性文化症,學術和教學始終處在新陳代謝不通暢的病理狀態,那些學有建樹而年過半百的老學者像點綴在校園面容上的文化老年斑,而這就是學術功底扎實和深厚的文化象徵。
但是,他們無疑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神聖負荷者。
當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菲利普·巴格比(PhilipBagby)在《文化:
歷史的投影》中曾沈思價值和觀念積澱在文化中的代際反差:
“確實,這些被文化的負荷者建構起來的理想、準則、信仰和規範常常與表現在實際行爲中的價值和觀念有驚人的差距。
”也正是這些學術文化的負荷者用“知識”爲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建造了一個孤獨而隔膜的學術世界:
“多年的學院生活強加給我許許多多有關寫作的繁文縟節,其唯一目的無非是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規約這種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自由的個人活動。
”
但是無論如何,好奇和空虛點燃了他們處在東西文化交彙巨瀾中的生活欲望和求知欲望,在青春的野性被老年性文化症絕對壓倒的不可調和中,欲望的無可填補性又使他們必然跌入苦悶的深淵。
橡子在《穿越冰山》中以數千字的篇幅描述了他進入大學後的苦悶:
“苦悶是心靈的渴望無法滿足的折光,是一種消磨靈魂的慢性病,它潛伏在發黑的灌木叢中的某個地方,伺機向生命的陣地進攻。
最初的興奮與騷動過去之後,苦悶像陰雨天一樣,沒有警示,沒有預兆,悄悄向我們籠罩而來”,“苦悶,苦悶是我的遺産……苦悶成了生存的一種基本狀態。
”楠鐵在《幻象四種》中描寫了自己被苦悶和壓抑逼進了教堂:
“我去缸瓦寺教堂純粹是爲了感受那裏的宗教氣氛。
有一年左右的時間,每個周日我都去做禮拜,坐在教堂大廳的最後面一排,獲得一種俯視衆生的感覺。
那個時候我知道了牧師的虛僞。
”吳偉卿在《孤獨談》中以一種孤獨感來沈思孤獨:
“孤獨照原意來說應解釋爲沒有人陪伴自己,梭羅卻說:
孤獨是最好的朋友。
看似荒謬,仔細推敲,它真正道出世之常情,理之常然。
我們有時看書看得太久暈了頭,想得太多昏了頭,不免起一種孤獨的感覺……”西方現代派文化思潮的苦悶感與孤獨感在他們文本的敍述中折射出來。
但是,這無疑是他們的幸運。
因爲正是這種苦悶構成了這些學院派文學聖徒們的“最佳生存狀態”,橡子以一首小詩掬起一種難舍的孤獨:
“就像你從孤獨中逃出/走入一種更深的孤獨”,正是這種“苦悶的最佳生存狀態”把他們逐出那個孤獨而隔膜的學術世界,跌入了更深的孤獨──繆斯空間。
無疑,這是一種“詩意性逃避”。
這就是西川爲什麽在《預感》一詩中這樣詩意地呤詠苦悶:
“你又從思想中引來了黑夜/你又從苦悶中引來了風/你把風引進大門/它敲著明鏡:
我祖先的明鏡”。
“苦悶是文學的象徵”,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在苦悶的冥想中對“文學是怎樣發生”的詩意性描敘在這裏産生了同頻共振。
從西方心理學的視角來透視這些文學聖徒們,生存狀態的失衡必然導致精神狀態的缺損,平衡生存狀態失衡和修補精神狀態缺損的唯一有效選擇只能是海德格爾式的“詩意性逃避”。
自從人類創造了文化以來,人類生命存在的文化要義就是不斷地逃避文化的一生,從“逃避”到“再逃避”,這是人類命中注定在逃避的惡性輪回中不可逃避的劫數。
唯有“逃避”不可逃避。
然而,在80年代的學院派文學現象中,“逃避”已經失去了這一話語自身的本然意義。
“詩意性逃避”在被引入學院派文學聖徒們的生命之後,在這裏展現爲一種“亢奮”式的生存反抗。
在法國哲人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Pascal)那裏,“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思想”,而學院派文學聖徒的“詩意性逃避”就是爲了俘獲思想的自由,學院派文學聖徒們正是在“詩意性逃避”的思想自由中找到了自我存在及其價值,在思想上接受了法國哲人布萊斯·帕斯卡爾。
實際上,他們在詩意性逃避中就是爲了一往深情地尋找自我存在的“詩人”品格。
在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的哲學沈思中,“詩人”也正是在深切地認識到思想和文化的貧困時,先于他人以詩意的沈思發現且領悟了自我存在及其自我存在的價值。
二
在東西方的歷史上,文化的反抗者從來不是那些自視清高的文化負荷者,而是這些不曾負荷文化也不甚負荷文化的“淺薄者”,這是東西方文化史上的共通性。
在80年代中期,大陸發燒般的“文化熱”把所有自視清高的文化負荷者和不甚負荷文化的“淺薄者”統統捲入了文化的反思中。
那是一個倘若你要生存就必須反思文化的年代。
實際上,大陸80年代中期的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在這場發燒般的文化反思熱中卻處於文化的斷裂狀態。
在生存的歷程中,他們絕然沒有體驗過“文化大革命”對人從靈魂到肉體所賦予的“血與火”的洗禮,因此,他們也絕然沒有像盧新華、張抗抗、遇羅錦、張承志、鄭義、北島等那一代“老三屆下放知青”對“文化大革命”的痛苦體驗,“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傳說在他們童年夢中的一場“現代神話”。
在他們稚氣的心靈上沒有烙燙著以葬送一代人的青春和命運所烙刻下的傷痕。
歷史在精神上從不同情受難者的靈魂,往往那些被苦難的歲月折磨過的生命怎地也無法忘卻對苦澀的追憶,在學院派文學聖徒的視界中“回憶是衰老的象徵”;但歷史就是這樣把盧新華、張抗抗、遇羅錦、張承志、鄭義、北島等無情地推向對已逝去之痛苦的無限回憶之中,這也正是那一代人所擁有的文化憂患意識。
在理性的沈思中,這種痛苦的回憶從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蹣跚地走完了三個文學驛站: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終於帶著濃重的文化懷舊意識把80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推到了輝煌的極至。
黑格爾以辯證理性把西方古典哲學在體系的建構中推向了輝煌的極至,從而也宣告了西方古典哲學的終結。
的確,在理論意義上,任何輝煌的極至都意味著走向死亡的終結。
在這個理論層面上,8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輝煌極至也宣告了8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終結。
1985年,在北京大學“三角地一帶出現了幾個賣詩的人,嚷嚷著要‘打倒北島’,號稱他們的詩歌是無理論”什麽的。
嚴格地講,北島不是現實主義詩人,他的朦朧詩是新時期東方大陸現代派詩歌的濫觴,但他在創作和理論上沒有走向現代派思潮的理論自覺。
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張揚“打倒北島”,表現了他們拒斥一切權威的偏激,他們就是要使詩壇隕落霸主的太陽:
“詩壇無主,詩歌統一的太陽已經破碎。
我們拒絕以任何方式引導別人,同時我們更拒絕被別人引導,我們一度的沈默和容忍只是爲了更大的崛起。
”以北島爲首的朦朧派詩人曾經也是非常偏激的,他們張揚要以自己的朦朧派詩把崇尚現實主義的中國第一號當代大詩人艾青送火葬去。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見出在80年代,文學思潮及流派之間的衝突也是非常複雜的。
終於,現實主義文學在學院派現代主義文學張揚的非理性生命衝動中失卻了轟動效應。
的確,在現實主義文學的終結期,學院派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崛起於80年代文壇成爲歷史的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85年後仍有一些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在低潮中苟延,但全方位支撐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理論已逐漸銷聲匿迹。
就是這樣,一個以理性支撐現實主義文學的時代被另一個以非理性支撐現代主義文學的時代驅逐到了文化的邊緣。
大陸學院派文學的崛起在審美的非理性精神亢奮和意志張揚中帶著崛起的理論自覺。
學院派文學聖徒的幸運就在於他們涉世未深的淺薄使他們的創作沒有爛在生活淤積的泥沼裏,像那些在生活淤積的泥沼裏泡透、泡爛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尋根作家,一輩子沒有理論的自覺而永遠被折磨自己的生活寫自已;寫完生活後,“人到了一定年紀,詩寫到一定程度,生命激情和語言激動均被錘煉得一窮二白。
”這是橡子在《穿越冰山》中的表達。
學院派文學的創作在理論上有著自已的宣言,這些宣言的深層獨白就是學院派文學聖徒們遁入繆斯空間張揚非理性生命衝動的反抗。
學院派文學的理論宣言散見於學院派文學的各種流派之中。
這一點特別受西方諸種現代派藝術思潮的影響,他們都有著自覺的理論宣言書。
嚴格地講,學院派文學作爲一脈現代派文學思潮其內部又呈現爲審美風格不同的諸種流派。
讓我們來檢視一下學院派詩歌。
在徐敬亞選編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中,其僅集入的學院派詩歌流派及其理論宣言就有多種。
非非主義詩派宣稱:
“我們要將語言推入非確定化……我們的批評崇尚對這個世界的自由出入。
”
上海的海上詩群宣稱:
“詩歌出現了,技巧從我們的手中漸漸消失。
詩歌生命反抗著另一類‘生命’或死物。
(我們)都孤獨得可怕……躲在這座城市的各個解落裏,寫詩,小心翼翼地使用這樣一種語言。
爲了真誠……我們可以不擇手段。
”
四川的莽漢主義詩派宣稱:
“搗亂、破壞以至炸毀封閉式或假開放的文化心理結構!
……莽漢們本來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態誕生於中國詩壇一片低吟淺唱的時刻。
”
福州的星期五詩群宣稱:
“我們把星期五這個大家都清閒的日子命名於詩群。
我們沒有自稱什麽流派,近乎是爲了能更自然地窺視出詩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那部分。
”
杭州的極端主義詩派宣稱:
“(詩)崇尚借代!
崇尚極端!
反對模式!
文明對於它來說不過是一件破衣服……詩歌必須從虛無中走回來,回到最基本的層次。
詩歌就是極端。
”
上海的撒嬌派詩人們宣稱:
“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慣。
看不慣就憤怒,憤怒得死去活來就碰壁。
頭破血流,想想別的辦法。
光憤怒不行。
想超脫又捨不得世界。
我們就撒嬌。
……寫詩就是因爲好受和不好受……只是因爲撒嬌詩會上撒了太多的嬌,我們才被人稱作爲撒嬌詩人。
”
全國的大學生詩派宣稱:
“大學生詩派本身僅僅作爲一股勢力的代號被提出。
它具有不確定意義。
當朦朧詩以咄咄逼人之勢覆蓋中國詩壇的時候,搗碎這一切!
……它所有的魅力就在於它的粗暴、膚淺和胡說八道。
它要反擊的是:
博學和高深。
”
安徽的病房意識派在宣言中稱:
當代社會意識的典型特徵,就是“病房意識”這種意識氛圍。
詩人是一群叫驢。
詩本身在今天無所謂形式。
詩內容是自己的當然的蹄印。
詩語言,應如同驢鳴,怎麽得勁就怎麽嗥。
這就是東方大陸學院派文學特有的“詩加哲學式的反抗”,也是東方大陸學院派文化在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下,把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投射在東方大的漢語文學創作中。
結集出版的《中國當代先鋒詩人叢書·總序》宣稱:
“詩的本質特徵,亦即海德格爾所說的詩的‘神’性,……先鋒詩人的詩都處於地下或半地下狀態,也許非得有一次大的地殼運動,他們才有可能重見天日。
”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來透視東方大陸中國學院派文學,支撐學院派文學創作理論的阿基米德點是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和西方後現代主義哲學。
嚴格地講,學院派文學聖徒們是棲息於東方大陸高校校園的西方現代派哲學的實踐者。
他們爲什麽帶著炎黃先祖注入娘胎的血腥氣呱呱墜地于華夏大陸本土,卻如此鍾情地一頭撲進西方哲學思潮與文化思潮的懷抱?
這是一個值得歷史爲此沈思的文化命題。
涉世未深的淺薄使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在代際文化的斷裂中所鑄造的未確定性人格從來就沒有文化負重感,社會的陌生感和歷史的距離感又使本土文化傳統對他們的人格心理侵蝕不奏效;因此,在人格的深層文化心理上,他們拒絕承受著沈重的文化負重感去沈思民族文化的命運,這種未確定性人格的開放文化心理使他們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成爲可能。
10年“文化大革命”作爲一場浩瀚的東方現代宗教偶像塑造運動,它以“一言爲天下法”的現代宗教聖語曾剝奪和毀滅了一個民族的思考,從而在民族的靈魂振蕩中形成了文化真空和思想真空。
正如當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托馬斯·伯恩斯坦所描述的:
“那些不能上大學的人所體驗的被遺棄的感覺……1968年下鄉的紅衛兵普遍感到幻滅,覺得自己被出賣、被利用。
”“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性終結反而使一個民族在習慣和適應於崇聖性思維中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
那批被生活的苦澀泡透、泡爛的現實主義作家們因此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而惶惑著,當他們用回憶向本土漢語文化傳統的舊日國度討回曾咀嚼過的苦難,用理性去沈思民族的命運時,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卻跨越了本土文化逃避到西方哲學的智慧搖籃中,去捕捉西方智者哲人的思想閃光。
從外域文化接受史的角度來看,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西方智者哲人的思想總是在東方大陸封建黑暗結束的黎明時刻作爲一脈曙光,啓蒙著這個古老的民族。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西方思想巨匠辭世後的思想餘輝曾完成了對這個古老民族的第一次文化和思想的啓蒙。
“文化大革命”終結後的文化真空和思想真空也必然導致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侵入封閉的現代東方大陸,從而形成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和思想的啓蒙;這也是世界東西方文化和思想對抗格局解構之際的歷史必然趨勢。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預言了這種歷史的必然性趨勢。
因此,東方大陸學院派文學聖徒們帶著青春的野性貪婪地擁抱著西方的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克爾凱戈爾、薩特、海德格爾、帕斯卡爾、弗洛伊德、馬斯洛、拉康、傑姆遜、德裏達、哈貝馬斯、利奧塔、福柯、賽義德、斯皮瓦克、巴巴等這些西方現代派、後現代派哲學家。
歷史就是這樣,殘酷地讓這些“淺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