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docx
《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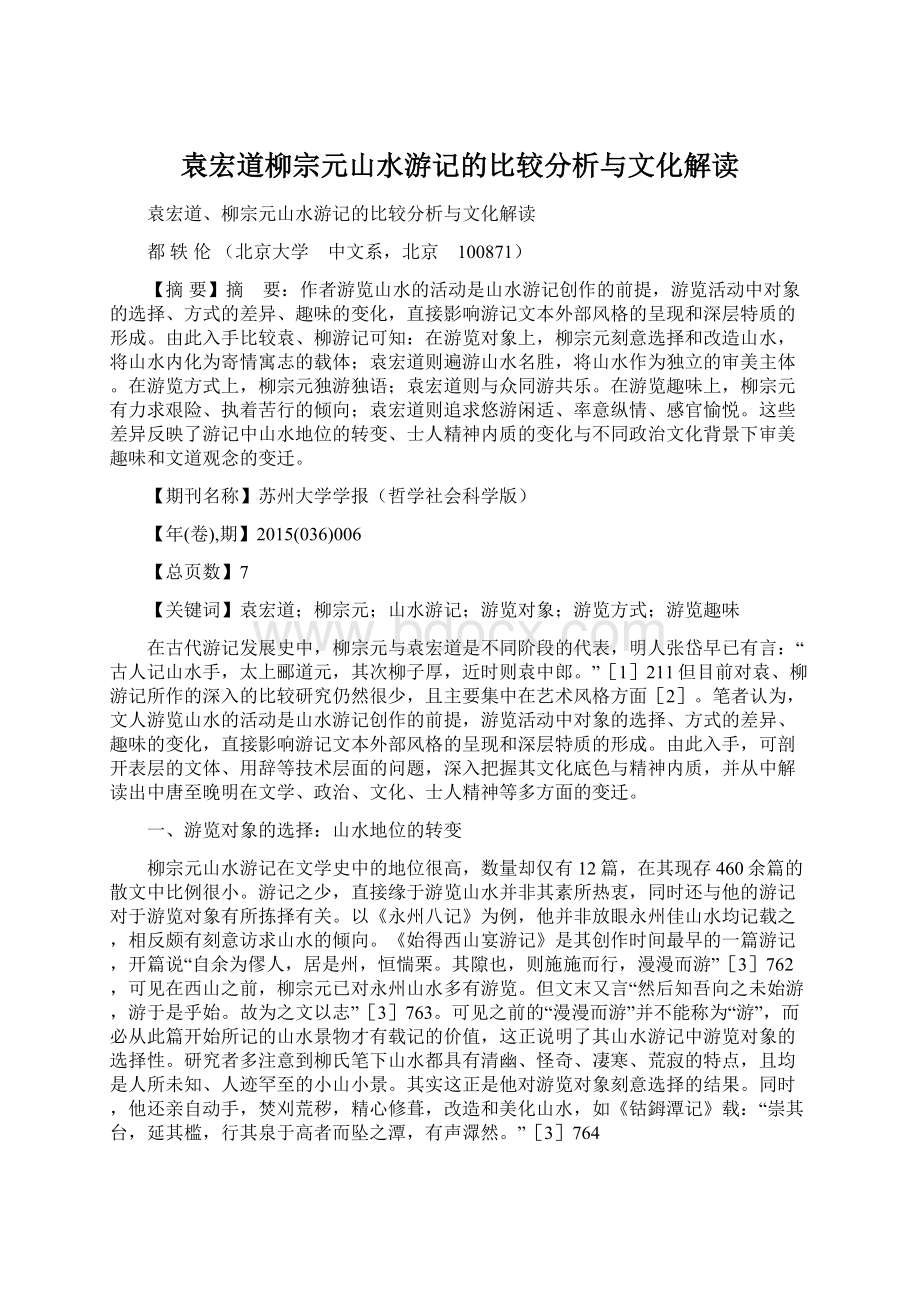
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
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
都轶伦(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摘 要:
作者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游记创作的前提,游览活动中对象的选择、方式的差异、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游记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和深层特质的形成。
由此入手比较袁、柳游记可知:
在游览对象上,柳宗元刻意选择和改造山水,将山水内化为寄情寓志的载体;袁宏道则遍游山水名胜,将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
在游览方式上,柳宗元独游独语;袁宏道则与众同游共乐。
在游览趣味上,柳宗元有力求艰险、执着苦行的倾向;袁宏道则追求悠游闲适、率意纵情、感官愉悦。
这些差异反映了游记中山水地位的转变、士人精神内质的变化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审美趣味和文道观念的变迁。
【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6)006
【总页数】7
【关键词】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游览对象;游览方式;游览趣味
在古代游记发展史中,柳宗元与袁宏道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明人张岱早已有言: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
”[1]211但目前对袁、柳游记所作的深入的比较研究仍然很少,且主要集中在艺术风格方面[2]。
笔者认为,文人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游记创作的前提,游览活动中对象的选择、方式的差异、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游记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和深层特质的形成。
由此入手,可剖开表层的文体、用辞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深入把握其文化底色与精神内质,并从中解读出中唐至晚明在文学、政治、文化、士人精神等多方面的变迁。
一、游览对象的选择:
山水地位的转变
柳宗元山水游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很高,数量却仅有12篇,在其现存460余篇的散文中比例很小。
游记之少,直接缘于游览山水并非其素所热衷,同时还与他的游记对于游览对象有所拣择有关。
以《永州八记》为例,他并非放眼永州佳山水均记载之,相反颇有刻意访求山水的倾向。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其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游记,开篇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3]762,可见在西山之前,柳宗元已对永州山水多有游览。
但文末又言“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故为之文以志”[3]763。
可见之前的“漫漫而游”并不能称为“游”,而必从此篇开始所记的山水景物才有载记的价值,这正说明了其山水游记中游览对象的选择性。
研究者多注意到柳氏笔下山水都具有清幽、怪奇、凄寒、荒寂的特点,且均是人所未知、人迹罕至的小山小景。
其实这正是他对游览对象刻意选择的结果。
同时,他还亲自动手,焚刈荒秽,精心修葺,改造和美化山水,如《钴鉧潭记》载:
“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
”[3]764
《石渠记》载:
“予从州牧得之。
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
”[3]770均是按照柳宗元本人的审美眼光,对自然景观进行重构。
可见柳氏不仅刻意寻访山水,还刻意改造山水。
与柳氏不同,袁宏道山水游记小品数量很多,现存文集中所收共计86篇,时间跨度纵贯其一生。
可见游览山水在袁宏道人生历程中的地位。
他游记中的游览对象,全然没有柳宗元那样着意拣择的倾向,而皆为其历官宦游或闲居林下时所经所见;也不像柳宗元那样刻意找寻人所未知的小山小景,而多为名山大川。
如他游览江南时所作《虎丘》《西洞庭》《东洞庭》《灵岩》《百花洲》《姑苏台》《游惠山记》《西湖》《孤山》《飞来峰》《灵隐》《龙井》《禹穴》《兰亭记》等,无一不是当地久已闻名、游人趋之若鹜的胜地佳境。
他赴京城后所作《满井游记》《游盘山记》为京郊胜景,而闲居公安时所作《入东林寺记》《云峰寺至天池寺记》《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由天池踰含嶓岭至三峡涧记》《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识庐山记后》均为庐山胜景,任职陕西时所作《游骊山记》《华山记》《华山后记》《华山别记》《嵩游》《游苏门山百泉记》亦均为名山大川。
游览对象的特点,体现出袁、柳二人对山水的不同态度。
柳文中的山水已经不是自然形态下的山水,而是按作者主观好恶着意选择和改造的山水。
有研究者认为,柳宗元游记为再现型游记,以描摹和刻画自然山水为主,而自我感受的抒发不占主导地位[4]183。
实则不然。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本质上并非为描摹山水,而是一种隐喻,是其在永州期间复杂心态的隐晦记录。
所以他笔下的山水景色均带有清幽、怪奇、荒寒的特点。
袁宏道则大为不同,他所赏爱的更多是山水本身,所以风格各异的山水风景均为其所欣赏流连、由衷赞叹。
表面上看,柳宗元更多是客观静摹山水,拟人与个性抒发较少;而袁宏道游记的个人情感抒发则大为增加,自我的地位在游记中得到提升[5]。
但从本质上看,柳宗元是将自我隐于山水之间,其笔下摹写的山水就是其自我人格的展现,看似是客观描写,实际上却已经过了人格化的投射。
若就作者对山水的精神内化程度而言,柳宗元是胜于袁宏道的。
游览对象的区别,还反映出山水在游记中地位的转变。
在柳宗元游记中,山水作为作者情感的投射,缺乏独立的地位,实质上只是喻体而非主体。
在袁宏道游记中,山水和作者是平等交流的关系,有其独立地位,而成为游记的主体。
袁宏道在《题陈山人山水卷》中言:
“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
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
”[6]1582直把山水作为与己平等的至交好友。
他在《游高梁桥记》中又言:
“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
”[6]682可见山水美景并非专为袁宏道一人,而是以一种独立开放的姿态面对所有游人。
江盈科在《解脱集序》中也说:
“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
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
”[6]1691此语肯定袁宏道笔下山水的人格化特征,而其中所言“貌神情”,是山水自身之神情,而非袁氏本人之神情。
也正因为其笔下的山水有着独立的主体地位,而非作者情感的单向投射,所以袁宏道游记中呈现出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山水形象也就不奇怪了。
更进一步说,柳宗元是为己而游、为己而记,作者本人是其所游景致的主宰者,是发现者和改造者,游览过程是刻意为之的,作者的情感心志是游记的内核;而袁宏道是为游而游、为游而记,作者更多是其所游景致的欣赏者,是旁观者和对话者,游赏过程是自然率性的,对风景的审美愉悦是游记的内核。
山水在游记中地位的转变,又与两者不同的游览动机直接相关。
柳宗元贬谪之前并未措意山水,贬谪后才被迫流连山水,山水只是一种寄托,在游记中也自然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
而袁宏道则是主动游览赏爱山水。
他在《游惠山记》《答陶周望》等篇中均明确直言其山水癖之深,如“意未尝一刻不在宾客山水”“游山若碍道,则吃饭着衣亦碍道矣”等,把游览山水视为生活之必需,与日常吃饭穿衣同等重要,甚至主动辞官而悠游山水。
山水在袁宏道人生中所占据的这种重要地位,促使他重视和欣赏山水本身的美,其游记中山水占据主体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游记中山水地位的转变,并非是袁宏道这一个体的单例,而是有着整个山水游记发展变迁的大背景。
明代中后期开始,对游记的认识较前代有了较大突破,游记小品大量出现,对过去以山水比德,借山水抒幽愤,由山水体悟哲理等写作模式有所改变。
清初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中就指出柳宗元游记“不过借山水一丘一壑,以自写胸中块垒奇崛之思,非游之大观也”[7]1270,而推崇《徐霞客游记》以山水为主
体,对山水进行亲身游历和真实记述。
《徐霞客游记》虽与袁宏道等人的游记小品有很大区别,但同为明代中后期游记的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前人不同的更重视游览对象的主体性,对山水在名教道德功利之外的本身的意义和地位加以重新发现和提高。
山水由士大夫借以托情寓志的附庸,转为更纯粹的欣赏和游玩的直接对象。
这或许也是文学和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和平民,以及山水从古典情志审美文化走向近现代旅游休闲文化的一种反映。
二、游览方式的差异:
独乐与众乐
柳宗元的游览方式具有鲜明的“独”的特征。
正如他在《江雪》诗中所描摹的“独钓寒江雪”那样,柳宗元的山水游览方式也经常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的。
《永州八记》中,《小石城山记》《石涧记》《石渠记》《袁家渴记》四篇皆仅有柳宗元一人出现,游览兴叹均为其独自一人所为。
其余四篇游记中虽然出现了一二位别的人物,但这些人或者并未参与游览活动,如《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卖地于柳宗元者;或者虽与柳氏同游,却并未真正成为山水游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未与柳宗元在游览中发生互动,而只是具列姓名作为实录而已,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同游者和《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仆人。
因此,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虽偶有他人的存在,本质却是柳宗元一人的独游、独语和独感,是自记游踪、自我抒写的孤寂篇章。
与柳宗元不同,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中,除他本人以外的其他人物,也占了相当的分量。
袁宏道所游多风景名胜,游人如织的情况是常有的,这在其游览东南苏杭之地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虎丘》[6]157-158一文共分四节,第一节从“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开始,大量篇幅所述均为游人之多,场面之热闹。
第二节更以整节的篇幅,描绘歌者吟唱之声之态,亦备极形容。
此篇以游人、歌者的出行娱乐场景为主,而将作者本人和景物置于次要地位,由喧哗众生构成的世俗场面成了主要的描写对象。
这与柳宗元以本人作为游记唯一的中心人物,以清幽凄静的景色为主要描写对象,恰好相反。
除《虎丘》之外,《荷花荡》一文更是全篇皆述游人游冶之态而不叙荷花荡之风景,直以游人为风景。
《光福》《西湖二》《湖上杂叙》等篇叙述游人情态的篇幅亦复不少。
除了游人之外,友人对游览过程的直接参与和互动,也常是袁宏道游记中的要素,往往占据大量篇幅。
其谓:
“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
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6]506袁宏道眼中三大败兴之事,无友朋相伴占据其二,可见友人在其生活特别是游览活动中的地位。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篇末仅列同游者姓名作为记录。
袁宏道《上方》则在具列姓名之外,还记录了同游者直接参与游览活动的情况:
“乙末秋杪,曾与小修、江进之登峰看月,藏钩肆谑,令小青奴罚盏,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胜,始归,归而东方白矣。
”[6]160情致盎然,其乐融融。
类似者还有如《飞来峰》篇末所记“初次与黄道元、方子公同登,单衫短后,直穷莲花峰顶,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6]428。
有些游记还以对话形式将游览过程中作者与友人的互动过程加以生动记录。
如《鉴湖》[6]445《西施山》[6]446二文记录了作者与陶望龄游赏对答之语,《百花洲》[6]178更将作者与江进之的对话作为全文的主要内容。
更有甚者,直以与友人同游之事构建全篇,形成多人游览的场景,如《御教场》[6]435《五泄一》[6]447-448二文。
以上所述袁、柳之异,其实体现出了二人“独乐”与“众乐”之别。
而这种不同的游览方式的取向与前文所论山水在二人游记中地位变化有直接关系。
柳宗元游记中的山水景观世界是他心灵的内化,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自我的,独自欣赏玩味便可,不愿也无法与他人分享,故而不需要他人的参与。
而袁宏道的山水世界则是常人所乐的人间胜境,是开放的、共享的。
人间的烟火气,朋友之间的人情温暖,与在美景中的自适,构成了袁宏道游记中同等重要的审美要素。
这种由“独”到“众”的转变,特别是游人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在社会与文化背景的转变中,文人士大夫从独特的个人审美趣味走向寻常的世俗审美趣味,从个人的精神世界走向现实的人情世界的明显变化。
在袁宏道游记中,游人大众带来的喧嚣热闹、众乐和合,友朋知己间的同乐、笑谑,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世俗情调,更是一种太平繁盛的假象,一种人情温暖的寄托。
在众乐之中,袁宏道对现实的忧虑以及精神上的无奈苦痛或可得到缓释。
矢志革新而遭远贬的柳宗元所面对的现实的困境与精神的苦痛深于袁宏道,他游
览山水也时有友朋或仆从相随,但他显然不愿意通过与游伴的对答笑谑来消解现实与内心的双重苦难,而选择在孤寂的自我精神世界中独自面对、消化和承担,这体现出士大夫独立、孤高的精神力量。
相较而言,晚明士人的精神在物欲消磨下似乎是有些弱化了。
三、游览趣味的取向:
苦行的执着与游者的纵情
因遭遇黜降贬谪,寄意山水以自放,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经历中是一种常有的形态,所以研究者也多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归为贬谪情结下的产物。
但一般失意文人游赏山水,大多是为了在名山大川中领略自然美感,以排遣忧愁。
稍加对比,柳宗元山水游记之不同便显示出来了。
他不仅在游览对象上选择险峻怪奇、人所未知的荒僻之地,而且游览趣味也总是主动寻求艰苦的道路: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望西山,始指异之。
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
(《始得西山宴游记》)[3]762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3]767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石涧记》)[3]772
他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明言其游览趣味:
“游之适,大率有二:
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
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
”[3]748可见柳宗元所喜爱的游览过程,一是在险阻陡峭之地,走出幽暗,突现一片开阔光明之景;二是抵达丘陵,经过荒莽,走过狭窄迂回的道路,走向幽密深邃的处所。
距离之远、道路之狭窄峭险,均无法阻碍其游览。
即使遇到无路可走的情况,也绝不停下,而与仆人一起“斫榛莽”“焚茅茷”“伐竹取道”,硬是从中辟出道来。
他追求的绝非流连美景、赏玩自适的游者之乐,而是在开山辟道中力求艰险、百折不回的苦行者之趣。
这种独特的游览趣味,很难用贬官情结来解释,因为与柳宗元同时遭逢贬谪的韩愈、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山水诗文所表现的情致和游赏趣味,都与柳宗元不同。
柳宗元这种游览趣味的背后,有其深层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因素。
袁宏道在这方面与柳宗元大相径庭。
他在游览过程中,不仅如自古文人游赏山水时的普遍状态那样,充满了悠游闲适之趣,且更为率意、任情甚至有些放纵。
以名篇《雨后游六桥记》为例:
寒食雨后,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
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
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
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
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
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6]426落红满地,桃花作别,本是颇为伤感之事,而雨后更当是一番清景,在这种情境下,往往会引人伤春叹逝。
但袁宏道却将其视为赏爱欢愉之景,偕诸友以游。
在游览之外,还躺在地上喝酒,以面受花,最后乘舟欢歌而返。
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士人闲适之乐的界限,而颇带任情放纵的游戏性。
在袁宏道的游记小品中,类似这样的篇章还有很多。
在其游览过程中,诸如舟、车、马、酒都是常备之物,游程中常伴随着谈笑、唱酬、嬉闹、醉酒等行为。
上文曾述及他在游览中与友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就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诸如“放舟湖心,披襟解带”(《阴澄湖》)[6]168,“强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御教场》)[6]435,“醉甚,戏弄马鞍上,几堕”(《六陵》)[6]443等等,都是袁氏游记中常见的情景。
如果说这种颇带放浪形骸性质的游览方式是受影响于所谓“夷以近”的东南繁华胜景,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袁氏叙写的“险以远”的登山游记:
泉莽莽行,至是落为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纤鱼数头,尾鬣可数,落花漾而过,影彻底,忽与之乱。
游者乐,释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则皆跃入,没胸,稍溯而上,逾三四石,水益哗,语不得达。
间或取梨李掷以观,旋折奔舞而已。
(《游盘山记》)[6]688
袁宏道在篇首曾概述此山“峭石危立,望之若剑戟罴虎之林”“游者可迂而达”“其山高古幽奇,无所不极”。
这与柳宗元在永、柳所游诸山相似,若柳宗元游此山,则必又是穷山之高、路之遥、道之狭,专门寻觅幽密深邃之地,开山辟道,极尽艰难。
而袁宏道一行人却悠然自得地欣赏美景。
见到清澈的潭水,如柳宗元,则必会感觉“凄神
寒骨,悄怆幽邃。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记》)[3]767。
但袁宏道他们却只觉得愉悦、兴奋,戏水嬉闹,毫无顾忌。
袁宏道也有好奇险的一面,在《游盘山记》以及游庐山、华山、嵩山诸记中均有体现。
但他好奇险是为了欣赏美景,获得身心最大的愉悦,如其所言“世上无判命人,恶得有此奇观也”(《游盘山记》)[6]689。
游览过程本身的危险性,在他那里也带有了寻找刺激的味道,其自言“至遇悬石飞壁,下蹙无地,毛发皆跃,或至刺肤踬足,而神愈王。
观者以为与性命衡,殊无谓,而余顾乐之”(《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6]1140,“扪级而登,唯恐险之不至”,“怖一而喜十,绝在奇也”(《华山别记》)[6]1473。
这显然大不同于柳宗元式的力求艰险的苦行的执着。
袁宏道在山水中纵情愉悦、追求感官上的享受,在其游记中还表现为大量的对山水的鉴赏评价之语。
其中偶尔会评点不足,但更多则是褒扬赞叹,如《西洞庭》[6]161-162就从山、石、居、花果、幽隐、仙迹、山水相得等七个角度总结出西洞庭风景的七胜。
除了给出具体评鉴外,他有时还会介绍自己独特的欣赏方式,如欣赏西湖景色不宜登高俯视:
“余为西湖之景,愈下愈胜,高则树薄山瘦,草髠石秃,千顷湖光,缩为杯子。
”(《御教场》)[6]435在这些具体的品评中,山水风景除了自身的审美特质外,没有像传统山水游记尤其柳宗元游记中的山水那样,附带任何超越的引申的意义,而是将山水还原成自然本体去欣赏,目的也仅在于获得心情的愉悦和感观上纯粹的审美享受。
除了游览时的纵情愉悦外,袁宏道在对山水景色游览和欣赏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就是喜欢拟之以美女。
如《灵岩》:
“廊下松最盛,每冲飚至,声若飞涛……此美人环佩钗钏声。
”[6]165《满井游记》:
“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
”[6]681《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水至此亦敛怒,波澄黛蓄,递相亲媚,似与游人娱。
”[6]1154例多不赘。
笔者以为,这一特点不仅是一般认为的在山水人格化比拟方面的新突破,还应看作是袁宏道在山水游赏中进一步加入世俗元素的一种体现。
声色之欲,虽是人的本能需求之一,却从来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但在晚明文化背景下,作为自适享乐的需要,士大夫公然宣扬追求女色并非罕见。
袁宏道自己就是深陷其中者。
他在著名的尺牍《龚惟长先生》[6]205中提及人生五乐,其中就有女色。
他还曾言:
“生平浓习,无过粉黛。
”(《顾升伯修撰》)[6]1232“往时亦有青娥之癖。
……今已矣,纵幽崖绝壑,亦与清歌妙舞等也。
”(《李湘洲编修》)[6]1233甚至还在诗中直言:
“见色不见山,此是山三昧。
”(《舟中望黄山》)[6]998就直接把游览山水与女色之乐联系在了一起。
其弟袁中道曾言:
“山水可以代粉黛……兄书中道及嘲胡仲修语,将谓世间人游山水者,乃不得粉黛而逃之耳……此真觑破世人伎俩也。
”(《答钱受之》)[8]1025-1026袁宏道的山水之癖,似也可以此来理解。
他中年后因纵情声色而健康日损,于声色之娱渐有收敛,却更加深了对山水游览的兴趣,或可视为一种欲望实现形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似有“不得粉黛而逃之”之嫌。
他将美色之喻大量引入山水游记,对于这一文体的冲击是很大的。
山水游记一直都是士人寻求自我人格提升和超越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在袁宏道这里却被赋予了浓厚的世俗人欲的成分,具有了近代人文色彩。
这在上述柳宗元和袁宏道游记游览趣味的对比中,表现得很清楚。
而二人游记之间存在的这种种差异,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两者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
四、文化背景的差异:
家世、政治的寄寓与市民文化的消遣
柳宗元在游览对象、方式、趣味方面的特点背后蕴含了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
简言之,这与柳宗元出身贵族世家又终生系心政治有关。
唐代家世门第观念浓重,家世背景在士人精神世界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构成了士人的情感倾向和文化底色。
柳氏在北朝至于隋唐,都可称是著名的门阀士族,“自中书以上,为宰相四世”[3]329,处于权力中心。
柳宗元身上带有唐代浓重的贵族世家文化色彩。
另一方面,政治抱负是士大夫精神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柳宗元被家族寄予了复兴厚望,早年积极从政,表现出急切的政治上进心和济世意识,然而遭到了当权者的敌视而被贬,贬地又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山水之地。
对于出身贵族世家又有极强政治抱负的柳宗元而言,贬谪对他产生的情感冲击是大大超过他人的。
他的游记和山水诗,虽力图以山水美景解忧,却始终“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看似超脱与出世,却内蕴着深厚的愤激与入世情怀,始终无法从家世与政治的羁绊中脱身。
由此看来,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经
常展现的旅程的艰辛、风景的奇险与他心怀忧恐、肩负压力、仕途艰危的现实境况之间,克服旅途之艰险、开山辟道、探访幽密之境与他虽处境艰危而无法舍弃政治抱负、仍执着追求的心境之间,改造荒弃之地而成优美风景与他不忘改革、怀抱理想的冀望之间,应该都存在一定的隐喻关系。
与其所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柳宗元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他在贬谪永州期间所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提出的“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3]873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又说:
“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
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
”[3]824可见在贬谪期间,“辅时及物之道”在其价值观中仍然是一以贯之的重要,只是因为贬谪而不能干预政治,所以将精力转向了可以从事的写作“以明道”“垂于后”。
故他在山水游记中始终含有个人身世和现实政治的寄托和隐喻,并不奇怪。
因而后世古文流派推崇包括《永州八记》在内的柳文,笔者以为本质上并不完全在于文体和语言上的古雅与法度,而主要在于他在山水中所寄寓的士人政治情感,符合古文的文以载道、托物言志的审美标准。
故其题材虽是悠游山水,主题却是严肃的,是符合文统道统的,其文体也因而是庄重的,是古典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与之相比,袁宏道所处的文化背景就大为相异了。
唐末五代战乱使传统贵族世家遭到沉重打击,宋代又将科举考试的规模扩大,录取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世家大族垄断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下层平民开始有更多机会晋身仕途乃至进入权力中心,社会阶层的流动加快。
下层平民参加科举进入政坛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平民文化、平民意识带入了士人文化中,整个社会文化随之转变。
一般认为晚明小品文所受的最大影响来自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这与宋代开始的文化背景的转变是有关系的。
具体到袁宏道所生活的晚明万历年间,一方面,由于政局的黑暗,许多文人看不到希望,就逐渐把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抱负从肩头卸去,远离政治,在追求自我身心愉悦中获得解脱和逃避。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整个社会出现了竞尚奢华享乐的风气,市民文化极为繁荣。
如游览山水,在晚明就已经发展为全民共尚的休闲生活方式。
在这种社会背景和风气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趋向世俗享乐也是很自然的。
同时,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传统儒家思想对士人的束缚已经非常薄弱,心学的传播和兴盛更为人欲解放和世俗享乐提供了思想上的根据。
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之个人的性情和遭际,袁宏道的审美趣味、政治态度等方面,当然也与传统存在很大差异。
他的审美趣味中虽然仍有古典审美理想中的高雅的成分,但市民文化中感性的、生理的欲望所促成的审美趣味却更为重要和明显,这种审美趣味,有时甚至脱离了美感的范畴,而沦入了快感的领域。
在山水游记之外,袁宏道小品中还有一些描写市井玩物的篇章,如《畜促织》《斗蚁》《斗蛛》等,这类文字也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文集中,足见市民文化对于文人士大夫的影响程度之深。
袁宏道不是没有政治抱负,对社会现实也不是没有关注,他对晚明国势衰退、朝政腐败、危机四伏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也有痛切之无奈。
但对现实的忧虑和精神的痛苦似乎并没有内化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柳宗元遭遇贬谪仍不改初衷的执着、深厚的政治情怀相比,他选择适世来做消极的逃避,追求自在惬意的人生,几次主动辞官游览山水就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