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民文化之诗意建构.docx
《现代市民文化之诗意建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市民文化之诗意建构.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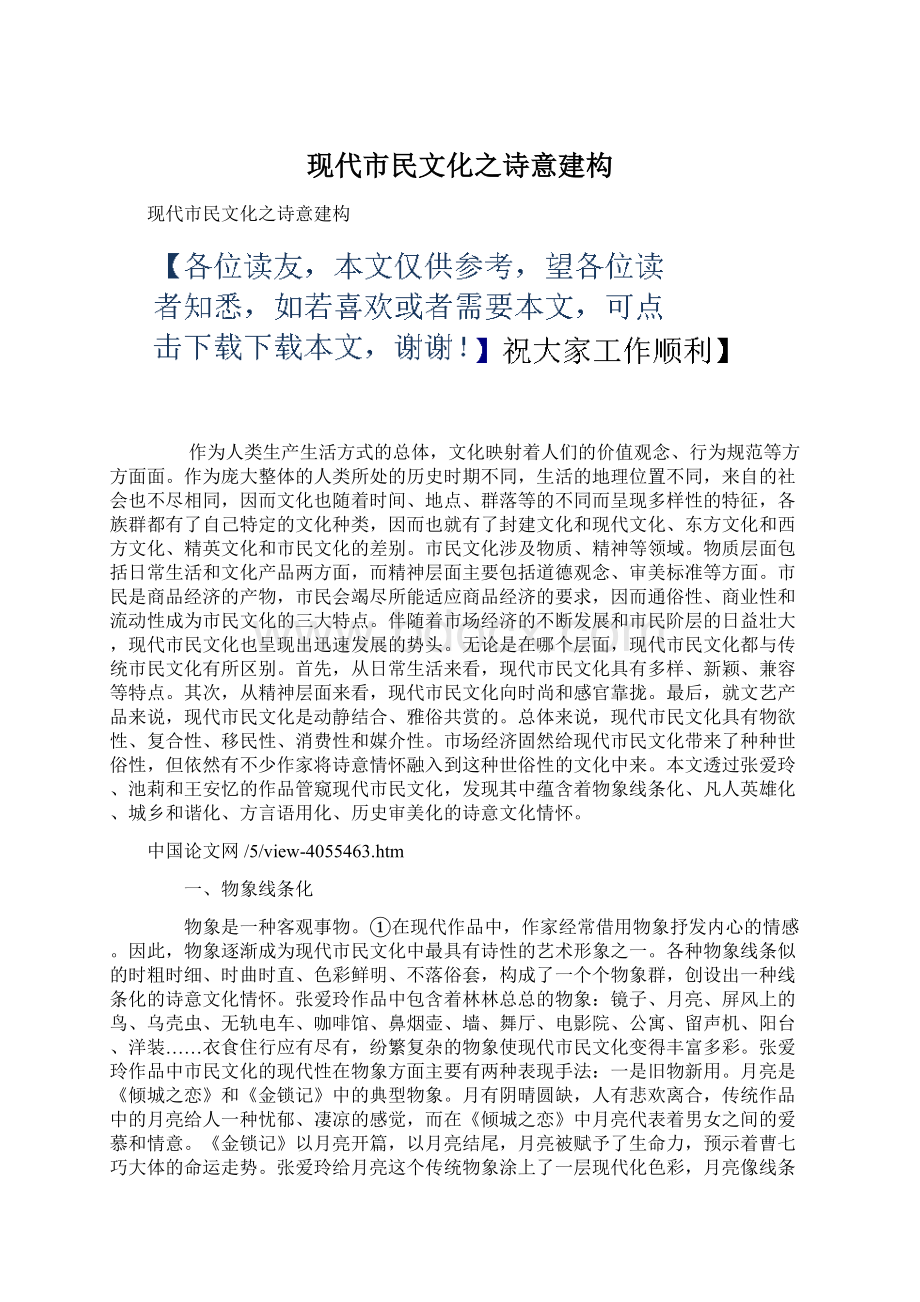
现代市民文化之诗意建构
现代市民文化之诗意建构
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总体,文化映射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
作为庞大整体的人类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的地理位置不同,来自的社会也不尽相同,因而文化也随着时间、地点、群落等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各族群都有了自己特定的文化种类,因而也就有了封建文化和现代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差别。
市民文化涉及物质、精神等领域。
物质层面包括日常生活和文化产品两方面,而精神层面主要包括道德观念、审美标准等方面。
市民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市民会竭尽所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因而通俗性、商业性和流动性成为市民文化的三大特点。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现代市民文化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
无论是在哪个层面,现代市民文化都与传统市民文化有所区别。
首先,从日常生活来看,现代市民文化具有多样、新颖、兼容等特点。
其次,从精神层面来看,现代市民文化向时尚和感官靠拢。
最后,就文艺产品来说,现代市民文化是动静结合、雅俗共赏的。
总体来说,现代市民文化具有物欲性、复合性、移民性、消费性和媒介性。
市场经济固然给现代市民文化带来了种种世俗性,但依然有不少作家将诗意情怀融入到这种世俗性的文化中来。
本文透过张爱玲、池莉和王安忆的作品管窥现代市民文化,发现其中蕴含着物象线条化、凡人英雄化、城乡和谐化、方言语用化、历史审美化的诗意文化情怀。
中国论文网/5/view-4055463.htm
一、物象线条化
物象是一种客观事物。
①在现代作品中,作家经常借用物象抒发内心的情感。
因此,物象逐渐成为现代市民文化中最具有诗性的艺术形象之一。
各种物象线条似的时粗时细、时曲时直、色彩鲜明、不落俗套,构成了一个个物象群,创设出一种线条化的诗意文化情怀。
张爱玲作品中包含着林林总总的物象:
镜子、月亮、屏风上的鸟、乌壳虫、无轨电车、咖啡馆、鼻烟壶、墙、舞厅、电影院、公寓、留声机、阳台、洋装……衣食住行应有尽有,纷繁复杂的物象使现代市民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张爱玲作品中市民文化的现代性在物象方面主要有两种表现手法:
一是旧物新用。
月亮是《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的典型物象。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传统作品中的月亮给人一种忧郁、凄凉的感觉,而在《倾城之恋》中月亮代表着男女之间的爱慕和情意。
《金锁记》以月亮开篇,以月亮结尾,月亮被赋予了生命力,预示着曹七巧大体的命运走势。
张爱玲给月亮这个传统物象涂上了一层现代化色彩,月亮像线条那样或粗或细,传达出一种诗意。
另一种表现手法是新物细刻。
这一类物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封锁》中的乌壳虫,作者在结尾处对乌壳虫进行了细细地刻画:
乌壳虫从房间的这头爬到了那头,灯开的时候它就停在了地板的中央。
②在这里乌壳虫就是吕宗桢本人的象征,封锁的过程中,吕宗桢从电车的那头走到了靠近吴翠远的地方,而封锁解除后,他又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吕宗桢就跟这只乌壳虫一样:
从这头跑到那头,最后停止不动,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这只现代化的乌壳虫走过的路像线条那样或曲或直,投射出诗性般的文化情愫。
物象在池莉的作品中有着更深刻的现代内涵,她摈弃了传统物象的写法,为物象的现代诗性书写开辟了新的天地。
《心比身先老》让人浮想联翩:
藏族高原上骑马的汉子带着备受冷落的汉族女子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奔跑,蓝天、白云、大地都成为人物的衬托,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幻化成幽美、深长的线条。
此外,武汉这座城市中比较有名的街道在池莉作品里随处可见,如“花楼街”、“汉正街”等等,各种街道排成了一条线。
池莉作品中比较有趣的物象还有《太阳出世》中的“天皇皇”,张贴“天皇皇”是赵胜天为解决朝阳哭闹问题而采取的措施,这一百张“天皇皇”成了现代都市中一段亮丽的风景线条。
同样是以上海为写作背景,王安忆笔下的物象与张爱玲的却不尽相同。
王安忆在《长恨歌》开篇就罗列了大量的物象:
弄堂、街道、楼房、天窗、瓦、月季、衣衫、山墙、阳光、水泥、晨雾、白鸽……这些物象具有明显的地方格调和区域风情,构成了色彩不均的线条,流露出一座城的诗意。
可见,物象的内涵和外延在现代市民文化中被线条化了,这种线条化的物象不断散发着诗性的光芒。
二、凡人英雄化
传统文化中的英雄指的是那些拥有优秀思想品质、武勇超群、舍己为人、值得人们钦佩的人物。
现代市民文化对英雄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英雄并不是那些具有超常能力、对他人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代名词,而是指那些虽然历经苦难却不认输,虽然普通却热爱生活的世俗人物。
现代市民文化中的新英雄是作家抒发诗意情怀不可或缺的一笔。
现代市民文化视域下的英雄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女性,突出体现在池莉的小说中。
《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努力逃出父母的双翼,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婚姻。
温泉并不喜欢父母安稳的生存哲学,而是尽量实现人生飞扬,凸显出清新、自由的诗意理想。
《不谈爱情》中的吉玲以汉口小市民特有的方式同家庭情况比自己优越的庄建非周旋,最终不仅赢得了尊严,而且使自己的婚姻具有传奇色彩,富有诗性。
《月儿好》塑造了月好这一开朗乐观的女孩,月好如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给人以卓尔不俗的诗意感受。
张爱玲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
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牢牢抓住了自己喜欢的金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了自己的前途毅然投入自私吝啬的梁太太和花花公子乔琪的怀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成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婚姻。
她们谋求幸福的手段有违常规,但她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诗意魅力。
其次是具有良好生活能力的男女凡人英雄。
池莉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向我们描绘了武汉普通百姓是如何化解高温烦恼,进而将高温下的生活变成其乐融融的风情画的,这种温馨的场景将读者带入了诗情画意之中。
《太阳出世》将美好生活打破了,将现世生活摆在了人们面前,作家不厌其烦地描述婚后夫妇对生活琐事处理方式的分歧与和解,最终他们的心灵在琐碎的人生旅途中得到了安顿,他们的理想也找到了一席栖息之所。
王安忆更是将柴米油盐酱醋茶写得绘声绘色,诗意十足:
《文革轶事》中将萝卜切成细丝,放上葱末和热油,便听见噼里啪啦的声响,红腐乳也被撒上了白糖和麻油;③《流逝》里也将红烧蛋的做法写的颇有诗意。
王安忆笔下人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的富有情趣,她作品中的人物将日常生活事件雕刻成了一件件优雅可爱的艺术品。
最后一类是拥有实际行动能力的女英雄。
池莉《你是一条河》中的女主人公辣辣自己拉扯着七个孩子,饱尝苦楚,然而命运的残酷并没有将她压垮,凭着活下去的生活信条,她与命运展开了搏斗,最终渡过了一切难关。
辣辣是泼辣、坚韧的集大成者,是现代市民社会中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代表,凡俗生命里透出崇高和诗意。
王安忆《桃之夭夭》里的郁晓秋也具有果断的行动力,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郁晓秋在挫折面前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她并不在乎母亲的责骂、兄弟姐妹的冷漠及恋人的背叛,但却不允许自己的尊严遭到践踏,她给要为自己起绰号的男生一记响亮的耳光,勇敢地维护了自己的形象。
现代市民文化下的凡人也展现出了种种不平凡,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体现着诗意的一面。
三、城乡和谐化
长期以来,都市和乡村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逐渐一体化,文坛上城乡对立的写作格局也被打破,作家更倾向于创作城乡和谐化的作品。
在现代市民文化中,城乡和谐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物质和谐,即生活富足。
无论农村人还是都市人,只要有一方生活上没有保障,城乡就会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
有过插队经历的王安忆对小鲍庄的芸芸众生进行了细微地描写,这个小村庄里的农民和都市里的市民一样都离不开衣食住行,作品中对这一切的刻画显得那么自然,一副具有新时代气息的诗意画卷便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在《伤心太平洋》中,父亲故乡的“绿色岛屿”被高楼大厦代替,年轻人日益国际化,城乡实现了物质和谐。
《青奴》里的青奴和泽浩给荒芜的小镇带去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月儿好》中的“我”从乡村去了都市,令人惊讶的是,“我”在乡下的童养媳月好并不想要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这些朴紊的叙述中都包含着城乡物质和谐的诗性意识。
张爱玲短篇小说《金锁记》中乡下麻油店的招牌七巧嫁到了城里,虽然精神上比较匮乏,但却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代市民文化中城乡和谐的一面。
其次,生存和谐,即城乡共栖。
城市和乡村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它们同为人们的生存家园,城市人可以下乡,农村人也可以进城。
《本次列车终点站》里的主人公排除各种困难终于回到了自己梦想的家乡——城市,可是城市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压力令他不堪忍受,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怀念起了自由而又朴实的天地——乡村,王安忆借此传达了对当今社会人类生活的关注以及实现生存和谐的迫切愿望。
在《富萍》中,王安忆找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契合点,那就是去上海闯荡的乡下姑娘;《上种红菱下种藕》则通过对一个小镇的描写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池莉《云破处》中男主人公金祥的父亲是老农民,他们金家之所以觉得自豪与骄傲,是因为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征服了这座城市。
④王安忆和池莉对城市和乡村的关注突出表现了她们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诗意关怀。
张爱玲擅长描写沪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些“传奇”中也存在着乡下人的面孔,《桂花蒸阿小悲秋》里的丁阿小便是其中的一位。
丁阿小是哥儿达家中的保姆,是典型的进城务工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阿小将乡下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生存状态带进了城市,为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增添了一抹诗意。
最后,精神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互通。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给现代人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不但表现在城市人身上,而且也在乡下人中产生了一定的效应,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心灵隔阂,因而追求精神和谐成为现代市民文化构建的题中之义。
池莉《心比身先老》中原生态的加木措对都市男女进行了灵魂上的洗礼;《不要与陌生人说话》里徐灵的通情达理与徐红梅的狂妄浮躁形成鲜明对比。
池莉用乡下人的淳朴为精神荒芜的都市人上了颇有诗意的一课。
王安忆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精神诗意:
如《民工刘建华》、《保姆们》都像朴实的香草在城市中坚强的生长;《蚌埠》回顾了在淮河的插队生活和精神;《荒山之恋》写出了乡下男子进入都市后的苦闷和彷徨,金谷巷女孩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诗性慰藉。
城乡和谐化给现代市民文化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闪烁着诗意的光辉。
四、方言语用化
方言是在某地区通用的语言变体,当代涌现出了一批方言小说家,方言也深深地根植在代表现代市民文化的市民小说之中,方言与小说中作者所写及所想密切相关,只有在特定场景或话语中才会产生某种蕴涵意义,体现了语用化的写作风格。
方言语用化不仅保持了文化的基本内蕴,也给予了文化活跃性与姿态性,散发出诗性情怀。
张爱玲大部分作品都采用标准普通话,但有时候为了表达的需要,也会选用一些方言,主要包括沪方言和吴方言两种。
在《等》这一短篇小说中,张爱玲将目光投向了上海沦陷区推拿医生的诊所里,通过细节描写刻画出了普通小市民的各色心态,其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就夹杂着不少沪方言,如“板定”、“格佬”、“蛮写意”等等;《桂花蒸阿小悲秋》中也有沪方言缠绕:
“家生”、“白相”、“姆妈”……这些沪方言的精确运用在增强小说趣味性的同时,也使得人物更加生动逼真,为作品蒙上了生活气息和诗意色彩。
张爱玲的著名小说《金锁记》字里行间都孕育着吴方言:
“约摸”、“焐一焐”、“稀朗朗”、“捻一捻”……这些口语化的方言使得这篇市民小说绽放出活灵活现的诗意美。
除上述两种方言外,张爱玲还在《创世纪》中采用了“拨聋”、“胶切片”等形象化的湘方言。
沪方言、吴方言和湘方言使得张爱玲笔下的人和事栩栩如生,透出一股语用化的诗意。
池莉也是比较有名的方言小说家,她用方言谱写出了诗意的世俗世界。
“细媳妇”、“打肚皮官司”、“起拱子”……写出了湘鄂地区市民独特的生活意趣;“家爷”、“家屋里的”、“家娘”等反映出湘鄂特有的市民文化。
有些方言还别具风味:
“瓜娃”、“瓜笑”、“瓜蛋”等是与“瓜”有关的词汇;“木木腾腾”和“木格登登”与“木”紧密相联。
这些方言词汇生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