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docx
《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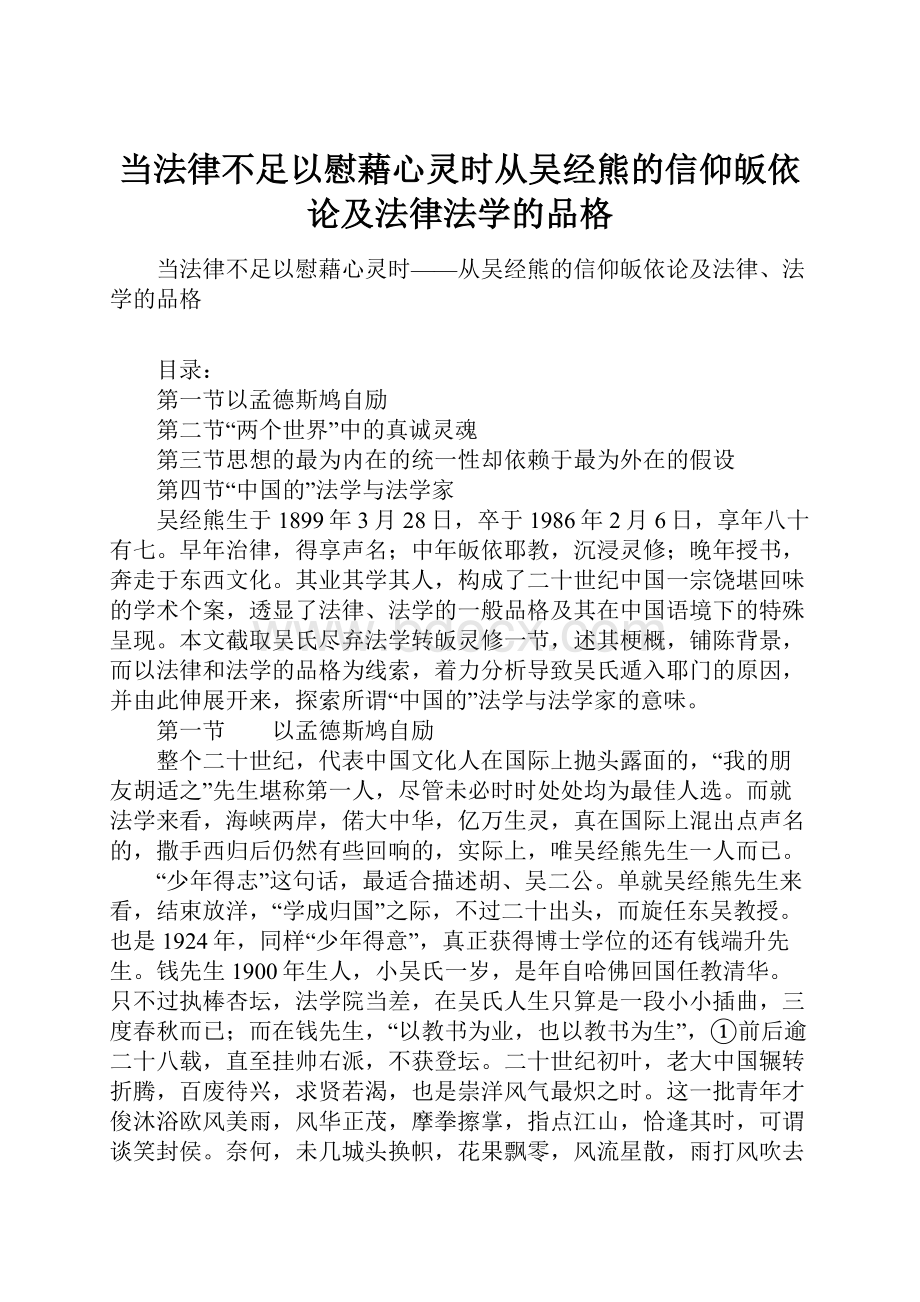
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
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
目录:
第一节以孟德斯鸠自励
第二节“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
第三节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却依赖于最为外在的假设
第四节“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
吴经熊生于1899年3月28日,卒于1986年2月6日,享年八十有七。
早年治律,得享声名;中年皈依耶教,沉浸灵修;晚年授书,奔走于东西文化。
其业其学其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宗饶堪回味的学术个案,透显了法律、法学的一般品格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呈现。
本文截取吴氏尽弃法学转皈灵修一节,述其梗概,铺陈背景,而以法律和法学的品格为线索,着力分析导致吴氏遁入耶门的原因,并由此伸展开来,探索所谓“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的意味。
第一节 以孟德斯鸠自励
整个二十世纪,代表中国文化人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堪称第一人,尽管未必时时处处均为最佳人选。
而就法学来看,海峡两岸,偌大中华,亿万生灵,真在国际上混出点声名的,撒手西归后仍然有些回响的,实际上,唯吴经熊先生一人而已。
“少年得志”这句话,最适合描述胡、吴二公。
单就吴经熊先生来看,结束放洋,“学成归国”之际,不过二十出头,而旋任东吴教授。
也是1924年,同样“少年得意”,真正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钱端升先生。
钱先生1900年生人,小吴氏一岁,是年自哈佛回国任教清华。
只不过执棒杏坛,法学院当差,在吴氏人生只算是一段小小插曲,三度春秋而已;而在钱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①前后逾二十八载,直至挂帅右派,不获登坛。
二十世纪初叶,老大中国辗转折腾,百废待兴,求贤若渴,也是崇洋风气最炽之时。
这一批青年才俊沐浴欧风美雨,风华正茂,摩拳擦掌,指点江山,恰逢其时,可谓谈笑封侯。
奈何,未几城头换帜,花果飘零,风流星散,雨打风吹去。
钱先生几乎销声匿迹,幸老来转福,“平反昭雪”,寿终正寝。
吴先生于现实和心灵的煎熬里早以皈依上主作结,更乘桴浮于海,最后落叶归于宝岛。
1986年,先钱公三年,宁波吴氏德生公驾鹤登天。
两位法学先辈虽迭遭磨难,而均大难不死,得享高寿,见证了老大中国波澜壮阔、贞下起元的二十世纪,实为同一时代诸多较为幸运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青年吴经熊,可谓才高八斗,雄心万丈。
生于世纪之交,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
怀家国忧愤,读书人各思报效。
早在负笈密执安大学之时,吴经熊像一般青年那样,出于崇仰,驰书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订忘年交。
此后更飞鸿驰往,酬唱交加,不亦乐乎。
1924年4月5日,归国前夕,在一封致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吴经熊满怀深情地预言:
“本世纪将目睹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再生,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的诞生,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②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的一封信中,吴氏即已憧憬:
中国不但将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它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而且在实现这一蓝图的过程中,我应当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
③
自期高远,报效愿宏,实为明道救世、士志于道的一切旧知识分子新士大夫们的通性,而况身处那样一个家国多难之秋。
果然,返国后登堂开讲,文论陆续刊行,一时间即在学界形成影响。
那一手温婉飘逸性灵灵的散文,非江南灵秀山水不能孕育,真是打遍“天下”。
返国仅仅四年,英文论集《法学丛稿》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刊行。
中文论集《法律哲学研究》1933年由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
法学界佳评甚众,很有些“引用率”呢!
而由于其不少作品曾以英文首先在美国面世,因而读者中注意到“约翰。
吴博士”这个“中国人”的,并包括了象施塔姆勒、庞德和卡多佐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④当其时,治法学的中国学者获闻于西方主流学界的,可能,唯王宠惠和吴经熊而已。
第二节 “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
但是,吴经熊的法学生涯极为短暂,没有也未能在自己的祖国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正像王宠惠宦海浮游终生,于法学终无建树。
“中西联姻的婴儿”的分娩遭遇持续阵痛自不待言,当吴氏在不惑之年结束放浪生涯,皈依基督后,几乎尽抛平生所学,与法学彻底分手,而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
在其后的岁月里,吴经熊翻译圣经,研习教理,沉心歌咏,虽穷困而不弃,战乱而不辍,一如自述,“按圣经而生活,非靠圣经来生活”。
⑤其执信之切,奉献之诚,践履之坦荡,在无神论者看来,几达走火入魔。
⑥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所为何来?
意欲何往?
今日往回看,导致这一选择或被选择的原因之网真是密密麻麻。
其间,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理性与经验,此岸与彼岸,灵与肉,等等等等,错综纠结,纷纭互动。
这里,让我们由小至大,自个人而社会,在东、西方及其时间之维的纠缠中,一层层剖析开来,静静省视先贤的心思。
首先,要言之,大凡成名太早,诱惑必多。
天分卓越,年纪轻轻,生活同时打开了多扇门,各种可能性都在殷勤起舞,把持不住,沿着人往高处走的法则往下走,便再自然不过。
仅从法律学术言,吴经熊正属于这一情形。
这样说话,读者或以立论轻浮问责,但情形如此,不得不说。
事实是,吴氏在密执安前后不过一年多,旋赴巴黎,再驱柏林,最后在归国前返美于哈佛小逗,是那个时代家境宽裕的中国留洋学生典型的“游学”经历,也是他个人天资卓越,后天勤勉用功,外在际遇嘉惠的复合效果。
他的“充满灵气和文雅的英文”,⑦得力于自幼所受教会学校的新式教育。
宁波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居民刻苦耐劳,又善于经商,遂能为子弟提供较好教育。
当其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后发亚非国家,洋文好,那还了得。
不但当时,现在也还如此。
而吴氏恰恰就是洋文好。
岂止是好,而且是非常之美好。
正是对于这一表意工具的娴熟掌握,使得吴氏得以将自己早熟的法意铺陈为文,贡献于诸如《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这样的杂志,为少年出道即铺一瓦,先奠一砖。
这是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那时回国的留学生,许多人有意无意,肩上都扛着一个名人作招牌,就像胡适之的“导师”是杜威一样。
⑧吴经熊的肩上扛着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和惹尼,大西洋两岸,美、德、法三家,交游既广,道行弥深;名家冶集一身,行头极为光鲜,最堪在崇洋风气最炽的上海、江浙之地谋生。
职是之故,以吴氏之天分,加上后天积攒的这种种资历,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他的一席地位,不代谋求,先已自成。
纵当事者不想唬人,人不敢不让唬,如果在此姑且能用“唬”之一字的话。
⑨一般读书人通常都需经历的寒窗苦读、清夜笔耕、长期煎熬的学者积累期和成长期,在吴氏这里几乎被压缩为零。
因此,他可以教书,也可以去做法官或者在立法院充任喉舌,还可以接着“出国”,回来当律师更赚钱。
民国政体风雨飘摇之际,甚至一度即将出任司法部长,旋因政故,转赴梵蒂冈任所。
可在学术领域,正常情形,诚实而自觉的学者自然明白,虚名代替不了真知,思想的果
实是清冷冷长期煎熬后的产物,而学术如练功,容不得一日松懈。
尤有甚者,法学以法律为对象,不同于诗文,事关实践理性,恰恰是一个需要人生阅历,依赖实用智慧,在“过日子”中于“过日子”多所体贴才能有望逐渐增益的学问。
纵才高八斗,无补于实践理性的冰冷法则。
年轻的“约翰。
吴博士”返国后已然无须再坐冷板凳,可他那纸上的法理终是英文写就,吃教科书的营养发育,真要别门立户,尚待培养,而要兑换为当下法制的智慧,相距更是何止万里。
因此,他可以将租界的案子打理清楚,立法院则万万玩不转。
可是,既无需“评职称”,亦不用为五斗米奔走于市,那么,离开了冷板凳的法学家没有进一步付出脑力的压力和动力,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
这样说,终究失之于浅,不足以深切触及先辈的心思,也太有点以小人“那个”君子的意思了。
这里,实际上牵扯到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品格问题。
通常而言,法律作为规则,是事实的写照,而以生活本身为蓝本,“观俗立法”因而成为一般的通则。
生活已然具有一定形制,益且相当稳定,才能凝练而为规则,抽象以为一般通则,然后再以此规则、通则网罗事实,组织生活,增益人生。
所谓盛世修史,治世用典,其反面自然是乱世何言法制,烽火连天之下哪有笔墨伺候的可能,如西塞罗所言,“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
道理甚为显明,乱世讲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自亮肌肉、凭盒子炮说话,恰恰是不要法制。
所以梁漱溟先生早有先见之明,慨然既是要“革命”,当然就不需法制,人家那边厢大讲特讲宪法宪政,当然都是打埋伏贩假货卖水货,跟着瞎起什么哄。
⑩再说,遽聚遽散的生活无法凝练、积淀为一般的事实,不成形制,哪里会有规则的立基之处。
的确,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处大变革时代,未容法律置喙,生活早已自作主张,无形制可觅,自然无法制来“原形”。
此时亟需治军,而非治律。
法律靠边站,法学自无用处,法律人偷生隙中,至多是个边缘的摆设。
因此,不幸但却真实的是,每当家国危机深重,祸乱频仍之时,恰是诗思忧结,发为歌咏之际,家国不幸诗人幸。
而包括法学在内的一般学术,则非赖“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可,否则无以为措。
退一万步讲,若连一张书桌都安放不下,怎么做学问,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八十年代,已故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曾谓,今后一阶段将是中国法学家的黄金岁月,也正是看到了社会-文化转型渐趋形制,踏上正途,转入常规,乱而后治,而此“治”正是工商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亦即法律文明秩序,因而必有法制即将登场的大势。
吴经熊那一辈法学公民,怀济世理想,拥治世之具,却恰恰逢当乱世。
此一乱世又非一般乱世,而是我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也!
经此一变,中国从传统小自耕农为基础的帝制时代,一去不回头,顿挫间迈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主法治新局面。
此种社会-文化转型,艰险备至,充满惊涛骇浪,真正是“历史三峡”。
11而其历程,至少以一、两个世纪为单位计算。
在此长程革命中,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悉予打碎、变组、搭架子再来。
以政治革命和武装争斗为表,生活常常于旦夕之间剧变,无以凝聚成一定形制,还未来得及细看,它已经又变了,无法构成规则赖以立基的事实。
12而欲在此基础之上搭建规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
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实在是事情本身如此,非人力所能控制,况乎法制。
这一切,均源于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吴公岂能不知,又岂会没有切肤之感受。
事实上,在一篇“微言大义”式的短论中,吴氏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询及“什么是法律?
”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
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
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问题常是:
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
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
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
13
当时中国法律领域的许多事,恰恰就属于这类毫无事实基础,“诚属荒唐”,但又不允许俟诸来日从容为之者,真正是“不得不然”。
14因而,整个二十世纪,至少在前半叶,中华文坛星斗甚繁,而法学大家为零,不全是什么“传统”使然或者当政者“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更不是中国人天生就笨,而实在是面对时代课题,法律法学无以措手足也!
法律人因而无以展长才、施抱负,只能做点零打碎敲的杂什,譬如,上上者做个诸方势力夹缝中各种“立宪”的秘书班子,下焉者起草个“镇压”什么或者“戡乱”什么的狗屁条例的笔杆子。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你能指望宁波吴公以一身而敌一时代,单单成就伟大法学吗!
时不我用,也时不我待,逼迫到头,以回避换进取,藉由糟蹋身子而保全心灵,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
而说到底,吴氏的中年皈依牵扯到法律之为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
简言之,凡通常所谓法者,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必为一种意义体系。
15其为一种意义体系,在于蕴涵了特定人文类型人民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追求,反映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憧憬,足以成为他们信仰的表达和寄托所在。
就是说,法律应当反映法律体系所置身其中的特定人文类型的道德理念、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将该人文类型的是非之心换形为法律的奖惩规则。
这样的法律源于居民的活法,说明了居民的说法,最后才落实为立法,因而才会为居民引为生活的矩绳,产生信赖乃至信仰,从而,获得其合法性。
用吴氏自己的话来说,法律的“感知”和法律的“概念”原本就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形面,所有能触动最外在的实在的东西,当然能够并且应当在我们感情的最内在处激起涟漪,从而,法律不过是我们可藉之抵达真理的一个部分,法律由此而“成为偶像”。
16一般情形下,人世生活但求安全与安宁,公平与正义,法律应当以此为目的为灵魂。
但凡能够提供安全与安宁的法制,便是良好的规则体系,而具备法律之为法律必因其具有法的效力这一基本前提;但凡满足了公平与正义要求的法制,便是值得信托的意义体系,而适成良法,有可能“成为偶像”。
而何谓公平与正义,则需诉诸特定人文类型,以该特定人文类型中一般居民的人生与人心为皈依。
迄止“约翰。
吴”洗手不干变成“若望。
吴”,他曾经有过兴味盎然之时,“中外报刊”对于他的判决的“良好评价”,使他感到中国的司法不仅正在“霍姆斯化”,而且,他还“正在用自己的法学观点塑造中国法律。
”17对于一个早熟的、具有浩然理想的法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鼓舞人心的呢!
但是,随着介入渐深,他所遭逢的法律,剔除字面涵义不论,最好的是一党之法,最差的乃是借法律之名而行毁法之实。
而他费神既巨、祈望亦切的“吴氏宪草”,终只是书生具文,敌不过盒子炮。
在此情形下,法学公民的吴经熊的法律热情焉能持久!
倘若吴公只是一介刀笔师爷或仅治部门法的专家型学者,并无价值追问或尚无需进行价值追问,那么,他当然也就无需面对这一苦恼;或者,倘若吴公属于闻一多式的血脉贲张、拍案而起型人物,或能尽抒胸臆,管他后果不后果,而免于低吟徘徊之苦;或如钱端升,出入于用世与避世之间,张弛不惊,善为调治,也行。
但是,吴先生是个温文善良的书生。
观其着述
,念其行止,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敏感而多愁,诗人气息浓郁,忧时伤世,而生活上则似乎甚至不脱江南士子的趣味和习性,恰是深蕴实践理性与实用智慧的法律法学所当避者。
181936年或者1937年,他写下的一则札记,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自己这种心境与情怀的正面省思: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
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
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
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
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19
这样子履行法曹职责,哪怕按新闻用语惊呼为什么“所罗门王”,其内心的煎熬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如果世道太平,吴公或按部就班,以他的天分、勤勉和人脉,继续书生事业,成就一家之言。
可他生逢乱世,时不予我,只能将一腔忧思,转而为虔信的热忱,在此世与彼世间流连辗转。
皈依前夕,吴氏写道,“身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困惑的人”;事后在回忆录中他复自述,“我年近四十,却仍未获得我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真是觉得不幸之至”,20凡此可为法律和法学不足以慰藉心灵的直接证据。
而一旦找到认为“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其世俗生活层面的“专业兴趣”随即迁转,也就极其自然。
实际上,当真诚的学者发生如此“专业兴趣”的转移之时,常常也就是遭逢难言隐痛之际。
距吴经熊皈依整整二十年之后,“八百年前是一家”的另一位吴教授恩裕先生,时任教北京政法学院,鉴于形势,“兴趣”也发生了变化,从治西方政治、法律学术转到了“红学研究”。
正如以明治乱、知兴亡为职志的史家陈寅恪,晚年二十载,从陈端生到柳如是,如其所述,“着书唯剩颂红妆”,其实,或内在或外在,都有其难言之隐痛,不得已而为之。
如此这般,以法律为业,可后者却难堪理想和信仰之寄托,“吾心怅然,无所为归”,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
再进一步,把视野扩大,前后左右上下环顾着看,当能看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更为尖锐的难题,即法律移植背景下法学公民精神领域“两个世界”的紧张与冲突。
对于两个世界洞悉愈明,涉入愈深,这种紧张和冲突愈甚。
我们知道,整个一部百年中国法制史,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法东渐的历史。
西方规则东来,意味着此种规则的知识和意义一来俱来,意味着其背后的情感和信仰因素同样要挥戈登岸。
但是,规则、知识和意义均立基于一定的事实,即植根于特定人文类型的生活及其传统之中。
事实不存在或一时尚不成形制,则规则难以立身,知识变不成力量,意义的“失落”同样不可避免。
反过来,从当事者的法律公民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是一个运用法律知识,将自己所体认的价值和情感、理想与信仰,贯彻于规则或者借助规则表达出来的实践过程。
当其时,如果规则西来,自己受的教育也是西式的,因而表达的上述种种同样是西式的,那么,难免会出现规则与当下的事实之风马牛,你所讲述的价值和理想与当下的人生和人心根本无涉这样的危局,如此,你这位法官或者律师,立法者或者教书匠,能不痛感灵魂被撕裂了吗?
能不四顾苍茫、忧思如焚吗?
甚至于,深感无知而无趣,无力也更无意义吗?
!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切所显现出来的西来规则及其意义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具有普适功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不止是法律问题,更且关涉到藉以“救国拯民”、济世安邦之道的正误问题,用什么东西来“救国救民”才最为有效最为有力的问题,一个不容回避的“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
-用终生提倡白话文的适之先生的话来说,“兹事体大”呀!
当日的中国,如上所述,事实不成形制,规则的世界是一个“时代的错位”的所在,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时间的丛集”所在,21因而,在当日中国的法律领域,事实与规则脱节,规则的知识和意义与中国的场景脱节甚至冲突的尴尬,乃是眼面前的事实,活生生的具象,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街头活报剧。
“大上海”的租界里,这一问题也许不突出,或者不十分突出,可一到“立法院”,面对的是支离破碎、“错位”与“丛集”的全中国,这样的事实则是无可回避的生活本身;英文语境下纯粹形上的运思时可能不突出,或者不十分突出,可落笔中文,表意工具顿时将意义世界联翩带出,意义世界又鬼使神差般地提醒作者它本源于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如前所言,乃是“支离破碎的全中国”,于是,这样的事实便是生活本身,纵然想逃避亦逃避不得。
今天往回看,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说这一尴尬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期内,再自然不过,纵然起五大法学家于九泉,延萨维尼、施塔姆勒“指导立法”,聘卡多佐、霍姆斯来“改革司法”,让韩非子、长孙无忌、沈家本、董必武、张君劢、江平等等一齐组成“法工委”,可只要火候不到,他们也莫奈之何,还不是叹几口气,跺几下脚,顶多最后拍桌子打板凳了事。
-不是他们没本事,实在是形势比人强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着急,尽人事,听天命,按部就班,随着社会-文化转型渐行渐远,其间的紧张自然烟消云散。
但是,身处过程之中,作为当事人的诸公,就算明了这一长程性质,却也难免东西、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现实举措之困,精神煎熬之苦。
要是不急不躁,那就成神仙了。
前文曾谓,吴公在心中已然揭橥未来的中国必为“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说明他对于此一社会-文化转型是堪具理性的了解的,对于自己即将面对的劳责,也是清晰而凛然的。
但是,如前所述,他的纸上的法理终是英文写就,而要兑换为当下法制的智慧,相距更是何止万里,说的就是身处过程之中的当事人必然会有这种苦痛。
不易不易,极难极难;明知不当急,还是急死人;尽管心急火燎紧赶慢赶,而事情却可能反而更糟,“治丝愈紊”。
而既然法律法学的目的和功用旨在料理、规范人事,服务、造福人世,讲究一个将事情办成办妥的事功追求,而事情总是办不成办不妥,因而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更不用提成为中国的孟德斯鸠了,而吴先生又是那样一个温文善良、敏感多愁的知识分子,于是乎,“两个世界”的沟壑及其紧张,遂益形突出,越发加剧,其势汹涌,一发不可收拾,招架不住,终致精神危机。
-真正的精神危机,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哟!
可能,人处困境,左冲右突,无以解脱之际,喝喝花酒也能暂时忘忧,聊可慰藉。
这不,“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
实际上,不含教训意味在内的所谓“堕落”,此为导火线之一。
然而,对于像吴经熊这样一位真诚君子,一个纷纷乱世中不堪“堕落”的善良知识分子,花酒只如鸦片,疗痛一时,终不能安顿心灵,正像执业律师赚得了白花花的银子却难掩心灵的困惑。
知识的洞见无以消弭眼前的困惑、现实的人生时时受到良知的感召却又难以自拔,理性之不能安顿感性,此时此刻,东西南北,一并发作,万箭穿心。
-这是吴先生作为法学家的失败处,却是吴经熊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性灵的超拔处。
怎么办?
他翻译的《圣咏集》中的诗句,也许可以用来描述他此刻的心境与情境:
醒来,我的灵魂啊
醒来,诗歌和竖琴
我将唤醒黎明
十七年前,他因惊异于“美国的上主是全能的美元”,目睹周遭美国同学“用最不敬的方式以基督之名骂人”的堕落气氛而放弃皈依,22此刻,在“两个世界”之间纠结的他,终于选择了或许能将自己的现世生活与精神生活两相统一的灵修之路,迎来了自己的精神“黎明”。
在半百之年撰述、讲叙自己灵修心路的《超越东西方》中,吴氏写到,“道”之一字,意味着不可用词句来表达的终极实在,一切事物和美德的不可分别、不可言喻的来源,“它是朴素,它是至一”。
23而他的“心智面貌的主要特征”,如其自述,“乃是谐调彼此矛盾的东西的持久倾向……通过谐调,人就超越于不谐调的世界之上。
”24至此,似乎,藉由放弃,放弃最具现世性的法律和法学,他获得了精神世界的“至一”。
-可能,这是一种更为勇敢的面对;至此,似乎,藉由“至一”,他“超越了东西方”,这一不谐调的现实世界,而获得了精神的安宁。
实际上,早在1923年2月5日,当霍姆斯读到了那篇发表于《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上的“霍姆斯大法官先生的法哲学”之后,即致信年轻的吴经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欣赏你对法律表示出来的狂喜。
我只是害怕当你潜入到生活的活动中时,这种兴奋会变得黯淡了。
但是,假如你像我所希望的,也像你的信所显示的那样,胸中燃着一把火,它就会幸存并且改变生活。
25
老法官一生专与麻烦打交道,判案无数,阅世多矣,深谙对于理想本身或者对于一个胸怀理想者的考验,“就是看他在困境中对于生活是否还抱有美好的希望,因为人在春风得意之时,难免要高谈阔论。
”26故而,老人看到孺子可教的同时,对于法律的道路上之前路迢迢、歧支纷出、危机四伏,也不能不说,即便言之含蓄,点到即止,甚至可能说了白说。
回国前夕,吴经熊给霍姆斯写了一封情感真挚、充满离愁别意的长信,其中有“我在沉重的使命前发抖了”27这样的句子。
时光流逝,上述两方之言均不幸成谶。
吴经熊“对法律的狂喜”在残酷的现实碾压下瞬息即逝,而那一把火,虽幸留存,却终于燃向了灵修。
-灵魂在上,法律法学云乎哉!
第三节 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
却依赖于最为外在的假设
折磨吴经熊的“两个世界”是一张由多重的互动关系编织而成的蛛网。
抽丝剥茧,举纲张目,我们发现,它包括法学思想的微观和法学思想所牵扯到的宏观两个层面,思想的内在和外在两条理路。
正是这两个层面和两条理路的纵横捭阖,铸造出将他的法学生涯早早扼困的铁栅。
从微观立论,仅就法律理性层面而言,吴氏的双肩即已重任如山,一如其夫子自道:
我的全部哲学都可视为调和霍姆斯和施塔姆勒法律思想的努力,调和感知与概念、生成与已成、内容与形式、利益论与正义论、经验与理性。
28
塔姆勒的学说辗转于理性追思,在逻辑谨严的古典哲学式论辩中,重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但据说因“极端抽象和晦涩”,而为论者诟病。
29霍姆斯则被视为实用主义的大师,以重在解决案件争讼而达成公正为中心,自司法过程当事者的视角,讲述法之如何为法。
二人的追求自然有别,思路和方法确乎不同,风格亦且迥异。
由“调和”的“努力”可见,吴氏心目中的法律图景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统一的意义体。
用吴氏自己的话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