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磨制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现状分析Word下载.docx
《国内磨制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现状分析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内磨制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现状分析Word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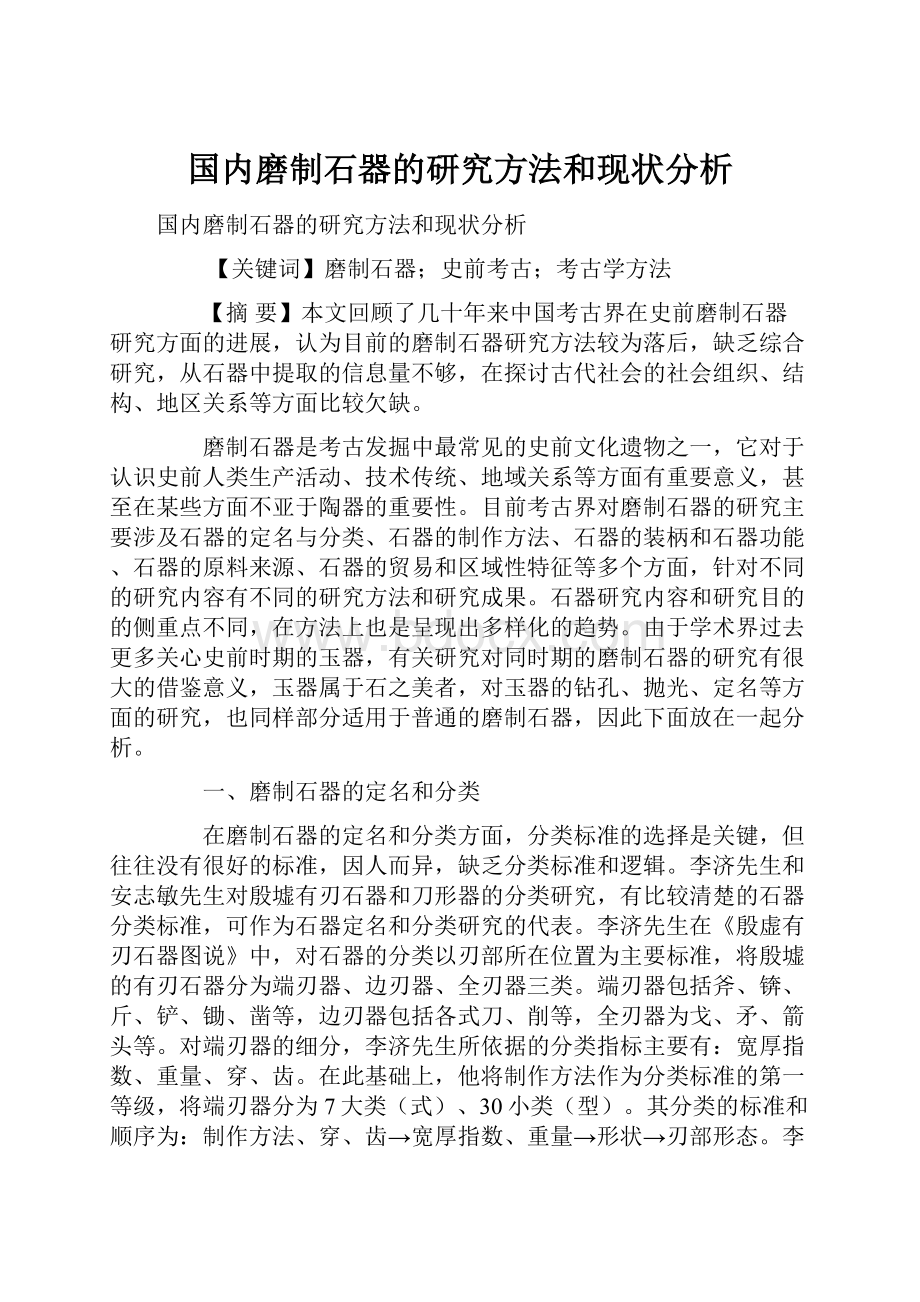
端刃器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它的形态和制作方法已经相对成熟,大部分器物都要经过打制、琢制、粗磨、细磨等制作过程,特别是琢制和磨制程度的多寡,可能对端刃器的使用并无太大的影响,古人所考虑的只是形制是否已经合乎使用要求。
分类的理想状态是还原古人的分类体系,对石器而言,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史前人类的石器分类首先应是功能上的,至少根据功能的分类应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李济先生的这一分类方案没有将端刃器在大类阶段就区分出功能的差别,而过于关注磨制面积的多少这些细节性的分类指标。
安志敏先生对石刀进行了分类的尝试[2]。
他根据基本形制分为有孔或两侧带缺口的石刀、镰形石刀、有柄石刀三类。
安先生的分类指标顺序为:
总体形状→次类特征和形状(两侧缺口、长方形、半月形)→形状、制作方法、刃部凸凹形态→钻孔数量、长宽比。
这一分类方案始终以形状作为最主要的分类变量,贯穿于整个分类中,而制作方法、钻孔数量和长宽比只作为辅助的分类变量。
这种分类方法可能与分类的器物――石刀有很大关系。
石刀相对于端刃器而言,功能相对稳定,使用方式固定,因此这种以形状为主的分类基本上可以满足区分器物的需要。
作者也注意到,各种类型的石刀必须从刃部的型式来区别它们的用途,用途的变化在刃部上表现最突出。
如直刃可以作为农具,也可兼作切割用的刀;
凹刃不适合切割,但可方便地用来割取谷穗;
凸刃适合于切割,但不适宜收割谷穗。
但这一功能上的区别并没有在分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由于缺乏统一的分类和定名标准,现阶段国内磨制石器的定名标准处于一种比较不清晰的状况,同样的困惑也出现在玉器的定名上。
对于无法将考古发现与后代记载的名称相联系起来的情况,夏鼐先生更倾向于主张使用描述性命名[3]。
二、制作工艺和技术的研究
石器制作方法的研究,大量成果集中在对玉器的研究上,研究方法主要有痕迹观察法和实验法。
研究的内容大体包括:
①材料选择的研究;
②工序过程的研究;
③石料切割方法的研究;
④钻孔方法和工具的研究;
⑤琢磨材料和工具的研究;
⑥制作玉石器的雕刻工具的研究;
⑦抛光工艺的研究;
等等。
这些方面目前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基本解决了玉石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问题。
石器的加工过程,是个减法的过程,从原料到毛坯再到细坯,不断消减,最终完成一件磨制石器。
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料,废料上保留的加工痕迹可为复原工艺和技术提供很好的研究资料。
因此在对石器制作工艺和技术的研究材料的选择上,有学者注意到废弃石料的研究价值,他们指出,治玉工艺中打磨和抛光等后几道工序,往往将玉器成品上前几道工序加工的痕迹磨灭殆尽,要想了解并复原出整个工艺过程,应注意到弃余物和留有加工痕迹的玉器成品[4]。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磨制石器研究中。
对于工序过程,安志敏和佟柱臣先生研究了磨制石器的制作步骤。
安志敏将石刀的制作复原为四个步骤,即磨制前关于器形的处理、磨制、刃部的处理、钻孔[5]。
佟柱臣先生将石制工具的制作工艺分为选料、选形、截断、打击、琢、磨、作孔等[6]。
考古发现的石器加工场中出土的大量半成品和毛坯,为复原整个石器的加工流程提供了可能。
近些年不断发现史前各个时期的石器制造场遗址,使得石器制作流程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分析玉石器加工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如对澳门黑沙[7]、周原制作坊的研究[8]。
通过调查材料来研究石器制作工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臧振华和洪晓纯对澎湖七美岛三处史前石器制作场调查材料的研究。
他们根据地表采集到的块状石料、石核、石片、素材、石器毛坯、残器、石子器、砍砸及磨石并用器等8类标本,复原了石器制造的程序和技术,认为石器制作包括剥取石核、从石核上打剥目的石片、截取素材、打制石坯、修琢石坯、磨制器身或器刃等6个步骤[9]。
张弛、林春在对宜都红花套遗址石制品的研究中,将石制品区分为成品、石料、废料和残次品等几大类,并据此复原了石器制作场的石器制作技术和流程[10]。
石料的切割方法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通过观察器物表面的残留痕迹和一些实验来探讨切割方法[11]。
学术界已基本总结出各种切割方法形成的痕迹特征,以牟永抗先生的总结最为全面。
他认为,切割痕迹可区分出硬性片状物切割和柔性线状物切割两种。
片状物切割留下的线条刚劲挺直,每条阴线的两侧及底缘平齐匀称;
线状切割的痕迹是多条近平行的弧形曲线,曲线中段的弧度较大,有的可能接近正圆,两侧的开口端,弧曲度较平直,有的近似直线,其形制和用轮制法制成的陶器底部常见的切割痕十分相像,并推测可能是用动物筋条等柔软的线状物带动砂粒等介质所造成。
另外,牟先生还比较了线切割痕迹与后世的砣具切割痕迹的区别,指出:
线切割表现为向心性,切割的前进方向作凹弧形,不时留下凸弧状的切割台面;
而砣具切割的作用力指向圆周,表现为离心性,切割的前进方向为凸弧形。
线切割的切割面由于两端牵动不能在一个水平线上,造成波浪起伏,鼓凸部分虽被磨去,但凹陷部分却被保留;
而硬性的砣具切割,虽可出现某种歪斜,但不能出现波浪形起伏面。
线切割的圆弧由外而内逐渐缩小,砣具切割的截面上保留的圆弧为等径圆[12]。
周晓陆、张敏认为,解玉的方法有三种:
一是砣具法,二是钢丝弓解玉法,三是竹片解玉法。
三种解玉方法在玉器和废料上留下了不同的痕迹。
以砣片解玉,旋转的砣片凸前缘加力切进,截割面较平,上面有一道道排列整齐、细密,且间距大致相等的弧线;
用钢丝弓解玉,由于用力不均,会造成截割面凸凹不平,留下间隔不等的抛物线痕迹;
以竹片加水蘸砂来回拉动解玉,截割面平而滑,痕迹为平行直线,比前两种方法慢许多。
对比标本上残留的加工痕迹,他们认为有用皮条弓和竹片加水蘸砂解玉的痕迹,截面上抛光光泽,为兽皮脂肪和竹片的竹沥摩擦浸渗所致[13]。
林华东认为,玉器上的切割锯痕呈“V”字形,应是使用硬度较高的石片(有的石片或许还带小齿)切割而成,如果用木片加砂蘸水切割,不会形成“V”字形锯痕[14]。
在钻孔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方面,安志敏先生认为在石刀上钻孔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挖孔,即在石刀相对的两面先摩擦成一条中央深、两端浅的凹沟,然后再在凹沟中较深的地方由两面挖透,孔的形状不整齐,代表一种原始的钻孔方法;
二是钻孔,即用木棒蘸水加砂,用手或附加弓形物加速转动,钻出的孔形制更规整。
他还提到,有的在钻孔前还有规划,即在相对的两面各划一条浅沟,作为钻孔位置的记号[15]。
北京玉器厂则分析了商代的琢玉工具及各种钻孔留下的痕迹形态[16]。
卢茂村根据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刀均为奇数,认为当时人类已经掌握了“中”的概念,采用“执子”的方式来规划钻孔[17]。
慈湖遗址出土有木钻头,钻头凹槽嵌入骨(角)刀片,用于木器上的钻孔。
林华东认为如果嵌入硬度高并且带有锋刃的石刀片,就可以在玉石器上钻孔。
他详细研究了良渚玉器的钻孔工艺,认为有实芯钻法、管钻法和琢钻法三种。
实芯钻出的现最早,多施于扁薄器物上,孔小且浅,钻具应类似现代仍然使用的木工钻,有学者用丹徒磨盘墩燧石钻头作过效果很好的模拟试验,表明其可以固定在拉弓式的木工钻上使用,又可直接用手研钻或刻画[18]。
牟永抗先生发现良渚玉器上的双面管钻孔的孔壁两侧深度基本相等,当出现某种歪斜时,相互错缝的深度往往相若,据此认为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两极钻具,掌握了双面钻进的管钻技术[19]。
朔知和杨德标对薛家岗石刀钻孔进行了精密测量和观察,认为中孔定位精确度很重要,其它孔的位置主要以相邻孔和刀边缘为参照系,各孔位对顶距的要求不严格,正反两面钻孔定位的精度要求较高,钻具有多种型号和种类,可组合使用[20]。
关于琢磨材料和工具,霍有光根据不同材料的不同硬度和文献记载认为,出土的早期玛瑙、水晶饰件,不是采用普通的石英砂作琢磨材料,而是采用了硬度高于石英砂的石榴子砂和刚玉砂,甚至金刚石砂[21]。
林华东推测良渚玉器打磨时有的可能利用了砣床,是把圆砂轮安在砣床上来磨制加工玉器[22]。
制作玉石器的雕刻工具方面,张明华推测良渚玉器可能使用了鲨鱼牙齿作为雕刻工具[23]。
林巳奈夫用该方法进行了实验,但没有成功[24]。
对于闻广提出的玉器先加热再雕刻的方法,林华东认为,玉器加热软化后雕刻繁密花纹时容易崩裂,而今日所见良渚玉器表面多坚硬光亮,线条纤细无崩裂,故而认为该说存疑,应是使用了比玉硬度更高的“它山之石”作工具,如磨盘墩遗址出土的燧石工具[25]。
郝明华也认为,像珠、管、坠等小件玉器上的孔径都很小,应是用燧石打制成的细石器两面对钻,并举张陵山出土的透雕玉为例,该玉件上的镂孔纹饰即是先用石钻对钻出圆孔,再以丝麻的纤维或兽类的筋毛穿入孔内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搓磨切割而成[26]。
但在何时开始出现采用砣具加工玉石器的问题上,目前还有很大争论。
学术界没有复制各种古代的砣具,并进行严格控制的对比模拟实验,仅凭主观的观察得出结论,是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玉石器的抛光工艺,只是根据传统方法进行了推测,没有依据具体玉石器材料来研究其具体的抛光工艺。
已有的研究很少,且主要是就玉器而论,如陈廉贞介绍了上世纪50年代苏州琢玉作坊的上光办法,是用火漆与金刚砂混合溶液置于圆模中冷却,加在轴上进行摩擦[27]。
林华东推测是把玉器放在木片、竹片或兽皮之类的上面不断摩擦,直至出现光泽,并提到清末李澄渊的《玉作图》中是用木砣及浸水黄宝料或用各色沙浆以磨之[28]。
三、功能和使用方法研究
石器的装柄方式和使用方式的研究,根据出土实物的形态进行推测和依据民族志进行对比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29]。
后一种方法由于缺乏非常详细的民族志石器报告,对比研究的结论无法得到确证。
通过出土实物来推测装柄方式则受限于材料的不足[30]。
相比之下,痕迹推测法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李京华先生使用痕迹推测法和实验法对登封王城岗出土的石铲、石刀的制造方法、使用痕迹、装柄痕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观察,并尝试根据石铲的刃部磨损痕迹,柄槽、柄窝痕迹和缚绳痕迹,复原了石铲的装柄方式及使用方式,通过对石刀缚绳痕和使用痕迹的观察,认为石刀似作刮、刨、锛具使用[31]。
近年公布的一批保存完整的良渚文化石器木柄[32],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装柄和使用方式,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助于跳出过去石器装柄方式复原的僵化思维。
用微痕分析的方法研究石器的使用痕迹是石器功能研究最主要的方法。
石器的微痕研究包括低倍法和高倍法,两种方法经Semenov[33]、Keeley[34]、Odell[35]等微痕研究学先驱逐步发展、完善和检验,逐渐成熟,被大量用在旧石器的功能研究上。
童恩正先生较早将微痕研究的方法介绍到国内,尤其是关注了因为石器的运动方向和加工对象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刃部磨损痕迹,很有借鉴意义[36]。
此后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对打制石器微痕的分析[37]。
对磨制石器微痕的研究始于朱晓东对赵宝沟石器的研究,他通过低倍显微镜观察了石斧、石耜两类石器的使用和制作痕迹,并对其功能进行了推测[38]。
王小庆首次运用微痕分析高倍法研究了兴隆洼和赵宝沟遗址的磨制石器,并制备实验磨制石器标本用于不同加工对象,以探讨微痕的形成与材质和加工对象之间的关系[39]。
谢礼晔以二里头遗址的磨制石斧和有孔石刀为材料,通过微痕分析探索其功能,并讨论了该方法如何在磨制石器功能研究中运用及是否有效的问题[40]。
除了微痕法以外,石器的力学分析法也是初步了解石器功能的有效方法之一,这方面的研究以佟柱臣、杨鸿勋、季曙行先生的研究为代表。
佟柱臣先生是较早使用力学分析法来研究几种主要生产工具使用痕迹的种类、部位、面积和方向的,进而考察劳动对象的特点、劳动方法、劳动强度等方面的情况[41]。
当时微痕分析方法尚未介绍到国内,佟先生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可惜的是,这一方法未能引起国内同行的太多注意。
杨鸿勋先生分析了石楔和石扁铲的力学特征,并将两者从石斧和石锛中区别开来[42]。
季曙行先生从力学的角度分析了石质三角形器和三角形石刀的用途,认为仅根据器形认为石质三角形器是石犁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型三角形器受牵引力的限制,小型三角形器受器形的限制,均无作为犁铧使用的可能性,常型三角形器由于受构造和犁床等方面的限制,大部分也无法作为犁铧来使用,应将此种器物定名为石耜,将三角形石刀看作石犁和破土器等农具也不合适,其应是砍刀性质的工具[43]。
通过力学分析的方法探讨石器的功能和定名,扩大了研究视野,较之单纯用类型学和比附的方法,有更强的说服力。
四、磨制石器的原料和流通体系研究
石器的原料来源研究,讨论比较多的是玉器的原料来源,主要通过鉴定玉器的矿物成分及其显微结构来进行,同时还要研究其微量元素成分特征及稳定同位素特征等,采用的是地质学中常用的室温红外吸收光谱、X射线粉晶照相、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等方法。
在对玉器的矿物成分和显微结构认识的基础上,比较周围地质条件和所产玉器的有关特性,可以初步确定玉器的原料来源[44]。
但当需要精确判定某类玉器是否来自某地玉石矿时,此类科学分析方法无法达到考古研究的需要。
近些年学术界开始重视普通磨制石器的原料来源,如对山东临淄桐林遗址[45]、山西襄汾陶寺遗址[46]、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47]、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48]、河南南阳盆地[49]等重要遗址和区域的磨制石器石料来源的探讨,不是局限于某一种石料,而是关注石器群的整体原料来源,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观察这种原料的开发和流动。
石器贸易、地区与时代特点的研究方面,张弛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石器的生产和流通问题的研究,是大范围石器生产贸易流通研究的较好例证[50]。
玉石器的地区与时代特点的研究属于磨制石器宏观方面的研究,安志敏[51]、林惠祥[52]、佟柱臣[53]、陈星灿[54]、傅宪国[55]等学者在一个较大区域范围内对某种特定玉石器的分布、传播、演变都进行过成功的探讨。
赵辉在北方石镞的研究中,将石镞的分布情况与由陶器特征划定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通过石镞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了生计模式、社会变迁及技术传统等更深层次的研究领域[56]。
陈星灿对偃师灰嘴遗址出土石器的综合研究,探讨了早期国家的石器工业开发模式,将石器研究纳入到早期国家形成模式的研究中[57]。
探究最初的国家权力对不同种类的石制品的分配和交流策略,以及各个不同等级聚落在这一玉石器交换、分配网络中的位置,有助于丰富国家的起源阶段社会状况的研究[58]。
但总的说来,目前这类研究比较缺乏,而且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五、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目前关于石器方面的研究很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不可否认,史前磨制石器的研究仍然不受重视,在发表的各种发掘报告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以石器研究为切入点解决的考古学问题并不多。
虽然近些年发表的考古报告逐渐有重视磨制石器研究的倾向,关注分类和术语的界定[59],强调在石器研究中进行量化测量和分析[60],并开始出现专门以磨制石器为研究内容的硕士、博士论文,对磨制石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但目前中国的磨制石器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研究方法的限制,缺乏对大型遗址所有出土石制品的综合研究,石器的整体面貌很难认识。
有学者也认识到新石器时代石器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分类和定名时往往因人而异,缺乏深思熟虑[61]。
磨制石器的研究历来是考古发掘报告中最薄弱的部分[62],目前多数报告只是简单地将石器分类,统计每类的个数,并挑选少量石器进行描述。
很难将这种简单统计与描述称之为研究,因为我们并没有通过报告了解到该遗址石器的整体特征,更无从谈起石器的时代变化、岩性变化、功能、技术传统等方面的情况。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早期发掘报告的写作目的有关。
早期的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是以解决编年体系为目标,而石器的形态变化频率不如陶器快,不是理想的分期器物,故而导致学术界长期对它的忽视。
但随着各地编年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石器作为史前人类生计的重要载体,其整体面貌的研究对认识史前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应受到充分重视。
第二,现在石器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工艺上,没有更好地挖掘石器背后的信息。
从上述现状回顾可以看出,磨制石器的工艺研究已相对比较成熟,现在研究应跳出石器本身,通过石器来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对石器刃部损耗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史前人类的加工对象、劳动强度等信息。
制作石器的原料在某些地域并非广布型原料,正是这一局部分布特征,为我们探讨史前人类的石器制作及流通情况提供了可能,甚至可以进而探讨史前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地区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石器分类的科学性不够,定名混乱。
石器的定名是对石器进行整理的首要步骤,在这方面过去学术界往往重视不够。
石器的分类随意性很大,没有比较一致的分类依据、标准和顺序,导致无法在不同种类器物间进行对比。
分类的理想状态是还原古人的分类体系,石器本身有许多特征和表现特征的指标,哪些特征是有分类意义的,哪些特征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有分类意义的特征其重要性程度如何,该如何确定权重,这些都是我们在分类时需要考虑的,是否能进行合理的取舍决定着分类的成功与否。
第四,石器描述和分析的统计方法落后,还停留在简单的测量和计数层面。
不同时期石器形态的变化不大,石器统计方法的落后,导致无法发现石器的形态差异及演变。
如果使用更高层次的量化的方法,可以使问题简化或减少工作量,或者看出某种隐藏在考古资料背后的趋势、变化、相关性等。
所以只要在某些环节上有量化的必要,我们都需要进行尝试。
这种量化的意识应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把量化的努力作为石器研究的取向。
磨制石器具有原料来源相对容易确定的特点,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基本保留在生产地,因此比较容易确定石器的生产地和消费地。
这一研究优势可以为探讨史前社会聚落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载体,相信未来的磨制石器研究必定会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研究内容。
――――――――
[1]李济:
《殷虚有刃石器图说》,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2年。
[2][5][15][51]安志敏:
《中国古代的石刀》,《考古学报》总第10期,1955年。
[3]夏鼐:
《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5期。
[4][13]周晓陆,张敏:
《治玉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三件玉制品弃余物的研究》,《南京博物院集刊》7期,1984年。
[6]佟柱臣:
《仰韶、龙山文化石质工具的工艺研究》,《文物》1978年11期。
[7]邓聪,郑炜明:
《澳门黑沙》,澳门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8]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原考古队:
《周原:
2002年度齐家制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b.孙周勇:
《齐家制作坊生产遗存的分析与研究――周原遗址齐家制作坊个案研究之一》,载《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c.孙周勇:
《西周石?
i的生产形态:
关于原料、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探讨――周原遗址齐家制作坊个案研究之二》,《考古与文物》2009年3期。
[9]臧振华,洪晓纯:
《澎湖七美岛史前石器制造场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部分,2001年。
[10]张弛,林春:
《红花套遗址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3期。
[11]a.如安志敏先生曾实验用木片加砂蘸水法切割石料,见[2];
b.席永杰,张国强:
《红山文化玉器切割、钻孔技术实验报告》,《北方文物》2009年2期;
c.邓聪,吕红亮,陈玮:
《以今鉴古――玉石切割实验考古》,载《故宫文物月刊》264期,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
[12][19]牟永抗:
《良渚玉器三题》,《考古》1989年5期。
[14][18][22][25][28]林华东:
《论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载徐湖平主编:
《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16]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
《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4期。
[17]卢茂村:
《浅议安徽省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刀》,《农业考古》1995年3期。
[20]朔知,杨德标:
《薛家岗石刀钻孔定位与制作技术的观测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6期。
[21]霍有光:
《从玛瑙、水晶饰物看早期治玉水平及琢磨材料》,《考古》1992年6期。
[23]张明华:
《良渚古玉的刻纹工具是什么?
》,《中国文物报》1990年12月6日。
[24]林巳奈夫: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雕刻技术》,载同[14]。
[26]郝明华:
《良渚文化玉器探析》,载同[14]。
[27]陈廉贞:
《苏州琢玉工艺》,《文物》1959年4期。
[29][52]林惠祥:
《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
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3期
[30]肖梦龙:
《试论石斧石锛的安柄与使用――从溧阳沙河出土的带木柄石斧和石锛谈起》,《农业考古》1982年2期。
[31]李京华:
《登封王城岗夏文化城址出土的部分石质生产工具试析》,《农业考古》1991年1期。
[32]赵晔:
《良渚文化石器装柄技术探究》,《南方文物》2008年3期。
[33]S.A.Semenov,Prehistorictechnology:
anExperimentalStudyoftheoldestToolandArtefactsfromtracesofManufactureandWear.AdamsandDart,Bath,England,1964.
[34]Lawre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