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精品教育doc.docx
《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精品教育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精品教育doc.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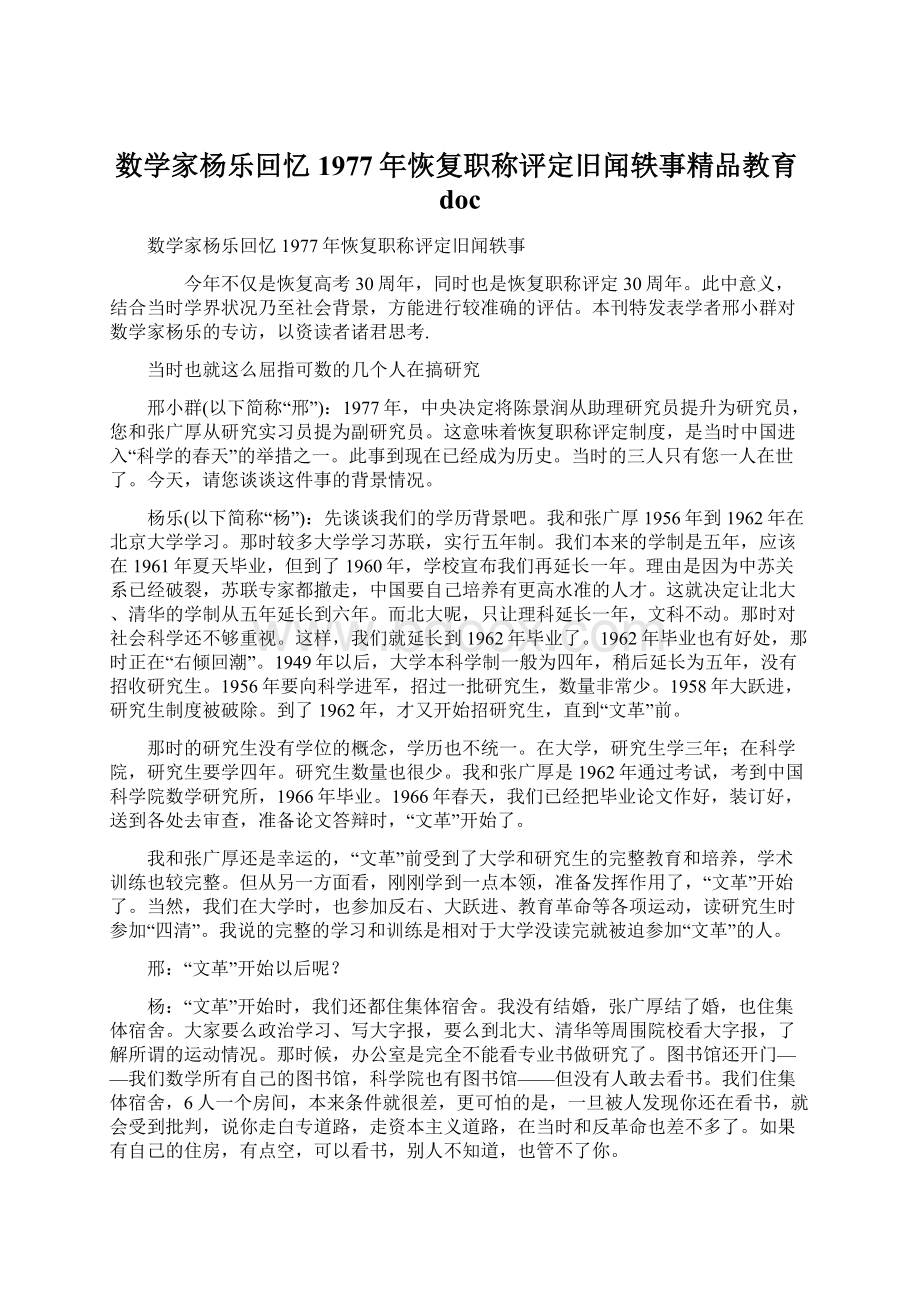
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精品教育doc
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
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
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
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
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邢小群(以下简称“邢”):
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
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
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
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
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
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
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
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
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
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
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
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
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
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
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
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
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
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
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
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
研究生数量也很少。
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
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
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
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
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邢:
“文革”开始以后呢?
杨: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
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
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
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
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
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
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
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
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
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
他上世纪80年代才结婚。
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做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做了他的住房。
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
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
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
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
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
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
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做十几岁刚入伍的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
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
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
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
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
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
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
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
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
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
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
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
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
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
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
“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
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
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
《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一年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
《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
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
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
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
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
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邢:
您还能回忆起对您和张广厚大力宣传的情况吗?
杨:
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
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
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
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呢?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
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
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
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
“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
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
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
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
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5位是搞纯粹数学的,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
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
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
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
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
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
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
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的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
但是很快,就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简报也就搁置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
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
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那么一小块报道罢了。
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
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
邢:
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
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
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
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
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
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
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
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
中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
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
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
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杨乐夫人)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
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
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确实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
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
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
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
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
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年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的院士)与我们的会见。
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
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