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穆旦的短暂Word格式.docx
《1957年穆旦的短暂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57年穆旦的短暂Word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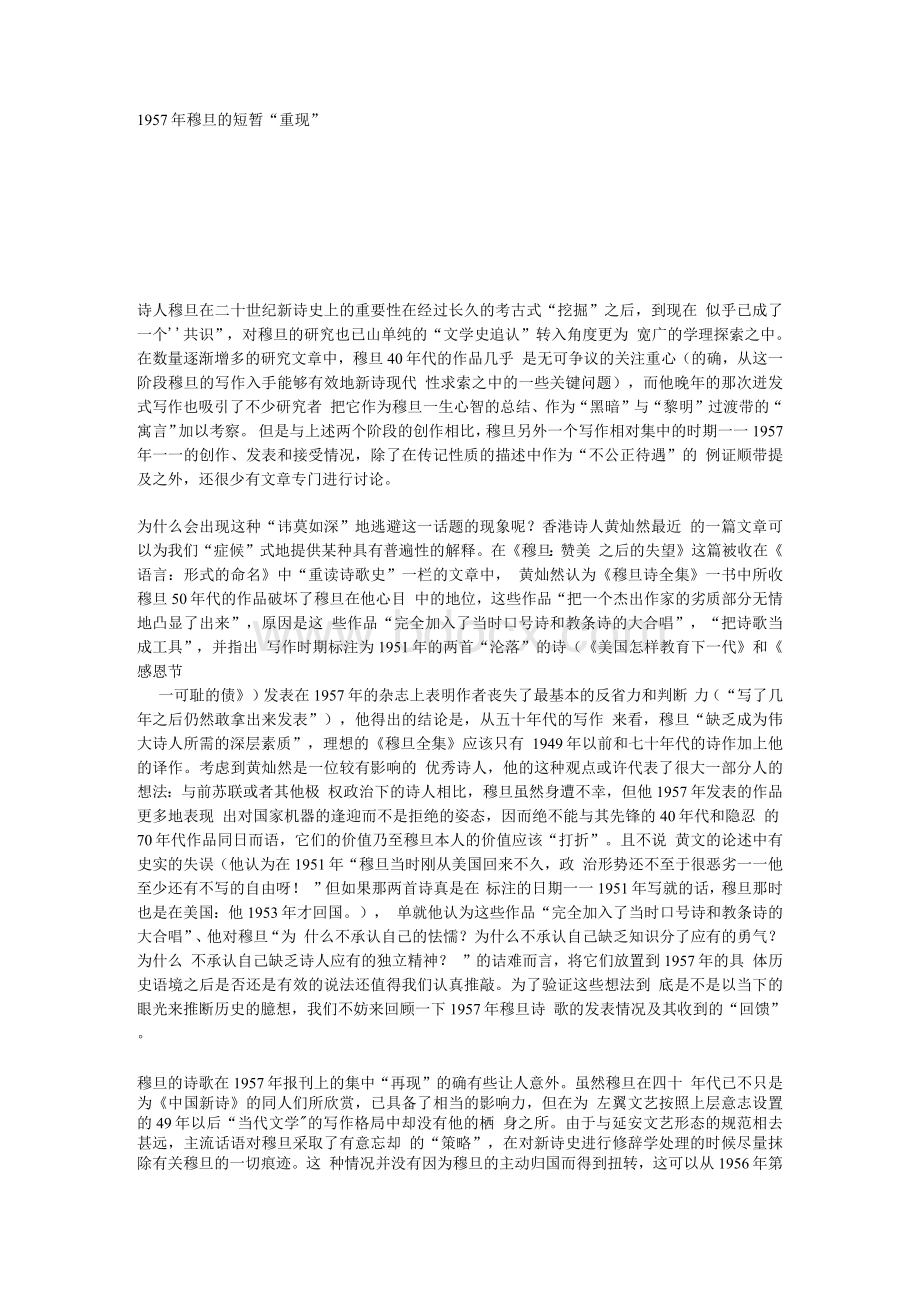
香港诗人黄灿然最近的一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症候”式地提供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
在《穆旦:
赞美之后的失望》这篇被收在《语言:
形式的命名》中“重读诗歌史”一栏的文章中,黄灿然认为《穆旦诗全集》一书中所收穆旦50年代的作品破坏了穆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些作品“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了出来”,原因是这些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把诗歌当成工具”,并指出写作时期标注为1951年的两首“沦落”的诗(《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
一可耻的债》)发表在1957年的杂志上表明作者丧失了最基本的反省力和判断力(“写了几年之后仍然敢拿出来发表”),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十年代的写作来看,穆旦“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理想的《穆旦全集》应该只有1949年以前和七十年代的诗作加上他的译作。
考虑到黄灿然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优秀诗人,他的这种观点或许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
与前苏联或者其他极权政治下的诗人相比,穆旦虽然身遭不幸,但他1957年发表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对国家机器的逢迎而不是拒绝的姿态,因而绝不能与其先锋的40年代和隐忍的70年代作品同日而语,它们的价值乃至穆旦本人的价值应该“打折”。
且不说黄文的论述中有史实的失误(他认为在1951年“穆旦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至于很恶劣一一他至少还有不写的自由呀!
”但如果那两首诗真是在标注的日期一一1951年写就的话,穆旦那时也是在美国:
他1953年才回国。
),单就他认为这些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他对穆旦“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怯懦?
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分了应有的勇气?
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缺乏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
”的诘难而言,将它们放置到1957年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是否还是有效的说法还值得我们认真推敲。
为了验证这些想法到底是不是以当下的眼光来推断历史的臆想,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957年穆旦诗歌的发表情况及其收到的“回馈”。
穆旦的诗歌在1957年报刊上的集中“再现”的确有些让人意外。
虽然穆旦在四十年代已不只是为《中国新诗》的同人们所欣赏,已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在为左翼文艺按照上层意志设置的49年以后“当代文学"
的写作格局中却没有他的栖身之所。
由于与延安文艺形态的规范相去甚远,主流话语对穆旦采取了有意忘却的“策略”,在对新诗史进行修辞学处理的时候尽量抹除有关穆旦的一切痕迹。
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穆旦的主动归国而得到扭转,这可以从1956年第一号《文艺报》上一幅颇具象征意味的大型作家群像漫画《万象更新图》得到侧面证明:
在这幅寓示着“新中国”文坛人员构成情况的“钦定清单”上没有穆旦的影子。
但是一年之后,在诗歌创作上长期销声匿迹的穆旦连续地在《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长诗《葬歌》、在《人民日报》5月7号第八版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在《人民文学》第七期上发表了《问》、《我的叔父死了》、《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也许”和“一定”》、《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一一可耻的债》七首诗。
这是否意味着穆旦为了适应“当代文学”的写作规范已彻底调整了自己的“文化性格”?
是否暗示了穆旦在一定程度上已被主流文坛部分地接受?
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从发表的背景、作品本身的意蕴以及作品的接受情况加以综合考察。
首先,穆旦的诗歌“再现”于1957年这一特殊的年份而不是其他时期,这一文学事实本身就暗示了从1957年的文学状况入手可以发掘到当代文学看似铁板一块的整体构成之中一些微妙的“另类”因素。
兴许是当下思想、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许多人习惯于臆想“另类”成分存在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一一沉默、拒绝、抗争,而忽略了在“一体化”构成的内部缝隙中查找“另类”的赋形方式,凡在十七年期间以非地下的面目出现的作品常常被时下历史感簿弱的人统统视作“与主流媾和"
,这样,主流文艺形态自身在十七年期间的几次艰难的自我调节努力就会被轻易地埋没。
1956、1957年的“百花文艺”正是这几次“自我调整”之一。
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不只是统治阶层根据特殊的国内、国际形势实施的思想统治“策略”,在文艺界内部也是左翼文艺对规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常识着进行自我改善的结果,非主流的文学力量对规范的质疑和文艺领导者对规范化步骤的适度放松(这被有些研究者成为“窄化主流”之后的“退却”)同时并存,其标志不仅是左翼内部诸种岐见之间的讨论、争鸣得以展开,更表现在新刊物的大量创办与老刊物的改版上,这导致一部分被遗忘者开始在刊物上“重现”,强化了对当代文学写作惯例、文学史编撰和文学批评的质疑。
《诗刊》是创刊与1957年当年的刊物,因而在贯彻“双百方针”上一度比较得力,直到1957年4月在形势出现波折之后召开的依次文学期刊编辑会上,有《诗刊》在内的几个文学刊物仍把编辑重点防在“大放”和“大开门”上。
《诗刊》所刊载的与穆旦同属“被遗忘”性质的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解冻》象征性地点出了当时《诗刊》的气氛,所以穆旦的《葬歌》出现在《诗刊》上也并不是那么意外。
《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刊登穆旦的诗也是源于“双百时期”《人民日报》的“改版”。
从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由4版增至8版,其第八版副刊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言论集散地,它“宽容”到了甚至“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在此背景下,1957年5月7号穆旦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
而发表穆旦《诗七首》的《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在显示“异质性”、昭示文学体制内的自我调节能力方面更始具有代表性。
《人民文学》本来就在“双百时期”办得比较活跃,再加上这一期《人民文学》的主办人在山雨欲来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阳谋”,更大胆地编印了包括大量有争议的小说、杂文、诗歌的特大号,里面的作者不仅有年轻的挑战者(如李国文、宗璞、丰村等),更有象穆旦、沈从文这样的文学休眠火山的最近喷发物,以致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一期“特大号”始终是批判的焦点。
由上述的发表背景可以看出,至少这些刊物在1957年采纳穆旦的诗并不意味着只是把穆旦当作规范化进程中的一颗螺钉来使用,与其说穆旦这些诗“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不如说它们参与组成了1957年各刊物上的“反口号和反教条诗的迭唱”,并不是穆旦完全放弃写作个性以屈就主流,而是“主流”因内部的变异主动要求容纳穆旦这样的另类因素。
而这些诗究竟是从哪些角度、以怎样的方式质疑了“规范”,我们需要探讨这些文本所包含的曲折的意蕴。
进入十七年作品的一个前提是必须避免拿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前苏联、东欧的流亡、准流亡作家的写作伦理和立场来衡量一些当时的“另类”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化性格,这样很容易得出“反抗不纯粹、不彻底”的结论。
事实上,许多49年后被冷却的知识分了,包括穆旦在内,他们多新生政权和新的话语机制的态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既有真诚的拥戴、又有冷静的反思,既有投入的愿望、又有疏离的勇气,既有愤怒、牢骚,又有犹豫、迟疑,当然也有策略性的迎奉。
只有深入到当时的文本/现实语境中我们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复杂、微妙的情感张力以及这种张力传达出的带有历史宿命色彩的悲剧意味。
穆旦1957年的这些作品透露出来的正是“丰富与丰富的痛苦”在1949年之后新的延续形式:
一种在质朴的真诚和深刻的怀疑之间来回磨蚀的心态。
标注写于1951年的两首直截了当的西方社会“风俗画”式的讽刺诗的确显示了与40年代创作的巨大断裂。
在作者以往诗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主”、“上帝”在这两首诗里成了讽刺的对象一一“黑衣牧师每星期向你招手,/让你厌弃世界和正当的追求”(《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一-上帝!
”(《感恩节-可耻的债》),而仅仅在三年前《诗》的第一首里还有“你,一个不可知,横越我的里面/和外面,在那儿上帝统治着/呵,渺无踪迹的丛林的秘密”这样把“上帝”一词抒情化、神秘化的诗句。
而耐人寻味的是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七首诗惟独只有这两首标注了写作年代,而这一年份恰好又是穆旦身在美国、容易引起政治“追审”的时期。
由于缺乏有关的传记史料,我们很难想象早在归国之前、在上帝的“老巢”一一西方,作者就已将他个人词汇表中的核心语码淘汰掉了。
可以猜测的是:
这两首诗是否是作者本人将写作时期该为1951年并醒目地标注出来以表明及时的“觉悟”?
抑或是真的写于1951年,但惟独这两首诗标上时期,其目的是否也是为了强调作者在1951年虽然空间上与“祖国”割裂,但在时间上却由于与“上帝”的割裂而与新政权建立了某种亲和关系?
应该看到,即使是处于这样那样或惶恐或狡黠的考虑,作者也没有放弃独特的节奏感和情绪强度。
《葬歌》一诗包含了四十年代“新诗戏剧化”观念的延续。
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作者往昔惯用的“指称分裂”的手法把自己剖成一个“你”(旧日的自己)和一个“我”(现时的自己),通过“我”对“你”轻声诉说的口吻表露出与过去永别的愿望。
第二部分是典型的虚拟戏剧化场景,其中还包含了英诗中惯用的把“回忆”、“爱情”、“恐惧”、“希望”、“信念”等名词人格化的手法,设置了不同力量对“我”的诱惑、争取。
第三部分的“我”的声音消去了戏剧化的成分而与作者自己的声音叠合,用自白的语气真诚地讲述出了自己的心声:
因为“包袱很重”“我的葬歌只唱了一半”并预感到“有人回嫌它不够热情”。
全诗无韵诗体、诗剧体、素体诸体式配合错落有致,其形式本身就暗示了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迂回动荡的心理状况:
既有作者后来所说的“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诚挚,更有着一种优雅而犹疑的哈姆雷特式的矛盾。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新政权下几乎所有旧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对此梁秉钧曾在《穆旦与现代的“我”》一文的结尾部分提及:
“他诗中的’我’多少带着一种社会、文化或心理的身份......到了1957年,当他写作《葬歌》的时候,仍然是希望通过’我’的感受去反省思想的转变。
”
《问》这首诗写出了某种写作的困境:
在“夜莺”离开、不能再抒写生活的悲哀之后,如何面对“原野的风”写“空中的笑声”?
这隐约透露了自己是否能承受“颂歌式,,写作模式的怀疑。
有意思的是诗中把“生活”人格化为强大的“你”,写作的人被暗喻为被握的“笔”(生活呵,你握紧我这只笔),结尾以反讽的手法(唉,叫我这只尖细的笔/怎样聚敛起空中的笑声)质疑了“生活〃“我〃“笔”之间的关系,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对“创作反映生活”、“作家是政治的工具”等观念的暗中消解。
《我的叔父死了》是一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作者过去的隐晦风格、具有释义含混性的诗。
他由叔父死了以后自己既不敢哭也不敢笑的尴尬状态(对“自我检查”的反讽)迅速闪到孩提“过去的荒凉”和抑制眼泪的“希望”,诗的最后一节“平衡把我变成了一颗树,/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从某种意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渴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