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docx
《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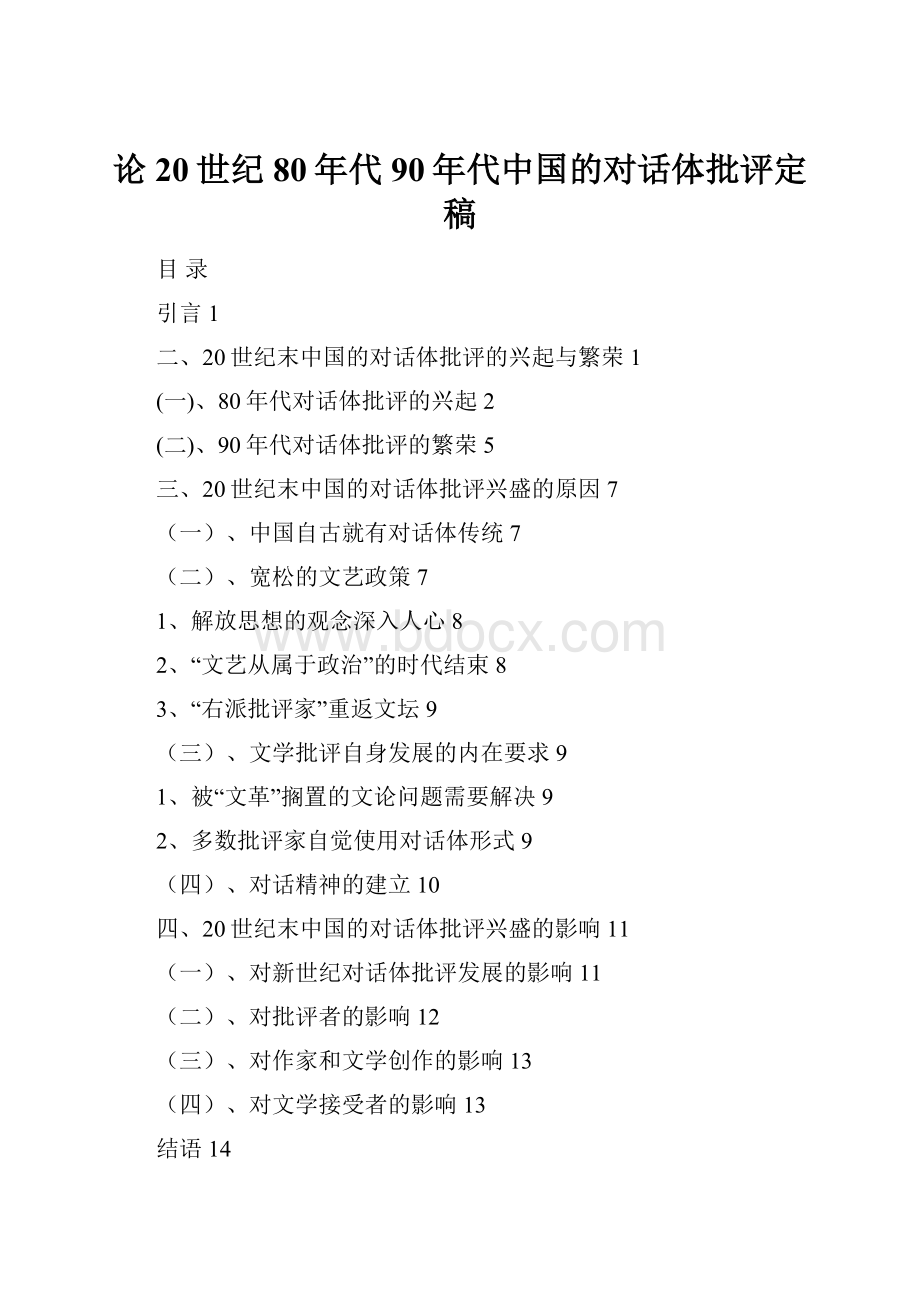
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
目录
引言1
二、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的兴起与繁荣1
(一)、8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起2
(二)、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繁荣5
三、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原因7
(一)、中国自古就有对话体传统7
(二)、宽松的文艺政策7
1、解放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8
2、“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时代结束8
3、“右派批评家”重返文坛9
(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9
1、被“文革”搁置的文论问题需要解决9
2、多数批评家自觉使用对话体形式9
(四)、对话精神的建立10
四、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影响11
(一)、对新世纪对话体批评发展的影响11
(二)、对批评者的影响12
(三)、对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13
(四)、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13
结语14
参考文献15
致谢16
论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
引言
对话体文学批评文体是一种以对话为呈现形态的批评方式,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话者对某种文学现象、某一文学思潮或者某个作家、某部文学作品进行共同批评讨论和对话交流而形成的一种文学批评文体。
巴赫金说:
“对话关系无疑绝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要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
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须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
”因此,我认为对话体批评从形式上来说,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批评主体,这是对话展开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必须要有讨论和对话的焦点,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有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
最后,从批评文共同的特征来说,在对话体批评中,批评主体围绕话题展开讨论,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必须是在同一个文本中呈现的。
事实上,对话体批评并不是新时期的产物,相反,它是一种古老的文艺批评体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对话体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交锋与对话使对话体批评出现在了大量诸子百家的典籍中。
《论语》实际就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以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形式编撰而成。
在古代西方,最典型的对话体文艺批评莫过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用对话体写就文艺批评文集——《文艺对话录》。
纵观中国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史,对话体批评样式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绽露头角。
例如徐可在《谈谈<落花生>的评论特色》一文中提到:
“茅盾在写《落花生论》时,假借主客体对话,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而成。
”
而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真正走向兴盛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本文将对20世纪末中国对话体批评兴盛的状况、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
二、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的兴起与繁荣
(一)、8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起
对话体批评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在批评界形成一种气势是到新时期以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继“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后的第三个文学时期。
因此,这里的“新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多的标示着中国当代文艺新的精神走向,包含着打破束缚、推陈出新的意味。
在新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更迭愈加频繁,文艺争鸣愈演愈烈。
1981一1984年前后,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杂志、大学学报以及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商榷性的文章。
如曾繁仁的《论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与薛涌、王瑞生同志商榷》,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鲁子涛的《我对列宁讲的“自由的文学"的理解——与杜书瀛、李中岳二同志商榷》,鲁枢元的《关于灵感论的一点质疑——与庄其荣同志商榷》以及庄其荣与之相回应的《关于艺术认识与审美创造的几点浅见——兼答鲁枢元同志》沈敏特《批评不能靠臆测——与刘金同志商榷》,吴国琳、王新民《究竟谁离真理更远——答刘金同志》等等。
这类商榷性文章大多发表在著名的文艺类杂志上,如《读书》、《文艺理论研究》等,因此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也向更多的读者和作者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在文艺界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讨论。
同时这种商榷的方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广泛接受和喜爱的。
商榷的各方态度是平和的,地位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文艺批评者们文艺、文学理论领域各种问题发表的观点被尊重和关注,他们获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这对促进新时期真正的对话体批评文的出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商榷性文章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体批评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
商榷性文章往往是对另一文章即目标文章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参与讨论的对象往往就是目标文章的作者,而目标文章的作家往往是在其他文本中答复商榷者提出的问题。
(如:
鲁枢元的《关于灵感论的一点质疑——与庄其荣同志商榷》和庄其荣与之相回应的《关于艺术认识与审美创造的几点浅见——兼答鲁枢元同志》)。
而对话体批评最常见的形式是讨论双方或多方观点集中呈献在一篇文章里。
另外,商榷性文章在学术上的讨论多是“单向质疑”,鲜有“双向交流,对话体批评是对话双方无阻碍地自由交流的呈现。
这也是商榷性文章和对话体批评主要的不同之处。
那么新时期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体批评文是什么呢?
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中提到:
“就笔者视野范围,新时期最早的对话体批评大概要算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
——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
”这篇对话体批评文记录了一个新艺术家与他的一位友人在初夏的某天傍晚在公园的长椅上又谈起了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艺术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辩与探讨。
如果说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商榷性文章为新时期的对话体批评奏响了前奏,那吴亮的这篇《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
——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正式拉开了新时期对话体批评的序幕。
在大多数批评者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对话体这一批评体式的作用和意义时,吴亮又是如何想到用这种方式呈现对话双方的观点的呢?
吴亮在《答友人问》中如是说:
“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一份由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
……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
”确实,对话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交流,在对话双方的平等交流、言语交锋中碰撞出的思想的火花蕴含着极大的价值。
正如吴亮所说,这种对话或者没有一个十分明朗的结果,但是这种未成结论的思想最逼近真实,也非常吸引接受者,它驱使着批评者自觉地记录下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体批评应运而生。
虽然吴亮的这篇《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
——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文艺批评家的注意,甚至已经有不少批评家认识到对话、交流在文艺批评领域的重要性,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直接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出的批评文很少,也就是说,批评家很少直接将对话内容写进文本。
很多批评家还是倾向于一些商榷性的批评文体。
随着讨论问题的增多和讨论话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意识到商榷性文体的弊端。
商榷性文体讨论的双方在不同的文本中,而且往往发表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上,导致沟通交流上的诸多不便,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拖延了文艺界争论、解决的进程。
商榷性文体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当时文艺论争的需要。
从1981年到1985年,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关注成为文艺界的热点问题。
波特莱尔、卡夫卡、海明威等作家名字逐步被国内文艺界熟悉并接受。
大量新潮文学、电影、音乐等也涌入大陆。
1983年周扬在几年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很多批评家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
在这场讨论中,西方的许多文论、哲学思潮被引进。
这一时期,文艺争鸣的焦点也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围绕具体作品转向纯粹的理论性问题。
如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批评方法问题,这样就引发了“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文艺界的这些讨论的广泛性和迫切性使批评家们急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比商榷性文体更便于争论的批评体式。
同时,1985年、1986年这两年,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又成为了评论界的热点问题。
批评家们将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的批评文体。
对话式的批评文体也重新登上了评论界的舞台并大放异彩。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的对话体批评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方面是由于这三位作家当时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比较高,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观念上的现代性和文体形式的新颖性吸引了大批读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中这样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这篇对话体批评带有浓郁的‘新’与‘现代’的色彩,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话体以众多声音的差异、交流、互补构成一种合力的姿态,显示出了这一思想观念的长久酝酿与分量。
反过来,这篇对话体也提高了对话体批评的地位和魅力。
”参与讨论的三位著名学者以平等的方式,心平气和的态度发表个自的观点,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整篇对话体批评文完整地展现了新的观点在对话、交流、碰撞中产生的全过程,让读者仿佛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即了解了三位学者的观点,又参与了批评的进程,感受到了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学术魅力。
这篇对话体批评让更多的批评家、学者看到了对话体批评问题在现实批评领域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并且具有独特的优势。
因此,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批评家参与其中,尝试运用对话式文体进行文学批评,并且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从此,对话体批评文便迅速发展起来,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批评体式。
庆西、钟本康的《关于新笔记体小说的对谈》在1986年第2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发表,《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在《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上发表,《文学的与艺术的情思—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文学对话》发表在988年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吴方、黄子平的《关于小说主体学》发表在《北京文艺》1989第2期上。
王干、王蒙《感觉与境界》发表于《光明日报》1989年4月25日第三版。
1988年初,年青的批评家李劫在京沪等地连续与许多批评家、作家对话。
新时期对话体批评的先驱——吴亮更是将1981年起陆续写的系列“对话”结集为《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百家争鸣的局面蔚为大观,而对话式批评文体更是成为了众多学者的宠儿,参与其中,热衷于创作对话体批评文的即有当时刚刚在批评界崭露头角的新鲜面孔,陶东风、陈晓明等,也不乏批评界的元老如贾植芳、钱谷融等。
在批评所涉及的内容上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古代文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等传统问题的探讨,又有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文学新问题的论争。
众多批评者尝试对话体批评文体更使这一批评体式的地位迅速上升,它在处理文艺争论上的文体优势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从本质上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学者接受并赞同茨坦·托多洛夫根据巴赫金的一个理论观点——“对话”提出的“对话的批评”。
(二)、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繁盛
如果说,对话体批评20世纪80年代犹如一颗新星,逐步在文艺批评界流行起来,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话批评己成了最基本、最引人注目的批评范式之一,它的流行达到了高潮。
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所谓后新时期之说。
这标志着与80年代文学相比,90年代文学又有了巨大的差异。
可以说9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转型年代,也是诸多文学思潮涌现、碰撞的年代,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新写实主义思潮、新生代文学思潮⋯⋯在90年代文学思潮中,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思潮、讨论事件最初大多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的。
1993年6月,《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王晓明和他的几个研究生的谈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对于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读书》杂志专门为这场讨论刊发了一组“寻思录”。
在这场大讨论中,许多作家、学者参与进了对话体批评,如张汝伦、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等。
据统计,仅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发表在全国著名文艺类刊物上的对话体批评文就有几十篇。
如朱向前、陈骏涛《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与互补》,蒋孔阳等《立足高标准,反对平庸》(《文论报》1993年1月2日)。
一些国内知名文学杂志在这一时期更是成为了对话体批评的主要阵地。
《上海文学》上有王晓明主持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陈思和主持的《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上海文学》1993年第7期)、谢冕主持的《理论的文学史框架》(《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陈平原主持的《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印国明主持的《话说正统文学的消解》(《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沈乔主持的《文学和它所处的时代》。
《读书》杂志上刊发了张汝伦、王晓明等人的《人文精神:
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
《钟山》有陈晓明主持的《新“十批判书”》、李陀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5期)等。
《作家》上也频频出现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的对话录。
潘凯雄、朱晖等人在1993年12月11日下午的谈话被整理成文《对话录:
批评号脉》发表在《作家》1994年第3期。
王晓明、陈思和、等大家也以《作家》为阵地,主持了《精神废墟的标记》(《作家》1994年2期)、《关于世纪末小说多种可能性的对话》等影响深远的对话体批评。
特别是陈思和主持的《关于世纪末小说多种可能性的对话》分别在《作家》杂志1994年第4期、第6期、第8期第10期刊发了4篇系列对话体批评。
刘振云、李振声、郜元宝、余华等知名作家均有参与。
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对于一种古老的批评文体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也都有专门的对话批评专栏,影响比较大的对话体批评文有:
王干等《“新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傅杰、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丁帆等《晚生代:
“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性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王光明等《两性对话:
中国女性文学15年》(《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孙绍振、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
可以说在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而新颖的批评体式在20世纪九十年代如同枯木逢春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此,杨扬在《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作了概括:
“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
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
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
三、20世纪末中国对话体批评发展、兴盛的原因
(一)、中国自古就有对话体传统
笔者在上文就提到过,对话体批评并不是在中国新时期以来产生的新的批评文体式,相反,它是一种古老的批评文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话体批评的传统。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下,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思想的交锋与对话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这直接促进了对话体这一形式的发展并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为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先哲们就已经用对话体创作了一系列著作。
例如《论语》实际就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以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形式编撰而成的,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崇文尚儒的国策使北宋的文人群体不断壮大,文人自发组织的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也逐渐增大。
集会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便是谈论古今诗文,评鉴诗作。
这种文艺批评是在群体讨论中产生的,它有别于一般的文艺批评,是一种典型的对话体批评。
参与对话的文人一般具有同样水准的文艺修养,由于个人的审美角度和能力的不同,从而针对同一作品发表不同的评论,甚至是展开争论,形成了一种对话体文艺批评。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与叶致远、苏轼与毕仲游都展开过此类的文艺批评对话。
袁济喜在论文《从先秦诸子的对话体看汉语批评》中提到:
“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汉语批评的母体。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形成组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
”因此,可以说,对话体是中国古代思想发生、发展,得以传承的重要工具。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对话体充分体现了“包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
对话、交流、“和而不同”的思想早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
所以,新时期以来,对话体批评的异军突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二)、宽松的文艺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将近30年的时间中,中国文学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两个阶段。
对于文学界和文艺批评界来说是一个束缚不断加剧的时期。
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在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的状态。
事实上,早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确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
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是在批判、斗争中进行的。
而文艺界的批判、斗争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完成的。
权威话语权对文艺进行了过多的政治干预,使批评界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或不敢开口,或只是迎合上层政策和指示,批评界缺乏宽容精神和必要的言论自由。
比如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因为一篇社论的发表,批评界一致批判电影的“反动性”,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文艺将以政治标准评判艺术问题。
再比如文艺界集体对胡风文艺思想以及胡风本人的批判,最终上升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批判。
在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将近30年里,文艺工作已俨然成为一项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文艺评论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只是一味地对政治风向的迎合,连实事求是的评论都不多见,更谈不上对话和争鸣。
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批评家们对文艺界的敏感问题噤若寒蝉。
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对话体批评基本上已经被无形的禁止。
1、解放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从否定过去尤其是10年“文革”中所推行的文艺政策、文艺观念起步的。
国家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文艺政策。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
特别是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
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
“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无疑更加推动了新时期文艺复苏和文艺争鸣。
2、“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时代结束
在宽松的文艺政策下,人们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引发了新的辨识和争鸣,在这场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0年7月26日)。
“两为”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文艺丛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批评界终于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大量商榷性的文章蜂拥而至。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话体批评才得以复苏并逐渐被广泛运识和争鸣,以至于迅速流行起来。
因此,可以说宽松的文艺政策为对话体批评的新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3、“右派批评家”重返文坛
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一批作家、批评家重新获得了应有的权利,重返文坛,成为“重放的鲜花”如吴祖光、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高晓声等等。
一些批评家、作家在历经挫折后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积极投入到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在推动文艺争鸣和文学思潮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蒙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投入到对话体批评的创作中,与一批青年批评家的对话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提携了年轻学者的同时也推动了对话体批评的发展。
(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1、被“文革”搁置的文论问题需要解决
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很多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被压制、搁浅,在新时期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于此同时,中国文学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
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的介绍和讨论成为了文艺界的热点,西方的许多文论、哲学思潮被引进。
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现象学等等。
之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即“三论”)等被引进并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高潮。
新时期,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对朦胧诗、文艺心理学、复杂性格、文学主体性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这样一个旧问题急待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外国的理论、思潮和方法蜂拥而至,各种理论研究推陈出新的时代,在中西方文化、理论交流碰撞的时代,对话交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多元文化的交流促使对话体批评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走向繁盛。
2、多数批评家自觉使用对话体形式
被从批评主体来说,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结束前,文学批评只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附庸,甚至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很多批评家被迫丧失了自我,一味迎合政治风向,成为了“传声筒”。
所谓的文艺评论往往代表少数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批评家的观点,并且是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威性定论。
绝大多数评论家、批评家们在当时实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被剥夺了发表言论的自由。
在经受过这样的重压之后,这些批评家、评论家们突然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流,在宽松的政策下,曾经被束缚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各种思想、言论、话语冲破压抑和束缚,喷薄而出,势不可挡。
他们更加迫切需要同行之间的交流,无阻碍的,自由平等的对话,而对话体批评恰好是能够满足他们这些需求的最好的批评体式。
同时,对话体批评这一批评体式象征着自由、平等的学术交流,这对于长期被权威话语压制着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很快被众多批评家接受并自觉使用。
这直接推动了对话体批评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
(四)、对话精神的建立推动对话体批评的兴盛
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的批评体式在沉寂了千百年以后,在20世纪末突然兴盛起来,除了得宜于宽松的政治气氛,顺应文学争鸣的需要外,我认为还与对话精神的建立密不可分。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巴赫金和哈贝马斯。
巴赫金是前苏联著名的美学家,在他的众多美学思想中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他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
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
巴赫金还认为,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存在。
思想的存在是对话的前提。
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建立了“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相互理解的行为,理解过程则是语言过程,即是一种交谈和对语。
哈贝马斯说过:
“纯粹的主体问性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
对话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操演时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