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烟妆.docx
《小烟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小烟妆.docx(3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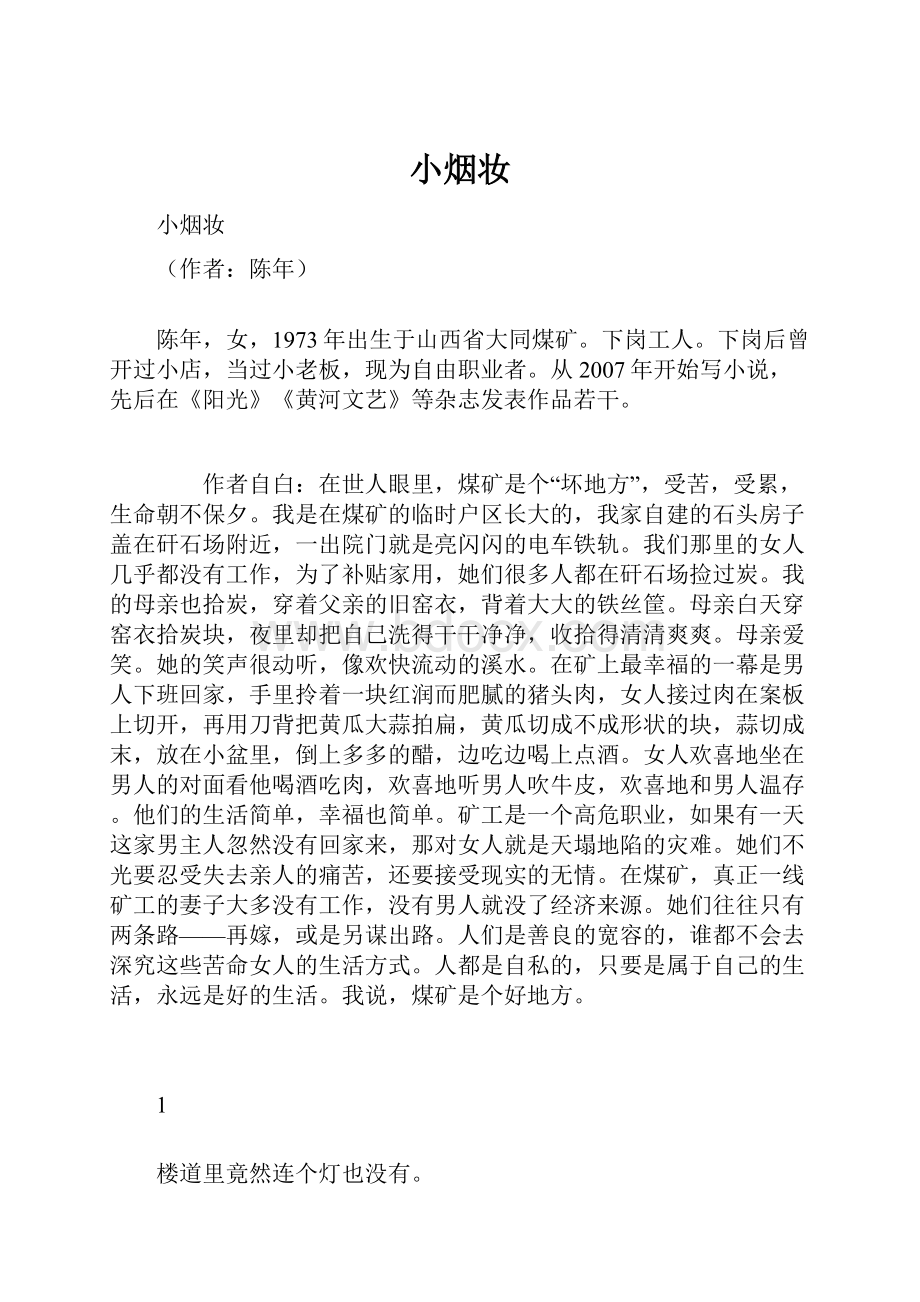
小烟妆
小烟妆
(作者:
陈年)
陈年,女,1973年出生于山西省大同煤矿。
下岗工人。
下岗后曾开过小店,当过小老板,现为自由职业者。
从2007年开始写小说,先后在《阳光》《黄河文艺》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
作者自白:
在世人眼里,煤矿是个“坏地方”,受苦,受累,生命朝不保夕。
我是在煤矿的临时户区长大的,我家自建的石头房子盖在矸石场附近,一出院门就是亮闪闪的电车铁轨。
我们那里的女人几乎都没有工作,为了补贴家用,她们很多人都在矸石场捡过炭。
我的母亲也拾炭,穿着父亲的旧窑衣,背着大大的铁丝筐。
母亲白天穿窑衣拾炭块,夜里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清清爽爽。
母亲爱笑。
她的笑声很动听,像欢快流动的溪水。
在矿上最幸福的一幕是男人下班回家,手里拎着一块红润而肥腻的猪头肉,女人接过肉在案板上切开,再用刀背把黄瓜大蒜拍扁,黄瓜切成不成形状的块,蒜切成末,放在小盆里,倒上多多的醋,边吃边喝上点酒。
女人欢喜地坐在男人的对面看他喝酒吃肉,欢喜地听男人吹牛皮,欢喜地和男人温存。
他们的生活简单,幸福也简单。
矿工是一个高危职业,如果有一天这家男主人忽然没有回家来,那对女人就是天塌地陷的灾难。
她们不光要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接受现实的无情。
在煤矿,真正一线矿工的妻子大多没有工作,没有男人就没了经济来源。
她们往往只有两条路——再嫁,或是另谋出路。
人们是善良的宽容的,谁都不会去深究这些苦命女人的生活方式。
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是属于自己的生活,永远是好的生活。
我说,煤矿是个好地方。
1
楼道里竟然连个灯也没有。
女人踩着高跟鞋噔噔地爬楼梯,男人摸黑跟在后面,心里不由得有点儿紧张,他想到了捉奸在床。
又为自己的念头好笑,紧张个屁!
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
窗帘都挂着,屋里光线很暗,男人的眼睛好一会儿才适应。
女人把包放在床头,顺手开了一盏小彩灯。
暧昧的粉红色一层一层铺开,光晕罩着床上的小碎花,有那么一点儿良宵苦短的意思。
一室一厅的小屋,根本藏不了第三个人。
男人还是不放心,借口上厕所,又把里里外外查看一遍。
确信很安全后,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松弛下来。
男人窝在沙发里点了一根烟,慢悠悠地吐出一大一小两个烟圈。
2
晚间的《平城新闻》插了一条封路通知。
通知说,从三月十八日晚上十时起,同泉路东段至西段开始施工,所有车辆请绕行。
住在城里的三鬼打电话给刘军,约他出来跑摩的。
刘军知道城里早就禁了摩的。
所以他说,我可不敢干,撞到警察手里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说不定连摩托车也给没收掉。
到那时不光丢把米,连鸡也被人家宰吃了。
三鬼在电话那头嘿嘿地笑,女人活个俏色,男人活个调对。
你这人真是个死脑筋,摩的禁是禁了,可眼下不是要修路吗?
修路了,公交绕道,出租车又开不进来,你让那些踩着十厘米高跟鞋的女人扭扭搭搭地怎么出门?
总不能拎着鞋光脚丫跑吧。
再说了,修路的时候警察也睁一眼闭一眼。
没人管闲事,只要避开那几个主要的交通路口,趁乱一个月轻松地抓弄个三五千。
不比你在矿上蹲守强。
我听说现在人们都搬到棚户区的新楼房,矿上跑出租的比坐出租的人还多。
刘军嗯了一声。
前天还因为抢客差点儿和人打起架。
平时刘军他们把车都停在汽车站路口,只要有中巴公交停下来,他们就拥上去问人家,要车不?
要车吗?
刘军干这行是老手,他不像别人见一个问一个,他专门问那些拿东西带小孩子的女人。
女人家力气小,拿不动东西就会打个车。
本来是他从中巴车搭好的客,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去张家湾,价钱都说好了,三块。
这时长腿从旁边冲过来硬插进一手,张家湾两块钱。
客人就被他撬走了。
刘军生闷气,等长腿拉完活,两个人约好在牛头山见。
架当然没打起来,长腿说,他孩子上学花了一大笔钱。
高价生,学费都是和亲戚朋友借的,要不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也不会这么不要脸地抢活儿。
刘军一句话也没说,转身慢慢往山坡下走。
不管长腿说的是真话假话,跑出租这个活儿是越来越难做下去了。
得另外想别的挣钱法子。
三鬼和刘军以前在一个掘进队上班。
三鬼是矿上从村里招来的农协工,合同到期后,赶上下岗的风头,就丢了工作。
三鬼不想再回村里种那几亩薄田,人有脸树有皮,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三鬼在矿上风风光光地当工人,现在领着老婆孩子灰头土脸地回去,还怎么见人?
还有孩子上学的事也让人头疼,村里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学校里没剩下几个孩子,一个老师同时教五个年级的学生,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是啥水平。
三鬼先在附近村办的小煤窑下井,人年轻又舍得出力气,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
他女人也没闲着,给一家手工馒头店和面蒸馒头,一个月给四百块,就这样一家人勉勉强强留在了矿上。
三鬼脑子灵活,很快发现了比下煤窑更挣钱的营生——跑出租。
那时候大矿附近的小煤窑很多,窑主只管出煤不管修路,矿区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中巴车根本不愿意进矿,工人出矿进矿都打摩的。
三鬼趁机买了一辆二手摩托停在矿门口跑出租,跑一趟小煤窑就有十来块的进项,一天下来倒比上班还强。
没用半年,三鬼便换了一辆新摩托。
三鬼请刘军喝酒时张牙舞爪地说,出租是没本的买卖,只挣不赔。
过两年换他辆汽车开开,到时候就是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
三鬼喝多了,连说带唱。
那年刘军出工伤后关系转到劳保科,工资少了一半,日子过得像是缩过水的布,怎么拉扯也是差一大截。
兄弟情深,困难关头三鬼拉了他一把,买摩托的钱都是和三鬼借的。
就这样刘军也加入了跑出租的大军,这行道果然挣钱,两个轱辘一转,家里一天的花销都有了。
还是有酒有肉的美日子。
跑出租挣的是活钱,老婆长八只眼也看不住。
两个人那时都偷偷摸摸地背着媳妇攒私房钱,想着挣够钱,买辆夏利汽车,当个体面的出租车司机。
他们商量好了,这笔钱谁买车谁先拿去用。
谁知后来煤矿整合,小煤窑被封,外地的煤老板拿着钱到别处去发财,窑里的工人东奔西走也散了。
跑出租的收入一天比一天少,买汽车当然成了没影儿的事。
青矿离城里近,三鬼就盘算着进城跑出租。
城里人多,打车人也多,挣得不会少。
刘军不能走,他有工作牵挂着走不开,留在矿上挣一个算一个。
三鬼可能正在跑出租的路上,刘军听到手机里传来汽车按喇叭的声音就说,三儿,小心点儿,别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
三鬼说,屁事没有。
电话里一个女人说,师傅到了,就在前边的那个路口停下。
然后是女人的高跟鞋声,咯噔咯噔越走越远。
你猜我刚才挣了多少钱?
三鬼拿腔捉调地问。
三块?
五块?
刘军猜不出。
十块呀,还不到五公里的路程,他妈的比开出租车都挣钱。
三鬼兴奋地叫。
刘军的心被十块钱的小火烤着。
三鬼唠唠叨叨,城里修路的时候摩的生意特别好,一天少说也能挣一张。
摩的方便,出租车过不去的小土道小窄巷子,摩托车“嗖”地就穿过去。
干咱这一行没有本钱,摩托车是现成的,除了油钱,挣多少往兜里装多少。
你不知道现在摩的的行情涨了,摩托和出租车一个价儿,都是六块钱起步。
不瞒你说,那些开出租车的眼红死咱,他们一天还有公司的两百块份子钱。
咱是干捏,一点儿水分都没有。
只要人机灵点儿,这一夏天的少说也能挣一股。
一股就是一万。
一万块钱就像一个亮堂堂的火把,把刘军皱巴巴的生活照得一片灿烂。
3
女人进卫生间冲完凉,穿着一件低胸的吊带睡裙出来。
男人慌忙低下头,两手攥成拳头,一双眼睛不知该朝哪儿看。
女人的脚很白,是那种没有血色滋润的苍白。
女人大大方方地说,大哥,你也进去冲冲吧。
大热的天,一动弹一身汗。
男人悄悄溜了一眼女人,头发湿湿地搭在肩上,后背上洇出一团水渍,衣服完全贴在肉上。
圆润的肩头耸动着,像一只淘气的猫。
男人急急慌慌地进去,五分钟后腰上裹着一条浴巾跑出来。
男人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脸上有些挂不住,心想自己这个急吼吼的样子像电视里那些不要脸的老嫖客。
女人擦干头发已经上床,手里夹一根烟,倚着枕头看电视。
女人没烟瘾,瞎抽,做她们这行的必须在男人们面前端出一副老辣的风尘样儿。
男人们都喜欢浪一点儿的女人,要是找贤妻良母,自个家里就有,何必舍近求远劳民伤财。
黑夜里站在影影绰绰的灯光背后,冲着走过来的男人轻飘飘地抛出几个烟圈,那简直就是抛出一个个红绣球。
被绣球砸着的男人晕头转向,骨头又酥又麻,站都站不稳。
再说隔着烟雾,看眼前的男人老少丑俊、高矮胖瘦都是一样的。
电视里的男人抱着女人啃来啃去。
男人受了刺激,也爬到床上,女人把抽了半截的烟摁进烟灰缸,从包里摸出一个小东西扔给他。
白色的小东西翻着跟头落在床边,男人从上到下红到脚趾头,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没病!
我一点儿病也没有,身子好着呢!
真的,我没病。
女人两个指头把搭在眼前的一绺头发撩到耳根后说,你不怕,我怕,染上病对谁都是麻烦。
男人只好接过那个小东西,转过身背着女人,窸窸窣窣好一阵忙活,女人手伸过去要帮他,男人手脚更乱。
女人轻声笑,说他的样子像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
男人自嘲,啥毛头小子?
老枪老炮的,子弹都生锈了。
他故意这样说,好给自己加点儿胆量。
说实话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怕。
尽管工友们私下都说,男人一辈子守着一个女人,活得还不如一只鸡。
4
接完三鬼的电话,刘军自己也琢磨进城的事。
矿上跑出租现在根本挣不着几个钱,狼多肉少。
矿上女人舍不得打车,她们出门子拎多少东西,也伸出两只手自己提着。
这两年汽油钱涨了,打车钱没涨,从汽车站跑到家属区还是两块,辛辛苦苦一天下来也就挣个青菜钱。
刘军人勤快,不赌,不嫖,除了抽根烟喝点儿酒没有不良的嗜好。
老婆荷珍又会过日子,一分钱也不胡乱花。
那小日子就像是一瓶廉价的二锅头,一小口一小口抿着抿着慢慢就醉了。
谁知去年冬荷珍查出病来,癌症,这个病比狮子的嘴还大,去了两次北京就把刘军的家底全掏空了。
那些钱女人攒着,本来是准备进城买套两室一厅的楼房。
现在别说楼,连个厕所也买不起。
荷珍不是矿上的正式工人,没有办医疗保险,所有的手术费用都是自费。
第三次去北京住院还落下两万多的外债。
钱都是和工友们借的,虽说人家不上门讨要,可刘军心里过意不去。
青矿是破产矿,工人的工资都不高,谁家也没有几个闲钱空搁着,一个萝卜一个坑,那钱早安排了用项。
出了院女人在家还要吃药维持,那种药不便宜,都是上百块一瓶。
越渴越舔盐,孩子又升了初中,学校里书钱补课钱天天不断。
旧账没清,新债又加,每天天亮一睁眼,不知道会从哪个地方就跑出要钱的事由。
愁得刘军吃不香睡不香,挣着有数的这几个死工资啥时候才能把该人家的钱还上?
刘军的心被油煎得吱吱冒烟。
吃晚饭的时候刘军和荷珍商量说要进城跑一段时间的出租,青矿离城也就十五六里路,白天跑出租,晚上回来上夜班,两不耽误。
荷珍的气色很差,刘军自觉理亏,他应该留在家里多照顾女人些日子。
好在女人明理,没说拉后腿的话。
只是问,一夏天能挣多少?
两万多吧。
刘军怕女人后悔,故意多说了点儿。
刘军相信自己勤快些能挣到这个数。
跑出租这活儿,说白了也就挣个辛苦钱,只要眼里有活儿,多跑几趟就多挣几个。
城里人懒,不爱走路,出门就喜欢招手叫车。
吃过饭孩子去写作业,女人把桌上的碗摞在一起,刘军跟在后面把空盘子送进厨房。
他抄起瓶子往碗里倒点儿洗洁净,打开水龙头拿洗碗布洗碗,洗洁净倒多了,白泡泡沾弄了两手。
女人笑着,笨手笨脚的,放下放下,还是我洗吧。
刘军让她出去休息,女人不走,倚在厨房的门框边慢悠悠地说,要是真像三鬼讲的那样,该人家的钱也能还上一些。
一提借的那些钱,荷珍比刘军还着急上火。
刘军让她别操心钱,钱的事他会想办法。
他是家里的男人,自然会想出办法来。
要是发愁能愁出钱来,那咱们啥事也别干,都坐在家里愁钱呗。
刘军一发火,女人讪讪地不再说话,慢慢眼泪也流下来,抽抽咽咽地边哭边说,我知道这个病是不会好了,这辈子是我害了你,也拖累了这个家。
刘军嘴笨,不会讲哄女人的甜言蜜语,可他心里记着女人的好。
自家的女人真是个好女人,要是他能像那些有本事的男人挣来大钱,女人也不会累下病。
他知道女人的病生生是累的。
他出工伤那年,家里家外都是女人一个人撑着。
女人早上五点就去小饭店给人家洗碗,一个月才给二百块。
就这点儿鬼舔钱,饭店的老板还说,人要讲良心,拿人家的钱,就要尽心尽力干活。
除了饭店,女人还在单身楼做着一份打扫卫生的活儿。
给住单身的工人洗衣服,一件衣服五毛钱。
女人的手整天泡在冷水里,手指头肿得就像红萝卜。
刘军心疼地看一眼女人,嘱咐她记着吃药,别瞎想。
做完两次化疗,女人瘦成了一个干巴枣核。
当初荷珍嫁给刘军的时候,可是一颗人见人爱汁水鲜美的桃子。
那会儿刘军是矿上的劳模,胸前戴着碗大的红花,人五人六地坐在主席台念别人给他写好的先进事迹报告。
会议厅里,四五个穿红旗袍的漂亮女孩子隔一会儿就给杯子里续满水。
刘军的眼睛瞅着报告,心思早跑到穿红旗袍的女孩子身上。
那些女孩子真漂亮,只是大冬天穿着露腿子的裙子,刘军心疼得舍不得,所以人家倒一杯,他喝一杯。
刘军就那一会儿工夫喝了五杯水,报告念到一半时,膀胱胀成一个大气球。
刘军捂着肚子,弯着腰苦着脸的样,可把队长气坏了。
真是一个扶不上台的刘阿斗。
后来刘军还真从矿上的招待所找了一个穿红旗袍的姑娘。
那姑娘就是荷珍,她也是矿工子弟,在招待所当临时工。
矿上有招待活动时,她们就穿戴起来当招待员,没活动了当打扫卫生的清洁员。
刘军小心眼,一结婚便不让女人去招待所上班了。
这么好看的女人,自己惦记着,防不住哪个领导背地里也惦记。
刘军进城和三鬼在小饭店喝了一顿酒,便把跑出租的事定下来。
荷珍心疼他的身子,说要不跑一天休一天吧。
刘军不同意,做啥都有回头客,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慢慢就丢了客人。
女人低头想想又说,平日里你和队长关系好,不行和他说说到矿上请个长期事假。
刘军有点儿心烦,请假更是没边儿的事,回头再把工作折腾丢了,以后全家三口人张大嘴全喝西北风去。
刘军端起杯喝口酒,把毛毛糙糙的心思压住。
刘军知道女人疼他,只好给她讲宽心话,也就几个月的事,天一冷,路修好啦,傻子还打摩的。
城里人最会活,人家还怕冻掉屁股蛋子呢。
你这样想,辛苦几个月就能挣一大笔钱,绝对值!
有了这笔钱,咱们该人家的钱就还清了。
以后清清爽爽地过日子,这是多好的事。
荷珍给他搛了一大筷子肉。
5
女人伸手抹下两根细带子,胸前两个圆圆的小皮球“呼”地跳出来。
男人眼直勾勾地,不知是该把皮球抱在手里,还是拍一拍让它们跳得更欢实些。
女人抿着嘴一笑,拉着男人平平地躺下来,两个人脸对脸默默地对看一眼,都没说话,男人的手忍不住先动起来,像一只觅食的小老鼠,躲躲闪闪地藏在黑处。
女人柔成一缕风,丝丝缕缕缠在男人的身上。
不一会儿饥饿的老鼠又变成一条动作麻利的蛇,女人瘦削的肩一起一伏耸动着,头最大限度地向后仰在枕头上,黑黑的发丝全掩在女人的脸上。
6
李春一只手摸着陈果的脸,一只手剥她乳罩后的扣儿。
扣儿滑滑的好几次都从他的手上溜走,有一丝丝慌乱在他心里闪来闪去。
李春用脚把陈果的裤头蹬下去,把女人抱在他的腿上。
陈果圆圆的膝盖头抵着他的腰窝,贴心贴肺地舒心,李春搂着女人细细的腰肢猛然出击。
女人身子抖一下,再抖一下,仰起脸,眼神迷离,春色满面……
陈果枕着男人的胳膊像孩子一样恋着他,她不愿让他走,他一走,这个屋子就空落落的。
眼看着到了上班的时间,李春有点儿烦躁,边抽胳膊边说,女人家就是啰唆,又不是出远门子走的日子长,不就是上班嘛,晚上就回来呗。
李春亲了陈果一下,陈果手里抓着李春的红裤头可怜巴巴地求他,今天就不要去了,请个假,我觉得不好,怕有啥事。
李春坚决地坐起来开始穿衣服,没事,有事也是好事,要发工资了。
这个月发安全奖,五百块,够你冬天买件羽绒衣穿。
就买“波司登”这个牌子的,名气大,质量好。
买件大红的,红颜色穿着年轻。
今年二十八,明年你就活成十八。
李春故意扭着屁股穿裤子,陈果被逗笑了,李春耸动着喉结让自己也大声笑,这些欢快的笑声,飘在屋子的角落里,陈果白天走到哪儿都能听到。
才四点半,外面天还黑着。
李春不让陈果起来给他做早饭,一个人的饭好弄。
他自己把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剩饭在煤气灶上热热,也不摆桌子端着碗站在厨房的地上吃,菜里面没有肉,又是剩的,一点儿也不合口。
嘴馋啦,想吃点儿好的。
你倒是会想。
老婆,咱晚上喝个鱼汤吧!
行,冰箱里还有两条带鱼,晚上我给你煎上。
不想吃,要吃就吃活鱼,活蹦乱跳的活鱼,死鱼味太腥。
倒是会吃,你知道今年活鱼多少钱一斤?
多少钱?
未必比房子还贵。
七块,比猪肉还贵两块。
咱家又不是天天吃鱼。
吃五谷想六味的,不买房了?
你看你,不就是吃条鱼嘛,一条鱼能把人吃穷?
你算算,一条鱼就是一块楼砖。
喝口鱼汤再吃肉,鲜死个人。
李春响亮地吞了一口唾沫。
其实陈果也觉得最近的饭菜素了点儿,李春受的苦重,不能亏他的身子。
可她还是故意这样说。
陈果心里也有一点点委屈,她已经好久没买新衣服了。
一个女人不能买喜欢的新衣服,心里总是有些失落。
李春和陈果有孩子后一直为城里的楼房艰苦地奋斗着。
他们决心要让孩子上城里的学校,受城里的教育。
为了买房,已经调到场面工作的李春,又写申请调到井下一线。
一线挣得多,一个月有二百块的入坑费,还有各种奖金。
陈果知道李春最怕下井,他曾经和她说过,他是最怕死的人,李春的爹就死在一场瓦斯事故中。
吃过饭李春把碗放进水池子里泡上,一会儿陈果起来洗碗的时候好洗。
李春和陈果结婚的时候就提了一个要求,不洗碗,别的啥营生都行。
我妈说过,一个大男人娶了老婆还扒锅边,一辈子都没出息。
陈果当时因为这句话还耍了小脾气,不过结婚后真没让他干过洗碗刷锅的碎活儿。
临走,李春上了一趟厕所,看到厕所没手纸了,提醒陈果记得放手纸。
陈果趴在被窝里懒洋洋地说,甩手掌柜,一天到晚就会支嘴,手纸就在厕所旁边的小柜子里,你顺手放一放不就行了。
李春哦了一声,开柜子门声,关柜子声,扯开塑料包装声,接着听到李春的穿鞋声,拿钥匙开门声。
让人好笑的是李春还从外面打了保险。
家属区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案子,男人上班走后,另一个男人乘机摸进来,女人还以为是自家男人返回来心疼自己,哼哼叽叽就把那事办了。
7
一群小蚂蚁从男人的骨头缝里游出来,张着触角四处寻找着食物。
男人不怀好意地从下面抽走了枕头,女人微微张着嘴巴,头用力顶着床头,身子拼命地摆动着挣扎着,如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兽。
莫名其妙的水滴声,就是在这时跑出来的。
就像寂静的雨夜里水敲在青瓦檐上的声音,那清冷的水声穿墙过屋久久不绝地缠在男人耳边。
男人已经很久没尝过女人的好,小肚子硬硬地绷成一面战鼓,就等东风吹,战鼓擂。
可是裆里的那玩意儿不争气,任凭他怎么努力就是不来劲。
他心里着急,暗暗责怪那个水声,那个水声总是干扰他不能一心一意地做事。
男人张嘴轻轻咬住女人耳环上的那颗小米珠,想让自己的精神集中一点儿。
8
才几天的工夫,同泉路就像是遭到了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破路机嘎嘎地怪叫着不停地把一根尖尖的铁棍子插进路面,刚才还平平的路面一下子就被扯得翻肠破肚。
为了方便客人用车,三鬼他们把摩托停到凤凰小区对面的显眼路段。
小区里的人只要一出来就能看到。
三鬼的汽车一直没买成。
虽然进城的这几年也挣了几个钱,可车一年比一年贵,他手里的那点儿钱连个出租手续都买不下来。
三鬼也就彻底死了心,不买汽车,就跑黑车,见了警察能跑就跑呗。
跑不掉罚上几个钱,罚完跑得更勤快。
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怎么也得活下去,不跑黑车又怎么能把被警察罚掉的钱捞回来。
凤凰小区算是城里的一处高档小区,小区里的随便一套房子也值一百多万,听说还要往上涨。
刘军心想,涨不涨价和他也没关系,就他那点儿工资,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房。
也不知城里人的钱从哪儿冒出来,是不是半夜里天上老悄悄地掉金馅饼给他们?
凤凰小区里面是啥样,刘军从来没进去过,门口有穿制服的保安把门,小区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
从外头看小区,的确是气派,修着假山、喷泉、小桥、休息用的亭阁,还有很多漂亮的叫不上名儿的花花草草。
听司机们说园子里随便一棵景观树就值好几万块钱。
那个被外国人烧掉的圆明园也不过这样吧!
刘军没有去过圆明园,带女人去北京看病,光待在医院里发愁了。
小区里平时车来车往的,现在一下子断了路,那些有钱人根本走不了这坑坑洼洼的路。
特别是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们要出门时,就站在小区石狮子的旁边,朝着对面马路喊,二轮,二轮。
刘军开始不明白啥意思,问三鬼,啥叫二轮?
三鬼低声骂,操,有钱人就是会起名字,啥是二轮?
咱不就是二轮吗。
刘军细一想就笑了,摩托车可不都是两个轮子。
四个轮子的那是汽车。
小区里的人果然个个都是有钱的主,打车找回的零钱说不要就不要了。
刘军开始不习惯,总要追着把零钱还给人家,要不就觉得平白无故占了别人的便宜。
三鬼骂他木头脑袋,有钱人根本不在乎这几块钱。
人家的房子光装修就要十几万,还是简装,要是精装,那就是几十万的事。
这么有钱的人,谁会在乎这点儿钱。
可不管三鬼怎么说,刘军心里特别不舒服,有点叫花子被施舍的感觉。
没活儿时,司机们凑在一起说闲话,三鬼瞅着门口的那对儿大狮子说,进去随便偷一家就够咱们这样的人家活几年的。
偷?
笑话,这里面你能随随便便进去?
就是混进去了,听说里面还有监控录像,人走到哪儿都能拍下影儿来。
你前头进去偷,后面警察就来抓人。
同泉路越来越难走,杏黄色的挖掘机举着长臂挖出一条又一条深沟。
工人们在沟里忙忙碌碌地铺着各种管道。
人们早上出门时还有路,晚上回来那条临时小土路已经改道。
摩托车不可能像出租车那样满大街地跑着拉客,费油,也怕栽到警察手里。
干这行磨的就是时间,有活儿就拉,没活儿歇驴。
司机们都把休息说成是歇驴。
刘军等客人时就看挖掘机怎么干活,那么大的家伙,几下就挖开一道沟。
三鬼在旁边拍拍裆里的玩意儿,说那个铁家伙比人的肉家伙厉害多了。
以前在井下干活工人们常开这样的玩笑,打眼工抱着打眼机,一口一个女人咋样,咋样。
现在进了城里,听着这话刘军就觉得耳朵有些发烧,生怕被过路的人听见。
路不平,为了安全,刘军总要嘱咐坐车人扶牢点儿。
有的女人抓住摩托后面的衣架,有的女人直接伸胳膊搂着司机的腰。
每当这时刘军就有点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心跳起码加快两倍。
风把女人的头发丝,香水味送到刘军的鼻子里,刘军心里爬满了小虫子。
那些虫子啃着,咬着,刘军疼着,难受着。
刘军想女人想得厉害。
自家女人得的是子宫癌,听大夫的话为了保命把子宫全切除了。
他已经很久没和女人那个过。
有时候难受得不行,只好用手自己快活一下。
三鬼也劝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又不是黄花大姑娘要守个清白身子。
守什么守?
男人的东西和摩托车的电瓶一样,老不充电,慢慢就报废了。
要不哥带你去火车站附近找个干净点儿的女人下下火。
刘军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三鬼骂,别看不起那些女人,我觉得比那些贪污犯强多了,最起码人家靠身子挣血汗钱,干干净净。
三鬼变了,以前和女人说个话都脸红,现在一看到火车站那些站街的女人眼神就黏黏糊糊的。
三鬼讲这些没正经的话,刘军就借口要上厕所。
拉开裤子,站在便池边,只尿出细细的一小股。
娇气的小和尚一碰到亮光,总要激灵灵打个冷战,本来瘦小的身子缩得更加干瘪。
它委屈的样子让他心疼。
刘军伸出手像抓一只垂死的鸟一样把它握在手里,鸟头从手指的前端探出来,哀哀地看着他。
他帮不了它,就像帮不了他吃苦受累的命。
记得爹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人再硬也硬不过个命。
这话他信,自己现在不就是被命牵着走吗。
三十如狼四十似虎,四十出头的刘军虽然不是虎狼之徒,可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男人,是男人就想床上的那点儿花花事。
这事说出来不光彩,可明事暗做,背地里哪个人也不是坐怀不乱的君子。
近来他老是梦见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都长着花朵一样的脸。
不知是不是应了三鬼的话,刘军发现自己的家伙真有问题,老是那么蔫头耷脑的没精神。
刘军拉上裤拉链时胡乱寻思得吃几个猪腰子补补,最好是腰花炒韭菜,壮壮阳。
男人们私下都传韭菜是还阳草。
9
男人的骨架大,女人瘦,硌得身子一阵阵疼。
不过女人硬撑出一个客人喜欢的笑浮在脸上。
这路也不知要修到啥时候?
女人没话找话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快了!
快了!
男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