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docx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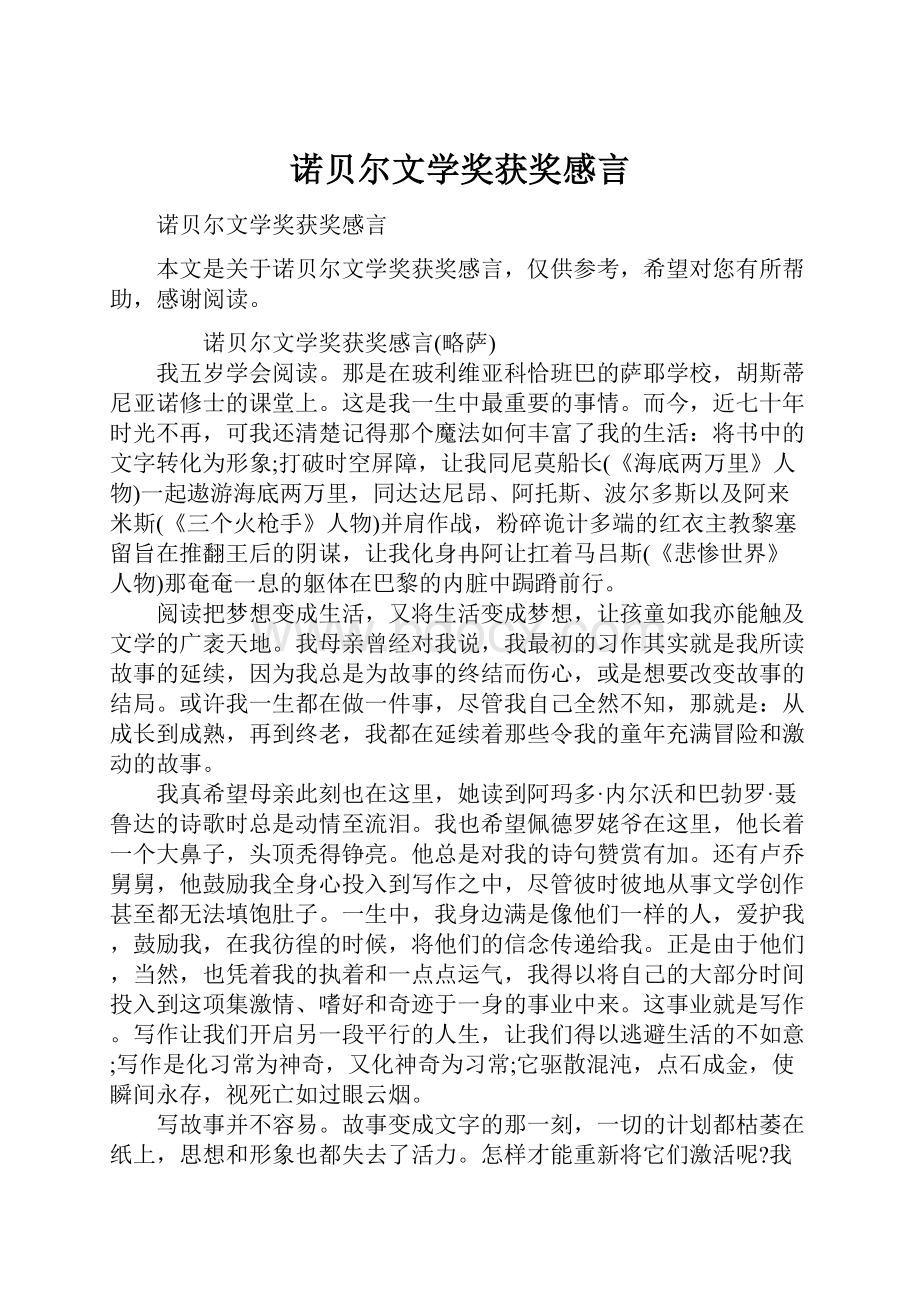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
本文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略萨)
我五岁学会阅读。
那是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萨耶学校,胡斯蒂尼亚诺修士的课堂上。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而今,近七十年时光不再,可我还清楚记得那个魔法如何丰富了我的生活:
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形象;打破时空屏障,让我同尼莫船长(《海底两万里》人物)一起遨游海底两万里,同达达尼昂、阿托斯、波尔多斯以及阿来米斯(《三个火枪手》人物)并肩作战,粉碎诡计多端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旨在推翻王后的阴谋,让我化身冉阿让扛着马吕斯(《悲惨世界》人物)那奄奄一息的躯体在巴黎的内脏中跼蹐前行。
阅读把梦想变成生活,又将生活变成梦想,让孩童如我亦能触及文学的广袤天地。
我母亲曾经对我说,我最初的习作其实就是我所读故事的延续,因为我总是为故事的终结而伤心,或是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
或许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尽管我自己全然不知,那就是:
从成长到成熟,再到终老,我都在延续着那些令我的童年充满冒险和激动的故事。
我真希望母亲此刻也在这里,她读到阿玛多·内尔沃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时总是动情至流泪。
我也希望佩德罗姥爷在这里,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头顶秃得铮亮。
他总是对我的诗句赞赏有加。
还有卢乔舅舅,他鼓励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尽管彼时彼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都无法填饱肚子。
一生中,我身边满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爱护我,鼓励我,在我彷徨的时候,将他们的信念传递给我。
正是由于他们,当然,也凭着我的执着和一点点运气,我得以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项集激情、嗜好和奇迹于一身的事业中来。
这事业就是写作。
写作让我们开启另一段平行的人生,让我们得以逃避生活的不如意;写作是化习常为神奇,又化神奇为习常;它驱散混沌,点石成金,使瞬间永存,视死亡如过眼云烟。
写故事并不容易。
故事变成文字的那一刻,一切的计划都枯萎在纸上,思想和形象也都失去了活力。
怎样才能重新将它们激活呢?
我们很幸运,大师们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遵从他们的榜样。
福楼拜告诉我,天赋即持之以恒和铁的纪律。
福克纳告诉我,形式,即文字和结构,可以加强也可以弱化主题。
马托雷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托马斯·曼告诉我,在小说中,视野和雄心同文体技巧和叙述策略一样重要。
萨特告诉我,话语即行动,一部介入当下、寻求更好选择的小说、戏剧或散文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加缪和奥威尔告诉我,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
马尔罗告诉我,英雄主义与史诗,适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时代,同样也适用于当今时代。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
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
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
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
我有时也扪心自问,在我们那样的国度里,写作是不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奢侈。
毕竟那里读者稀缺,穷人和文盲充斥,不公正所在皆是,文化则是少数人的特权。
但这种迟疑从未令我的热情窒息,相反,我一直笔耕不辍,即便是在为温饱而奔波几乎占据全部时间的那些岁月里亦是如此。
我相信我做对了,因为如果文学之花只能绽放在高度文化发达且自由、昌盛、公正的社会里,那么它断不会出现。
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
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
一如写作,阅读也是对生活之匮乏的一种抗议。
在虚构中寻找弥补阙如的人一定会说——其实何须言之,何须意识到这一点——此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远不足以满足我们对终极理想——人类生存之根本——的渴望,生活本该更加美好才对。
我们之所以创造了虚构,正是为了在某种意义上体会到我们渴望拥有的那许多别样的生活,因为往往我们甚至连其中之一种也无法完整拥有。
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将很难意识到能够让生活得以维持的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也很难意识到,生活被暴君、被意识形态、被宗教践踏而变成了地狱。
如果有谁不相信文学除了能够让我们置身美丽和幸福的梦想,还能警告我们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那么就请他问问自己,为何所有企图从襁褓到坟墓完全控制住公民的政权都如此惧怕文学,为何他们都要建立审查制度去压制文学,心存狐疑地监督独立作家的一举一动。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任由想象在书中自由驰骋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读者将使虚构成为可能的自由、在虚构中实践着的自由,与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蒙昧与惧怕作一比较,虚构就会激发人的反叛情绪。
不管其本意如何,也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在编织故事的同时也宣扬了不满。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是糟糕的,幻想中的生活远比日常的生活更为多姿多彩。
倘若这种思想扎根于民众的意识,民众就会变得难以操纵,难以让他们再相信生活在棍棒、检察官和狱卒中间更安全,更舒适的谎言。
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
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
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宁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城市通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
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恐惧,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惧则来自那些狂热分子,那些制造自杀性袭击的恐怖主义者。
他们抱着陈腐的观点,认为杀戮可以换来天堂,无辜人的鲜血可以洗清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将真理强加到错误的信仰之上。
每天,世界的不同角落都有无数无辜的生命被那些自认为掌握着绝对真理的人当做祭品。
我们曾一度相信,随着那些极权帝国的瓦解,共存、和平、多元、人权就会确立,世界将不会再有大屠杀、种族灭绝、侵略和毁灭性战争。
但事与愿违。
新的野蛮形式被狂热分子不断繁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日俱增,有朝一日任何一个以救赎者自居的狂热团体都有可能制造一场核灾难。
我们必须挺身而出,直面他们,击溃他们。
尽管他们的罪行每每令世界震惊,令我们惊恐以至于噩梦连连,但他们为数不多,我们决不能被他们吓倒,正是这些人夺走了我们漫长的文明征程中千辛万苦得来的自由。
我们要捍卫自由民主,尽管它有种种局限,但毕竟意味着政治多元、共存、宽容、人权、言论自由、法制、自由选举和轮流执政等,正是这一切使得我们脱离野蛮生活,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尽管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文学所虚构的完美生活。
那种美好的生活,我们唯有通过想象、描写和阅读,才能过上一遭。
我们必须直面那些狂热的杀人犯,必须捍卫我们梦想的权利,捍卫将我们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权利。
正如许多同代作家,我年轻时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曾相信社会主义是消除剥削和社会不公的途径,当时这二者在我们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愈演愈烈。
(疑似删节处)我对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的失望以及转向民主和自由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
(疑似删节处)民主和自由是我现在所努力追求的,我的转变最终得以完成是由于一系列事件。
更多亏了像雷蒙·阿隆(法国思想家1905-1983)、让·弗朗斯瓦·勒韦尔(法国学者1924-)、以赛亚·柏林,卡尔·波普尔(奥地利学者,1902-1086)等思想家,是他们让我重新评价民主文化和开放社会。
从小我就迷恋璀璨的法国文学,梦想有一天能够到巴黎去。
我相信只要住在那里,呼吸着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曾经呼吸过的空气,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相反,如果不能走出秘鲁,我将只是一个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写写东西的伪劣写手。
事实上,我很感激法国及其文化,是法国和法国的文化给了我难以忘怀的哺育,使我懂得了文学不仅是一种热忱,还是一项纪律,一个工作,一种执着。
我在法国居住时,萨特和加缪还健在并笔耕不辍。
那是尤奈斯库、贝克特、巴塔耶、齐奥朗(罗马尼亚旅法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和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的时代。
那个时代,我发现了上演布莱希特作品的剧院,放映英格玛·伯格曼(瑞典导演)作品的影院,演出让·维拉(法国戏剧家)作品的国立大众剧院,还有上演让·路易·巴罗作品的音乐厅。
那个时代,我听新浪潮音乐;读新小说;听安德烈·马尔罗的演讲,那是最美的文学篇章;亲睹了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和他的雷霆万钧,那或许也是当时欧洲最具戏剧性的场面。
不过,或许我最应该感谢法国的是,在那里我发现了拉丁美洲。
正是在法国,我认识到秘鲁是这个广阔美洲的组织部分。
共同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社会问题,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别有韵味的共同言说和写作的语言,将这个群体像兄弟姐妹一般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那个年代,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文学应运而生。
也正是在法国,我阅读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墨西哥作家)、卡夫雷拉·因方特(古巴作家)、鲁尔福(墨西哥作家)、奥内蒂(乌拉圭作家)、卡彭铁尔(古巴作家)、爱德华斯(古巴作家)、多诺索(智力作家)以及其他众多拉美作家的作品。
他们的创作为西班牙语小说带来了新意。
正是由于他们,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得以发现,拉丁美洲这个大陆并非只有政变、骇人听闻的军事独裁、胡子拉碴的游击队员、曼波舞的沙铃和恰恰恰,而且还有各种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想象,它们超越了光怪陆离的现实场景,说着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拉丁美洲都在不断进步,尽管不乏磕绊,尽管正如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所说,“兄弟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除却古巴,还有它的准接班者委内瑞拉,以及一些实行虚假的、闹剧式的民粹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如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不管怎样,拉美国家都实行了基于广泛民意的民主政治,并且在巴西、智利、乌拉圭、秘鲁、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以及几乎整个中美洲,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尊重法制、言论自由、选举和轮流执政的左派和右派。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如果能够坚持走下去,坚持和阴险的进行战斗,继续融入世界,拉丁美洲将不再只是未来的大陆,同时也属于现在。
在欧洲,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说实话,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异质感。
在所有我居住过的地方,巴黎,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柏林,华盛顿,纽约,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我都觉得像在自己家里。
我总能找到安身之地,安静地生活,工作,学习,幻想,交友,并且读到好作品,找到好题材。
虽然我并非有意为之,但我并不认为做一个世界公民就意味着削弱所谓的“根”,也即我同祖国的联系——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倘使果真如此,我的秘鲁经历就不会始终滋养我的创作,不会总是出现在我的故事中了,尽管这些故事看上去似乎离秘鲁很遥远。
恰恰相反,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久居故土之外,我和祖国的联系反而更加坚固了。
久居国外,我对这种联系看得更清楚,同时还多了一份乡思。
这种情感能够让我分清本末,并使回忆永存。
爱是不能勉强的,一个人对祖国的爱亦是如此。
这是一种从心田自然萌发的情感,犹如爱人、亲子、挚友之情。
秘鲁存在于我的五脏六腑,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在那里,我接受教育,度过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形成我的个性,锻造我的使命;在那里,我爱过,恨过,开心过,痛苦过,梦想过。
比起其他地方,那里发生的一切对我影响最深,令我感动最甚,自然也最让我难以释怀。
这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自然而然。
一些同胞说我背叛了祖国。
的确,我曾经差点儿丢了秘鲁国籍。
那是最后一个独裁统治时期,我曾请求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制裁这个独裁政权。
这也是我对所有独裁统治所持的一贯态度。
如果秘鲁再次发生政变,致使我们脆弱的民主遭到破坏——当然,这是历史不能允许的,是秘鲁人民不能答应的——那么我会再一次这样做。
这不是那些惯于从自己狭隘心理判断他人的评论家们所说的愤懑者的一时冲动,而是信念使然。
我坚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独裁是大恶,是暴政和的源头,是久难愈合的重创,会毒害国家的未来,滋生恶习,而这样的恶习将长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延误民主的重建。
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和独裁进行斗争,使用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
遗憾的是,各民主政府,非但没有树立榜样,支持那些敢于直面独裁的人,反而常常取悦于迫害他们的人。
那些勇士是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同时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
我的一位同胞何塞·玛利亚·阿尔戈达斯称秘鲁是一个“混血”的国家。
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秘鲁人,我们骨子里就是这个样子,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传统、种族、信仰和文化。
我很自豪,自己是这样一些文明的后人:
西班牙征服前的纳斯卡和帕拉加斯文化,它们会用羽毛编织衣物和披肩;莫奇卡和印加的制陶之人;奇穆文化;昌昌文化;库埃拉普遗址;西潘王墓;埃尔布鲁约遗址、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还有西班牙人,他们背着褡裢,佩着长剑,骑着马,为秘鲁带来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塞万提斯、克维多、贡戈拉、还有粗粝的卡斯蒂利亚语——安第斯山的人民使它柔和了许多;随之而来的非洲人带来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音乐,还有他们富有激情的想象力,从而丰富了秘鲁的多元和混杂。
如果再深究一步,我们会发现,正如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秘鲁是整个世界的微缩。
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特质,因为她有的是全世界的特质,这是何等的得天独厚!
诚然,美洲的征服是残忍的、暴力的,如同所有的征服一样,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批判。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犯下那些掠夺罪行的,大部分是我们的曾祖父、高祖父,是那些到达美洲并在那里繁衍生息的西班牙人,而非留在西班牙本土的西班牙人。
若要公正,这一批判应是自我批判。
因为,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后的两百年间,在那片旧殖民地上执掌政权的统治者们非但没有解救印第安人,为他们曾经遭受的主持正义,反而继续像征服者那样贪婪而凶残地压榨他们。
有些国家甚至对他们进行屠杀和灭绝。
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些:
两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的解放一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们至今尚未履行。
这个责任在整个拉丁美洲仍然悬而未决。
这一耻辱和羞愧我们概莫能外,每个人都有份。
我像热爱秘鲁一样热爱西班牙。
我对她的亏欠和对她的感激同样巨大。
如果没有西班牙,我永远也不可能站在这个演讲台上,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知名作家,却很可能像许许多多不幸的同行那样,混迹在那些缺乏运气的作家群中;他们没有出版人,没有奖项,没有读者,他们的天赋或许有一天会被后人发现,但那也只是一个凄凉的安慰。
西班牙出版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得到了夸张的认可。
我的朋友,如卡洛斯·巴拉尔、卡门·巴尔塞斯(略萨出版人和经纪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让我的故事拥有读者,他们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
就在我可能失去国籍的那个时候,西班牙授予了我第二国籍。
身为秘鲁人,同时拥有西班牙护照,对此我从未感到过一丝一毫的矛盾,因为我一直认为西班牙和秘鲁是硬币的正反两面,无论是对于我这个渺小的个体,还是对于历史、语言和文化这些本质的现实,都是如此。
我居住在西班牙土地上的那些岁月里,七十年代初在可爱的巴塞罗那度过的五年时光可谓历历在目。
那时,佛朗哥独裁政权尚存,枪杀还在继续,但已是强弩之末,尤其是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已经难以为继。
书报审查制度已经无法填堵不断出现的裂缝和空隙,西班牙社会开始吸收新的观点、书籍、思潮、艺术价值和形式,而这些在之前都会因其颠覆性而遭到禁止的。
开放之初,没有一个城市像巴塞罗那那样紧紧把握机会,对一切思想和创作都满怀激情。
那里变成了西班牙的文化首都,变成了一个可以率先呼吸到未来自由气息的地方。
在一定意义上,那里也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首都。
大批来自拉美各国的画家、作家、出版人、艺术家都聚居在那里,或者进进出出。
谁要是想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小说家、画家、作曲家,就应该待在那里。
对我来说,那些岁月是难以忘怀的,是同志之情、友情、共同谋划事业、智识成果大丰收的时代。
和以前的巴黎一样,那时的巴塞罗那也是一座巴别塔,是世界主义的、包罗万象的大都市。
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是激动人心的;在那里,内战以来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作家首次相聚在一起,结成兄弟,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传统的主人,在一个共同的事业和信念中结成联盟,那就是:
独裁即将灭亡;在一个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将成为主角。
虽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西班牙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却是现代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它验证了这样一个奇迹:
理智与理性占据上风,敌对的政治力量为了顾全大局而停歇纷争,发生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奇迹。
西班牙由极权到自由,又落后到繁荣,从一个充斥着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第三世界国家擢升为一个由中产阶级主导的中等国家,并在短时间内融入了欧洲,采用了民主文化。
这一切都令整个世界赞赏,加速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
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一切,甚至置身其中,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激动人心并且深受其益的经历。
但愿那些民族主义者不要破坏这段幸福的历史,毕竟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也是西班牙难以治愈的创伤。
我憎恶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狭隘的、短视的、排他的意识形态——或曰宗教,它缩小了心智视野,孕育着种族偏见,将偶然的出生地环境转化为至高无上的价值、道德乃至本体论的特权。
民族主义和宗教一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大屠杀,如两次世界大战,当前血腥的中东战争,等等。
正是拜民族主义所赐,拉丁美洲变成了又一个巴尔干,被愚蠢的斗争和倾轧弄得腥风血雨、乌烟瘴气,将巨大的资源浪费于购买武器,而不是建造学校、图书馆和医院。
不要将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
前者目光短浅而且排他,是暴力的种子。
而后者却是一种健康的、慷慨的情感,是我们对故土的热爱。
故土有我们的祖先,有我们最初的梦想,有我们熟悉的环境和景物,有我们所爱的人,铭刻着我们赖以抵抗孤独的回忆。
祖国并不只是国旗和国歌,并不只是对那些标志性英雄的绝对颂扬,而是一小块土地、一小群人,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将我们的记忆涂上悲伤的色彩;她还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永远都有那么一个我们可以回归的家。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我出生但从未居住过的阿雷基帕。
那是一座我通过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姨妈、舅舅的回忆和思念逐渐认识的城市,因为就像所有阿雷基帕人一样,我的家族也曾居无定所,却时刻将这座白色的城市带在身边。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沙漠中的皮乌拉城。
那里长满了角豆树,随处可见受苦受累的驴子。
我年轻的时候,皮乌拉人都管这些驴子叫“代足”,这是个多么美丽而又伤感的别称啊!
正是在那里,我初谙世事,发现小孩子原来不是白鹳送来的,而是男女苟且偶合的罪孽造出来的。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圣·米格尔学校和巴列达德斯剧院。
在那里,我第一次目睹自己的一个小作品被搬上舞台。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利马的观花埠(当时我们管那儿叫“快乐街区”)的迭戈——费雷和哥伦布两条街道的拐角。
在那里,我脱下短裤,换上长裤,抽了我人生的第一支烟;在那里,我学会了跳舞,学会谈恋爱,学会向姑娘表白。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纪事报》那布满灰尘、摇摇欲坠的编辑部。
十六岁时,我在编辑部为自己作为记者的第一次试手而彻底未眠。
记者职业则同文学一起,几乎占据了我的一生。
这份职业,如同书本一样,让我得以接触更多东西,得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得以结识三教九流——他们之中有人杰,有好人,也有坏人和恶棍。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
在那里,我认识到秘鲁并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堡垒,并不只是那个我一直受限却又安全生活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大的、古老的、血性的、不平等的国家,任何形式的社会风暴都会使她震颤。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卡魏德(秘鲁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几间狭小的地下室。
在那里,我同几个圣马科斯大学的学生一起筹划世界革命。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自由运动”(秘鲁政党,1987年由略萨创建,1990年略萨代表该党参加总统竞选并输给了藤森)的同志。
我和他们一起,为捍卫民主和自由文化,在炮火、停电和恐怖暗杀中度过了三年时光。
秘鲁对我来说,就是帕特丽西娅,我的那个长着翘鼻子的倔强表妹。
很幸运,我在四十五年前娶到了她。
她至今还忍受着我的疯狂、神经质和暴躁脾气,而这些都是有助于我写作的要素。
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早就成了混乱的漩涡,阿尔瓦罗、冈萨罗、莫尔迦娜也不会出生,更不会有我们的六个孙儿孙女,正是他们延续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悦。
是我的妻子为我操持一切,而且操持得很好。
她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管理经济,让混乱的局面恢复秩序,将记者和一些不速之客搞定,以确保我的时间;她安排会面的行程,打点行李,装箱腾箱。
她慷慨大方,即使她以为是在责备我,实际上是对我作了最高的褒奖:
“马里奥,你唯一的用处就是写作。
”
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
童年的天堂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文学神话,而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实,即我享用的快乐时光。
在科恰班巴,在我家那所拥有三个院落的大宅子里,我和我的表姐妹,还有我的同学,一起演绎着泰山和萨格里的冒险故事;在皮乌拉检察院的阁楼上,蝙蝠筑巢建窝,它们那静悄悄的影子让那片炎热的土地上夜晚的星空充满神秘。
在那些岁月里,写作就好像玩一个全家都会为我喝彩的游戏,我的天赋让我赢得大家的掌声。
在家中,我是外孙,是外甥,是儿子,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死了,去了天堂。
父亲魁梧、英俊,穿着海军制服,他的照片装点着我的床头柜,我对着照片祈祷,每晚睡觉前都要亲吻它。
皮乌拉的一个早晨——我想,至今我还未能从它的伤痛中摆脱出来——母亲告诉我,那位魁梧、英俊的绅士其实还活着。
她说,我们当天就要去利马找他,和他一起生活。
那年,我十一岁。
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
我失去了天真,突然意识到孤独、权威、成人生活和恐惧。
阅读拯救了我,阅读好书佳作,逃到书中世界去。
在那里,生活令人激动,节奏紧凑,冒险一个接着一个;在那里,我自由自在,又找到了幸福的感觉。
同时拯救我的还有写作。
我独自悄悄地写作,就像一个人被一种不可告人的嗜好、一种明令禁止的热情所征服。
于是,文学不再只是一个游戏了。
它变成了一种抵御不幸的方式,一种抗议的方式,一种反叛的方式,一种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负的方式;它变成了我活着的理由。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每当我觉得消沉或者压抑,每当我徘徊在绝望的边缘,我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来。
它犹如一盏明灯,指引人走出地道;又像是一块救生板,将落海的人带回岸边。
尽管写作让我颇费力气,它让我流下豆大的汗珠,并且像所有作家一样,我也时常感到江郎才尽、想象力枯竭的威胁。
但是,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区构建一个故事更令我感到享受,因为这个过程意味着从一个模糊的想法,一个记忆中收存的某次亲历的景象,发展成为一种忐忑,一种热情,一种遐想,而后又形成一个计划,最后变成一个决心,决心尝试将这层薄雾一般浮动的幻影变成一个故事。
“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福楼拜如是说。
的确,他说得非常准确。
写作是一种充满幻想和愉悦的生活方式;是头脑中火花四射的一团火焰;是同不听话的语言作战并最终将它驯服,这就像猎人为追踪令人馋涎的猎物而不断探索广阔的世界,目的是把最初的想象喂饱,使每个故事的巨大胃口得到满足,而这胃口越来越大,常常试图一口吞下所有的故事。
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甚至会感到头晕目眩,但小说一旦着床,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