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征.docx
《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征.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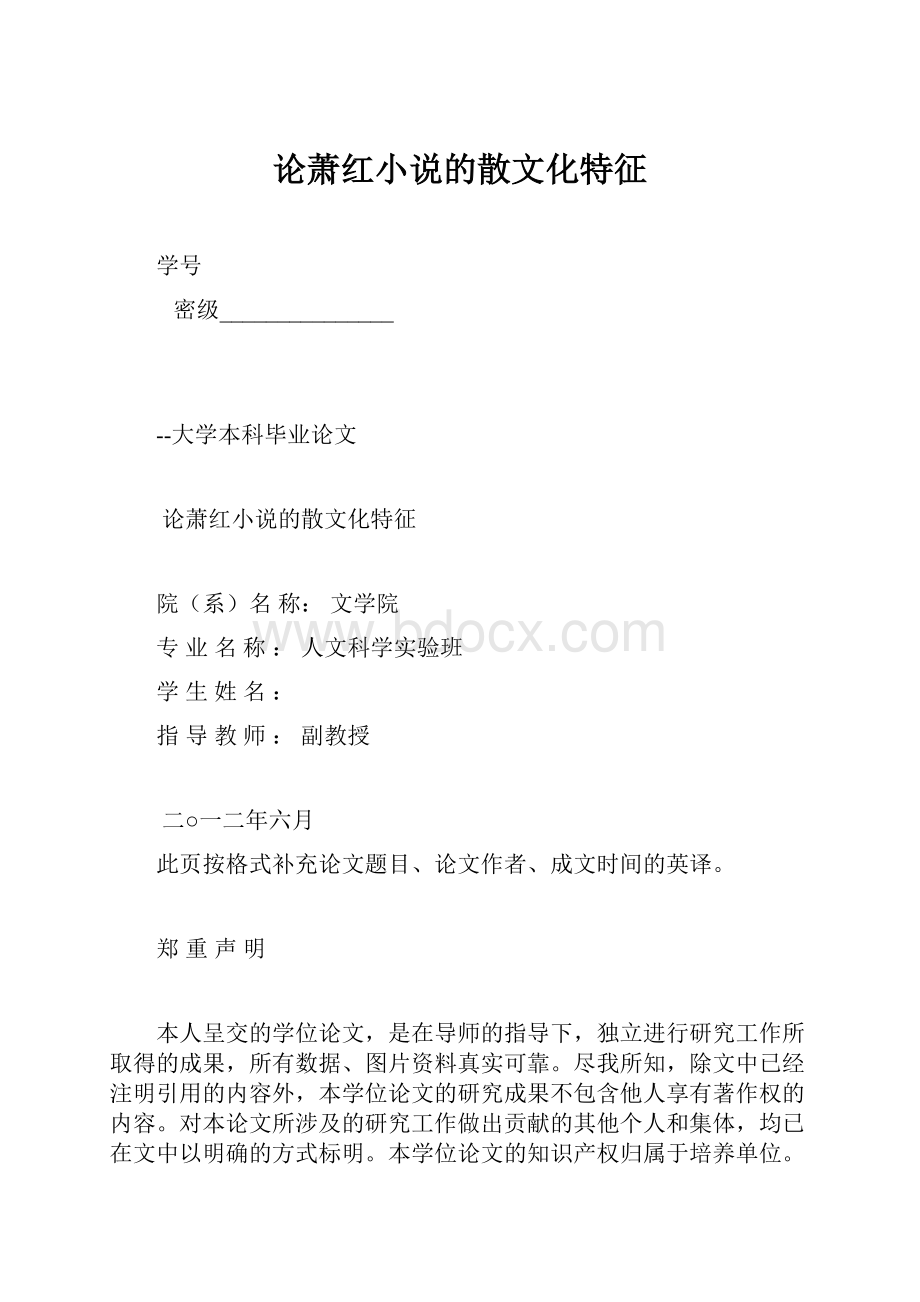
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学号
密级_______________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院(系)名称:
文学院
专业名称:
人文科学实验班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副教授
二○一二年六月
此页按格式补充论文题目、论文作者、成文时间的英译。
郑重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所有数据、图片资料真实可靠。
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
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
本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培养单位。
本人签名:
日期:
摘要
与同时代的左翼文学相比,萧红的小说有着更持久的生命力。
这不仅在于萧红小说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关注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更在于她的小说的形式。
萧红坚持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在小说创作中借鉴了散文的手法,从而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特征。
本文将从小说结构、叙事以及抒情手法三个方面阐述萧红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萧红小说的结构。
首先概括介绍了小说时空形式与作品结构的关系,然后分别分析了萧红小说的空间与时间形式:
萧红小说以“并置”的空间场景结构全篇,从而忽略情节的连续性;萧红小说中的时间多为叙述者体验的时间,具有假定性和非指向性,因此她的作品带有某种“非小说性”。
第二部分论述萧红小说的叙事。
无论是使用全知叙事视角还是限制性叙事视角,萧红小说在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本质上的第一人称叙事使得萧红的小说指向了散文抒情言志的功能。
第三部分论述了萧红小说的主观抒情性。
萧红在小说中借鉴了散文融情于景、意境的营造等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
同时作为一名“回忆型”作家,萧红小说多取材于童年与记忆中的故乡,因而她的小说往往笼罩着一种感伤的氛围,带有很强的抒情意味。
关键词:
萧红小说;散文化;时空结构;叙述视角;抒情手法
此页按格式补充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的英译
引言
经典文学史教材中对萧红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如下的论述:
“她注重打开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
萧红的忧郁感伤可以与郁达夫的小说联系起来看,但她并没有那样病态、驳杂,更有女性的纯净美。
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
”[1]
茅盾评萧红的《呼兰河传》时说: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像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一些的东西。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2]茅盾的评论中即已指出萧红的小说所包含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因素——它的结构的散化,对风俗人情的描绘,以及它的主观抒情性,萧红小说的这种异质性往往被概括为“散文化”。
她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闲散的结构、稚拙的叙述都构成了独特的‘萧红体’,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3]
纵观以往的关于萧红小说形式的研究,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单一地关于萧红小说的结构或叙事的研究,如赵园、刘媛媛、秦林芳等所做的相关研究;一是关于萧红小说散文化的理论思考,如皇甫晓涛《关于小说散文化的理论思考》从理论上回顾了“散文化”的因缘与演变。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萧红小说的“散文化”文体特征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从而在这方面的认识不够全面。
本文研究的宗旨即是以萧红小说的“散文化”文体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空间小说理论以及具体文本,从形式因素的角度对萧红小说进行全面分析。
第一章结构:
时空形式的建构
萧红小说结构的散漫、零散化、场景化源于其独特的时空形式。
萧红往往以各自独立、零散的“时空体”来结构全篇,这种空间化的叙述方式终止了小说时间的连续性,因而不存在贯穿全篇的完整的故事情节,小说以片段化的类似电影场景的空间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以情节取胜,但空间化叙述的生动性、形象化以及其中所包涵的耐以咀嚼的意味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萧红小说的时间都不是连续的,更多的是小说叙述者所体验的时间,不具有明确的指示性,带有某种主观性和恒常性,其时间的断裂造成了小说结构的不连贯性。
1.1小说的时空形式与作品的结构
时间和空间决定了小说的结构。
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提出了“时空体”的概念:
“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xpohoton)。
”[3]“时空体”的艺术特征表现在:
“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
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衡量。
”“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
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
”[4]
文学对现实的历史的时空体的把握,是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的。
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18世纪以前的欧洲流浪汉小说,在时间上遵循“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法则,近乎完整地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力求贴近现实;在空间上则以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见闻展开,前后具有连贯性。
这类小说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结构,它重视情节和戏剧化情境的构造,必定有着重刻画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学的译介,中国现代小说对传统小说有所突破。
鲁迅的《狂人日记》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时空形式,突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框架,以狂人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结构全篇。
《故乡》、《药》一类的作品也旨在揭露中国人的精神病苦,淡化了情节,构成情节要素的时间关系和因果联系被极大削弱,而注重空间构造,通过场景或场景的组合,来凸显社会思想的某个侧面。
《阿Q正传》、《孤独者》一类的作品,虽然有主要人物,但并没有围绕特定事件进行,而以突出的生活插曲相连结的写法,来刻画小说中心人物灵魂的各个侧面。
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继承了鲁迅的创新精神。
她并没有因为文学惯例上的教条而束缚了自己的艺术个性,而是选择在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里自由驰骋。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科夫的作品那样。
我不信这一套。
有各种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5]纵观萧红短短十年的文学生涯,从成名作《生死场》到生命后期的《呼兰河传》《后花园》等,无不体现出萧红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坚守。
胡风曾这样批评《生死场》:
“对于题材的组织力度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
”[6]萧红的小说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形象,小说情节主要由叙述者所感受或回忆的零碎的生活片段组合,时常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时间断裂,无论长篇或是短篇多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出现,每个可以独立成篇的场景“并置”,这与萧红对时空形式的独特处理有关。
1.2空间“并置”与生命的存在状态
约瑟夫•弗兰克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并置”。
所谓“并置”,“它是指在文本中并列地放置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向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和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
”[7]萧红小说闲散的结构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各种零散场景的并置,虽然这些场景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但是在前后的参照中,在并置场景的切换中,这些形象感极强的画面往往会使小说有一种整体上的浑融感,传达的意义比每一个独立的场景要大得多。
在萧红的作品中,空间往往超越了时间而作为一种独立性的存在。
以空间场景结构全篇最突出的例子当属《生死场》,这首先从小说所拟的十七个小标题就可以看出。
《生死场》以麦场、菜圃、荒山、屠场等场景为故事的空间背景,活动在空间背景里的人们并不是小说着力描述的对象,也就是说这部小说不需要中心人物,金枝、王婆等等不过是某种特定时空下极其卑微的人们的代表,空间背景以及空间里人们的活动所组成的一系列场景的组合承载了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意义。
麦场里活动着老山羊、二里半、麻面婆以及他们的孩子罗圈腿,中心事件是二里半寻找他的丢失的老山羊。
菜圃是金枝接触男人,由女孩变成女人并陷入女人的噩运的地方。
荒山上埋葬着被疾病、贫穷和男人的绝情折磨而死的月英。
屠场里王婆亲自将老马送上刑场。
这些“并置”的场景是不是如胡风所批评的那样“散漫”无序,“感不到向着中心发展”呢?
事实上小说的标题——“生死场”,足以说明这些并置场景的内在统一性。
戈特弗里德•本在谈到他的《表象型小说》(1949)时提出了“桔瓣形”小说结构,它合适地描绘了已经从中取消时间顺序的结构:
“这部小说……是像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的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他们都相互紧挨着(‘毗邻’——莱辛的术语),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这个坚韧的茎是表型,是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各部分之间是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
”[8]这个比喻——小说应该按桔状构造——与空间形式有效地发生了联系。
空间形式的小说不是萝卜,日积月累,长得绿意流泻;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许多相似的瓣儿组成的桔子,它们并不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核上。
《生死场》中看似散漫的场景即是这“桔瓣”,而“桔瓣”所向着的“坚韧的茎”正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全部意蕴——20世纪初中国北方乡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9]。
由于物质生活上的极度贫穷,“二里半”视一只老山羊如生命,麻面婆本能地畏惧自己的丈夫,孩子比麦子要精贵;金枝在男人的诱骗下陷入女性无穷的噩运中,变成男人泄欲的工具;老王婆的送老马进入屠场时不能自已的悲哀何尝不是对自己这一生无穷尽的悲剧的哀哭;五姑姑们忍受生育的刑罚……“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10]这些场景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最终指向了一个主旨——而这个主旨是读者通过这一系列场景形象地把握的,它并不唯一,而是随着时代、读者群的变化而生成不同的意义。
比如当时的人们对《生死场》主题的解读是“抗日”,而近来人们从《生死场》中看到了萧红对“五四”传统的继承[11],看到了萧红关注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12]等等。
萧红小说以空间场景来组织全篇,弱化了时间因素。
不论是在《生死场》、《呼兰河传》,还是《后花园》、《小城三月》中,小说里的空间都失去了时代特征,静态场景、画面成为了具有超越时代的无限性和永恒性的空间存在。
呼兰河城的东西二道街,属于“我”的小空间,“我”家的后花园,“我”家院子里的几户人家,这些空间以及活动在空间里的人们似乎永远都那样存在着,人们逆来顺受,麻木地活着。
呼兰河城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如同开篇那个“大泥坑”一样。
呼兰河人即使总是陷入不幸的泥潭,但是只要能够侥幸逃脱,他们仍然会袖手站在泥坑旁,把自己或者他人的不幸当成一种谈资以消遣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后花园》、《小城三月》中更多是以优美凄婉的笔调进行自然环境的描写,而很少有社会环境的描写,小说中的社会性时间消失了。
莱辛说,“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13]。
萧红学过绘画,曾一度想到巴黎专攻美术。
她似乎对空间更加敏感,常以空间塑形来打破时间的连续性。
萧红将小说由单纯的时间艺术转向了对空间描绘的重视,从重视情节的曲折、人物形象的刻画转向了通过场景的展现来承载小说的内容。
1.3个体的时间与生命意识
时序的概念对理解萧红作品的结构有时全无用处。
萧红小说中的时间更多的是叙述者所体验到的时间,她更关注的是“历史流动中看似凝固的一面,历史文化深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的普遍而久远的悲剧。
”[14]她的时间中熔铸着叙述者对生命的哲理性体悟,具有不确定性、非指向性。
《生死场》写四时流转,但是并没有如现实时序那样写某一年的四时流转,而是写散落在时间里的碎片化的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组接,传达一种沉滞、令人焦虑的文化氛围。
小说里的人物更没有时间意识,而是动物般地生死。
“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依旧似十年前。
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山下有牧童唱着歌谣,那是十年前的旧调。
”[15]即使猛然间意识到时间,那也是迫于外力:
“全村寂静下去。
只有日本旗子在山岗临时军营门前,振荡的响着。
村人们在想:
这是什么年月?
中华民国改号了吗?
”[16]
而在《呼兰河传》中,时间具有了更大的假定性。
是今天,也是昨天或是前天,是这一个冬天同时也是另一个冬天,是一天也是百年、千年。
小说中的时间感、时间意识从属于作者的主旨:
强调历史生活中共时性的方面,强调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由这种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发掘民族命运的悲剧性。
开染坊的,开扎彩铺的,卖豆腐,卖麻花,卖凉粉的,开粉房的,养猪的,拉磨的……不论时间怎样流转,他们仍然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生老病死的定律。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
风霜雨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只有那还没有被拉出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17]这段抒情性的文字毋宁说是小说的,不如说是散文式的,它不属于小说的时空,而只是叙述者对她的叙述对象的一种感慨,一种对生命本质的体悟。
时间在这些卑微的人们身上流过,却什么也没有改变。
他们的命运毋宁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带有“共同命运”的意味,而这正得益于作者的叙述方式,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时间意识、历史意识。
“很难说这种时间意识是属于散文的,但至少它足以弱化情节、弱化‘小说性’的,也因而可能助成某种‘散文特征’。
”[18]
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时间由模糊、重叠到假设性、非规定性,因而愈增添了“非小说性”。
而叙述内容的假定性,目的正是为了表现过程的重复性,生活的循环性。
这不是具体的哪一天,因而才是无论哪一天,都是无穷无尽的呼兰河人的日子。
萧红的这种叙述方式使她的作品情境在虚实之间,在具体与非具体,特定于非特定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写实与寓言之间。
而萧红进而把对时间的这种体悟上升为一种生命哲理意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
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嫂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过日子。
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19]有论者称,萧红的小说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顽强生命力,就在于她的创作具有悠远深长的哲学意味。
“这种哲学意味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种诗意的妙悟,是对描写对象本身的超越。
”[20]萧红的哲学不是对于读者的强加的哲理,她是把自己对生命、对时间的体悟化入了她的小说的形式之中。
化入了“形式”的思想,本身即有可能成为审美对象。
而时空结构又何尝只是“形式”呢?
它们同时是内容。
综上所述,传统的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多是依照线性时间的发展来组织故事情节,而萧红的小说中则往往忽略时间的连续性,终止具体时间的流动,造成时间的中断与碎片化。
萧红看到了时间的恒常性背后生命的真相:
人们像卑微的蚁子一般麻木地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日子,在生、老、病、死的法则中苦熬。
萧红以假定性的、非指向性的时间写呼兰河城,写生死场,使小说看上去支离散漫,带有散文的某种特质,但是这种时间形式事实上参与了小说内容的建构,使小说的悲剧意蕴更加沉静而有力度。
葛浩文认为,“由于萧红的作品没有时间性,所以她的作品也就产生了‘持久力’和‘亲切感’。
”[21]
第二章叙事:
本质上的第一人称叙事
叙事角度的切入反映了一个作家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方式,而不同的叙述视角也决定了不同的故事形态,同时也内在地决定了小说的结构形态。
萧红的小说尽管叙述视角一再转换,有时全知叙述,有时又限制性叙述,但是“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她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
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
”[22]从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来看,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便于作家灵活地叙事、抒情。
它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主观感受作为表现的中心,以叙述者的主观感受来安排故事发展的速率,因而摆脱了“故事”的束缚,突出作家的审美体验和感情态度。
因此,第一人称的叙述同时指向了抒情功能。
“当叙述主体的‘我’与作为作品中人物的那个‘我’合二为一重叠在一起时,只要不违反性格轨迹人们是很难察觉的。
所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亲切感也往往意味着鲜明的主体性和浓郁的抒情性。
”[23]正是这种萧红式的第一人称叙事,使得萧红的小说具有了抒情言志的特征,从而带有散文化特征。
2.1全知叙事视角下的叙述者的声音
全聚焦模式是最传统、运用最普遍的一种的小说叙述模式。
“在这类模式中,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不仅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他们的过去与未来;而且活动范围也异常之大。
”[24]“创造作品的作者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自由移动:
他可以从结尾到开头,从中间到开头,同时却不破坏所描述事件中时间的客观流程。
”[25]徐岱将全聚焦模式分成了三个类型:
主观型,客观型,混合型。
其中主观型叙事模式的叙事者不仅全知全能,而且君临一切,常常以第一人称直接登场亮相凌驾于故事之上,通过发表感想与议论来干预叙述的过程。
《呼兰河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作者采用了全知叙事的角度。
作者虽然没有作为人物在小说中出现,但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超越于所有人物和故事之上,洞察一切,比其中的任何人物知道得要多。
在这两章中,叙事者扮演着“导游”的角色,带领读者熟悉呼兰河城这个空间以及世代居住在呼兰河城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者笔下的呼兰河城有并不繁华而略显冷清的东西二道大街,有行人深受其害但永远不会改变它的大泥坑,开扎彩铺的,买豆腐的,卖麻花的,开药店的,呼兰河人的物质生活是“卑琐平凡”的;而呼兰河人每年最大的精神盛举就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看野台子戏以及四月十八的娘娘庙大会了……叙述者的视角可以在呼兰河城这个空间里自由移动,用充满了色彩感和音乐性的笔调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多彩的风俗画。
但是萧红的全知视角并不是客观地描述和展现,而是以一种温婉亲切的笔调在诉说,并且不露声色地传达出叙述者对呼兰河城的情感和态度,其中有温情的怀念,有深刻的悲凉和无奈,也有辛辣的讽刺。
在萧红的一派全知叙述的背后,呼兰河城的全貌以及呼兰河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读者也意识到在这叙事背后叙述者的声音。
萧红对于呼兰河人逆来顺受、麻木地日复一日的生活是充满无奈和同情的,她的情感是悲凉的。
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因独子掉在河中淹死而发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静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仍是静静地活着。
”[26]作者反复地强调“她仍是静静地活着”,句式的复沓背后,叙述者对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无奈之情跃然之上。
叙事者甚至跳出故事,直接表露自己的感情,比如写扎彩铺一段,叙述者直接发表自己的议论和感慨: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
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
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嫂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过日子。
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27]
这段议论性的话语游离于故事之外,与故事的发展无关,是叙述者情感的宣泄和对人生感悟的表达,使整部小说带有一种抒情言志的调子,在结构上虽嫌松散,不如故事性的小说紧凑,反而像一部长篇的优美散文。
萧红的小说无不有叙述者发出的声音,即使没有直接表达,在作者的叙述背后也会使读者感受到叙述者的情绪、思想,这种主观化的全知叙事方式也是萧红小说散文化的特征之一。
2.2限制性叙事:
儿童视角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充满童心童趣的作家,鲁迅就很欣赏萧红的这种坦率和天真。
萧红的小说并不是单一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而是会变换叙述视角,她常常会从一个儿童的角度,通过一个儿童的见闻感受来叙述故事,使得故事的讲述更加真切可信,但是即使在限制性叙述的视角下,仍然是有叙述者的影子。
《呼兰河传》的第二章以后的部分,作者放弃了全知叙述的视角,选择从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的角度进行叙述。
作者写祖父和“我”在后花园里的生活,写了祖母的去世,写“我”跟祖父学唐诗,写“我”家屋子的构造,写“我”家后院里住的几户人家,写了三个人物的故事:
小团员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通过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的感受、见闻来叙述的。
这种儿童视角的运用在使作品获得了真实感的同时,更增加了作品的意蕴。
比如写祖母去世一节,作者这样写道:
“等人家把我抱了起来,我一看,屋子里的人,完全不对了,都穿了白衣裳。
再一看,祖母不是谁在炕上,而是谁在一张木板上。
”[28]这大概就是死亡对于“我”最直观的印象了,从儿童的视角来看死亡,就是如此直观、感性的认识,而儿童的天真烂漫与死亡这一沉重的人生命题的对比又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照生命的方式,发人深省。
然而作者、叙述者、作品中的“我”之间的间隙读者仍能从叙述中感受到。
保有儿童的感觉方式的作者,寄寓着作者形象的叙事者,毕竟不等同于作品主人公的那个孩子。
因而在作者的叙述中,隐含着微讽,以及沉重的、严峻的、悲悯的、无可奈何的诸种混作一团的情绪。
比如小团圆媳妇生病了,“于是有许多人给他家出了主意,人哪能够见死不救呢?
于是有善心的人都帮起忙来。
他说他有一个偏方,她说她有一个邪令。
”[29]人不应该“见死不救”,“有善心的人”,这些都明显不是一个儿童的智识所能达到的高度,明显是叙述者的讲述,带有微讽的意味。
再如,在写到开粉房的一家时,作者写道:
“他们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
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地唱着。
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逆来顺受。
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
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
不得已怎么样?
人生是苦多乐少。
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
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这明显不是一个儿童的认知所能及,而是叙述者的声音。
与现代派作家相比,萧红并不具备通过自觉的转换叙述视角来讲述故事的意识。
尽管她的小说中叙述视角也在不断切换,有时使用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有时通过儿童视角或者旁观者的视角(比如《手》)来叙述,但那都是比较随意的和不自觉的。
“她(萧红)对叙事角度不自觉的变换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生活、观察生活、多方透视生活、呈现生活,并且在对客观世界的多向影射中,同时充分展现自己的情感判断和理性判断,因而,它完全是服从于内容的现实和情感的表达的。
”[30]她在限制性叙事的同时又会不露声色地发表叙述者的观点,表达叙述者的情绪,因而在本质上都是一派萧红式的讲述,用温婉的声调向读者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