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docx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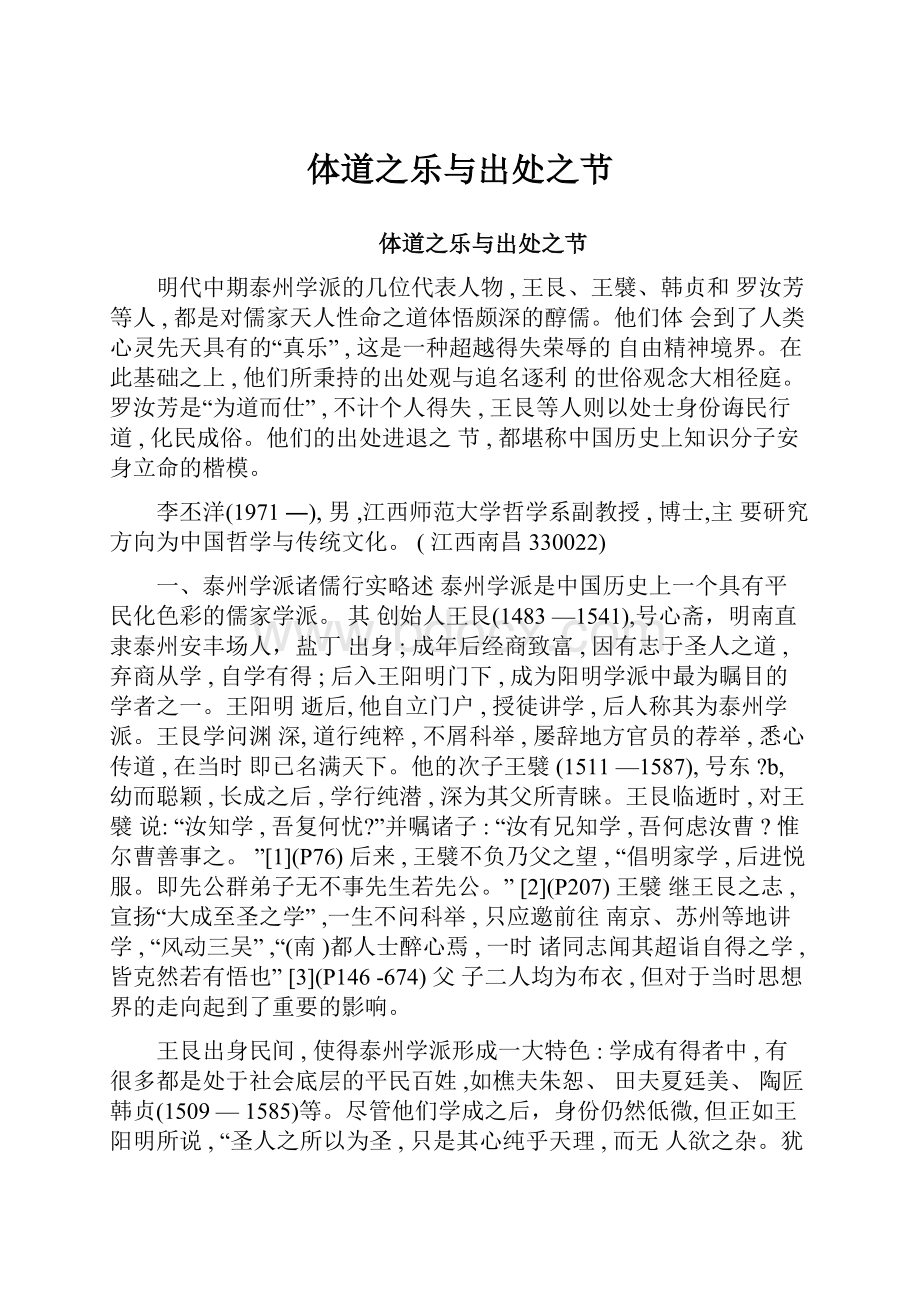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
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
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
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
罗汝芳是“为道而仕”,不计个人得失,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化民成俗。
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李丕洋(1971―),男,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江西南昌330022)
一、泰州学派诸儒行实略述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平民化色彩的儒家学派。
其创始人王艮(1483—1541),号心斋,明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人,盐丁出身;成年后经商致富,因有志于圣人之道,弃商从学,自学有得;后入王阳明门下,成为阳明学派中最为瞩目的学者之一。
王阳明逝后,他自立门户,授徒讲学,后人称其为泰州学派。
王艮学问渊深,道行纯粹,不屑科举,屡辞地方官员的荐举,悉心传道,在当时即已名满天下。
他的次子王襞(1511—1587),号东?
b,幼而聪颖,长成之后,学行纯潜,深为其父所青睐。
王艮临逝时,对王襞说:
“汝知学,吾复何忧?
”并嘱诸子:
“汝有兄知学,吾何虑汝曹?
惟尔曹善事之。
”[1](P76)后来,王襞不负乃父之望,“倡明家学,后进悦服。
即先公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
”[2](P207)王襞继王艮之志,宣扬“大成至圣之学”,一生不问科举,只应邀前往南京、苏州等地讲学,“风动三吴”,“(南)都人士醉心焉,一时诸同志闻其超诣自得之学,皆克然若有悟也”[3](P146-674)父子二人均为布衣,但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走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王艮出身民间,使得泰州学派形成一大特色:
学成有得者中,有很多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如樵夫朱恕、田夫夏廷美、陶匠韩贞(1509—1585)等。
尽管他们学成之后,身份仍然低微,但正如王阳明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
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4](P27),他们实际上都达到了圣者的境界。
当然,泰州学派
门下也不乏后来做了大官的人物,其中,学行最为高卓、超迈的莫过于罗汝芳了。
罗汝芳(1515—1588),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年少时即矢志圣学,二十六岁时,他在南昌偶遇泰州学派的颜钧讲学,闻其言曰“体仁之妙,即在放心”而大悟,从此师事山农,成为泰州学派门下之人。
罗汝芳三十岁会试中榜,却十年不赴廷试,潜心学问,三十九岁才廷试得中,开始为官。
他治事干练,居官清廉,颇有声望,虽然仕途上有升有黜,但丝毫不介于心,公务之暇,专以讲学明道为己任,成为扛起心学大旗的一代名儒。
如果从世俗眼光来看,王艮和王襞父子不事科举、谢绝荐举,以及罗汝芳十年不赴廷试的行为,简直傻得出奇,这和《儒林外史》等文学典籍中描述的儒生们汲汲求取功名的行为大相径庭,这难道同属于一个儒家范畴吗?
客观地讲,他们同属儒家,但有俗儒和真儒之别。
前者,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个“龙门”来跻身显贵的官方儒学,众多生员营营苟求,口是心非,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
后者,则是以修身明道为目标、以化民成俗为己任的士人儒学,他们无论是否做官,目的都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孔孟颜曾等先圣的真血脉,以期天下之人都能明明德,止于至善。
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了王艮等泰州学派名儒安身立命的思想理念之后,就会对以往关于儒家思想的模糊认识做出极大的修正,重新树立起对先哲的景仰之情,并反思现代社会时尚的人生价值观的合理性。
二、泰州学派诸儒的体道之乐
首先,需要搞清的是:
泰州学派诸儒一辈子专心于学问,到底学的是什么?
概而言之,他们所学的不是俗儒的那套八股时艺、章句训诂,而是一个“道”字。
先秦儒学元典《中庸》开篇即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句话把儒家修道哲学的真容一笔勾出。
宋明时期,由于占据官学地位的朱子学在方法上繁琐支离,士人们想要由此明道,十分困难。
在这种背景之下,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迥异于朱学的心学命题,特别是“良知即是道”[5](P69)的思想,把儒家修道哲学的脉络勾勒得一清二楚。
泰州学派诸儒得阳明之真传,跻先圣之绝域,在这一为学的方向性问题上具有鲜明而一致的观点。
例如,王艮曾说:
“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
识得此
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
”[1](P38)又说:
“道在天地间,实无古今之异,自古惟有志者得闻之。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余何足言哉?
”[1](P28)“闻此良知之学,闻天命之性,可谓闻道矣。
”[1](P63)王襞亦曰:
“良知之传,千圣之秘藏,而阳明先师翁,从万死一生中拈出者,盖以此物不明,一切学术尽皆支
离,掇拾之繁而影响形迹之似,心劳而日拙,于性命根源了无有交涉,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6](P218)
概括而言,泰州学派认为,明“道”是探讨学问的根本目的。
这个“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贤哲那里有不同的称谓,先秦时期曾叫做“天命之性”,也叫做“未发之中”,宋代称为“天理”,到了明代,王阳明称之为“良知”,其实所指都是一个东西。
但不管叫什么,这个“道”的内涵,都是关于宇宙的本体、生命的本质等关键性的内容。
明白了这个“道”,便是人生的彻悟,也意味着人们对内外各种束缚的根本解脱。
正因为如此,泰州学派把明道、传道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
王襞曾说:
“直信人生只有此一事,千古只有这一件,舍此一事皆闲勾当;离此一件总是糊涂。
安忍将有限光阴,却付闲勾当,去无穷明妙,乃坐糊涂相也。
”[6](P222)罗汝芳在云南为官时,亦曾对诸生讲:
“人生世间,惟有此一件事,最为紧要。
”[7](P172)由此可见,泰州学派有一个“道”字贯穿始终。
需要指出,这个天人性命之“道”,并不是像朱学认为的那样可以从章句训诂中得来的。
王艮明确指出:
“是道也,非徒言语也,体之身心然后验矣。
”[1](P48)他还提出:
“夫六经者,吾心之注脚。
心即道,道明则经不必用,经明则传复何益?
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
”[1](P70)
王艮的本意,是要求学者们切己涵养,笃实践履,以期体悟真道,反对一味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王襞也秉承此意,一生不事著述只重口授心传,说:
“道本无言,因言而生解,执解以为道,辗转分明,翻成迷会。
”[6](P216)韩贞亦曰:
“千圣难传心里决,六经未了性中玄。
”[8](P174)可见,泰州学派贯彻了阳明心学注重践履、“知行合一”的思想,与沉溺于八股时文、章句训诂的俗儒学风泾渭分明。
正因如此,当代学人考察泰州学派的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遗言遗训的诠释上――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材料,比起朱子门中的儒者来,实在少得可怜――必须结合其一生行迹来判断其思想的真实面貌,特别是要按他们所说的践履与体悟方式去如实领会他们所说的“道”的内涵,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心灵世界。
或许有人会问:
“如果体悟到了王心斋等人所说的那个道,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益处?
”简而言之,通过孜孜不倦的修道,最终可以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涵,并且从中获得一份“真乐”作为人生的受用。
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涵,其实也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本然境界。
这种境界,用语言是无法描述清楚的,正如王襞所说的“道本无言”。
不过,那份“真乐”倒是可以略述一二,
它指的是一种在体悟良知(或曰“道”)的基础上所必然伴生的
一种精神上的自如无碍、愉悦和畅等永久性的心灵感受,即精神的自由境界。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曾赞誉其高徒颜回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又自述说: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这体现了孔子和颜回不在乎个人功业的成败,不
计较生活境遇的贫富,恬然自处,自得其乐的圣者心态。
到了宋代,理学家把它称为“孔颜真乐”(或曰“孔颜乐处”)。
无疑,这是一种超越世俗得失计较的心灵境界,谁体悟到了,便跻入圣域,获得了人生极为宝贵的受用。
对此,王艮、王襞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获得这种“真乐”的感受,肯定这种“真乐”的价值。
例如,王艮曾说:
“学者不见真乐,则安能超脱而闻圣人之
道?
”[1](P19)“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后能宰万物而主经纶,所谓乐则天,乐则神。
”[1](P19)王襞则以诗文表达自己的体道之乐:
“人固有蒙幸,我幸安可比?
自觉换骨清,哪羡羡门子。
感念父师恩,交颐涕如雨。
无忝吾所生,至乐不可拟。
”[9](P266)又说:
“我从一得鬼神辅,入地上天超今古。
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
闲唱壶中白雪歌,静调世外阳春曲。
我家此曲皆自然,管无空兮琴无弦。
得来惊觉浮生梦,昼夜清音满洞天。
”[9](P270)
至于善工诗文的韩贞,这方面的文句自然更多,如:
“跳出樊笼打破空,一身漂泊太虚中。
心忘物我先天合,性悟鸢鱼造化同。
两袖清风挥宇宙,一肩明月任西东。
轻轻展足乾坤内,踏遍千山兴未穷。
”[8](P182)此诗没有明言一个“乐”字,但是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韩贞在悟道之后所达到的自如无碍、愉悦和畅的精神境界。
对于基于实践的体道之乐,泰州学派历来是相当重视的,以罗汝芳为例,史载:
问曰:
“孔子蔬水,颜子箪瓢,皆自有其乐者,恐正是此去处得力否?
”罗子曰:
“岂惟孔、颜哉!
从古圣贤,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9](P201)
正因为有超越性的“真乐”在胸,罗汝芳才能对个人仕途的得失成败看得淡然。
据史料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值十分赏识罗汝芳的王门后裔徐阶为首辅,他本意要将罗汝芳予以擢升不料弄巧成拙,吏部错会其意,把罗汝芳外放为宁国知府。
吏部尚书陆光祖将此事告知罗汝芳之后,罗汝芳笑曰:
“兄且休矣。
宁国不足以取公卿,独不足以取圣贤乎?
”陆光祖拱手谢曰:
“壮哉!
罗兄志也。
此岂人所及哉?
”[7](P838)这就是“体道之乐”给人带来的受用,它使人超脱了一己之私的得失与喜忧,能够随遇而安,无处不乐,诚如王艮所说:
“尘凡事常见俯视,无足入虑者,方为超脱。
”[1](P13)
三、泰州学派诸儒的出处之节
因为有体道之乐,泰州诸圣贤达到了一种“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的生命境界,因而能够“铢视轩冕,尘视金玉”[10](P41),把个人的荣辱利达看得轻淡,于是弃科考如敝屣,辞举荐若浮云。
然而,切莫把泰州学派诸贤看成是只追求个人逍遥自在的隐者。
儒家心学一派之异于佛老在于“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11](P17)
这就是说,儒家是以“经世”为务的,其奋斗场所始终是现实的社会,不像佛家那样以“出世”为根本目标,只注重追求个人的解脱。
王艮等人一直怀抱“欲尧舜其君,欲尧舜其民”[12](P50)的恢宏志向,并不屑于做像陶渊明那样的田园隐者。
王艮的经世志向其实很强烈,但是,基于对历代封建政治的清醒认识,他制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念原则――“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
”关于这一出处之节,王艮屡有论
述: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
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进不失本,退不遗末,止至善之道也。
”[1](P13)“出不为帝者师,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则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是独善其身,而不讲明此学,则遗其末矣。
”[1](P21)
王艮晚年创立“大成至圣之学”,以为凭此圣学在胸,治天下若运于掌上,只待君王或公卿大夫来虚心求教,聘请他出山,辅弼明主,经略天下。
正因为从政动机与只为个人功利的俗儒全然不同,他才能一再推辞地方官员的举荐,安然坐于乡间,终生讲学传道,成为一代民间儒学大师。
王艮的经世观,可以分为两
极一一“得君行道”和“诲民行道”。
遗憾的是,当时的嘉靖皇
帝并非有道明君,从未想过要向远在泰州的王心斋求教,因此,王艮就不可能“得君行道”,终生所做的只能是“诲民行道”,和儒家先祖孔子一样,成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了。
当然,王艮的出仕观也并非如后人误会的那样呆板,他说过:
“知此学,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
有为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为贫而仕者,为贫而仕,在乎尽职,‘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1](P16)
无疑,王艮本人是“为道而仕”的,其出处之节毫不含糊。
除了个人志向外,家境比较富裕也是他绝不苟出的一个原因。
可是,他的许多弟子并没有他那样殷实的家境,因此,王艮从来不否认可以把“为贫而仕”作为一种谋生途径,只是强调儒者“为贫而仕”,不可营营苟求,只要做到“尽职”即可。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的族弟王栋了。
王栋(1503—1581)出身贫寒,在科考上不甚得意,只中过秀才,五十六岁时被任命为江西南城县训导,后来又调任他处,所任仍是训导、教谕之类卑微的学官,最高也不过是深州学正。
显然,王栋是“为贫而仕”的,但他一面清廉自守,一面谆谆教诲士子百姓,所到之处信从益众,颇得声望。
因为学行优胜,他曾“屡署州县事”,但“毫不受私,致仕归,清贫如洗,悦乐自如。
”[13](P142)可以说,王栋将“为贫而仕”和“为道而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对此,他也有论述:
“圣人经世之功,不以时位为轻重。
今虽匹夫之贱,不得行道济时,但各随地位为之,亦自随分而成功业。
苟得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却原是圣贤经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
”[13](P186)这就是说,只要能够依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本分而行事,不论功业大小,任何人都可以起到移风易俗、行道济时的作用,哪怕只是对“一邑一乡”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都符合“圣贤经世家法”,体现出“天地生物之心。
”
泰州学派的韩贞更是一个化民成俗的倡导者。
韩贞,陶匠出身,终生不事科举,晚年也不过是一个乡贤村儒而已,但他“以化俗为己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
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知行合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14](P720)当地县令慕名而来,向他问政,他答道:
“某窭人,无能辅左右,第凡与某居者,幸无讼谍烦公府,此某所以报明府也。
”[8](P194)县令不信,查阅将几年来的案卷,果然没有一宗案件是韩贞乡里百姓所犯,化民成俗之效,可见一斑。
当然,王艮这种“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出处观,带有一些“狂者”气象,究竟是否允当,还可商榷。
在泰州诸贤中,出处进退之节把握得最好的,当属罗汝芳。
罗汝芳三十岁会试得中,不就廷试而归,寻师问友,周游四方十年。
三十九岁出仕之后,当过知县、知府、屯田副使、参知政事等许多职务,无论官职尊卑,一心以苍生为念,所到之处,或者为百姓纾难解困或者振兴礼乐教化,惟独不在乎个人的仕途升迁、荣辱利达。
奸相严嵩曾以同乡之谊,邀其相见,许以台省要职,他置若罔闻;权相张居正遣其子拜谒门下,示以拉拢重用之意,他不为所动。
万历五年(1577),他因在京讲学触怒张居正,被勒令致仕。
归里后,远近就学者益众。
据记载:
或曰:
“师以讲学罢官,盍少辍以从时好?
”师曰:
“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
况今去官,正好讲学。
”时严禁讲学,或曰:
“师宜辍讲,庶免党祸。
”师曰:
“人患无实心讲学耳,人肯实心讲学,必无祸也。
党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实心讲学者也。
”[7](P848)
果然,罗汝芳在乡讲学终老,当朝者谁也没有来找过麻烦。
同乡退休官员司寇朱大器来访,对其说:
“出处士人大节,我兄难进易退。
讲学以身而非以口矣。
”[7](P422)应当说,这个评价是相当公允的。
罗汝芳一生,为官多年,或主地方,或治刑名,或治水利,或治兵事,公务之暇总是以讲学传道为业,而听者云集,觉悟者亦不在少数。
他一生的志向就是要将先圣之道传遍海内,使海内之人都能明明德,止于至善。
对他而言,这件事其乐无穷,乃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
罗汝芳的出处进退之节,为后世活脱脱地诠释了一个圣者的形象,有鉴于此,现代学者中有人将其视为“王学的圆熟境界”。
[15](P88)
本文所论,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安身立命之道,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真儒与俗儒的区别。
王艮等人以修身明道为目标,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在自身修道、悟道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世俗得失荣
辱的自由精神境界。
由于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束缚,进而欲明明德
于天下,于是,他们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
王艮提出了“出不失本,处不遗末”的经世思想,其他学者以自己
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