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诗文中的生命原则透析.docx
《顾城诗文中的生命原则透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顾城诗文中的生命原则透析.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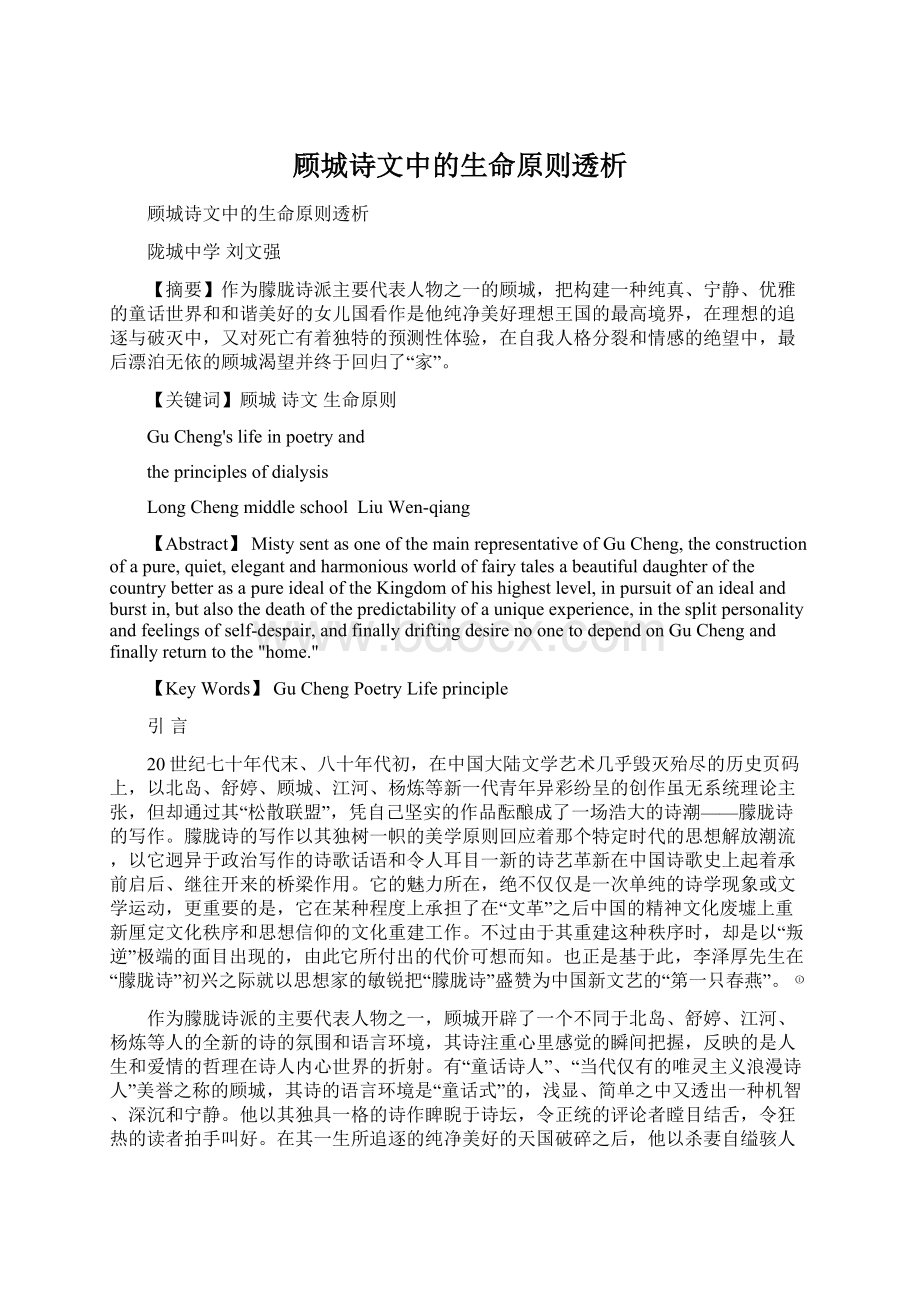
顾城诗文中的生命原则透析
顾城诗文中的生命原则透析
陇城中学刘文强
【摘要】作为朦胧诗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顾城,把构建一种纯真、宁静、优雅的童话世界和和谐美好的女儿国看作是他纯净美好理想王国的最高境界,在理想的追逐与破灭中,又对死亡有着独特的预测性体验,在自我人格分裂和情感的绝望中,最后漂泊无依的顾城渴望并终于回归了“家”。
【关键词】顾城诗文生命原则
GuCheng'slifeinpoetryand
theprinciplesofdialysis
LongChengmiddleschoolLiuWen-qiang
【Abstract】MistysentasoneofthemainrepresentativeofGuCheng,theconstructionofapure,quiet,elegantandharmoniousworldoffairytalesabeautifuldaughterofthecountrybetterasapureidealoftheKingdomofhishighestlevel,inpursuitofanidealandburstin,butalsothedeathofthepredictabilityofauniqueexperience,inthesplitpersonalityandfeelingsofself-despair,andfinallydriftingdesirenoonetodependonGuChengandfinallyreturntothe"home."
【KeyWords】GuChengPoetryLifeprinciple
引言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学艺术几乎毁灭殆尽的历史页码上,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新一代青年异彩纷呈的创作虽无系统理论主张,但却通过其“松散联盟”,凭自己坚实的作品酝酿成了一场浩大的诗潮——朦胧诗的写作。
朦胧诗的写作以其独树一帜的美学原则回应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以它迥异于政治写作的诗歌话语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诗艺革新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作用。
它的魅力所在,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诗学现象或文学运动,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在“文革”之后中国的精神文化废墟上重新厘定文化秩序和思想信仰的文化重建工作。
不过由于其重建这种秩序时,却是以“叛逆”极端的面目出现的,由此它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也正是基于此,李泽厚先生在“朦胧诗”初兴之际就以思想家的敏锐把“朦胧诗”盛赞为中国新文艺的“第一只春燕”。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顾城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人的全新的诗的氛围和语言环境,其诗注重心里感觉的瞬间把握,反映的是人生和爱情的哲理在诗人内心世界的折射。
有“童话诗人”、“当代仅有的唯灵主义浪漫诗人”美誉之称的顾城,其诗的语言环境是“童话式”的,浅显、简单之中又透出一种机智、深沉和宁静。
他以其独具一格的诗作睥睨于诗坛,令正统的评论者瞠目结舌,令狂热的读者拍手叫好。
在其一生所追逐的纯净美好的天国破碎之后,他以杀妻自缢骇人耳闻,引起诗界热爱他诗作的读者们一片哗然。
作为诗人的顾城,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研读的诗篇;作为惨案制造者的顾城,同样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沉思。
一、纯净的天国美
在《英儿》中,顾城曾说:
“我的最深处从来没有八岁。
我想让人收留我的时候,门就都关上了。
”因此,顾城和热情关注社会、直面惨淡人生的北岛、舒婷、江河、杨炼不同,他的诗歌是以回避丑恶现实的表现为表征的。
他说:
“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
∕我总是长久的凝望着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深深感到一种净化的愉快。
∕我渴望进入这样一种美的艺术境界,把那里的一切,笨拙的摹画下来,献给人民,献给人类。
∕我生活,我写作,寻找美并表现美,这就是我的目的。
”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惟有童心和自然依旧璞玉浑金,散发着古朴纯真的气息,所以他格外沉迷于“梦”的制作,津津乐道于童心和自然的歌吟,以干净的意象、单纯的基调,以外冷内热的情感,着意构建了一个独立于自我和现实之外的“纯净美”的艺术世界,“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
”(《学诗笔记
(一)》)让他的灵魂长久栖息其中,抖落痛苦,平静躁动。
他的诗往往以貌似超脱、故作轻松的儿童话语和纯朴的自然包藏起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觉醒者的深刻剧痛和孤独寂寞,而一意地、固执地用一种“成人仿拟童话”的特别格式,表达对“人”生存境况的特别关注,在一个宽广的视域内传达出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意识,从而建立一个纯净美的理想世界。
(一)以自然美为生活背景的童话世界
顾城曾在他的《学诗笔记》中说:
“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他以一个孩子的梦,用“纯银”一样的声音去构筑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更纯更美,构筑这个纯净世界的材料:
一是未被污染的大自然,二是孩子的心灵和眼睛。
大自然是产生童话的最好土壤,“在我的少年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书可读,我读得最多的一部书就是大自然。
”(《关于诗的现代创作技巧》)在他的诗中,自然是有生命的人格化的自然,具有各种感官,有自己的语言动作,可以和人进行交流对话,如“野花∕星星点点∕象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无名的野花》),“一棵树闭着眼睛∕细听着周围对自己的评论”(《一棵树的判断》),“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他的籽/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门前》),“我厌恶∕我长久的睡着∕和大大小小的种子睡在一起∕只有我,不会萌发∕不能用生命的影子覆盖土地”(《化石》))……
发现了自然也就发现了生命,顾城对自然的发现与感受比一般人要早,这来自他对生命的感悟与关爱,“我觉得诗和生命是一体的,它们又有着各自独立的命运过程。
就我的诗来说,刚开始显然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到后来才发生分离,诗一步步脱离生活趋向生命。
”
因此,他那无处不在的生命意识在诗行中激越地跳荡,“当我成为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就成了我”、“太阳是我的纤夫,他拉着我∕用强光的索∕一步步∕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生命幻想曲》)。
正如顾工所言: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
”
一踏上诗歌之路就渴望在诗中执拗地寻找一个类似童话般纯洁、精美、绝对的理想王国,企图构建一种比坚硬的现实生活更高级、更超越的精神现实,“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夜晚和苹果。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是以赤子之心向别人传递真实的思想和描摹自己真实的世界,毫无遮掩地流露出真情实感。
作为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而言,他不可能丢失自己那份纯真的天然情感:
稚气和滑稽。
虽然童年时的不幸使梦破灭,但他仍执着的追求幻想。
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诗人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和感受世界,希望能够用彩色的蜡笔勾画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人生蓝图,画下“笨拙的自由”、“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没有痛苦的爱情”、“遥远的风景”等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于他的纯美“童话世界”,他有着宗教般虔诚、偏执狂般的热情,不厌其烦地从多角度、多侧面以丰富的意象来充实其内涵,使之逐渐清晰、丰满。
在童话世界里,有“欣赏着暴雨的舞蹈”的蓝海洋(《小春天谣曲》),“干干净净的月光”(《草原》),“洁净的洋槐花”(《初夏》),“褐菌的部落”、“花香和雾的涌泉”(《水乡》),有“没有杀乱的市场∕没有众多的居民”、“没有森严的殿堂∕没有神圣的坟墓”(《我是一座小城》),有“蜷缩在树洞中”的松鼠(《雪后》),“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的树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长满了纯银的鳞和羽毛”的鱼和鸟(《梦痕》),有隐藏在“百里香和野菊的草间的蟋蟀,在我的车中做窝”的黄尾太平鸟(《生命幻想曲》),有“所有早起的小女孩∕都到田野上去∕去采春天留下的∕红樱桃∕并且微笑”(《初夏》)……这众多纯洁而充满童趣的意象,组成了一个优美完整、晶莹洁净的“天国”。
它散发着清新恬淡、平和明朗的气息,于自然明丽、质朴中显现出如雾如银的“纯净”。
这个用儿童天真无邪的眼睛作镜鉴而光照着成人世界的“天国”,如“皎皎空中孤月轮”,用一尘不染的童真向荒芜的人心、异化社会、龌龊的世界洒下柔和的爱之光,也说明了“顾城对‘童心’的刻意维持,既是他自身气质、情感、审美情趣、审美方式所决定的,也体现出了他明确坚定的美学追求。
”
在诗中,顾城始终以孩子气的眼光关注、打量身边的世界,用纯美的诗行、冲淡的心绪对童年旧梦做着专一而执着的叙述,在“现在”时间的童话叙述里,昭示“应到如此”的未来人性。
他的童话诗歌大多取材于和谐、温馨的童年记忆,但又不是简单的自然主义描摹,“此童年”大多是在“彼童年”基础上经过典型释取、渗进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理想而再创造的“童年”。
除《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之外,他在《生命幻想曲》中叙述到:
“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用金黄的麦秸∕编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装好纽扣的车轮∕让时间拖着∕去问候世界。
”在这种毫无矫饰的原生性淡泊情韵里,跳动的是纯真热烈的心,可以说他的童话就是他捧出的一掬蓝色的清澈透明的本真人性之泉。
他这种以孩子眼光触到的观察,正好符合舒婷在1980年送给顾城的《童话诗人》“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一个命运被污染的远方∕出发……”
(二)以女性美为生命主体的理想国
“我所渴望的美,是永恒与生命。
”(《美》)而生命的主体主要是女性。
由于顾城对女性的天然崇拜心理,所以他的理想王国核心是建立一个“女儿国”。
用他的话来说:
“永恒的女性的光辉使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有了生命,就像春天使万物有了生机一样。
”他最欣赏《红楼梦》里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因此,他也将人的世界分为女性和男性两类,女性的世界天然纯净、和谐美好,男性的世界肮脏污浊、渣滓遍地。
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写道:
“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诗中的她是顾城理想的情人,他对这种女性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性,实际是对母性的依恋,只有孩子对母亲才能产生这种近乎幼稚无理的要求和担心。
谢烨正是具有这种母性的女性,因而顾城始终像孩子依赖母亲一样,依赖着她,离不开她的呵护。
然而,顾城的女性观又是复杂的,他认为女性除了具有母性之外,还应具有女儿性和女孩性。
因此,他的女儿国中有着不同的女性,将女性分为三种:
“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
“女人性”以他的妻子谢烨为代表,温和、宽容、大度、有圣母样的慈悲胸怀,可以给他提供保护;“女孩性”以他的情人英儿为代表,活泼、任性、机敏、聪慧、充满活力、欲望强烈,能给他带来刺激和好奇心,让生活充满趣味;“女儿性”是一种由女儿体现出来的精神,清雅、性情淡泊、无欲无求,但并非女人既有女儿性,顾城本人就十分渴望女儿性,厌恶自己的男儿身,曾在《红毛衣》中表达出这种愿望及其无法实现的哀怨:
“我要穿红毛衣∥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穿着它∕在暖洋洋的草原上走∕在淡红的太阳中走∕像一团小小的火焰∥可是,我没穿∕因为∕我是个男孩子……我永远不能穿红毛衣∕我哭了∕因为永远。
”暖暖的阳光下,绿绿的草原上,慢慢地走着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这是一幅温馨而美妙的画面,“像一团小小的火焰”在顾城心中燃烧着,使他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要穿红毛衣”,可这只能是一个不能拥有的梦幻,他为他人生的遗憾而伤心哭泣。
在《英儿》中更是设想:
“我的心就是女孩子,谁碰了我的心就犯了我……我要是女孩子,一定很放肆,但也许会……没办法,他们把我的东西给人了。
他们以为是自己的呢,这个精神是我的,不能毁坏它。
”
在女儿国中,顾城描写到:
“英儿从山坡上下来的时候,我已在水边站着。
她慢慢走过来,身上穿着天蓝的裙子。
我觉得周围一切都不存在了。
”在描述雷与英儿在一起时:
“他看到她们一起行走,就好像看见了童年的梦幻。
”心中说不出一种和谐美满的幸福滋味。
基于他对女性的崇敬和热爱,在《英儿》中他作喻说:
“女孩如水”,“女孩是上天无尘的花朵”、“我怕世界把她们拿走,女孩被碰了,我的心就会发抖,因为那是我的心。
”他对女性的痴爱是对美的体验,对生命的体验。
二、生存的毁灭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哈姆雷特)属于存在型诗人的顾城,在社会陷入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的意义。
顾城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的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在这个没落的时代把对终极的目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
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考时间,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
(一)死亡的预言
顾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期待一种在雨滴中闪现的至美至纯的世界。
这样,童年的记忆培养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事物超人的敏感度,也同时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13岁的少年,却似乎已经对他作为诗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类型的诗人)的一生所难以违逆的命运逻辑有了足够的领悟:
“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虽没有死亡字眼,但幼小的心灵已明白“生命的美,千变万化∕却终为灰烬”的无奈(《美》)。
17岁时的诗歌就出现了鲜明的死亡字眼,“让死∕来麻醉∕我翻滚的心灵”(《雨》)。
此后死亡意象不断出现,“你靠着黄昏∕靠着黄昏的天空∕像靠着昼夜的转门∕血的花朵在开放∕在你的胸前∕在你胸前的田野上”(《牺牲者·希望着》),“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到来的偏偏是绝望∕……痛苦之路的终点∕决不是默默的死亡”(《歌乐山组诗》),“现在,我卸下了一切∕卸下了我的世界∕很轻,像薄纸迭成的小船∕当冥海的小波∕漫上床沿∕我便走了∕飘向那永恒的空间”(《最后》)……在顾城的生命观里,死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物”,它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仪式。
由惧怕死亡转而品味死亡,不仅在于他想借此驱逐内心对死亡的畏惧而确立的一种“生死自然”的思想,还在于他并没有把死看作简单的死,而是看成转生,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
因此,他笔下的死亡似乎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我将死去∕将变成浮动的谜∕未来学者的目光∕将充满猜疑”(《遗念》)。
长期的梦幻生活,使他分不出生与死的界限,又使他的意识常处于一种超验的状态,表现在诗中却充满灵性,有一种近乎唯心的天赋灵感,超现实的感悟力。
这种超常能力使他似乎对他的死亡早就有预感,“是的∕我不用走了∕路已到尽头∕虽然我的头发还很乌黑∕生命的白昼还没开始”的年轻生命的过早消失(《就义》),“昨天∕像黑色的蛇∕盘在角落∕它活着∕是那样冷∕死了,更不会热∕它曾在∕许多人的心上∕缓缓爬过∕流下了青苔∕涂去了血色”所描述的他死后的情景一样令人触目惊心(《昨天,象黑色的蛇》),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忧伤和绝望:
“她老在门口看了张大嘴的阳光∕一条明亮的大舌头∕在地上拖着∕早晨的死∕甲虫从树枝突然跌落”长长的舌头在阳光下拖出了早晨的死亡(《颂歌世界》),代表希望和生机的黎明消失了,世界只剩下了一片黑暗和混乱。
在《墓床》中: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冷静的叙述着死后他与自然相伴的话,他将感到很满足,而“并不悲伤”,散发出一种凄美的光,一种悲壮的力量,一种令人灵魂颤抖的痛。
一种看似歌颂死亡实则是回归自然的理想,在现实中因为难以实现而凝结为无奈和反抗的诗句:
“去死∕躺在路中间微笑∕耳朵里长出兰树枝和∕新鲜的树叶∕并且面色红润”(《布林·发现》)。
顾城对自然的欣赏本质上是对自我生命的体验。
他与自然生命同呼吸共生存,理想自然在心目中改变了面貌,他也就一步步陷入绝望境地的疯狂状态,早期灵性的诗预言也就转化成类似疯狂的诞语,只凭感官、潜意识让笔自由行走。
也许是受现代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在对死亡题材的反复描写之中,我们看到顾城诗中死亡情结日渐深重和强烈,死亡、墓地、黑色等意象语汇密集地出现,“坟墓,我知道∕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都会困扰,在灯光暗淡的一瞬∕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简历》),“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在这宽大的明亮的世界上》),后期他甚至在诗中还将死亡与杀人、自杀反复加以美化,有些描写叙述极为真切,“昨天杀了四个∕两个在卧室,两个在她身边∕你把刀给她看∕说,你要死了∕她笑,说你有八个娃娃……”(《后海》),“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城·新街口》),说明当时他已经陷入了生命的极度矛盾和冲突中,顾城的内心与外在世界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像一头困兽一样用极端丑陋的方式(死亡)来左右突出,精神上陷入崩溃和疯狂状态。
在《英儿》中,死亡更是频繁反复出现:
“我是属于死亡的,我知道……但是我并不爱它,我希望有灵魂回到我。
”“我希望能得救,不太寂寞。
”“只有在空气中,我的手没有松开,我才知道,什么是我的,全部是我的。
”所以他说:
“我要睡觉”,“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
死亡成为诗人唯一的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家,收住心灵的自由,守住宝贝。
“一起从悬崖落下去,什么都不要了。
这是最后的安宁。
”诗人对体验死亡的焦虑、痛苦和恐惧,终于回复到一种平静。
于是,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寻找返乡和回家的路,在生命的最后又呼唤儿子木耳,“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
”(《回家》)顾城“失去了土壤,失去了历史,更可怕的是他失去了激情和思考,而上述的种种一旦失去,就已注定了死亡。
”
回家也就成为他理想之翼折断后的重新选择,回家是回归故土,实质是回到生命本来的原始状态,死亡回归,“把有限的死看作永恒的生,并把死的形式烘托出神奇的光焰,让灵魂化为不朽,形成他创作的尾声——‘死亡创作’,汇同他一生的创作,构成他作品的完美结局,这种‘死亡创作’是他欣赏的美,使他能把最后的精神羽化为仙,定影为彩虹。
”
(二)死亡之因
顾城的诗作,以孩子般天真的凝望和喜悦的心理诉说,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奏响生活的乐章。
诗人在给我们以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时,却已经远离了我们,告诉了我们的期待,走向永远的不归之路,自杀了。
当我们怀念、叹息逝去的生命的时刻,我们总要说这不应该。
我们几乎是在悲痛中窒息,时不时地问:
他为什么要走,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反复为许多人(读者、学者、批评家……)所探讨,有人说是死于诗歌创作的枯竭感,有人说是死于他一向存在的轻生死的观念和对死亡美的推崇,也有人说是死于爱情的破灭,更有人说是死于斧头情结……众说纭纭。
纵观顾城诗文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顾城的死因情况。
1.人格分裂症
(1)与人、城市现实的关系
顾城写了些他称之为“心得笔记”的作品,如《凝视》、《疑惑》、《远和近》等,侧重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心理探求。
人对自然竟毫无戒心,但是对他人却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和防范。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远和近》)人与人之间,即使是亲密的情人之间,“我不会问∕你也没有说。
”(《凝视》)“你在路上∕我在路旁∕究竟有什么相象。
”(《疑惑》)这种心理状态是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造成的,人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亲朋好友、父子夫妻,转瞬间成了陌路之人。
善良的与邪恶的,正直的与奸诈的,软弱的与精明的,各自按自己的逻辑焦虑着、猜测着、苦恼着。
这种沉重的社会心理负担不会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立即消失,而将在人们心头投射下漫长的阴影。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物质需求渐渐增多,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可是对于顾城却喜欢天然的,不喜人为的。
“‘城市’在顾城看来,意味着窄狭的空间、规定好了的道路、恶浊的空气和时装包裹的灵魂,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现实中那种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机械统治力量,这种力量把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符号和代码;无论在生存还是文化的层次上都是如此。
”
“城市”似乎集中体现了工业文明一切的愚蠢和邪恶。
“我不习惯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并且写作。
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
我不能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类的坩锅,我只有负载着他们前进,希望尽快能走出去。
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
我老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
”因此,在他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诗话录》)他把自己一面现实中的人性全部投放到了桃花源式的世界中,从而,自己异化了自己的人格。
(2)诗歌边缘化后的文化失衡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诗歌曾经有着饥渴般的需求,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未来怀揣者热切的憧憬和期待,对诗歌充满着圣徒般的热情,对诗人满怀敬意。
可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商品力量的无孔不入和世界的日渐散文化,人类和诗性栖身的自然关联被无行地隔断,变轻的精神意义被金钱神话抽空了,诗歌的价值诉求也被置换成“金币写作”策略。
在物质世界、大众文化和学历教育对诗神的合力挤压下,江河等个别“坚强”的诗人,徒增悲壮的英雄感,将诗提升到理想和宗教信仰的范畴——“王者的事业”高度认识,还滋生出一种“大师情结”;大部分先锋诗人则在诗歌没落的背景下,困惑沮丧异常,这从当时民间诗刊《异乡人》、《反对》、《大骚动》、《象罔》、《厌世者》等的名字即可窥见一斑,甚至少数个体就“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权限冲击下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
属于存在型诗人的顾城,把诗作为生命和生存栖居的方式,将诗当作逃避入世纷扰的心灵堡垒。
置身于诗性消亡的语境里,顾城曾做过顽韧的抗争,期望在激流岛上构筑精神家园,逃避工业文化,怀想远去的自然之梦。
但是,被幻想宠坏的“任性的孩子”垒砌的自耕自足、夫唱妇随的天国,说穿了不过是太虚幻境。
作为执着于精神和生命意义追寻的诗人顾城,“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
而又逃避无门面临的唯一主题只有死亡,或者说只有诗人的死亡,才能成为诗歌的可能和神圣性的体现。
(3)童话的破灭
随着顾城阅历的丰富,他的人生观、诗学观发生了变化。
1980年失业,1983年结婚以后,城市的现实生活越来越使顾城感觉到无法逃避物质的束缚、城市的压迫、生存的困境,生存世界破坏了顾城心中纯净美好的天国,是生存世界砸碎了顾城童话般的诗心。
由于对现实生活陷入绝望,顾城因此似乎已经无法再行使“童话诗人”的职责了。
在理想和现实的对峙中,诗歌曾经起过调解中和作用,曾经满足了顾城避世和幻想的欲望,但现在不行了,从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颂歌世界》可以看出,底蕴反思,格调冷静,对世界充满失望甚至诅咒:
“那些容易打开的罐子∕里也有光∕内壁有光的痕迹∥忽明忽暗的走廊∕有人披着头发”(《群狼》),整首诗歌失去了往日的明丽和纯净,变得晦涩难懂,充满智性,有“罐子”、“忽明忽暗的走廊”等不祥意象。
“你登上了/一艘行将沉没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直到水手舱浮起清凉的火焰。
”(《方舟》)这里不但充满了不祥意象,甚至有作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