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原文摘抄加赏析水浒传摘抄加赏析.docx
《水浒传原文摘抄加赏析水浒传摘抄加赏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水浒传原文摘抄加赏析水浒传摘抄加赏析.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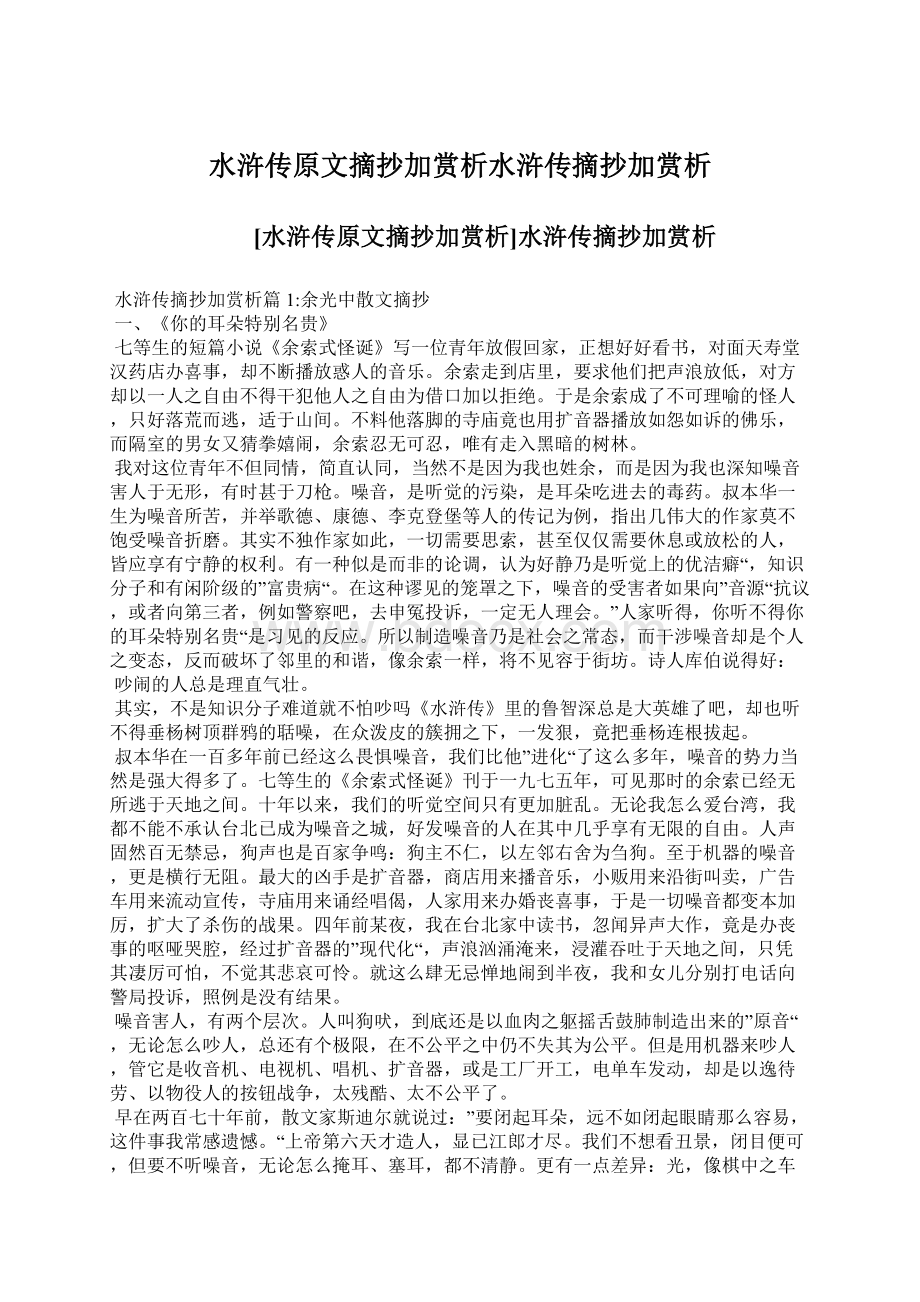
水浒传原文摘抄加赏析水浒传摘抄加赏析
[水浒传原文摘抄加赏析]水浒传摘抄加赏析
水浒传摘抄加赏析篇1:
余光中散文摘抄
一、《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
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
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
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
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
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
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
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
”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
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
诗人库伯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
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
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
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
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
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
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
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
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
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就说过:
”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
“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
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
更有一点差异:
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
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
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
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
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
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
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
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
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
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二、《三间书房》
小说大家吴尔芙夫人生前有个愿望:
但愿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那当然是指书房。
对比之下,我一人拥有三间书房,而且都在楼上,应该感到满足。
当然,这三间书房并不在一起。
第一间在厦门街的老宅。
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幢古屋,它早已拆掉改建了。
目前的老宅也已有了十五年的风霜。
我的书房在二楼,有十二坪之宽。
当初建屋,这一间就特别设计,所以横亘二十五尺的墙壁全嵌了书橱,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一眼望去,卷帙浩繁,颇有书城巍巍的气象。
这么宽敞的书房,相信一般人家并不常见。
比我阔的人太多了,但是绝少阔人会把这么阔的房间拿来当书房。
所以刚搬进去时,我委实踌躇满志了一阵子。
不过得意了没有几年,就像台湾的人口一样,这书城的人口也迅告膨胀。
幸好不久我就来了香港,六百册书随我一同西来。
书城的人口压力暂时稍减。
我在沙田山居的书房,只有厦门街的这间一半大,可是一排五扇长窗朝西,招来了对海的层层山色,和我共对一几。
所以这间书房,这临海的高斋,室虽小而可纳天地,另是一番气象。
人迁之初,架上的六百册书疏疏落落,任其或立或倚,一副政简讼清的样子。
照例闲不了多久,新的图书杂志,各有各的身材、身价、身世,从四面八方盲目地投奔而来,于是这小小书城的人口很快地就饱和如香港的人口。
终于我不得不把走投无路的书刊,一叠又一叠,陶侃运甓那样,搬去我的办公室。
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在太古楼的六楼,位于长廊尽头。
这六楼已是绝顶,我的房间又在绝顶的绝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在门外过路。
绝对的安静归我一人独享,简直是耳朵的放假。
临窗俯眺,半里之外的斜坡道上争驶着小轿车和长长的货柜车,看不尽多少的长安道上客。
我却高高坐着,像尼采,像宙斯在奥林匹斯之巅。
教授的办公室其实也就等于书房。
不要多久,这第三书房也书满为患。
于是又把无处安顿的书一批批运回家去。
我的办公室在太古楼,静寂亦如太古,这清福实在修来不易。
以前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位于碧秋楼二楼,正当梯口,又隔着走廊与教师的联谊室斜斜相对,既扼要冲,自为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门外总是笑语喧阗,足音杂沓,不时更有人在长廊的两头此呼彼应,回声不绝,或是久别重逢,狭路相遇,齐发惊叹。
长廊未半有女工坐守柜台,别处的女工不时来访,印证了广东人的一句话:
”三个女人一个墟“。
再过去是厕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同事们出入其门,少不了又有一番寒暄。
从那里搬到太古楼来,简直是听觉的大赦。
水浒传摘抄加赏析篇2:
余光中散文笔记摘抄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
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
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
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
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
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
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
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
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
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
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0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牙,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
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
韩黎诗:
“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1华兹华斯诗:
“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
”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
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
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
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
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
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
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
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舶。
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
”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
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
诗人库伯说得好: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
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
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
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
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
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
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
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
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
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就说过:
”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
“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荆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
更有一点差异:
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
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
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校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
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
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
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眩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
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
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
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剩。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
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
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改装的旅馆里,为“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
晓寒袭人,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
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
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
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
西欧的旅馆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
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
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
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保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
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
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
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
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
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
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
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
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
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
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
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开车,一路又干又热,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
可是那是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
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
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
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桑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
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古桥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
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
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
从我一夕投宿的鹰头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
“Inmethetigersniffetherose。
”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
“好一处蛮荒的所在!
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1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
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
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
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
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
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
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
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
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
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上,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为之“绝倒”。
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
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
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
”又是何等境界!
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
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
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
“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
”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
“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
”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
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