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例.docx
《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例.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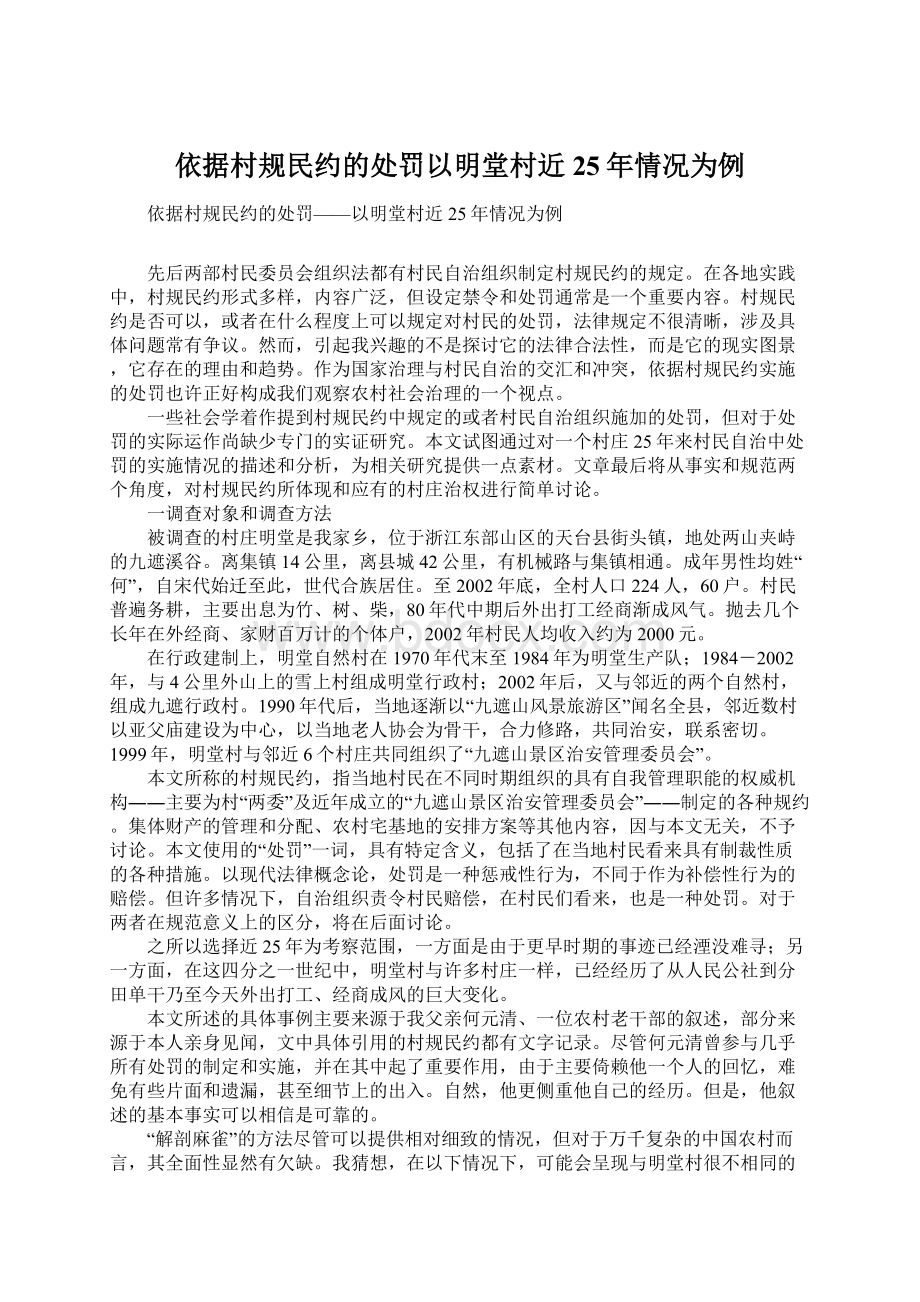
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例
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以明堂村近25年情况为例
先后两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有村民自治组织制定村规民约的规定。
在各地实践中,村规民约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但设定禁令和处罚通常是一个重要内容。
村规民约是否可以,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规定对村民的处罚,法律规定不很清晰,涉及具体问题常有争议。
然而,引起我兴趣的不是探讨它的法律合法性,而是它的现实图景,它存在的理由和趋势。
作为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交汇和冲突,依据村规民约实施的处罚也许正好构成我们观察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个视点。
一些社会学着作提到村规民约中规定的或者村民自治组织施加的处罚,但对于处罚的实际运作尚缺少专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村庄25年来村民自治中处罚的实施情况的描述和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素材。
文章最后将从事实和规范两个角度,对村规民约所体现和应有的村庄治权进行简单讨论。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被调查的村庄明堂是我家乡,位于浙江东部山区的天台县街头镇,地处两山夹峙的九遮溪谷。
离集镇14公里,离县城42公里,有机械路与集镇相通。
成年男性均姓“何”,自宋代始迁至此,世代合族居住。
至2002年底,全村人口224人,60户。
村民普遍务耕,主要出息为竹、树、柴,80年代中期后外出打工经商渐成风气。
抛去几个长年在外经商、家财百万计的个体户,2002年村民人均收入约为2000元。
在行政建制上,明堂自然村在1970年代末至1984年为明堂生产队;1984-2002年,与4公里外山上的雪上村组成明堂行政村;2002年后,又与邻近的两个自然村,组成九遮行政村。
1990年代后,当地逐渐以“九遮山风景旅游区”闻名全县,邻近数村以亚父庙建设为中心,以当地老人协会为骨干,合力修路,共同治安,联系密切。
1999年,明堂村与邻近6个村庄共同组织了“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
本文所称的村规民约,指当地村民在不同时期组织的具有自我管理职能的权威机构――主要为村“两委”及近年成立的“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各种规约。
集体财产的管理和分配、农村宅基地的安排方案等其他内容,因与本文无关,不予讨论。
本文使用的“处罚”一词,具有特定含义,包括了在当地村民看来具有制裁性质的各种措施。
以现代法律概念论,处罚是一种惩戒性行为,不同于作为补偿性行为的赔偿。
但许多情况下,自治组织责令村民赔偿,在村民们看来,也是一种处罚。
对于两者在规范意义上的区分,将在后面讨论。
之所以选择近25年为考察范围,一方面是由于更早时期的事迹已经湮没难寻;另一方面,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明堂村与许多村庄一样,已经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单干乃至今天外出打工、经商成风的巨大变化。
本文所述的具体事例主要来源于我父亲何元清、一位农村老干部的叙述,部分来源于本人亲身见闻,文中具体引用的村规民约都有文字记录。
尽管何元清曾参与几乎所有处罚的制定和实施,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主要倚赖他一个人的回忆,难免有些片面和遗漏,甚至细节上的出入。
自然,他更侧重他自己的经历。
但是,他叙述的基本事实可以相信是可靠的。
“解剖麻雀”的方法尽管可以提供相对细致的情况,但对于万千复杂的中国农村而言,其全面性显然有欠缺。
我猜想,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呈现与明堂村很不相同的图景:
一是村庄内人口众多而又构成复杂,势立分化乃至对立的;二是集体经济发达并为村民依赖的;三是城市近郊,村民利益独立,关系松散的等等。
在上述情况下,需要另行调查研究。
二处罚依据及其制定
自治组织的处罚一般以事先制定并公布的村规民约为依据。
通常,不会以没有事先公布的规约作为处罚的依据,哪怕被处罚行为是国家法律明确禁止的。
但在个别情况下,对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具有公共危害性的行为,即使没有村规民约规定,由村民自治组织给予处罚也并非不可思议。
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规民约应当由村民大会制定。
但该村历次制定的村规民约从未提交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习惯做法是由“村干部”制定。
通常由村主要干部提出动议,并事先拟好草稿,与会人员可能对草稿提一些补充、修改意见,讨论中一般争论不大。
在当地,村干部的范围一般指村委会成员和村党支部成员,即“村两委”。
有几次,还请下列人员参加:
党员、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人大代表、老人协会会长、村民代表等。
这时,可以算是“两委扩大会议”了。
从实际看,只要具有足够权威,“村两委”讨论决定就可以,邀不邀请其他人完全在于“村两委”的自愿。
自1984-2002年,明堂行政村村委会、党支部由明堂和雪上两个自然村共同选举产生。
但在内部事务管理上,明堂自然村几乎完全独立,尽管有时借用村委会、党支部名义。
除了本村干部独立制定的禁令,近年还出现了几个相邻村庄联合制定的“联防公约”。
1999年5月30日制定的7村“联防公约”,在序言中声明“经七村两委及各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但事实上并没有各村村民代表会议开会讨论。
我看到的只是加盖7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打印件。
“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成立后,在维护治安和实施处罚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2000年5月20日,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发出“通告”:
“近日天气久晴干燥、河水干涸,本治安管理委员会重申:
坚决执行上级有关指示和七村联合公约,对在景区内烧山、捕鱼的予以严厉打击,决不轻贷。
望景区人民共同配合,及时举报。
”通告盖有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公章,在管委会前还署上街头派出所,但没有盖章。
制定村规民约的另一个推动力来自政府。
在搞所谓“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新农村建设”等运动中,在抓计划生育工作中,乡镇政府或者县政府有关部门总是自上而下地要求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
有时,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还提供村规民约的范本供各村参考。
例如,《明堂村计划生育处罚办法》就是根据镇政府的要求制定的。
又如,天台县公安局在1994年印发该村的《治保会工作制度与规范》的小册子里,就有村规民约的范本,并注明“供参考,请结合实际情况修订”。
值得注意的是,该范本中含有处罚的内容:
“违者视其情节轻重、态度好坏,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经济处罚,直至移送上级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1999年的7村“联防公约”,就是在派出所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
该联防公约序言也声明“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下”制定。
至于2000年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禁止烧山、捕鱼的通告,更是依仗了“上级指示”和当地派出所的权威。
村规民约讨论通过后,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公布。
1990年代前,最常用的形式是在放电影、开社员大会等场合口头宣布。
我小时候,还见生产队长在村庄各个道地边走边喊某项禁令,偶尔还停下来向某个没听清楚的社员解释一下。
有件事特别能说明禁令公布方式的非正规:
有一次,禁令制定后,待
放电影时宣布,但到放电影那天,因村长有事外出,禁令由村长老婆、一位泼悍的妇女代为宣布。
尽管有人讥笑“其他村干部哪里去了?
”,但没有人质疑禁令的有效性。
近年来,电影不放了、村民会议也很少开了,村规民约更多靠书面方面公布。
简单的,在村口挂一块木板,歪歪斜斜地写上“禁止挖笋,违者罚款”。
那个“联防公约”、“通告”都是用大号字打印后张贴的;《明堂村违反计划生育处罚办法》是用油漆写在墙上,以郑重其事。
最郑重的,可能数“联防公约”禁止捕鱼的规定,它被刻在石碑上,石碑树立在九遮景区入口处路边。
当三年一届的村委会改选后,新上任的村委会成员常常发动对原有禁令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一个。
这使得25年来,村规民约被多次制定、修改或重申。
现在已说不清楚到底制定过几个村规民约。
虽然村规民约从不明言其有效期限,但很难想象,新一届村委会会援引以前村委会发布的禁令实施处罚。
三禁令的内容
事无穷而令有限,禁令只能针对常发的危害行为作简单的规定。
从各种禁令的规定和实际处罚的情形看,给予处罚的主要有盗窃、赌博、斗殴、诽谤等治安问题。
禁令也涉及违反计划生育、违章建房这两类乡镇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明堂村违反计划生育处罚办法》,对非法多胎生育规定了最高3000元的罚款。
从实际执行看,处罚得最多的是盗窃,共20多起;赌博、斗殴、诽谤等都只有个别例子;至于违反计划生育和违章建房,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从未处罚。
被处罚的盗窃行为绝大部分是盗窃村民集体财产,盗窃个人财产,发生的少,被处罚更罕见。
盗窃集体财产又以盗窃集体所有的竹笋树柴为主。
这与该村地处山区,竹笋树柴是当地主要财产和收入来源有关。
90年代初一条禁令规定:
“偷毛竹一株,罚20元,竹归原主;已卖,加20元。
”
随着当地日益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村民环保意识增强,近年开始出现了禁止捕鱼、烧山等保护自然环境有关的内容。
1999年5月30日,7村制定“联防公约”,是我看到内容最为全面的一个禁令。
全文照录
“为加强社会治安,维护景区秩序,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下,经七村两委及各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特制定本公约:
1、不论何人在景区寻衅滋事不听劝阻者,造成后果的除赔偿损失外,扭送公安机关处理。
2、进入景区应增强防火意识,严格野外用火,如用火不当,乱丢烟蒂、火柴头、放爆竹等引起山林火灾,根据情节轻重,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送交公安机关或其它有关部门处理。
3、景区林木严格保护,如在景区内砍伐林木每株口径在10公分处以50-100元赔偿,口径在10公分以上处以100-500元赔偿。
4、不准在景区内损坏建筑物、财物、花草,违者视情节轻重处理。
5、景区内溪坑不许毒鱼,违者处以环境污染赔偿500-1000元,对电鱼、网鱼及其他捕鱼没收渔具,情节严重的处经济赔偿。
6、严禁赌博,不听劝阻者报公安机关处理。
7、七村联防可以协助各村对重大民事纠纷、山林纠纷共同协商处理,如处理不了按有关规定移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8、本公约经何村、溪地、遮山口、道蓬岩、桐桥、东江、明堂等七村联合制定,敬请广大村民及外来游客共同遵守执行为盼。
“
村规民约针对的处罚对象既有本村村民,也有邻村村民,甚至外乡镇的人。
7村“联防公约”的内容,明确显示了这一点。
邻镇一位医院院长的儿子,就曾因违禁捕鱼被罚款。
相反,本村村民在外地“犯法”,本村并不过问。
这一点体现了村规民约效力的“属地主义原则”。
1980年的一起事例显示“属地主义原则”得到普遍尊重。
邻近的祥和公社白泥坦生产队社员夏××盗伐明堂生产队林木,明堂队干部赴祥和公社,请求公社及白泥坦队干部协助处理。
白泥坦队干部偏袒夏××,主张按该队规定处罚,但公社干部表示:
“事情出在那边,就按那边规定办。
”事情按此获得解决。
运用最多的形式是罚款。
罚放电影也曾是常用的处罚方式,即请公社电影队到村放电影,由被罚的人负担电影费。
偶尔,被处罚的人还被责令在电影场上当众表示悔过。
有一次处罚形式比较特别:
有一处集体林木被成片盗伐,社员怀疑是生产队长暗中允诺别人砍伐以中饱私囊,该队长矢口否认,于是众人决定,买菜杀猪办酒席,全队每户派一人吃一顿,以后查明是谁干的就由谁负担酒席费用。
结果是那位队长自食其果。
总之,处罚的形式并不完全固定。
但是25年来,没有发生过游街、拘禁一类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四处罚的实施
形式上,处罚通常由村“两委”研究决定,其他干部也可能被召集参与决定;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现在也成了一个处罚主体。
乡镇政府官员对依照村规民约所作的处罚持支持态度。
遇有村干部难以对付的情形,还可能下村亲自参与,或者把违反禁令的人传唤到乡镇政府做工作。
1988年,明堂村发生多个村民偷伐集体所有的“样山”柴事件,乡干部驻村数天,参与调查处理,最后以“村两委”名义决定收缴盗伐的柴并罚款。
在处罚涉及附近乡、村的村民时,如果证据确凿、处罚合乎情理,该乡、村干部也能提供协助。
前述对白泥坦生产队夏××的处罚便是一例。
有时,村民群众的舆论也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述对那们生产队长的处罚方式,几乎是在一片起哄中决定的。
整个处罚决定的作出过程,形式上似乎是村民自治组织单方的举动,但有时更象是双方交涉的结果。
偶尔也有弄得面红耳赤,喉大声粗,甚至手脚相向,但总得来说,是平和的、讲理的。
1988年邻村一位“小青年”偷伐明堂村两株树。
开头他矢口否认。
当明堂村干部拿出他家的斧头,与他一起上山核对树桩上留下的砍痕后,他还抵赖,只承认偷了一株。
何元清恼怒之下,煽了他一耳刮,厉声质问:
“到底几株?
”这位“小青年”才全部认债。
最后,他自动送回了偷伐的树木,并按要求交了几百元现金作为罚款。
另一个例子是,几个当地人在村边溪坑上夜里用鱼网捕鱼,被参与“联防公约”的道蓬岩村十几个“小后生”抓住,第二天在亚父庙“讲事”,管委会几位主要干部参与。
一名偷鱼者亲自开着摩托车把何元清接到亚父庙。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鱼网没收,罚款60元,但没有加收村干部的误工费。
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收到的罚款,通常交给设在亚父庙里的当地老人协会。
处罚的实施具有很大灵活性。
村干部除了要维护禁令的严肃性和自身权威,维护公共秩序,较多地考虑村民群众的舆论,照顾各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村规民约对罚款数额有规定的,一般照章办事;没有规定的,临事而定。
前述镇医院院长的儿子用电瓶捕鱼,罚了20
元。
这个数额虽有人情因素,倒也不算“法外开恩”。
但即使有规定的,也可能临事而变,不拘规定。
例如,1995年两位村民偷伐集体山上的柴,被卖掉的柴梗整整一拖拉机,念其及时坦白,又考虑到他们家境贫困,只罚了100元-这个数字还抵不上柴梗的价值。
尽管这与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相差甚远[10],但在村干部看来,已经对他作过处罚了,已足够儆戒效尤,村民们也没有太多意见。
另一方面,对盗伐林木之类行为,犯者本人拒不承认,罚款额中则可能还要加上村干部为此调查、处理的误工费。
处罚决定作出后,基本能够得到执行。
对于本村村民,罚款大多是从年终分发的集体收入分成或者本人应得的其它款项中扣除。
对于外村村民,则要求交纳现金。
25年来,没有发生过强行扣押、变卖被处罚人财产以抵缴罚款的事。
当然,碰到棘手事情,还得由政府机关出面。
当地一所小学窗玻璃被砸,管委会认定是该村的何××所为,要求赔偿,何××拒不承认,还顶撞、辱骂管委会人员。
有意思的是,当被惹怒的管委会人员何元清要扭送他去派出所时,他立刻说:
“不用抓,我自己去。
”他果然跟着去了。
在派出所,他被关了两天,赔了100元。
五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何以存在?
尽管我们可以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组织处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是,目前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一现象,仍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6年前,当我着手调查并撰写本文初稿时,我曾断言并猜测:
“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处罚,在维护明堂村社会秩序方面仍有一定作用,但其实施频率、合理性和有效性正在下降。
是否会有一天,被处罚的村民因不服处罚而提起诉讼,对处罚的合法性进行挑战?
抑或在那一天之前,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悄悄地消失?
”但是,直到今天,我仍没有看出这种迹象。
确实,这25年来,明堂村变化很大。
原先集体经济的存在,不但加强了村民对社区的依赖,而且使处罚的执行更加方便。
80年代初,因地“包产到户”,以后又落实了自留山、责任山。
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瓦解,集体经济不再是村民收入主要来源,目前已近乎于零。
[11]相应地,约在80年代中期以后,村民纷纷外出做工、经商,并有增无减。
[12]对相当部分家庭来说,外出做工、经商的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这样,村民对集体的依赖性和集体对村民的控制大为减弱。
对于一个长年在外谋生或者说只要愿意就可以长年在外谋生的村民,都更容易与村庄自治组织的处罚决定“作对”。
在此情况下,对于拒不接受处罚的人,村民自治组织可能运用的手段非常有限,往往不得不由政府依法制裁。
与此同时,几年内,当地村庄架设了电话线路,扩建了到集镇的公路,每天有几辆私人运营的小客车往返集镇,交通、通讯大为方便。
可以设想,一旦发生治安案件,警察可以在半小时内赶到。
但是,政府管理能力在技术上的加强并没有导致村民自治组织处罚的消失。
近几年,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这个跨越村庄的自治组织,使一度减少的处罚重新在当地重新活跃起来。
“联防公约”宣布后,管委会处罚了不下5起捕鱼事件。
原因可能在于,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确实有助于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
该村离集镇有14公里之遥,距离导致政府管理力量在该村趋于相对薄弱,对治安案件、民间纠纷的调处有“远水不解近火”之感。
而且,镇政府、法庭、派出所人员、精力有限,管辖事务繁多,对于一般盗窃、赌博、斗殴等案件往往无暇顾及。
村民自治组织起到了填补政府管理力量不足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政府职能,减轻了政府负担。
政府官员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持肯定和支持态度,有意识地把村民自治组织的调解、处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第一道防线”。
针对当地的自治管理,镇领导、两任派出所所长都曾多次表示赞赏:
“我们省心多了,平常去都不用去。
”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之所在能够实施,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政府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显示了支持、鼓励的态度。
这使得村规民约获得官方的认可,增加了权威性。
九遮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设立后,街头派出所为支持其工作,还在当地的宗教活动中心亚父庙设立了“警务工作站”,还一度每月初一派人值班。
县公安局领导曾莅临挂牌,当地电视台也予以报道。
“街头派出所警务工作站”和“九遮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赫然并立,昭示着管委会的权威。
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当一个违法行为业经村民自治组织作过处罚,对政府而言纠纷已经解决,政府就不再处罚。
这使得村民自治的处罚获得准官方的效力。
如果一个违法村民拒不接受村自治组织的处罚,那么他可能受到政府依照法律作出的更为严厉的处罚。
权衡利害,违法的村民自然更愿意受村里处罚了事。
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能够被执行,还取决于村民群众乃至被处罚人本人对村庄公共权威的认同。
明堂村在传统上是一个宗族,族长对于违犯族规的行为具有一定惩罚权。
对非官府处罚的认同,也许积淀在村民的集体意识当中。
随着宗族自治转换成村民自治,族长的惩罚权转换成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权,也许在村民看来是一件自然的事。
除了传统的强大惯性,现实的生活状态也减少了处罚实施中的对抗因素。
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世代生活于此的熟人社会,周围的舆论、自己的“面子”非常要紧。
违犯大家认同的禁令,如果拒绝接受处罚,无疑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
尤其是,盗窃等不光彩的行为被发现后,被处罚人很少抵制。
25年来,没有一个村民因对处罚不服而向政府申诉,或者到法院告状。
何元清说,他多次“做恶人”,罚了人家,但除了个别,并没有积下仇怨,反而有个被处罚的人事后还表示钦佩。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能够得以实施,还取决于村主要干部的决心和技巧。
当违反禁令或者其它应当处罚的事发生以后,是否给予处罚,村主要干部的权威和意志往往起决定作用。
前述对两位参与赌博的村干部的处罚,就是在村主要干部极力主持下作出的。
如果村庄缺乏“强人”,或者主要干部不够强有力,就可能罚不了,甚至干脆听之任之,村规民约因此成为具文。
这一点也导致村规民约缺乏连续性,完全可能人换政息。
另一方面,村干部对处罚尺度和火候的掌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明堂村历次处罚规定,从情形和幅度上,都在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象有些地方规定的那样极端,如“猪、羊在地里吃青,打死不赔偿”,“偷摘他人龙眼、荔枝一粒,罚款100元”,“违反计划生育,3年不给落户口、不给分田地”。
即使根据“上级”布置,郑重其事写在墙上的“超生子女罚款3000元”云云,村干部们实际并不当回事。
在具体实施处罚时,也是该硬则硬,该轻就轻,见好就收,免得自己也下不来台;实在处理不了就送交派出所,或者让当事人上法院解决。
国家法律的默认、当地政府的支持、社区“强人”的活跃,共同支持起明堂和邻近村庄村民自治的事业。
在可预计的将来,村民自治组织实施处罚,还将在这些山村演出。
与之同时,实施处罚的情形和形式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某些处罚从数量上趋于减
少。
前面曾指出,盗窃竹树曾是导致处罚的最主要违禁情形。
随着社会开放,谋生手段多样化,村民经济收入提高,盗窃案件大幅度下降,处罚相应减少。
统计明堂村25年来发生的总共20余起处罚,大部分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中期后,除了对违禁捕鱼的处罚,已多年没有发生。
其次,有些处罚,象责令违犯禁令的人在电影场上当众表示悔过的处罚方式,在今天已不可思议。
六村规民约与村庄治权
下面分别讨论村规民约所体现的村庄治权,以及它在法律上的限度。
村规民约所体现的国家法律与村庄秩序的关系,是政治、社会学者一个关注的话题。
张静教授曾从国家法与习惯法、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管制秩序关系的视角,讨论了村规民约与村庄治权。
她把各地乡规民约的实践理解为,“两个性质上非常相似的管制规范,竞争各自的管辖地位和范围,力图加强自己治权”。
她认为,就常规事项而言,国家法律没有改变以习惯法为依据的地方管制秩序。
[13]
在明堂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中,我们确实看到村民自治组织所享有的村庄治权。
说它是一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自治组织的处罚由村庄干部主导,而不是村庄干部与被处罚人平等商谈的结果。
当一起事件发生,村庄干部不但是当事人,还是仲裁者,身肩二职。
虽然实施的处罚以被处罚的村民和外村人接受告终,但不是每一个人对处罚都心服口服,而可能多少慑于村干部的权威。
这种村庄治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一方面,它相对独立于村民。
在明堂村的经验中,虽然所制定的村规民约基本上体现村民愿望,但其制定程序上并非由村民会议讨论。
村干部实施处罚,尽管他们不可能不考虑社情民意,但主要出于其主动性。
另一方面,村庄治权也相对独立于国家法律和地方政府。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权,本来不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授予,似乎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和修改没有多少关系。
村干部对政府推销的不符合当地需要的文本,仍然可以虚以委蛇;而对符合自己胃口的法律、法规,乃至不清楚具体内容的“上级指示”,则实行“拿来主义”。
是否移交给政府处理,村干部决定也有很大的自主权。
政府对村庄干部已经解决的案件,通常予以默认,也不再施加处罚。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了村庄治权相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以及村庄管制秩序对国家法律秩序的抵制。
虽然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在明堂村源远流长,但没有形成清晰、牢固的习惯法,更没有村民自治组织专属、政府不能干预的权力领地。
虽然政府提出的一些口号或推销的村规民约文本并没有被村民自治组织不折不扣地实施,但政府有时提出一些口号,并非执意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去落实,很大意义上只是做宣传,甚至做样子。
虽然政府会默认村民自治中某些不完全符合他意愿的行为,但政府并没有失去对全局的掌控。
我们可以设想,那些违背政府意志的处罚很难实施,更无法长期存在。
相反,正是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符合国家治理需要,政府才对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予以支持。
通过把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有效地纳入其治理体系,政府省心却有力地维持着当地的秩序。
至少在本文的视野内,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管制秩序的明显冲突。
相反,国家政权已经成功地伸入到明堂这个偏僻的山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治理的延伸。
虽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观念等多个角度解释村庄治权的存在,我更愿意强调它对基层政府、村庄干部乃至一般村民的现实好处。
从根本上讲,一定范围的村庄治权对各方来说是互惠的。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在当地起到了凝聚社区团结和加强社区安定的作用,不但帮助了政府管理,甚至还能够为政府官员“贴金”。
同时,地方精英们在积极参与当地治安管理、调处民间纠纷的过程中,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和成就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变得更密切。
与其他村庄相比,明堂以及九遮山诸村获得政府更多关注和支持。
当明堂村准备推倒大部分房屋,重新规划时[14],政府打破一村一年一张“屋基表”的惯例,通过村干部给所有建房户统一办理了“屋基表”。
这种互惠有时也意味着资源的交换。
政府不但对当地村干部移交的案件会更加重视,还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