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教授访谈录.docx
《田国强教授访谈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田国强教授访谈录.docx(3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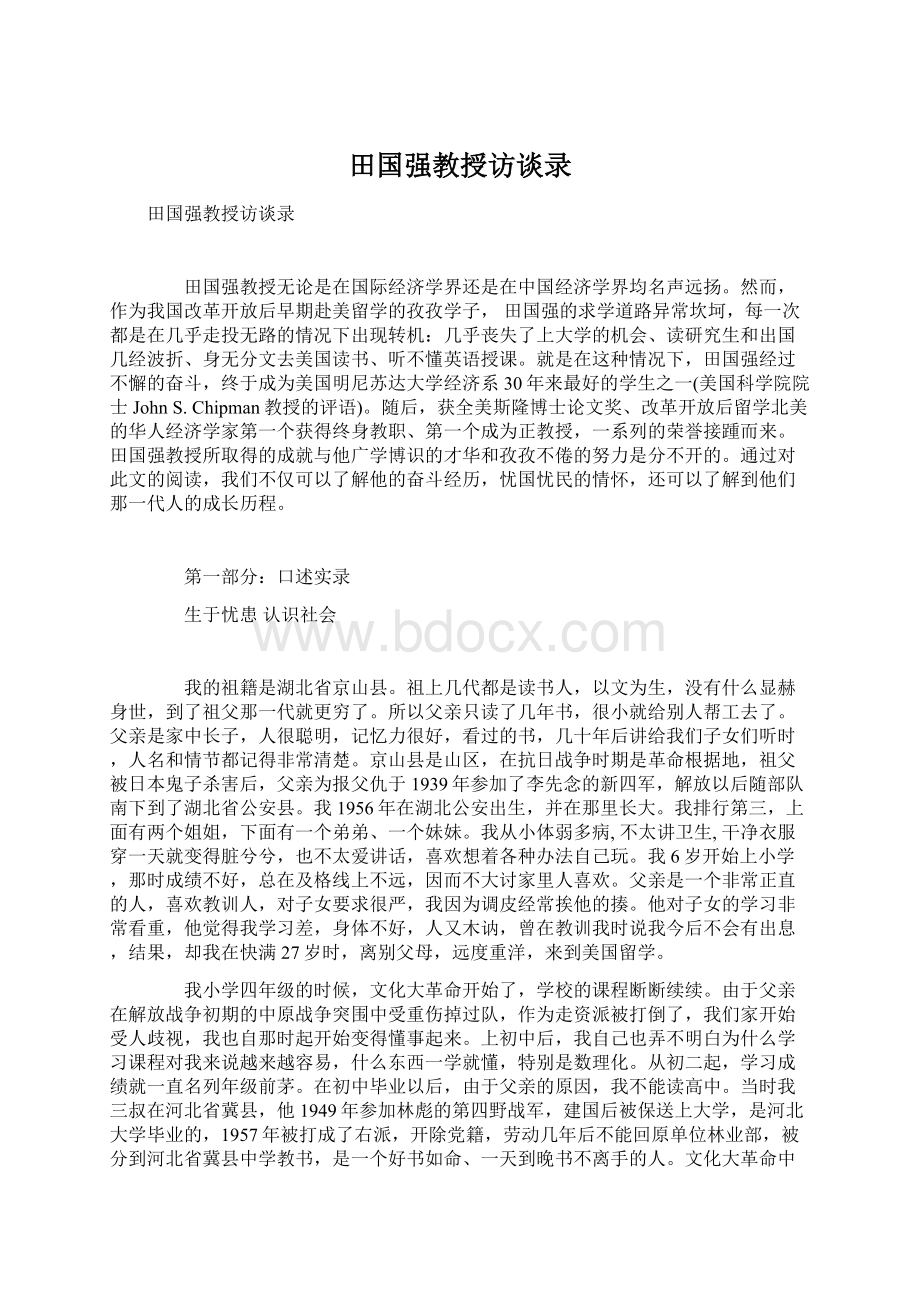
田国强教授访谈录
田国强教授访谈录
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
然而,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每一次都是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现转机:
几乎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读研究生和出国几经波折、身无分文去美国读书、听不懂英语授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田国强经过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年来最好的学生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S.Chipman教授的评语)。
随后,获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
田国强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广学博识的才华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通过对此文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的奋斗经历,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以了解到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第一部分:
口述实录
生于忧患认识社会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
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穷了。
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很小就给别人帮工去了。
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
京山县是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解放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县。
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
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从小体弱多病,不太讲卫生,干净衣服穿一天就变得脏兮兮,也不太爱讲话,喜欢想着各种办法自己玩。
我6岁开始上小学,那时成绩不好,总在及格线上不远,因而不大讨家里人喜欢。
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喜欢教训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我因为调皮经常挨他的揍。
他对子女的学习非常看重,他觉得我学习差,身体不好,人又木讷,曾在教训我时说我今后不会有出息,结果,却我在快满27岁时,离别父母,远度重洋,来到美国留学。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
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
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
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
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
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
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
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
77年高考恢复后,77至78届大学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
由于自己小时候老实,受人欺负,文革中又遭受歧视,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人也开始变得调皮和活跃起来,很快在同学中有了威信,也常爱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的事情。
1974年我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
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
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近三年。
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
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
刚下乡时我最怕一个人在夕阳下度过,阳光斜射下来,给人一种惨兮兮的样子。
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
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
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
我们知青队的一个知青可以将锄头拿在手中几个小时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没有这个耐心,在这点上,我真是佩服他。
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
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结果,我所下乡的地方一天的报酬只有三、四毛钱,有的地方甚至更穷,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一年下来几乎家家超支。
每天劳动的时间也特别长,一天至少十二小时以上,赶上农忙、赶插稻谷时,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平时也没有肉吃,我曾经半年没有吃过肉。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我用小时候练出来的弹弓手艺,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斑鸠,一晚能打到好几只斑鸠和知青战友们分享。
干体力活,饭量变得很大,每餐八两,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米。
不过,我的体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壮,一般农民也没有我的力气大。
我记得在为我们知青队建房时,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块的红砖70多块走百米左右,没有这么结实的扁担,只能用胳膊粗般的树棒当扁担。
我还学会了干许多农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担子。
那时为了图表现,其中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尽管我下乡地方离县城不到100里。
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学二年级,才戒掉吸烟。
也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
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
我现在作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的非常融洽。
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
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
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求学路上历经坎坷
当时我虽然有读大学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困难很大。
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取决于你是否根正苗红。
那时已经有了不正之风,看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领导的子女。
刚打倒“四人帮”后不久院校开始招生,但极左的风气还很浓,正处在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峰。
对所招工农兵大学生今后出路的政策是“队来队去,社来社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个人如果是从生产队(或公社)进大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回到生产队(或公社)去。
结果,很多有关系的、父母亲有权势的就没有报名上大学,这却增加了我上大学的机会。
我当时想:
即使上大学后让我回农村,我也愿意。
我觉得即使种田也需要科学知识,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就是自己的了,况且说不定今后形势还会发生变化呢。
父亲那时还没有解放,对我能上大学的事不看好,但母亲对我想上大学的愿望非常支持。
母亲为我的事上下奔走,向人求情,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
但让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很难实现的事。
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父亲原来的下级、母亲的同事,加上我下乡的表现也很不错,于是大队、公社同意推荐我上大学,没有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中专-----湖北水利电力学校。
后来那个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却又不招生了,连中专也上不成了。
这次招生事件对我打击较大,知青队的人都被招生或招工走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平时热闹非凡的知青队那时显得异常的冷落,使人感到非常寂寞和心情低沉。
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我对上大学的事已不抱希望、心灰意冷。
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个月以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师资班。
朱校长是武汉大学英语系大学生,抗战时奔赴延安,是延安抗大出身的老干部。
朱九思老校长是一位非常有眼光,有气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认为,如果由他当中国的教育部长,中国现在的教育可能更上一层楼。
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就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中国出现,认识到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致力于将华中工学院办成中国,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
所以他求才若渴,大量收揽人才和培养师资。
华中科技大学现在许多教学和科研骨干都是文革后在朱校长亲自过问下一个个调进学校的。
招师资班就是他当时的一个举措。
当年华中工学院特招了数学、物理、机械、电力和政治五个师资班。
并且不象73年以后招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在全国恢复高考之前,朱校长又首先想到让华中工学院出试卷对推荐进师资班的知青进行数学和语文两门考试。
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去见县教育局的一位潘局长,他很同情我没有入学的处境。
正好有这个机会,潘局长便向华中工学院招生的人推荐了我。
时间很紧迫,我接到通知后,只复习了一天就参加了考试,结果数学考了满分,语文也得了很高的分。
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原因,华中工学院去招生的老师开始不想要我,潘局长对他说,就只有他了,我们不推荐其他人选。
于是招生老师将情况上报学校,经学院党委集体讨论同意后,我终于被招进了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
接到入学录取通知的那天,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这是我在求学路上,历经坎坷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苦下功夫打好基础
我们师资班的同学是77年5月进校的,比同级学生晚了大半年。
我在华中工学院的物理师资班呆了两三个月,由于一次数学考试,成绩还不错,于是将我换到数学师资班,当时我非常地不情愿,因为我从小的愿望是当科学家。
我感觉人的命运有时真的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巧遇或历史误会,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变更,都不会是今天的我,瞑暝天意中,似乎总有人在指引我的人生道路。
比如差一点上不成大学,比如专业的转换。
最后的转换专业造就了今天的我。
如果当时我学物理,将来可能有机会做一名物理科学家,但我便不会有机会师从林少宫教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也说不定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刚进大学的时候,头一年我不是非常用功,在班上成绩也只能算中上。
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古典小说,可下面县城这样的小说不多,所以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从校图书馆借的各种世界名著。
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觉得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只有那些已做了许多研究的人才能有资格当研究生,才考得上,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
后来,我们班上两位同学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对我触动很大。
我想别人能考上,我也能考上。
当时我们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教的东西相对简单。
于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改邪归正”,不再整天看小说,并制定了自学计划,规定自己每周自学60个小时。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学习计划。
相当于上午上完课后,每天要自学8个半小时以上。
在随后的一年中,我没有了节假日和周末,也取消了睡午觉的时间,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同学的睡眠,有时我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那年春节也没有回家,人一下瘦了很多。
我自学了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许多数学教材,象菲赫金哥尔茨八卷的微积分教程和复旦大学文革前出版的数学分析我就至少看了十遍以上,吉米多维茨5000道数学分析习题集也做了几遍,并且把文革前各个大学历年数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弄来反复做。
这段学习经历,为我的数学基础、逻辑分析能力及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即使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记得数学分析中几乎所有定理的证明。
一年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
我当时的理想是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
当时是一个人才空档,非常优秀的人已经在78年考上研究生了,77级大学生才进校一年多,我认为自己考上的机会还是较大的。
可是朱九思校长非常爱才,当知道我班上两个同学7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后,批评系领导不该批准他们考外校研究生。
结果华工就卡着不放他们走,直到他们在武大读完研究生后,粮食、人事关系也没有转到武汉大学去。
由于这个事件,朱九思校长就给全校下了一个规定:
优秀学生不让考外校,只能考本校的研究生。
我就这样被朱校长留在华中工学院。
当时华中工学院数学系有几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其中一个是林少宫教授的数量经济学。
林老师195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专业是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大师、现代经济学主要推动人之一郝太林(Hotelling)很欣赏他,邀请林老师去他那里工作,但是林老师还是回国了。
当时计量经济学才起步,林老师如果那时不回国,现在一定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世界著名教授。
回国后,由于不让教西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林老师就改行教数理统计,结果林老师成为国内应用数理统计方面的权威。
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78年三中全会实行经济改革后,我感觉到经济学研究将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领域,所以就报考了林老师的数量经济研究生。
当时林老师准备招收四个研究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
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成绩是全校第二名。
我从小就比较自由散漫,说话直爽,不喜欢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那一套,欣赏道家无为而治的处世态度。
道家的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指要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取得成功,一切要顺其自然(“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
当时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还不是系,只是教研室,统属华中工学院基础课部。
我当时不被基础课部领导喜欢,一个原因是认为我政治上不求上进,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我讲穿着。
由于我穿解放鞋出脚汗,喜欢穿皮鞋,于是他们就说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另外,由于我忙于准备研究生考试,从早到晚在学习,对其他的事情不太关心,所以他们认为我在走白专道路。
参加完研究生考试后,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刚好我祖母病了,我向寝室长请了假,没有参加期末考试就回家去了。
寝室长也没有把我请假的事汇报给系领导。
当时基础课部领导认为我刚考上研究生就骄傲了,居然不参加期末考试,再加上数量经济专业原打算招四名研究生,却只有我一人够分数线,最终把我的研究生资格取消了。
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沮丧。
记得我独自在县城的长江边上静坐了4个小时,心乱如麻,不过还要强制自己理顺思路,自我检讨,如何汲取教训和制定今后的打算。
那时,文革后恢复高考已经使我认识到:
自己头上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一定要摘掉,否则就像右派的帽子,如泰山压顶,让你今后抬不起头。
我自己对自己说,哪里倒下去,就要在哪里站起来,一定不要泄气。
然后,立即赶回学校,那时暑假才刚刚开始,准备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试。
在随后一年,我处处注意,力争有一个好的表现,参加所有班、部活动,结果被评为学校优秀共青团员,基础课部三好学生。
由于表现和成绩都不错,在80年5月毕业时我被留校当老师。
随后我报考了80级研究生,又以高分考上了。
我终于在1980年9月成为林少宫老师的首届研究生,成为林老师的首席大弟子。
这是我苦下功夫的结果,为我今后的经济学研究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协助带我们研究生的,还有李楚霖教授。
在这些恩师的悉心指引和传授下,我从此走向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不归路。
出国留学几经周折
我成为研究生之后,学校不久就开始推荐研究生出国留学,我也被列为公派出国留学人选之一。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也是一件大难事。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出国留学。
从父亲对出国留洋及对钱学森、华罗庚等人高度推崇的言语中,我从小就认为出国留洋对自己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
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对英语口语根本不感兴趣,我觉得能看懂英文文章就可以了。
当时我只掌握了不到一千个英语单词,我对在大学时学英语从来不开口的短视行为感到非常后悔,自责自己太没有眼光,但这并没有减低我出国的热忱,只是下定决心恶补英语。
朱九思校长办学的干劲非常大,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他对出国留学非常重视,想尽可能多地派人出去留学,但那时每个学校的出国留学名额有限,怎么办呢?
朱校长刚好那年秋季到美国考察。
在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访问中,朱校长知道了在国外读书可以拿奖学金,而不须国家花费的好事。
他一回国,就让我们这些已推荐出国的人自己申请奖学金,一旦申请成功后,就把公派出国名额让给其他人,这样就可以多派人出国。
朱校长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是一大创举,那时许多学校和学生根本都还不知道可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这么一回事。
由于朱校长的这一举动及采用其它种种措施,在我出国时,华中工学院已派出200多人留学,在当时所有的大专院校出国人员为第二多。
朱校长对出国人员非常重视,无论怎么繁忙,也要挤出时间接见每一个即将出国的留学人员。
我在申请出国留学和奖学金的时候,也规划好自己要干的事。
我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也刻苦学习英语,并开始做硕士论文。
我的论文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是关于经济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
我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
在攻读硕士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专业论文。
我的硕士论文后来寄给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费雪(FranklinFisher)教授,获得他的好评。
我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的学校。
把写好的论文寄到所申请的学校。
在林少宫和李楚霖两位老师的建议下,当时我申请了四所学校,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及李楚霖教授写了推荐信,最后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奇普曼教授(JohnS.Chipman)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就给了我研究助理奖学金。
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不会说,但是已经能写了。
明尼苏达大学曾经专门安排一位在北京大学访问的教授,带来当时流行的国际学生英语水平测试Michigan英语试卷单独让我考,我没有通过。
但奇普曼教授对我很有兴趣,他是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讲座教授,在学校很有地位,由於他坚持要我,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通过特赦的方式把我的英语免了,并给我了奖学金。
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次寄给我的是标准的I-20入学通知表,要我1981年秋季入学。
但学校希望我学成后回国,把我作为公派留学的形式出国,因而要求我用访问学者所用的J-1签证出国留学。
在我拿到IAP-66入学通知表后,很不幸那年夏天教育部有了新的规定,在校研究生不能出国,只能毕业以后再出国。
这样,我就决定加快学习进程,尽快早毕业。
结果只用了半年的时间,1982年元月的时候,我就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
明尼苏达大学又给我寄来了82年元月入学的表格,但国内办出国手续特别复杂,来不及,推迟到1982年9月入学,结果又错过了。
这样明尼苏达大学前前后后给我寄了五张入学表格,直到1983年1月底我才终于成行。
我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博士生。
到美后,系里秘书告诉我,在我之前,经济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我这么费周折才能入学的学生,明尼苏达经济系主管研究生的主任布朗利(OzBrownlee)教授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在美国政界有不少关系,怕我申请美国签证时被拒签,特别通过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中国使馆打招呼,为我的签证申请放行。
这样,出国留学的愿望经过几经周折终于实现了。
总结自己求学的经历,我发现只要你敢想,然后去努力,你的理想多半会实现,就怕你没有想法。
我追求的目标,比如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出国,当教授,目前基本都如愿以偿。
当然,你对自己要有一个大致的定位,不能空想,一旦目标明确后,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
要想办法实现目标,也就是军事上所谓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百分之一的希望,按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执行。
没有前面‘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哪有后面‘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前景,没有前面‘踏破铁鞋无处寻’不折不挠的千辛万苦,哪有后面‘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人成果。
事在人为,即使你没有成功,只要你努力了,就不会遗憾和后悔。
补短扬长摆脱困境
我83年1月底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刚到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非常大,主要表现在生活、学习和语言方面。
首先是生活问题。
由于我是自费公派,自费和公派的好处都得不到。
因为不是公费留学,所有的公费待遇完全没有,自己需要交学费和买医疗保险,也不象自费留学生,都有亲戚在美国,需要时能得到帮助。
我到美国时几乎身无分文,80年代初,国内美元异常缺乏,有钱也换不到美元。
去了以后,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要等到一月后才能拿到。
幸好一位来自于香港叫练乙铮的学长异常热情,给了我很多帮助,没出国之前,就主动写信与我联系,告诉我有关出国事项,到美后接我飞机,帮着找房子,带着我注册,并借给我400美元做生活费,雷鼎鸣学长在我刚到美国时也给了我许多帮助。
学费是系研究生主任布朗利教授自掏腰包借给我的。
练乙铮和雷鼎鸣在美国当了几年教授后现在都回到香港工作。
练乙铮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过教,当过香港信报总编辑,现在在香港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
雷鼎鸣回到香港后就一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
他们两人现在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
布朗利教授在我还在明尼苏达大学时就由于癌症去世了。
当时四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床垫、家具都是捡别人扔掉的。
其实在美国捡家具是一件正常的事,许多人都捡,我们几个研究生捡的家具、床垫都不错。
我们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还有个学生也去了明尼苏达,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结果消息传到了华工的数学系,有的老师就说,田国强很潦倒,捡了一个床垫睡觉,田国强混不下去了。
林少宫老师听到以后很生气,他说:
田国强有困难也是暂时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
我听说了以后很感动,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学得最好,不让林老师失望。
林少宫老师的人格魅力非常大,他的研究生都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在中国大陆介绍和讲授现代经济学的大学之一,培养了一批现代经济学人才。
其中不少人象我一样在国外继续深造后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2001年夏天,林老师的十多个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到母校,专门为祝贺林老师从教50周年及80华诞而特地举行讲座,大家介绍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和个人研究成果。
讲座论文也专为祝贺林老师80华诞编集为《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论文集,已于2002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次是学习问题。
我当时去美国学经济学时困难的确很大。
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时,学校早已开学了大半年,况且自己现代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困难可想而知。
现代经济学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国内研究生阶段学的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及运筹学方面的东西。
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但几个月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困难了。
因为别人的困难是学经济学时遇到一个数学公式他看不懂,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而我当时的困难却不同,由于数理基础强,一看就懂,只是自己经济学基础差,需要抓紧时间去恶补。
我首先花了两个星期就把维瑞安(Varian)的《微观经济分析》自学完了,基本上有了信心。
我的听力差,听不太懂教授讲的课,但是我的自学能力很强,这是考研究生时候锻炼出来的,我就向同学借笔记。
我的许多课程就是这样通过自学完成的,毕业时,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是A。
第三就是语言问题。
我的英语差对我的学习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由于我没有通过英语考试,学校就让我边上专业课边去学英语。
当时我的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和奇普曼教授一谈话,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
因为我的英语根本没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给我奖学金让我过去的。
当时奇普曼只好让我作一些核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
我看了数据就头痛,费时间,且学不到东西。
我想,这多半是一个对我失望的信号。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我应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我就问奇普曼:
你有什么文章能给我看。
花了一个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后,我说我有一些想法想与他讨论,我一说出来他就两眼发亮。
然后我又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
这时,我刚到美国才两个月左右,这篇文章是关于线性开支函数估计问题的一篇论文。
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难度是其误差项的方差距阵是奇异的,有很多种估计方法,就是没有一个精确估计的完美答案。
后来奇普曼对系里的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说,田国强真的不错!
从此奇普曼不再让我弄数据了,即使暑假也给我提供奖学金,和他一起写论文,到我毕业时,我一共和他写了5篇论文,后来都发表在经济学期刊和论文集中了。
等到我博士毕业,奇普曼在为我找工作的推荐信中写到:
“田国强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30多年来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仅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而且进步神速,远超于一般的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