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docx
《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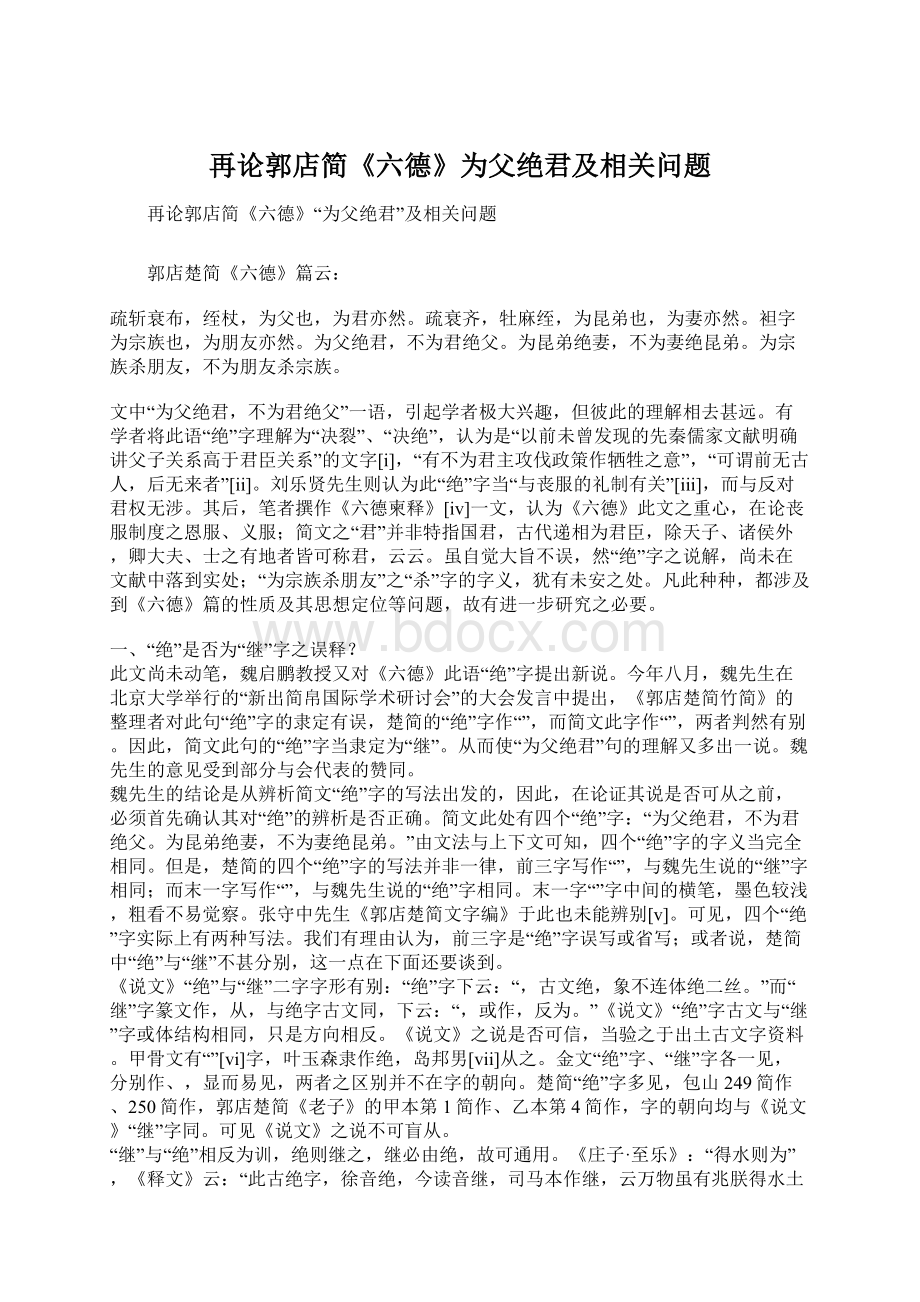
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
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
郭店楚简《六德》篇云:
疏斩衰布,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
疏衰齐,牡麻绖,为昆弟也,为妻亦然。
袒字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
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
文中“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一语,引起学者极大兴趣,但彼此的理解相去甚远。
有学者将此语“绝”字理解为“决裂”、“决绝”,认为是“以前未曾发现的先秦儒家文献明确讲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的文字[i],“有不为君主攻伐政策作牺牲之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ii]。
刘乐贤先生则认为此“绝”字当“与丧服的礼制有关”[iii],而与反对君权无涉。
其后,笔者撰作《六德柬释》[iv]一文,认为《六德》此文之重心,在论丧服制度之恩服、义服;简文之“君”并非特指国君,古代递相为君臣,除天子、诸侯外,卿大夫、士之有地者皆可称君,云云。
虽自觉大旨不误,然“绝”字之说解,尚未在文献中落到实处;“为宗族杀朋友”之“杀”字的字义,犹有未安之处。
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六德》篇的性质及其思想定位等问题,故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一、“绝”是否为“继”字之误释?
此文尚未动笔,魏启鹏教授又对《六德》此语“绝”字提出新说。
今年八月,魏先生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郭店楚简竹简》的整理者对此句“绝”字的隶定有误,楚简的“绝”字作“”,而简文此字作“”,两者判然有别。
因此,简文此句的“绝”字当隶定为“继”。
从而使“为父绝君”句的理解又多出一说。
魏先生的意见受到部分与会代表的赞同。
魏先生的结论是从辨析简文“绝”字的写法出发的,因此,在论证其说是否可从之前,必须首先确认其对“绝”的辨析是否正确。
简文此处有四个“绝”字: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
”由文法与上下文可知,四个“绝”字的字义当完全相同。
但是,楚简的四个“绝”字的写法并非一律,前三字写作“”,与魏先生说的“继”字相同;而末一字写作“”,与魏先生说的“绝”字相同。
末一字“”字中间的横笔,墨色较浅,粗看不易觉察。
张守中先生《郭店楚简文字编》于此也未能辨别[v]。
可见,四个“绝”字实际上有两种写法。
我们有理由认为,前三字是“绝”字误写或省写;或者说,楚简中“绝”与“继”不甚分别,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谈到。
《说文》“绝”与“继”二字字形有别:
“绝”字下云:
“,古文绝,象不连体绝二丝。
”而“继”字篆文作,从,与绝字古文同,下云:
“,或作,反为。
”《说文》“绝”字古文与“继”字或体结构相同,只是方向相反。
《说文》之说是否可信,当验之于出土古文字资料。
甲骨文有“”[vi]字,叶玉森隶作绝,岛邦男[vii]从之。
金文“绝”字、“继”字各一见,分别作、,显而易见,两者之区别并不在字的朝向。
楚简“绝”字多见,包山249简作、250简作,郭店楚简《老子》的甲本第1简作、乙本第4简作,字的朝向均与《说文》“继”字同。
可见《说文》之说不可盲从。
“继”与“绝”相反为训,绝则继之,继必由绝,故可通用。
《庄子·至乐》:
“得水则为”,《释文》云:
“此古绝字,徐音绝,今读音继,司马本作继,云万物虽有兆朕得水土气乃相继而生也。
或本作断,又作续断。
”《说文》:
“断,截也。
”断与绝义通。
可见,古时流行的文本中,绝、继二字之字形亦不甚区别。
关于“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句的文义,魏先生解释道:
为父服丧时,逢君之丧,则将君之丧放在其次;为君服丧时,逢父之丧,则不能将为父服丧置于其后。
为昆弟服丧时,逢妻之丧,则将服妻之丧放在其次;为妻服丧时,逢昆弟之丧,则不能将为昆弟服丧置于其后。
但是,根据魏先生对“绝”字的新解,此句当读作“为父继君,不为君继父。
为昆弟继妻,不为妻继昆弟”,如此,便无法得出与魏先生相同的结论。
传世文献之“继”,多训为“次”,如《周礼•秋官•大行人》:
“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
”郑注:
“继小国之君。
言次之也。
”贾疏:
“云继小国之君,言次之也者,谓行礼次在小国君之后。
”类似之例,在在多有,此不赘举。
因此,“为父继君”之“继君”,只能理解为“次于君”,即父丧次于君丧之后,这就与魏先生的理解大相径庭了。
同样,“为昆弟继妻”,也只能理解为昆弟之丧次于妻丧之后。
如此则恩服次于义服,内亲次于外亲,宗法秩序完全颠倒,于理难通,也有违于魏先生的本意。
因此,我们认为魏先生的“继”字之释不可从。
二、“绝”当作“绝服”解
刘乐贤先生认为,上引《六德》“句中的‘绝’、‘杀’都是丧服用词,是减杀之意”,“当服父丧与服君丧冲突时,可以将君服做减省,而不是为君服丧而减省父丧”。
刘说实际上是将“绝”与“杀”类同,与礼书习见的“降杀”一词对应。
但是,典籍之“绝”,均无“减杀”或“减省”之义;而且,若将“为父绝君”解释为“为父丧减省君丧”,在礼书中也得不到证明。
鄙见,《六德》此“绝”字,当与礼书之“绝服”相当,敢作申论如下。
“绝”字本义为“断丝”,已见上引《说文》。
引申之,凡事与物之断,皆得称“绝”。
礼书每每以“绝”字称亲属关系之断裂,并进而论丧服变化。
《礼记·大传》云:
“绝族无移服,亲者属也。
”《正义》:
“绝族者,谓三从兄弟,同高祖者。
族兄弟缌麻,族兄弟之子及四从兄弟为族属,既绝,故无移服。
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
”是断绝于宗族者,不再为之服丧。
《大传》此语亦见于《丧服》,《齐衰杖期章》之“传曰”在回答出妻之子为母何以服期之问时云:
“绝族无施服。
”若妻为丈夫所出,则其已绝于宗道,故出妻之子仅为本生之母服期之丧,而于母族不再服丧。
此亦是断绝于宗族者绝其服之义。
以上两例“绝”字用法相同,均非“减省”丧服。
古代丧礼还有一种“绝服”制度,尽管文献对此没有作正面的、系统的表述,而似乎只是顺便提及,但礼家的研究表明,“绝服”之制确乎存在,并揭示了它的内涵与实质。
由于其复杂性,故需要从丧服的基本制度谈起。
古代丧服,大总而言不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类,恩重者服重、恩浅者服轻,简单明了。
但是,在宗法制度下,家庭成员之间暗含着种种复杂因素,如长子承重,庶子不承重,所以父为长子与为庶子的丧服不同;女子已嫁与未嫁,为父母的丧服也不同;此外还涉及到君臣关系、死者名分及长幼等错综的问题,使丧服制度极形纷繁。
《礼记·大传》将种种复杂的服丧方法归纳为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等六种“服术”。
郑注:
“术犹道也。
亲亲,父母为首。
尊尊,君为首。
名,世母、叔母之属也。
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
长幼,成人及殇也。
”亲亲、尊尊为“六术”之纲,由此而有恩服、义服、加服、降服、绝服等多种名目。
恩服,即为直系亲属所服之丧服,主为血统关系,体现亲亲之道。
由于血缘家庭通常是被“尊者”组织在社区或国家范围内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为了表示对尊者的敬意,尽管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尊者丧亡时亦为之服丧,此即所谓义服,义服主为君臣关系,体现尊尊之道。
从理论上讲,亲亲与尊尊并重,尊不得掩亲,亲不得掩尊。
故《丧服》规定,为至亲与为至尊服丧,丧等相同,都是斩衰。
《六德》云“疏斩衰布,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正是此义。
在丧服制度中,亲亲之服与尊尊之服每每在不同的丧等中同时出现,如《丧服》之斩衰有两类,一为正斩,一为义斩。
子为父,父为长子、妻为夫为正斩。
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属义斩,即是最典型之例。
但是,在丧服制度中,尊者与卑者的丧服一般并不是对等的,无论是在血缘家庭中,还是在国家范围内,都是如此。
在血缘家庭中,妻为夫服斩衰三年之丧,而夫为妻仅服齐衰一年之丧。
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大功三月,而天子于诸侯之大夫无服。
诸侯、天子是一国或天下的至尊,故其丧服自有特殊体系,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即所谓“绝服”。
古代丧服是宗法制度的体现。
天子、诸侯是尊者,其宗法行君统,不行宗统。
《礼记·大传》云: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郑注:
“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
所以尊君别嫌也。
”孔疏:
“此一经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绝宗之道也。
”可见君统与宗统是分离的,天子、诸侯服丧的原则与普通人有所不同。
明确提到天子、诸侯服丧的原则有别于普通人的是《中庸》:
“期之丧,达乎大夫”,郑注:
“期之丧达于大夫者,谓旁亲所降在大功者。
其正统之期,天子、诸侯犹不降也。
大夫所降,天子、诸侯绝之,不为服。
所不臣,乃服之也。
”按照儒家丧服制度的常例,对于旁系亲属之丧,应该为之着大功之服,服丧的时间为“期”。
但是,天子、诸侯是尊者,为了体现“尊尊”的原则,天子、诸侯仅为直系亲属服丧,而不为所有的亲人服丧,其界限划定在旁亲的期之丧,即所谓“旁期”。
因为天子、诸侯与“旁期”之亲的关系与君臣关系相当,故不能为之服丧。
旁系亲属的最高服叙为齐衰不杖期,所以,天子、诸侯服丧的原则之一是“绝旁期”。
大夫及大夫以下者则不在此例,必须为旁亲服丧,《中庸》的“期之丧,达乎大夫”,即是此义。
郑注云“天子、诸侯绝之,不为服”,是对“为父绝君”之“绝”字的最好注脚。
在现实生活中,丧主往往会遇及前丧未了、后丧又起之场面,两件丧事交叉发生,使丧服的穿着益形复杂,礼书中讨论特殊情况下的丧服之处很多,如《礼记·杂记》:
“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
丧服”。
“虽诸父、昆弟之丧,而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皆服其
除丧之服。
卒事,反丧服”。
“如三年之丧,则既●。
其练、祥皆行”。
“王父死,未练、祥,而孙又死”。
“父母之丧,将祭而昆弟死”。
“大夫士将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
《礼记·间传》也提及先后发生两件丧事事,丧服如何处理的问题:
“斩衰之丧,既虞、卒哭,遭齐衰之丧。
轻者包,重者特”。
“既练,遭大功之丧。
”
“齐衰之丧,既虞,卒哭,遭大功之丧,麻、葛兼服之”。
《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一语,虽不见于礼书,然其文义甚明,旨在权衡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两者孰轻孰重。
《六德》云“疏斩衰布,绖杖,为父也,为君亦然”,两者的丧服等级相同,与《仪礼·丧服》斩衰章一致。
但尽管如此,两者仍有轻重。
父子血亲,是宗法制度的起点,为父服服斩衰是“恩服”中之最重者。
为君服斩衰,是出于“尊尊”的原则,以君为“至尊”,再以“资于事父以事君”为尺度确定其丧服标准。
故亦为之服斩衰。
此其一。
父子关系一经确立,则终身不变,故嫡长子为父亲服斩衰亦不可变。
而君臣关系不然,在人的一生中,有可能先后臣事几位君。
且君臣关系不如父子关系稳定,一旦发生变化,则丧服也随之变化。
据《丧服》,君一旦不再居其位,则丧服等级就要下降,如为“寄公”,只服齐衰三月。
此外,如果臣已致仕退休,则先前臣事过的君就成为“旧君”,为旧君的丧服,不再是斩衰三年,而是齐衰三月。
以上两种情况,丧等变得相当之低。
可见,为父与为君,实际上有所区别。
此其二。
天子、诸侯虽然至尊,但尊不敌亲,故虽贵为天子,亦不敢降其正服,必须与常人一样为父服三年之丧,所以《中庸》说:
“三年之丧达乎天子。
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于情于理,均不能以尊屈父。
《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正义》引刘炫云:
“母,亲至而尊不至,岂则尊之不极也?
君,尊至而亲不至,岂则亲之不极也?
惟父既亲且尊,故曰兼也。
”又引刘瓛云:
“父情天属,尊无所屈,故爱敬双极也。
”此其三。
为父与为君,虽然同为斩衰三年,但丧服仍有细微区别。
《丧服》贾疏解题云:
“斩有二,有正有义[viii],为父以三升为正,为君以三升半为义,其冠同六升,三年。
”丧服之布,有粗有精。
丧愈重则布愈粗,愈轻则布愈细,故于丧服用布之粗细,可知丧之轻重。
古制,布之粗细以“升”为单位,郑注云“布八十缕为升”,升数越多,布越细密。
为君丧服用布为三升半,多于为父的三升,可见前者轻而后者重。
此其四。
总之,父丧重于君丧。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即当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应服父丧而绝君之丧服,不得服君丧而绝父之丧服。
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处理“亲亲”与“尊尊”关系时一种立场。
郭店简《语丛一》云:
“有亲有尊,……尊而不亲。
”“长弟,亲道也。
友、君、臣,无亲也。
”可见当时学者在丧服问题上很注意分别内与外、有亲与无亲,主张在同一丧等中,有亲之服重于无亲之服。
[i]李存山:
《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页269,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
[ii]姜广辉:
《郭店楚简与〈子思子〉》,《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页88,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
[iii]《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386,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iv]载《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2000年8月;此文将正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研究》第四辑。
[v]见张守中等:
《郭店楚简文字编》,页177,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
[vi]《乙》8370,《前》,《库》1511,《拾》,《合》263等。
[vii]《殷墟卜辞综类》页472,汲古书院,1971年。
[viii]此语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引文如此;阮本作“斩有二义不同”;毛本作“斩有正义不同”;此处从《通解》引文。
三、关于妻与昆弟的丧服
《六德》云:
“疏衰齐,牡麻绖,为昆弟也,为妻亦然”。
是为妻与为朋友之丧等相同。
而《丧服》为妻服齐衰期,为昆弟服齐衰不杖期,则两者有等差。
廖名春先生认为,《六德》所记之丧服制度与《丧服》不尽相同,有可能保留了较早时期《丧服》的面貌。
廖说不无道理。
事实上,《礼记》所论丧服制度与《丧服》经传所记丧服制度并不完全一致,前贤早有论述,此不赘述。
郭店简《六德》、《性自命出》等篇属于刘向《别录》所说“古文《记》二百四篇”之列[i],与《礼记》本属同一体系,因而篇中出现与《礼经》相左之处,亦在情理之中。
《六德》作者十分强调内外之别,将父子、夫妇、君臣等“六位”分为“内三位”与“外三位”[ii],以父、子、夫为内位,而以君、臣、妇为外位,故父子重于君臣。
《丧服》齐衰不杖期章《传曰》:
“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
”夫妻、昆弟虽皆一体,而仍有差别。
昆弟为至亲,属内亲。
妻为异姓,本为路人,属外亲,故《六德》将其列入“外三位”,并明确提出“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
《丧服》关于宗亲、外亲、妻亲之丧服的规定,似有前后不能一贯之处:
宗亲之丧,都在大功以上;属于母党的外亲,以外祖父母为最高,但仅为小功之服;属于妻党的妻亲,仅为岳父母服丧,而且是缌麻之服。
据此则《丧服》对宗亲、外亲、妻亲的亲疏,分别甚严。
但是,《丧服》为妻是杖期,为昆弟是不杖期,妻之丧服又高于昆弟,与上述宗亲、外亲、妻亲的丧服明显不相称。
因此,我们认为,《六德》“为昆弟绝妻”提出了一种比《丧服》更为合于逻辑的服叙。
此外,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即在《六德》作成的时代,齐衰期作为一种丧等,并不区分杖期与不杖期。
理由是,《六德》仅仅说到“疏衰齐,牡麻绖”,而没有提及“杖”。
严格说来,先秦丧礼中的“杖”不属于丧服。
先秦丧礼中“杖”的作用,《丧服》有很详尽的说明。
斩衰章“传曰”:
“杖者何?
爵也。
无爵而杖者何?
担主也。
非主而杖者何?
辅病也。
童子何以不杖?
不能病也。
妇人何以不杖?
亦不能病也。
”郑注:
“爵,谓天子诸侯卿大夫也。
无爵,谓庶人也。
担犹假也,无爵者假之以杖,尊其为主也。
非主,谓众子也。
”于此,可以对“杖”的作用,可得到如下认识:
首先,天子、诸侯、卿大夫作为有爵者,在丧礼中可以用杖,这是其身份的象征。
其次,士庶之人虽无爵,但在担任丧主时也得用杖。
显然,以上两种情况所用之杖,都不表示丧等的高下,而仅仅是在社会中或丧事中的身份的标志。
再次,庶子虽非担主,若因哀痛致病,可用杖扶持病体。
此时的杖,也与丧等无关。
又次,未成年的男子、女子,哀思不至于过甚,故都不用杖;这再次说明杖仅仅是辅病的工具。
先秦时代表示丧服轻重的只有衰麻、首绖、腰绖之类,故有“男子重首,女子重要”之说,故《六德》略而未言。
四、关于“为宗族杀朋友”
《六德》云“袒字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又云“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
文义同上,先言为宗族与朋友服丧等级相同,都是“袒字”;再言若宗族与朋友两者相提,则宗族高于朋友。
简文“袒字”之“字”,裘锡圭先生已经指出,为“免”字之误写[iii],至确。
“袒”即袒去衣袖,裸露左臂;“免”是用宽一寸之布,从项向前交于额,再向后绕于紒。
袒非丧服,免亦不成冠,不属于正服[iv]。
袒免作为五等丧服的延伸,只适用于两种情况。
一是对五世之亲,即共承高祖之父的亲戚。
五等丧服只及于四世之亲,即同高祖的亲戚,为之服缌麻。
五世之亲是已出五服的远亲,欲表哀思,只能用袒免之制。
六世则同姓而已,无亲可言。
故《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
”二是为死于他邦的朋友主丧。
朋友死于他邦,周围无亲人为之主丧,彼此虽然无亲,但有同道之恩,此时可比于五世之亲,以“袒免”为之主丧。
楚简云“袒字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与传世文献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楚简“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之“杀”字当作何解释。
与刘乐贤先生一样,笔者在《六德柬释》中从旧说,将“杀”字解释为“减杀”。
但是,袒免是五等丧服之外唯一的丧饰,是丧饰的边界,袒免之外,已无可供减杀的丧饰。
因此,将此处之“杀”理解为减杀,有碍难之处,当另求它说。
传世文献所见之“杀”字有二音,《玉篇》杀部云:
“杀有二切:
所札切,断命也;所界切,疾也。
”所札切之杀,为杀伐之杀,毋庸赘言。
所界切之杀,礼书多训为“减杀”,《中庸》云: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即其例。
“杀”每每与“降”并用。
“降杀”为丧服或礼数减等之义。
礼书屡云降服,即因某种原因而将丧服降低一等,如子为父母应服三年之丧,其已出嗣者,则为本生父母降三年之服为一年之服。
《丧服》:
“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为士者。
”疏:
“大夫为此八者本期,今以为士,故降至大功。
”敖继公:
“大夫于士为异爵,故其丧服例降其旁亲之士者一等,虽世叔父母亦降之,所以见贵贵之义胜也。
”
《丧服》:
“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
”郑注:
“大夫虽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逾之也。
士谓大夫庶子为士者也。
己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
”
其实,所界切之“杀”字,另有一义,可以训为“断”、“止”。
《荀子·大略》云:
“霜降逆女,冰泮杀止。
”[v]《孔子家语·本命》云:
“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
冰泮而农桑起,昏礼而杀于此。
”是“杀”训“止”、“断”之证。
又《荀子·在宥》:
“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
”《释文》:
“崔云,谓弹正杀之。
”此句“制”、“杀”、“决”三字类同,皆有“断”义。
此“杀”字训“断”、“止”之又一证。
《大传》“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
”《正义》云“五世袒免,杀同姓也”者,“减杀同姓也”。
鄙见,此处之“杀”,亦当训为“断”、“止”。
《大传》此语之“穷”、“杀”、“竭”三字,字义相类,皆有“断”、“止”之义。
“四世而缌,服之穷也”,言为四世之亲服缌麻三月,五服至此而穷尽。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言为五世之亲袒免,与同姓之亲为断。
“六世亲属竭矣”,六世则亲属已竭尽。
如此,方文气贯通,字义畅达。
若以“杀”为“减杀”,则与上下文义不协。
《丧服小记》云: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郑注:
“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
”《正义》云:
“上杀者,据己上服父祖而减杀,故服父三年,服祖减杀至期,以次减之”;“下杀者,谓下于子孙而减杀。
”“旁杀者,世叔之属是也”。
郑玄、孔颖达之意,杀为减损之义。
亲情以父子为最深,上及父、下及子,是为“三”。
向上至祖,向下至孙,是为“五”,故云“以三为五”;再向上推及曾祖、高祖,向下推及曾孙、玄孙,是为“九”,故云“以五为九”。
曾祖、高祖,亲情渐疏,是为上杀。
曾孙、玄孙,亲情渐疏,是为下杀。
横向,则由骨肉至亲之兄弟推至从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亲情亦渐疏,是为旁杀。
是为对“杀”为“减杀”的传统解释。
然细玩《丧服小记》这段文字,所谓上杀、下杀、旁杀,意在说明五服及于九族,落脚点在“而亲毕矣”一句上。
如果将上杀、下杀、旁杀理解为对九族上、下、侧面范围的界定,可能更合于文义。
此外,这段文字与《大传》“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立意一致,也是要说明“亲服”的范围。
此处的“杀”与表示礼数降等的“降杀”不同,前者表示界限的截止;后者则表示循级而降,如丧服由大功降为小功、由小功降为缌麻之类。
因此,将上引《大传》和《丧服小记》两段文字中的“杀”字训为“断”、“止”,恐怕更合于文义。
《六德》之“杀朋友”与《大传》之“杀同姓”句式相类,意义相同。
《六德》“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句两“杀”字,亦均应训“杀止”,字义的指向,在丧服之边界。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注释:
[i]参阅拙作《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ii]参阅拙作《六德柬释》。
[iii]《郭店楚墓竹简》189页,注释19。
[iv]参见拙作《六德柬释》。
[v]今本此语脱“止”字。
《召南·摽有梅》、《陈风·东门之扬》正义两引此句,皆作“冰泮杀止”。
《周礼·地官·媒氏》疏引王肃论引此句及《韩诗传》,亦皆作“冰泮杀止”。
此据王先谦《集解》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