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docx
《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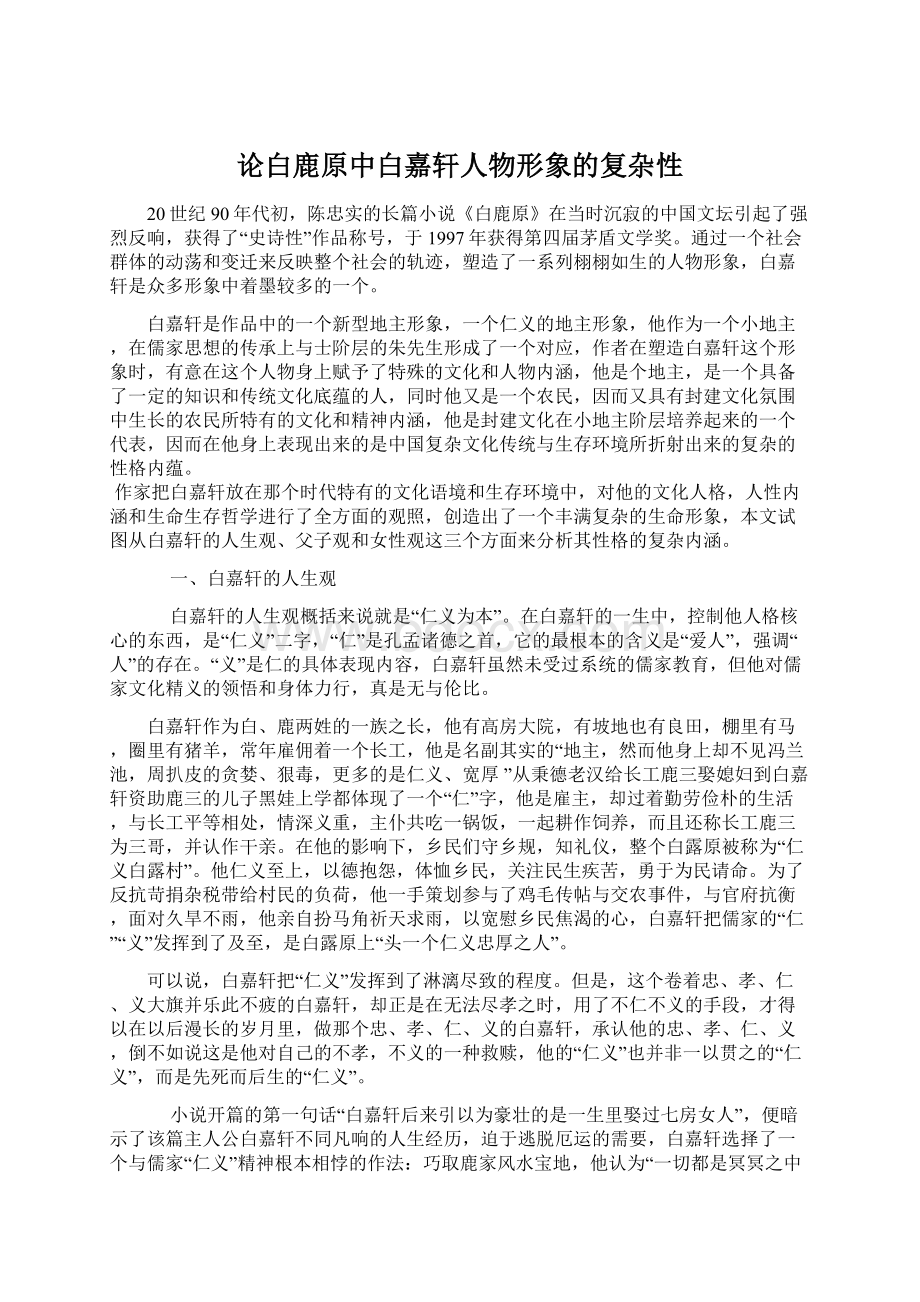
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时沉寂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史诗性”作品称号,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通过一个社会群体的动荡和变迁来反映整个社会的轨迹,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白嘉轩是众多形象中着墨较多的一个。
白嘉轩是作品中的一个新型地主形象,一个仁义的地主形象,他作为一个小地主,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与士阶层的朱先生形成了一个对应,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个形象时,有意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和人物内涵,他是个地主,是一个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传统文化底蕴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农民,因而又具有封建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农民所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他是封建文化在小地主阶层培养起来的一个代表,因而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复杂文化传统与生存环境所折射出来的复杂的性格内蕴。
作家把白嘉轩放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中,对他的文化人格,人性内涵和生命生存哲学进行了全方面的观照,创造出了一个丰满复杂的生命形象,本文试图从白嘉轩的人生观、父子观和女性观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性格的复杂内涵。
一、白嘉轩的人生观
白嘉轩的人生观概括来说就是“仁义为本”。
在白嘉轩的一生中,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仁”是孔孟诸德之首,它的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强调“人”的存在。
“义”是仁的具体表现内容,白嘉轩虽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无与伦比。
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的一族之长,他有高房大院,有坡地也有良田,棚里有马,圈里有猪羊,常年雇佣着一个长工,他是名副其实的“地主,然而他身上却不见冯兰池,周扒皮的贪婪、狠毒,更多的是仁义、宽厚”从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娶媳妇到白嘉轩资助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都体现了一个“仁”字,他是雇主,却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与长工平等相处,情深义重,主仆共吃一锅饭,一起耕作饲养,而且还称长工鹿三为三哥,并认作干亲。
在他的影响下,乡民们守乡规,知礼仪,整个白露原被称为“仁义白露村”。
他仁义至上,以德抱怨,体恤乡民,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民请命。
为了反抗苛捐杂税带给村民的负荷,他一手策划参与了鸡毛传帖与交农事件,与官府抗衡,面对久旱不雨,他亲自扮马角祈天求雨,以宽慰乡民焦渴的心,白嘉轩把儒家的“仁”“义”发挥到了及至,是白露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可以说,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但是,这个卷着忠、孝、仁、义大旗并乐此不疲的白嘉轩,却正是在无法尽孝之时,用了不仁不义的手段,才得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做那个忠、孝、仁、义的白嘉轩,承认他的忠、孝、仁、义,倒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的不孝,不义的一种救赎,他的“仁义”也并非一以贯之的“仁义”,而是先死而后生的“仁义”。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便暗示了该篇主人公白嘉轩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迫于逃脱厄运的需要,白嘉轩选择了一个与儒家“仁义”精神根本相悖的作法:
巧取鹿家风水宝地,他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沉着,冷静,善于算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而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
”
磨难把白嘉轩逼到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生存,他情愿放弃“仁义”,在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苦难”表演之后,白嘉轩采取“卖地”的曲折路线成功地从鹿子霖手中换回了那块宝地,从而为自己日后的发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此时白嘉轩身上显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在苦难中挣扎的本能,此时的白嘉轩身上并无“仁义”的显现,“买地风波”是一个转折点。
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教诲使白嘉轩猛然意识到儒家“仁义”精神的重要;时世突变中朱先生镇定自若的“断时论世”使他豁然开朗,白嘉轩突然发现“仁义”对人们起着巨大的约束作用,在白嘉轩的意识里,早先对朱先生儒家文化身份的企慕开始发展,他有了对自己儒家文化身份的朦胧设想,在此之前,白嘉轩几乎还曾想到过追求“仁义”,他在父亲去世后两个月即开始一个一个地讨女人,此为不孝,他工于心计,换回宝地,此为不义,他种植罂粟,炼制鸦片而致富,此为不仁,这些都表明他心思缜密,头脑冷静,重利践义,有时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惜损人利己,不同的是他把他的那些欲望,计谋掩藏在心灵深处不易为人觉察,白嘉轩这段时期的一系列行为几乎是发源于人的生存本能,甚至是立足于乱世之中要保持家财两旺的必要手段,此时白嘉轩无法顾全大仁大义,“仁义”在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其实是一种奢望,一种空谈而已。
在乱世之中,白嘉轩相信了朱先生“只一碗包谷糁子”的理想,不再热衷于政治,对“仁义”的热情建构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和最终目的,在白鹿原上一片腥风血雨,屠杀和复仇轮番登台表演时,白嘉轩冷眼旁观,似乎有着超然物外的洒脱,但他的一句“我的戏楼真成了赘子了”的叹息却把他的讥讽,痛心与惋惜暴露无疑,在田福贤狠斗农协头目时,白嘉轩甚至还上台为这些曾斗过自己的人下跪求情,这些无不凸现出白嘉轩对于村民肆意践踏乡约的无奈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状的痛心与无奈,也表明他对自己“义”的爱护与偏执之情,在对待小娥的态度上也能体现出白嘉轩这一复杂情感,《论语》上说:
“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昏礼者将二姓之好,上以事宇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在白嘉轩的意识里,小娥不在他的“仁义”德行保护范围之内,这些无不表明,白嘉轩所热切追求的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着悖谬,看来“人者爱人”“仁者知人”都是有限度的,它并不是普适于所有需要爱,需要帮助的人,更不适合于小娥这样的女人,“万恶淫为首”这是白嘉轩切齿痛恨小娥的根本原因,白嘉轩在祠堂狠狠惩治小娥勾引孝文,使白嘉轩族长的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白嘉轩认定小娥是破坏白鹿村“仁”美名,使村民道德败坏,礼仪崩溃的罪魁祸首,但白嘉轩并没有打算亲手杀死她,他不屑于动手,而小娥在“遭受完一个女人在旧中国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一切凌辱和损害以后,是被她心爱的黑娃的父亲亲手杀死的。
鹿三几乎是替白嘉轩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白露原上瘟疫流行,人们大量死去,惶恐,荒凉,悲戚遍布白露村时,面对小娥死后不散的阴魂,白嘉轩依然镇定,沉着,他固执地认为,小娥活着是个坏种,死了也不是个好鬼”因此不管阳世不管阴世,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他不顾族人的求情,执意要惩治恶鬼,白嘉轩以他的正气与妖邪作斗争,并以焚尸,修塔镇鬼的举措再一次表明他超人一等的智慧,和其不可动摇的信心,对儒家文化的强烈依恋使白嘉轩认识不到“仁义”在某些时候实在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使白嘉轩在很多时候显的冷漠,不尽人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白嘉轩“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又是最冷血的食人者”[7]这也许正是白嘉轩这一复杂形象的人格魅力所在。
二、白嘉轩的父子观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父亲”文化,它强调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因此,在父子关系中,父亲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儿子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权,必须为父亲而活,白嘉轩的父子观,主要指他与长子白孝文的关系。
白嘉轩的父子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个“严父”的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的社会角色不大一样,分别称为“严父慈母”,“慈”与母性有关,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常与“爱”相连,也叫“慈爱”。
人们一说到“慈”,很自然的就想到母亲,想到母爱。
而“严”的内涵相对比较复杂,它虽然含有“爱”的因素,但这种“爱”是伦理意义上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父亲必须疏远子女,以合乎礼法。
白嘉轩对孝文、孝武就是这样。
他父爱不亚于任何一位父亲,他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常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地瞅着那器官鼓出的脸”。
按照传统意义上“严父”的形象,他只能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看他们,不能说“亲热的话”、做“疼爱亲昵的动作”.这表明白嘉轩早已置身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之中,他必须在儿子面前有足够的威严,他是不能松懈的,是不可让人知的。
那么,他对“子”有什么要求呢?
那就是“孝”。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核心。
“孝”的产生,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宗法制度,即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为核心。
白嘉轩对儿子孝文严格以“孝”的标准来规范要求,其实与这种家庭、家族的本为思想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客观地带有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继承性。
孝文作为长子,理所当然是族长的合法继承人,即封建家长和宗法族长的社会角度和地位,所以,白嘉轩对孝文的教育培养更是尽心尽力,用心良苦。
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人格”。
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言传身教,唯恐失传。
为让儿子懂得粮食的意义,特命次子孝武及未成年的幼子孝义跟着长工鹿三到几百里以外的山里去背食。
往返七天的路程使孝义双唇燥起一层黑色干皮,嘴角淤着干涸的血垢,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抚着血泡的脚片痛不可支。
作为家境富裕的家长能如此教子确是难能可贵。
白孝文对父亲言听计从,十分孝顺,一步一个脚印按照白嘉轩说的道路迈进。
他读四书五经,接受“耕读传家”,为家族利益结婚生子,在宗族祠堂里做族长继承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然而,他并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能充分认识到所做的一切同自己的关系。
他只是按既定的目标做事,自己的天性和个性都被日常的点点滴滴所掩盖,他似乎不会成为白嘉轩那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他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了堕落。
他不但毁了自己,也差点毁了白家,他成了家法宗教文化的“不孝”子孙。
作为一族之长,白嘉轩忠实地捍卫着封建伦理道德,对“不肖子”必须严格惩罚,宗法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
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规,毁的不是一个孝文,白家都要毁了。
”白孝文是未来的族长。
因此只有祠堂进行惩罚,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不论是谁的言行违反了礼法,冒犯了族规,白嘉轩都会毫不手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
然而,他们终归是父子,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
更何况儿子是家族香火的延续,嫡长子的地位仅次于父亲,具有一定的权威。
孝文的堕落虽然给白嘉轩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他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作为封建家长、宗法族长是不能原谅这样的“败类”,但作为父亲,他早已原谅了儿子,他可以同儿子分家,却分不开骨肉之情。
孝文当了保安团营长,要求回原上祭祖,得到了白嘉轩应允,这与一开始对孝文的态度大相径庭的。
白嘉轩之所以允许他回家,是因为他“出息”了,没有丢他的脸,还给他挣回了面子,给白家带来了荣耀。
所以说,白嘉轩的父子观其实是亲情与伦理相互交织的一个表现过程,是同一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互相作用的结果。
三、白嘉轩的女性观
白嘉轩看不起女人,他有一种典型的宗法农民的男权中心意识,女人被他示作泻欲对象、传白嘉轩的女性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他的父女观,二是他的女性观。
先以白灵为例来看看白嘉轩的女性观。
如果说白嘉轩在孝文的世界里是个始终如一的“严父”形象的话,那么他对白灵则是从“慈爱”的父亲到“严酷”的族长的两个的极端。
白灵是白嘉轩唯一的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任其娇纵,白嘉轩对她是极尽宠爱之能事,简直就是家中的“小公主”,这与他对孝文兄弟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常常忍不住咬那手腕,咬得女儿哎呦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
他虽然很清楚女儿更应该“严管”的道理,“只是他无论如何对灵灵冷不下脸来”“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
他甚至违背了自己的原则送灵灵去学堂受教育,而当白灵灵偷偷独自跑到县城去上“新学堂”后,他也显得无能为力。
白嘉轩之所以不容白灵,一是女儿的叛逆行为威胁到了他所维护的旧秩序,二是白灵的人生追求和信仰与他的人生哲学格格不入,所以说,白灵与他的对立是必然的,这已超出了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白嘉轩对儿子与女儿的态度是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