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docx
《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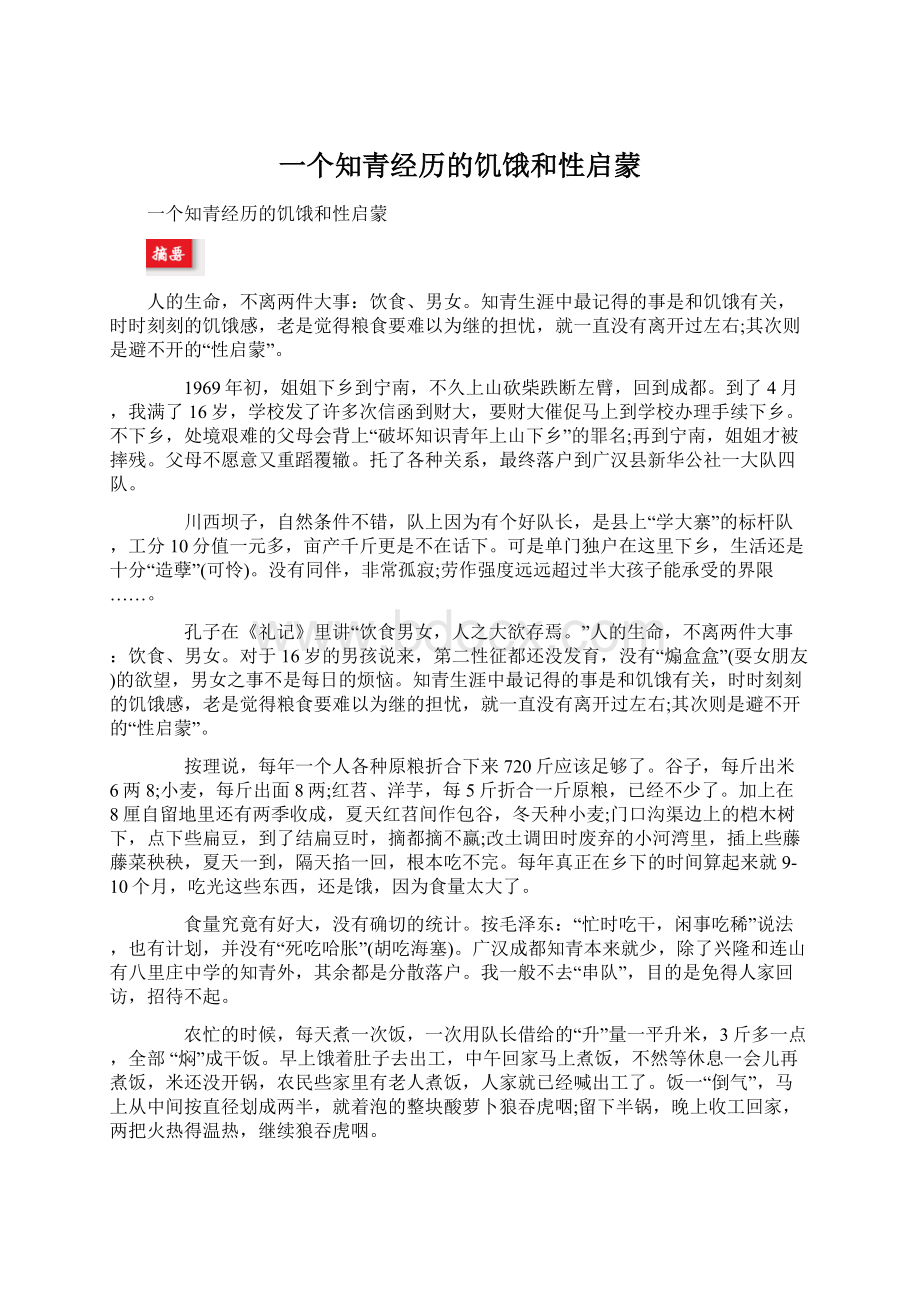
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
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
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
饮食、男女。
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
1969年初,姐姐下乡到宁南,不久上山砍柴跌断左臂,回到成都。
到了4月,我满了16岁,学校发了许多次信函到财大,要财大催促马上到学校办理手续下乡。
不下乡,处境艰难的父母会背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再到宁南,姐姐才被摔残。
父母不愿意又重蹈覆辙。
托了各种关系,最终落户到广汉县新华公社一大队四队。
川西坝子,自然条件不错,队上因为有个好队长,是县上“学大寨”的标杆队,工分10分值一元多,亩产千斤更是不在话下。
可是单门独户在这里下乡,生活还是十分“造孽”(可怜)。
没有同伴,非常孤寂;劳作强度远远超过半大孩子能承受的界限……。
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
饮食、男女。
对于16岁的男孩说来,第二性征都还没发育,没有“煽盒盒”(耍女朋友)的欲望,男女之事不是每日的烦恼。
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
按理说,每年一个人各种原粮折合下来720斤应该足够了。
谷子,每斤出米6两8;小麦,每斤出面8两;红苕、洋芋,每5斤折合一斤原粮,已经不少了。
加上在8厘自留地里还有两季收成,夏天红苕间作包谷,冬天种小麦;门口沟渠边上的桤木树下,点下些扁豆,到了结扁豆时,摘都摘不赢;改土调田时废弃的小河湾里,插上些藤藤菜秧秧,夏天一到,隔天掐一回,根本吃不完。
每年真正在乡下的时间算起来就9-10个月,吃光这些东西,还是饿,因为食量太大了。
食量究竟有好大,没有确切的统计。
按毛泽东:
“忙时吃干,闲事吃稀”说法,也有计划,并没有“死吃哈胀”(胡吃海塞)。
广汉成都知青本来就少,除了兴隆和连山有八里庄中学的知青外,其余都是分散落户。
我一般不去“串队”,目的是免得人家回访,招待不起。
农忙的时候,每天煮一次饭,一次用队长借给的“升”量一平升米,3斤多一点,全部“焖”成干饭。
早上饿着肚子去出工,中午回家马上煮饭,不然等休息一会儿再煮饭,米还没开锅,农民些家里有老人煮饭,人家就已经喊出工了。
饭一“倒气”,马上从中间按直径划成两半,就着泡的整块酸萝卜狼吞虎咽;留下半锅,晚上收工回家,两把火热得温热,继续狼吞虎咽。
收麦子和菜籽的时候,早就没有米下锅了,等到生产队分了洋芋和新麦子,锅里煮半锅洋芋块,旁边贴上一圈新面粉做的饼,按上面的办法操作。
农闲时,煮2/3升米,加上一大瓜瓢红苕块,煮成一大锅红苕稀饭,分三次吃完。
嫌吃饭的碗小了,还专门去场上供销社买了一最小号的搪瓷洗脸盆当成饭碗。
每天消耗的食物,折合成原粮,少则2斤多,多则接近4斤,那区区720斤原粮当然不够吃。
于是为修好“五脏庙”(肠胃,成都俚语),也就是那时候知青流行“吞饭”“杀伙食”(吞饭、吃饭,杀伙食--用种种办法混饭吃,知青流行语)等词语,煞费苦心地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
喝蜂蜜 川西地区,每到油菜花开季节,就有放蜂的人从南面逐花而来。
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一个原来的寺庙“巫家寺”的后面两重殿,大雄宝殿和前殿已经在宝成线修路时拆毁,后面的林盘就是放蜂人的宿营地。
晚上无聊孤寂到极点,经常到他们的宿营地看他们摇蜂蜜,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一天,蜂蜜摇完了,看见养蜂人把蜂蜜面上漂的蜂蛹舀到碗里隔水蒸。
一见有吃的,馋虫被逗起来,于是找话题和养蜂人神侃,意在拖延时间分一杯羹。
养蜂人看出用意,用一个小碗给我舀了一点。
那个好吃哦!
现在想起来还齿颊留香。
吃完了,还涎皮赖脸的要再舀。
养蜂人正色道不能多吃,吃多了会“服不住”(受不了)。
不信这个邪,一番死磨滥缠后又吃了一碗。
第二天早上醒来,无论如何睁不开眼睛。
摸到镜子,用手搬开眼皮一看,眼皮水肿成了“汤司令”(电影地雷战里的汉奸,有格外肿胀的眼皮),当然睁不开。
吃肥料 点小麦的时候,习惯是用熔化牛油拌种,然后再加上磷肥粉裹成一个个的黑颗粒。
牛油那时候是没有人吃的,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农民,也不会打牛油的主意。
队上的牛油就堆在保管室外面的屋檐下,一看左右无人,用报纸包上一块就跑。
晚上,现在门口的苕田里扯几根苕田萝卜,切成细丝用牛油一炒,加水烧开再丢几根干面。
好大一锅,煤油灯下也分不出面和萝卜,就站在锅台边一碗接一碗的吃,直到不敢弓腰,唯恐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倒出来。
很多年以后,想到这东西好吃,照此操作,虽然鸡精、胡椒放齐,但是已经吃不出当年的感觉了。
孟子“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说法,由此相信。
偷公社南瓜 要想得到公社推荐招工,得表现积极。
使劲挣工分,“丰收舞”(成都知青专用名词,偷农民和生产队的农作物和家禽)少跳。
为了回城,不少恶行被迫收刀拣卦。
不久,公社认为我还可以教育转变,要大队选我成“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到公社开“先代会”。
他们哪里知道,人在会场坐到,心里却“贼心不死”。
上厕所路过公社食堂,案板上一个“癞子南瓜”,外观只有那么标准。
一看左右无人,抱起来就扔过后面的矮墙。
会议结束,外面秧田里捡起南瓜“凯旋’而归,晚上自然焖起南瓜干饭大快朵颐。
打狗 每到菜籽开花的季节,疯狗出没,只要发生一例疫情,县上就组织打狗。
各个林盘的农户的狗,只要不栓好,一律捕杀。
农民们都是乡里乡亲,不愿意得罪人,还不愿意杀生,不参加这件事,打狗队的成员自然是以知青为主。
每天10分工分记起,一柄锄头扛起,在公社范围的每个林盘巡游,一见没栓好的狗,逼到角落,两锄头打死。
遇到不要死狗的农户,狗尸拿回家里剐了,加上干海椒炖了吃。
狗们肯定有交流的办法和狗语,直到离开乡下,公社范围的狗,不管传说如何凶恶,见了我都只有夹起尾巴逃跑。
跳“丰收舞” 要“凫上水”(骂人的话,伪装积极),偷鸡我不敢放手。
根据其他地区知青传授的经验,丢上几颗谷子,待鸡过来啄食,一根细竹竿横扫,击中鸡的颈部,鸡立即倒地抽搐。
迅速塞进帆布书包,溜之大吉。
关键的问题是鸡毛不好处理,农妇丢了鸡,会大范围搜寻,发现一地鸡毛立马漏馅。
最好下手又最解决饥饿,偷玉米是最佳选择。
玉米刚刚灌浆,晚上背起书包出去,选一个离住处远一点的玉米田,钻到田的中间开始掰,留下田边的不动就不会被人发现。
回到家里,煮上一锅,灶里再塞上两个烤起。
吃完了,所有玉米皮和芯全部丢到门口沟渠内冲得无影无踪,待到收玉米时发现田中间只剩杆杆没有玉米,与我何干?
黄鳝 青蛙的“天敌”广汉的农民很少吃黄鳝,即使有几个少年扑捉,也是为了卖到县城里换点盐和煤油钱。
青蛙更是没有人吃的东西,谁要是吃青蛙会被人视为“怪物”。
几杆烂纸烟,求少年教他们的“秘笈”并得到一把黄鳝夹夹(逮黄鳝的工具)。
轮到自己操作,全然不是那么简单,弄得满身泥浆还“斩获”寥寥。
花5角钱买少年的,囊中羞涩也买不到几回。
至于青蛙,那就“如探囊取物尔”。
电筒一照,趁青蛙不动之际一竹竿“掺”得四脚朝天,一会儿就是一“笆笼”(竹编容器)。
拿回来剐了,只要后腿,用一点油,大火炒食。
最后,吃得我队蛙声稀疏,队长打招呼才收手。
从此,一辈子不再吃蛙肉,哪怕是“干锅美蛙”,进口就是一股土腥味,马上想吐。
吃援越大米 队上每年会接上级任务,为援助奋战在抗美前线的越南兄弟上缴若干高品质大米。
所谓高品质,谷子不能用打米机打,要用传统的水碾,还要用风谷机多次筛选,保证碎米率达到高指标。
这些米要交到离队上8里路粮站,而且队长安排送粮都是在接近收工的时候。
队上的壮劳力有加重自行车,两百多斤米装车上,一会儿可以跑两趟,我却只有用“鸡公车”推。
两麻袋米,大约500斤,平时不成问题。
可是有一天下午就不行了,中午的红苕稀饭已经消化得差不多,推到一半路程时,人家骑自行车的已经完成了两趟,还催我走快些,粮站就等这一车好记账。
要到粮站的路,有一个缓坡,不是很陡,但是很长。
车行到坡底,只觉得虚汗涟涟,眼前无数金花晃动。
坐下歇一会儿没有好转,该死的是路上没有行人,不可能有人搭把手。
晓得这是饿了(当然不清楚这是低血糖现象),顾不得啥子“光荣的政治任务”,解开米袋子,刨出一些装在帆布书包里,摇摇晃晃的走到一里外场镇供销社饭铺。
倒出米一称,2斤1两,先是要饭铺换成4碗4两的米饭加两碟5分钱的泡菜,一阵狼吞虎咽下肚。
吃完了,汗不冒了,金花也消失了。
剩下半斤,觉得还有剩余的地方可以装下,又要饭铺煮成一大碗面吞下。
事毕,摸摸肚子,感觉到吃饱了的快意。
快意一过,感觉恐怖,原来要吃饱要这么多粮食啊!
虽然饭铺肯定克斤扣两,但是实打实的1斤7两是没问题的,按此计算要保证餐餐吃饱,720斤原粮的定额要翻一倍,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辈子都会维持半饥饿状态。
争当点种人 队上有一块旱地,每年要种黄豆;所有水田的田埂上也要用“打杵子”杵上两排坑洞点黄豆。
两人一组,一人用锄头或“打杵子”(川西农具。
有一个“Y”形木把,下端有铁制筒状物),一人丢种,轮换进行。
想偷奸耍滑和有更深的企图,总是争着点种。
估计要“歇间”(休息)了,事前就把两个破旧中山服的口袋里装满豆种。
一到休息,借口回家喝口米汤,把剩余的豆子倒在家里。
上下午休息两次,晚上一碗香喷喷的炒黄豆就有了。
好景不长,队长出工前宣布,所有豆种都用“1605”拌了,吃了要“醪人”(中毒)的,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不敢再打主意。
吃老鼠 保管室的谷仓里有许多老鼠,天吃谷子、米、麦子长大,个个膘肥体壮,摆到面前的肉哪有放过的道理。
几天观察,发现老鼠在木板谷仓底下咬了一个洞,由此自由进出。
约上队长的儿子(和我同年同月同天出生),我钻进谷仓底部,双手用一根麻袋口圈住洞口,要他进保管室惊动老鼠。
只感觉到老鼠一个接一个的钻进口袋,扎紧袋口钻出来,把麻袋按到沟渠的水里,一会儿,吱吱乱叫、拼命挣扎的动静都消失了。
“惊世骇俗”的举动,引得农民围观,都说“雷娃娃”居然要吃耗子。
众目睽睽之下,把老鼠一个个全部模仿剐兔子的模样加工,用盐腌好,一根篾条穿了,挂在灶门上熏。
多年以后,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宴会上吃到“鼠干”,才晓得这不是我的发明,是一道难得的美味。
挣“耙合”工分 凡是有“耙合”工分挣,又能吃饱饭的机会,都千方百计的去钻营。
冬闲时,川西各县都要组织各公社的壮劳力到上游彭县的“官渠堰”整修河堤。
修堤的人,每天只交大米一斤,但是“甑子饭”敞开舀,还记10分工分。
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不顾那时候才16岁,身高不过一米六多一点,抬“连二石”(石条)勉为其难,报名参加。
一天,县上革委会的头脑来视察,见河对岸的什邡民工修的河堤上有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写在修好的河堤上,于是发话,广汉修的河堤上也要写一幅。
字要比对岸的大,字数要比对岸的多。
带队的干部发愁了,哪里去找写这么大字的人?
仗着文革时期练就写标语大字的过硬功底,毛遂自荐,接下了这个“业务”。
接到接下来了,可是好久写过20米见方的黑体大字?
没法,晚上睡到铺上冥思苦想。
第二天,让几个农民牵绳子,在河堤上下先画出直线,量出距离和间隔,用白石灰标出格子。
我拿红绿彩旗走到河对岸,指挥他们在河堤上移动一块红布,约好红旗指向的方向就是他们移动的方向,绿旗一举就停止,用白石灰标记那个点。
关键点定好了,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一根长竹竿比量笔画的宽度,用白灰勾出轮廓,余下的事就是农民用石灰浆“填红”。
半个月过去了,我“优哉游哉”好不快活。
县上革委会的头脑再来视察时,一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巨型标语已经出现在河堤上,自然是勉励有加。
字写完了,还是继续去抬石头。
同队的魏家三兄弟,个个膘肥体壮,从下乡时就千方百计要欺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原因),看见我轻飘飘的就挣了那么多“耙合”工分,天天找我“捉对”抬石条,他高我矮、他壮我弱,还有意要我走靠坡的那一边。
要是脚一软滚下去,接到滚下来的就是石条。
几天以后,受不了了,但人家是副队长,在队里是一个大家族,要“凫上水”不敢惹,咋办?
想起听说的一个整人的办法。
晚上等他们全部睡死了,悄悄爬起来,用草纸片沾上白酒,揭开被子下方,贴在脚心的“涌泉穴”上。
第二天天不亮,几兄弟爬起来洗内裤,边洗边埋怨:
“狗日的活路这么恼火,还要“跑马”(遗精)!
”这一下该我提劲了,来三!
继续抬石头。
农民对这个生理现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抬起石头觉得脚杆“打闪闪”,第二天就找借口请假溜回队上,日子也就好过了。
忆苦饭 农村“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节目,全大队的人在大队开会,事前会安排妇女在苕田里摘许多苕菜,煮成大锅的苕菜稀饭,待会后大家“忆苦思甜”。
台上老贫农忆苦,头几句还合标准,三句话后就不能听了。
“吃食堂那几年哦,啥子都没得吃的了,娃娃些饿得连“巫家寺”的高门槛都“恰”(跨)不过,要吃饭要爬到上头滚进去…….”。
虽然听得好笑,却一心想到的是苕菜稀饭好了,没有菜咋个吃?
“走遍天下离不得钱,山珍海味离不得盐”,在近处农民那里要了一些食盐,安心等候开饭。
开饭了,所有农民都象征性的舀上半碗,就连小孩也是如此,唯独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捧着大碗边吹边喝,一头大汗……。
农妇们在旁边交头接耳,胆大的给我说,苕菜稀饭是喂才断奶的乳猪的,哪里是人吃的哦?
管他的,无外是“断齑块粥”,加上盐还是不错的“正餐”。
大队书记曾信民看了也觉得好笑,说是态度端正,我也顺着说:
“认真体会!
认真体会!
”
即使仓满粮足,也要有燃料做熟,不然就茹毛饮血。
队上分配燃料,菜籽杆、麦草、玉米秸秆,按人头加猪头(猪的多少)为单位来计算,单身汉按三个计算。
农民一家烧一口灶,我一个人烧一口灶,燃料消耗的增加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
一点燃料,几天就烧完,还得费尽心机搜寻可燃物。
无奈之际,连改土平坟挖出的腐烂棺材板都拿来烧,弄得一屋子恶臭。
……
所有努力还是有效果,招工回城体检,脱了衣服外科检查,身高1.75米,体重140斤。
全身古铜色,肌肉块块毕现,全然没有“枵腹饥僝”的样子。
知青生活留下的许多烙印,一辈子都不会消失。
回城几十年了,每顿饭必须有一碗米饭加泡菜,不然就会觉得差了什么。
即使是刚吃完龙虾刺身的宴会也要服务员送一碗米饭加泡菜,全然不顾别人讪笑,“老孪二”(成都知青专用语,对农民的蔑称)的本性不改。
下乡时,行囊里有一本《中国电影》1957年11、12期的合订本,里面刊登了苏联作家、导演杜甫仁科的电影剧本《海之歌》。
这个剧本获得“列宁奖金”不是浪得虚名,看完会得出一个结论:
每个人都需要拷问自己的心灵,里面是大海的广阔还是泥潭的狭窄。
广阔使人幸福,狭窄使人悲哀。
天天为一粥一饭苦恼,心灵会变成何等的扭曲?
摆脱这种烦恼,哪怕是暂时的,都是必须的。
所以,就有了下面每天必修的“功课”。
唱歌 知青流行的“黄色小调”不会唱,没有那个生理渴望要宣泄。
夏天晚上,跳进门口的溪流洗澡,让小鱼吸吮满身过敏而起的脓包。
舒服过后,对着黑暗的原野放声歌唱。
最常唱的有几首:
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哪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苏联电影《亲密的朋友》插曲,“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苏联歌曲《海港之夜》,“……再见吧可爱的城市,明天将航行在海上。
明天黎明时,亲人的蓝头巾,将在船尾飘扬”。
没有听众,尽力把对生命美好的渴望表现在歌声中,白天的劳累和郁闷就好了许多。
看书 下乡时带了几本书,分为三类,几本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等;三本中华活页文选;一套四本《战争与和平》。
下乡时特意买了一个三号桅灯,破败的小草屋中一切东西脏乱不堪,唯独这盏灯擦得明亮如新。
睡上床,把桅灯摆在枕头边的一摞书上,就开始“神游”。
马列著作艰深难懂,我对革命又全无兴趣,读起打脑壳。
直到一天在县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自然辩证法》,回家一读,快哉快哉!
反复读了许多遍,还在书上用红蓝铅笔细细标注,写上心得和批注。
中华活页文选辑录了大量古文,其中有许多是中学的课文。
反复阅读背诵,基本上就完成了全部中学的语文课程,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语法和写作方法,这一辈子写点东西还不成问题。
终身难忘的是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一个大丈夫的柔情与豪情跃然纸上。
尤其令人感动是读到: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
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
抑汝能之乎?
”孤灯摇曳,一声哽咽,两颊挥泪如散珠。
四本《战争与和平》,1964年版,布面精装,封面上印着一只步枪和一根绿色的橄榄枝。
这本书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到现在还能背诵中间的若干章节。
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奥斯特里兹的山岗上,看着天上的白云依然缓缓地在苍穹上移动,想到人间的争斗是那样的渺小和无意义;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站在春水泛滥的渡口边,望着天边的晚霞,谈论什么是来生;娜塔莎坐在窗台上,望着皎洁的月亮……。
读书可以暂时忘却饥肠辘辘,觉得林觉民烈士临刑前在一方手帕上一气呵成千古绝唱的情景就在眼前;也能幻想就在俄罗斯广袤的田野和白桦林中,闻到了矢车菊的芳香……。
怀念那几本书,没有它们,我一定除了忍受肉体的饥饿外,还要忍受精神的饥饿。
除了饥饿的困扰,避不开的“性启蒙”也是困扰我的问题。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启蒙,已经成为现在社会重视的大问题,有专家、有专著、有讲座。
随便“XX”一下就得到了下列词语:
“性启蒙的定义是:
通过言行来提供关于生命、繁殖和性交的基本知识,帮助青少年建立责任感并在性关系中承担应有的责任,理解家庭和文化中的价值观,建立他们自己认同的观念,增强自信,认识和理解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关系带来的责任。
”基本知识、责任感、价值观、认同的观念……,多么重大严肃的问题啊!
我们这一代也年轻过,虽然每个人得到这种启蒙的时间、方式不同,但是都经过这种启蒙。
相同之处在于,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正处于一个压抑人性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小说、电影、美术、戏剧直到群众性的文娱演出,都鲜有爱情的内容,性更是讳莫如深。
性被看作是龌龊的、淫秽的、低级下流的。
那时候公园、餐馆、电影院、大街上看不到情侣们手拉手,也看不到热恋的人拥抱接吻。
因为那是行为不端和道德败坏,是耍流氓。
如果男的被冠以“骚哥”(流氓,成都俚语)头衔,女的被加上“梭叶子”(妓女,成都俚语)的称谓,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情。
我从小爱好画画,先是画静物、风景,1958年的贝尔格莱德世界儿童画展,我的一幅画得了鼓励奖,奖品是一盒48色彩色铅笔。
到了小学三年纪,晓得如果没有老师教,自己涂鸦,技艺再不会有长进。
请老师教艺术,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一般家庭难以企及的开支。
五岁的时候曾经请一个川音的老师教小提琴,“束脩”(老师酬劳)要每月七十元,只能放弃。
不可能请绘画老师,少年宫绘画班的各种石膏几何体早就画了N遍,奈何?
看见美术教科书称:
画人体素描是每一个画家的必修课。
人体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变化最多的东西,画得越多,基础越牢。
不可能有现实的“魔豆”(网络语言:
模特),这是做不到的功课,只能在胡开文文具店买一个维纳斯和一个“腊孔”头像的石膏像画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把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著名雕塑照片画了N次,《大卫》、《吻》等等。
有这段经历,对异性的裸体不陌生。
年纪太小,没有任何冲动的想法,感觉只是比石膏几何体更复杂的写生而已。
上了中学,大环境的气氛是援越抗美、是猪湾登陆战、阶级斗争、刘文彩等,在这些关键词引导下,加上班上大多数人都是小学五年教改班的毕业生,年龄比一般68级的小一岁,所以少男少女之间的火花几乎可以说没有。
某男同学给同桌的女同学三颗水果糖;某男同学和某女同学在小学同台演出《美丽的哈瓦拉》等等,都成了男生们肆意踏谑的谈资。
现在想起来,一群昏娃娃,不晓得禁锢了好多“多情”、“怀春”的同学,摧毁了好多“至纯至美”的好事。
下乡之前的复课期间,情况毫无改善。
主流的男生群体,忙于咋个翻出墙边厕所的窗户,逃脱工宣队的“忠字舞”训练;忙于咋个避免休息时抽劣质纸烟,进教室时不被工宣队“水”(许)师傅发现。
班里最早“醒事”的男同学T见我等这样“冥顽不灵”,数次大呼:
初68.1班,该天亮了!
所谓天亮,就是该“扇盒盒”(耍女朋友)了。
T同学本人,忙于在各班女同学里寻找有几个“粉子”(漂亮女孩),哪几个是“巨粉”(极其漂亮的女孩),最后居然和街对面27中的好事者,评出了四中的“五朵金花”。
大部分男生就在浑浑噩噩中嬉闹,直到“作鸟兽散”,下乡插队。
那个年代的农村,落后、偏僻、贫困,毫无娱乐可言;吃饭、干活、睡觉构成了农民的全部生活内容,每天都重复着上一天的故事,时间空间似乎凝固了。
而性话、性笑话,就在这平静的水面中激起圈圈涟漪,是枯燥的生活的调味剂。
下乡插队,尤其是单独插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种氛围中。
我的性启蒙教育是被农民启动的,田间地头,性是农民的主要谈资,且无论男女。
刚下乡时,农民认为我干不来农活,只能和妇女一起出工。
那些结了婚的农妇在田间的主要话题无不涉性,包括和老公的性事,描述、交流、相互揶揄,说得兴起,越来越不成体统,经常要妇女队长谭金秀呵斥才暂时打住。
麻烦的是,说着说着就轮到已经躲得远远的我身上,一个说:
“雷娃娃,你有没有盒盒?
”,另一个接上:
“他?
毛都没有长全。
”,再一个接上:
“你看到了嗦?
”……,有本事你就接招,那就会说得更闹热,皆大欢喜;没有本事,最好是不开腔。
稍后,学会了不少农活,和男劳力一起出工。
男人在一起,说起性话题更肆无忌惮,那是你躲不过去的。
队上有一个“老革命”谭克成,解放前被抓壮丁,宝鸡战役时被解放,参加了一野。
兰州战役时他身带数个炸药包,在攻克外围阵地时立了大功。
本来想听听兰州战役亲历者的叙述,可是三句话后,他讲的却是驻守北疆时,哈萨克姑娘和他男女混浴。
还有一些不雅的语言和劳作分不开,抬拌桶、打谷机,抬后面的人是看不到路的,前面的人要给后面的“报路”。
“天上明晃晃”,后面接“地下水凼凼”;“天上鹞子飞”,后面接“地下牛屎堆”……,古来有之,是劳作的必须。
一些农民在走平路的时候也会“报路”,用“荤”话插诨打科,“天上乌云撵乌云”,“好吃不过茶泡饭”等等,如果我抬后面,只能接“地下婆娘撵男人”,“好耍不过人重人”。
倒是和读过书的富农分子代友根,还有交流《桃花源记》等古文阅读心得的可能。
队上的未婚男女就是这样完成的性启蒙,有胆大者还“野合”,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忌讳。
一天晚上,从县城回来,路过生产队的谷草堆,听见草堆有悉悉索索的声音。
电筒一照,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正行“云雨之事”。
我大窘,未等看清是谁,连忙关了手电急步离去。
走得太急,慌不择路,田埂上一滑,栽入秧田。
肯定当时我的样子极其狼狈且极其好笑,以致当事者居然在我身后笑出了声音。
日积月累,原来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中那些懂不起的涉及性行为情节,似乎有了清晰的注释。
现在看来,这些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偏僻的农村,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一些原始状态的人性,一代代的性启蒙就是这样完成,谁都改变不了。
即使是孔老夫子参与编撰的《诗经》也无可避免的保留了一些民歌中的涉及性行为的词语,例如《野有死麕》中: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用大白话翻译出来,一样不雅观。
真正使我“修完”性启蒙课程的事情,来源于本队的“土知青”(本地知青)和与知青相关的事情。
生产队在我落户前后,还有三个本地知青落户,两女一男。
女知青Z,比我大,相貌身高大概可以打70分左右,下乡前就和高中的某同学耍朋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叫“闶了盖盖”;女知青G,年龄和我相仿,相貌属于等外品,“吾不欲观之矣”;男知青H,比我大一点,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伙同几个当地土知青,在县城和各公社流窜,据说是从事“杀鸭子”“接表哥”(扒窃)勾当。
自认为我乃“洋知青”,不愿意和他们来往,所以基本上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农业学大寨”标杆队,农闲时晚上开会读报是必须的程序,不去参加当日的工分就不记,所以每个人必到。
昏暗的油灯下,我读报纸,周围的农民个个昏昏欲睡,鼾声不断。
1971年夏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