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文摘故乡费里尼.docx
《《大家》文摘故乡费里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家》文摘故乡费里尼.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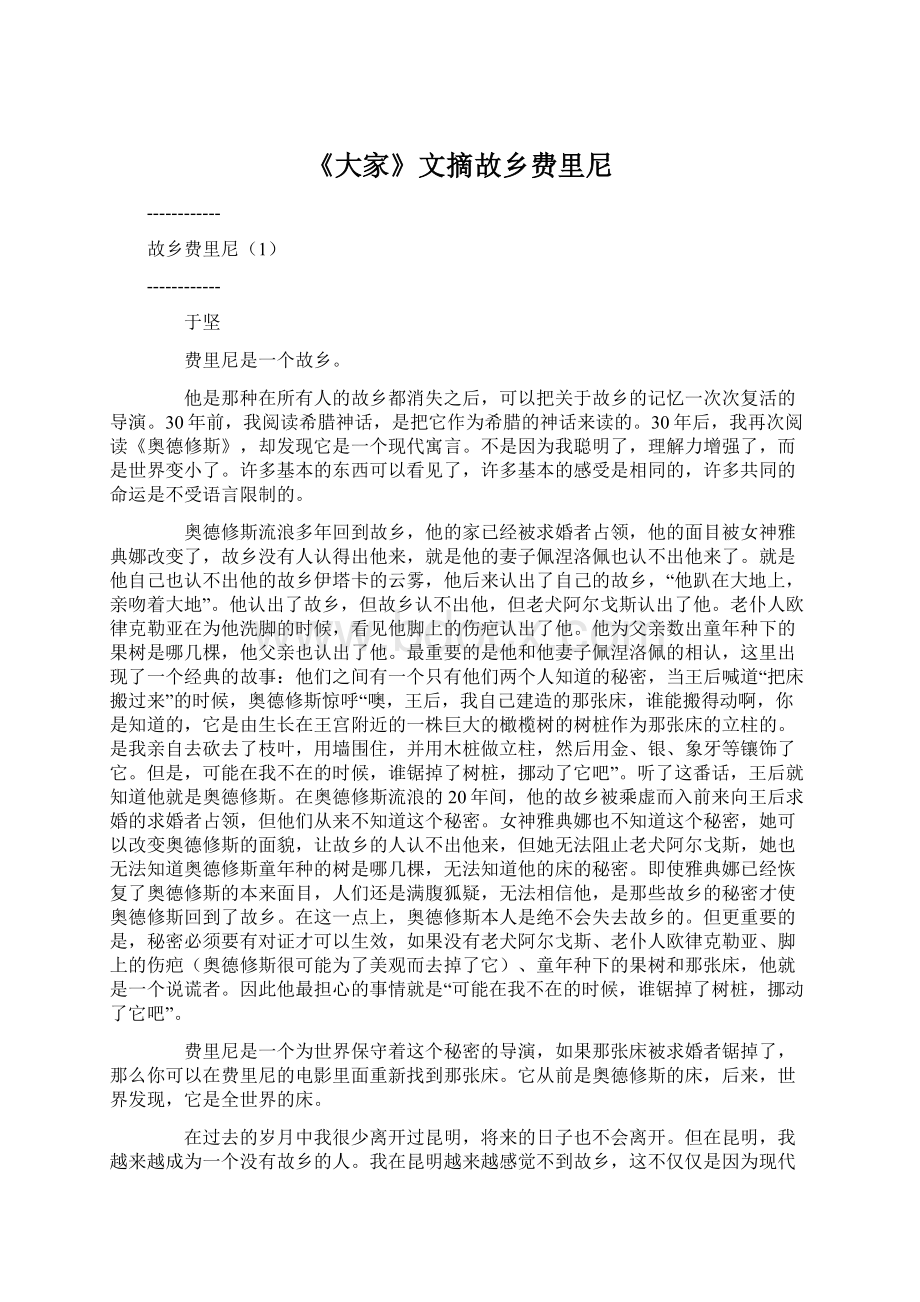
《大家》文摘故乡费里尼
------------
故乡费里尼
(1)
------------
于坚
费里尼是一个故乡。
他是那种在所有人的故乡都消失之后,可以把关于故乡的记忆一次次复活的导演。
30年前,我阅读希腊神话,是把它作为希腊的神话来读的。
30年后,我再次阅读《奥德修斯》,却发现它是一个现代寓言。
不是因为我聪明了,理解力增强了,而是世界变小了。
许多基本的东西可以看见了,许多基本的感受是相同的,许多共同的命运是不受语言限制的。
奥德修斯流浪多年回到故乡,他的家已经被求婚者占领,他的面目被女神雅典娜改变了,故乡没有人认得出他来,就是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也认不出他来了。
就是他自己也认不出他的故乡伊塔卡的云雾,他后来认出了自己的故乡,“他趴在大地上,亲吻着大地”。
他认出了故乡,但故乡认不出他,但老犬阿尔戈斯认出了他。
老仆人欧律克勒亚在为他洗脚的时候,看见他脚上的伤疤认出了他。
他为父亲数出童年种下的果树是哪几棵,他父亲也认出了他。
最重要的是他和他妻子佩涅洛佩的相认,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典的故事:
他们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当王后喊道“把床搬过来”的时候,奥德修斯惊呼“噢,王后,我自己建造的那张床,谁能搬得动啊,你是知道的,它是由生长在王宫附近的一株巨大的橄榄树的树桩作为那张床的立柱的。
是我亲自去砍去了枝叶,用墙围住,并用木桩做立柱,然后用金、银、象牙等镶饰了它。
但是,可能在我不在的时候,谁锯掉了树桩,挪动了它吧”。
听了这番话,王后就知道他就是奥德修斯。
在奥德修斯流浪的20年间,他的故乡被乘虚而入前来向王后求婚的求婚者占领,但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秘密。
女神雅典娜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她可以改变奥德修斯的面貌,让故乡的人认不出他来,但她无法阻止老犬阿尔戈斯,她也无法知道奥德修斯童年种的树是哪几棵,无法知道他的床的秘密。
即使雅典娜已经恢复了奥德修斯的本来面目,人们还是满腹狐疑,无法相信他,是那些故乡的秘密才使奥德修斯回到了故乡。
在这一点上,奥德修斯本人是绝不会失去故乡的。
但更重要的是,秘密必须要有对证才可以生效,如果没有老犬阿尔戈斯、老仆人欧律克勒亚、脚上的伤疤(奥德修斯很可能为了美观而去掉了它)、童年种下的果树和那张床,他就是一个说谎者。
因此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可能在我不在的时候,谁锯掉了树桩,挪动了它吧”。
费里尼是一个为世界保守着这个秘密的导演,如果那张床被求婚者锯掉了,那么你可以在费里尼的电影里面重新找到那张床。
它从前是奥德修斯的床,后来,世界发现,它是全世界的床。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很少离开过昆明,将来的日子也不会离开。
但在昆明,我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我在昆明越来越感觉不到故乡,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化的推进使昆明焕然一新,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价值观、道德、速度都完全变了。
“可怕的美诞生了”(叶芝),但可怕不只是时代的新美学,可怕的是新美学对故乡世界的毁灭。
那些求婚者锯掉了那张床。
我记得在费里尼的电影《甜蜜生活》的结尾里面有一个镜头,人们从海里打捞上来一个四不像的怪物。
隐含在整个电影中的那种故乡世界就要消失的担忧成为一个具体的象征。
在费里尼那里,还只是对“要出事了的”隐忧。
在我这里,故乡已经成为无处可逃的落后于时代的怪物本身,“求婚者们”甚至没有为它准备一个墓地。
而那个费里尼电影中的怪物,则成为把故乡吃掉并受到欢呼的神灵。
奥德修斯最终杀死了求婚者,那些没有故乡的鬼魂,回到了妻子佩涅洛佩身边。
费里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只有自己在电影里重建一个故乡。
我的寓所外面是一大群玻璃和水泥的怪物,它们有着兵营的内部结构和自由市场的华丽外表,一到夜晚,距我家窗子数百米远的另一栋大楼的霓虹灯广告牌就亮起来,这是一个丧失故乡的时刻,置身其间,我每一次都不知道我身在何地。
几年前,我在荷兰的鹿特丹首次看见这样的场景,印象深刻。
鹿特丹在二战中被炸成平地,城市是重建的。
我住的旅馆外面包围着公司、商场、公寓。
一到夜晚,幽暗的楼顶上的某一块蓝色霓虹灯牌子就亮起来,上面的字母跳跃着,流动着。
它孤零零的,那一带的建筑物只有它一块。
下面是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灰色的灯光亮着,看起来像实验室或者医院。
因为时差,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愣愣地看着那霓虹灯广告牌,等待着睡意来临。
它比什么都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这个词的含义。
后来我在巴黎的飞机场的机舱口,另一个雨夜,我们的飞机因为雷阵雨被迫降在巴黎,我再次看见黑黝黝的建筑群之上孤零零的霓虹灯广告牌,后来我在悉尼的一家旅馆也看到过。
最后这家伙来到我的故乡,就在我的窗子外面,雨夜、秋天,一到夜晚就是它的世界,总是这样,吸引着我的目光,使我在自家的窗台上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异国的什么城市,在鹿特丹,在哥本哈根……我的故乡并没有经历过大轰炸,然而,那令我们摧毁故乡并重建一切的是什么?
我在某个早晨进入费里尼的电影,我进入的就是《想当年 我记得》。
我是一个鸡鸣即起天一黑就定要睡觉的人,这是童年时代在故乡世界养成的生活习惯,也确实是一只大公鸡帮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我记得当年我住在一个干部大院里,那个大院像一个村庄那样,大多数人家都养鸡,但是没有专门的鸡舍,天一黑,鸡们就三三两两各自回自己的家去,我永远记得童年时代的那一幕,鸡探头探脑出现在家门口,黑夜也就跟着来到了。
我家用一个鸡笼把鸡关在桌子底下,天快亮的时候,它就嘹亮地叫起来。
我小时候不喜欢它,非常仇恨它,我总是还在梦乡就被它吵醒,鸡一叫,外祖母就起来把它放到外面去,我又回到梦里,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大公鸡,或者说它们有过很多只,但在我的记忆里只是那一只。
这只鸡使古代的时间延续到我的生命中,我成为一个总是遵循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规律的人。
即便后来我家取消了养鸡的古老传统,我依然是鸡鸣时分即醒来,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灰蒙蒙的黎明。
有一日我看一部法国电影,说那个主人公专门到乡间居住,为的是享受黎明,每天像世界那样开始和诞生,但最后他失败了,他的生命已经无法黎明即起。
我这才意识到我是多么有福,我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稀有的和“农民式的”,就像城市人今日视为珍稀的“土鸡”一样。
感谢神,在我生命里延续了故乡的时间,土鸡的时间。
这种习惯在今天已经成为朋友们的笑柄之一,它意味着一个守旧的、不入时的落伍者的滑稽形象,世界的时间观已经改变了,人们正在研究可以使春天在九月到来的技术,一只在漫天飞雪中开屏的孔雀。
我一意孤行,因为起得早、睡得早,我在这时代里常常感到孤独,思想的孤独是来自生命和生活习性的孤独,我经常早早地开始工作。
等待着那个夜生活过度、眼睛浮肿的世界醒过来,我在世界的梦里写作。
所以我第一次看费里尼的电影,是在早晨八点钟,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会在早晨八点钟看费里尼电影的人来了。
为了可以播放这个片子,我新买了DVD,我不太会使用它,我不知道这个机器里面有一个语言字幕显示的选择键。
《想当年 我记得》这张碟有意大利语、英语和汉语可供选择,放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片子没有翻译过来,我就看意大利语的,就像老费家的邻居一样。
我发现我完全明白这片子说的是什么,甚至猜得到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大笑、微笑、会心一笑,仿佛这电影说的是我少年时代的事情。
后来马云告诉我有一个语言选择键,我才又看了一遍汉语版的,那些台词和我猜的差不多,尤其是那个疯叔叔爬到树上去喊的那些话,我猜那是在喊“我爱什么人”吧,他喊的是“我要一个女人”。
他渴望的是基本的东西,女人和生殖。
------------
故乡费里尼
(2)
------------
费里尼创造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故乡。
这个故乡不是费里尼的故乡,而是人类基本的故乡,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个故乡,那个早晨,在昆明通过一部意大利的电影我重返故乡。
费里尼的力量就是这样,他为我们保持着故乡,使我们关于故乡的秘密不会死无对证。
他把那张床重造在他的电影里,并且永远不可能被锯掉了。
“这个过去应该要像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的历史了然于心那样被保存下来,值得好好体会以便更有意识地活在此刻”(费里尼)。
在这个时代,故乡自己没有力量保存它自己,保存故乡成为诗人和艺术家们的使命。
我可以通过费里尼的电影回到故乡,就像惊讶的奥德修斯,九死一生回到伊塔卡,发现他的妻子依然在116个求婚者的包围中等待着他。
就像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一片乡音中热泪盈眶。
费里尼的镜头对准的是最基本的事物。
那些场景甚至在普通的下面,比普通更为基础。
河流,普通的是水,但更基本的是河床,是河床中不动的石头。
普通流逝了,但河存在着,河并不是水。
使河存在的那种东西是容器,费里尼表现的是容器,是床,是这个世界得以承载的那种东西。
悖论是,他是以一个说谎者的身份重建故乡的。
他用谎言来保守一个真实的秘密。
里米尼已经不存在了,他只有虚构出它,但他虚构的不是里米尼,而是世界关于故乡的记忆,他没有说谎的是记忆。
他的谎言是里米尼。
记忆是真实的,记忆引发的感动是真实的,是不是那张床不再重要,锯掉它也可以,但只要进入费里尼的电影,床就会出现。
每一次进入费里尼的同一部电影都像是进入一部新电影,就像人生本身,在现场的人总是忘记了刚刚发生的,只是在特定的时刻,才可以记忆。
而每一次记忆都是不一样的。
人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人也无法重现同样的记忆。
无论记忆起来的细节如何彼此矛盾,重要的是记忆本身,它是河流,你一踏入,往日就会重现。
他的电影像人生一样没有戏剧性的机关,只是有冬天、春天、早晨、晚上这样的顺序。
你进入过这个电影但你无法完整地转述它,你最多只可以讲出一些片段、小段子,这就是记忆。
记忆不是回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心灵通过时间之流在此刻复活。
故乡是令我们复活的地方。
它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我记得”,只是一些片段的组合,却有整体的力量,令我们深陷故乡之中。
他是一点小花哨都不玩的导演,正因其如此,后来的导演才从他那里出发,玩出许多新花样。
例如在貌似现实主义的氛围中,总是出现反常的事物,一只在冬天开屏的孔雀、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怪物等等,这种费里尼式的象征被后来的导演尽情发挥,例如安东尼奥尼的《放大》,结尾时出现的那些戴假面具的人。
费里尼表现的并不是某种怪力乱神、荒诞不经的事物,而是一种预感,在那些最具漫画风格的场景中,它暗示的依然是最基本的情绪。
这电影是怎样强烈地令我回到故乡啊。
它的气味、氛围、语言、故事,我几乎以为我经历过那一切,我可以把我的“当年”与他电影中的“当年”互置。
文革、少年时代的青春期冲动,每个少年都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大众情人……一个伟大的故乡,电影中全城出动去大海上等到深夜看美国来的巨型游轮的那一幕,使我记忆泉涌。
我记得在1972年前后,昆明还是个比一个小镇大不了多少的城市,两个小时足够你把这个城市绕一圈了。
有一天,有一个谣言忽然传遍全城。
在北郊发现了一棵到下午六点钟就冒烟的树,某个黄昏,不约而同,倾城出动,人们穿过金黄的夕阳和田野,都去看那冒烟的树。
这是超现实的时刻,成千上万的人,黑压压地围着昆明卷烟厂附近的几棵树,伸长脖子,一直到黑夜来临。
那个时代人们渴望生活发生某种变化,已经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即使一棵树冒出烟来,他们也相信那是某种吉兆。
他们其实是指望那树尖上冒出一个戈多、一个上帝、一个新世界来。
这正是费里尼的电影要表现的,人们迷信着未来。
各种制度下的人民,存在状况肯定不同,但未来“将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渴望是完全一致的。
深夜的大海上,格蕾丝卡在灯火辉煌的豪华游轮经过的一刹那,张开手臂向那个现代天堂投去的一吻,其表现出的人类对某个虚无的现代庸俗而朴素的向往的真挚感情是无与伦比的,那是电影最伟大的镜头之一。
其实这并不是费里尼的意思,他是最没有意思的导演,因为“世间一切皆诗”,也就无所谓诗意与非诗意的,当他最无意义的时候,意义的潜流却汹涌澎湃,因为他有立场,立场自己就是坐标,自动释放着意义,而不是在某个沉默的星球之外释义。
费里尼的电影有一种活的互文性,你进入他的电影故乡,你却在书写自己的家乡。
第一个镜头是什么?
晾在阳光下的衣服,一个母亲出来晾衣服,抬头看了一眼晴朗的天空,春天的飞絮在飘摇。
一个镜头就把你带回了故乡。
仿佛你一直在那里,在那个女人的家门外晒着太阳,那个女人看天空的时候,你也看着她身体的某一部分,飞快地旋转着下流念头,她是王大娘家昨天来的远房表妹。
世界哪里没有这样的故乡呢?
最基本的故乡,它不会被任何意识形态所污染,它不能被普通话那样的语言暴力所灭绝,法西斯主义不是末日、集中营不是末日、文革不是末日。
可怕的末日是当这种镜头里面所呈现的生活的日常性都被摧毁的时候。
费里尼捉弄你,一个光头从理发室出去了,他的身份不清楚,也许他是纳粹分子或者街痞,那个深夜骑摩托穿过小镇的神秘人物,其表情意味深长、阴险、耐人寻味,你以为后面要出什么严重事情,凶杀、告密的电话,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此人在电影中也从此不见了。
中国电影导演最大的本事是把脸拍成正确的或错误的,或者高明一点,朴实或狡猾、高贵或粗野,人类的脸有这种性质吗?
费里尼说:
“所有的脸都正确无误,人生是不会错的。
”观众可以猜测想象脸的内涵和价值、意义、风格,依据约定俗成或者自以为是的知识、概念、教养和世故,把世界分成红脸、白脸,他们就是这样与世界的脸打交道的。
但费里尼从不这么做。
衣着光鲜的太太说的是“那医生是个傻B”之类的粗言秽语,英俊漂亮、符合《生活》杂志审美标准的男士同时也是智力方面的超标白痴。
人物的对话再日常不过了,仿佛都是在菜市场或者医院交费处偶然飘进耳朵的一句,却解构着整个电影。
晚上的规模浩大的迎接春天的营火活动是白天理发室的一位顾客摸着剃好的头随意说出来的一句,不过是说出了无数琐事的短语中的一句,耳背点还听不见。
他当然也可以在小便后抖动左腿,扣好扣子的时候说“革命开始了”,这种话不必只是在冬宫说。
------------
故乡费里尼(3)
------------
啊,格蕾丝卡,故乡的乳房和臀部,故乡的春梦、谣言和童话,故乡的激情、嫉妒与雄性较劲的机器们的加油站。
格蕾丝卡象征着生命的活力、希望和饱受折磨的热情。
谁的故乡没有格蕾丝卡,谁的青春没有出现过那个大众情人,“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歌德)。
结局都是一样的,最终黯然离去,背井离乡,“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我们总以为那是个奇迹,神话里的白马王子一类的故事一定会发生在她身上。
故乡所有的男子都在自卑中暗恋着她,以为她一定会嫁给“更某某的”,实际情况却是,她在激情、孤独与自怨自艾中等待着某个庸人娶她回家,她渴望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一个家而已。
她却被误解为好高骛远,直到她真的对故乡绝望,就要成为真正的怨妇的时候,终于跟着远方的另一位庸人背井离乡,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画工毛延寿。
格蕾丝卡的新郎令所有的观众失望,一个多么没有风度而且平庸的胖子啊!
费里尼的意思是,其实她本来是属于你的,是你让她等到三十岁,把她的一生毁掉了。
你受的教育,你的知识,你的教养都不允许格蕾丝卡嫁给你这样的小人物,你是故乡,而格蕾丝卡不是,她是未来,她是属于美国来的豪华游轮上的一员。
你从来不知道,格蕾丝卡也不是那游轮上的一员。
她是未来,但她是里米尼方言的未来,这个未来与过去并没有什么区别,传宗接代,生儿育女,这个未来就是电影开始处,一个母亲在柳絮飞扬的春天里晾衣服的情景,那就是格蕾丝卡渴望的未来,而不是什么美国来的大船。
但虚荣心令里米尼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一点,它只是小声嘀咕、犹豫不决。
老实说,在这一点上,里米尼除了体现在电影中的主人公蒂达身上的古典激情、青春期性冲动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力量,它从未像“现代主义”或者法西斯那样成为强有力的意志。
意大利是未来主义和法西斯猖獗的地区,费里尼对此刻骨铭心。
格蕾丝卡不是“现代主义”的未来,它是里米尼的未来。
当她走掉之后,里米尼的心就空掉了,人生忽然无聊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单调重复。
法西斯主义和现代主义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自命代表着“未来”,都是它自己时代的“正确意志”。
而在费里尼看来,真正的未来是里米尼的格蕾丝卡,但是她多么孤独啊,“没有人愿意娶我”,“未来”最终被迫背井离乡,未来没有家了。
作为象征,现代主义的未来是那只在冬天的雪花中不祥地反常开屏的孔雀,它使古典的时间发生了错误,而其实它是很符合现代主义时间逻辑的,速度快了,更快而已。
我经常在昆明看见招牌上写着什么“一分钟见效”、“中药提速疗法”。
而格蕾丝卡的未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正如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大地有大地的速度”,“春天并不是一部电梯/一按电钮/就升到绿色的那一层”。
在另一部电影《甜蜜生活》中,马尔切尼所羡慕的过着幸福生活(别墅、汽车、名牌衬衣、小康以上生活水平)的某人毫无道理和预兆地自杀了,我相信那个人就是“格蕾丝卡”的丈夫,那个里米尼俗人憧憬的未来。
在这个电影里面,反常的事物再次出现,在《想当年 我记得》中是冬天开屏的孔雀,在这里,人们从海里打捞到一个巨大的怪物。
我们生活在没有“格蕾丝卡”的现代主义未来中。
我们只有前进,没有过去。
套用福山的时髦理论,“格蕾丝卡”的历史已经终结,方言的历史已经终结,英语,哦,不,在中国是普通话和英语——以及塑料芭比娃娃和麦当劳快餐,是我们的未来和宿命。
费里尼对有心灵的人来说,是一个故乡,是对遗忘的治疗。
在《想当年 我记得》中,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小丑式的人物在介绍里米尼的历史,他提到但丁,这位伟大的诗人来过里米尼。
但丁,一个落满灰尘的名字。
只是在费里尼这样的诗人心中,他才继续活着。
这是但丁的故乡,但丁死了吗?
他是过去吗?
他不是未来吗?
但丁是一个故乡。
他不是什么中世纪最后的诗人和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那是以进化论为基线的枯燥理论,但丁是故乡。
他的故乡一直延续到费里尼的电影中。
格蕾丝卡——就是贝雅得丽采,诗人们的永恒情人,就是奥塞罗的苔丝蒙娜,就是被毛延寿遮蔽起来的王昭君,就是哈姆雷特的奥菲丽雅……当然,格蕾丝卡离我们最近,她就住在同一个大院里。
奥德修斯最终回到故乡,因为他妻子佩涅洛佩在无数求婚者中间等待着他。
格蕾丝卡的命运不同,她的故乡认为她应该嫁给美国大船上的求婚者,她的故乡自动锯掉了那艘船。
奥德修斯的流浪与我们时代的“在路上”不同,他的流浪是为了永远地回到故乡,我们的“在路上”是要抛弃故乡,抛弃最基本的世界。
别的不说,我们抛弃了多少脸孔啊。
昨天我看到美容院的整容标准照片,世界未来的脸只剩下不到20个模式,这是画工毛延寿的乐园。
格蕾丝卡就是故乡,女人是我们时代离故乡最近的。
男子们已经无可救药,是不想回家的奥德修斯。
女人,祖母、外祖母、母亲、嫂子、姐妹……为什么故乡是温柔的。
女人的古典传统、生殖创造的本能是现代主义最大的障碍,她们总是使一切付诸东流,重新回到最基本的记忆中去,生殖的记忆,生活的记忆。
现代主义用同性恋、用无数的美容院来对付女人,它们把格蕾丝卡的床锯掉。
但费里尼保存了格蕾丝卡,延续着格蕾丝卡,他使格蕾丝卡令人失魂丧魄地住在我们隔壁,瞧啊,她就是对面公寓七楼正在浇花的那位女士,她的裙子带来了春天。
费里尼是一个可以使你深入的世界,他是一个母的,如果你的心灵可以生殖的话。
你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你的心灵就越丰富,越深刻,虽然在我的词典里“深刻”是一个装样的词,但我还是要说费里尼深刻。
他是一个有立场和心灵如海的导演。
他并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批判现实主义者,他表达基本的东西。
基本,这个被喧嚣浮华遮蔽着的世界呈现时,你发现那是一个立场,费里尼是一个地主,他是有地的,他的立场、他的身体和他的感觉,他不是穿裤子的云。
这是基本的东西被表现出来的结果,基本的东西是不会自然呈现的,它不会像现实主义那样,自己有一层貌似朴素客观的外表,现实主义津津乐道的“客观”只是真实的幻觉,它只是巧妙地用朴素来虚构事实,它是没有立场的。
因为“事实变得更复杂,更多伪装,不再那么外显、那么招摇地渲染”。
“那个事实,因为藏匿在令人懊恼的熟悉之中,隐藏于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最显眼的事物之内,有其恒定的必然性和完整性,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我是说谎者》)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个熟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是那种把“招摇地渲染”着所遮蔽着的显示出来的能量,它是令事实虚假、令谦虚夸张、令愤怒平静、令暴力软下来的力量,一切都回到基本的层面。
费里尼的故乡并不是那些所谓美好的事物,那些在浪漫主义和小资格调中被广为称颂的温情事物。
《想当年 我记得》最初的另一个名字是《小镇》,但后来没有用。
故乡在当代文化中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心心相印的怀旧,夕烟、小镇、小桥、流水什么的。
这不是故乡,而是遮蔽着故乡、混吃混喝的求婚者。
费里尼的故乡是存在本身,它无所谓新旧、正确的、丑陋的、美好的、高雅、正派、粗俗等等。
它既包括里米尼小镇,格蕾丝卡、乳房巨大的小卖部老板娘,春天、雪、夜晚……也包括那时代意大利的法西斯空气,告密、审问和疯狂、道德败坏、淫荡,亲切、朴素、诚实、粗暴、残忍、夸张、虚荣、滑稽等等。
故乡世界不是正确的意识形态(既不是江湖的也不是庙堂的)所支持的乌托邦,而是存在。
它甚至就是制作费里尼电影的基本方法:
“拍片没有什么理想状况,或者应该说,各种状况永远都是正确的,因为就是它们让你拍出来你现在正在拍的电影。
”(《我是说谎者》)
------------
故乡费里尼(4)
------------
费里尼一再宣称,他的电影是表现的。
是啊,我们曾经再现过什么吗?
费里尼是诉诸感觉的导演,他是有力量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所谓现实的导演。
因此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导演,如果那种感觉是夸张,他可以夸张地表现,例如在《想当年我记得》中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一场戏。
如果那种感觉是形而上的,他可以抽象夸张地表现,例如海里打捞上来的四不像怪物等等。
而这种对感觉的忠实,比任何所谓的“现实主义”都更有力量,它恰恰呈现了生活的荒诞性、喜剧性和悲剧精神。
感觉是很容易飘掉的,而且感觉是没有方向的,费里尼的力量在于,他是一个有立场的导演,他总是能把他的感受控制在他的基本立场上,因此在他的电影里,我看到的是各种表现的和谐,《想当年我记得》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朴实动人的回忆,但它里面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多么矛盾。
夸张处几乎就是漫画,自然的地方,又像是纪录片的风格。
由此我想到中国电影,那些导演在所谓技巧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它们永远像音乐学院的苦练技巧,像为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的中学生那样,没有立场,没有灵魂。
他们偶尔也会拍出一点光芒微弱的东西,但后来你马上发现,那不过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罢了,所以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同一个导演身上。
他可以导演出《秋菊打官司》这种有点意思的,风格看上去也还朴素的东西。
突然间,他又飘到《英雄》这种毫无灵魂的商业片的羽毛上去了。
另一场戏拍的是在里米尼小镇的广场上举行营火晚会,迎接春天,烧毁象征着寒冷和饥饿的女巫的仪式。
这个场景令我把里米尼这个故乡与云南联系起来了,在昆明你已经无法拍摄到这样的事情,古老的迎接春天的仪式已经在革命中被禁止然后被遗忘。
想想中国城市今天所谓的“春节”,与五一节、国庆节有什么区别呢?
而“春节”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多么重要、繁琐、神秘的仪式啊。
里米尼迎接春天的仪式令我想起的是云南高原上那些少数民族的节日。
我记得居住在怒江附近的傈僳族有一个刀杆节,节日的尾声也是人们在火焰的余烬上跳来跳去。
费里尼如果要在云南找一个里米尼,他在昆明找不到,但可以在少数民族的乡村找到而且到位。
但在云南,这些破旧古老的“里米尼”在官员们看来,是多么落后和丢人现眼啊,它绝不是日常生活发展的方向,没有必要尊重和保留,只是旅游资源而已,由歌舞团来保留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如今里米尼的春天仪式是否也成了招揽游客的表演项目,费里尼已经死了,人们今天看的是电视——“一件家具”(费里尼)。
在1966年的革命之后,我对这个国家也曾经有些失望。
后现代式的“怎么都行”在中国有着天然的基础,其根源可以上溯到“道在屎溺”。
费里尼也讲老子,但他从老子那里获得的是立场。
这种立场针对有着逻格斯和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文化是新的血液。
“当然,《想当年我记得》并未通过意识形态和历史鉴定的角度,由外对法西斯进行审核、还原及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