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福建钱币学会教材.docx
《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福建钱币学会教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福建钱币学会教材.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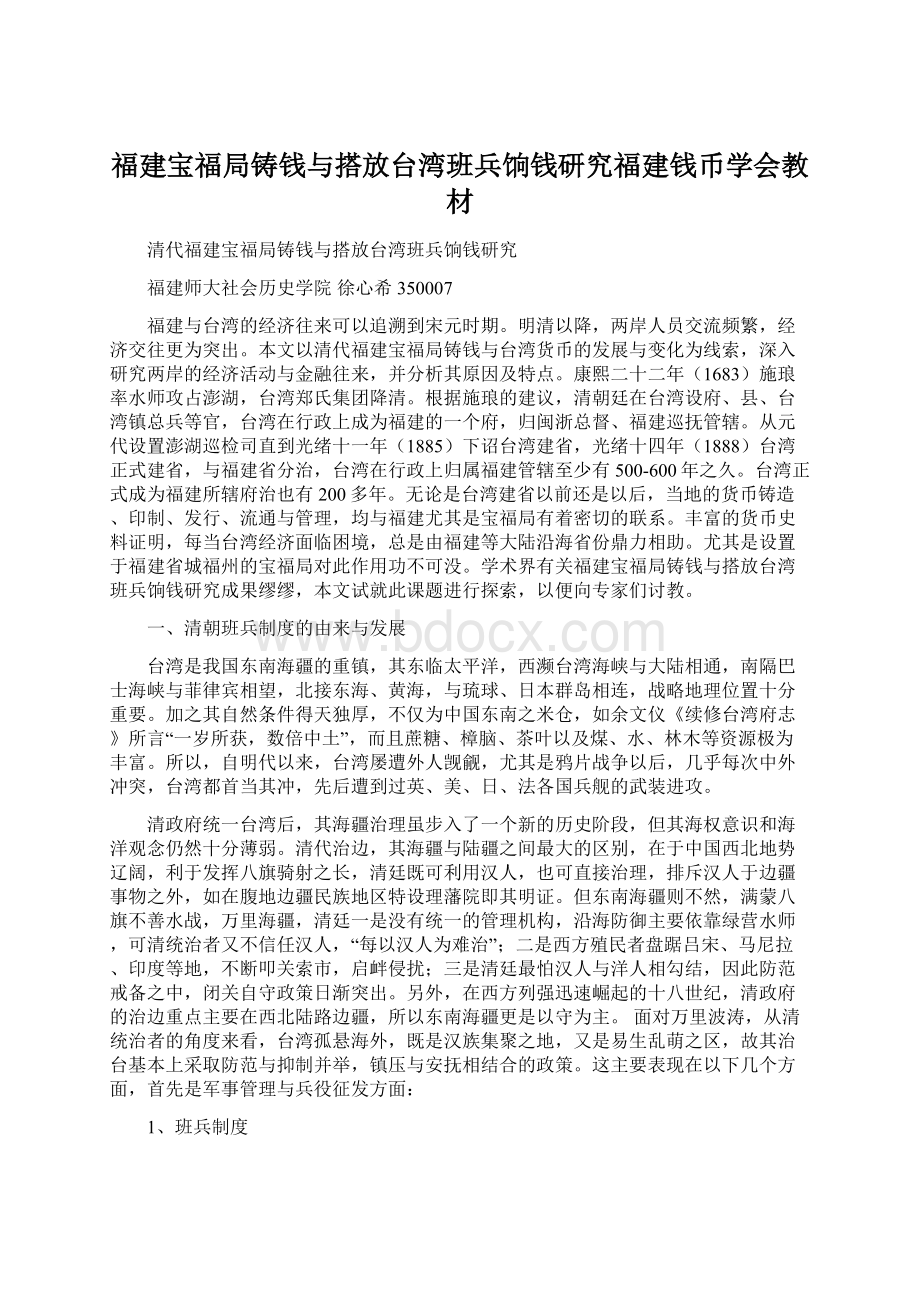
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福建钱币学会教材
清代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
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徐心希350007
福建与台湾的经济往来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
明清以降,两岸人员交流频繁,经济交往更为突出。
本文以清代福建宝福局铸钱与台湾货币的发展与变化为线索,深入研究两岸的经济活动与金融往来,并分析其原因及特点。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水师攻占澎湖,台湾郑氏集团降清。
根据施琅的建议,清朝廷在台湾设府、县、台湾镇总兵等官,台湾在行政上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归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管辖。
从元代设置澎湖巡检司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下诏台湾建省,光绪十四年(1888)台湾正式建省,与福建省分治,台湾在行政上归属福建管辖至少有500-600年之久。
台湾正式成为福建所辖府治也有200多年。
无论是台湾建省以前还是以后,当地的货币铸造、印制、发行、流通与管理,均与福建尤其是宝福局有着密切的联系。
丰富的货币史料证明,每当台湾经济面临困境,总是由福建等大陆沿海省份鼎力相助。
尤其是设置于福建省城福州的宝福局对此作用功不可没。
学术界有关福建宝福局铸钱与搭放台湾班兵饷钱研究成果缪缪,本文试就此课题进行探索,以便向专家们讨教。
一、清朝班兵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疆的重镇,其东临太平洋,西濒台湾海峡与大陆相通,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北接东海、黄海,与琉球、日本群岛相连,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加之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为中国东南之米仓,如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所言“一岁所获,数倍中土”,而且蔗糖、樟脑、茶叶以及煤、水、林木等资源极为丰富。
所以,自明代以来,台湾屡遭外人觊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每次中外冲突,台湾都首当其冲,先后遭到过英、美、日、法各国兵舰的武装进攻。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其海疆治理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其海权意识和海洋观念仍然十分薄弱。
清代治边,其海疆与陆疆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西北地势辽阔,利于发挥八旗骑射之长,清廷既可利用汉人,也可直接治理,排斥汉人于边疆事物之外,如在腹地边疆民族地区特设理藩院即其明证。
但东南海疆则不然,满蒙八旗不善水战,万里海疆,清廷一是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沿海防御主要依靠绿营水师,可清统治者又不信任汉人,“每以汉人为难治”;二是西方殖民者盘踞吕宋、马尼拉、印度等地,不断叩关索市,启衅侵扰;三是清廷最怕汉人与洋人相勾结,因此防范戒备之中,闭关自守政策日渐突出。
另外,在西方列强迅速崛起的十八世纪,清政府的治边重点主要在西北陆路边疆,所以东南海疆更是以守为主。
面对万里波涛,从清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台湾孤悬海外,既是汉族集聚之地,又是易生乱萌之区,故其治台基本上采取防范与抑制并举,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军事管理与兵役征发方面:
1、班兵制度
康熙平台以后,首先遣返郑氏官兵回籍安插,并将郑克塽、刘国轩等郑氏首要送京入旗,在“解散而消弭”郑氏武装集团的基础上,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据《清实录》载,清廷始行班兵制度,其内容主要是戍台兵丁不用台民,在福建各地绿营包括福州、邵武、龙岩、建州、泉州、漳州等营中抽拔,选调之人既要求“年力精壮,有身家”,又不许携带妻室,“更迭往戍,期以三年”。
同时,将漳、泉两地兵丁与在台漳、泉两籍移民分开,隔离戍守,即漳州籍兵丁分拨到泉州移民区,泉州籍兵丁到漳州移民区戍守。
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要在防备戍台兵丁“岁久各立家业,恐意外致生他变”。
清代海防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以大海为长城,以重要海岛为要塞,岛岸相维,水陆一体,并与沿海属国相呼应,最终达到屏障中原,保卫京师的目的。
而台湾居东南沿海之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清领台湾后,政治上闽台合制,军事上则是闽台一体联防。
其台澎地区的兵力部署,初设绿营陆路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二员,水陆官兵共10营,兵力一万有余。
其后多有添设,至鸦片战争前,增至水陆16营,额兵14656名。
2、人事制度
台湾的用人制度有别于内地,主要在于:
一是文员不经吏部遴选,而是由福建巡抚“于闽省现任官内拣选调补”,它虽有利于地方调配,选用熟悉风土的贤官能吏,但这种授权督抚且寓牵制于放权之中的作法,又使督抚用人格外慎重,以免牵连受过。
二是清廷规定,台湾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各官,三年俸满即升,以后年限虽稍有变化,但任期唯短、无致久任是台湾人事制度中的一大特点。
实际去除前后交盘、协办、渡海候缺等时间,独当职任往往不足一年,结果贤能者难有作为,怀有二心者亦难能成事。
三是闽台合制、以汉治汉。
台湾建省以前,岛内郡县均由福建管辖,同戍台班兵一样均为闽台合制。
台湾文职之首,初为台厦道,分巡台湾、厦门两地。
雍正五年(1727)改为台湾道,专辖台澎地区,并兼学政带有兵备衔,但“一应军务机宜并地方事件,仍听内地督抚管制办理”。
台湾武职最高为总兵,虽加挂印,但受福州将军、闽浙总督和福建水师节制,遇事不可专擅。
同时,台兵、台饷由闽省调拨,人力、财力处处牵制,不能分而为二。
四是御史巡台,强化监督。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台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朱一贵起义,清廷因此认识到,台湾远隔重洋,耳目不周、控制不力的严重性。
乱平后,清廷在改善吏治的同时,又采取御史巡台制度,即每年自京师“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台湾)巡察,一年更换”,其权力涉及司法、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成为皇权的耳目和智囊。
以上诸端,形成周密的人事制度,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统一台湾到甲午战争失败,清治台共193年,其中农民起义和各种民变共有132次之多,但没有一次是由台湾的官兵率众起事的。
3、民政制度
与防台政策相辅相成,清廷对台湾发展的抑制政策,主要表现在“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的各种消极措施上。
如:
其一,行政建置消极滞后。
清领台湾之初,设一府三县,其时人口约10万(不包括番社人口),到日本侵台前的同治十三年(1874),190年间台湾人口增加20余倍,但行政建置只增加了一县三厅,其中雍正元年(1723)增设的一县二厅(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是在朱一贵起义之后,清廷为免北路空虚,以防不测,才接受兰鼎元“添兵设官,经营措置”的建议(淡水厅治直到乾隆二十一年尚留在彰化境内),而时隔87年之后,噶玛兰厅的建置方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
这种不宜辟地,建置迟缓的决策,对清代前期台湾的经济开发影响甚大。
其二,在禁止硝磺、铁器、油棕、军器等私自入台的同时,清廷还实行若干严渡政策,不许携眷赴台,以限制台湾汉族人口的集聚增殖。
为此,如《乾隆朝清实录》所言,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乾隆曾经心有余悸并且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林爽文等纠众滋事,设其家属俱在内地,贼匪等自必有所牵顾,何至敢于肆逆至此,是台湾民人禁止搬眷居住,未必非杜渐防微一法。
”其三,汉番隔离之策。
随着台湾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土地的逐渐开发,汉番冲突时有发生。
康熙六十一年(1722)夏,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以沿山一带,易藏奸宄,命附山十里以内民居,勒令迁徙。
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筑长墙以限之,深凿濠堑,永以为界,越界者以盗贼论”。
第一次提出了汉番隔离的边禁措施,后经漳浦籍巡台使兰鼎元上书力争,虽未大规模迁徙,但清政府仍于雍正七年(1729)宣布封山禁令,“饬沿山各隘立石为界,禁民深入”。
乾隆二年(1737),又禁止“汉番通婚”,违者离异治罪。
其四,强化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相沿已久的治民政策,清领台湾后,不仅承袭这一政策,而且进一步发展强化,变单一的陆上保甲为水陆联保,即将保甲、汛防与稽查三者结为一体,“出则注明所往,入则查其所来”,形成东南海疆独特的保甲制度,以维持台湾和东南海疆的封建秩序。
为控制台湾和宁谧海疆,在一系列防范和抑制政策的同时,清廷对台湾还有诸多安抚政策。
如在经济上,除重荒政、办仓储,采取某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之外,清廷对戍台之班兵多有犒赏和补贴。
如《雍正朝清实录》所载,雍正二年(1724),诏曰:
“台湾换班兵丁,戍守海外岩疆,在台支给粮饷,其家口若无力养赡,则戍守必致分心,每月着户给米一斗。
……按户给发,务使均沾实惠。
”此为台湾眷米之始。
七年(1729),清廷再谕,每年赏银4万两,以为台兵养赡家口之用。
这样,戍台之兵既有兵糈,又有眷米,“所得较之内地(兵丁)倍多”,加之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于显戮而不敢有异心,故百余年中,台湾“有叛民而无叛兵”。
在政治上,清廷为鼓励任台官吏忠于朝廷,实心任事,在实施防范政策的同时,亦多方安抚。
如在吏治方面,崇其体制,奖励升迁。
在文化方面,清政府在大力推行儒化教育,创办各种义学、书院,奖励台湾子弟向学的同时,亦对应考的台湾士子实行保障名额制度,严禁冒籍应考,以维护台湾籍考生的权益。
总之,清代前期,清廷在台湾采取的一系列包括班兵在内的政策和措施,维护了海疆宁谧,巩固了其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其中,福建宝福局在经济保障方面的特殊作用则是不可替代的。
二、宝福局的设置、发展与局务管理
宝福局原为顺治六年(1649)设置的福建省局,至雍正时沿袭各省惯例以“宝”字加各省简称遂成“宝福”、“宝临”、“宝宁”、“宝原”、“宝宣”、“宝同”、“宝江”、“宝东”、“宝前”、“宝蓟”、“宝昌”、“宝浙”、“宝陕”等局,另外福建还设有宝漳局、宝台局等地方铸钱机构。
所以坊间流传有口诀以便记忆。
康熙通宝铸于清圣祖康熙年间(1662-1722年)。
钱径2.5-2.7厘米,重3.8-5.5克。
钱面文字“康熙通宝”以楷书书写,从上而下而右而左直读。
康熙通宝按照背面文字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仿“顺治四式”的满文钱。
钱背满文“宝泉”、“宝源”左读,是户、工两部所造。
另外一类是仿“顺治五式”满汉文钱。
钱背穿孔左边是满文局名,穿孔右边是汉文局名,共计有22个铸局。
其中主要的20局记名改为口诀便是:
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
另外有甘肃巩昌局铸的“巩”字钱,山西省局铸的“西”字钱,都是少见的品种。
以上两类钱在制作上也与顺治钱相同,其钱径2.5-2.7厘米,重3.8-5.5克。
康熙四十一年(1720)又铸半重“轻钱”,折价使用,但流传于世上却不多。
现在流存于世上的劣等小砂版、鹅眼钱等都是私铸钱。
另外还有少许数量的背铸星月的钱,还有合背钱,记地支钱,当十大钱等,品类很多,但数量较少。
宝福局该局原址设在福州城内都司巷,即今福州鼓楼附近。
至乾隆四年(1739)迁移至位于今鼓东路的新址,此后沿用至清末而未曾改址。
《榕城考古略》是晚清福州文人林枫所著的乡土文献,成书于清道光间,是福州地方史志文献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史料。
由于资料丰富,贴近现实,备受社会人士的青睐。
《榕城考古略》分上、中、下三卷,曰城橹、坊巷、郊坰。
闽中才子谢章铤在序言中评之“叙述有法,而采摭群书,附注征之,名人题咏亦录焉”。
可见翔实可靠。
该书卷中坊巷篇记“宝福局在卫巷口,原为观风整肃使署,乾隆年间改为宝福局,同治年间曾一度改为军装局专贮军装。
”康熙铸钱背面记地大多以省级为名,“宝福”局康熙通宝在康熙六年(1667)就已经铸行。
到雍正年间,“雍正通宝”铸于清世宗雍正时期(1723-1735)。
钱径一般约2.6-2.8厘米,重3.6-5.4克。
雍正通宝钱按顺治四式满文钱造,钱面文字“雍正通宝”以楷书书写,从上而下而右而左直读。
钱背穿孔左边是满文“宝”字,穿孔右边是计局的满文,其局共计有20字(除户、工二部外,均为省局名,州、府局已废);泉、源、巩、河、苏、广、昌、浙、陕、桂、福、云、南、台、武、黔、川、晋、济、安。
雍正钱形态工整,规格统一,在清代钱币中居于少而精的地位,由此可知雍正钱法严谨。
现今流传于世上的还有贵州黔局大样钱一种,形制类折二钱,很少见。
这里附带要说明的是宝漳局的铸钱。
清康熙皇帝在位61年,先后设有22个铸钱局(另有24、25个钱局之说)铸造康熙通宝。
在这22个铸钱中有一种“宝漳”局康熙通宝,是迄今有史可查的福建漳州最早的铸币,它的铸行可说是为清政府统一台湾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漳州地处我国东南边缘,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远离政治中心,历史上中州的动荡和外族入侵,对漳州的影响较小。
从汉、唐及至明末漳州一带使用的大多为中原中央政权发行的货币,未有自行铸造货币。
明隆庆年间,海澄月港兴起,由于海外贸易繁华,外国银元开始大量流入漳州。
这时,民间出现了仿造“番银”所铸造的货币。
明末清初,郑成功军队与清廷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近40年,由于年年战乱,清政府急需发行货币用于筹饷。
清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巡抚奏准铸造“宝漳”局康熙通宝钱。
该钱面文对读“康熙通宝”,背满、汉“漳”字,钱径28毫米,穿宽6毫米,重4克-4.9克。
康熙铸钱背面记地大多以省级为名,“宝福”局康熙通宝在康熙六年(1667)就已经铸行,为何在有了福建省局铸钱后,又加铸了漳州府局制钱,这与300多年前清政府收复台湾,统一祖国不无关系。
漳州地方学者认为,宝漳局康熙通宝铸于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二十一年(1682)停铸,而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者不可能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作为清政府收复台湾的前沿阵地,在当时的闽南重镇漳州铸行钱币,其军事目的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宝漳局康熙钱的铸行,为清政府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宝漳局康熙通宝有黄铜、白铜两种质地,面文有单点通、双点通以及“臣熙”等版别,背面“漳”字还有多种书体。
这些不同版别的宝漳局康熙通宝钱是钱币集藏者苦苦搜寻的对象,尤其是白铜质、楷“漳”等版别更是钱币中的罕见品。
陈寿祺著道光《福建通志》“钱法志”记述宝福局自开铸以来曾经多次停炉罢铸,也曾多次复开。
顺治十三年(1656)诏令停福建铸局。
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铸钱时断时续。
顺治十七年(1660)复开,康熙元年(1662)又停;六年(1667)复开,但是正如《苏州府志》所云,次年因江宁、苏州等15个布政使司钱局开铸以来,“钱既多或致壅”,“得旨俱暂行停止”,故而又行停铸;至康熙二十四年复开局铸钱,且“允许民兼用古钱为便”,旋即骤停。
乾隆五年(1740)“以台湾一部钱贵殊常,令开局铸钱”,且“尽数运往台地搭放兵丁月饷”;道光四年(1824)以“福建银价昂贵,鼓铸成本亏折”,督抚奏请自本年夏季起暂停鼓铸。
直至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宝福局也是开停无序,时开时停。
据道光《福建通志》“钱法志”记载,宝福局的行政管理归福建布政使司。
按清廷规定,由布政使司总理,督粮道稽查,并且规定宝福局设监铸官一员,委用库官一员,登记铜铅出入书办一员,库丁、门役若干名。
如遇停铸,则撤去监铸官,只保留协办官一员处理局务。
每炉设炉头一人经理炉务,由该炉头转雇所需熟练工匠。
工匠分为看火、翻砂、刷灰、杂作、锉边、滚边、磨钱、洗眼八种,按卯按期鼓铸。
宝福局官员及办事人员之薪水与办公费用,“均系动支司库”,并且计入“该年公费项下”。
铸造钱币所需的铜、铅、锡等原料福建十分缺乏,多数来自西南的贵州、云南等省。
因而铸造成本高居不下,多铸多赔。
早期宝福局位搭放兵饷勉强铸造康熙通宝制钱以应付民间配合银两与酒钱流通使用。
乾隆初期朝廷整顿各省钱局,至乾隆四年(1739)宝福局在福州城内设“天、地、人、和”4座铸钱炉,之后鼎盛时期曾经扩增为8座钱炉。
当时因亏损严重,又陆续裁撤4座,基本保留4座钱炉铸钱以应对流通需求。
乾隆五十六年(1791)改为“物、阜、民、安”4座钱炉,每月开炉3卯(每卯铸钱10天)。
这里解释一下铸钱史研究中常出现的“卯”。
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考一》解释为:
“开铸之期曰卯。
宋以后,始有画卯、点卯之名,盖取其时之早,相沿既久,遂以一期为一卯。
”《钱法志》又云,清廷规定,每卯60秤,每秤20串,“每串重七斤八两,需配正红铜二斤十三两七钱一分零,正黑铜一斤六两八钱五分,白铅三斤十五两二钱九分,共用铜铅八斤三两八钱五分有奇,另外用于煤、罐子、黄砂、木炭、盐等工料银一钱六分一厘三毫零,加补串钱绳,每串(一千文)共用工本银一两三分七厘八毫”。
三、宝福局铸钱原料来源、成份配制的变动及其经营弊端
宝福局原料起初来自于云南红铜,并且搭配若干日本采买的洋铜。
由于长途贩运加之进口费用高昂,遂掺以闽赣两省地产的黑铜,以期降低成本。
嗣后又因黑铜成色低下,奏准将红铜三分、黑铜五分、洋铜二分三色均匀配置。
其后又将配方改为红铜三分五厘、黑铜十分五厘,照旧搭配洋铜二分冶铸。
如《福建通志》“钱法志”统计,宝福局每年所需净铜17.8022万斤,白铅14.7738万斤,黑铅2.3142万斤,点锡0.722万斤。
《清会典》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议定铜料预期委派专员赴云南购买,奏准采办限期为180天,并且规定红铜每百斤价银11两,黑铜每百斤价银9两,加上运脚盘费等开支,铜料(红、黑铜掺和)每百斤给银5两8厘2毫零。
如《清实录》所记,乾隆五年(1740)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
又记乾隆四十年(1775)闽浙总督钟英奏称宝福局铸钱铜六十万斤,请委员往滇省采买之。
可见云南铜料是宝福局在国内原料的主要来源。
江苏则次之。
其次是从日本采买洋铜,主要通过江苏商户进行。
如《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记,福建巡抚钟英核准每年经苏商从日本采购13船铜料。
因江苏客商从日本贩运洋铜往内地各省,间或有遭风吹至福建沿海的,则依福建本省定价每百斤17两5分之例收买。
白铅则委派官员赴汉口采购。
由于配用的铜、铅、锡等原材料均非本省所出,必须预先派员远赴云南、湖北、广东采办,路途遥远,脚费颇重且难免旅途损耗,成本甚高。
针对成本居高不下的弊端,道光二十三年(1843)闽浙总督刘鸿祥与布政使司等各司商洽之后,上奏朝廷极言福建宝福局铸钱之难,他说:
宝福局“每铸钱千文,应用例销银(即户部所规定的成本费用)一两三分七厘八毫,外捐津贴银(即补助费)二两二厘八毫,共银一两二钱六分零六毫。
近来银价愈增,每两值钱一千六百数十文,核计铸钱一千,亏折铸本钱一千一百数十文,全年额钱四万三千二百串,计应亏折例销、外损钱四万七千七八百文,为数甚巨”。
[1]即按上折提供之数统计和分析,估计宝福局每铸钱1000枚,成本却要花费2100枚,悬殊极大。
官方难以承担如此巨大的亏空。
依照顺治旧制,如《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所记官铸制钱应当“以红铜七成,白铅(即锌)三成,搭配鼓铸”。
但是实际上“国初铸钱,或听各省于铜额内兼办铅斤,或收用废钱旧器,分别生熟铜配铸”。
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定以铜六铅四配铸制钱之法。
因乾隆五年之前铸钱不加锡,故称之为黄钱,其主要成分即铜与白铅(锌)构成。
由于民间私自融化制钱以铸造铜器,故于乾隆五年(1740),遵浙江布政使张若愚之议,以金属成分红铜占50%、白铅占41.5%、锡2%,铸成所谓青钱,令各省依此比例鼓铸。
咸丰年间,因为通货膨胀,滥发钱币,造成信用危机。
朝廷只好同意各省铸造咸丰大钱,为提高币值和信用度,一律使用紫铜铸造。
然而现今民间收藏颇多黄铜质的咸丰大钱,那是因为咸丰后期紫铜用料告罄只得将就以黄铜代之。
光绪十四年(1888)又对铜铅比例实行调整,改为铜54%,铅4%。
实际上在铸造过程中,偷工减料的现象时有发生,朝廷有关保证钱文品质的规定往往形同虚设。
特别是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私铸盛行,官员参与民间私铸的案件层出不穷,乃至各省官钱局员工铤而走险,趋之若鹜。
嘉庆二十五年(1820)御史王家相上奏言事:
“意官铜偷铸小样钱,每钱一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2]。
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官修的《清史稿》“食货五钱法篇”也直言不讳记载各省官局多有“局私秘匿”。
咸丰九年(1859)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张集馨也在所著《道咸宦海见闻录》书中回忆说宝福局铸钱“多年不报部”,以致“钱局弊窦极多,炉头向非善类,每卯发铜,炉头必两卯一发,此中大有通融”,且“局门不锁,炉匠人等恣意出入,何弊不生?
”这些官员巧立名目,内外勾结,大肆鼓铸轻钱和劣钱从中渔利,由此可见一斑!
四、宝福局铸钱与搭放班兵饷钱
前面已经说明,宝福局铸钱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用于搭放驻防省城的兵丁与派驻台湾的班兵兵饷。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驻防闽台的班兵数量。
据道光年间任分巡台湾兵备道的姚莹《筹议商运台谷》估计:
“闽省内地水陆官兵五十三营,与驻防旗兵,不下十万。
”台湾驻军数量如文献所载,至乾隆后期“添设戍兵一千二百十六名,共计应以”13392名“匀派。
每名每月分银二钱五分八厘九毫零,足敷支给”;“旧额新增年共估银四万八百两游巡等费”。
[3]《清会典》“兵典”确切记载“台湾各营额拨戍守共兵”14661名。
则闽台两地驻防班兵数量在12万左右。
所应当颁发的月分银更不在小数。
即使以台湾的正常年份(即不发生内乱,勿需朝廷派兵弹压)根据陈盛韶《问俗录》“鹿岗亭”、“屯饷”、“戍兵”等卷所记兵员与饷钱数字统计,每年即需饷钱6万串,需铜48万斤。
乾隆年间宝福局鼓铸之初,以850文抵银一两来搭配发饷,八旗与绿营兵丁意见纷纷。
自乾隆八年(1743)经朝廷批准,规定第二年起每银一两折钱1000文搭配分发兵饷,宝福钱局经费与水脚费准予公费报销,成本亏损部分则由地方财政予以补助。
于是规定每员兵丁每月搭饷50文。
乾隆四十年(1775)后英国鸦片开始进口中国,白银开始外流,银价日渐高涨。
至五十九(1794)年议准因钱贱银贵兵饷停止搭配制钱,均以银两支付,嘉庆年间搭放制钱以充兵饷的制度时断时续。
至道光四年(1824)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甚至高达1240文才能兑换一两白银,发放兵饷时若再以1000文抵银一两搭配给兵丁,则兵勇大哗,拒绝接受。
倘若按照1240文抵银一两,则需地方财政大量补贴,福建布政使司又极感捉襟见肘。
闽浙总督遂决定发放兵饷停止搭配搭放制钱,全部以白银支付。
道光皇帝于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谕旨:
“谕内阁,赵慎畛(即闽浙总督)等奏,请暂停鼓铸一折。
闽省宝福局鼓铸钱文,系为搭放兵饷之用。
据该督等查明现在市价银贵于钱,局铸成本,折耗甚多,其各州厅县捐款津贴,需用铜铅运费,办理亦多掣肘,且兵丁等领饷后,以钱易银,核计每两短钱二百余文,殊形支绌,自应量为调剂。
著照所请。
自道光四年夏季起,将局铸暂行停止。
其应搭兵饷,亦自夏季起,停搭饷钱,统以银两全支。
所有局内现存钱文,并本届委员所办,及旧存铜铅,均著存贮局内。
该督等察看情形,如钱价稍贵,即行奏明开铸。
各营兵饷,仍照旧例搭放。
该部知道。
”[4]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二月,浙江方面发现因为各省停铸,制钱日少,银价攀升,提出各省一律开炉鼓铸,准以制钱1500文折银一两,以利兵饷搭放。
继之浙、桂、黔、晋、赣、苏、湘诸省相继开铸。
唯有福建与湖北二省以每年开铸将蚀本钱二、三万两,负担甚重,派捐者州县苦累,搭放则兵丁拮据,奏请暂缓宝福局鼓铸事宜。
是此,“道光通宝”福字钱传世珍品有限,民间多见当年之私铸轻钱及薄钱。
另见《福建省例》“钱法例”记载有关宝福局的珍贵史料:
“省会钱价每至月底,值旗营各标领饷之时,必更加昂。
从前省城钱贵,原有局卖官钱之例,但委官设局,不无胥役冒销滋弊。
查各旗营兵兵饷赴领,向搭局钱。
可否嗣后钱价平减之时,如每两纹库银易钱在八百五十文以外,仍应发银。
其遇钱价昂贵之时,每两纹库银易钱在八百五十文,领饷暂行给钱。
如钱价稍平,照旧领银。
俾钱文流通,以平市价等语。
”福建布政使司核计之后遂行文宪台(即巡抚)衙门:
“本司道查闽省宝福局鼓铸钱文,从前社会钱价昂贵,向有贱卖官钱,按照八五易换平价之例,但委员设局,难免胥役混冒。
查鼓铸钱文,原为搭放兵饷之需。
各旗营兵丁按月所领饷银,势须换钱行使。
每遇钱少价昂,徒受钱铺之居奇。
不若竟放钱文,既可免其换钱之烦,又得沾平价之惠。
且各兵丁日逐行用钱文,复散布在民,似与兵民均有裨益。
”有司决定:
“兹查省城满汉各标并福协等十营,除营员养廉及公费各银外,实兵一万八百余名,照官八五定例,每兵每月请酌搭钱三百四十文,坐扣饷银四钱,月计兵需钱三千六百余串。
”布政司统计宝福局库存钱文:
“查宝福局截至(乾隆)二十三年底,应存发换平价钱四万三千余串。
请于此内拨出钱四万串,即以本年四月起,按月搭放。
总系钱价减至八五以外,即行停止配搭。
仍令闽、侯二县于每月下旬将省城钱价每纹库一两实可换钱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