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docx
《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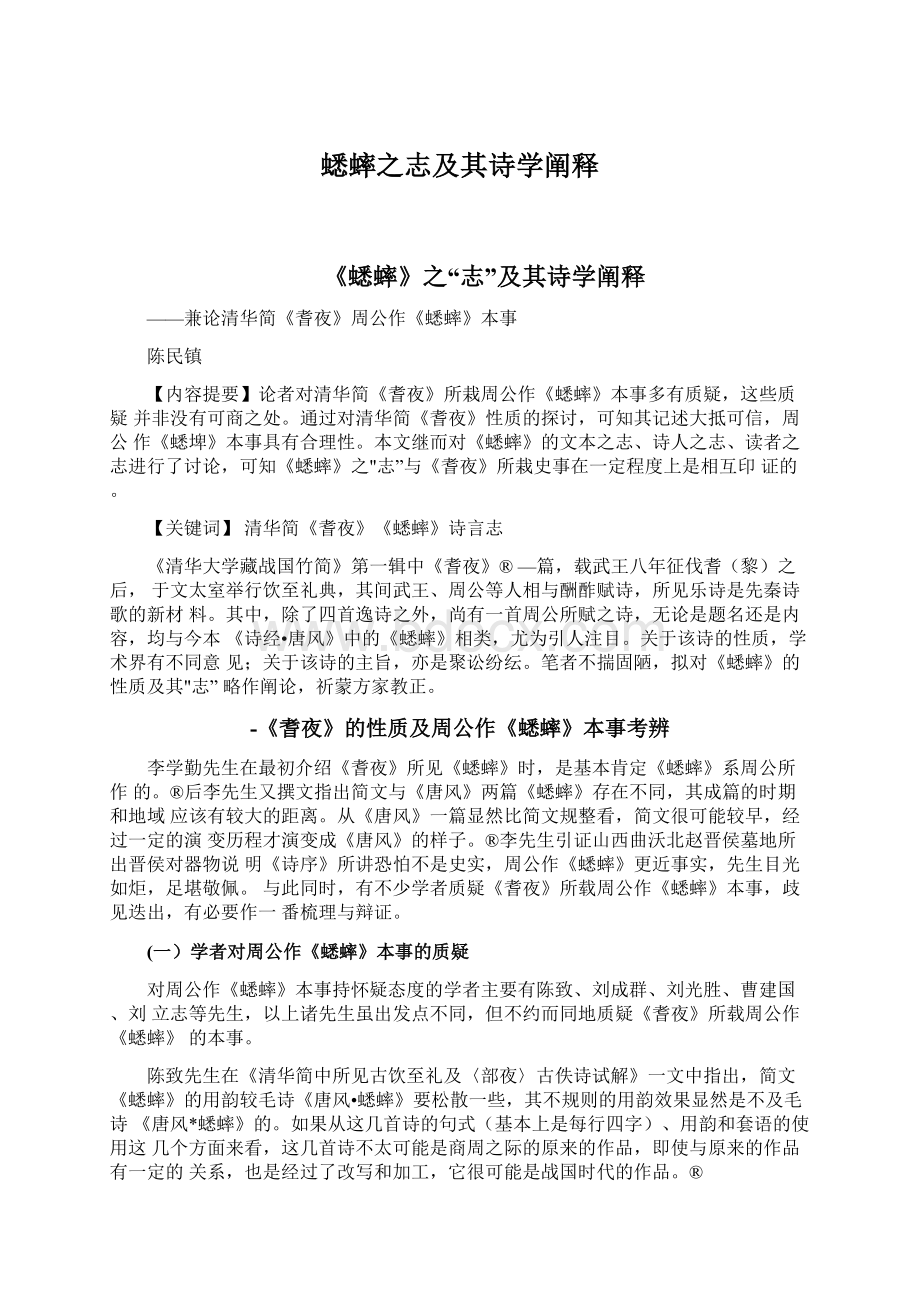
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
《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
——兼论清华简《耆夜》周公作《蟋蟀》本事
陈民镇
【内容提要】论者对清华简《耆夜》所栽周公作《蟋蟀》本事多有质疑,这些质疑并非没有可商之处。
通过对清华简《耆夜》性质的探讨,可知其记述大抵可信,周公作《蟋埤》本事具有合理性。
本文继而对《蟋蟀》的文本之志、诗人之志、读者之志进行了讨论,可知《蟋蟀》之"志”与《耆夜》所栽史事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印证的。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蟋蟀》诗言志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耆夜》®—篇,载武王八年征伐耆(黎)之后,于文太室举行饮至礼典,其间武王、周公等人相与酬酢赋诗,所见乐诗是先秦诗歌的新材料。
其中,除了四首逸诗之外,尚有一首周公所赋之诗,无论是题名还是内容,均与今本《诗经•唐风》中的《蟋蟀》相类,尤为引人注目。
关于该诗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关于该诗的主旨,亦是聚讼纷纭。
笔者不揣固陋,拟对《蟋蟀》的性质及其"志”略作阐论,祈蒙方家教正。
-《耆夜》的性质及周公作《蟋蟀》本事考辨
李学勤先生在最初介绍《耆夜》所见《蟋蟀》时,是基本肯定《蟋蟀》系周公所作的。
®后李先生又撰文指出简文与《唐风》两篇《蟋蟀》存在不同,其成篇的时期和地域应该有较大的距离。
从《唐风》一篇显然比简文规整看,简文很可能较早,经过一定的演变历程才演变成《唐风》的样子。
®李先生引证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所出晋侯对器物说明《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周公作《蟋蟀》更近事实,先生目光如炬,足堪敬佩。
与此同时,有不少学者质疑《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本事,歧见迭出,有必要作一番梳理与辩证。
(一)学者对周公作《蟋蟀》本事的质疑
对周公作《蟋蟀》本事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主要有陈致、刘成群、刘光胜、曹建国、刘立志等先生,以上诸先生虽出发点不同,但不约而同地质疑《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的本事。
陈致先生在《清华简中所见古饮至礼及〈部夜〉古佚诗试解》一文中指出,简文《蟋蟀》的用韵较毛诗《唐风•蟋蟀》要松散一些,其不规则的用韵效果显然是不及毛诗《唐风*蟋蟀》的。
如果从这几首诗的句式(基本上是每行四字)、用韵和套语的使用这几个方面来看,这几首诗不太可能是商周之际的原来的作品,即使与原来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也是经过了改写和加工,它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
刘成群先生在《清华简〈部夜〉〈蟋蟀〉诗献疑》一文中对周公作《蟋蟀》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其质疑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
其一,据《耆夜》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
其二,在僑家后学关于孔子的记忆资料里,也找不到孔子关于周公作《蟋蟀》的只言片语;
其三,如果《蟋蛑》系周公所作,它即使不被采于作为鲁诗的《豳风》中,至少也不会被采人《唐风》;
其四,如果《逸周书》乃是“战国之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的作品,那么大致产生于同一时期并与其极为相似的清华简《保训》也一样有可能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
其五,在战国时期楚地这样一个有着丰厚《诗》学水准的土壤上,是极有可能出现对《诗》的拟作和与《诗》有关的情节化操作的;
其六,《耆夜》里的《蟋蟀》句式参差不齐,看起来要比今本《诗经》中的《唐风•蟋蟀》古老,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周公所賦《蟋蟀》诗的原始风貌;
其七,《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含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亊比附,那么《耆夜》同样也可以。
®
刘光胜先生指出,淸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
淸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
曹建国先生则认为简本<蟋蛑》当系战国时人仿《唐风•蟋蟀》而托名于周公,与《唐风•蟋蟀》旨趣不同,也不能因此否定《毛诗序》对《唐风•蟋蟀》的解读。
不仅如此,《耆夜》记载武王等作诗也不可信,传世文献记载的周公作诗问题也需要重新审视。
®
刘立志先生也认为清华简所载《蟋蟀》本事当是后人拟撰附会,并一一分析了《诗经》中与周公有关的诗篇,认为这些周公作诗的说法基本不成立。
®
(二)周公作《蟋蛑》本事释疑
以上诸先生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精义迭出,有助于疑云的澄清。
但以上诸说并非没有可商之处。
首先来看陈致先生的观点。
陈致先生分析了三种可能,其一是简文《蟋蟀》是《唐风*蟋蟀》的前身,其二是《唐风*蟋蟀》是简文《蟋蟀》的前身,其三是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是源自两个平行互不相干的文本。
陈先生认为这三种可能性在逻辑上应是均等的,但陈先生显然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小。
陈先生是从句式、用韵和套语的使用这几个方面出发来分析简文《蟋蝉》的。
然而,简文《蟋蟀》的不整饬很难说是它晚出的证据,《唐风•蟋蟀》的严整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经过加工与整理的事实。
刘成群先生就简文《蟋蟀》提出了许多疑点。
其中第一、第二点主要是针对周公作《蟋蟀》本事不见传世文献而言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耆夜》的记载不可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清华简《楚居》关于楚人世系及迁徙的许多信息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些信息没有流传到现在便质疑出土文献的可靠性。
关于第三点,《蟋蟀》何以被采入《唐风》现在尚难以究明,李学勤先生曾提出这样的猜想:
“耆(黎)国与唐有一定关系。
《帝王世纪》等古书云尧为伊耆氏(或作伊祈、伊祁),《吕氏春秋•慎大》还讲武王‘封尧之后于黎’。
春秋时的黎侯被狄人逼迫,出寓卫国,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和《诗*旄丘》序,其地后人于晋。
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
”®笔者试提出两点想法:
其一,很多学者忽略了周公与唐的关系,《史记•晋世家》云: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
”唐为周公所灭,周公与唐并非没有关联。
准此,周公作《蟋蟀》并被采入《唐风》便不难解释了。
1992年至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翼城、曲沃两县的交界处——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了晋侯墓地,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
®有多位晋侯埋葬于此,其中便包括《诗序•蟋蟀》提及的晋釐侯。
在天马一曲村遗址第31号墓,发现了一件被称作“文王玉环”的器物,铭文曰:
“文王卜曰:
我及唐人弘战贾人。
”李学勤先生推测玉环上的文字系唐人所刻,至周公灭唐,成王以其地封晋,这件玉环便归晋公室所有。
®总之,周公曾灭唐,周公所作诗流传于唐故地,本无足怪。
其二,江林昌师曾据天马一曲村遗址推论《唐风》地望正在山西翼城一带,®而《耆夜》载武王八年戡耆(黎),耆(黎)地望在上党,即现在的山西长治西南,与翼城相去不远,在戡耆(黎)后周公所作《蟋蟀》,自然有可能被采人《唐风》。
以上是笔者对《蟋蟀》何以被
采人《唐风》的初步推测。
第四点是关于《逸周书》性质的问题。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査)》所公布的九篇文献中,有三篇明确与《逸周书》有关,分别是《皇门》《祭公之顾命》和《程寤》。
其中,《皇门》与《祭公之顾命》见诸今本《逸周书》,基本一致,清华简本可订正今本许多讹误。
《程寤》已佚,在今本《逸周书》中仅存其目。
但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文献中,载录了《程寤》的前部分文句,与清华简本所见基本一致。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
“《世俘》《商誓》《皇门》《尝麦》《祭公》《丙良夫》等篇,均可信为西周作品。
”®刘起釺先生书学史》指出《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七篇可确认为西周文献,《程典》《酆保》《文儆》《文传》等十余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其文字写定可能是春秋时,《大开》《小开》等篇,虽然也是关于自文王历武王至周公各时期的史料,然已近战国文字,当系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
®总之,《逸周书》虽然内容驳杂,甚至包括类似《六韬》的兵书,但有许多是可信的史料。
《逸周书》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它绝非简单的“私相缀续”。
刘先生认为《逸周书》是“私相缀续",继而否定《耆夜》的内容,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上,刘成群以及刘光胜先生均认为《耆夜》属于《逸周书》,这也恐怕有待验证。
虽然《耆夜》尊隆周公,与《逸周书》的基本精神相近,但《耆夜》的体例与《逸周书》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至于第五、第六、第七点质疑,均是通过相关背景的推论,都很难说明《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本事不可信。
再看刘光胜先生的观点。
刘先生一方面指出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另一方面认为《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
刘先生还是相信周公“作”《蟋蟀》的,只是认为《蟋蟀》并非周公所作,而是原已有之的篇章。
然而,《耆夜》所见武王、周公等人之间相与酬酢的诗篇,从内容看均是针对伐耆(黎)胜利以及饮至礼的。
至于《蟋蟀》,更是因为一只蟋蟀突然闯人,周公有感而作,《蟋蛘》的意象乃至主旨均是切合当时情境的。
故《香夜》所见五首诗篇,更可能是应景之作。
更为重要的是,与春秋时代賦古诗盛行、《诗》经典化不同,西周时期是造新诗的时代、积累“诗”的时代,《耆夜》表现的便是周人造诗的情境。
曹建国先生认为《毛诗序》对《唐风•蟋蟀》的解说符合诗旨,简本《蟋蟀》当是《唐风•蟋蟀》的仿作,继而认为《耆夜》所载佚诗均为战国人的作品,《耆夜》谓周公作《蟋蟀》如《金滕》所见周公作《鸱鸮》,乃战国时儒者尊崇周公的造圣新说。
关于《蟋蟀》的诗旨,笔者下文再论。
关于周公作诗,为文献所艳称。
笔者认为,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有其依据的,《诗经》中的确有不少篇章与周公有关。
至于《金滕》载周公作《鸱鸮》,清华简亦见及《金滕》,与今本《金滕》大率一致。
过去论者就《金縢》所载史事的真实性问题尚有争议,如明人王廉、张孚敬,清人袁枚等,皆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
事实上,《金縢》的内容所折射出的,正是宗周的神道思想。
周公欲代武王死,即楚简所见“代祷”,亦见诸《左传》哀公六年及《元秘史》的相类传说,前贤已有所揭橥。
《金滕》的故事存在合理的内核,以及真实的历史背景。
刘起紆先生认为“《金縢》的故事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而篇中所载周公册祝之文,不论是它的思想内容,还是一些文句语汇,也都基本与西周初年的相符合。
因此这篇文件的主要部分确是西周初年的成品,应该是肯定无疑的。
……但其叙事部分则可能是后来东周史官所补充进去的”®。
良是。
刘立志先生认为周公作“诗”是不可信的,但愚意以为虽则《诗序》将著作权归诸周公的某些篇章未必尽是周公所作,却不能否定周公在周初制礼作乐以及构建宗周社会礼乐诗三位一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臀如刘立志先生亦怀疑《金縢》的可信性,继而质疑《鸱鸮》非周公所作。
这一问题已如前述,《金縢》的基本内容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不能置信。
以上就诸先生的说法作了简单的平议,《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本事,尚是一个未能遽定的问题。
质疑周公作《蟋蟀》本事可信性的说法固然不是没有漏洞,而要证明周公作《蟋蟀》确有其事,同样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三)《耆夜》的性质与周公作《蟠蟀》本事
笔者认为,欲确定《耆夜》所见周公作《蟋蟀》本事是可信的,一要说明《耆夜》的记载是可信的,二要证明《蟋蟀》的主旨与《耆夜》的故事背景是相一致的。
笔者认为,《耆夜》的历史背景、礼典仪式、乐诗内容等均有真实之素地,绝非向壁虚构。
这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其一,《耆夜》所叙历史背景的真实性。
《耆夜》所叙,正是“武王八年”周人戡耆(黎)而归。
《耆夜》的“耆”,正是《尚书•西伯勘黎》的“黎”,《尚书大传》《史记》以降,史家多定“西伯”为周文王,几成定说。
然唐人孔颖达于《尚书正义》有所质疑,宋人胡宏则在《皇王大纪》中提出西伯即周武王,此后学者多有争论。
宋代是“西伯戡黎”公案的肇端期,也是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时期。
这与当时理学盛行的大背景有关,因为不少论者的出发点便是:
以文王的德行,不可能去征伐黎国的。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从当时的情势出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
《尚书•西伯戡黎》所叙事件,乃是危及殷商王畿、引起商朝震恐的大事件,与清华简《耆夜》所记述的情况相合。
从周人东进的路径、当时的情势等方面看,可以肯定,《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中所伐之“耆”。
此外,据今本《竹书纪年》,周文王可能也征伐过一个黎(耆)国,但今本《竹书纪年》的可信度一直备受质疑,需审慎看待。
®
其二,《耆夜》所叙礼典的真实性。
《耆夜》载武王戡耆(黎)归来于文太室举行饮至礼,按“饮至”《左传》凡五见,隐公五年杜注云:
“饮于庙。
”桓公二年孔疏云:
“饮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庙中饮酒为乐也。
”《春秋左传词典》云:
“出国返回告庙饮从者。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隐公五年》云:
“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
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慰劳,谓之饮至。
其有功者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
”®饮至是行军程序的一个环节,在凯旋后,出征者回到宗庙祭告先祖,献俘授馘(可参见小盂鼎、虢季子白盘、敔簋等彝铭),并行饮至之礼,与此相伴随的有舍爵、策勋、大赏等仪式。
甲骨文、金文习见的“大室”(传世典籍作“太室”)、天亡簋(《集成》4261)的“天室”,即指宗庙的构成部分。
《耆夜》所见“文太室”,简文作“文大室”,“饮至”便发生于此。
④结合文献的记载,可知“饮至”有如下几点要素:
其一,时间在凯旋之后;其二,地点在宗庙,《耆夜》所谓“文太室”;其三,“饮至”主要是为了慰劳功臣并祭告祖先;其四,广义的“饮至”包括献俘、饮酒、赋诗、策勋(书劳)等;其五,狭义的“饮至”便指“舍爵”,即饮酒、酬酢赋诗。
《耆夜》的“饮至”,便是狭
义的概念。
除了传世典籍,“饮至”在甲骨文与今文中均有反映。
周原甲骨H11:
132载见“王會秦”一语,李学勤先生指出“贪秦”即周公东征鼎(《集成》2739,又称塱方鼎)所见“會秦”,也许是“饮至”一类庆祝凯旋的礼仪,此礼不见于殷墟卜辞。
®李先生此论独具卓识,在清华简出现之后先生又重申了这一点。
®陈致先生从李先生说,指出“貪秦”当是“饮臻”,即“饮至”。
®周公东征鼎铭文曰:
“惟周公于征东夷,丰伯、薄姑咸翦,公归繫于周庙。
戊辰,會秦會。
公赏塱贝百朋,用作尊彝。
”从这段铭文看,周公东征归来,于周庙行“饮至”,并“大赏”功臣,这与载籍的记述是一致的。
此外,腿侯驭方鼎(《集成》2810)等亦见“饮至”的相关记述。
由《耆夜》所见,“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姬®甲为位,作册佚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各安其位,尊卑有序。
与“饮至”密切相关的“策勋”即“书劳”。
《耆夜》载“作册佚为东堂之客”,“作册佚”简文作“作策逸”,系周武王时史官,其厕身周王室“饮至”的队伍中,其最大的任务当是“策勋”,并且记录这场饮至礼典以及赏赐情况。
《耆夜》的主要内容或原始素材或出自作册佚笔下,自当可能。
总之,《耆夜》所叙饮至礼的程序绝非向壁虚构。
其三,《耆夜》所见宴飨诗的真实性。
《耆夜》中,共涉及五首宴飨诗,分别是《乐乐旨酒》《糟乘》《姬赖》《明明上帝》《蟋蟀》。
其中除《蟋蟀》与今本相似之外,另外四首均不见今本《诗经》,属逸诗。
笔者曾系统梳理过《大雅》《小雅》中的宴獪诗,《香夜》所见逸诗的语言特征、文本结构、句式特征均与二雅所见宴飨诗一致。
《耆夜》所见逸诗有不少语句也与二雅的宴飨诗相类,如武王酬毕公的《乐乐旨酒》云: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乐乐旨酒”犹“旨酒乐乐”,义同《诗经•大雅•凫鹙》中的“旨酒欣欣”,亦可与《诗经•小雅•颉弁》“乐酒今夕”中的“乐酒”类观。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可与《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合观。
武王酬周公所作《辎乘》云:
“辎乘既饬。
”可与《诗经•小雅•采薇》“戎车既驾”、《诗经•小雅*六月》“戎车既饬”相参证,意谓整治战车。
周公酬武王的《明明上帝》云: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
”可参看《诗经•小雅•小明》的“明明上天,照临下土”,郑笺云:
“明明上
天,喻王者当光明。
”《耆夜》所见逸诗,许多词汇见诸金文,时间跨度由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
这几首逸诗可能经过后世的改写与整理,但其基本内容当是可信的。
其四,周公等人作诗有其合理性。
文献艳称周公制礼作乐,而“诗”正是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
《金縢》载周公作《鸱鸮》是值得相信的史料,许多将著作权归诸周公的诗篇,亦不能轻易否定。
此外,笔者认为春秋以前是诗歌大量创作、积累的时期,®与春秋时期赋古诗的风尚迥异,这也是与《耆夜》的记载相合的。
综上,《耆夜》的记载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
具体到《蟋蟀》上,还要讨论其诗旨。
《诗小序》云:
“《蟋蛑》,刺晋僖公也。
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
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
”谓{蟋蟀》是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
晋偁公,即《左传》桓公六年的晋僖侯、{史记•晋世家》的晋釐侯,于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公元前840〜前823年)在位。
在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中,发现了“晋侯对"的一批青铜器,“晋侯对”即晋僖公。
李学勤先生指出,历史上的晋僖公实际不是生活过俭,以致不合礼制,激起人们作诗以“刺”的君主,亊实刚好相反。
®李先生引证了与晋僖公有关的几件器物,其中有一组盥铭文曰:
“惟正月初吉庚寅,晋侯对作宝W阪盥,其用田狩湛乐于原隰,其万年永宝用。
”另有一件铺,铭文曰:
“惟九月初吉庚寅,晋侯对作铸W铺,用旨食大饗,其永宝用。
”李先生指出:
级铭说“田狩湛乐于原隰”,“湛乐”可参照《诗•常棣》“和乐且湛”。
其实"湛”可以通作“沈”,有不好的意思,如《诗•抑》“荒湛于酒”,《墨子.非命下》“内湛于酒乐”。
铺铭“旨食大餮”,“旨食”意是美食,“饗”我想应读为"燔”,即烤肉,铺是豆类器,可用以陈肉食。
将两篇特异的铭文结合起来,不难看出晋倍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敢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责族。
《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
《耆夜》所提供的简文《蟋蟀》的历史背景,则完全没有上面说的矛盾和
问题。
®
李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
因为根据《诗小序》,言《蟋蟀》是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但与《唐风•蟋蟀》的内容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古来多有异说。
李先生引证晋侯对的器物,一方面抽去了《诗小序》说法的根基——晋僖公绝非“俭不中礼”,恰恰相反,晋僖公是湎于逸乐的;另一方面,清华简《耆夜》的历史背景,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诗小序》将《蟋蛑》归人《唐风》解释为“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颇显牵强。
后世论者又多在《诗小序》这一说法的基础上益加发挥,在唐尧的问题上徘徊。
笔者上文对《唐风》地望以及《蟋蛑》果若系周公所作何以被归人《唐风》的问题均已有所涉及。
除了李先生所指出的晋侯对器物之外,最早对《蟋蟀》的解读同样有参考价值。
目前所见较为明确的、较早的对《蟋蟀》的解读主要有两则材料,其一是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记述:
“《蟋蟀》知难。
”整理者以为岁月难留之义,李奪先生则读为“戀”,系惶恐、惭愧之义。
®同样,《诗小序》所谓“俭不中礼”是难以与《孔子诗论》的记述相契合的,而清华简《耆夜》的历史背景却无这样的问题。
《耆夜》所见,周公赋《蟋蟀》正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过度淫乐,这与“知难”并无矛盾,而且相互呼应。
第二则材料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述了赵孟欲观子展、伯有等“七子之志”,请“七子”一一“赋诗”。
其中印段赋了《蟋蟀》,赵孟曰:
“善哉!
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正义》释“保家之主”:
“大夫称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
”《左传》同章又记载文子语:
“其余皆数世之主也。
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
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正义》曰:
“印段赋《蟋蟀》,义取好乐无荒。
无荒,即不淫也。
好乐则用乐以安民也。
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爱之。
守位必固,在人后亡,不亦可乎?
”③同样,这里的“赋诗之志”与《诗小序》存在矛盾,却与《耆夜》相契合。
《孔子诗论》与《左传》虽然没有提及《蟋蟀》究竟是何人所作,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耆夜》的记述。
结合晋侯对的器物,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诗小序》的说法缺乏依据。
关于《蟋蟀》的诗旨,便牵涉“志”的问题,以下试作阐论。
二“诗言志”义与《蟋蟀》的文本之志、诗人之志
诗之“志”可区分为诗人之志、读者之志和文本之志,本部分主要讨论《蟋蟀》的文本之志与诗人之志。
(一)“志”与“诗言志”
过去学者多关注“志”的诗学意涵,事实上,“志”亦是重要的思想史概念。
除了存在于“诗”中,“志”亦显现于“书”“易”中,饶宗颐先生归纳为诗言志、书溪志、易蔽志。
①《尚书•益稷》云:
“禹曰:
‘安汝止,惟几惟康。
其弼直,惟动丕应。
祺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左传》哀公十八年引《夏书》曰: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
”“志”之观念为先秦时人所保重,固属不诬。
“志”之观念,于淸华简《保训》亦有体现。
《保训》简4云:
“自稽厥志。
”“志”,整理者引<列子•汤问》注:
“谓心智。
”②<保训》第9号简见及“寺”字,文中读作“志”,不过作动词解。
“厥志”一语可参见《尚书•盘庚中》“以丕从厥志”。
<尚书•泰誓上》:
“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饶宗颐先生云:
“古人极重视‘志’。
‘志’为心所主宰,故云‘志,心般’(笔者按:
见郭店简《语丛一》)。
‘志’可说是一种‘中心思维’,思想上具有核心作用。
”®明乎此,不难理解“自稽串志”之神圣性矣。
饶公复征引《尚书•盘庚上》“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尚书•盘庚中》“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指出“中”是旗帜,设旗帜于心,作行为之指导,“设中于心”便是“志”;“志”所以为气之帅,正如“旗”“物”之为兵之帅,军队之立旗,与心之“设中”,道理没有二致的。
®饶宗颐先生的相关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厘淸“志”的意涵,有助于把握“诗言志”的内在含义。
《尚书•舜典》曰:
“诗言志。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
“诗以言志。
”《国语•楚语上》云:
“教之《诗》,而为
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庄子•天下》云:
“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云:
“诗言是,其志也。
”郭店简《语丛一》简38~39云:
“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
”《毛诗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皆谓诗言志。
《说文》云:
“诗,志也。
”按:
“志”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二者亦可相通。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26
“志,,写作爹,楚简的“诗,,多作鲁或今,郭店简《语丛一》简38所见“诗”的繁构作
辑,“诗”“志”二者的构形存在一定关系,《古文字谱系疏证》认为属同一派生系列。
②
“志”隶章纽之部,“诗”隶书纽之部,音近相假。
但“诗”与“志”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分疏。
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作者的内在蕴藉,“诗”则是“志”的外在呈现与言语反映。
中国古代文论向来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歧,然所谓“诗言志”,本身便包括“情”的质素。
所谓“诗言志”,不仅仅是就作诗而言的,在春秋诵古之风大炽的时候,它主要是就用诗之学而言的。
钱穆先生认为,所谓“诗言志”,古人多运用在政治场合中,所言之志都牵涉政治。
③朱自淸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将“诗言志”区分为献诗陈志、賦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
®朱先生从诗的用途的角度对“志”作了区分,这固然是一个角度。
但从文本的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文本看,诗之“志”可划分为诗人之志、读者之志和文本之志。
®这种划分方法,有助于区别诗的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