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docx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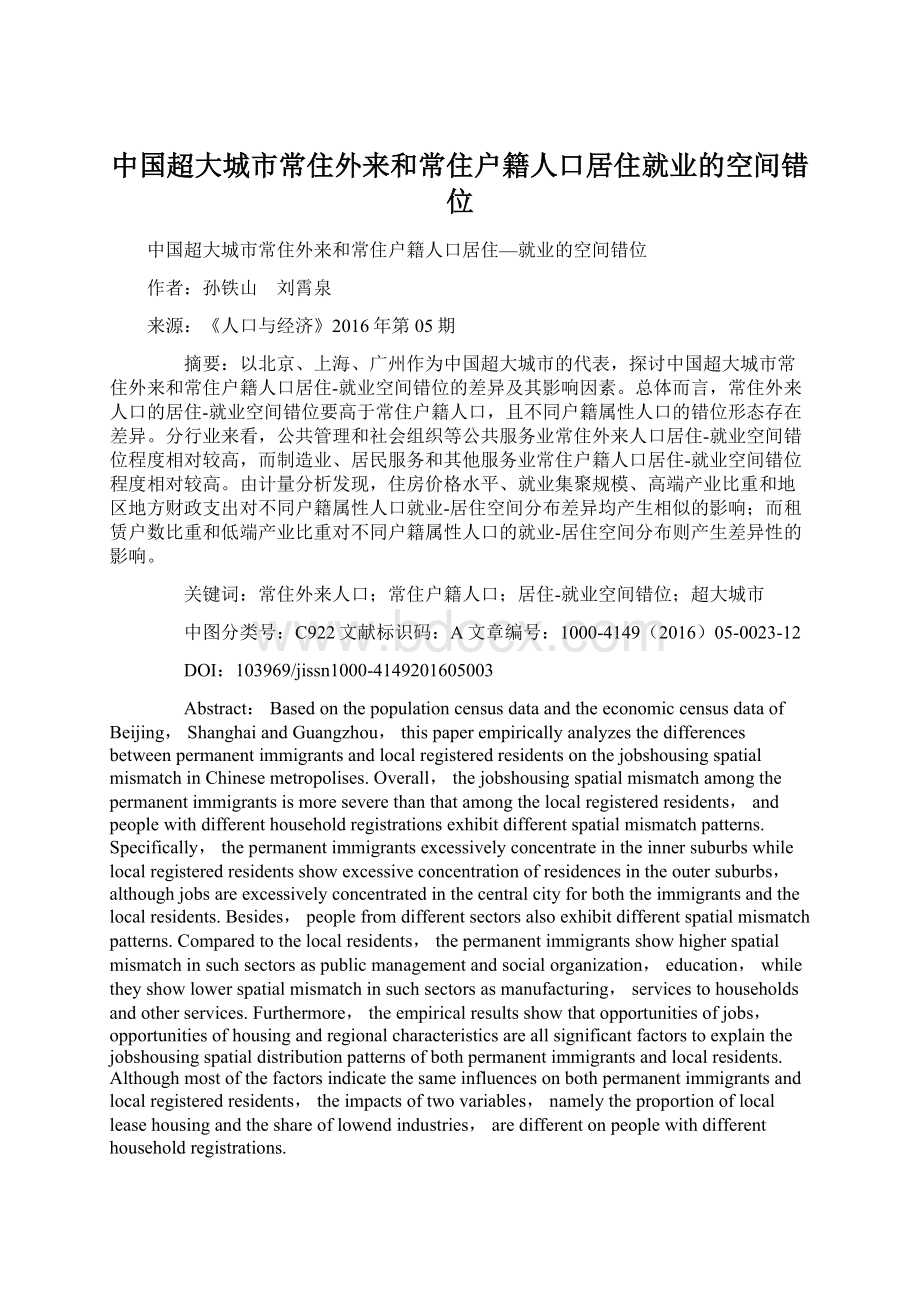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
作者:
孙铁山 刘霄泉
来源:
《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05期
摘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
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
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关键词:
常住外来人口;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超大城市
中图分类号:
C9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4149(2016)05-0023-12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1605003
Abstract:
BasedonthepopulationcensusdataandtheeconomiccensusdataofBeijing,ShanghaiandGuangzhou,thispaperempiricallyanalyzesthedifferencesbetweenpermanentimmigrantsandlocalregisteredresidentsonthejobshousingspatialmismatchinChinesemetropolises.Overall,thejobshousingspatialmismatchamongthepermanentimmigrantsismoreseverethanthatamongthelocalregisteredresidents,andpeoplewithdifferenthouseholdregistrationsexhibitdifferentspatialmismatchpatterns.Specifically,thepermanentimmigrantsexcessivelyconcentrateintheinnersuburbswhilelocalregisteredresidentsshowexcessiveconcentrationofresidencesintheoutersuburbs,althoughjobsareexcessivelyconcentratedinthecentralcityforboththeimmigrantsandthelocalresidents.Besides,peoplefromdifferentsectorsalsoexhibitdifferentspatialmismatchpatterns.Comparedtothelocalresidents,thepermanentimmigrantsshowhigherspatialmismatchinsuchsectorsaspublicmanagementandsocialorganization,education,whiletheyshowlowerspatialmismatchinsuchsectorsasmanufacturing,servicestohouseholdsandotherservices.Furthermore,theempiricalresultsshowthatopportunitiesofjobs,opportunitiesofhousingandregionalcharacteristicsareallsignificantfactorstoexplainthejobshousing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sofbothpermanentimmigrantsandlocalresidents.Althoughmostofthefactorsindicatethesameinfluencesonbothpermanentimmigrantsandlocalregisteredresidents,theimpactsoftwovariables,namelytheproportionoflocalleasehousingandtheshareoflowendindustries,aredifferentonpeoplewithdifferenthouseholdregistrations.
Keywords:
permanentimmigrants;localregisteredresidents;jobshousingspatialmismatch;metropolises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空间不断扩张、道路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郊区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由此带来的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逐渐凸显。
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超大城市的居民平均居住-就业通勤耗时约50分钟
数据来源于XX《2014年我的上班路全国50城市上班距离及用时排行榜》。
,较2006年增长了10分钟以上
数据来源于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编制的《华普城市畅行指数———中国城市畅行指数2006年度报告》,http:
//
继凯因(Kain)于1968年提出美国城市普遍存在黑人因居住隔离和工作岗位郊区化而导致居住-就业的空间不匹配假说后[1],对于美国城市内部职住空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并主要围绕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弱势群体。
这些研究不仅从居住、就业分布角度切入,分析住房市场中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壁垒所导致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问题[2-3],还从职住分离的时空对比、过度通勤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政策机制等方面做了研究[4-6]。
2000年以后,国内对中国城市内部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内总人口的职住匹配关系上[7-9]。
尽管现有研究对城市内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关注相对有限,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开始显现。
已有研究发现,弱势群体大多居住于距离城市中心15-20千米处,而对于特定群体职住空间不匹配的特殊性的探讨则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围绕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差异[10-12];二是分析由于就业行业性质、购房选择壁垒等社会性因素的限制而产生的职住分离现象[13-16]。
尽管中国城市内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现象不是由于种族隔离而产生的,但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人口中占比越来越高的常住外来人口所享受的工作机会和城市生活福利待遇与常住户籍人口有着显著差异[17]。
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的常住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均已超过35%
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1》、《上海统计年鉴2011》与《广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
因此,这些城市中不同户籍属性的人口所形成的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和错位程度,由于住房和劳动力市场障碍和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
目前,针对中国城市内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较多[18-21]。
这些研究发现,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间存在居住隔离的现象,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常住外来人口也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策壁垒。
从居住角度来看,城市中住房供给的受众为常住户籍人口,无论是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均主要面向常住户籍人口,并且常住户籍人口在住房贷款、公积金等住房金融上享有更多的福利,从而使他们更易于实现购房自住;相比之下,常住外来人口享有的福利较少,并且大部分的常住外来人口经济实力较弱,负担不起市区相对高昂的房价,因此常住外来人口大多在市区的外围地带形成租住集聚区。
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常住外来人口在进入事业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单位时都存在较多的限制,他们在这些单位中通常属于合同制员工,不享有与事业编制员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这些研究都指出了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就业活动中准入门槛和待遇的差异,但上述研究主要针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居住分布展开,并没有讨论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在居住-就业空间错位上的差异和机制。
总体上,我国城市中常住外来人口所面临的职住空间关系问题与美国少数族裔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我国超大城市内部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总体特征及差异情况。
目前,对于中国城市内部居住-就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匹配关系的研究大多针对单一城市的总人口和总就业,对城市中少数群体的空间分布研究也仅限于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的居住分布差异,并未引入就业分布来探讨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
实际上,中国城市中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在居住与就业待遇方面存在许多不容忽视
的差异,因而他们在居住-就业空间关系上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本文主要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探讨中国超大城市中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错位程度,重点关注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一级标题二、数据与方法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是指就业人口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在空间上的过度分离。
由于缺乏基于个体的居住地-工作地信息,本文中所说的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是指宏观层面上城市内就业人口居住分布和就业机会分布的差异,本质上是比较两种分布的空间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就业人口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测度使用的是不同地区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户籍就业人口和就业岗位的数据。
就业人口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分区县的常住就业人口数和常住外来就业人口数,反映城市内不同户籍属性就业人口的地区分布;就业岗位数据则来自于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中分区县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反映城市内就业机会的地区分布。
由于人口普查是基于居住地统计,而经济普查是基于工作地统计,对两者进行对比即可呈现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情况。
关于数据使用有两点情况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本文中就业人口居住分布使用的是人口普查资料,而就业机会的分布使用的是经济普查资料,存在年份不一致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人口普查中并不调查工作地信息(尽管人口普查中有就业信息,但人口普查中的就业是基于居住地的,因此不能反映就业机会的地区分布),因此就业机会的信息就只能依据经济普查,而两类普查在年份上并不一致。
从数据年份上看,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人口数据和2008年就业数据,虽然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来说,2008-2010年间就业有所增长,但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的是就业地区分布,即每个地区在全市就业中的占比,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大的变动。
因此,本文假设就业机会的地区分布在2008-2010年间相对稳定,用2008年就业地区分布反映2010年就业机会的分布情况,并不会严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
其次,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面临不同的机会和壁垒。
比如,常住外来人口由于户籍限制、受教育程度、所具备的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差异,与常住户籍人口相比,可能获取的就业机会更有限。
因此,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在空间上分布可能是不一致的。
但由于经济普查中就业数据并未按户籍属性区分,因此无法掌握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就业机会地区分布的差异,所以本文只能假定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在空间分布上是一致的。
对于不同户籍属性人口所面临就业机会差异导致的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问题,在本文中并未予以考虑。
此外,其他需要说明的数据情况包括:
①上海在2009年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将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因此相应调整经济普查中浦东新区数据;由于广州市人口普查资料中并没有常住外来人口数据,因此以跨县(市、区)流动人口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流动人口界定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可分为县(市)内流动人口、省内跨县(市)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
故此处流动人口属于常住外来人口。
的就业人口数据代替。
②由于经济普查仅对第二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进行统计,因此剔除掉人口普查中分行业就业人口数据中的农、林、牧、渔业和国际组织。
③人口普查中就业人口数为长表抽样数据,需要按10%抽样比推算就业人口总数。
为了比较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本文使用马丁(Martin)提出的空间错位指数(SpatialMismatchIndex,SMI)[4]测度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程度,匹配程度越高即空间错位程度越低,SMI越小,反之则SMI越大。
户籍属性j人口的空间错位指数SMIj计算如下:
SMIj=12Pj∑ni=1eiEPj-Pij
式中,Pij是i区县j户籍属性的就业人口数,ei是i区县的就业岗位数,Pj是该城市j户籍属性总的就业人口数,E是该城市总的就业岗位数,n是城市内的区县个数。
一级标题三、常住外来与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总体特征为分析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在超大城市中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分别计算北京、上海、广州三座城市汇总数据中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整体上,常住外来人口在三个城市中均呈现出比常住户籍人口更严重的空间错位问题(常住外来人口的SMI值均高于常住户籍人口)。
其中,三个城市中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空间错位指数差异最大的是广州,说明相比于北京、上海,广州常住外来人口的空间错位比常住户籍人口更严重。
为了进一步分析三个城市中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分别绘制三个城市各区县就业人口和就业岗位占全市比重随到城市中心距离分布变化的散点图,并进行局部回归拟合。
由图1可见,三个城市均表现出中心城区就业过度集中(在城市中心附近,就业分布拟合曲线高于居住分布拟合曲线),近郊区常住外来人口居住过度集中(在距城市中心20千米左右,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高于就业分布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远郊区常住户籍人口居住过度集中(在距城市中心40-50千米以外,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高于就业分布和常住外来人口分布的拟合曲线)。
这说明总体上,三个城市的就业机会仍相对集中在城市中心区,而居住活动的郊区化程度更高。
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更集中于经济活动聚集的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是因为常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更希望接近就业机会,因此不倾向于居住在离城市中心区过远的郊区地带,另一方面则由于城市中心区经济集聚导致地区住房价格过高,超出大多数常住外来人口的承受范围。
相比之下,常住户籍人口的居住分布则相对分散,户籍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在城市近郊区的集聚峰值较低,整体分布更加均衡。
此外,通过分城市的比较可知,三个城市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形态相对固定,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则会随着就业分布拟合曲线而产生变化,且与就业分布的拟合曲线更为贴近。
这也说明,相比于常住外来人口,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低。
相比于常住户籍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以公共服务业为主,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等。
这些行业
的正式员工通常属于事业编制,拥有本地户口且享受单位住房福利,并且该类住房大多是与工作地相对接近的单位居住区,从而更易于实现职住平衡。
相比之下,这些行业的常住外来人口一般为合同制员工,享受单位住房福利的可能性较小,需要在权衡通勤和住房成本后选择居住位置,相对难以实现职住接近,因而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程度要明显高于常住户籍人口。
以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例,图2显示了三个城市这两个行业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以及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情况,这两个行业均呈现出常住户籍人口的居住分布更加分散,且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与就业分布的拟合曲线贴合程度更高。
相比于常住户籍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较低的行业主要有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
这些行业的常住户籍人口面临相对更严重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
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广州都进行了产业布局的调整,工业企业向郊区转移[22],相比于其他行业,制造业的就业郊区化程度最高。
同样的,随着城市内部人口的郊区化,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也不断向郊区转移。
而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更加集中在城市近郊的外围地区,相对更加去中心化,因此常住外来人口在这些行业中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程度相对较高。
除此以外,原因还包括:
在工业企业郊区化搬迁的同时,早年分配的单位大院仍保留在了城市中心[23],所以出现了就业机会已经郊区化,而居住仍在城市中心区的空间错位。
以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例,图3显示了三个城市这两个行业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以及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情况。
由图3可见,相对于常住户籍人口的居住分布,就业机会与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布郊区化程度都更高,且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分布的拟合曲线更贴近于就业分布的拟合曲线。
一级标题五、常住外来与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二级标题1.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进一步分析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借鉴马丁提出的空间错位指数,并将其分解到各个区县,测度三个城市分区县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并以此为因变量建立实证分析的回归模型。
因变量的构建以每个区县就业岗位占所在城市的份额减去就业人口占该城市的份额,反映了各区县相对于人口居住的就业集聚情况,即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
也就是说,该指标越大,说明该区县的就业机会占全市的份额越高于居住人口占全市的份额,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越倾向于过度就业集聚;而该指标越小,则相反,说明该区县的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越倾向于过度居住集聚,就业机会供给相对不足。
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表明,居住与就业的相对分布会对居民的通勤行为、城市内土地和住房价格、工资水平等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会进一步反馈作用于居住和就业的空间互动关系[24]。
也就是说,住房决策和就业决策的形成不仅仅受到了个人和家庭特征的影响,还会因为住房市场、就业市场、地区环境等外部区域特性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城市中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企业和居民两类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进行区位决策所产生的结果。
本研究将人口区分为常住外来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探讨不同户籍属性居民的选择差异。
由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是居民居住地和就业地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在研究居住-就业空间匹配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单纯作用于居住选择或就业选择的地区住房机会和就业机会,还要考虑同时影响居民居住和就业选择的区域环境特征。
从居住机会来看,地区提供的居住机会越大、可进入的门槛越低,则对人口有更大的居住吸引力,形成过度居住集聚的可能性也越大。
在考虑居住机会对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时,要分别考虑自住与租住两种居住形式。
对具备购房能力的人群来说,购房决策会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人们通常根据其可承受房价的房屋分布范围来进行购房选址。
从而,相对于低房价地区,住房价格较高的地区可能会挤出更多的居住人口,[JP2]更倾向于形成过度就业集聚。
对于租住人群来说,地区的租住门槛越低,则对承担不起高昂房价需要租住的居民吸引力越大,越倾向于形成这类人群的过度居住集聚。
因此,选取地区人均GDP(pergdp)作为地区住房价格水平的代理变量,考察住房价格因素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影响。
选取地区家庭户中租赁住房比重(rent)反映地区租赁住房供给情况,考察地区租住门槛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影响。
三个城市各区县人均GDP是以各城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各区县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常住人口数得到的。
而租赁户数比重(rent)是基于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的家庭户住房状况表,以租赁户数除以总家庭户数计算得到的。
[JP]
与居住机会类似,就业机会从影响就业分布的角度对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通过集聚经济和规模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从而进一步扩大地区的就业机会。
因此,地区现有的就业集聚规模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重要因素,就业集聚规模较大的地区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往倾向于形成过度就业集聚。
虽然整体就业规模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产生的就业吸引力是相当的,但由于不同人群存在受教育程度和技能上的差异,而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本需求也不同,因此对于不同户籍属性人口面对相同的就业机会,在劳动市场上面临的选择障碍是不同的。
所以,不仅地区就业集聚规模会影响就业机会大小,地区的就业结构特征(地区经济中不同行业的构成)也会影响到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将面临的就业机会大小。
因此,选取地区就业集聚规模(employ)、高端产业比重(hedu)和低端产业比重(ledu)三个变量考察就业机会对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其中,就业集聚规模(employ)以经济普查资料中各区县就业岗位(从业人员)数占全市就业岗位(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测度;高端产业比重(hedu)和低端产业比重(ledu)是以各行业从业人员学历水平为依据,根据人口普查中分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筛选出三个城市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比重较高的行业作为高端产业,比重较低的行业作为低端产业,并分别计算各区县中这两类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
其中,高端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低端产业包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除了居住机会和就业机会外,影响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因素还包括其他的区域环境特征,比如完善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既会影响居民的居住选择,也会影响地区的就业集聚。
本文采用《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三个城市各区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作为代理变量,反映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水平(fiscal),对其进行城市内的标准化处理,作为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
此外,在回归模型中,进一步考虑三个城市的独特性和相互差异,从而加入了北京(bj)和上海(sh)两个虚拟变量以消除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异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