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docx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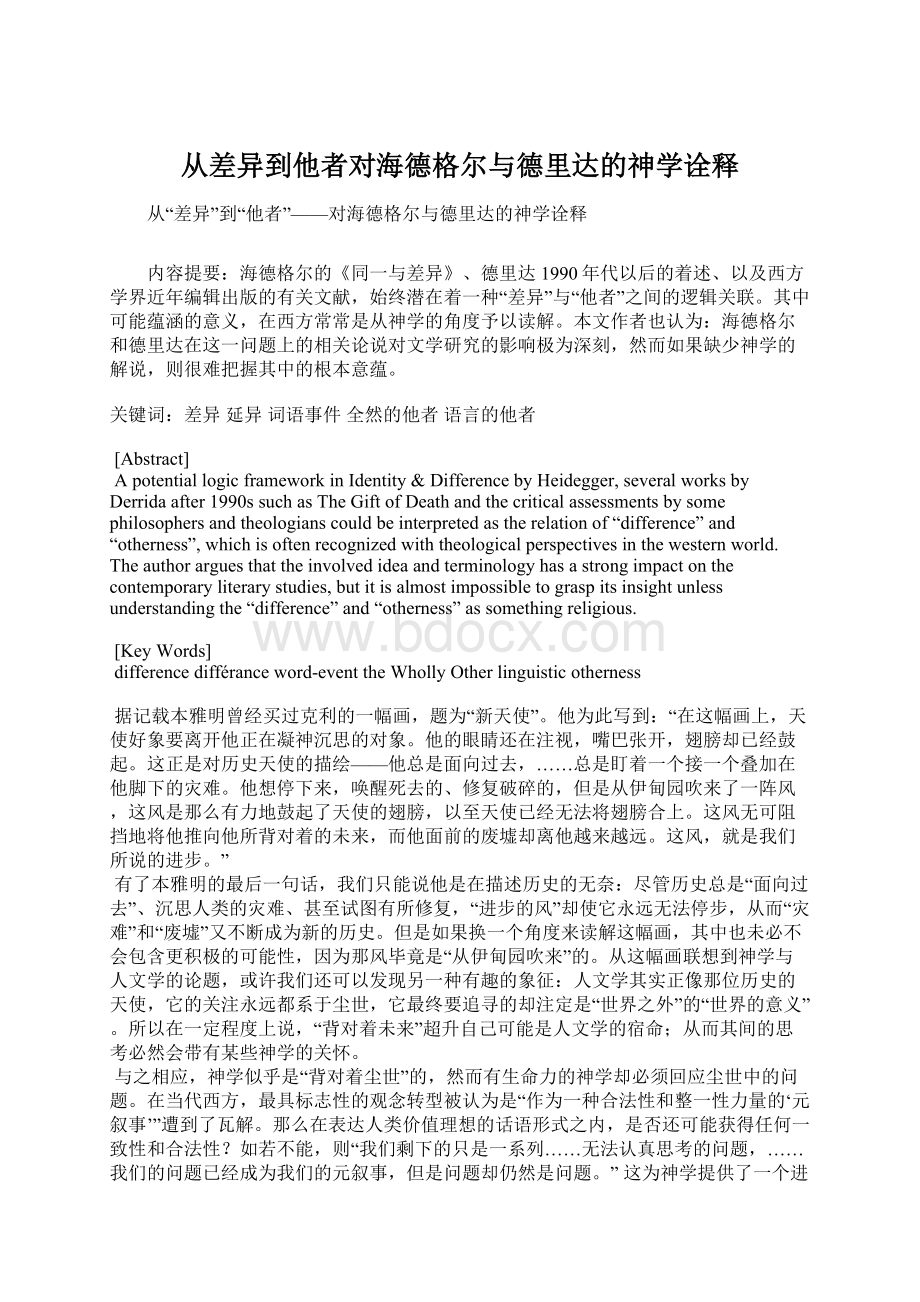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诠释
内容提要:
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德里达1990年代以后的着述、以及西方学界近年编辑出版的有关文献,始终潜在着一种“差异”与“他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其中可能蕴涵的意义,在西方常常是从神学的角度予以读解。
本文作者也认为: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然而如果缺少神学的解说,则很难把握其中的根本意蕴。
关键词:
差异延异词语事件全然的他者语言的他者
[Abstract]
ApotentiallogicframeworkinIdentity&DifferencebyHeidegger,severalworksbyDerridaafter1990ssuchasTheGiftofDeathandthecriticalassessmentsbysomephilosophersandtheologianscouldbeinterpretedastherelationof“difference”and“otherness”,whichisoftenrecognizedwiththeologicalperspectivesinthewesternworld.Theauthorarguesthattheinvolvedideaandterminologyhasastrongimpactonthecontemporaryliterarystudies,butitisalmostimpossibletograspitsinsightunlessunderstandingthe“difference”and“otherness”assomethingreligious.
[KeyWords]
differencedifféranceword-eventtheWhollyOtherlinguisticotherness
据记载本雅明曾经买过克利的一幅画,题为“新天使”。
他为此写到:
“在这幅画上,天使好象要离开他正在凝神沉思的对象。
他的眼睛还在注视,嘴巴张开,翅膀却已经鼓起。
这正是对历史天使的描绘——他总是面向过去,……总是盯着一个接一个叠加在他脚下的灾难。
他想停下来,唤醒死去的、修复破碎的,但是从伊甸园吹来了一阵风,这风是那么有力地鼓起了天使的翅膀,以至天使已经无法将翅膀合上。
这风无可阻挡地将他推向他所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废墟却离他越来越远。
这风,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
有了本雅明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描述历史的无奈:
尽管历史总是“面向过去”、沉思人类的灾难、甚至试图有所修复,“进步的风”却使它永远无法停步,从而“灾难”和“废墟”又不断成为新的历史。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读解这幅画,其中也未必不会包含更积极的可能性,因为那风毕竟是“从伊甸园吹来”的。
从这幅画联想到神学与人文学的论题,或许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有趣的象征:
人文学其实正像那位历史的天使,它的关注永远都系于尘世,它最终要追寻的却注定是“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意义”。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背对着未来”超升自己可能是人文学的宿命;从而其间的思考必然会带有某些神学的关怀。
与之相应,神学似乎是“背对着尘世”的,然而有生命力的神学却必须回应尘世中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最具标志性的观念转型被认为是“作为一种合法性和整一性力量的‘元叙事’”遭到了瓦解。
那么在表达人类价值理想的话语形式之内,是否还可能获得任何一致性和合法性?
如若不能,则“我们剩下的只是一系列……无法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元叙事,但是问题却仍然是问题。
”这为神学提供了一个进入人文学论域的最主要入口,因为可能只有神学才不得不把问题逼到极处。
当代人纷纷谈论“信仰的危机”,其实他们最基本的感受和最普遍的疑问,从根本上说应当是“意义的危机”。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基督教神学,那么它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也不仅限于“信仰”,而同样是首先关联着“意义”。
神学与人文学共同分有的问题领域,至少有两个关键的入思之处,即:
“意义本身”和承载意义的“语言”。
“意义本身”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对我们可能获得的“意义”有所质疑;承载意义的“语言”,则同样充满了弹性和张力。
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最为深刻,而以神学为参照解读其中的意义,却可能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一、“意义”:
“存在”与“存在本身”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结构”,在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一书中被专门设为一节,他在《什么是形而上学》第五版的前言中也曾提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性质”。
为什么“本体论”和“神学”可以被拼接为同一个词?
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不能简单地断言“形而上学是神学,因为它是本体论”,但是可以将问题转换为“神性是如何进入了哲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神学结构的根源何在”?
在他看来,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同整个哲学史对话”,特别是同黑格尔的存在之思相关联。
海德格尔的立论,接续着康德的“超验”与黑格尔的“同一”观念。
如他所述:
“对黑格尔来说,‘思’就是‘思本身’”,而“只有通过康德的观点、通过超验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思本身’;当黑格尔谈论‘作为思本身的思’之时,他的目的就是……将‘思’的超验本质……绝对化。
”
进而言之,“思”就是黑格尔的“理念”,而“理念”发展到最高的自由,则是所谓的“绝对理念”。
海德格尔注意到:
“在《逻辑学》接近结尾的地方,黑格尔提到这种‘绝对理念’:
只有‘绝对理念’才是存在,才是不朽的生命、自明的真理,亦即真理的全部。
”
按照海德格尔的读解,黑格尔从“思”追索终极意义的方式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意味。
第一,黑格尔将“存在”称为“不确定的直接性”。
所谓“不确定”是因为“存在”只能“通过绝对观念得以展示”,或者说“只有绝对之思才是关于存在的真理”;所谓“直接性”则是因为“存在”终究是“关于‘思’的绝对的自我之思”。
如果“关于存在的真理”既是“直接”切入“绝对之思”、又注定要取道于“不确定”的表现,那么也许只能如海德格尔所分析的那样,“真理总是含有这样的意味:
可知的东西本身是通过一种绝对肯定的‘知’而得以认知的”。
而黑格尔“将‘思’的超验本质绝对化”,便包含了使二者“同一”的可能。
第二,黑格尔还将“思”的问题置于“思”的历史。
在海德格尔看来:
“他与哲学史的关联是‘思’的、正是因此也是历史的。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的外在性是同理念关联在一起的,是理念之自我外化的结果。
从而外在性本身也是一种辩证的确定性。
……对于黑格尔,‘思’的问题本身是历史性的;……只有在‘思’的发展中才能思考‘思’之本身……”。
由此,历史的“外在性”与理念的“确定性”也必然是“同一”的。
针对上述的第一个方面,海德格尔最终要面对的“存在”仍然带有某种“自明”的性质,但是已无“直接性”可言。
因为对“存在”的认知要以某种“绝对肯定的‘知’”为前提,从而被遗忘了的“存在本身”既非任何具体的存在,也不可能同一于“绝对之思”。
在这里,“直接性”的“同一”已经被一种绝对的“差异”所取代;而一旦如此,神学的逻辑便隐含其间。
正如《同一与差异》一书的英译者所说:
“对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思’都是与存在相关,然而黑格尔的存在是‘绝对之思’对其自身的思索,……‘绝对’成为‘绝对的理念’;……海德格尔却并不追求无所不包的总体性,他的‘思’试图回复到尚未显示的真理,这一回复使得‘作为差异的存在’存在于‘思’之前,而不是‘思’的对象。
”这种不仅“被思”、而是先于“思”的存在,被认为是“跳出形而上学、切入了形而上的根基”。
神学家卡尔•巴特对认知关系的描述恰好与之相应:
“从根本上说,对上帝的认知……永远是间接的”。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存在之思”的进一步解说,同样为神学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黑格尔是在‘存在’之最空的‘空’处——亦即最一般的意义上——思索‘存在’。
同时,他也是在‘存在’之最完满的‘完满’中思索‘存在’。
”从“最空的空处”表达“最完满的完满”,这种思辨逻辑其实已经成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典型特征。
因此《圣经•腓立比书》中的“虚己”概念,可以在20世纪神学中得到一系列衍生。
比如大卫•特雷西的“自我倾空”,约翰•柯布的“倾空神性的上帝”等等。
卡尔•巴特对《罗马书》“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一句的释义,则集中体现了神学之“空”的存在意味:
“这里只有‘生’与‘死’、‘有’与‘无’之间最终的、无与伦比的矛盾,无处逃避。
……为了使死的活过来,活着的必须死去;为了使无变为有,有的必须变为无。
……上帝是全然的否定,他既是‘此’又是‘彼’。
他是否定之否定,……他是我们的死亡之死、我们的‘非存在’之不存在。
”
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说中,也许特别需要去辨析他所谓的“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神学结构的根源”。
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特征,是在于“存在”被视为“所有存在物共有的普遍基础”,被视为“所有存在物之上的最高基础”;如果由此推出“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也就使其带有了某种“本体论-神学的性质”。
然而黑格尔的“存在”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是“思”或者“绝对理念”,因此“有如他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所说:
‘真实即理性,理性即真实’。
这种A=A的同一原则,在费希特那里被表达为‘我’=‘我’。
”这固然是“将‘思’的超验本质绝对化”,而“存在本身”的“超验”问题可能也随之消解。
海德格尔从黑格尔“最空的空处”解说“存在”,当然也包括“空”掉“存在之思”的主体,当然是要通过源头的追索去确认“尚未显示”、或者根本不能对“我”显示的“真”。
用神学家的话说,那就是“真际”。
针对上述的第二个方面,海德格尔又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问题,引出他与黑格尔的“同一”与“差异”之辨:
“当我们试图与黑格尔进行‘思’的对话时,我们不仅是要与他讨论的同样的问题,而且也要使用同样的方法。
然而‘同样’并不是纯粹的同一。
在纯粹的同一中,差异消失了;在‘同样’中,差异则会出现。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黑格尔是以‘历史性的思’思考‘存在物’的存在;这就使黑格尔的‘思’属于历史的一个时期”。
而他自己,则是要“历史地思考存在”。
其间的实质性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最终都希望通向的“存在本身”,却仅仅在于究竟是让“不确定性”、“外在性”、“历史性”与“绝对之思”相互“同一”,还是持守它们之间的绝对“差异”。
所以海德格尔将黑格尔的问题概括为“关于存在物的存在”,即:
“在‘绝对之思’之中、也是作为‘绝对之思’而被思”。
而他则试图将这一问题转换为“关于区别于存在物的存在本身”。
简而言之,“黑格尔的‘思’的问题是作为绝对观念的理念”;海德格尔的“‘思’的问题则是作为差异的差异”。
从神学的角度切入“同一”与“差异”的不同思路,也许更容易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神学性质”。
神学的本体,只能意味着“存在本身”与“存在物”的绝对差异,乃至在“存在物”的意义上谈论上帝的存在与否,早已不是20世纪的神学方式。
所以约翰•希克直言:
“我们所思考的……命题不是‘上帝存在’,因为这等于将神的存在当作一个孤立的受限制的事实”;“我们不可奢望经验到神之存在的无限性”。
关于这种对于“存在本身”的意识,在神学方面还有卡尔•巴特的命题与海德格尔相互呼应:
“我们自身并不能理解真理”,所以应当“让上帝成为上帝”。
有如海德格尔从“差异”求得的Being与beings之别,卡尔•巴特从“差异”推出的,也是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的Word与words。
而当基督教在希腊传统的影响下从犹太教当中衍生出来、并且成为西方的主导性宗教时,最大的变化之一正是将犹太教以“上帝的话语”来代表的耶和华转换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将“词语”转换为“事件”。
由此,当代西方出现了两位对于意义诠释最富启发性的神学家:
艾伯林和托伦斯。
而他们所使用的关键词,恰好都是“词语事件”。
从另一方面看,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之后,一再论及宗教和伦理的问题,如《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早期希腊思想中的神圣》、《价值的本体论问题》。
特别是他在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六篇论文,越来越多地通过宗教-伦理问题讨论诠释学的意义。
为什么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研究领域启发了诸多“敞开的文本”,他自己却返回古希腊-基督教的意义系统,为“诠释”导入“神圣性”和“价值伦理”的维度?
无论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何种结论,显然都会与倾向于“消解性”的“诠释”有所不同。
在其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加达默尔也是用同样的思路对海德格尔作出诠释,认为海德格尔“从早期就开始被宗教问题折磨着,……以后转向诗乃出自于宗教关怀”等等。
如果进一步将海德格尔的讨论还原于“意义”问题,则需要追寻的也应当是“意义本身”、而不是可以回避这一追寻的“文本的愉悦”。
这样,我们会发现“差异”的观念在德里达的“延异”中得到了延伸。
更重要的是:
“延异”同样未必是消解性的,同样与神学的“意义”存在着可能的同构关系。
二、“延异”:
“他异性”与“全然的他者”
一般而言,“延异”当然是要揭示最终意义的不断被延缓、不断由它与其它意义的差异得到标识,从而表明“意义”永远都是相互关联的,永远不可能自我完成,永远不会有一种固定意义的存在。
“延异”概念的这一义涵似乎很明确,但是当代神学的另一种相关讨论,又使它凸显出完全不同的指向。
这也许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重新检点“延异”在人文学领域的命运。
就“延异”的思路而言,“能指”与“所指”是最基本的概念工具。
按照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的描述:
作为“结构层面”的“能指”和作为“意义层面”的“所指”构成“第一级符号”;“第一级符号”又作为“第二级符号”的“能指”,与新的“所指”共同构成“第二级符号”;这样的“意指行为”还可以衍生出三级、四级乃至无限的符号系统,没有终极。
罗兰•巴尔特的话题也可见之于德里达的论说:
“符号指涉概念,概念又指涉世界,从而使我们得以把握……世界;……但是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区别,又意味着没有任何符号可以完全等同于它所指涉的对象;符号并非直接指涉事物,而是指涉其它符号,其它符号也同样是指涉另一些符号。
”
在罗兰•巴尔特看来,这似乎可以成全一种无限圆满的意义神话或者他所谓的“文本的愉悦”,但是“意义”不断被延缓、衍生和变化,并不能从“存在本身”的意义上解决“意义”的问题,亦即并不能解决“意义本身”的问题。
在一般的文学阅读中,这也许可以带来某种“愉悦”,不过信仰或者价值的问题毕竟很难从属于这种“审美的统治”。
因此德国神学家库舍尔做出了一针见血的归纳:
“符号理论的存在,有赖于它洞见了‘洞见在本质上的不可能’;其意义产生于对所有符号的‘终极无意义性’的认识;其真理则是描述‘人类可能不存在绝对真理’的事实。
”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世纪的另外一些神学家的论说似乎却与这种消解意义的符号理论完全一致。
比如大卫•特雷西几乎是带着一种赞赏的语气重述着德里达的观点:
“为了使意义得以发生,我们……需要延宕我们对完整意义提出的要求,……所有的差别都始终在延缓意义的完整,‘差别’已经成为‘延异’”。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的讨论也同德里达如出一辙:
“《圣经》……仅仅是符号,而且是符号的符号,即先知和使徒对耶稣基督这一基本符号之启示的见证”。
以罗兰•巴尔特的“意指行为”为据,卡尔•巴特所说的“符号的符号”当然可以翻译为德里达的“符号指涉符号”。
所以才有论者用德里达的理论模型去诠释卡尔•巴特的辩证神学,甚至认为“德里达发展出来的概念工具比巴特自己的工具更适合巴特的主题”,因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可以使巴特语言神学的一致性更为清晰”。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
卡尔•巴特所谓的“符号的符号”,是要强调“不可理解的上帝是通过耶稣得以理解,不在世、不可见的上帝是通过耶稣而在世和可见”,其要旨是去证实一种不断被“延异”、却又是作为“绝对”而存在的“意义本身”。
这当然也是一种“意指行为”,但是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没有终极”,而是在于阅读主体和被阅读的文本都不可能完全企及这一终极。
从另一方面看,如何理解这一“终极”又关涉到阅读活动中的“他者”概念。
正如米勒所说:
“在德里达的全部着作中,‘他者’的概念都是最重要的,即使有时是使用不同的称谓或者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延异’……”
无论“延异”还是“意指行为”,都是经由文本或者主体的“间性”,隐约通向一个“他者”。
但是对于“文本间性”或者“主体间性”而言的“他者”,只是由不同的文本或主体相互充任的,因而所谓的“他者”不过是相对于此一“文本”或此一“主体”的“对方”,与彼一“文本”或彼一“主体”并无根本的差异。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差异的差异”之思路,“延异”中的“他者”也应当具有一种绝对的“他异性”。
一旦由此入思,最终获得的几乎必然是一种神学式的概念,亦即卡尔•巴特的“全然的他者”。
“他异性”或者“全然的他者”也正是德里达所使用的概念,但是他的“他者”本身就充满了“他异性”,很难说是经由“延异”指向的一个终极,有时甚至很难与一般而言的“他者”相区别。
那么,这样的“他者”是否可以通向“全然”的神学意义?
这样的“他异性”又是如何与“意义”的追索相关联?
德里达在1992年出版的《赠予死亡》一书,第四部分正是专门讨论“他异性”的问题。
然而从标题开始,德里达似乎就想将我们带入一种难以理解的同义反复:
toutautreesttoutautre。
根据德里达自己的解释:
“辨识出同一个字tout的两种语法功能和两种涵义,也就可以区分两个autre”。
tout既可以是形容词,意指“某个”、“某一个”或者“另一个”;也可以是副词,意指“完全、绝对、鲜明、无限的另一个”。
而如果第一个tout是形容词、第二个是副词,“那么第一个autre就成了名词,第二个则完全可能是形容词或者修饰语”。
据此,该书英文本译者采用了everyother(one)isevery(bit)other的表达方式——在前一个“他者”之后加入的one和后一个“他者”之前加入的bit,正是为了表明前者的名词性质和后者的形容词性质。
这样,“每一个他者就是每一个他者”便成为“每一个他者都是他异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
德里达不仅用“完全、绝对、鲜明、无限”等等“副词”来界说“他异性”,不仅直接使用卡尔•巴特的神学概念“thewhollyother”,他甚至还将toutautreesttoutautre与巴特式的命题Diusesttoutautre相互并置。
因此米勒和卡普托都干脆用巴特的概念翻译德里达:
Everyotheriswhollyother。
不过,德里达的落点似乎又并非“上帝”,却反复强调“每一个他者都是全然的他者”。
从巴特神学的角度看,其中的问题是相当明显的:
如果“全然的他者”不能与“每一个他者”有任何质的区分,那么即使“延异”可以从“存在”、“意义”通向“存在本身”和“意义本身”,上帝式的“他者”仍然不会是它的最终归宿,从而“本身”的问题可能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一点,是德里达的“延异”与“他者”之所以会引出诸多歧义的关键。
比如,约翰•卢林用“意义的延迟、延送和延误”来描述德里达的“意指过程”。
莱维纳斯则认为德里达的作用有如康德,是“使正统哲学与批判哲学相区别的分界线”。
但是在“德里达的诗学”中,“起初一切都井然有序,而在几页或者几段文字之后,通过可怕的质疑,思想已经无处容身”。
对于这位法国籍的犹太思想家,阅读德里达甚至会使他“想到1940年的大逃亡”,即:
撤退的法国军队来到那些毫无准备的地区时,咖啡馆、时装店、理发厅、面包房还在照常营业,而仅仅是由于传来了“纳粹入侵”的消息,仅仅是由于这种“纯粹的文字效果”,“一个小时以后,一切都被解构、一切都被摧毁了”,“记载着昔日荣耀的道路”成为人们的逃亡之路。
不过莱维纳斯特别提到一段“象征性的插曲”:
一位喝得半醉的理发师拦住撤退的士兵,为他们免费刮脸。
相对于当时的混乱,莱维纳斯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延宕”,是“未来的延异”,是将“明天”拉到了“今天”。
因此他与约翰•卢林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于:
尽管那位理发师可能属于柏拉图所说的第四种“迷狂”,但是“西方形而上学的话语”正是由此保存。
也就是说,如果“延异”使不属于今天的意义对今天产生意义,那么这未必不可能成为“抛弃逻各斯中心话语”之后的形而上学。
在此,莱维纳斯又是以相当神学化的方式,称之为“全然的其他”。
在德里达本人的具体论述中,他确实是借助“全然的他者”之概念,区别了toutautreesttoutautre所包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
“一种是要为上帝自身或者为任何单一的个体持守它所可能持守的‘全然的他者’之性质,亦即‘无限的他者’。
另一种则是从‘全然的他者’之无限的‘他异性’之中,……辨认出每一个他者,……比如每一个男性和女性。
”这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读解,而德里达认为:
其中始终有一种“差异性与相似性的游戏”,即“上帝与邻舍的相似,作为上帝的无限他异性和作为他人的无限他异性之相似”。
在德里达看来,“绝对的独一性”其实正是“来自人与他人之关系的绝对的他异性”。
也就是说,承认每个人的差异就是承认每个人的独一;承认每个人的独一就要放弃“上帝的他异性”和“他人的他异性”之区别。
所以“将他异性联系于独一性”意味着“普遍性与独一性个案之间的协定”。
这样,德里达相信可以用“上帝”置换toutautreesttoutautre之中的任何一个toutautre,使之成为“每一个他者都是上帝”或者“上帝是他异性的”。
后一种置换“是将上帝界定为无限的他者、全然的他者和他异性的”;前一种置换则是说“每一个他者、每一个他人都是上帝,因为他或者她是像上帝一样的全然的他者。
”
总之“这两个独特的‘他者’正如同一个‘他者’”,从而“他者”虽然未必是“延异”的归宿,却也与“文本间性”或者“主体间性”对“他者”的简化截然不同。
相对而言,德里达类似于文字游戏的复杂推导,或许是要成全一种“语言的间性”,正如他自己所说:
“这种文字游戏似乎包含了一个可能的奥秘,这奥秘在唯一的句子、更准确地说是在唯一的语言中既隐匿自己又揭示自己;至少,是在一类有限的语言之中,是在向无限敞开的语言的有限性之中”。
如果将“他者”比之于“意义本身”,那么按照德里达的看法,恰恰是这种“语言的间性”才“使拯救的希望得以展开”。
仅就“语言”论,也许还可以说德里达只是强调toutautreesttoutautre的难以译解:
至少“在传统的翻译之意义上,其字义不是可以普遍翻译的”。
但是他反复证明“这种不可翻译性……就像一个藏在母语中的奥秘”,至于它为什么能“使拯救的希望得以展开”,德里达进一步把“母语的奥秘”关联于“圣父明察的奥秘”和“以撒牺牲的奥秘”。
因此,不能不说这种语言的“奥秘”中包含着某种神圣的成分。
关于“圣父的明察”,德里达反复称引的正是《新约•马太福音》中的经文:
“你的父在暗中察看”。
他认为“在他者之间,不可见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
第一是“可见的不可见”,德里达的例子是在地下藏匿核武器等等,总之这只是表层的不可见。
第二种才是“绝对的不可见”,即“你的父在暗中察看”,这就涉及了“与全然的他者之关系”。
通过“绝对不可见”的奥秘,德里达发现“我”只能听、却不能看,“上帝看着我、我却看不见他”,从而“一切决定都不再是我的,……我只能去回应那决定”;不过“正是在这种对我的凝视中,我的责任才得以产生”,因为“责任”就在于“对他者的……回应”。
同时,“当‘我’的身份在奥秘中战栗时”,“我是谁”的问题便不再是意指“我是谁”,却是要追问“谁是那个可以说‘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