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历史6558529502593.docx
《自然权利与历史6558529502593.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自然权利与历史6558529502593.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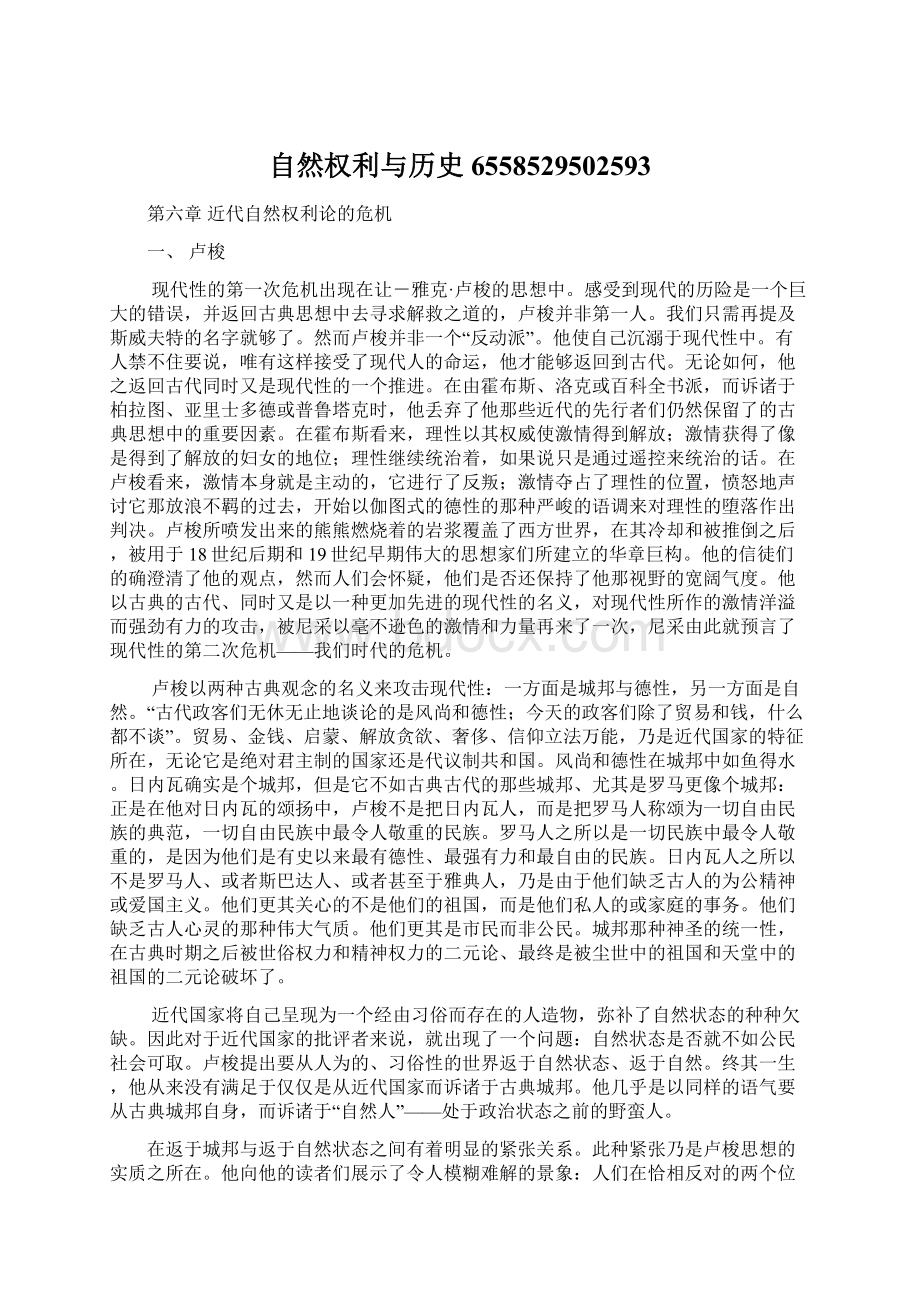
自然权利与历史6558529502593
第六章近代自然权利论的危机
一、卢梭
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让-雅克·卢梭的思想中。
感受到现代的历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返回古典思想中去寻求解救之道的,卢梭并非第一人。
我们只需再提及斯威夫特的名字就够了。
然而卢梭并非一个“反动派”。
他使自己沉溺于现代性中。
有人禁不住要说,唯有这样接受了现代人的命运,他才能够返回到古代。
无论如何,他之返回古代同时又是现代性的一个推进。
在由霍布斯、洛克或百科全书派,而诉诸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普鲁塔克时,他丢弃了他那些近代的先行者们仍然保留了的古典思想中的重要因素。
在霍布斯看来,理性以其权威使激情得到解放;激情获得了像是得到了解放的妇女的地位;理性继续统治着,如果说只是通过遥控来统治的话。
在卢梭看来,激情本身就是主动的,它进行了反叛;激情夺占了理性的位置,愤怒地声讨它那放浪不羁的过去,开始以伽图式的德性的那种严峻的语调来对理性的堕落作出判决。
卢梭所喷发出来的熊熊燃烧着的岩浆覆盖了西方世界,在其冷却和被推倒之后,被用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建立的华章巨构。
他的信徒们的确澄清了他的观点,然而人们会怀疑,他们是否还保持了他那视野的宽阔气度。
他以古典的古代、同时又是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现代性的名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激情洋溢而强劲有力的攻击,被尼采以毫不逊色的激情和力量再来了一次,尼采由此就预言了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我们时代的危机。
卢梭以两种古典观念的名义来攻击现代性:
一方面是城邦与德性,另一方面是自然。
“古代政客们无休无止地谈论的是风尚和德性;今天的政客们除了贸易和钱,什么都不谈”。
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近代国家的特征所在,无论它是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还是代议制共和国。
风尚和德性在城邦中如鱼得水。
日内瓦确实是个城邦,但是它不如古典古代的那些城邦、尤其是罗马更像个城邦:
正是在他对日内瓦的颂扬中,卢梭不是把日内瓦人,而是把罗马人称颂为一切自由民族的典范,一切自由民族中最令人敬重的民族。
罗马人之所以是一切民族中最令人敬重的,是因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有德性、最强有力和最自由的民族。
日内瓦人之所以不是罗马人、或者斯巴达人、或者甚至于雅典人,乃是由于他们缺乏古人的为公精神或爱国主义。
他们更其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他们私人的或家庭的事务。
他们缺乏古人心灵的那种伟大气质。
他们更其是市民而非公民。
城邦那种神圣的统一性,在古典时期之后被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论、最终是被尘世中的祖国和天堂中的祖国的二元论破坏了。
近代国家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经由习俗而存在的人造物,弥补了自然状态的种种欠缺。
因此对于近代国家的批评者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自然状态是否就不如公民社会可取。
卢梭提出要从人为的、习俗性的世界返于自然状态、返于自然。
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满足于仅仅是从近代国家而诉诸于古典城邦。
他几乎是以同样的语气要从古典城邦自身,而诉诸于“自然人”——处于政治状态之前的野蛮人。
在返于城邦与返于自然状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此种紧张乃是卢梭思想的实质之所在。
他向他的读者们展示了令人模糊难解的景象:
人们在恰相反对的两个位置上持续不断地前后摆动。
有时他诚挚地为个人或心灵摆脱一切限制或权威的权利而辩护;有时他又同样诚挚地要求个人完全顺从于社会或国家,站在了严苛的道德或社会戒律的一边。
今天,绝大部分严肃的卢梭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他最终成功地克服了那在他们看来是暂时的摇摆不定。
他们认为,成熟期的卢梭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在他看来同样地既满足了个人的、又满足了社会的合法要求,解决之道在于某种类型的社会。
此种解释碰到了关键性的反对意见。
卢梭至死都认为,即使是正当的社会也是一种形式的束缚。
因此,他顶多把他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看作不过是一个能够容忍的近似的解决方法——一种人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的近似的解决之道。
因此,告别社会、权威、限制和责任,或者说返于自然,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
于是,问题就不是他如何解决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是他是如何看待那种无法解决的冲突的。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为我们更准确地阐述这一问题提供了锁钥。
在他那篇最早期的重要著述中,卢梭以德性的名义来攻击科学与艺术:
科学与艺术是同德性不相容的,而德性乃是唯一要紧之物。
德性显然需要得到信仰或有神论(尽管不一定是一神论)的支持。
然而他所强调的还是德性自身。
卢梭通过提到公民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布里索斯、以及尤其是伽图(伽图乃是“最伟大的人”)的样板,对于德性的内涵作了对其目的而言足够清楚的暗示。
德性主要地乃是政治品德,爱国者的品德,或者是一整个民族的品德。
德性要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而自由的社会又以德性为前提:
德性与自由的社会彼此相属。
卢梭在两个地方偏离了他古典的楷模们。
他追随孟德斯鸠,将德性视作民主制的原则:
德性与平等或对平等的承认是不可分的。
其次,他相信,为德性所必需的知识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他所谓的“良知”(或者“纯朴心灵的崇高科学”)或情感和本能提供的。
他所指的情感将表明原本是同情的情感,那是一切真正的善行的自然根基。
卢梭在他之倾向于民主制和他之将情感置于理性之上之间,看到了某种联系。
由于卢梭认为德性与自由社会是彼此相属的,他就可以通过证明科学与自由社会不相容,来表明科学与德性是不相容的。
《论科学与艺术》中的推论可以简化为五个主要论点,在那本著作中这些论点的确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在阅读《论科学与艺术》时还考虑到卢梭以后的著述,这些论点就会相当清晰了。
在卢梭看来,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他认为,公民社会只有在其具有自己的特性时才会是健康的,而这就要求其个性要由民族的、独一无二的制度来创造和养成。
这些制度必须要由某种民族“哲学”、某种不可能转让给其它社会的思维方式来赋予其生机:
“每一民族的哲学不大会适用于另一个民族”。
另一方面,科学或哲学本质上又具有普遍性。
科学或哲学必定会削弱民族“哲学”的力量,从而削弱公民们对于他们那共同体的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或风尚的依恋。
换句话说,尽管科学本质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却必须由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一种与民族的仇敌誓不两立的精神来激励。
政治社会乃是一个要针对别的国家来防卫自己的社会,它必须培养尚武的美德,而且它通常养成的是一种好战的精神。
相反地,哲学或科学是要破坏好战精神的。
此外,社会要求其成员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共同利益,他们要为了他们的同胞而费心操劳:
“每个懒惰的公民都是一个恶棍”。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悠闲乃是科学的要素,悠闲被错误地与懒惰区分开来。
换言之,真正的公民献身于职责,而哲学家或科学家则自私地追逐他的快乐。
另外,社会要求其成员对某种宗教信仰坚定不移。
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定信念,“我们的信条”或“法律授权的神圣信条”,受到了科学的威胁。
科学关注的是真理本身,而不在意它所能带来的功利,因此由于它的用心就会有导向无用的甚而是有害的真理的危险。
而实际上,真理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对真理的寻求导向的是危险的错误或者是危险的怀疑主义。
社会的要素乃是信仰或意见。
因此,科学,或者说要以知识来取代意见的努力,必定会威胁到社会。
再者,自由社会的前提是,其成员放弃了他们原初的或自然的自由,来换取习俗性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要服从于共同体的法律或者统一的行为准则,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制订这些法律和准则出力。
公民社会要求服从,要求将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转变为公民。
然而,哲学家或科学家却一定要以绝对的真诚来依循他“自己的天才”,全然不顾公意或共同的思维方式。
最后,自由社会是通过以习俗性的平等取代自然的不平等而实现了。
对科学的追求,需要对天赋的呵护,那是属于自然的不平等的;它对于不平等的悉心照顾乃是它鲜明的特征,因此人们蛮可以说,对于卓越性或者傲气的关切,乃是科学或哲学的根源。
卢梭是凭藉着科学或哲学建立起了这样的论旨:
科学或哲学与自由社会、从而与德性是不相容的。
在这样做时,他就默认了科学或哲学也可以是让人心生敬意的,也就是说,与德性是相容的。
他并没有停留于此。
正是在这篇《论科学与艺术》中,他高度赞颂了那些有学识的社会,那些社会的成员必须将学问与德性结合在一起;他把培根、笛卡儿和牛顿称作人类的导师;他提出第一流的学者们要将君王的宫廷当作自己光荣的避难所,好从那里对人民就他们的职责进行启蒙,并因此为人民的幸福作出贡献。
卢梭对这一矛盾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
照第一种解决方法,科学对于一个好社会而言是坏的,而对于一个坏社会而言是好的。
在一个腐化的社会中,在一个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对于一切神圣的意见或成见的攻击都是合理的,因为社会道德不会比它如此这般的模样更糟糕了。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只有科学能够给人们提供救济之道:
对于社会的基础的探讨,可能导致发现对于当下种种恶行的救治之方。
倘若卢梭的著作只是对他的同时代人——亦即腐化社会的一员——发言的话,这种解决方法就足够了。
然而他想要成为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作者,而且他预见到了一场革命。
因此,他的写作也考虑到了一个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比迄今为止的社会都更加完美的社会)的需要,那种社会在革命之后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此种对于政治问题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哲学发现的,而且也只能由哲学来发现。
因此,哲学就不仅仅对于一个坏社会而言才是好的;它对于最好的社会的出现不可或缺。
照卢梭提出的第二种解决方法,科学对于“个人”、亦即对于“某些伟大的天才”或“某些得天独厚的心灵”或“一小群真正的哲学家”(他自己是其中之一)而言是好的,对于“人民”或“公众”或“庸人”(leshommesvulgaires)而言则是坏的。
因此,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普及化了的科学或科学知识的流播。
科学知识的流播不仅对于社会,而且对于科学或哲学本身都是灾难性的;科学一经普及,就蜕化为意见,或者,对于偏见的反抗本身就成为了偏见。
科学必须保持为极少数人的领地;对于普通常人来说,它一定得是秘而不传的。
由于每本书不光是极少数人、而且也是每一个识文断字的人都能看到的,卢梭的原则就迫使他在表达他的哲学或科学学说时作了很多保留。
他确信,在一个像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样的腐化社会中,哲学知识的流播就不再是有害的;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不只是为同代人写作的。
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才能理解《论科学与艺术》。
那本书的功用是警告人们要远离科学,但指的不是所有的人,而只是普通人。
当卢梭把科学当作纯然坏的东西来加以拒斥时,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对普通人说法。
然而他又暗示,他远不是什么普通人,而只是一个以普通人的面目出现的哲学家,而且,他并不是在最终向“人民”发话,而只是在向那些不屈从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或他们的社会的意见的人们发话。
这样看起来,卢梭之相信在科学与社会(或“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谐,乃是他之相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的主要原由,或者是他最终给“个人”、亦即极少数“得天独厚的心灵”反对即使是来自最好社会的要求留有余地的主要原由。
卢梭在肉体的需求中找到了社会的基础,以及他在谈到自己时说,没有任何与他的肉体利益相关的东西会真正占据他的心灵这样的事实,验证了我们的这个印象:
他自己只有在纯净的、无功利心的沉思——比如说,以提奥弗拉斯特的那种精神来研究植物——所带来的欢愉和狂喜之中,才能找到完美的幸福和像神一样的自足。
于是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
卢梭是在试图恢复与启蒙运动相反对的古典的哲学观念。
他之再度强调人们在智力天赋方面的自然不平等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与启蒙运动是针锋相对的。
然而我们必须马上就补充说,卢梭在采取了古典观念的同时,又再次拜倒在他所竭力要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之前。
那迫使他从公民社会来求诸于自然的同一种力量,又迫使他从哲学或科学来求诸于自然。
《论科学与艺术》中有关科学的价值的矛盾之处,由卢梭的第三种解决方法得到了完备的解决,第一和第二种解决方法都构成了其中的组成部分。
前两种解决方法都是通过区分科学的两种接受者来解决矛盾。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区分两种科学来解决矛盾:
一种科学是与德性不相容的,人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或者纯粹的理论科学),还有一种科学是与德性相匹配的,人们可以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乃是自我认识;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因此那是一种怀疑论,一种“并非出自本心的怀疑论”,但这不是一种危险的怀疑论。
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德性并不能等同,因为德性乃是“纯朴灵魂的科学”,而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个纯朴的灵魂。
虽然所有人都可以是有德性的,但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却是极少数人才能够保有的。
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本质上是次要的;细微无声的德性的践履才真正要紧。
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有着针对种种诡辩巧计来保护“纯朴灵魂的科学”或良心的职责。
对于此种保护的需要并非偶尔才有,也不限于腐化之时。
就像卢梭最伟大的信徒之一所说的,纯朴或天真确实是美好事物,然而却容易误入歧途;“因此,那在其它方面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或克制而行的智慧,需要科学。
”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的,不是苏格拉底,而是那些纯朴的灵魂或人民。
真正的哲学家要履行绝对必须的职责,成为自由社会的德性的导师。
作为人类的导师,他们,也只有他们,能够就人民的义务以及善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来启蒙人民。
为了履行此种职能,苏格拉底式的智慧需要全部的理论科学作为其基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乃是理论科学的鹄的和王冠。
理论科学并非本来就要服务于德性,因此是不好的,要使它变好,就必须使它能够服务于德性。
然而,只有它的研究仍旧还是那些天生就注定了要指引人们的极少数人的领地,它才能变好;只有某种秘而不传的科学才能变好。
这并不是否认说,在那些腐化的时代,对科学普及化的限制可以而且必须放松。
如果卢梭的最高标准乃是有德性的公民而非“自然人”的话,这种解决方法就可以看作是一劳永逸的了。
然而在他看来,哲学家在某些方面比之有德性的公民更接近于自然人。
我们在此处只需提到哲学家与自然人所共同享有的“懒惰”。
卢梭以自然的名义,不仅对哲学提出了质疑,而且也对城邦和德性提出了质疑。
他之所以不得不如此行事,是因为他那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最终是以理论科学,或者不如说是以某种特殊的理论科学也即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
要理解卢梭的理论原则,我们必须转向他的《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和当今大多数研究者的倾向相反,他一直认为这部著作“有着头等的重要性”。
他声称,在这部著作中他将自己的原则“完整地”发挥出来了,或者说,《论不平等》乃是他“最直截了当、勇敢无畏地”表达了他的原则的著述。
《论不平等》的确是卢梭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其中包含了他根本的反思。
尤其是,《社会契约论》是在《论不平等》所铺垫好的基础上展开的。
《论不平等》确实是一个“哲学家”的著作。
道德在那里,不是被当作一个未经质疑的或者无可质疑的预设,而是被当作一个对象或者一个问题来加以考虑的。
《论不平等》旨在成为一部人类的“历史”。
那部历史是以卢克莱修在他的诗篇的第五卷中所叙述的人类命运为样板的。
但是,卢梭将那一叙述从其伊璧鸠鲁派的背景中提取出来,将其置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之中。
卢克莱修描述人类的命运是为了表明,不求助于神明的活动,人类的命运也完全能够得到理解。
就他不得不谈到的那些病症的救治之方而论,他是从哲学从政治生活中的退隐来寻求它们的。
另一方面,卢梭讲述人类的故事,是为了发现与自然权利相吻合的那种政治秩序。
而且,至少在开始时,他追随的是笛卡儿而非伊璧鸠鲁:
他认定动物乃是机器,而人超越了一般的机械或者说是(机械的)必然性的方面,只是因为他的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
笛卡儿将“伊璧鸠鲁派的”宇宙论整合到了一种有神论的框架之中:
上帝创造了物质,确立了物质运动的规律,除了人的理性的灵魂之外,宇宙乃是经由纯粹的机械过程而产生的;理性的灵魂需要特殊的创造方法,因为思想不能够被看作是对于被动的物质进行修正而产生的;理性乃是人有异于禽兽的特殊之处。
卢梭不仅质疑了物质的创造,而且也同样质疑了传统上对于人的定义。
他接受了禽兽乃是机器的观点,认为人类和禽兽之间在知性(understanding)上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或者说机械的规律就可以解释观念的形成。
不能从物质角度加以解释的,是人进行选择的能力和他对于此种自由的意识,而这就证明了他的灵魂的精神性。
“构成了人之作为自由行动者的特质而使他区别于动物的,并不在于知性”。
然而,无论卢梭对这一点如何地深信不疑,《论不平等》中的论证并不是基于意志自由乃是人的本质的这个假定的,或者,说得更宽泛一些,它并不是基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
卢梭继续说,上述对于人的定义会引起纷争,因此他要用“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来代替“自由”;没有人能够否认人是以可完善性区别于禽兽这一事实的。
卢梭想要将他的学说置于不败之地;他不想让它依赖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那是要遇到“无法化解的反对意见”、“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或者“无法克服的困难”的。
《论不平等》的论点既要能让唯物主义者接受,又要能让别的人接受。
它要在唯物主义与反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或“科学”——今天意义上的科学。
《论不平等》中的“自然的(physical)”研究就等于是对于自然权利的基础从而也就是道德的基础的研究;“自然的”的研究旨在揭示自然状态的确切性质。
在卢梭看来,要确立自然权利就必须返回自然状态,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接受了霍布斯的前提。
他摈弃了古代哲学家们的自然权利学说,认为“霍布斯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所有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定义的缺陷”。
“现代人”或者“我们的法学家们”(有别于“罗马的法学家们”,也即乌尔比安)错误地以为,人本于自然就能够充分地运用他的理性,也即人作为人是服从于自然法的不折不扣的义务的。
卢梭所谓的“自然权利的现代定义”,显然指的是在当时的学术思想中还占据着支配地位的传统定义。
因此,他赞同霍布斯对于传统自然法学说的攻击:
自然法的根基必定在于先于理性的原则之中,也即在于不见得就一定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之中。
他还进而赞同霍布斯在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找到了自然法的原则,那一原则就包含了每一个人作为何者为其自我保全的恰当手段的唯一裁判者的权利。
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此种观点预先就假定,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乃是“离群索居”的,也就是说,其特征不仅是社会的阙如,而且还是社会性的阙如。
卢梭以“较不完满、然而可能更加有用的准则‘利己不损人’……”来取代了“理性的正义的崇高准则‘待人如欲人之待己’”,他以此表达了他对于霍布斯对自然法学说的变革忠诚不贰。
他与霍布斯同样严肃地通过考察“人类的实然状况”而非他们的应然状况,来寻找正义的基础。
并且他接受了霍布斯之把德性简约为社会的德性。
卢梭之所以脱离霍布斯,与他脱离所有以前的政治哲学家是出于相同的两个理由。
首先,“审查过社会的基础的哲学家们,全都感觉到了回到自然状态的必要性,然而没有任何人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所有人都是描绘了一个文明人,然后号称是描绘了一个自然人或者说是自然状态中的人。
卢梭的先驱者们试图以观察人的现状来确立起自然人的特征。
一旦假定了人本于自然就是社会性的,这种程序就有了合理性。
一经作出了这种假定,我们就可以通过将习俗的等同于明显由习俗所建立者,从而在自然的与实在的或习俗的之间作出划分。
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将至少是所有那些独立于社会裁可而产生的情感视作是自然的。
然而,一旦和霍布斯一样否认了人有天生的社会性,我们就必定认为,有可能我们所观察到的人心中所出现的多种情感是习俗性的,只要它们是在社会、从而是在习俗的曲折和间接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卢梭偏离了霍布斯,是因为他接受了霍布斯的前提;霍布斯极其前后不一,因为他一方面否认人天生有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参照他对于人的阅历(那是对于社会中人的阅历)来确定自然人的特征。
通过思考霍布斯对于传统观点的批判,卢梭直接面对着困扰了当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难题:
并不是对于人们关于人的阅历的反思,而只是某种特殊的“科学”程序似乎才能够给人们带来有关人性的真知。
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的反思与霍布斯的反思相比照,具有着“自然的”研究的特色。
霍布斯把自然人视同为野蛮人。
卢梭常常接受他的这种看法,并且由此广泛地运用了当时的人类学文献。
然而他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在其原理上是独立于这类知识的,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野蛮人是已经被社会所塑造了的,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人了。
他还提出了一些实验方法,可能会有助于人们了解自然人的秉性。
但是这些实验完全是将来的事情,不能成为他学说的基础。
他运用的方法是“思索人类心灵中最初的和最单纯的运作”;那些以社会为前提的精神活动,不可能属于人类的自然构成,因为人天然地乃是离群索居的。
卢梭之所以偏离霍布斯的第二个原由可以表述如下。
霍布斯曾经教导说,自然权利必定要植根于情感中才会切实生效。
另一方面,他又显然是以传统的方式来看待自然法(规定了人们的自然义务的准则)的,将其视作理性的诫命;并把它们说成是“由定理推出的结论”。
卢梭得出的结论是:
既然霍布斯对于传统观点的批判是健全合理的,那么,人们就必定要对霍布斯的自然法观念产生疑问:
不仅自然权利,而且自然法或人的自然义务或人的社会德性都必定植根于情感之中;它们就必定有着比之推理或盘算更加强有力的支柱。
依据自然,自然法“必定直接道出自然之声”;它一定是先于理性的,是由“自然情操”或情感所驱策的。
卢梭以人天性善良的论断,总结了他对于自然人的研究所得到的结果。
这个结果可以理解为是从霍布斯的前提出发、对霍布斯的学说进行批判而产生的成果。
卢梭是这样论证的:
人的天性是非社会的,正如霍布斯所坦言的。
但是骄傲心或amour-propre[虚荣心]为社会的出现做了铺垫。
于是自然人不可能是骄傲的或者虚荣的,而霍布斯却辩称自然人乃是如此这般的。
然而正如霍布斯也辩称的,骄傲或虚荣乃是万恶之源。
因而,自然人于种种邪恶毫不沾染。
自然人被自爱心或者说对于自我保全的关切所支配着;因此他就会伤害他人,只要他认为这能够使他保全自己;然而,他也不会为着伤害他人而伤害他人,而如果他是骄傲的或虚荣的,那他是有可能如此行事的。
此外,骄傲心和同情心是不相容的;就我们关切着自己的声誉而论,我们对于别人的受苦受难是无动于衷的。
文雅或习俗的增进,伴随着同情心的减弱。
卢梭认为,自然人是充满同情心的:
倘若自我保全的本能的强大推动力没有为同情心所缓解的话,在任何习俗性的限制出现之先,人类是无法生存下来的。
他似乎认为,保全物种的本能愿望分成两个部分:
生殖的愿望和同情心。
同情心乃是一切社会德性都由之而来的那种情感。
他的结论是,人天性善良,因为他天生是被自爱心和同情心所支配,而与虚荣心和骄傲心无缘。
出于与自然人缺乏骄傲心的同样的理由,他也缺少理智或理性,并且从而就没有自由可言。
理性与语言相伴而生,而语言又是社会出现的前提:
在社会之先,自然人是在理性之先的。
卢梭在这里再次得出了由霍布斯的前提出发而霍布斯并没有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
具有理性就意味着具有一般观念。
然而,有别于记忆的形象或想象的一般观念,并非某个自然过程或者无意识的过程的产物;它们是以定义为前提的;它们有赖于定义而存在。
因此,语言乃是它们存在的先决条件。
既然语言不是自然的,理性也就不是自然的。
由此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卢梭为什么要以一种新的定义来取代传统之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再就是,既然自然人是先于理性的,他就完全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关自然法(也即理性的法则)的知识,尽管“他[依据]理性赋予了自己以对于他所需之物的权利”。
就每一方面而论,自然人都是先于道德的:
他全无心肝。
自然人乃是次人(subhuman)。
卢梭关于人天性善良的论旨必须借助于他关于人天生乃是次人的观点来加以理解。
人天性善良,乃是因为他天生就是既可为善又可为恶的次人。
对人来说,没有什么自然的构成可言:
一切专属人类的东西都是由人为或习俗而获得的,或者说最终是依赖于人为或习俗的。
人本于自然几乎是可以无穷地完善的。
对于人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进步而言,或者说对于他使自己从邪恶中解放出来的能力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障碍。
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人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堕落而言,也不存在什么自然的障碍。
人本于自然有着几乎是无穷的可塑性。
用芮那尔神父(Abb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