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视野下中西艺术形式与思维范式的阐释与比较.docx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中西艺术形式与思维范式的阐释与比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审美人类学视野下中西艺术形式与思维范式的阐释与比较.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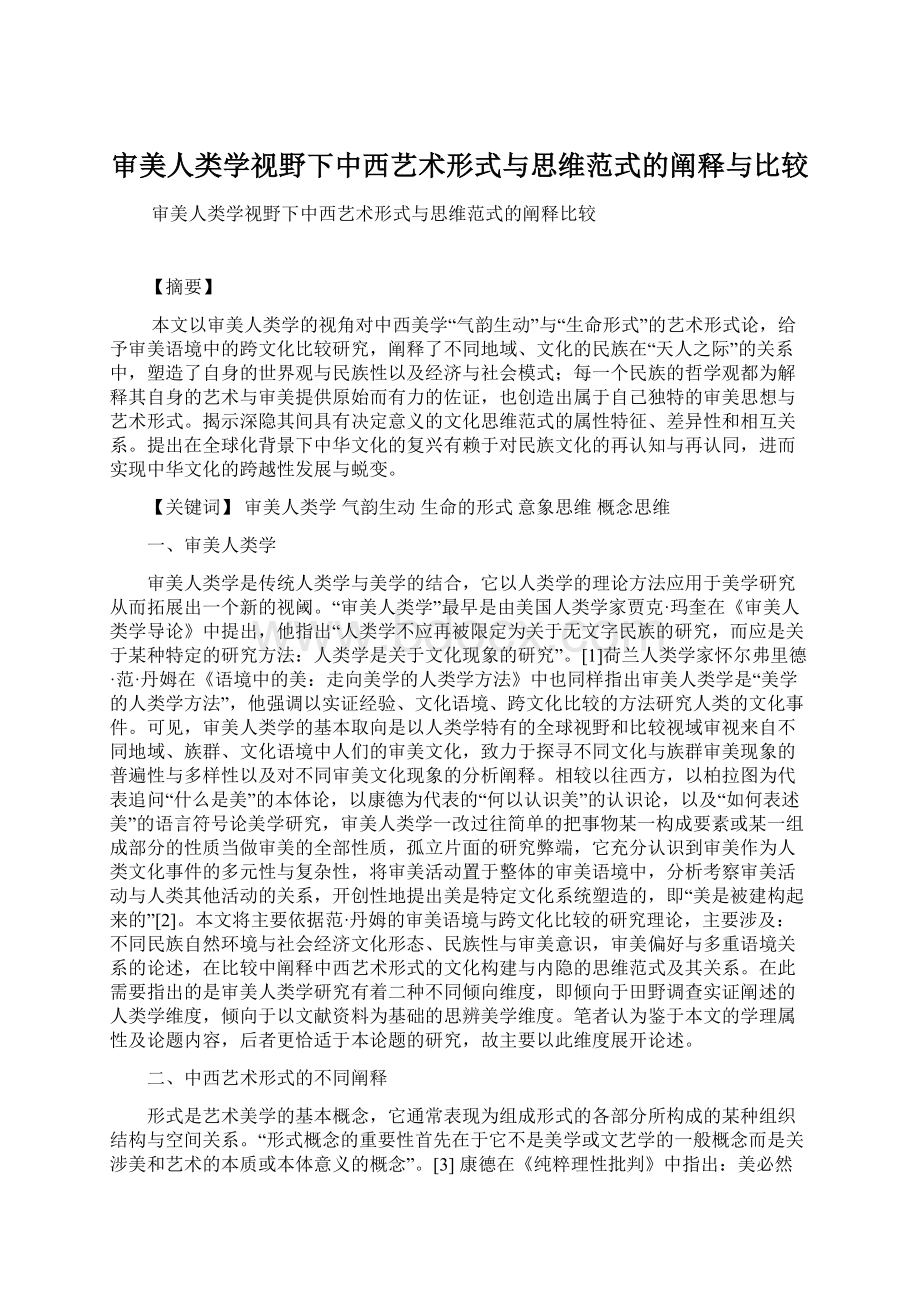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中西艺术形式与思维范式的阐释与比较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中西艺术形式与思维范式的阐释比较
【摘要】
本文以审美人类学的视角对中西美学“气韵生动”与“生命形式”的艺术形式论,给予审美语境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阐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民族在“天人之际”的关系中,塑造了自身的世界观与民族性以及经济与社会模式;每一个民族的哲学观都为解释其自身的艺术与审美提供原始而有力的佐证,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与艺术形式。
揭示深隐其间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思维范式的属性特征、差异性和相互关系。
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复兴有赖于对民族文化的再认知与再认同,进而实现中华文化的跨越性发展与蜕变。
【关键词】审美人类学气韵生动生命的形式意象思维概念思维
一、审美人类学
审美人类学是传统人类学与美学的结合,它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美学研究从而拓展出一个新的视阈。
“审美人类学”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贾克·玛奎在《审美人类学导论》中提出,他指出“人类学不应再被限定为关于无文字民族的研究,而应是关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是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
[1]荷兰人类学家怀尔弗里德·范·丹姆在《语境中的美:
走向美学的人类学方法》中也同样指出审美人类学是“美学的人类学方法”,他强调以实证经验、文化语境、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研究人类的文化事件。
可见,审美人类学的基本取向是以人类学特有的全球视野和比较视域审视来自不同地域、族群、文化语境中人们的审美文化,致力于探寻不同文化与族群审美现象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以及对不同审美文化现象的分析阐释。
相较以往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追问“什么是美”的本体论,以康德为代表的“何以认识美”的认识论,以及“如何表述美”的语言符号论美学研究,审美人类学一改过往简单的把事物某一构成要素或某一组成部分的性质当做审美的全部性质,孤立片面的研究弊端,它充分认识到审美作为人类文化事件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将审美活动置于整体的审美语境中,分析考察审美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开创性地提出美是特定文化系统塑造的,即“美是被建构起来的”[2]。
本文将主要依据范·丹姆的审美语境与跨文化比较的研究理论,主要涉及:
不同民族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形态、民族性与审美意识,审美偏好与多重语境关系的论述,在比较中阐释中西艺术形式的文化构建与内隐的思维范式及其关系。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审美人类学研究有着二种不同倾向维度,即倾向于田野调查实证阐述的人类学维度,倾向于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思辨美学维度。
笔者认为鉴于本文的学理属性及论题内容,后者更恰适于本论题的研究,故主要以此维度展开论述。
二、中西艺术形式的不同阐释
形式是艺术美学的基本概念,它通常表现为组成形式的各部分所构成的某种组织结构与空间关系。
“形式概念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不是美学或文艺学的一般概念而是关涉美和艺术的本质或本体意义的概念”。
[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
美必然涉及对形式的意识,审美是一种被赋予了形式的情绪体验状态。
美产生于一种想象力结合悟性能够自由活动于其中的可把握的合规律的形式。
尽管不同的美学理论对于艺术美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形式始终与美密切相关并成为具有本体意义的核心问题。
人类艺术审美的差异是不同文化模式与审美表达系统差异的显现。
当我们以审美人类学全球的视野来审视人类的审美文化活动时较为突出的现象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美学理论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美学思想彼此并立又迥然相异。
在二者诸多差异性中对于艺术形式的不同阐释又成为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东方美学思想对于美的形式给予一种“气韵生动”的诗性言说,而西方美学理论却提出“生命的形式”的理性论断。
任何一种伟大的美学思想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哲学母体中,审美人类学认为:
不同地域、族群所构建的不同文化,在根本上取决于他们各自对世界本初的认知假设与认知方式的不同与表达,即源自不同的哲学思想。
这似乎应和了普罗泰戈拉著名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尽管这一论断有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它却客观的表述了人类文明中的现象。
东方“气韵生动”的诗性言说。
“气韵生动”出自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并居“六法”之首。
此说提出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广泛的应用于艺术领域,成为中国艺术美学思想中最持久、最富内涵与民族特色的美学命题,被称为“千载不易”、“万古不移”(宋郭若虚)。
“气韵生动”说蕴涵着博大精深的美学意蕴闪耀着古老东方美学智慧的光芒,可以说不把握“气韵生动”的精神实质就无法把握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
“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最为核心与本原性的哲学范畴。
老子的“道生一”,“道”是虚空本体的无,即“有生于无”。
“一”乃天地阴阳未分之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一气氤氲化转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合化生万物。
《易传·系辞》曰:
“精气为物,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
宋儒张载也说:
万物之源为太虚之气,“大虚无行,气之本体”(《正蒙·太和篇》)。
由此,万物皆由气化生并以气互通。
“气”以一种空无一物而又涵盖万有的形态弥漫在宇宙虚空之中,充斥于实在形体之内,“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
这种“气论”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后历经数次转化,先是由先秦时期的“元气”本体论进入魏晋时期“神”的主体精神品藻,开始进入艺术审美领域;后成熟于汉唐,并在历代发展中成为美的本质和艺术生命的根源。
“气”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美学以“气”为特色以“气”为统一,“气”贯穿于中国美学思想的全部。
[4]综合来讲,“气”在中国文化里基本包涵了三个层面:
“气”不仅是化生万物的本原与生命,而且也是“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构成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整体,更为重要的是“气”构成了以“气韵生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核心内涵。
“韵”也是极具中国特色与普适性的美学概念。
“韵”最早使用于音乐领域,指和谐的声音。
刘勰《文心雕龙·声伴篇》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韵”指世间最美妙的和声。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论韵说:
“有余意之谓韵,韵生于有余”(范温《潜溪诗眼·论韵》)他将“韵”理解为“余意”、“余味”的音乐性余韵。
“韵”在中国美学思想中也呈现出二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蕴涵审美形式之韵的“体韵”、“雅韵”,一是蕴涵审美内容之韵“神韵”、“精韵”,前者侧重艺术形式的和谐优雅后者侧重内容的精神与情感共鸣。
[5]“韵”是与“气”紧密相关的,“韵”以“气”为基础,音之生必依于声,韵之生必依于气,气与韵是密不可分。
“气”阴阳运动化转的二元属性,为其成为艺术形式提供了可能与广阔的空间。
“气”隐喻着阳刚之美,“韵”则内涵阴柔之谐,正所谓阴阳相济。
“气”与“韵”合而为“气韵”代表了两种极致美的对立统一。
徐复观先生指出:
“气”概括了天人的本质,“韵”统辖物我的呈现。
他还从“形”与“神”的关系论述将“气韵”与中国美学“传神”说联系起来,提出“气韵”即“传神”。
[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世界本原的“气”不仅关乎存在而且指向发展,“气”的根本属性在于运动,而内涵丰富的“韵”则是“气”运动的状态属性,也即为一种“生”,这种“生”的运动绝非毫无章法的乱动,而是一种动态系统的有节奏、有韵味的律动、即为“韵”,“韵”的本质正是艺术形式的生命节奏。
“生”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具有着本体意义与民族特质。
《周易》中“生”即为核心范畴,“天地之大德曰生”阐释了宇宙万物永远处在“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流变中。
张岱年先生认为“生”是创生、生灵、生存、运动生变与发展[7]。
这样“生”就不仅是形而下的变化发展的生命创造,而且是形而上的创生之道—“生生谓之易”。
中国古代这样一种对宇宙“生”的运动生成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生成论中似乎也有着某种呼应,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质料因在形式因的动力推动下向着更高的形式动态生成,质料因的潜能向着目的因发展,质料因与形式因就构成相对运动的、有机的生态世界。
古代中国人不仅将宇宙视为“生生”的世界,而且还通过“生”的观念给予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一种生命的理解并进而构建起一个大化流行的生命宇宙统一体。
“生动”是由“气”的运动变化引起的,“生动”与“气”是不可分的。
王充《论衡·自然篇》中指出:
“天之动,行也,施气也。
体动,气乃出,物尔生矣”。
简言之,“生动”就是万物生命运动的节奏韵律的丰富变化状态。
综上所述,“气韵生动”艺术形式说是有着深厚中国哲学思想基础的,它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宇宙生命意识与美学思想,“气韵生动”的核心要义是“气的美学本体”和“韵的艺术呈现”的完美结合也是艺术形式的完美显现。
西方“生命形式”的理性论断。
探究世界本原始终是古希腊哲学重要的论题,由此而阐发的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也必然影响着他们对于美的形式的认知。
古希腊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很早就关注存在于具体事物背后抽象的数,探究以数为中心,以形为内容的数理关系,他们认为美的形式在于比例协调,并确立了“黄金分割律”。
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源,在自然界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
”[8]从而开启了西方美学以理性的“数”与空间性的“形”为特征的艺术形式的逻辑起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几乎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周易》成书的大致年代。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形”美学与《周易》的“象、数、形”三元时空互渗的“象形美学”有着某种契合之处,二者都有着相似的“数”的理论起点,却又分别沿着完全不同方向发展演进。
柏拉图致力于寻求万物流变背后永恒不变的“理念”也就是他说的“美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美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四因说”理论,阐释了形式对于判断一个美的事物尤为重要,“事物常凭其形式取名,而不凭其物质质料取名。
”[9]因此,亚里士多德将美的形式确立为秩序、匀称与和谐。
古罗马晚期普洛丁将柏拉图的“理念”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建立新柏拉图主义,他以上帝创造世界的顺序划分美的等级,将美的形式确立为分享上帝赋予的理性光辉。
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创始人康德基于其“先验形式”论,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美是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的著名论断,其先验形式美学是西方美学史承前启后的理论创造。
黑格尔则纠正了康德过分强调审美主体的主观性,从而导致的内容与形式、物质与精神的分离对峙。
他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10]这样直至十九、二十世纪西方的现象美学、接受美学、格式塔美学等学派在对艺术形式与审美经验的研究中强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
总的来讲,在西方悠久的艺术形式研究中,大致经历了由形而上的对艺术形式本质的追问到形而下的对艺术形式审美体验的探究,由传统的自然本体论、理性本体论向生命本体论的转向。
在这个西方美学发展历程中洞悉艺术形式与生命关联的先贤大哲有着诸多著名的论述,歌德说美的形式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11]康德说“精神(灵魂)在审美的意义里就是那心意付于对象以生命的原理”[12];黑格尔指出“是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式的意蕴”[13];利普斯认为是“生命的扩展和丰富,是主体的‘生命灌注’与‘人格化的观照’”。
十九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反对理性主义“霸权”,弘扬人的主体性,反思生命与存在的思潮,尤其是以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的发展,他们系统的将艺术创造与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将艺术视为一种生命的活动,创立了以生命为原点的美学形式论。
其中生命哲学代表人物柏格森认为艺术形式就是“生命的绵延和生命冲动的自觉形式”。
二十世纪美学家符号学家苏珊·朗格在汲取生命哲学并结合卡西尔文化符号学和克莱夫·贝尔形式主义美学的“有意味的形式”等相关理论,从符号美学的视角提出了艺术即“生命的形式”的理论。
她认为艺术形式“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者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
[14]艺术形式与生命、情感之间存在着逻辑意义上的同构性,艺术形式本身就是对主体生命形式的一种表现,“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
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理论是西方形式美学的一座理论高峰。
三、中西艺术形式不同阐释的审美人类学分析
当我们审视中西美学对艺术形式迥然相异的阐述时,不禁会问产生这种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和跨文化比较的视域,对不同文化语境中审美事件的探究,其本质仍是对于人的研究。
依据卡西尔文化哲学理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切文化都是符号形式,人类一切的文化活动都是人类精神寻求客观化的自我赋形的方式,即符号化的产物。
诚如格尔兹所言“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5]。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封闭性社会”文化模式认为:
某一部族、社群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内生存即会产生相对原生独立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元素使得这一部族社群的全体成员形成了某种共通性的对待事物的认知思维与行为方式,它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无可避免地发挥着主导作用。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也阐释了相同的观点,“任何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都存在着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它包含着一套构成认识的基本假定和概念,并预先决定了人们所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和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16]人类的审美形式与体验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有着不同的意味,这是认知主体与客体在特定的“情景遇合中的产物”。
审美人类学认为对于不同地域、族群与文化模式中不同的文化符号的理解与阐发,正是基于不同族群对于世界本初基本认知的不同假设以及认知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而这种不同的认知假设又集中体现在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也就是文化还原最根本的结构关系是天人之际。
由于不同地域与族群所假设与建构的文化符号不同,就决定了他们的思维范式与行为模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在审美意识与趣味的相异。
然而,当我们层层剥去中西美学思想诸多差异的表象,深入探究中西艺术形式的深层内核,会发现是其各自文化体系中最幽深根本的内核,并具有某种先验性的基本认知假设与思维方式。
具体说来就是,由于中西文化在各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因而各自独立构建起不同的宇宙观,加之迥异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与各自民族性的制约等诸多因素便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明显差异性。
这就如同荣格分析心理学阐述的“原型”概念。
“原型”是指最初的模式,即一个民族原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具有无意识的社会性。
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世界的某些方面做出认知与反应的最初的模式与先天的倾向,也就是原初的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型。
李泽厚先生称之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它具体涵盖:
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
他认为“这个文化心理结构作为形式,是超越任何个体存在的,但正是它给予整体游戏者(个体)以游戏的规则”。
[17]正是这种“原型”或“游戏规则”的差异性,直接导致了中西文化在一开始的哲学宇宙观的差异,表现在艺术与审美上则呈现出中西美学思想的不同、审美关注和趣味的各异,以及极为重要的对于美的认知与思维范式的差异。
“意象思维”与艺术审美
审美人类学将上述差异视为人类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与心理事件,这样就逻辑的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拓朴心理学创始人库尔特·勒温在研究人类审美活动时所提出的问题:
情景—反应(S—R)。
即“为什么一定情景S(Situation)中特定的个体P(Personality)处在特定的环境E(Environment)中产生事件B(Behavior)产生了结果R(Result),而不是其他事件结果?
为什么恰恰出现这种情景?
”。
[18]以审美人类学的视域置言之,就是为什么一定情景S会导致产生这样的审美认知R,而不是其他的。
勒温在心理学研究中引入了“情景”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与审美人类学所强调的“审美语境”相契合,这种“审美语境”或“情景”是探究特定族群审美意识形成极为重要的因素。
“审美人类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考察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是如何‘看’世界”的。
[19]人类天然的面对着一个充满奇幻变化令人惊异的大自然,人作为大自然界的一部分探究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也必然成为东西方美学的首要问题。
在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论题上,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通过丰富的史料论述了:
人类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相互作用。
此外,汤因比在其著名的《历史研究》从人与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中,也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于属地文明与民族性格的塑造与影响。
然而,对此最富影响的理论出自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他认为决定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是多元的,如:
政治、经济、自然、宗教等因素,其中他尤为强调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乃至决定作用。
他在《论法的精神》中通过大量篇章论证了包括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因素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情感、宗教、道德风俗乃至国家政体、经济结构都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尽管这一理论提出后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比如无法解释同为海洋地域环境的英国、日本却有着绝然相异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发展。
但是,当我们追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审美意识的源起时,先民对自然认知的假设以及由此而内生的思维模式,必然是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所派生的经济生产模式与社会结构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时期这种作用通常是决定性,同样自然地理环境也会极大地影响着人类对于宇宙与生命的感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与体验。
自然崇拜在人类古代文明中是一种普遍的跨文化现象,它源于人类共同的自然崇拜心理,但是不同地域、族群的自然崇拜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这样的亲和关系,人与自然的亲和性是中国文化性格的重要特征”。
[20]华夏民族自古就生活在东有浩瀚大海、西有茫茫戈壁、西南有青藏高原、北有广袤草原,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但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发祥地的地理环境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在相对独立于世界之外较为封闭的自然地域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原生的中国文化体系,创立了高深玄妙、意境极致的中国艺术美学。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流域,暖温带的气候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使先民定居于此并开展农耕生产奠定了“农耕立国”的根基。
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的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中,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耕社会结构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内敛内向、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
土地是农耕经济财富的根本基础,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得中国人子子孙孙依附耕耘于这块世代相传的土地上,逐渐建立起以孔子“正名”为宗旨的复杂而有序的家族制度与伦理规范,这种组织严密的家族制度伦理规范又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组织结构,建构起“家天下”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伦理体制。
超稳定的家族体制与生产的往复性以及“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经济特性,建构起华夏先民与自然的亲和依附关系,形成了民族原初的哲学宇宙观,即“天”的观念。
“天”在中国文化中是具有核心地位的思想范畴。
在中国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天与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周而复始的农耕收获被看做是“天”的赐予,所以道家把“天”(自然)称为“造化”,天的一切神奇变幻都是对于人的助益或惩罚。
因此,人因恩赐而膜拜。
“天”是人的主宰,而作为自然的“天”其昼夜交替、斗转星移是有着自身的规则,即“天道”,体现为“反者道之动”。
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天”与“道”是紧密相关,道家的理论就是承继了朴素“天”的观念并进一步哲学化、精致化、人文化从而上升至“道”的宇宙本体高度。
所以,作为人要“敬天”、“奉天行道”也就是道家的宗义。
“天道”不仅是“天”运行的规则,也普遍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洞悉人与社会也必须遵循从“天”到“人”的根本路径,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天人的哲学思想在汉儒董仲舒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被系统地阐释为“天人感应”。
他认为:
“人”是“天”的副本,“天”与“人”之间存在相感相动的关系。
“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这样就将四时更替、宇宙天象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
“明天理”、“通天道”进而“知人事”就成为了华夏民族文明发展的文化原点,围绕着“通天”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文化样态。
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就记载了尧派羲和氏观天制历以明察天意。
“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时”。
《易传》中有:
“天垂象,见凶吉,圣人则之”等大量“通天”的表述。
有趣的是,中国人崇尚的“天”与“天道”在行使功能的方式上不象西方的神以神谕的方式直接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为,而是以一种“不言”的“天兆象”,“以象示人”的隐喻含蓄的方式表达。
那么中国人又该如何感应这隐喻含蓄的“天象”体悟“天道”呢?
首先,汉字“象”原指视觉感知的大象,后演变到知觉层面的形象、卦象以及动词的象征、效法;在演进中主观意想与心理的成分逐渐增强,至先秦哲学中“象”已具备本体化的意义,成为与“道”相近的“原象”。
也就是“象”成为“道”的中介与替身,“象”作为不可见也无法显现“道”的可见物,它并非现实世界中的实象,却又以可感知的形象来传达可推想的信息,一种超验对象的象征性表达。
被儒家尊为“大道之源”,道家奉为“三玄”之首的《周易》就是一部以卦爻象示人通天以悟道的“天书”。
《周易》作为一部探究天地之道预测占筮之书,它是由卦辞与爻辞所营造的“象”示人,“象”是《周易》的核心。
卦爻之象旨在预测天意推演人事,我们在卦辞、爻辞、意象之间表面看似互不关联的事物中却有着基于“生”的宇宙大生命体的内在关联性,这种互动关联是非逻辑的。
卦、爻的组织与转化所呈现的“象”体现的是天地之道,“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
老子对“象”是有着精辟阐述“惟恍惟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这种“恍兮惚兮”之“象”是直观可感之象,是动态变幻不可分割的整体之“象”。
“象者疑于有物而非物也”(吕惠卿《道德真经传》),“象”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用概念的规定性加以把握。
而以“象”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特有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诸多典籍中通常是运用简短的寓言、故事、比喻、警句生动形象化的借喻暗示,这种以“象”暗示哲学思想相较于西方哲学必然是不够明晰的,因为它所表示的不是一个演绎推理中的概念,但正是这种“象”语言所特有的模糊性、虚拟性和暗示性,所以它所寓意与暗示的内涵可以是无限的,同时它又是直观可视的能够为人所把握的。
应该说“象”的流变“恍惚”、“窈冥”似有若无的特征本身就极具艺术审美的蕴涵,实际上《周易》对于中国艺术美学也同样具有着决定性意义。
刘纲纪先生在《<周易>美学》中指出:
《周易》有关“太极”、“天文”、“象”的理论在两千多年前就为中国美学阐明艺术发生与本质的理论依据,《周易》有关象、阴阳、刚柔、开合、变化、神等论述,为中国美学探索艺术形式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21]其中尤以“象”的论述更是影响深远。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在绘画书法上,王微在《叙画》中说“图画非止艺行,诚当与易象同体”;张怀灌在《书断》中指出象为“文字之祖,万物之根”,备受中国艺术美学推崇极富特色的“意境”论也是基于“象”的营造,由此可见“象”对于中国艺术美学的生成发展的重要影响。
由《周易》卦辞与爻辞构成的蕴含审美意味的“象”,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美学的另一重要命题:
“言、象、意”。
王弼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故立象以尽意”,(《周易略例·明象》)。
“立象以尽意”阐明了“言”之根本在于“明象”,“象”之根本在于“得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
对此庄子也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
这些都阐释了作为“得意”的中介“言”本身的局限性,而“立象”则是“尽意”的最佳途径与手段。
那么如何“立象以尽意”呢?
《易传》对于“象”的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