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docx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docx(3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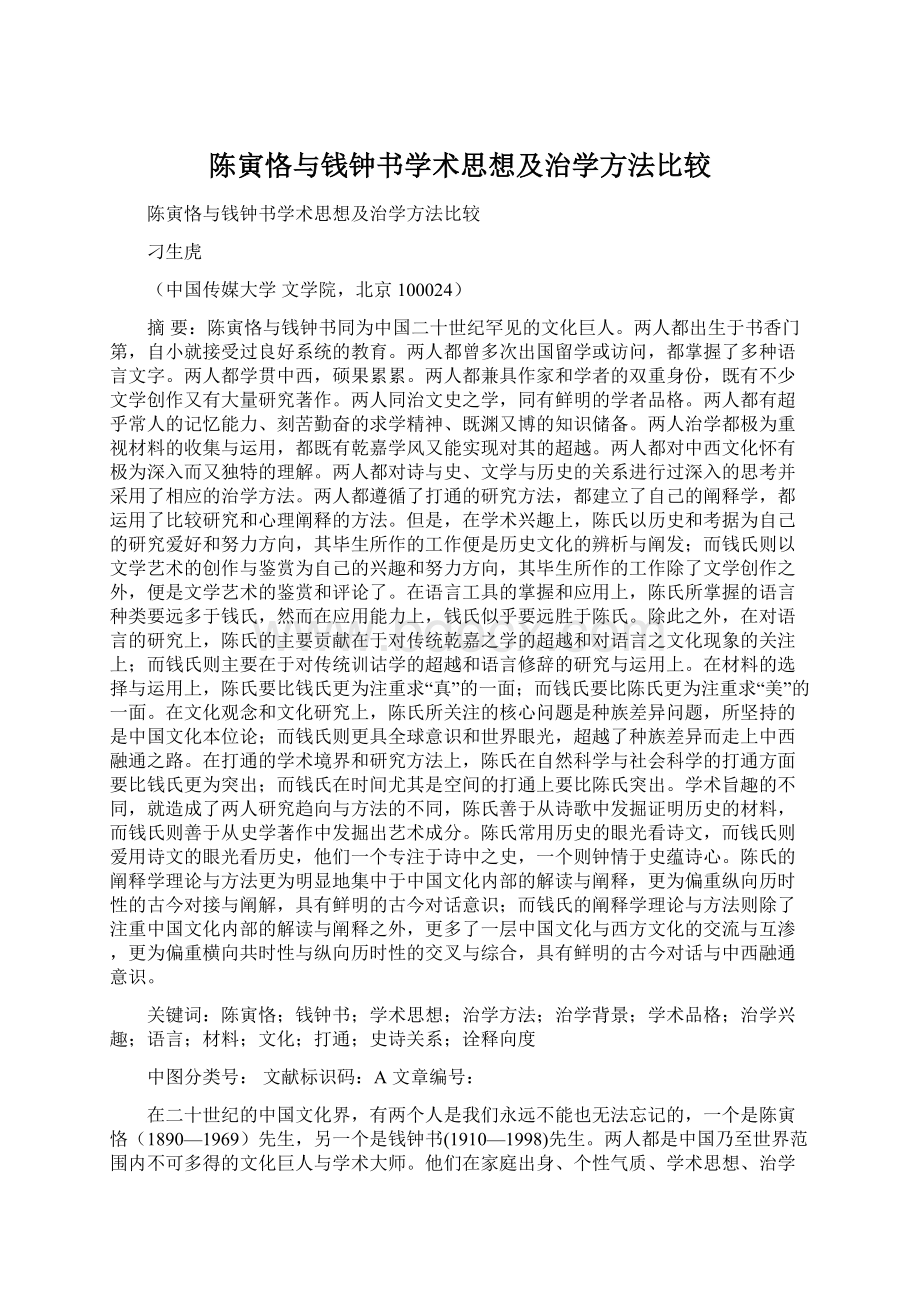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
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文化巨人。
两人都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就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
两人都曾多次出国留学或访问,都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
两人都学贯中西,硕果累累。
两人都兼具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既有不少文学创作又有大量研究著作。
两人同治文史之学,同有鲜明的学者品格。
两人都有超乎常人的记忆能力、刻苦勤奋的求学精神、既渊又博的知识储备。
两人治学都极为重视材料的收集与运用,都既有乾嘉学风又能实现对其的超越。
两人都对中西文化怀有极为深入而又独特的理解。
两人都对诗与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采用了相应的治学方法。
两人都遵循了打通的研究方法,都建立了自己的阐释学,都运用了比较研究和心理阐释的方法。
但是,在学术兴趣上,陈氏以历史和考据为自己的研究爱好和努力方向,其毕生所作的工作便是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而钱氏则以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为自己的兴趣和努力方向,其毕生所作的工作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便是文学艺术的鉴赏和评论了。
在语言工具的掌握和应用上,陈氏所掌握的语言种类要远多于钱氏,然而在应用能力上,钱氏似乎要远胜于陈氏。
除此之外,在对语言的研究上,陈氏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传统乾嘉之学的超越和对语言之文化现象的关注上;而钱氏则主要在于对传统训诂学的超越和语言修辞的研究与运用上。
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陈氏要比钱氏更为注重求“真”的一面;而钱氏要比陈氏更为注重求“美”的一面。
在文化观念和文化研究上,陈氏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种族差异问题,所坚持的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而钱氏则更具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超越了种族差异而走上中西融通之路。
在打通的学术境界和研究方法上,陈氏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打通方面要比钱氏更为突出;而钱氏在时间尤其是空间的打通上要比陈氏突出。
学术旨趣的不同,就造成了两人研究趋向与方法的不同,陈氏善于从诗歌中发掘证明历史的材料,而钱氏则善于从史学著作中发掘出艺术成分。
陈氏常用历史的眼光看诗文,而钱氏则爱用诗文的眼光看历史,他们一个专注于诗中之史,一个则钟情于史蕴诗心。
陈氏的阐释学理论与方法更为明显地集中于中国文化内部的解读与阐释,更为偏重纵向历时性的古今对接与阐解,具有鲜明的古今对话意识;而钱氏的阐释学理论与方法则除了注重中国文化内部的解读与阐释之外,更多了一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渗,更为偏重横向共时性与纵向历时性的交叉与综合,具有鲜明的古今对话与中西融通意识。
关键词:
陈寅恪;钱钟书;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治学背景;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材料;文化;打通;史诗关系;诠释向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有两个人是我们永远不能也无法忘记的,一个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另一个是钱钟书(1910—1998)先生。
两人都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与学术大师。
他们在家庭出身、个性气质、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众多领域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但所有这些,无论是同还是异,都并不影响他们各自成为垂范后世的一代宗师。
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治学背景:
家学?
天才?
勤奋
众所周知,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均在众多领域做出了常人所无法比拟的卓越贡献,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甚至具有开创性意义。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的知己吴宓就已对二人等量齐观,做出了极为崇高的评价:
“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
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1]而他们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因素,那就是,一方面都有极为深厚的家学渊源,另一方面都有先天罕见的资质禀赋和后天超人的刻苦勤奋。
这是他们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前提条件。
1.深厚的家学渊源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独特的成长经历为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外部条件。
陈寅恪巨大成就的取得即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
吴宓在《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说道:
“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讬命者也。
寅恪自谓少未勤学,盖实成于家学,源孕有自。
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
”[2]陈寅恪出生在江西“义宁陈氏”家族里。
祖上曾居福建上杭,后先祖陈腾远由闽入赣,定居江西义宁州。
自以耕读为业,逐级考取高科。
腾远之子陈克绳,同为读书之人,幼子陈伟琳少即端庄静默、勤奋好学,长更重视子女教育,“训子弟及亲戚后进,必勤勤启诱,终日不倦。
虽农夫野老亦敬而爱之,感化者众。
”[3]并曾教导幼子陈宝箴曰:
“学须豫也。
脱仕官、虚疏无以应,学又弗及,悔何追矣。
”[4]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曾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和郭嵩焘赞为“见解高出时流万万”[5]。
他领导的湖南新政真正赋予戊戌变法以实际意义,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中国最富有生机的省份。
其父陈三立(1853-1937),少年博学,才识通敏,为清末进士,曾授吏部主事,但他淡于名利,未尝一日为官,时有“维新四公子”之称。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隐庐山,作诗赋文,成为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民初诗坛泰斗,有《散原精舍诗》和《散原精舍文集》传世。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是近代著名画家,与鲁迅交谊甚厚,常与齐白石切磋画艺。
他把绘画、诗词、书法、篆刻熔于一炉,四者相得益彰。
可惜48岁便英年早逝。
被时人称之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
其侄子陈封怀(陈衡恪次子),是著名植物学家,被植物学界尊为“中国植物园之父”。
而“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始终是这个家族所遵奉的圭臬。
在这个家族的历史上,读书始终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陈宝箴曾说过:
“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
”他们崇尚文墨,于躬耕之余,勤于课读,建书屋,立义学,祖传的一袭墨香,亘古而强劲地承传着。
所有这些,都为陈寅恪日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江南钱氏家族也是一个书香门第。
钱钟书的祖父钱福炯就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秀才。
父亲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被称为江南才子,是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校教授。
钱基博先生学识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经学通志》、《版本通义》、《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多部,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专门论著与广博涉猎,曾自述治学旨趣为: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诀摘利病,发其阃奥。
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
子部钩稽,亦多匡发。
”[6](P4)他深厚的国学造诣为钱钟书后来的治学提供了良好的旧学环境。
不仅如此,钱基博治学十分严谨与勤奋。
据吴忠匡先生记载,为了撰写《中国文学史》一书,他遍读了古今诗文集数千家,写有提要者不下五百家,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大部头的总集也都通读,并对每个作家都做出评论。
[7]正因如此,钱基博先生对儿子的管教也极其严格。
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影响下,钱钟书慢慢走上了正途。
所有这些,都为其以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通人”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个人天才与勤奋要成为超越常人的学问家,光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尚远远不够。
好的家庭环境只是为个人的成功准备了外部条件,真正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个人的天分和努力程度,在成功的链条中,前者只是一个非主导的外因,而后者则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内因。
陈寅恪与钱钟书两人便在这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陈寅恪便是如此。
据俞大维先生说: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
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
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8](P6)陈寅恪在55岁后由于双目失明,只能依靠以往读过的书和请人代读一些书进行学术研究。
据陈晚年的助手黄萱称,他需要参证的,大都是些孤僻的诗文史料。
他提示黄萱,这些史料可以在某书第几卷第几页上找到。
令黄惊讶的是,十之八九不会出现差错。
面对这样一位奇才,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
作为中外文化史上罕见的天才学者,陈寅恪深厚渊博的学养和惊人的记忆力,不只一般人望尘莫及,即使在堪称一流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自知难以企及。
陈寅恪深厚渊博的学养和惊人的记忆力,是以他艰苦卓绝的读书精神和扎实不苟的治学作风为基础的。
据其幼女陈美延追忆:
“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
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9](P52)又其长女陈流求回忆说:
“从我记事起(本年流求五岁)我家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距西校门不远。
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
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
晚上照例伏案工作。
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9](P82)又据其侄子陈封雄回忆说:
“先叔在童稚之年即嗜书。
他对我说过,十岁前即开始翻阅先曾祖所藏之各种佛经,觉其怪奥难懂,但颇感兴趣,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数十年致力于研究佛教典籍的最初基础。
他在十三岁时跟随先父衡恪赴日本读中学,初步学习了第一种外国语。
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学了英文并杂览经史古籍。
由于他非凡的记忆力和求根究底的性格,他不但能背诵《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和他终生精思细考的治史态度不无关系。
”[10]而陈寅恪去世后,其家属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同仁清理遗物时,发现他留学国外期间的学习笔记,竟有六十四本之多。
所有这些,都为其成为深受海内外推重的学术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钟书更是如此。
他首先具有异乎寻常的天分。
这主要表现在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常的领悟能力。
其同学郑朝宗先生在《忆钱钟书》一文中回忆说: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论怎样艰深的书,他读起来都不怎么费力,这就可见他的悟性。
他的记性尤不可及,当他在高谈阔论时,忽然想起一句黄山谷或王荆公的诗,或者在改英语作文时,忽然想起一位古罗马作家的名言,他只伸手向书架上抽出一本有关的书,认真翻了几下,立刻便能找到原文。
世间一切给记忆力差的人准备的‘引得’之类的东西,对他似乎全无用处。
他在大学时发表的英文论文,奇字之多颇使一般教师感到难读,而他所作的旧体诗,用的典故有些连老前辈都不知出处。
”[11](P3)夏志清先生曾在《追念钱钟书》一文中写道:
“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和晚辈,还没有比得上他的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的。
”[12]吴忠匡先生在《记钱钟书》中亦云:
“中书博闻强记,凡经他浏览过的典籍,几乎过目不忘,一些名家的大集不说,某些杂记小说和小名家诗文,你只要考问他,他也能够穷源溯流,缕述出处,甚至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13](P74)而治西方哲学的张申府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
“钱默存先生乃是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现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
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14]而柯灵先生对钱钟书的学识与风范更有极为精辟的概括:
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
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
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下的警句。
渊博与睿智,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锺书了。
[15]
不仅如此,钱钟书更有超乎常人的刻苦精神。
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他便开始数十年如一日,惜时如金,嗜书如命,与书为伴,刻苦攻读,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可以说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用到了读书上。
纵观钱钟书的一生,读书与著书已化作他生命的血肉和筋骨,并支撑着他成为中华学术文化的脊梁。
钱曾自述他上大学前读过《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大部头著作,虽“绝鲜解会,而乔作娱赏”,“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16](P346),但这对一名中学生而言实属不易。
及入大学,他即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誓言。
钱的大学同学许振德先生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一文中回忆道:
“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许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钱锺书“家学渊源,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自谓‘无书不读,百家为通’。
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
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
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美哲爱迪生所谓天才乃百分之九十九之血汗及百分之一之灵感合成之语,证之钱兄而益信其不谬。
”[17](P15)而同乡族人钱穆先生也回忆说:
“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
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
”[18]等到留学欧洲期间,据杨绛先生回忆,每到夜幕降临时,大多数留学生都到酒吧去过夜生活,惟有钱钟书夫妇于灯下静静读书。
既使在后来钱钟书下放到“五、七”干校,晚上灯光暗淡,他便站在凳子上看书。
[19]钱钟书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以《管锥编》为例,该书是在钱氏五大麻袋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
据后来编过《〈管锥编〉〈谈艺录〉索引》的陆文虎先生统计,《管锥编》涉及古今中外的作者达四千人,典籍近万种。
[1](P267)正是这种“读书破万卷”的刻苦精神,才铸就了他“下笔如有神”的日后奇迹。
二、学术品格:
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与真理之勇?
文章之德
陈寅恪作为一名现代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其毕生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为王国维所撰的纪念碑铭,既是赞颂死者,更为勉励生者: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P218)
王国维究竟是否因独立自由之意志而死这一点虽然不敢断言,但这种追求定为陈寅恪个人的固有信念却是毋庸置疑的。
时过二十四年,陈寅恪在其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强调这一原则: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21](P111-112)
由此可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原则,也是其治学方法的根本基石。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临死即立下遗训:
不求功名、不治田产。
陈家一直遵照执行。
陈寅恪更是视学术文化为自己的生命,治学的目的就在治学的过程之中,从来“不籍时令”,“不假乎功名”,不受世局及外缘的影响;在学问上总是持“审慎态度”,“博考而慎取”,“有误必改,无证不从”。
陈寅恪认为,只有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拒绝把学术沦为谋取功利的手段,才可以从治学中领略真正的乐趣,也才可以发现走向真理的坦途。
昔日留学哈佛之际,其已对同辈中人群趋海外争学工程实业持有不同看法,认为技术知识虽然于国有用,但多数人心存追慕富贵的功利意识却实不足可取:
今则凡留学生,皆学二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
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冲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
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
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
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
凡时凡地,均可用之。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
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
[22](P9)
1942年他在给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编》一书所作的序中感慨道: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
先生少日即已肆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
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
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呜呼!
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
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
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
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
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
又何叹哉?
又何叹哉?
[23](P230-231)
陈寅恪在此借评述杨氏学术研究之价值表明了自己贱功名而贵学术之高远情怀。
他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
例如他虽然在欧美留学多年,但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纯粹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对此,萧公权先生曾有一番感慨:
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
史学名家陈寅恪是其中最为特出的一位。
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
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
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
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
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
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24](P69-70)
正反对比之下,陈寅恪的学术品格显得更加宝贵。
正因如此,蒋天枢先生曾饱含深情地说:
先生一生,操持俊杰,自少至老始终如一。
甲辰夏师赠枢序文,有“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义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等语。
复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者相昭示。
先生之情于斯可见。
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
早岁游历欧美各国时,仍潜心旧籍,孜孜不辍,经史多能暗诵。
其见闻之广远逾前辈张文襄;顾其论学实与南皮同调。
[9](P174-175)
因此,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力主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反对外来的、强加的束缚,坚持心灵之自由、独立之精神,可以说是陈寅恪最为根本的学术原则和观念。
其自述“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25](P144);“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26](P162)。
所学所论“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27](P219)。
所愿在“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26](P162),将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最高理想。
钱钟书也是如此,平日极少会客,极少开会,保持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意志,而专注于学术事业,淡泊名利,反对别人研究他,反对“钱学”之称。
在《谈艺录》中,钱先生痛斥“文人而有出位之思”的丑恶行径。
[16](P87-88)认为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并以此为“进身之道”的“陋儒”且不说,以“学业”为各种各样的“进身之举业”的,则是“曲儒”。
[16](P353)面对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研究,钱钟书曾经说过: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
”[28](P771)面对众人的膜拜和慕名而来,钱钟书说:
“兄平生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
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
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
’比年来多不做复,客来常以病谢。
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悉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
”[28](P25)对他而言,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一切的宣传都是干扰,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不仅如此,钱先生一生为学,极力反对“附庸风雅,随声说好,做文字批评上的势利小人(snob)”[29]。
而是主张:
“谈艺论文,一秉至公,极力消除势力门户之见。
”(季进语)正因如此,他在《管锥编》中谈及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编二《文德》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一切义理、考据,发为‘文’章,莫不判有‘德’、无‘德’。
寡闻匿陋而架空为高,成见恐破而诡辩护前,阿世譁众而曲学违心,均‘文’之不‘德’、败‘德’;巧偷豪夺、粗作大卖、弄虚造伪之类,更郐下无讥尔。
黑格尔教生徒屡曰:
‘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每叹兹言,堪笺‘文德’。
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
”[30](P1506)真正的学术研究,当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当以“真理之勇”为“文章之德”。
这是钱钟书毕生所奉为法则并教诲我们的学术信条。
三、治学兴趣:
历史考论与文艺鉴赏
就治学兴趣而言,陈寅恪重在史学和文化方面,最终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钱钟书则重在文学和艺术上,最终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
就是对同一研究对象,陈寅恪重在其思想,而钱钟书则重在其艺术。
比如钱钟书爱读小说,陈寅恪也自称: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31](P1),但是,陈寅恪的注意点在“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32](P185)、“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33](P192)等等。
而钱钟书的注意点则在其“有趣”和“美文”上。
钱钟书家学深厚,幼承庭训,其父子泉对他管教甚严,因此自幼年起,他就对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有广泛的涉猎,并酷爱文学,除系统地阅读过《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典籍外,对中国古今小说、译林小说以及外文原版小说也是异常痴迷,常常陶醉其间。
钱钟书在《谈艺录》开篇首句就说:
“余雅喜谈艺。
”[16](P1)又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再次表明自己的学术兴趣:
“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34](P7)这就决定了钱终其一生的研究重心在于文学和艺术的鉴赏和评判上。
而与一般艺术鉴赏著作相区别的是,钱之著述乃是立足于古今中外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重在揭示文心与诗心的著作。
本身就是诗人的钱钟书,在学术研究中,并不专注于注释、考证“作者之身世交游”之类的考察,而是沉浸于诗中,以诗人的眼光,用志不分地对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的诗心文心,抉幽探微,辨别是非,从而达到对“诗眼文心”“莫逆暗契”[16](P346)之“禅彻悟境”[16](P595)。
学术兴趣与研究取向就不由自主地影响到钱钟书的风格,对此柯灵先生曾有一个很好的评价:
钟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著作……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
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汇今古,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戛戛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
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
只有理智和感情的高度融合,高度升华,高度平衡,才能达到这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35]
这就揭示出了钱钟书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其创作有学者的风格和魅力,其学术有作家的魅力和风格。
可以说,钱钟书的创作是“学人之创作”,钱钟书的学术是“作家之学术”。
两者相较之下,陈寅恪则将更多的兴趣和精力倾注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上。
其曾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36](P239)。
俞大维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
“他研究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