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史资料讨论学期报告.docx
《六朝文史资料讨论学期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六朝文史资料讨论学期报告.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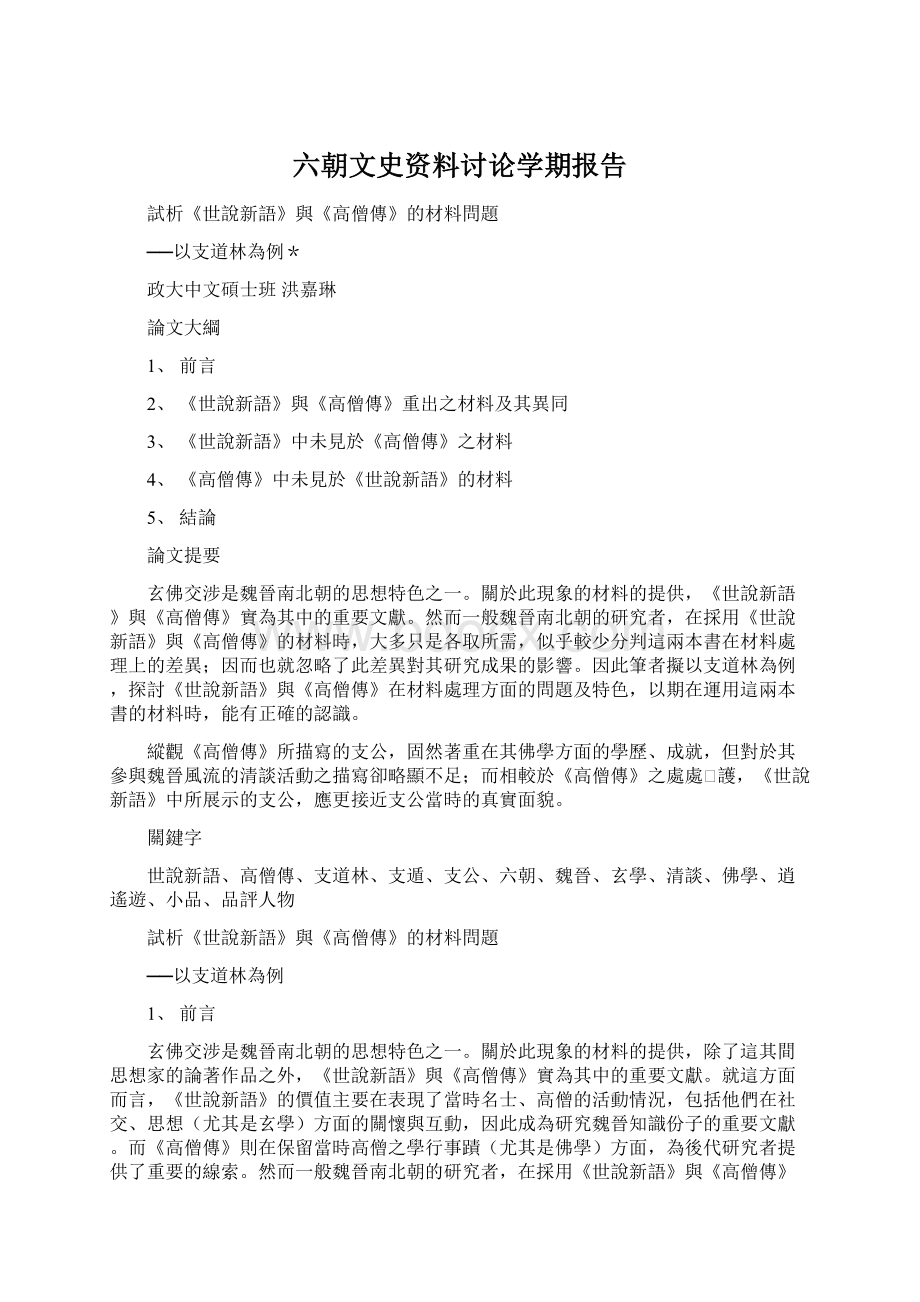
六朝文史资料讨论学期报告
試析《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問題
──以支道林為例*
政大中文碩士班洪嘉琳
論文大綱
1、前言
2、《世說新語》與《高僧傳》重出之材料及其異同
3、《世說新語》中未見於《高僧傳》之材料
4、《高僧傳》中未見於《世說新語》的材料
5、結論
論文提要
玄佛交涉是魏晉南北朝的思想特色之一。
關於此現象的材料的提供,《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實為其中的重要文獻。
然而一般魏晉南北朝的研究者,在採用《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時,大多只是各取所需,似乎較少分判這兩本書在材料處理上的差異;因而也就忽略了此差異對其研究成果的影響。
因此筆者擬以支道林為例,探討《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在材料處理方面的問題及特色,以期在運用這兩本書的材料時,能有正確的認識。
縱觀《高僧傳》所描寫的支公,固然著重在其佛學方面的學歷、成就,但對於其參與魏晉風流的清談活動之描寫卻略顯不足;而相較於《高僧傳》之處處護,《世說新語》中所展示的支公,應更接近支公當時的真實面貌。
關鍵字
世說新語、高僧傳、支道林、支遁、支公、六朝、魏晉、玄學、清談、佛學、逍遙遊、小品、品評人物
試析《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問題
──以支道林為例
1、前言
玄佛交涉是魏晉南北朝的思想特色之一。
關於此現象的材料的提供,除了這其間思想家的論著作品之外,《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實為其中的重要文獻。
就這方面而言,《世說新語》的價值主要在表現了當時名士、高僧的活動情況,包括他們在社交、思想(尤其是玄學)方面的關懷與互動,因此成為研究魏晉知識份子的重要文獻。
而《高僧傳》則在保留當時高僧之學行事蹟(尤其是佛學)方面,為後代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然而一般魏晉南北朝的研究者,在採用《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時,大多只是各取所需,似乎較少分判這兩本書在材料處理上的差異;因而也就忽略了此差異對其研究成果的影響。
因此筆者擬以支道林為例,探討《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在材料處理方面的問題及特色,以期在運用這兩本書的材料時,能有正確的認識。
支遁(314~366A.D.),字道林(時人又稱支氏、支公、林公、林道人、林法師,以下簡稱支公),是東晉時期著名的僧人之一。
當時清談玄風盛行,而佛學亦逐漸開始流行,支公身為此時期的沙門,既能熟悉外典,以致得以躋身於清談名士之間;又能精通內典,在佛學領域上創發新義。
因此研究者或以支公為「中、印兩大學術思想連類融會之代表人物」,或認為支公「對中國文化思潮由玄學向佛教的轉變,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可見支公確足為當時玄佛交涉的代表人物之一。
關於支公的資料,《世說新語》中共有五十二條,筆者擬以《高僧傳》之材料與之相互比對,期能一探《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在材料處理方面的特色與價值所在。
基於論述方便起見,筆者擬將材料分為「《世說新語》與《高僧傳》重出」的部份、「《世說新語》未列入《高僧傳》」的部份,及「《高僧傳》未見於《世說新語》」的部分,其下亦依材料狀況各分成幾個小項目。
其中並將選擇可以表現二書特色之材料於本文中加以討論;至於其餘材料,則放在附錄討論。
2、《世說新語》與《高僧傳》重出之材料及其異同
關於此部分,《世說新語》的材料共有十七條,以下乃就五個方面討論如下。
(1)支公個人生活表現方面
筆者先就《世說新語》與《高僧傳》支公之傳記(以下簡稱〈本傳〉)中重出的材料來討論。
大致分為支公在交遊方面的表現及生活嗜好方面的表現。
而在交遊方面的材料有兩條:
1.〈雅量〉第31條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
蔡暫起,謝移就其處。
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
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
坐定,謂蔡曰:
「卿奇人,殆壞我面。
」蔡答曰:
「我本不為卿面作計。
」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值得注意的是,這條資料在《世說新語》中,其記述之目的乃在表現謝、蔡二人之雅量,故列於〈雅量〉篇。
因此對於蔡舉謝擲地、及二人對答之過程有所著墨,最後並記述道:
「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而在《高僧傳》中,則僅記述到蔡舉謝擲地,而謝不以介意。
其後即接著慧皎之評論:
「其(支公)為時賢所慕如此」。
可見《高僧傳》引述這條資料的目的,乃在表現支公之受時賢之企慕,其目的不同於《世說新語》之表現當時時賢的雅量。
由此可見二書著述面向之異。
2.〈傷逝〉第11條
〈傷逝〉第11條所討論的是支公對知己──法虔的感情。
這條資料在《高僧傳》中描述得較為簡略,曰:
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
「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于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
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
」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
而《世說新語》則加了兩筆形容語句曰: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喪,風味轉墜。
」而在引述完「昔匠石廢斤於郢人……余其亡矣。
」一段話之後,《世說新語》旋道:
「卻後一年,支遂殞。
」可以說,《高僧傳》引述支公與法虔之事,除了表現出支公對法虔相知相惜之情外,更用意在以此帶出支公之死,並敘及其著作──〈切悟章〉;而《世說新語》之記敘,則集中在表現支公對法虔之知己之情,故此則列入〈傷逝〉。
以上兩條資料雖皆顯示出支公之當時名士所重,以及支公對同學法虔的珍重之情,但二書在記敘的目的與面向上,亦確有些許出入。
關於支公生活嗜好方面的材料有兩條,皆在〈言語〉篇。
其中〈言語〉第76條及《高僧傳》皆有提到支公養鶴一事。
《高僧傳》記錄於支公養馬之事後:
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
「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
」遂放之。
於此條中所顯示的支公人格,是愛惜高潔之物的,亦與前所謂愛馬之神駿意義連貫。
可知《高僧傳》記此事,乃在表示支公對於高潔神駿者之敬重。
然而,《世說新語》顯然有不同的認知。
〈言語〉第76條:
支公好鶴,往剡東山。
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
支意惜之,乃鎩其翮。
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
視之,如有懊喪意。
林曰:
「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就《世說新語》之材料來看,支公最後固然有《高僧傳》所表現之敬重高潔神駿者,但更難得的記錄,是支公嘗鎩鶴之翮令不能飛去一事。
若《世說新語》之記錄不妄,則支公之人格顯非始終一如《高僧傳》表現之高潔。
而支公仍會因愛物而豢養之,亦曾有傷物以滿足己意的舉動。
至於〈本傳〉以外重出之材料僅有〈排調〉第28條: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
「未聞巢、許買山而隱。
」
就《世說》的材料來看,深公嘲諷的意味頗濃,而嘲諷同時也意味著深公之量淺。
而此段資料記錄在《高僧傳》卷四竺法潛(即竺法深、深公)傳中,深公之答語有兩句:
「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
」則深公之語並非以嘲諷為主,反可表現出深公之開闊慷慨。
若對照於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曰:
「遁得深公之言,而已。
」則可知這段資料本來所表現的,似乎並非深公對支公的嘲諷,而是深公之開闊明白,以及支公之不明而荒謬。
(2)人物品評方面
此部分包含「支公對他人之品評」與「他人對支公之品評」兩部分。
在支公對他人之批評方面,同於〈本傳〉的材料在〈文學〉第42條: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
王長史宿構精理,並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
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
支徐徐謂曰:
「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
」王大慚而退。
《世說新語》所表現的,是王長史與支公在多年之後重逢時,支公已有所長進,而認為王長史無論在義理或言談上皆未有成長。
《高僧傳》亦引述此段資料,而謂王長史為王濛,但於「濛慚而退焉」後緊接著說:
「(濛)乃歎曰:
『(支公)實緇之王、何也。
』」此句評論亦出現在《世說新語‧賞譽》第110條: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
「向高坐者,故是凶物。
」復東聽,王又曰:
「自是釪後王、何人也。
」
而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曰:
王濛恆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
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
濛云:
「聽講眾僧,向高坐者,是釪後王、何人也。
」
依此言,則王為王濛。
於此,王濛對支公先後有兩種不同的評價。
但根據《世說新語》來看,後一評價似乎並非「支道林住東安寺中」時之事。
而王曉毅認為,王濛與支公相遇、及其對支公有「自是釪後王、何人也」的評價之事,當在永和元年到二年之間,地點在會稽山陰的祗洹寺;至於升平五年在東安寺與之清談者,當為王坦之。
則就《高僧傳》之資料而言,可討論如下:
其一,若將「支公住東安寺」時之事與評價支公為「釪後王、何人也」的事件拆開來看。
則支公在東安寺時期與之清談者確當為王坦之。
若又依《高僧傳》所言,王、支公之清談與王之評價支公是同一件事,時間又在支公在東安寺時期,則王亦應非王濛,而當為王坦之。
則《高僧傳》對於清談與評價者的記載是錯誤的。
其二,若將《世說新語》、《高僧傳》、《高逸沙門傳》三份材料相互比對,而以多數為準,則如王曉毅之考定,王長史與支公在東安寺清談一事(升平五年,361A.D.)實在王濛評價支公為「釪後王、何人」一事(永和元年,345A.D.)之後。
如此一來,《高僧傳》之記錄顯然顛倒了事件的順序,則其所言「(濛)乃歎曰」之「乃」字應如何解釋?
若《高僧傳》之「乃」字無誤,則至少王、支之清談一事當在王濛評價之前。
如此一來,似乎與《高逸沙門傳》言王濛於祗洹寺評價支公的記錄矛盾。
其三,若《高僧傳》是將兩段不同時間地點的材料剪貼在一起的,但誤解了《世說新語》或二書同源材料的記錄,以為在東安寺與支公清談的王長史為王濛。
則與支公清談的或為王坦之,而評價支公者確為王濛。
則與《高逸沙門傳》與《世說新語‧賞譽》之記錄皆無抵觸。
因此,就資料的立場來看,王曉毅之考定是較為合理的。
則《高僧傳》之剪貼兩段材料並顛倒了事件順序,似欲以簡潔之手法表現支公的卓然,以及支公在玄學或清談上地位之崇高。
就《世說新語》而言,〈文學〉中記敘王、支清談一事,乃在表現王之不足與支之有餘;而〈賞譽〉引述王濛前後不同的評價,主要當在表現支公在祗洹寺時之卓越,及其在清談或玄學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而就《高僧傳》所言,雖然誤將王為王濛,但其引述王、支清談一事,主要用意不在表現王之不自量力,而在引出「緇王何」之說,也因此顛倒了事件發生之順序。
由此可見《高僧傳》之取捨與筆法。
在他人對支公之品評方面,共有五條資料,本文但討論其中四條如下:
1.〈賞譽〉第98條與〈賞譽〉第110條
此二條實為相輔相成之資料。
承前所言,〈賞譽〉第110條引述王濛前後不同的評價,主要當在表現支公在清談或玄學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賞譽〉第98條則曰:
王長史歎林公:
「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
而此王長史究竟是王坦之抑或王濛?
劉孝標注引〈支遁別傳〉曰:
「……王仲祖稱其(支公)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可知此評價支公者當為王濛。
則由此二則均可看出支公在魏晉玄學與清談中,實據有領袖群倫之地位。
而此二則資料,除了〈賞譽〉第110條省卻了王濛早前謂支公為凶物之記錄外,其餘大致相同。
由此亦可知《高僧傳》在支公之傳記中,實有所護。
2.〈輕詆〉第24條
〈輕詆〉第24條下劉孝標注所引〈支遁傳〉與《高僧傳》之記載相同,《高僧傳》曰:
(支公)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
謝安聞而善之,曰:
「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
」
然〈輕詆〉第24條卻恰可匡正〈支遁傳〉與《高僧傳》之誤。
以〈輕詆〉第24條所記,所謂「(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
」者,實非謝安所言。
以謝安之答庾道季語來看,謝安認為此語實為裴啟《語林》自己編造出來的。
若此,則可以《世說新語》正《高僧傳》之謬誤。
然就《高僧傳》之記述而言,其重點乃在稱許支公之為學,能以意會,而不拘泥文字之特色。
故正此一謬誤可視為對《高僧傳》之補充。
而《世說新語》提及此語之目的,卻不在討論支公之為學,而在表示謝安對《語林》之評價,以及謝安評價在當時受重視的程度。
當然從中也顯現出《語林》記載之錯謬,及其對於「草野傳聞,不加考辨」的情況。
3.〈品藻〉第67條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
「林公談何如嵇公?
」謝云:
「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
」又問:
「殷何如支?
」謝曰:
「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
然亹亹論辯,恐殷欲制支。
」
《高僧傳》所載與此大同小異。
依此所言,則謝安認為在清談方面,嵇康不如支公,而殷浩與支公各有所長。
余嘉錫認為:
本篇(〈品藻〉)載安答王子敬語,以為支遁不如庾亮。
又答王孝伯,謂支并不如王濛、劉惔。
今乃謂中散努力,纔得及支;而殷浩卻能制支,是中散之不如庾亮輩也。
乃在層累之下也。
夫庾、殷庸才,王仲祖亦談客耳,詎足上擬嵇公?
劉真長雖有才識,恐亦非嵇之比。
支遁緇流,又不足論。
安石褒貶,抑何不平?
雖所評專指清談,非論人品,然安石之去中散遠矣!
何從親接謦欬,而遽裁高下耶?
此必流傳之誤,理不可信。
《世說新語》此條資料表現的是支公與嵇康、殷浩在清談方面的高下。
就清談而言,謝安認為支公遠勝嵇康,而殷浩特長在雄辯、支公特長在其「超拔直上」。
而余嘉錫之認為此言不可信,筆者試從兩個方面來看:
其一,余嘉錫於〈賞譽〉第50條下箋疏道:
凡題目人者,必親見其人,挹其風流,聽其言論,觀其氣宇,察其度量,然後為之品題。
其言多用比興之體,以極其形容。
依余嘉錫之意,則當時人從事品評,必得親見其人。
而謝安與嵇康年代相去甚遠,無由親見,自不應有品評之可能。
但當時之清談卻也有談論古代人物以為品鑒理則者,如〈言語〉第23條及72條,分別記錄了王衍與王戎曾談論季札、張良之事;以及伏滔與習鑿齒之論青、楚人物。
在此〈品藻〉第67條中,嵇康或許不是作為謝安具體人物批評的對象,而是被當成一個清談人物典範,以襯托出支公在清談方面的評價;其後謝安又論支公與殷浩二人時,則確為具體人物批評,此時便適用於余嘉錫提出的原則。
其二,當時名士常互相稱譽、標榜。
謝安稱譽支公而貶抑嵇康,或許正緣由於嵇康去之甚遠,而支公卻是當時清談名流之一;至論同時期的支公與殷浩時,其品評便認為各有所長了。
此外,就今日遺留下來的資料來看,嵇康雖善談,其對於魏晉清談主要的貢獻恐怕還是在於其著作。
或許正因為嵇康所處的時期不利於清談,所以其清談的記錄亦不多見。
而對於其清談方面的表現,自不似謝安與支公等人的成就如此顯而易見。
然此論終究只能是後見之明,謝安等人當時對嵇康的看法,今人亦不易盡悉,余嘉錫的懷疑也自有其道理。
而就表現支公在清談方面的卓越此一目的而言,《世說新語》與《高僧傳》是相同的。
但就表現殷浩之特長的方面,固然《世說新語》意在如此,但在《高僧傳》,因為〈本傳〉的敘述主角是支公,故殷浩之特長只是作為陪襯而已。
由是亦可見二書在引述資料時亦有敘述脈絡上的不同。
(3)清談方面
就清談方面而言,《世說新語》與〈本傳〉重出的材料分別為〈文學〉第36、40條。
其中〈文學〉第36條與《高僧傳》皆提及王羲之與支公相會談論《莊子‧逍遙遊》之事,但兩段資料不盡相同。
在《高僧傳》中:
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
「一往之氣,何足言。
」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
既至,王謂遁曰:
「〈逍遙篇〉可得聞乎?
」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
王遂披衿解帶,流連不能已。
仍請往靈嘉寺,意存相近。
在此,王羲之是自己去找支公,有較量之意。
末後拜服支公,而請支公往靈嘉寺,「意存相近」。
然在〈文學〉第36條中則有不同的記載: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
「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否?
」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
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
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
」因論《莊子‧逍遙遊》。
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
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於此,王羲之至會稽的時間比支公晚,而支公與王羲之相會時還有孫興公作為穿針引線者,介紹二人認識。
但王羲之自負其氣,未肯與支公交言,有輕視支公之意味。
於是支公其後藉機與王羲之交談,且一談就是支公擅長的《莊子‧逍遙遊》,終於使王羲之折服。
就兩段記載來看,《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各有詳盡之處。
而《高僧傳》中的支公是被動地與王羲之談論《莊子‧逍遙遊》,其胸懷則似較《世說新語》之記載寬闊;而《世說新語》中,支公是感於王羲之之輕視而主動與王羲之談論,則似較為氣狹,未能無待於他人之寵辱。
再者,《高僧傳》與《世說新語》用以描述支公論《莊子‧逍遙遊》之精采的形容詞略有小異。
《高僧傳》作「標揭新理,才藻驚絕」,《世說新語》作「才藻新奇,花爛映發」。
由此可知,《高僧傳》言此事,似較看重支公《莊子‧逍遙遊》義在義理上的新奇;而《世說新語》則較著重在支公清談時的修辭技巧。
此外,《高僧傳》隨後即道王羲之請支公往靈嘉寺,充分表現出王羲之對於支公的欽慕之情;也同時帶出支公往住靈嘉寺之事。
然鑒於《高僧傳》常有剪接材料之舉,因此筆者以為王、支論《莊子‧逍遙遊》之事,與支公往靈嘉寺之事之間,或許還隔了一段時間,而非隨後即往。
而與〈本傳〉之外的部分重出者,在於〈文學〉第45條: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忿,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
于時支公正講《小品》。
開戒弟子:
「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
」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
「舊此中不可復通。
」弟子如言詣支公。
正值講,因謹述開意。
往反多時,林公遂屈。
厲聲曰:
「君何足復受人寄載!
」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1,于法開在學問上與支公意見相左,而後學界逐漸以支公見解為是。
而法開意甚不平,仍以己解為優。
2,法開與支公皆精研《小品》,其意見相左處可能正包括《小品》。
3,支公在《小品》方面,一直都有理論上難通之處。
及至法開遁跡、支公講經時仍未能通。
4,對於意見相左一事,兩人都不平於心,無法忘懷得失。
故法開令弟子攻難,而支公責該弟子之受託於法開,實亦責法開之令支公難堪。
關於此事,記錄於《高僧傳》之〈于法開傳〉中,並著明該弟子為于法威。
而其餘諸事大抵相同,遂不復言。
唯此事之未錄入〈本傳〉,或許正是因為這場辯難是法開勝支公,且顯示出支公的器量不足,故慧皎置之〈于法開傳〉中,以顯法開之能。
而支公器量,於此又可見一斑。
(4)玄學方面
關於支公在玄學方面的成就,於《世說新語》中有四條資料皆與〈本傳〉重出;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文學〉第32條中有關支公「逍遙義」的記錄。
《莊子‧逍遙遊》本是魏晉清談論辯的主題之一。
此問題由向、郭之注《莊》開始受到玄學家和清談家的重視。
而在支公以前,玄學家與清談家對於《莊子‧逍遙遊》的理解與認識,主要仍不出於向、郭之外。
〈文學〉第32條曰: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
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
後遂用支理。
而《高僧傳》之記錄為:
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
「各適性以為逍遙。
」遁曰:
「不然,夫桀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
」於是退而注〈逍遙篇〉。
群儒舊學,莫不歎服。
此二處資料可互為補充,而其間有幾處略有差異,試析如下:
其一,與支公在白馬寺談論的,或曰馮太常,或曰劉系之等,可見《高僧傳》與《世說新語》所引材料或本有所異;又或「劉系之等」即包括馮太常,而《世說新語》僅舉馮太常為例、《高僧傳》則僅以劉系之為例而略去其他人。
又或者支公在白馬寺論及〈逍遙遊〉本不只一次,而二書各有所本、各自記錄而已。
其二,依《世說新語》之資料來看,似乎意味著,支公是在與馮太常清談時提出自己的逍遙義,從而蔚為風尚;而《高僧傳》中則是於白馬寺與劉系之等清談後,「退而注〈逍遙篇〉」,而群儒歎服。
若兩段記錄皆無訛誤,則或許與劉系之等清談之事在前,此次清談後支公回去注釋〈逍遙篇〉。
而後在與馮太常清談時提出其逍遙義,從此支氏逍遙義遂行。
其三,《高僧傳》提示於讀者的是支公注〈逍遙遊〉的動機,也說明了支公之所以不贊成向、郭的逍遙義,乃在於其「適性」之說。
而《世說新語》則敘述了支公逍遙義的特長,在於「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說明支氏逍遙義之所以盛行的原因。
其四,《高僧傳》所欲表現的,當是支公對《莊子‧逍遙遊》深有所得,故其後並提及王羲之與支公論〈逍遙遊〉一事;而《世說新語》則意在表達支公對於玄學──尤其是莊學的貢獻,故特地交代了魏晉學者理解《莊子‧逍遙遊》的情況,以及其來龍去脈。
因此,《高僧傳》重在支公的學問;而《世說新語》則側重於逍遙義的理解趨向。
此外,支公的〈逍遙遊〉注,除音義上的注釋有五條被保留在《經典釋文‧逍遙篇》之外,其逍遙論今已佚失,唯一可見的即劉孝標本條注所保留的資料。
在此資料,吾人可略窺支公的逍遙義所在。
而劉孝標於文末言道:
「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則或許劉孝標所引的內容,亦只是劉氏認為向、郭所不足的部分而已。
而關於這段資料的內容主旨,前人已多有論述,故此處不再加以討論。
(5)佛學方面
在佛學方面的材料與〈本傳〉重出者,在〈文學〉35條: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
支曰:
「默而識之乎?
」王曰:
「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
於《高僧傳》中,只述及支公著作〈即色論〉,卻未引述此條資料。
或因此條資料顯示出王中郎之不服支公的〈即色論〉,故慧皎略而不談,只述及支公對當時佛學的貢獻,在於立「即色義」。
而《世說新語》此則亦顯示出當時佛經流傳的情況,至少有些已足成為名士們共同閱讀的文本,因此王坦之隨口即能以《維摩詰經》的內容作為典故。
從以上《世說新語》與《高僧傳》中重出的材料來看,可看出以下幾點:
一,《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皆表現出支公在清談、玄學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與崇高的地位,並為時賢所重。
而《世說新語》雖呈現出支公在清談方面,及其對於《莊子‧逍遙遊》的領會確為時賢翹楚;但亦呈現出支公當時在參與清談活動時,亦未必盡得其義的情況。
這點在《高僧傳》中是看不出來的。
對於支公在清談時亦有氣狹而似已流於意氣之爭的情況,《高僧傳》將該資料記錄於他人的傳記中,顯見《高僧傳》在處理材料時確有所護。
因此材料有不利於支公者,則或有所刪削,又或轉錄在他人的傳記中。
二,《世說新語》與《高僧傳》二書在著述態度上有所差異。
同樣有與支公相關的材料,《高僧傳》側重於表現支公個人的學行風範。
而《世說新語》側重在表現魏晉名士風流的事蹟,如征虜亭中蔡謝之「雅量」;也因此《世說新語》對於支公的材料可以善惡兼取,無所顧忌,而今日之讀者亦才能從中見得支公較真實的生活面貌。
三,以《世說新語‧輕詆》第24條可以正《高僧傳》所訛傳聞之誤。
3、《世說新語》中未見於《高僧傳》之材料
《世說新語》中關於支公的材料而未見於《高僧傳》者共計有三十五條,以下分從四個面向討論之。
(1)人物品評方面
在人物品評方面,筆者分為「支公對他人之品評」與「他人對支公之品評」兩部分來討論。
在支公對他人品評之方面,共有十一條資料,揀述如下。
甲、評人物學問
1.〈文學〉第30條
〈文學〉第30條記載了一段支公與北來道人講《小品》的資料: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
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
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
此道人每輒摧屈。
孫問深公:
「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
」深公笑而不答。
林公曰:
「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
」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從這條資料中可以看出支公的自負,及其對竺法深的輕視。
按支公是「即色宗」的代表人物,而竺法深是「本無異宗」的代表人物,於此孫綽謂深公是「逆風家」,或許意味竺法深的「本無異義」和支公的「即色義」至少可以抗衡,故似應在支公與北來道人的論辯中發言。
而支公顯然不以為然,反而認為竺法深未能與之較量。
於此可知支公對於竺法深學問或清談方面的評價,以為必不如己。
此外亦可見支公與竺法深對於《小品》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當各有其見解。
2.〈輕詆〉第21條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
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
「箸膩顏帢,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