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docx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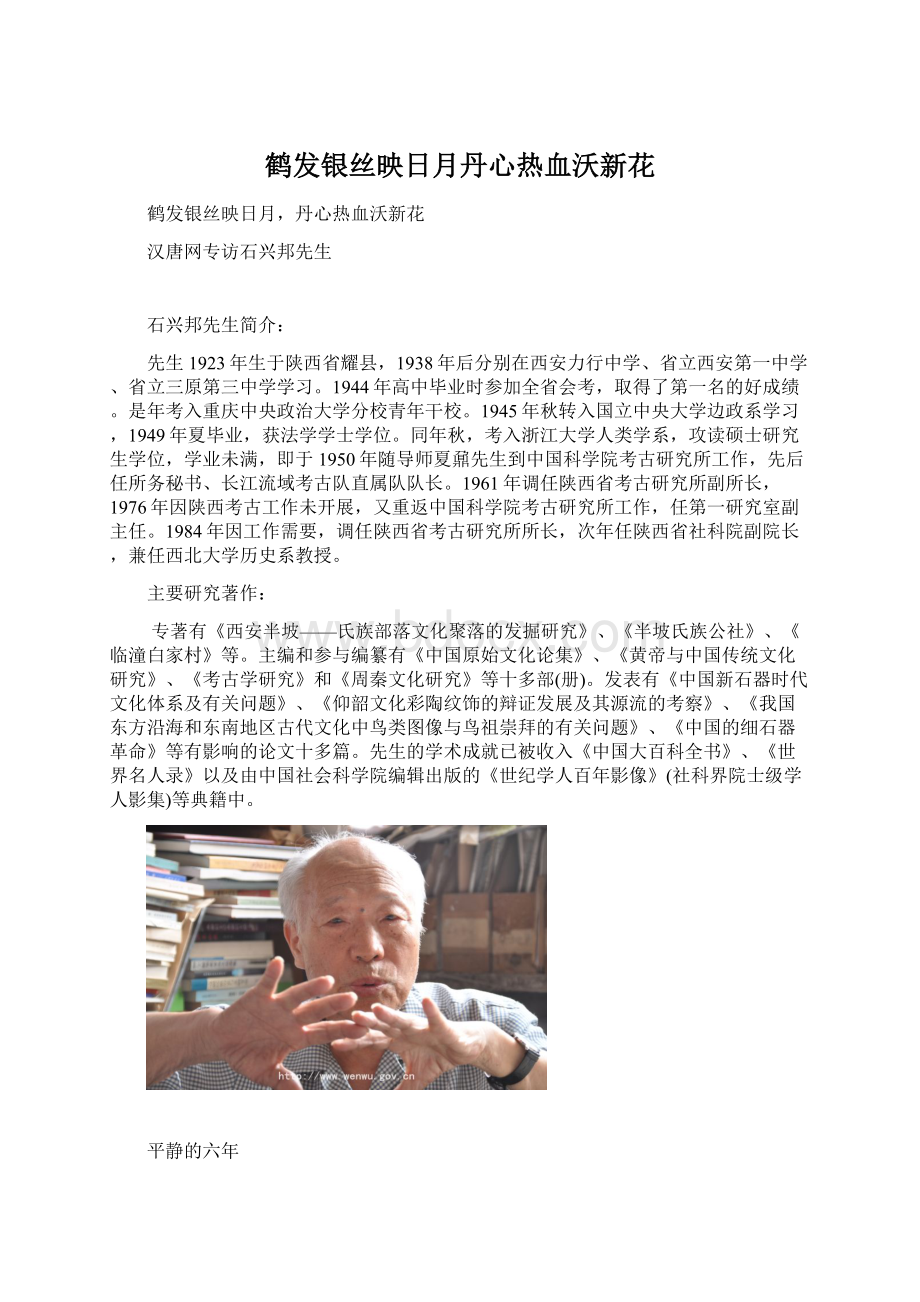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
汉唐网专访石兴邦先生
石兴邦先生简介:
先生1923年生于陕西省耀县,1938年后分别在西安力行中学、省立西安第一中学、省立三原第三中学学习。
1944年高中毕业时参加全省会考,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是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分校青年干校。
1945年秋转入国立中央大学边政系学习,1949年夏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同年秋,考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学业未满,即于1950年随导师夏鼐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任所务秘书、长江流域考古队直属队队长。
1961年调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76年因陕西考古工作未开展,又重返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
1984年因工作需要,调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次年任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兼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研究著作:
专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发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等。
主编和参与编纂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等十多部(册)。
发表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等有影响的论文十多篇。
先生的学术成就已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世纪学人百年影像》(社科界院士级学人影集)等典籍中。
平静的六年
汉唐网:
非常感谢石先生今天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汉唐网的采访,能跟我们谈谈您的学习经历或者生活经历么?
石兴邦:
我就是陕西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家里还是属于富裕中农的样子,不是很富裕,但是还可以自给,不缺吃穿,也比较保守。
我出生的耀县,过去叫同官,现在叫铜川,我在同官十字镇上的小学,平常的时候上学,假期我就在家里放羊,我家里有上百的绵羊,所以不缺吃穿,还有些富余,再是羊的副业,可以卖羊,可以剪毛,还可以擀毡,我们那个时候自己做的毡帽子,毡袜子,你看我这个毡,就是我自己擀的。
(先生指着自己椅子的坐垫展示着)
农村的生产除了摇耧我不行,其他的比如践地(实践操作土地),耕种我都会,我那个地方还怪的很,下的片场雨,就是山这边下雨,山这边不下,下完了片场雨后,我们这边的谷子、小米就打的很好,我家的那个地方还是个山边边(靠近山的平原),关中的女娃娃都愿意嫁到我们这边来。
那个时候政治也比较复杂,因为正好是国共两党期间,那时候在我们家那边画了一条线,我家就划到了国统区,那一边叫陕甘宁边区,到耀县我上小学的时候,娃娃上学就是识字为光耀门庭不受骗就行了,当然传统的想法都是升官发财,很多人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个县长就行了,我那个时候有个优点,就是从小学到大学遇到的都是好老师,所以成绩一直都比较好。
也就是这六年过的比较安稳,学的也比较系统、扎实。
一中的校歌
到了1937年(民国26年)红军改成了八路军,我就上了西安一中,当时西安最好的学校有三所:
西安一中、二中和三中。
西安一中即现在的西安中学,那是关学的正统,比较保守,考试的时候,一中(的分数)都在前面。
西安二中即现在的师大附中,那是革命的学校,那个校长讲话都是革命革命的。
西安三中就是三原中学。
还有三个私立中学,西安私立学校,即现在的民心中学,是个女中。
我上的西安一中,那是关学①的正统,我只上了半年学,日本就开始轰炸了,就是“七七事变”卢沟桥事件期间,先占河北再占山西,就快到了同官,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开始搬迁了,一中搬至汉南了,在一中虽然只住了一学期,但是关学教育给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比较严,那是全才教育,要能够写字画画、数学、理化,我还记的我们一中的校歌:
“一中一中可爱的一中,荟萃三府精英,锻炼气派,修养学行,济济一堂乐融融,关学重实践驷铁美秦风,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莫让那骄子立柱燕然勒名,天载独光荣,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我这样一说你就知道了,把陕西历史上的光彩一下就都说清楚了,就说你这个青年要继承历史光荣,莫让那骄子立柱燕然勒名,骄子立柱就是马援征伐越南立柱为证,东汉窦宪为保卫西北疆土抗击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燕然山就是今天的外蒙古杭爱山,不要独自奋斗,要大家一起都光荣。
一中出来的学生,那个国民党里面出了几个将军,有个关麟征,有个杜律明,都是一中出来的,也别看,我们一中出去的学生,还真的把日本人打跑了很多。
所以陕西的这个教育,应该是成功的,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继承了陕西的精神,陕西的也就是中国的。
后来我就到了三原中学。
①关学:
绵绵秦岭北麓,巍峨太白山下。
900年前,北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张载在眉县横渠镇之侧,设帐讲学,创立“关学”,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名言以及“民胞物与”的治世理想,历久不衰,一任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关学思想的人性光辉闪烁依然。
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关学是他在关中地区讲学而形形成的一个大的学派。
比他稍晚的是程颢、程颐兄弟创立的洛学,(因是洛阳人而得名),再就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了。
关学和洛学是理学的学派之一,也是朱熹思想的先驱。
从眉县“起根发苗”的张载关学思想,最终成为一个有独特学术旨趣和风格的思想流派。
他的思想还成为推动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对宋以后历代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今天,张载之学对于国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第一名的成绩免试上了高中
初中毕业时,我是全班第一,免试上了高中,本来我那边毕业了后可以教书,我家里都跟我说好了让我去教书,后来我接到同学的来信说免试生可以免费上高中,所以我就接着上高中,叫工读生,就是四个学生分一个教师的工资。
这就到了抗战时期,其实我家里那边还是不太安宁,我家那边是险要的地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抵抗那会不是拿正规军参战,是用各个地方的保安团队的人。
我家里是养羊的,把我的羊吃完了,那个时候根本不讲道理,一个羊能卖十几块钱,人家只给你一块钱,你不卖也得买,你不要钱还不行,后来我就把羊都卖了,家里也没有了收入,嫌麻烦。
那六年,真学的好,安安静静的,生活也相对较好。
中国抗战是人为的也是天意,年年丰收,全中国就丢下一个四川、一个陕西,其他地方都弄的破破烂烂的,就是丰收把兵养活了,把干部养住了,维持了下来,不亡中国也是天意,保存了实力。
学生也很吃苦,吃的也不比现在差。
到高中的时候,某些大学的课也讲,我们那个时候占了便宜,因为二战区的山西大学搬来了,我的老师有些是讲师,有些是副教授,给你讲地理啦、讲生物啦什么都讲,讲课的质量很高,比西安、宝鸡的很多高中讲授的质量都高,我的那些同学也都很优秀,有些是战区跑来的,有些是本地请来的,全国各地的很多学生都到三原来了,这是1944年抗战结束,那个时候抓的紧,高中会考,以省为单位,我那班是陕西会考第二次,第一次是我上一班,考的第一名是我耀县人,后来去了西北农学院,这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搬迁的学校。
第二次会考是全国会考,我在我们省上会考是第一名,省上来人到三原会考,西安那个时候是空的,驻守西安的是一个司令,叫陶峙岳,是国民党37集团军军长,这个人爱文化、爱学生、爱国,那个时候他就让两边安的大炮,日本的飞机来了,就开始响警报,他后来去了新疆,听说是跟苏联有联系。
实际当时汉中、三原才是中心,因为山西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武功农学院都在那里,一中也就沾了这些大学的光。
战火中我的大学志愿
到了1944年,我是33级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志愿表上填的是中央大学政治系,再一个是新疆学院民族系,因为我对张骞通西域,马援和班超的故事就很感兴趣,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教育部在重庆,他们就觉得这个学生还怪,还学政治呢!
边政系就是那一年成立的,1944年,当时成立边政系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西北大学边政系,主要管西北和东北;再一个就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主管东南这一块。
当时苏联和新疆活动的很厉害,国民党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把我拨到了边政系去了,没想到还学对了,边政系当时学啥呢?
我跟你说,就是中央大学的一批老师教我们,教授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原始社会、村民社会、考古等课程,当时学下这些东西有啥用呢,这还说不来,后来做了考古才知道还真是学对了。
西北大学可惜了,把这个系取消了。
我就是这样到了重庆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重庆)、北大、清华在云南,中央大学包括的学校多,八个学院都集中在哪里,法学院、民族学院也都在那里,学的都是民族学的课,古人类的课,所谓边政就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制度,我的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这些课程都是那个时候学的,我就学了这些。
我们边政系学的都是很好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当时学的原始人类化石全世界各种人都学了,怪异不齐的,人里面还有些奇丽怪状的我也都学了。
后来边政系还没有毕业,1948年南京就乱了,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下面对着十万人一讲话,很多人都到台湾去了,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南京当时都是空的,但是我的系主任还在,我就说我留下,那段时间,我还觉得挺闲适的,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找事情做,自己整理边政系当时遗留的资料。
后来也联系上了工作,4月21号我还记得,因为我的几位老师,韩先生(韩儒林)回来到上海,还到台湾去了一趟,我说你赶紧回来,不要到哪里去,我就把他叫回来了,后来我就把边政系的工作都移交给了他。
那个时候有人说边政系教授的都是大汉族主义,就把边政系取消了,实际上我没有毕业,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系工作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我学的好,老师也非常看重我,我们系主任也换了,原系主任调到了历史系。
报考硕士
当时我还在中央大学当助教,但是他们要把这边的资料都给了边疆名族教育馆去,我说这咋办,也就是正好在那一年,浙江大学在招研究生,我们的一个老师,叫徐益棠,是金陵大学的教授,他介绍我去浙江大学面试。
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就拿了我的一篇论文和成绩单到浙大的人类学系去了,去了一看,教授民族学的教授都认识我,因为之前我们开过几次民族学的会,我还是民族学会的秘书呢,参会的教授就是那几个人,都熟悉的很,有一篇论文,再是讲我的简历,把我就取上了,测验了一下我的英语,说我是:
英语要加强。
(笑......石先生很幽默和健谈,整个谈话过程很怡然)
就这样我就到了浙江大学当研究生,在这之前,我们边政系毕业的时候,和其他系不一样,我们分三个组:
维吾尔组、西藏组、蒙古组。
我选的是蒙古组,毕业的时候,要求我跟其余四个同学一组共同翻译一本书,我们翻译的是《蒙古秘史》,没有多长时间就翻译完了。
他们也都没有另外做论文,就我一个做了论文,出了题目是《唐代中国与波斯的关系》。
后来我就到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夏鼐先生刚好在那边教考古学,还有吴定良先生教体质人类学。
特别的老师
给我们教体质人类学的是吴定良先生,那个人学问大的很,就是不给学生教,比较保守呵呵呵.....找老师是他没有学问不给你教,他是有学问不给教。
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你说人类学在骨骼上有啥区别?
他就不说,我就说啊呀你就给咱说一下嘛,老先生保守得很,也可惜的很,就是不说,后来他被我逼得没有办法,就跟我说了,他说白种人和黄种人在骨骼上都有特点,我知道。
我说你说一下,他说就拿锁骨来说,黄种人是扁的,白种人是三棱状的,就是有棱棱的。
肯定还有别的,他就不说了,我说我再不问了,再问别的他也死活不说了,他写的书也很好,他有些书就是不让人看,这老师麻烦的很,人是很好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他学的那一套不容易,轻易把这个弄出去,他还不高兴,所以也不给人教,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都比较保守。
我他家里整个吃、喝、住了一个月,后来他到了复旦大学,惨的很。
他回到北大的时候,我还去看了他。
我说的清楚不,我就这样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我这个经历很少有人知道。
汉唐网:
您说的很明白,您这也是口述历史吧。
石兴邦:
还有这个1948年开始,南京就乱了,大家就说不行,我就留下来了,边政系的事情,叫我代理上。
我是研究生开始学考古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底子比较厚,学的东西都用上了,有些现在都很难学到。
这个事情很好,吃的穿的都发,都还不错。
1949年这个时候,解放了,夏鼐就到了中国社会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也成立了。
那个暑假后,我就跟夏所长说,让我到北京考古研究所去,因为学下的那些东西,在考古上都能用上,现在还学不到那些东西,在一个就是考古正是雏形,也红的很,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中,排在第一个就是考古学家,挖那个殷墟,把考古工作的地位提得很高,作为一个人类学物质文化主要的组成部分。
一生怀有感恩之心
汉唐网:
您还记着有那些老师对您影响较大?
石兴邦:
我感觉一生都遇到好老师,印像都好。
我小学的时候,在乡村大庙里上课学习,有个老师叫寇怀义,给我的启蒙高,给我讲了很多新思想。
晚上我就跟老师住在一起,晚上说这呀说那呀,感觉很高兴,他讲很多东西都很吸引我。
但是到了白天对学生要求很高,他思想很开放,重视艺术、新思潮,开朗的很,要求写字要好,我在写字方面狠下了功夫。
还有一个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名字不记得了,他是共产党,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报上见他“脱离共产党申明”,后来也悔过了,那个时候和现在情况不一样,脱离共产党的多,教师也不一样,真心教。
他是北大一毕业就到商南当教师,所有人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就爱看报纸,我还想这个人还很有意思还脱离共产党,呵呵呵....他后来,很进步,很厉害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他讲起话来很有革命家的气势,到处演讲共产主义,是个好共产党员,他是北大毕业,不知道怎么样就到了我们商县中学,由商县又被请到了别的学校,那个校长是个进步校长。
解放后,他活到了90多岁,我很敬重他。
在中央大学,我有个老师叫韩儒林,教授我们蒙古史的老师,还有就是夏鼐先生。
在浙江大学,当了一年的研究生,那个时候结识了俩个学生,一男一女,那个时候老师带学生是一人坐一个凳子。
那个女同学叫啥我想不起来了,她人非常好,她家里比较富裕,父亲是个正派的商人,金石学非常厉害,我还跟她说你金石学学的这么好,报考古没有错的,但是可惜的很,她后来自杀了。
另一个叫沙孟海,是个书法名家,还给我写了一副字,前几天我还看见来着。
人呐一辈子就得有几个好老师,这个错不了。
1949年时候,那一段有几个共产党人对我产生很大影响,这一段我很平安。
我出去还没有犯错误,能让我安心地搞事业,那个时候都有很多新型的人,但是新型的人都有老型的特点,比如尹达老师,尹达其实是中央研究院的学生,大家说那是革命的国民党,后代还是激进的共产党,人这个变化,后来也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考古方面来讲,比较说起来,跟上共产党年轻,过去是四书五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马列主义,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是解放以后社会科学院第一期培养的干部,让你先去了当学术秘书,去了先是让读马列主义的书,马列主义的书我都读了,俄文的,英文的,都看了。
凡是当学术秘书的这一层人,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人都要去看。
我现在还跟我中学时候的老师有联系,师大有一个,医学院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有一个。
中国第一个史前博物馆
汉唐网:
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当年参加半坡发掘时候的故事或者感受么?
石兴邦:
我最近刚写了一个关于半坡的东西。
感受么,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我觉得自己观念意识上都不落后,当时我们知道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因为我在大学里学的原始社会、村民社会,以及后来解放以后学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接触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这些东西,都通过在半坡的发掘中得到了印证,感觉到一点也不错,所以现在人们喜欢谈这个谈那个,你现在要找中国无论那一个阶段的考古实例都能找到,就是看把那个安排的恰当不恰当,他要把那个皇帝放在哪里要看考古实际在不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要踏踏实实的,因为考古跟别的行业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亦即我们通常所言的“实证科学”)。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那是1954年,第三届考古人工作人员训练班选择西安地区进行田野实习,我参加了训练班,并负责田野实习总辅导工作,实习的地点选择在东郊基建区,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基建区会有那么大的发现,就是后来的半坡遗址。
位置就是在白鹿原下面的二级阶地上,墓葬实习点选在白鹿原三级阶地上的国棉三厂福利区,哪里正在施工建设,并发现了不少汉、唐墓葬,两地相距很近,工作生活都方便。
田野实习大约是9月份开始的,先发掘墓葬,再发掘遗址。
那次我们改变了工作方法,采用探方法,大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做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第二步的发掘计划和方法。
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方型房子的残迹,以及其他房屋建筑遗迹,迹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揭露出完整的史迹,与过去打探沟、切成条条分割大有不同,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大,方法对头,我们也很高兴。
在举办结业典礼时,北京文物考古界的领导同志都来了,当时裴文中先生也来了,我记得他还说:
“这个方法发掘遗址好,过去打探沟把整体房屋都‘切切糕’,切掉了,石兴邦这次做的不错”。
裴文中先生看了当时半坡出土的器物后,认为这些东西有些怪,是否是仰韶文化还不能确定。
直到这个遗址整理到了第三年,到了1955年5月份,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类型后,才确定了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让我感到很遗憾的事。
当时我们训练班结束后,考古所参加的同志留下继续工作,像余伟超、金雪山、杨建芳、张云鹏、王镇江等同志都参加了发掘。
训练班的陕西学员也全部留下工作,我还记得有王世昌、唐金裕、王玉清、杭德洲、杨正兴、郝树屏、尹绍祖、何修颐、王子华等20人。
没有挖到底的继续下掘,对揭露出来的进行解剖,以了解内涵及层积。
那时,由于没有想到以后要在这里建博物馆,所以将几处的房址一块块地解剖掉了,大型房子除将两个柱础全部取出土拿回外,将房屋都一段段地切开,将其残块堆到已挖过的地方,将圆形房子一片片地取下,将居住面也一层层剥开,整个房子被化整为零,使我们了解到房子内部的结构和包含物。
虽在当时看来是应该这样做的,但在博物馆成立后,要恢复大房子的原貌就难了,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遗憾,现在想起来都遗憾的很。
1955年春,西安组织人力在半坡遗址北部,就是半坡聚落的墓葬区取土,修建浐河桥东岸至国棉三厂约1000米长得路,取土范围相当大,取土高程达1.5-2米,万余方土方。
那时,我在西安整理半坡遗址发掘报告,事先并不知道修路取土问题,发掘也没有将遗址范围探清。
那年5月初,听人说在半坡遗址起土挖出来一批尖底瓶。
我闻讯赶到后吃了一惊,挖掘的土方中有零星的陶器和残断人骨,地上也散落着陶片和骨骼,一看确属半坡聚落的墓葬区。
于是我当即向取土工地负责人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后,让人停了工改在另一处取土。
我们停止了部分室内整理工作,带了几个熟练技工赶赴工地,先进行墓葬的清理工作。
当时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所是王伯洪同志负责,夏鼐所长兼主任,我当即给夏鼐先生写了一封信,建议继续发掘。
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一方面配合基建工程,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
记得他当时的回信原文是:
“半坡遗址墓葬区遭到破坏,很可惜,要赶快派人进行配合发掘。
当然可以叫石兴邦同志继续发掘半坡的工作。
”王洪波同志接信后立刻通知我负责这项工作。
我接到通知后,当即停止了资料整理工作,带上杨建芳、金雪山、余万民、牛永禄等同志赶到工地,正式开始发掘,不长时间,我们就将残留的100多座墓葬清理出来,并全部保留下。
负责筑路的领工同志看了后,连连叹息道:
“唉,真可惜,将这全部发掘出来,绘成一个完整的图,多有价值”。
当时大概破坏了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样子。
不仅如此,这次筑路还破坏了墓葬区,还有聚落北部的居民区,至少将一座双连灶的大房子推掉了。
大量的遗迹暴露在外面,大房子中的双连灶、两个火烧的圆圈清晰可见,这起事故的教训很深刻。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都很难过。
汉唐网:
通过这次访谈,也能让更多的年轻考古学者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半坡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当时建馆的情况么?
石兴邦:
谈到建立么,要说说1955年6月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盛会,在那次会上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等4个部。
这次学部大会除成立有关机构外,各学部开展了学术讨论,讨论的范围很广,包括发展科学的方针、政策和学术成果。
考古方面提出将“半坡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意义”作为考古学一个新发现和成果。
考古成果由我在会上宣读。
考古所尹达、夏鼐和我被列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郭宝钧、陈梦家等老科学家都是列席大会的,当时出席大会的都是学部委员和有关单位领导,列席大会的著名学者不少。
我在历史组,当时考古就包括在历史组内,做了汇报,大多数数学者感到新奇有趣,提出不少问题。
考古方面的专家王天木做了评价和肯定,顾颉刚先生问得很仔细,个别同志也讲了不同的意见。
我非常喜欢大会的那种学术气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十分融洽热烈,许多老前辈和著名学者们做了精彩的发言,使我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受益良多。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大家各做各的研究,互相之间,也不怎么交流,遇到学术研讨会也不怎么发言。
到了那年的秋天,北大考古专业班学生32个人来半坡实习,由李仰松先生带队,开展遗址部分的发掘。
这些年轻的学生,文化程度相当,事业心强,学习热情也高,还很勤快,发掘出的都是重要遗迹,房屋、窑穴、瓮棺葬和大批的工具和陶器,为半坡博物馆的建立作了不少基础性工作。
这批学生当时还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就是在发掘现场举办一个展览会,因为工地紧邻着大路,已经吸引了不少群众来参观。
我们经过研究,同意了学生们的意见,展览分为两部分开始进行,一是在发掘现场由学生现场讲解,再是在墓葬区的断崖下划出30多米长的一段,挂了些图片和绘图,由学生轮流讲解。
没想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连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领导陈柏仁等老前辈也来参观,并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支持。
展会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时间,参观的人数很多,有附近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累计下不数十万人。
还有不少来访的外国人,多数是东欧人,在华工作的苏联和东欧专家。
一位教育部工作的苏联高级顾问在西安工作期间也来参观,他回北京后,向教育部说了有关情况,引起了教育部长钱俊瑞的关注,并专门带人来半坡视察后,要了30多张遗址和器物照片,回去要给总理汇报,并嘱咐我们好好保护。
也就是因为那次展览,为半坡遗址扩大社会影响,建立博物馆,制造了舆论,打下了群众基础。
那年的冬天,中国科学院评奖时,半坡遗址的发掘成果得了一等奖,发了500元奖金,我一半给了北大的学生,一半给了考古队的同志们。
到了1956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总编邓拓同志从苏联访问回国,路过西安,特来半坡遗址参观。
见到我时,他第一句话就说:
“石兴邦同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那时,有些发掘出的房屋是用芦草席覆盖的,我一个个揭开让他看,后来还带着他看了些出土文物,他询问我半坡遗址在史籍上有无记载,我说史前的东西没有,他还让我查查《山海经》看看有没有。
他临走时表示,以后若有新发现,还想来看。
过后,半个月左右,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有些新发现,并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过了20天,他回信提出要将发现的情况和意义撰写成稿,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
我就写了一篇《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的生活场景》,5000多字,给他寄去,我还记得是11月9号那天就全文刊载出来了。
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读者来信,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时隔好久,我们在侯马开会时,我与谢元璐同志谈起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工作问题时,他告诉我说:
“你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国家文物副局长王冶秋很赞赏,认为这是考古界多年来最好的一篇文章,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
既有学术价值,也有政治意义。
”
到了195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