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曾亦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docx
《思想曾亦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思想曾亦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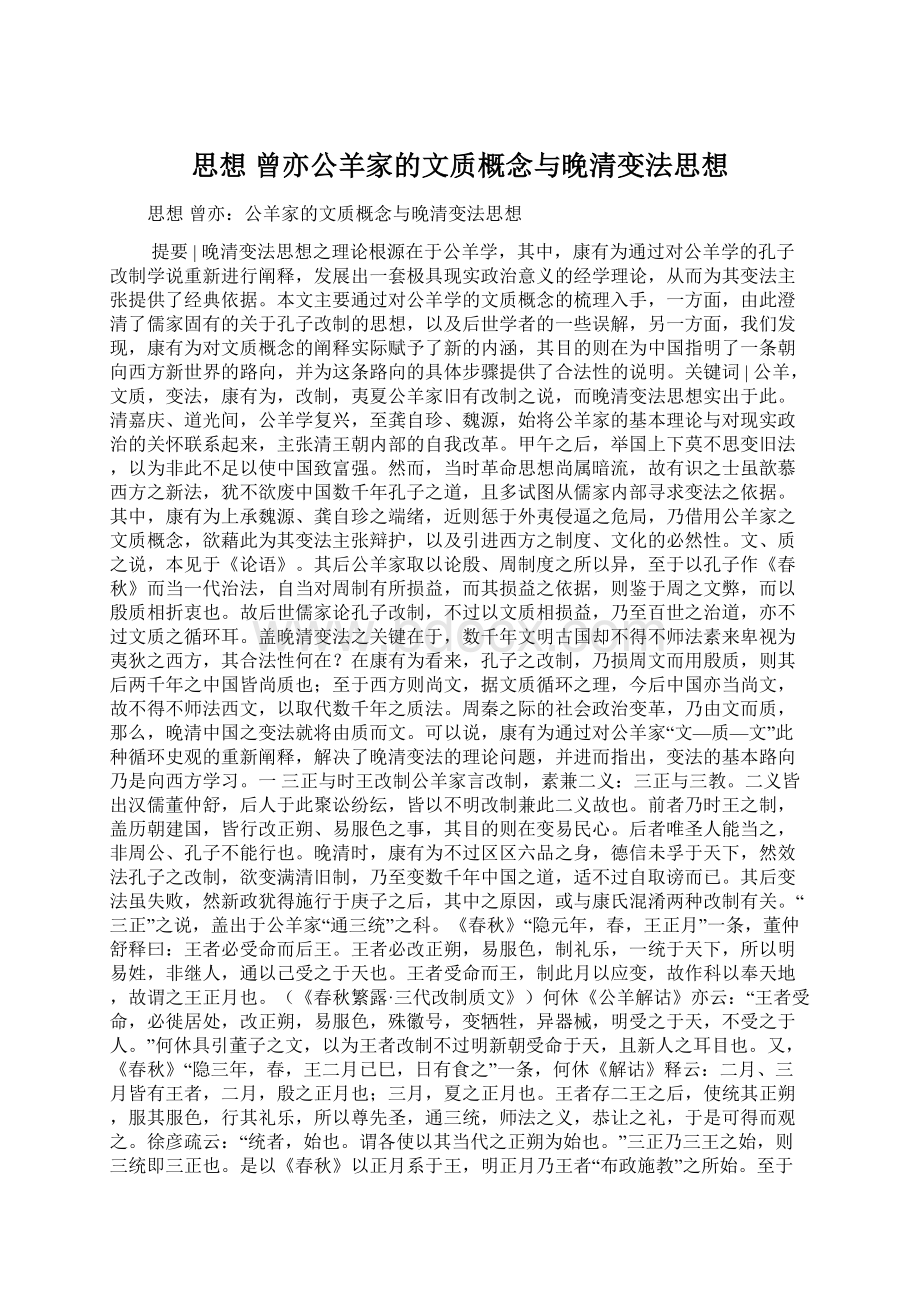
思想曾亦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
思想曾亦:
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
提要|晚清变法思想之理论根源在于公羊学,其中,康有为通过对公羊学的孔子改制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发展出一套极具现实政治意义的经学理论,从而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经典依据。
本文主要通过对公羊学的文质概念的梳理入手,一方面,由此澄清了儒家固有的关于孔子改制的思想,以及后世学者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康有为对文质概念的阐释实际赋予了新的内涵,其目的则在为中国指明了一条朝向西方新世界的路向,并为这条路向的具体步骤提供了合法性的说明。
关键词|公羊,文质,变法,康有为,改制,夷夏公羊家旧有改制之说,而晚清变法思想实出于此。
清嘉庆、道光间,公羊学复兴,至龚自珍、魏源,始将公羊家的基本理论与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联系起来,主张清王朝内部的自我改革。
甲午之后,举国上下莫不思变旧法,以为非此不足以使中国致富强。
然而,当时革命思想尚属暗流,故有识之士虽歆慕西方之新法,犹不欲废中国数千年孔子之道,且多试图从儒家内部寻求变法之依据。
其中,康有为上承魏源、龚自珍之端绪,近则惩于外夷侵逼之危局,乃借用公羊家之文质概念,欲藉此为其变法主张辩护,以及引进西方之制度、文化的必然性。
文、质之说,本见于《论语》。
其后公羊家取以论殷、周制度之所以异,至于以孔子作《春秋》而当一代治法,自当对周制有所损益,而其损益之依据,则鉴于周之文弊,而以殷质相折衷也。
故后世儒家论孔子改制,不过以文质相损益,乃至百世之治道,亦不过文质之循环耳。
盖晚清变法之关键在于,数千年文明古国却不得不师法素来卑视为夷狄之西方,其合法性何在?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之改制,乃损周文而用殷质,则其后两千年之中国皆尚质也;至于西方则尚文,据文质循环之理,今后中国亦当尚文,故不得不师法西文,以取代数千年之质法。
周秦之际的社会政治变革,乃由文而质,那么,晚清中国之变法就将由质而文。
可以说,康有为通过对公羊家“文—质—文”此种循环史观的重新阐释,解决了晚清变法的理论问题,并进而指出,变法的基本路向乃是向西方学习。
一三正与时王改制公羊家言改制,素兼二义:
三正与三教。
二义皆出汉儒董仲舒,后人于此聚讼纷纭,皆以不明改制兼此二义故也。
前者乃时王之制,盖历朝建国,皆行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其目的则在变易民心。
后者唯圣人能当之,非周公、孔子不能行也。
晚清时,康有为不过区区六品之身,德信未孚于天下,然效法孔子之改制,欲变满清旧制,乃至变数千年中国之道,适不过自取谤而已。
其后变法虽失败,然新政犹得施行于庚子之后,其中之原因,或与康氏混淆两种改制有关。
“三正”之说,盖出于公羊家“通三统”之科。
《春秋》“隐元年,春,王正月”一条,董仲舒释曰: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何休《公羊解诂》亦云:
“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何休具引董子之文,以为王者改制不过明新朝受命于天,且新人之耳目也。
又,《春秋》“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一条,何休《解诂》释云: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
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
徐彦疏云:
“统者,始也。
谓各使以其当代之正朔为始也。
”三正乃三王之始,则三统即三正也。
是以《春秋》以正月系于王,明正月乃王者“布政施教”之所始。
至于政教之始,乃取法乎物之始,即物之牙色也,故三王所尚有黑、白、赤之不同,而政教所施亦有三者之不同。
董仲舒又曰: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
曰:
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
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
顺数四而相复。
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
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
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
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
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
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
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
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
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
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
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三代改制质文》)董仲舒历陈上古帝王改制之事,至于《春秋》,亦有“应天作新王之事”,王鲁、新周而故宋,当一代之黑统,种种制度施设,皆不同于周制。
可见,每当一代王朝建立,皆有改制之事。
盖三正之说,乃承《公羊传》“新周故宋”一语而来。
何休以新周、故宋、《春秋》当新王为三科之一,此即通三统之例也。
《公羊传》无明文,然《解诂》所发此义,似与经、传文不合,颇嫌牵强,故后人诋之汹汹。
晋王接首揭此议,谓“黜周王鲁,大体乖硋”。
(《晋书·王接传》)其后,宋苏轼、陈振孙皆祖此说,谓《公羊传》无明文,甚至以何休为《公羊》罪人。
清人苏舆谓董仲舒“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证兴礼之意”,实与何休之意不同。
公羊家之“通三统”,虽语涉玄怪,然其精神则甚为显豁。
概言之,则有二端:
王者必尊贤,尊贤则所以法古也,法古所以奉天也,故存往昔故事以备取法,此其一也。
又,王者尊贤不过二代,其封二王后为大国,则自有亲、有故、有绌。
公羊家以《春秋》当一新王,则周为胜国,于周为黜,于鲁为亲,于三统之序则为新;至于宋,为殷后之大国,于孔子为故,于新封之周为故,于三统之序为故;而夏则绌,不为师法之礼矣。
此犹古礼之祭祖,新死者为鬼,此为新周;新鬼于生者为亲,旧鬼自疏,此为故宋;天子止立四亲之庙,庶人叙亲亦不过高祖,则高祖以上之旧鬼不享祭矣,此为绌夏。
此非独新朝有亲,有故,有绌,祭祀亦然,至于新君即位,例有封赏,而皆循此亲、故、绌之义焉。
可见,通三统之义至为明显,后世朝廷亦多能行此义者。
清人苏舆即以为,“汉自为一代,上封殷、周,不及夏后,正用此绌夏、故宋、新周之说。
……我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致奠明陵,谕曰:
‘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寢。
’……舆谓绌夏、亲周、故宋,犹今云绌宋、新明、故元。
古者易代则改正,故有存三统、三微之说,后世师《春秋》遗意,不忍先代之遽从绌灭,忠厚之至也。
”[1]苏舆虽斥清儒之附会,然其所论,皆本诸董义,颇不类后人牵引《穀梁》、《左氏》,以弹正公羊家之说。
然而,“三正”说包括的改制之义,不过表明新王朝的合法性而已,即通过改正朔而表明“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
(《春秋繁露·楚庄王》)苏舆极申此说,以为《春秋》无改制之义,至于董仲舒所论,不过有为而言也。
汉承秦兴,未遑改制之事,制度典章一依秦旧,贾谊多讥其因循,盖以此也。
设若苏舆所言,则董仲舒倡言改制,盖托圣人之《春秋》为言,以讽汉廷改制也。
董氏为汉儒宗,地位巍巍,诚非后汉何休可比,是以晚清维新派尊董以改制,而保守派乃操戈入室,亦力陈董说之本意,而将改制之妄说归咎于何休。
然董仲舒谓孔子受命作《春秋》,实有改制之义。
董氏曰: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
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
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也。
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
(《春秋繁露·符瑞》)董氏言之凿凿,苏舆乃弥缝其说曰:
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后能改元立号,制礼作乐,非圣人所能托。
道不变者也,周德既弊,而圣人得假王者以起义而扶其失,俟来者之取鉴。
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犹云为后王立义尔。
[2]盖自苏舆视之,孔子改制,不过托乎《春秋》以立义耳,非实改其制也。
“三正”本指夏、殷、周三代之历法,即周以夏之十一月为正月,殷以十二月为正月,而夏则以十三月为正。
每当新王朝受命,必确定新年之岁首,此即“改正朔”。
其后,秦以十月为岁首,即用此三正循环之说也。
新王受命,不独改正朔,至于服色、徽号、牺牲、器械等制度,莫不有变异,此为王者之改制。
其用意则在表明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即非受之于人,而是受之于天。
显然,此种内涵的改制绝非作为素王的孔子所能为,唯开国之君始得为之。
然而,改制尚别有一义,即三教之循环。
二三教与文质再复新王受命改制,不过就其表言之,至其里,则三代之循环,不过文质再复而相损益耳。
公羊家改制之说,此为另一义也。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三统循环如此。
至于三代之制度,则实然有别,此所以有三教之不同也。
董仲舒曰:
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鸾舆尊,盖法天列象,垂四鸾,乐载鼓,用锡舞,舞溢员;先毛血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故立嗣与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亨,妇从夫为昭穆;制爵五等,禄士三品;制郊宫,明堂方,其屋卑污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丝,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鸾舆卑,法地周象载,垂二鸾,乐设鼓,用纤施舞,舞溢方;先亨而后用声;正刑天法;封坛于下位。
(《三代改制质文》)可见,董仲舒明言孔子改制,不独不从周,实损益四代而为新制也。
后儒颇攻何休误读董仲舒,实未得其情。
至晚清,康有为极推崇《三代改制质文》一篇,曰:
孔子作《春秋》改制之说,虽杂见他书,而最精详可信据者莫如此篇。
称《春秋》当新王者凡五,称变周之制,以周为王者之后,与王降为风、周道亡于幽、厉同义。
故以《春秋》继周为一代,至于亲周、故宋、王鲁,三统之说亦著焉,皆为《公羊》大义。
其他绌虞、绌夏、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听孔子所推。
姓姚、姓姒、姓子、姓姬,皆听孔子所象。
白黑、方圆、异同、世及,皆为孔子所制。
虽名三代,实出一家,特广为条理以待后人之行,故有再、三、四、五、九之复。
……惟孔子乃有之。
董子为第一醇儒,安能妄述无稽之谬说?
此盖孔门口说相传非常异义,不敢笔之于书。
故虽《公羊》未敢骤著其说。
至董生时,时世殊易,乃敢著于竹帛。
故《论衡》谓孔子之文传于仲舒也。
苟非出自醇实如董生者,虽有此说,亦不敢信之矣。
幸董生此篇犹传,足以证明孔子改制大义。
[3]可见,在康有为看来,公羊家改制之说,实出自孔子之口说相传,至汉时始得著于竹帛。
又,《汉书·董仲舒》引《举贤良对策》云: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
孔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仲舒既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不变,又以三王政教有文质之不同。
尧、舜、禹三圣之禅让,有改正朔、易服色之变,然此乃治世之相继,故无文质损益之变。
若夏、殷、周三王之革命,则乱世之相继也,故有文质损益之改。
《春秋》之作,本拨乱世而反诸正也,是以其言改制,实在文质损益方面。
仲舒此论足为后世变法、革命之说张本。
至清末苏舆,有感于康有为轻言改制而致清社倾覆之祸,作《春秋繁露义证》,专明改制之旨仅止于改正而已,而不取乱世救弊之义。
苏舆以为皆清儒解经之误使然,甚至其将病源上溯至何休,以董子之说正《公羊》之本来面目。
公羊家本以文质明三代之不同,其后又有三教之说。
《白虎通·三教》云:
王者设三教何?
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
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
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
继周尚黑,制与夏同。
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
[4]此以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为三教也。
然三教之说,实本诸《论语》三代文质损益之说,如《雍也篇》云: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为政篇》云: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又云: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可见,汉人三教之说,诚渊源有自也。
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实集两汉论文质改制之大成。
如其释《公羊传》文“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一语云:
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
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
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
文家为周家,质家为殷家,《春秋》继统之法盖从周文也。
又,桓十一年,郑忽出奔卫。
《公羊传》曰:
“《春秋》,伯子男一也。
”《解诂》云:
《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
……王者起,所以必改质文者,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
天道本下,亲亲而质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烦。
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质而亲亲。
及其衰敝,其失也亲亲而不尊。
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
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亲,故复反之于质也。
质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
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
合三从子者,制由中也。
此明文质迭用,皆所以救前敝也。
又,隐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公羊传》曰:
“母弟称弟,母兄称兄。
”《解诂》云:
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
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
而隐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解诂》云:
滕序上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先封同姓。
此二段皆明《春秋》之从殷质也。
故《春秋》改制,明三教之所以不同,或从殷,或从周,或损周文从殷质,或变殷质用周文,其实皆不过承衰救敝而已。
可见,汉人由三教而言改制,唯圣人能当之,即因前代之利弊而有所损益,如是而造就一代新制。
改制之说,虽出于公羊家言。
盖《公羊》推孔子为素王,故所作《春秋》行改制之实,而当一代新王矣。
汉人习于此说,遂便孔子为汉制法,其所改者,盖损周文以益殷质而已。
汉末郑玄折衷今古,其所注礼尤采此说,即以合乎《周礼》者为周制,其不合者为殷制。
历代制度之不同如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确实有改制之实焉。
三以夷变夏与以夏变夷驯至晚清,中国当衰微之际,故不得不用西法。
用西法,则不得不变更古制,此晚清变法之所由起也。
康有为谓“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5],此说可谓得圣心焉。
虽然,中国自古又有夷夏外内之说。
盖中国素以夏自居,而有变夷之道;今若参用西法,甚至以西法为上,则不免以夷变夏矣。
故康有为以三世说与内外说参比而为论,即以吾国居据乱世而为夷,西方处升平、太平世而为夏,则中国若变法,亦以夏变夷也。
其后,康有为又推衍《春秋》三世之说,以孔子本有大同之说,则西法亦不出吾儒范围,是以吾国虽用西法,亦不过祖述孔子小康、大同之说耳。
因此,梁启超论康有为之改制曰: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
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
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
喜言张三世。
三世者,谓据乱世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
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6]盖通三统明制度当随时因革,而张三世则明因改制而进化,因此,自梁启超视之,康有为言改制变法,实出于公羊家通三统、张三世之旧论也。
康有为欲变之古制实有二:
其一,有清一代祖宗之成法;其二,数千年一统之法。
其中,祖宗成法尤关系国本,稍有不慎,即致国家倾覆。
康有为乃托于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以变之,谓“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7]又假康、乾间变易八贝勒议政旧制之成例,以为祖宗之法亦无有不可变者,今当国运颠踬之时,祖宗之地既不可守,不若变祖宗之法以济时艰。
其时,守旧者又多托圣人之法以阻挠变法。
康有为乃极言数千年一统之法,非列强竞争之世所宜,“方今当数千年之变局,环数十国之觊觎,既古史所未闻,亦非旧法所能治”[8],“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9]。
可见,康有为以中国数千年皆处据乱之世,则其所欲变者,非止有清一代之法,实欲变数千年之法也。
当时之守旧派,如朱一新攻康有为,谓其实欲以夷变夏也,“阳尊孔子,阴祖耶苏”[10],“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11]。
对此,康有为说道:
其地之大,人之多,兵之众,器之奇,格致之精,农商之密,道路邮传之速,卒械之精炼,数十年来,皆已尽变旧法,日益求精,无日不变,而我中国尚谨守千年之旧敝法。
[12]康有为以西夷已进乎升平、太平之世,今之夷实不同于古之夷,故不可纯用“以夷变夏”之旧论视之。
朱一新又以夷夏伦理纲常不同,而康有为乃列举法国刑法、民法之条目,以证夷人亦讲礼义廉耻,与吾国不异,“至于三纲五常,以为中国之大教,足下谓西夷无之矣,然以考之则不然”,“至于人心风俗之宜,礼义廉耻之宜,则《管子》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有国有家,莫不同之,亦无中外之殊也”[13],又谓“今日泰西之法,实得列国并立之公理,亦暗合吾圣经之精义,不得谓之西法也”[14]。
康氏又自叙其心意,谓反对变法者“恶夷狄之名,不深求中外之势,故以西学为讳”[15]。
可见,康氏盖本《春秋》之旨,亦持文化普遍主义之立场,故不以夷、夏判然有别也。
其后,康门弟子徐勤亦借《春秋》以破夷夏之大防:
《春秋》无通辞之义,《公》《穀》二传未有明文,惟董子发明之。
后儒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知此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
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
呜呼!
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
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
若无董子,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
[16]盖汉代公羊家论夷夏之别,本有二义:
其一,严夷夏之防,盖为攘夷张目也;其二,远近大小若一,故有进退夷夏之法,而为大同修涂也。
宋儒孙明复、胡安国以夷狄之势凌逼中国,乃专取夷夏大防为论。
清代公羊家则反是,亦偏取一说,其初言满汉大同,至康有为,则倡言中外大同矣。
董子有“《春秋》无达辞”一语,盖泛论条例之有变也。
康有为则举夷、夏之辨而论之,以为夷、夏之辞皆从其事,非专有所指也。
是以夷狄有礼义,则予以夏辞;诸夏无礼,则夺以夷辞。
《春秋》书“晋伐鲜虞”,盖以晋伐同姓,故退以夷狄之也。
宋儒于夷狄之创痛尤深,故严夷夏之防,遂以夷夏为定名。
谭嗣同亦据《春秋》为论,然别创新旧之义,以论夷夏之进退。
其《湘报后叙》有云:
《春秋传》曰:
中国亦新夷狄。
《孟子》曰:
亦以新子之国。
新之为言也,盛美无憾之言也。
而夷狄、中国同此号者何也?
吾尝求其故于《诗》矣,周之兴也,僻在西戎,其地固夷狄也,自文王受命称王,始进为中国。
秦虽继有雍州,春秋人不以所据之地而不目之为夷。
是夷狄中国,初不以地言。
故文王之诗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旧者夷狄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
新者忽旧,时曰新夷狄;旧者忽新,亦曰新中国,新同而所新者不同。
危矣哉!
己方悻悻然自鸣曰守旧,而人固以新夷狄新之矣。
是夷狄中国,果不以地言,辨于新,辨于所新者而已矣。
然仅言新,则新与所新者亦无辨,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旧,至明日而又已旧,鸟足以状其美盛而无憾也。
吾又尝求其故于《礼》与《易》矣,《礼》著成汤之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孔子之赞:
日新之谓盛德。
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
[17]若谭氏之言,则西方不恒为夷狄,而今乃为中国矣;而中国不恒为中国,而今乃为新夷狄矣。
揆诸《春秋》以夏变夷之说,则此时中国方为夷狄,其用西法而改用新制,实不违《春秋》之义。
谭氏之说,盖欲藉经说以杜反对者之口耳。
梁启超则径谓“以夷变夏”为是。
其《变法通议》云:
孔子曰:
天子失官,学在四彝。
《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
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
……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
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18]礼失求诸野,则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矣,其学于夷狄者,殆亦古圣贤之道焉。
《春秋繁露·竹林》云:
“《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
引之鲁,则谓之外。
引之夷狄,则谓之内。
”徐勤发挥其师说曰:
引之鲁,则谓之外。
引之夷狄,则谓之内。
内外之分,只就所引言之耳。
若将夷狄而引之诸地、诸天、诸星之世界,则夷狄亦当谓之内,而诸地、诸天、诸星当谓之外矣。
内外之限,宁有定名哉?
[19]则今日之西夷,就地球言之,亦可谓之内也。
今日有“地球村”之说,则以内外如一矣,如是而为大同。
故徐勤释《春秋繁露·奉本》“远夷之君,内而不外”一语曰:
“外而变内,是天下无复有内外之殊矣。
圣人大同之治,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
。
”[20]可见,康门弟子皆不讳言变法乃“以夷变夏”,因此,保守派的叶德辉乃攻击南海,谓“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21]。
近人钱穆亦有类似评价,谓“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
是长素尊孔特其貌,其里则亦如彼”[22]。
康有为又以文、质别夷夏。
公羊家素以孔子损文用质,则《春秋》盖取质法也。
其后董子亦谓《春秋》为质法,如“承周文而反之质”(《春秋繁露·十指》),“此《春秋》之救文以质也”(《王道》),“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玉杯》)。
然康氏犹别自有说,曰:
天下之道,文质尽之。
然人智日开,日趋于文。
三代之前,据乱而作,质也。
《春秋》改制,文也。
故《春秋》始义法文王,则《春秋》实文统也。
但文之中有质,质之中有文,其道递嬗耳。
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皆升平世质家也。
至太平世,乃大文耳。
后有万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
[23]公羊旧论素以《春秋》为质家法,今康氏据人类进乎文明之义,谓《春秋》法文王,乃文家法。
又以王朝之更迭,为一文一质之递嬗,故清世为质家,而康氏之变法犹效孔子改制,抑或以文王自居也。
盖康氏所谓文家法,多取文明进化之意,“夫野蛮之世尚质,太平之世尚文。
尚质故重农,足食斯已矣。
尚文故重工,精奇瑰丽,惊犹鬼神,日新不穷,则人情所好也”。
[24]又以孔子为文王,盖因文明道统在兹,斯为教主也,“盖至孔子而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后世,乃为人道之始,为文明之王。
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
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
……盖为孔子上承天命,为文明之教主、文明之法王,自命如此,并不谦逊矣。
”[25]康氏以孔子不独传承周文,至谓中国数千年文明,实自孔子而开辟也。
此说虽属不经,尤其未必与公羊家之“文”义相类,然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中国将变法而使文明进步也。
四东西优劣与晚清思想之不同路向戊戌变法之重心在政治方面,即以西方之君主立宪取代中国数千年之君主专制。
然而,庚子以后,康有为乃追述魏源“师夷长技”之论,主张师法西方之物质文明。
1904年,康有为在其《物质救国论》一书中,强调西方文明之优势全在物质方面,至于中国之衰弱,则不过出于科技之不发达,因此,中国欲求民族之生存与强大,惟一途径只能是学习西方之“奇技淫巧”。
此种立场似乎回到了早先洋务派的立场,而与后来的西化论有着根本区别。
康有为虽然根本上是一“世界主义者”[26],不过与西化论不一样,尤其到了晚年,更多强调本民族自身的特殊性。
《春秋》谓太平世乃“远近大小若一”,此说对南海影响尤深,致使其自始至终皆持一世界主义立场,主张人类存在着某种普遍价值。
譬如,《孟子》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