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弟子们的哲学思想.docx
《孔子和弟子们的哲学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孔子和弟子们的哲学思想.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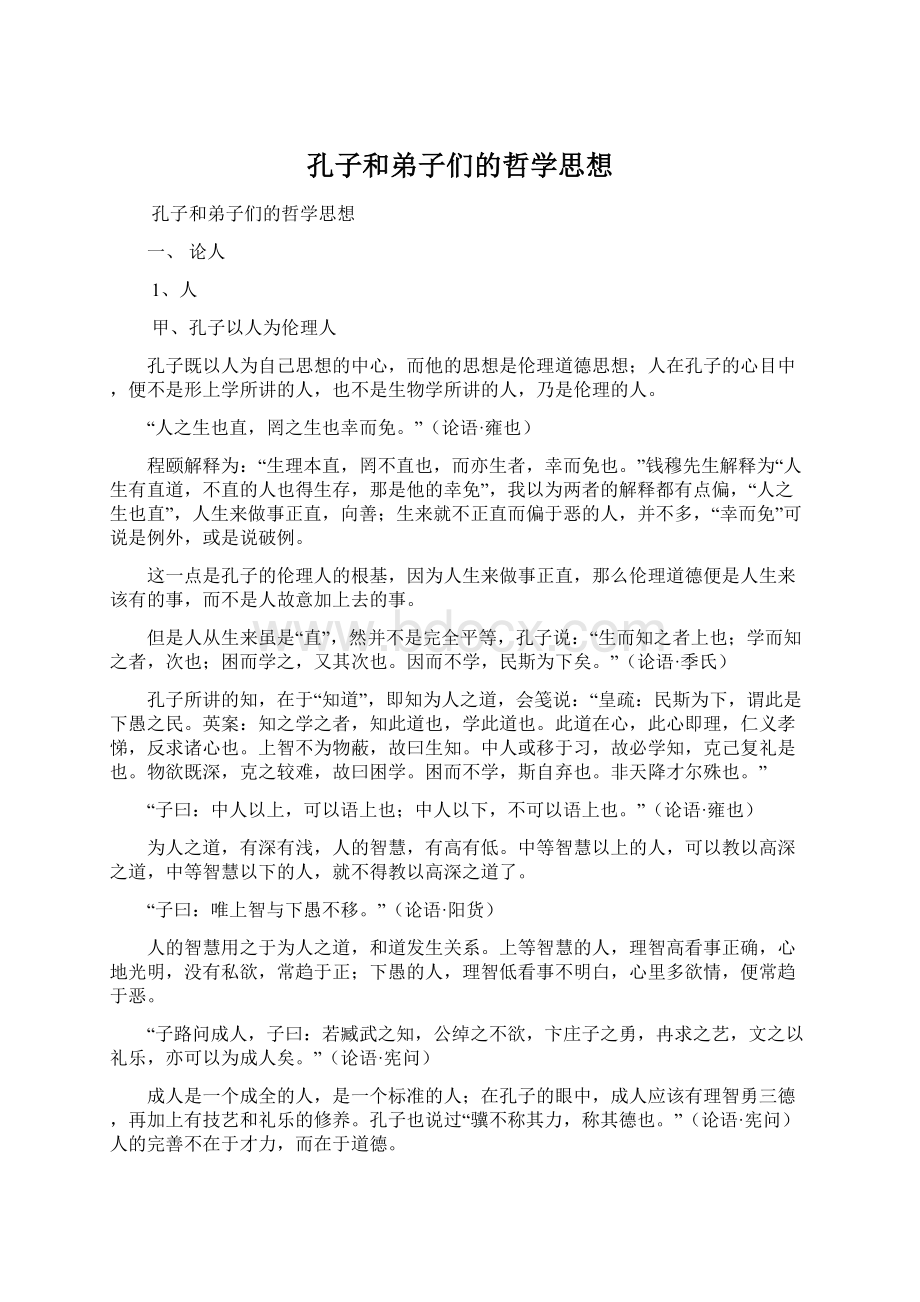
孔子和弟子们的哲学思想
孔子和弟子们的哲学思想
一、论人
1、人
甲、孔子以人为伦理人
孔子既以人为自己思想的中心,而他的思想是伦理道德思想;人在孔子的心目中,便不是形上学所讲的人,也不是生物学所讲的人,乃是伦理的人。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论语·雍也)
程颐解释为: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也。
”钱穆先生解释为“人生有直道,不直的人也得生存,那是他的幸免”,我以为两者的解释都有点偏,“人之生也直”,人生来做事正直,向善;生来就不正直而偏于恶的人,并不多,“幸而免”可说是例外,或是说破例。
这一点是孔子的伦理人的根基,因为人生来做事正直,那么伦理道德便是人生来该有的事,而不是人故意加上去的事。
但是人从生来虽是“直”,然并不是完全平等,孔子说: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因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孔子所讲的知,在于“知道”,即知为人之道,会笺说:
“皇疏:
民斯为下,谓此是下愚之民。
英案:
知之学之者,知此道也,学此道也。
此道在心,此心即理,仁义孝悌,反求诸心也。
上智不为物蔽,故曰生知。
中人或移于习,故必学知,克己复礼是也。
物欲既深,克之较难,故曰困学。
困而不学,斯自弃也。
非天降才尔殊也。
”
“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为人之道,有深有浅,人的智慧,有高有低。
中等智慧以上的人,可以教以高深之道,中等智慧以下的人,就不得教以高深之道了。
“子曰: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人的智慧用之于为人之道,和道发生关系。
上等智慧的人,理智高看事正确,心地光明,没有私欲,常趋于正;下愚的人,理智低看事不明白,心里多欲情,便常趋于恶。
“子路问成人,子曰:
若臧武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成人是一个成全的人,是一个标准的人;在孔子的眼中,成人应该有理智勇三德,再加上有技艺和礼乐的修养。
孔子也说过“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人的完善不在于才力,而在于道德。
君子和小人,在古代为君王和平民的称呼,为社会上的制度。
孔子把君子和小人改为品德的高低,品德高者为君子,品德低者为小人。
这两个名词乃成为中国社会的传统称呼,在人们心中看为很严重的伦理评判。
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里,人是一个伦理人,人的价值由伦理道德而定,人的生活也以伦理道德为中心。
乙、礼记以人为天地之秀气
礼记的礼运篇说: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
这种思想,继承易经的思想,易经以人和天地为三才,人代表天地间的万物。
易经又以万物由阴阳相结合而成,以天地代表阴阳,常说天地相交而化生万物。
但是五行的思想在五行里还没有出现,要到战国时才盛行,所以在孔子以后,取代了八卦。
易经以阴阳变化而成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卦代表物。
战国时代的思想,以阴阳变化成五行,五行相合而成物,不再讲卦;讲卦时,专为卜吉凶。
礼运篇有战国时期的思想,以人为五行这秀气所成。
“天地之德”,天地代表乾坤,人具有乾坤之德,乾刚坤柔。
“阴阳之交”,阴气和阳气的交会,五行的每一行,都由阴阳的结合交会而成。
“鬼神之会”,若按汉朝儒家和宋朝理学家的思想,鬼为魄,神为魂,人具有魂魄,故称为鬼神之会。
但按易经的思想,鬼神代表灵明,代表动作的神妙,人为鬼神之会,指着人具有灵明之心,人心的活动神妙莫测。
“五行之秀气”,五行之秀气为金木水火土;然而所谓秀气,则又是一个新名词。
注疏说秀是秀异,秀气为气性之纯,气纯则没有杂物,不杂而纯则清,宋朝理学家乃以秀气为气之清者,清则虚灵,人乃有鬼神的灵明。
但是人之生,不仅是有灵明,同时也有感官,所以说“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然而说:
“五行之端也”,则和五行之秀气,似乎有些矛盾,五行的开端不能是五行的极端之秀气。
我们便要从另一方面去解释;因为在这一段里,礼运讲人的七情,以五行、四时,十二月、配声味色,和七情发生关系,乃说: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以情之动,有似于天地之动,人之心乃得天地之心而为心。
这一点也是易经的思想。
礼运接着说:
“五行之端也”,在上面曾说:
“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
”后面也说: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
”这个端字,不是开端之端,乃是“事”,心之大端即是心之大事,或是心之重点。
“五行之端”,解为五行之重点。
但端也可以解为动之端,欲恶为心动之端,人为五行结合之端。
礼运篇虽为五行之秀气,同时也以人为伦理人,因为礼运全篇讲礼义。
在礼记的另一篇中,即曲礼中说: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曲礼·上)
人是人而不是兽,人的特点,在于知礼义。
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伦理道德。
人的一生,由少到老,生理上变迁很大;曲礼把生理变迁和伦理义务相联:
“人生十年曰幼,学。
二十曰弱,冠。
三十曰壮,有室。
四十曰强,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传。
八十九十曰耄。
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颐”(曲礼·上)
少壮老在生理体力上有分别,在伦理义务上也有分别;少年是求学的预备时期,壮年是负责做事的时期。
老年是受人尊敬的时期。
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里,从古到今,流传不绝。
大载礼/本命篇从生理方面论人,孔子家语本命解篇以大载礼的话,为孔子的话。
“人生而不具者五:
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
三月而昀,然后能有见。
八月生齿,然后食,期而生膑,然后能行。
三年合然后能言。
十有六情通,然后能化。
阴穷反阳,阳穷反阴。
辰故阴以阳化。
阳以阴变。
……二八十六,然后情通,然后施行。
女……二七十四,然后其化成。
”(大载礼记·本命第八十)
2、人性
甲、孔子论性
论语中谈性的问答,可以说是没有,而且弟子记述孔子的教育方法: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治长)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诗书礼乐便是夫子之文章。
文章不指着文字的作品,乃指着一个人在人格上有端庄文雅的仪表。
“性与天道”,性是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天道是天的运行之道;这两点在易传里有所说明,在论语里,则没有说明。
这是孔子教育的方法,从伦理道德方面教门生做一个成人,不从形上学方面讲人之所以为人。
但是“不可得而闻”,并不是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只是说不容易听到老师讲论这事,也是说虽然听了也不容易懂。
若是易传是孔子作的,而孔子晚年学易而作易传,当然他就给门生们讲人性和天道了。
“性相近,习相远。
”(论语·阳货)
性相近,即是凡是人,在生来的人性方面,彼此是相近,即相似的;从来因着各人所染的习惯,彼此在行为上便不相同,彼此离得远了。
这个性字,为人生来所有的性,指着人心生来所有的倾向,在人心生来所有的倾向上,凡是人都是相近的。
论语的性字,没有朱熹注疏所讲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意义,也不像程颐所说的性之本,为理,人人相同而不能说相近。
孔子说性,不是从形上学的理去说性,这是后来的思想;孔子是从人的行为方面去说性,人在行为上若按人心生来的倾向,大家都相近。
后来孟子讲性,就是从这方面去讲。
孟子讲性善,论语没有性善的主张,大学、中庸也没有明白地提出;但是在谈论伦理人时,孔子和门生都假定人性是善的。
论语上说:
“人之生也直。
”
然而性善的观念,在论语里不但不明显,而且也不稳定,因为论语里有“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主张。
上智固然是性善,下愚则似乎是性恶了。
当然,下愚也可以从理智力和欲情两方面去解释,不牵涉到人性,可是“不移”两字,真真的牵涉到性字。
无论如何,孔子在论语里,没有正式讲论人性;我们便不能根据偶然提到人性的一句话,来说明孔子对人性的思想。
我们只能说:
孔子知道4有人性,人性是人心生来所有的倾向,也是人之活动的根据。
乙、大学·中庸论性
由性字方面去看论语、中庸、大学和易传,我们可以看出论语对性字的解说最简单,在时间上应为最早,中庸和大学的性字,意义较深刻,然而尚在伦理范围内,在时间上必定在论语以后,易传的性字,已经进入形上学范围,这是因为易经一书的性质为宇宙论,但在思想变迁上,似乎应在大学和中庸以前,虽然也可以在同一时代发展。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第一章)
中庸不从生字去论性,便是不从人心倾向方面去论性,而从形上方面去论性,以性为天命。
这一点应来自易传。
人性是什么呢?
是人所有的天命。
天命是什么?
天命为上天之命,书经和诗经都以上天造生人物,对于人物定了规则。
这种规则为人物运动的规律,既然是上天所定,便称为天命,。
人性就是上天为人的活动所定的规则。
易经称人的活动规则为人道,宇宙运动变化的规则称为天道,宋朝理学家称为理或天理。
中庸以人所受于天所定扔规则为性,按照人性去活动,称为人生之道,即是人道,指导人遵照人生之道去修身行善,就是教育。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第二十二章)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中庸·第二十五章)
这两章的性字,和第一章的性字,意义相同。
人性有仁有智,故人按性而行,乃有为人之道。
至诚的人,能把人性之善,尽量发挥出来。
故说“自诚明,性也。
”(中庸·第二十二章)性本来就是“明”的,人只要诚于自己,性自然由心而明。
大学是讲教育的书,而且讲人生的望德上达教育。
上达教育应该是中庸所讲的“修道之谓教”,大学便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第一章)
明明德为高等上达教育的初步,也为上达教育的基础。
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有发扬、有光明昭著的意义;明明德即是使明德能够光明昭著,即是发扬明德。
第二个明字为形容词,形容“德”是光明的。
这种光明的德是什么呢?
就是人性之善,宋朝理学家称之谓天理。
朱熹注说: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所谓“虚灵不昧”不能指着理,“理”是一个抽象的理,无所谓虚灵不昧,虚灵不昧只能指着人心,人心有得乎天的性,为人活动的规律。
人心之性称为明德,乃假定人性为善,否则不能称为德,更不能称为明。
中庸也假定人性为善,总说:
“率性之谓道”,又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
然而大学、中庸所假定的性之善,不是伦理行为之善,而是行为规则之善。
行为规则即为天理,天理必定是善。
在这进而附带说一下,徐复观以“天命之谓性”为“使人感到自己的性是由天所命,与天有内在的关联,因而人与天,乃至万物与天,是同质的,因而刀是平等的。
”这样的结论真太牵强。
两者有内在关系,并不表示同质和平等;例如,原因和效果有内存联系,并不确定原因和效果常常是同质或是同等的。
对于天命,在研究书经、诗经和易经的哲学思想时我们已有说明,我们不承认天和人同质同等。
礼记论性的篇章,还有乐记篇说:
“动静有常,大小殊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
”
《乐记》篇把性命连在一起,性命的意义,是物的类和群,所以相同和相异的理由,这正是物之所以为物之理,物之性相同,则是同类,性不相同便不是同类。
人之性都相同,人和狗的性便不相同。
大戴礼的“本命”篇说: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
”这个性字和礼记的性字意义相同,形于一,是使物之所以成物,同于一类。
3、命
甲、孔子论命
论语里记述孔子论性的语只有一句,却记述好几次孔子论命的话。
命对于人的实际生活很有关系,孔子在实际的人生上讲到命。
子罕篇说:
“子罕言:
利与命与仁。
”这处的罕言不能作为稀少的罕,因为孔子在论语里常常谈到“利与命与仁。
”这个罕字该作为特别注意的意思。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论语·尧曰)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论语·宪问)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
亡天,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
子夏曰: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
“五十而知天命。
”(论语·为政)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孔子在论语里讲天命、讲命,天命和命似乎是两件事。
论语里孔子所讲的天命,一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意义不相同。
中庸的天命是一种概括的命,是对一切的人而言,凡是人都受了同样的天命,即是受了相同的人性,为人之为人的“道”和“则”。
孔子所讲的天命,乃是指着上天所给一个人的使命,这种命是个别的,是单独的。
孔子常承认自己受有上天所给的使命,上天给他的使命在于承传尧舜文武之道。
所以他自己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何”(论语·述而)
这种命,是天命,是孔子所说的“知命”之命。
不知道这种使命,一个人不能成一个君子,因为不能满全使命。
道行不行是命,这个命也是天命。
伯牛有疾的命,和死生之命,则是普通所说的命运。
死生和富贵都在命之中,本人没有抵抗的力量。
子夏说所听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两句话平行,不相对立,死生和富贵相平行,命和天相平行;因此死生富贵都属于命,命则是天。
孔子所讲的命运,也是天命。
这种命运,虽也是突命,然并不使人盲目听命运摆布,或是消极听命运的安排,自己一点不努力。
因为寿夭的命运,不取消人从事工作的心火;富贵的命运也不妨碍寻觅前途的心火。
谁也不预先知道自己的寿命长短,谁也不预先知道自己的穷达贫富,人便尽力奔赴自己的事业。
在事情过去后,才知道暗中有命。
如孟子所说:
“吾之不遇鲁候,天也!
”(惠王下)
韩诗外传,记孔子的话说:
“哀公向孔子曰:
有智寿乎?
孔子曰:
然。
人有三死,而非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
少以敌众,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杀之。
故有三死而非命,自取之也。
诗云: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韩诗外传·卷一)
乙、中庸·礼记论命
A、中庸论命
“天命之谓性。
”(中庸·第一章)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中庸·第十四章)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中庸·第十七章)
“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第十七章)
中庸论命,不以性命相连,而单独说命。
第一章所有的天命,不是普通所说的命,乃是指的天的命,或天的定夺。
第十四章所有的命,正是普通所讲的命。
这种命字指着一个人的穷达,一个人能否行道,都有命。
易经很注重时字和位字,就是等待命所定的时间,和居在命所定的位置。
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便是这种思想,君子人常常在人事变易中居在当居的位置,以等待命所定的时间,决不乱动,小人则冒险,反对命运而希望徼幸有所得。
命的规定并不是偶然的,上天对于一个人的规定,也看这个人的本身究竟若何,是有才德呢?
是作恶的小人呢?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
”因此,有大德的人,上天规定他的命,必是“得其位,得其名,得其寿”。
这样,命和每个人的操行相关连。
当然,大德的人并不多,寥寥如晨星,大恶的人也不多,普通一般人的命,也就不明显了。
战国末年乃有帝王受命和五德终始说。
B、礼记论命
礼记上还有乐记,礼运、祭法等篇里,提到命。
大戴礼也有命字。
“动静有常,大小殊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
”(礼记·乐记)
“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杀以降命。
命降于社之谓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
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礼记·礼运)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其降也曰命,其官于天也。
”(礼记·礼运)
“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者皆曰折,人死曰鬼。
”(礼记·祭法)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
故命者,性之终也。
”(大戴礼·本命)
礼记的乐记篇所讲的性命,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篇的性命两字连用,所有的意义和性字的意义相同。
大戴礼的本命篇的命、性、生、死等字,都有形上哲学的意义。
本命篇以道为宇宙所以成为宇宙之道,也就是天道。
宇宙之道分而成人道,称为命。
人得人道以生;人道形成一类人,称为性。
人是怎样生的呢?
是因阴阳的变化,乃因着人性而成人形。
阴阳的变化停止了,人的寿数完了,便是死。
本命篇称命为性之终,意义是指着性在人死的时候,但终止了;因为人死了已经不是人。
而人之死,在于命,故称命为性之终。
这样说来,本命篇的两个命字,前后意义似不相同,因为在上方面说,性的始终都由于命,唐君毅先生说:
“此命贯于物之性,物之生之始与终者。
”性为天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所以成立,乃由于命,也即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
但是阴阳变化的穷尽的停止,人的寿数完结,也由于命,这种命便不是形上之命,也不是分于道之命,而是普通之所谓命运了。
本命篇把两个命字用在同一文句昊,表示两个命字的根由相同,都是来自天。
祭法篇的命字,也和这个命字的意义相同。
所以中庸大学和礼记的其他篇章,分命字为两种,一为形上的天命之性,一为个人的命运。
礼运篇的命字,注疏恋爱为教令。
君王行政以天下为本,“肴以降命”效法天而下教令。
教令在礼上去施行,以“社”礼施教令,为效法地;以祖庙礼施教令,为仁义;以山川祭礼施教令,为兴作器物,以五祀祭礼施教令,为社会制度。
这个命字不是哲学上的命,是政治上的命。
4、心
甲、孔子论心
“心”,在中国哲学思想里,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点。
在书经和诗经里,心的意义,已见端绪,在易经里没有发展,在孔子的论语里,渐见完满,在中庸、大学里多有发挥,到了孟子和荀子,乃得完成。
论语里孔子讲到“心”,只有三处: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论语·雍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
”(论语·阳货)
从这三个心字去看,孔子以心为善恶的中心;人之为善为恶,由于自己的心。
孔子说自己到了七十岁,可以从心所欲,不会逾越伦理的规矩。
他一生的修养,都为达到这个目的。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还在青年练习修养的时候,能够在三个月的长久时间,他的心不违背仁道;孔子称赞他的善。
孔子又说普通一个人,天天饱食,不用心做事。
他就必定作恶。
心为什么是善恶的中心呢?
孔子以心有欲有志。
欲是心的天然而动,志是人反省之动。
对于心的天然之动,人所该做的,在于以心的反省而予以约束。
因此孔子说: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这种修养方法很合于心理和生理。
“欲”是人心天然所有的,和人的生理心理相连;所以人心的欲情之动,必有生理和心理的条件。
为克欲,孔子教导注意这两方面的因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己欲立而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为使“欲”向善,不能单用消极的克制,而要用积极的引导。
积极地引导向善,则在于心经过反省,规定一个目标,使心中的“欲”趋向这一目标,这称为“志”。
志是心之所向。
孔子常教导门生好好定志。
“五十有五而志于学。
”(论语·为政)
“子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颜渊季路侍,子曰:
盍各言尔志?
……”(论语·公治长)
心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善,他的心便专注在这一点,便会集中自己的理智力和意志力,去完成自己的志向。
专是由心去定,由心去把持;心便是行善的动力。
在“志”里,我们看到心要知道志的对象和条件,心要选择志的对象,心要发指导理智力和意志力去追求对象。
后来孟子和荀子,以心能知、能主宰便是引伸和发挥孔子的思想。
乙、大学·中庸论心
大学讲人生大道,以修身为本,进而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生大道的本和始,在于修身,修身以正心为主。
大学乃正式提出儒家的“正心”之道。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大学·首章)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大学·第六章)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大学·第七章)
为什么要正心呢?
因为人的一切行动都靠着心,假使心不在,五官的感觉也不能行动。
这就是说人的行动,以心为主,身由心主宰。
大学虽然没有主宰的名词,已有主宰的实事。
孔子在论语里讲修身之道,常因人设教,没有系统地讲述,大学和中庸则是有系统地讲而且注重内在的道德。
中庸以人之性为伦理标准,人之性由主而显。
大学以人性为明德。
明德怎样可以显明呢?
由心去明。
所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心为能明明德,心应该是正直的,因此修身之道在正心。
大学和中庸都没有说明心的本体。
但已经假设“心”的本体是虚明的。
这一点要等到荀子,才有说明。
中庸对于心,没有提到过,三十三章里没有一个心字。
但是中庸前一半讲“道”,道须臾不可离,故君子慎独,“此谓诚于中,形于外。
”(大学·第六章)这种道便是在人心,后一半讲“诚”,诚由心而实行,故心字在中庸里可以说是隐而不显,况且中庸讲喜怒哀乐之发和未发,情之发,就是心之动。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都靠着心去主宰。
中庸又说:
“自诚明,性也。
”(中庸·第二十一章)性本来是明的,性的明,由心而明。
人自己诚于自己的性,性自然由心而明。
故唐君毅先生说:
“中庸于此乃更不言心不言意念,而只言明。
明即心知之光明,人至诚而无息,则其心知只是一充内形色的光明,以表现此自诚之性,此外更无心可说。
”我虽不同意“明”代表心知的光明,更不同意“此外更无心可说”,但我赞成“自然明”是由心明,顺为心的本体为虚明。
大学有明明德,中庸有自诚明,都以“明”代表心的虚明。
5、情
甲、论语论情
“情”在后代儒家的思想里,占着重要的位置,朱熹解释性的善恶时,以性为善,情可善可恶,人之善恶来自情。
可是在论语和大学、中庸里,竟只找到三个情字。
不过,情的意义,或情的对象则实实在在地存在。
孔子在论语里,有几次提到喜怒哀乐: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论语·雍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论语·述而)
“颜渊死,子哭之恸。
”(论语·颜渊)
“君子有九思:
……忿思难……”(论语·季氏)
孔子讲喜怒哀乐,是在实际生活上谈人的情欲,只有在季氏章的九思里讲忿思难,讲到原则,在发怒时,要反省发怒以后的困难,便不要乱发怒。
在实际生活上谈情欲,孔子所举的例,也是指着情欲的善,喜怒哀乐于道。
乙、中庸论情
中庸虽没有情字,但在第一章即提出了情欲的大原则: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这项原则,在后代儒家中,成为善恶的规律。
注疏说:
“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依,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
但是情的基本,虽在于性,然不由性而发,而由心而发。
故情的基础在于心;因为情发时,是由心而发,不是由性而发。
性只是抽象的理,心则是活活的生命中心。
情未发时,心平静不动,如秋水不起波,可以明明看见心中的性;这种状态称为中。
情发时,由心而发心乃动,心动而合乎心内的性理,便称为和,便是中节,便是善。
孔子在论语里所举例的喜怒哀乐,都是“中和”的情。
情发而不中节,便不中和,便是恶。
这样说来,不是善恶都来自情吗?
同时又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人的一思一言一行,都带有情,因此,乃有善有恶呢?
孔子和弟子们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从中庸首章所说: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们可以知道中和为伦理道德之大本和达道,就是善恶的基础。
我们便可以说:
善恶由情而来,人的思言行为都带有情。
这一点造成了后来朱熹的性为善情为恶的主张,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是情之发由心主宰,情发时中节或不中节而造成的善恶,应由心负责。
不过心既由情而动,情欲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