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事现实和想像之间.docx
《在往事现实和想像之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往事现实和想像之间.docx(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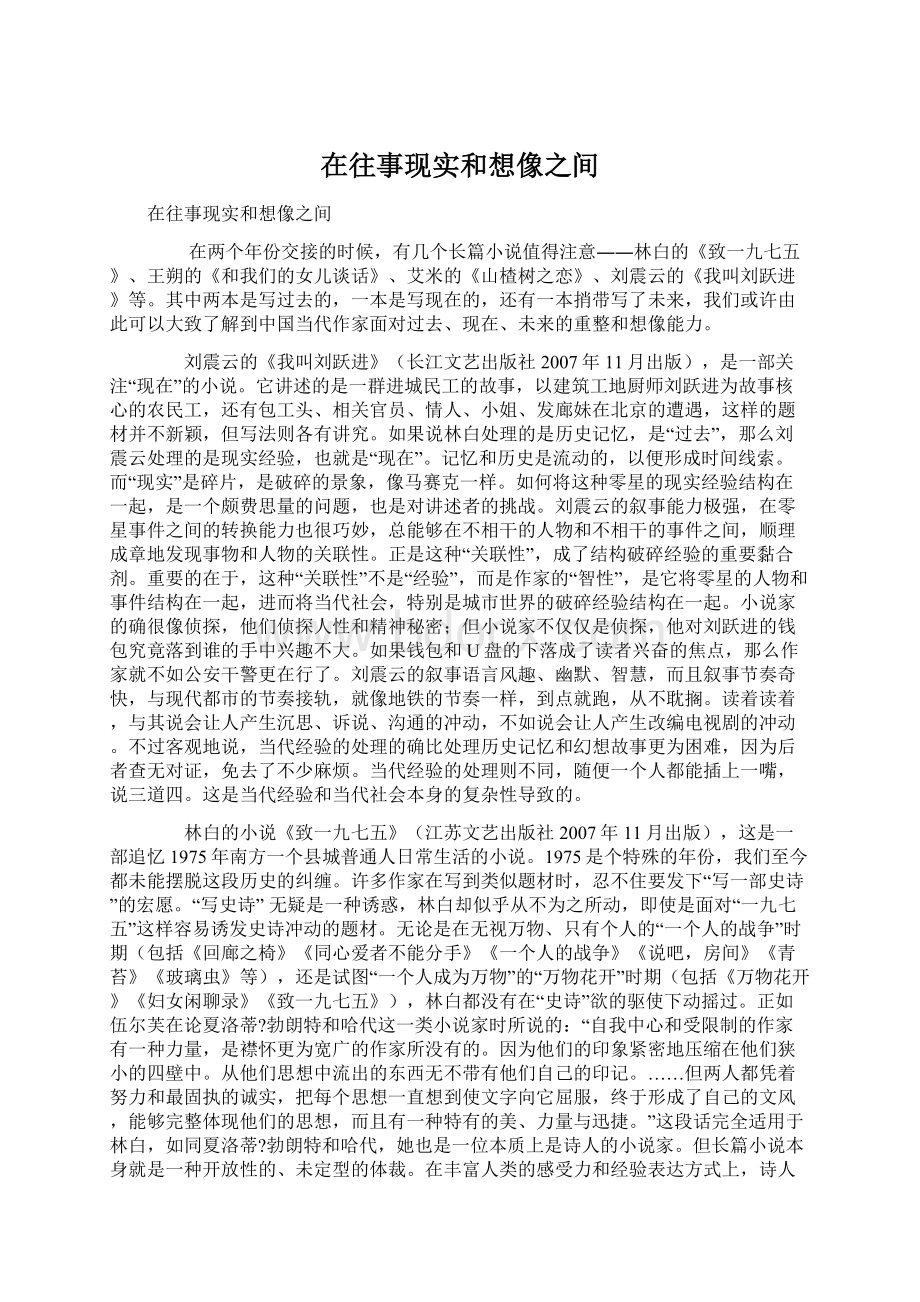
在往事现实和想像之间
在往事现实和想像之间
在两个年份交接的时候,有几个长篇小说值得注意――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等。
其中两本是写过去的,一本是写现在的,还有一本捎带写了未来,我们或许由此可以大致了解到中国当代作家面对过去、现在、未来的重整和想像能力。
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是一部关注“现在”的小说。
它讲述的是一群进城民工的故事,以建筑工地厨师刘跃进为故事核心的农民工,还有包工头、相关官员、情人、小姐、发廊妹在北京的遭遇,这样的题材并不新颖,但写法则各有讲究。
如果说林白处理的是历史记忆,是“过去”,那么刘震云处理的是现实经验,也就是“现在”。
记忆和历史是流动的,以便形成时间线索。
而“现实”是碎片,是破碎的景象,像马赛克一样。
如何将这种零星的现实经验结构在一起,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也是对讲述者的挑战。
刘震云的叙事能力极强,在零星事件之间的转换能力也很巧妙,总能够在不相干的人物和不相干的事件之间,顺理成章地发现事物和人物的关联性。
正是这种“关联性”,成了结构破碎经验的重要黏合剂。
重要的在于,这种“关联性”不是“经验”,而是作家的“智性”,是它将零星的人物和事件结构在一起,进而将当代社会,特别是城市世界的破碎经验结构在一起。
小说家的确很像侦探,他们侦探人性和精神秘密;但小说家不仅仅是侦探,他对刘跃进的钱包究竟落到谁的手中兴趣不大。
如果钱包和U盘的下落成了读者兴奋的焦点,那么作家就不如公安干警更在行了。
刘震云的叙事语言风趣、幽默、智慧,而且叙事节奏奇快,与现代都市的节奏接轨,就像地铁的节奏一样,到点就跑,从不耽搁。
读着读着,与其说会让人产生沉思、诉说、沟通的冲动,不如说会让人产生改编电视剧的冲动。
不过客观地说,当代经验的处理的确比处理历史记忆和幻想故事更为困难,因为后者查无对证,免去了不少麻烦。
当代经验的处理则不同,随便一个人都能插上一嘴,说三道四。
这是当代经验和当代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
林白的小说《致一九七五》(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这是一部追忆1975年南方一个县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小说。
1975是个特殊的年份,我们至今都未能摆脱这段历史的纠缠。
许多作家在写到类似题材时,忍不住要发下“写一部史诗”的宏愿。
“写史诗”无疑是一种诱惑,林白却似乎从不为之所动,即使是面对“一九七五”这样容易诱发史诗冲动的题材。
无论是在无视万物、只有个人的“一个人的战争”时期(包括《回廊之椅》《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青苔》《玻璃虫》等),还是试图“一个人成为万物”的“万物花开”时期(包括《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林白都没有在“史诗”欲的驱使下动摇过。
正如伍尔芙在论夏洛蒂?
勃朗特和哈代这一类小说家时所说的:
“自我中心和受限制的作家有一种力量,是襟怀更为宽广的作家所没有的。
因为他们的印象紧密地压缩在他们狭小的四壁中。
从他们思想中流出的东西无不带有他们自己的印记。
……但两人都凭着努力和最固执的诚实,把每个思想一直想到使文字向它屈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文风,能够完整体现他们的思想,而且有一种特有的美、力量与迅捷。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林白,如同夏洛蒂?
勃朗特和哈代,她也是一位本质上是诗人的小说家。
但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性的、未定型的体裁。
在丰富人类的感受力和经验表达方式上,诗人式的小说家,比如歌德、雨果、契诃夫、爱伦?
坡、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巴别尔、博尔赫斯、卡内蒂等,他们为小说赚取了许多,而不是让小说赔本。
《致一九七五》也没有让当代汉语小说赔本。
这部小说以自传式叙述的方式,以年少无知的视角(“我们就是这样懵懂,缺乏觉悟”)和为所欲为的语言魔法,将懵懂女中学生、闲散知青李飘扬的有限生活经历,转化为似乎无限的回忆能力,从而获得了“特有的美、力量与迅捷”。
与《致一九七五》形成有趣对照的,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同样是写“文革”题材的长篇。
这部小说以“文革”时期上海中上层家庭的生活为中心,讲述“干部公寓”子弟自我启蒙的精神冒险、爱欲游戏。
然而,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个人,而是“上海城市精神”。
作者试图表明,在一个政治消灭文化的特殊时代,这种“城市精神”依然艰难地维持了其基本的尊严,并或多或少地庇护了它的子民。
这使得小说把这座被赋予“传奇”色彩的城市当作仰视的对象,当作语言,当作意识形态,当作制约每一思想、心理以及人物言行的东西。
我们想和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个人问题单独呆一会儿,“城市精神”却老要作陪,还不断在旁边插话。
书写“城市史”的重负,时刻压制着小说家不受限制地观察世界、探究人性的本能。
结果,作为小说之根本的人性经验,被当作“修志”的工具,成为“城市精神”礼服上的补丁。
可见,对于一位无论是在城市知识还是人性现象方面都并非百科全书式的作家来说,写“城市史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收获》2008年第1期)。
王朔在沉默了若干年之后,近期新作迭出,媒体哗然。
继《我的千岁寒》(近年作品集)、《致女儿书》(中篇?
小长篇?
)之后,近期又推出了长篇《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王朔新作的出现,给那些习惯于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口径谈论他作品的人带来了麻烦。
上个世纪80年代,王朔自称“流氓”,而年轻一代读者却一心要捧他为大师。
这两年,当王朔试图要以大师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年轻一代读者却都准备开溜,可见人心之混乱。
在王朔的新作中,原有的语言风格依然存在,但增加了更多高远的思考,增加了更多的机锋,读者仅靠“过瘾”来阅读是不够的。
与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关注“过去”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关注“现在”不同,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一本关注“未来”的书。
“未来”并不是凭空的幻想和虚构,它建基于“过去”和“现在”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王朔,用一种个性鲜明的语言风格关注着“现实-历史”。
“现实-历史”一直像“父亲”一样在压抑他,所以他这个“儿子”要越俎代庖做“你爸爸”,要“过把瘾”,要用个性或个人主义抵御现实、审判历史。
现在他真成“爸爸”了,同样要面对儿女们的审判。
这种审判的声音已经在他的内心响起了。
所以,王朔在想像中跳进了“未来”,转身回望“现在”,用“未来”审判“现在”。
王朔用这样一种奇怪的想像方式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关系。
朋友的女儿咪咪方自国外回来,做一个文化项目,采访“北京老王”云云。
现实和历史在未来面前化作一片虚无。
中国作家有的对“过去”很敏感,有的对“现在”很敏感,但对“未来”如此敏感者还是很少见的,这种敏感正确与否是无关紧要的。
这里涉及到对不同的经验(现实)、时间(历史)在文学叙事中产生不同意义的理解方式,拟另文专门论述,在这里不再展开。
最后要谈到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这部小说的前身,是美籍华裔学者静秋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记,和一个她未曾发表过的中篇小说。
旅美作家艾米在此基础上改写而成,保留了原来的基本事实材料和人物对话。
这是一个在人性压抑和扭曲的特殊环境之下发生的爱情故事和情感悲剧。
2007年,该小说在中文网站《文学城》连载,在网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包括一些小说家,都被它所感动。
在一个大众媒体和符号生产的时代,纠缠着我的问题是,这种写作方式和感人效果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今天为什么没有这种“纯洁的”、“惊天动地的”爱情?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和观众,我在看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只不过爱情的阻力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家庭和传统观念,父母观念变化了,矛盾就解决了。
《山楂树之恋》的感受更为复杂,因为故事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一个潜伏在一代人记忆之中的压抑和扭曲的历史,小说叙事激活了历史记忆,让我们百感交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除了感动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悖谬,由此产生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只要纯洁的爱情故事,而不要伴随着这个爱情故事的历史语境,我们赞美前者,批判后者。
问题在于它们是相生相克、祸福相依的关系。
历史的压抑有两种结局,一是集体精神失常,一是情感的升华(像《山楂树之恋》的故事)。
升华是压抑的结果。
压抑消除,升华的可能性也就消除,只能出现一个欲望的故事,像《我叫刘跃进》中的故事一样。
今天,这种压抑基本消除,或者说发生了转移,那么为什么没有类似的故事产生呢?
这是一个当代问题。
正是思想解放导致的社会解放和欲望释放,才使得那段历史消失,那个故事也随之消失,成了我们的梦想,才会出现《我叫刘跃进》《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这样的故事。
我们正在处理今天因“解放”所面临的新问题。
历史记忆和情感故事的编织并不难,使人感动也不难,难的是它如何从更为广阔的精神角度切入当代精神生活。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记忆和想像中有多少遗憾,我们或许都应该记住奥登的一句诗:
“四面八方堆积着/同样的虚无和绝望,/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