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焚书坑儒研究的状况.docx
《历史研究焚书坑儒研究的状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史研究焚书坑儒研究的状况.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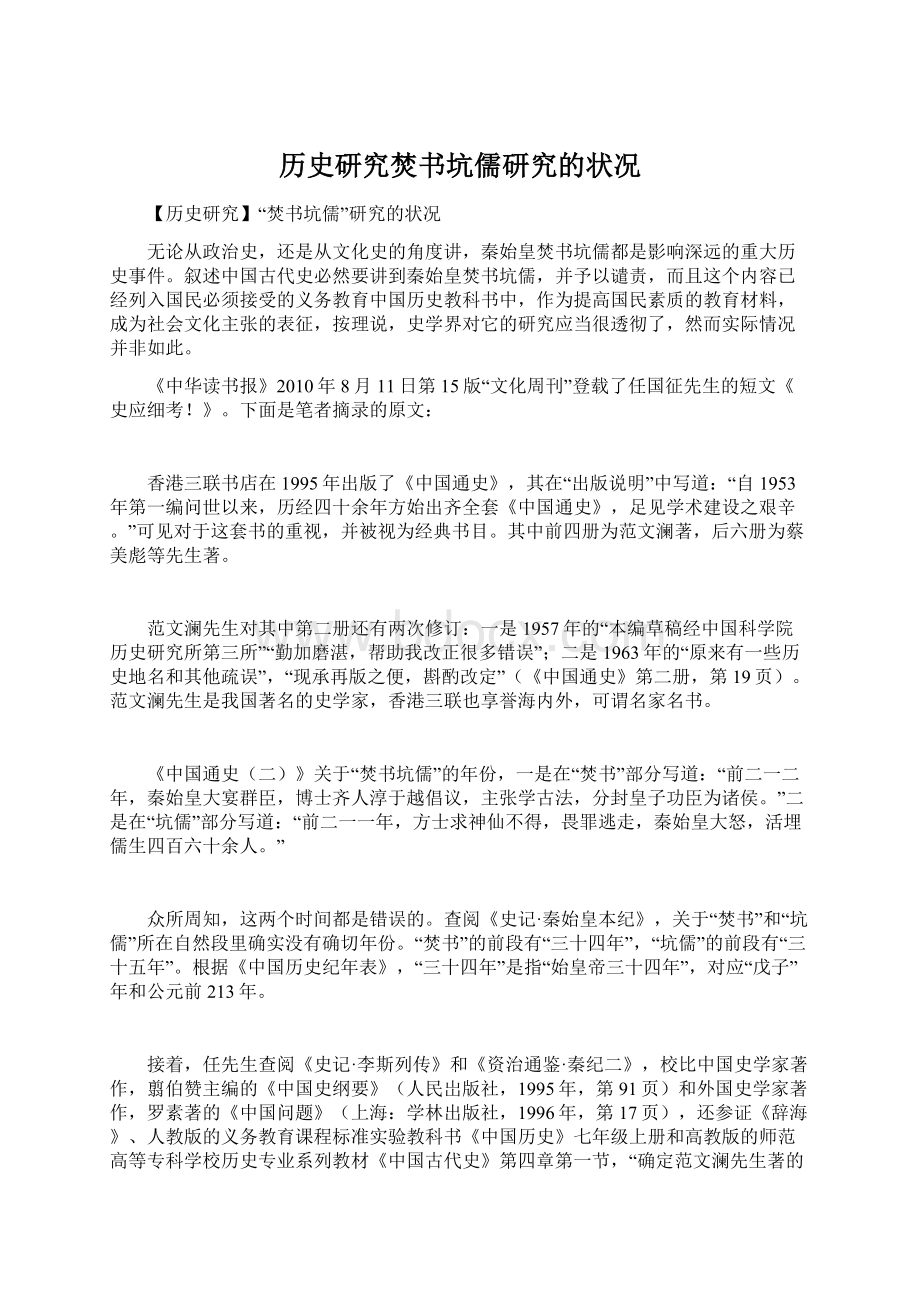
历史研究焚书坑儒研究的状况
【历史研究】“焚书坑儒”研究的状况
无论从政治史,还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讲,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叙述中国古代史必然要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予以谴责,而且这个内容已经列入国民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材料,成为社会文化主张的表征,按理说,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应当很透彻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第15版“文化周刊”登载了任国征先生的短文《史应细考!
》。
下面是笔者摘录的原文:
香港三联书店在1995年出版了《中国通史》,其在“出版说明”中写道:
“自1953年第一编问世以来,历经四十余年方始出齐全套《中国通史》,足见学术建设之艰辛。
”可见对于这套书的重视,并被视为经典书目。
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等先生著。
范文澜先生对其中第二册还有两次修订:
一是1957年的“本编草稿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勤加磨湛,帮助我改正很多错误”;二是1963年的“原来有一些历史地名和其他疏误”,“现承再版之便,斟酌改定”(《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9页)。
范文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香港三联也享誉海内外,可谓名家名书。
《中国通史
(二)》关于“焚书坑儒”的年份,一是在“焚书”部分写道:
“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
”二是在“坑儒”部分写道: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
”
众所周知,这两个时间都是错误的。
查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焚书”和“坑儒”所在自然段里确实没有确切年份。
“焚书”的前段有“三十四年”,“坑儒”的前段有“三十五年”。
根据《中国历史纪年表》,“三十四年”是指“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应“戊子”年和公元前213年。
接着,任先生查阅《史记·李斯列传》和《资治通鉴·秦纪二》,校比中国史学家著作,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岀版社,1995年,第91页)和外国史学家著作,罗素著的《中国问题》(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7页),还参证《辞海》、人教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和高教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确定范文澜先生著的《中国通史
(二)》关于焚书坑儒的时间有误:
焚书的时间不是公元前212年而是公元前213年,坑儒的时间不是公元前211年而是公元前212年。
”并且进一步列举章太炎先生在1901年写的《秦献记》和1910年写的《秦政记》、马克斯·韦伯1920年著的《儒教和道教》为例,指出:
“关于‘焚书坑儒’的年份在中外学术界却被有意或无意忽略”,从而说明“‘史应细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笔者完全赞成任国政先生的意见。
时间是构成历史事件的要素之一。
人们总爱把历史比喻成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某个时间发生了某件事情,那么,这个具体的时间就会把这个具体的事件,锁定在它发生的一段河道上。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人们都能根据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去了解它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时间是人们了解历史事件、认识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忽视不得。
范文澜先生是史学大家,范氏《中国通史》是史学名著。
大家名著,又在四十余年中经过不只一次的修订,居然还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两个年份都搞错了,这件事情本身就让广大读者很难理解。
这还不算,范氏《中国通史
(二)》对“坑儒”的叙述也存在问题: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
”方士欺骗秦始皇跟秦始皇活埋儒生,这原本是两码事,读者看书至此,不禁会问:
“方士欺骗了秦始皇,而后畏罪逃走,秦始皇理应下令捕捉、惩治方士,为什么要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呢?
”范氏《中国通史
(二)》的这段叙述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转译来的。
原文说: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在这里,司马迁将方士欺骗秦始皇和秦始皇活埋儒生这两码事的联系讲得很清楚,秦始皇认为,方士不仅欺骗他,而且诽谤他,因此联想到诸生,就派人查问,发现诸生也有制造怪诞邪说来惑乱百姓,挑动百姓对朝廷不满的。
于是派御史审问诸生,诸生辗转告发,最终将触犯法禁的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
范文澜先生是史学大家,自然不会连《史记》都看不懂,可却偏偏忽视了方士欺骗秦始皇和秦始皇活埋诸生这两件事的联系,结果给读者制造了原本不应该出现的疑问。
这个问题出得蹊跷,令人费解。
所以,笔者认为任国政先生的“史应细考”提得好,好就好在它揭露出史学界浮华的痼疾。
史学界的浮华在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既然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学家就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然后才能用它教育群众。
可是,秦始皇一生“坑”过几次“儒”,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两千多年以来就一直存在分歧,始终没搞清楚,似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搞清它,相反,却有人在故意制造混乱,让人们无所适从。
在汉代史籍中,详细记载秦始皇制造的“坑儒”事件只有两次:
一次是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因方士欺骗、诽谤秦始皇而后畏罪逃走,使秦始皇联想到诸生也有妖言惑众者,经审问,获犯法违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
另一次是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所说的,秦始皇焚书后,害怕天下诸生不服从所变更的新法,就设计一个阴险的圈套,将博士诸生七百人,诱骗到骊山陵谷中温处坑杀。
这两次“坑儒”,事发的原因不同,经过不同,坑杀的方式和人数也不同,自然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
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所载“坑儒”,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事件发生的年份,但已经说明事件起因是“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焚书令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下达的,那就可以判断:
此次事件发生不会距焚书令下达太久。
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记的“坑儒”事件与卫宏所记的“坑儒”事件是两码事,但这两码事发生的时间相距不远。
可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只记载秦始皇一次坑杀四百六十余人的“坑儒”事件,不记载秦始皇一次坑杀七百人的“坑儒”事件,这说明他根本不承认卫宏所记的那次“坑儒”事件的存在。
反过来,卫宏并未否认司马迁所记载的秦始皇一次坑杀四百六十余人的“坑儒”事件,只是再补充一次秦始皇的“坑儒”罪行。
这说明早在汉代关于秦始皇“坑儒”的次数已经出现意见分歧。
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史学大家,卫宏是两汉之际的经学大师。
他们俩人在学术上地位崇高、享有盛誉。
所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很少有人怀疑他们的说法。
像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就说: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
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
为伏机,杀七百余人。
”马端临对汉代史籍记载的秦始皇两次大规模的“坑儒”,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确信是事实。
马端临是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
他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详尽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
后世人们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明备精审”。
在现今一些中国通史和秦汉史研究者的眼里,马端临肯定了司马迁和卫宏记载的秦始皇“坑儒”真实可信,秦始皇的“坑儒”罪状就算“坐实”了。
像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的林剑鸣教授,他著有《秦史稿》,这是一部享誉学界的秦史专著。
该书正文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了秦始皇“坑儒”罪行,但在探讨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六十余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的时候,以注释的形式说明:
“关于坑儒还有另一种说法”,于是附录了卫宏所记秦始皇设计诱杀七百人的坑儒故事,然后说:
“《文献通考·学校考》把这一记载与《史记》中的记载当做两回事叙述”,又引用了《文献通考·学校考》的那段原文,最后总结说:
“以上两条资料虽晚出,亦可为旁证,故附于此。
”旁证虽非主要证据,但既可为证,就必不能假,非真实不可!
看来,林剑鸣教授是相信卫宏说法的。
《秦始皇帝大传》的作者安作璋、孟祥才两位先生,在该书中采用《史记》上秦始皇“坑儒”的说法,写道:
“牵连进此案的四百六十多个方士与儒生被坑杀于咸阳以东的渭水河畔。
今陕西临潼以西二十里有一处名叫洪坑沟的小山谷,据清亁隆《临潼县志》记载又名坑儒谷,就是当年秦始皇下令坑杀儒生的地方。
”这段话说得虽然很肯定,可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上只说在咸阳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并没有说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的地方是“咸阳以东的渭水河畔”。
作者的说法根据何在?
应该有明确交待。
今陕西临潼的坑儒谷,相传是卫宏所说的秦始皇设计诱杀儒生七百人的地方。
卫宏所说的坑儒事件跟司马迁所说的坑儒事件毫不相关,完全是两码事。
临潼这个地方确实在咸阳以东,又离渭水不远,可谓“渭水河畔”。
作者讲的是秦始皇杀害百六十余人那一次坑儒,用的却是卫宏所说的另外一次坑儒事件发生的地点,这就难免有拼凑历史,糊弄读者的嫌疑。
作者或许辩解:
“卫宏说的那次坑儒事件也是可信的。
”可是,那您得说清楚,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呀!
比《秦史稿》和《秦始皇帝传》作者爽快,《秦始皇大传》作者郭志坤在书中专门设一目讨论秦始皇“坑儒是一次还是多次?
”其中写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讲明被坑儒生为四百六十余人,而《诏定古文尚书序》又说七百人被坑杀。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学校考》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笔者注:
马端临并没有作考证,更谈不上进一步,只是引用。
):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
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
为伏机,杀七百余人。
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杀数十人。
’这里指出:
秦朝除了坑杀四百六十余人这一次之外,又坑杀了七百余……。
这说明,坑儒并不是一次,而是发生多次。
这是完全可能的,其一,这是秦王朝一贯的政策所决定的。
焚书令规定,焚书之后,‘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而儒生的特点就是‘师古’。
荀子对秦昭襄王说: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
’(《荀子·儒效》)儒生们以习读《诗》、《书》、百家语为业,偶然议论《诗》、《书》者便处以死刑,稍谈当时政治者就要犯‘以古非今’之罪而被杀家灭族,儒生随时都有被坑杀的可能,这样势必发生多次。
其二,坑之咸阳的四百六十余人‘犯禁者’全是咸阳地区捉来的。
随着审问的深入,追查的扩大,必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这样一来,犯禁者就远远超过四百六十余人。
由于交通的限制以及‘犯禁者’的反抗,捉到的儒生往往是就地处决了。
秦始皇为了达到‘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的目的,也就必然在全国范围多处多次展开对儒生的镇压。
秦始皇杀人数岂止数百数千,连数字也搞不清,史书上往往以‘皆杀之’、‘死者众’、‘无复出者’等字眼来记载,秦始皇对儒生的杀戮犹如宰割了一批又一批的绵羊、牛马一样轻而易举。
”在郭志坤先生看来,秦始皇“坑儒”绝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而是多次,并且简直多得数不过来。
一个小小的秦始皇“坑儒”次数的问题,两千多年以来众说纷纭,始终未能搞清楚,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现代大史学家们又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都只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讲述秦始皇在咸阳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而对卫宏所说的秦始皇设计在骊山温处活埋儒生七百人一事,避而不谈。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名家或权威单位主编的大部头中国通史著作相继问世,如白寿彞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是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到1998年9月完成,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名誉主编李学勤、主编朱大渭的《中国通史图说》10大册,1999年由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博物馆编的《文物中国史》(彩色图文本)8大册,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其中第四册是《文物秦汉史》。
我原以为,这些新出版的大部头中国通史著作容量增大,会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有深一步研究,能够解决一些像秦始皇坑儒次数这样长久争论不休的问题,结果,拜读了这些书籍以后,大失所望。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依旧是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只讲秦始皇在咸阳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其他一概回避。
以白寿彞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为例,书中写道:
就在焚书的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生的事。
这件事是由几个方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
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
他甚至宣称:
“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
”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
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
而秦法规定:
“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
始皇知道后大怒道: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得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审讯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
诸生转相牵连告发,结果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于咸阳。
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
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比较,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对秦始皇坑儒事件的叙述,除了详细很多之外,并无新意。
《中国通史图说·三·秦汉》和《文物中国史·文物秦汉史》共同的特点是书中配有大量历史文物、历史遗迹的照片,想做到图文并茂,富有说服力。
可是,拜读之后,感觉问题更严重。
《文物中国史·文物秦汉史》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焚书堆·悯儒谷”开头就说: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
在今陕西渭南湭水东岸土丘上残存有灰堆遗迹,据说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地方。
在今陕西临潼洪庆堡村西南还有坑儒谷遗址,据说当年无数儒生就被掩埋在这里,因此又叫做悯儒谷。
”接着,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了焚书坑儒事件的经过,还特别强调“秦始皇在诸生中亲笔圏定四百六十余人,将他们活埋在咸阳。
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发生于前212年。
”这里,编书者已经把“坑儒”事件的时间、地点和人数讲得清清楚楚。
如果配上“焚书灰堆”的照片挺完美。
可编书者偏偏配上“坑儒谷”的照片并说明:
“在今陕西临潼洪庆堡村西南”,这就生出问题了。
这个“坑儒谷”是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所说的秦始皇设计诱杀儒生七百人的地方,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坑儒”四百六十余人,不是一码事,人数有矛盾,配不上。
这个问题编书者是心知肚明的。
怎么掩盖这个人数的矛盾,硬让其勉强相配呢?
编书者在开头介绍“坑儒谷遗址”时故意说:
“据说当年无数儒生就被掩埋在这里”。
用“无数”替代“七百”,故意将史籍上记载的两次坑儒事件混为一谈,这真可谓“煞费苦心!
”如果我们批评编书者削足适履,张冠李戴,伪造历史,编书者肯定喊寃,会说:
“我们讲的是‘无数’,并不是‘四百六十余人’,没有说坑儒谷活埋的是四百六十名儒生。
”可是您忘记了您编写的这部书的特点,既然称为《文物中国史》,就是要用历史文物、历史遗迹的图片来印证历史,表明真实可信。
然而图文原本不匹配,用主观改造的办法,强令结合,编书者的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编写这部书的本意,造成了误导广大读者的恶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享有盛誉的权威部门。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名义编写出版的历史普及读物,理应对祖国的历史负责、对亿万读者负责,编写态度必须十分严肃认真。
《中国通史图说·三·秦汉》在“秦代图说”:
“专制、集权、‘急政’、‘暴政’”标题下的第三节“巩固统一的措施”中谈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写道:
“为了统制思想文化,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两起重大事件。
”接着,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了焚书坑儒的经过,其中谈到,“焚书次年,又发生坑儒事件。
其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无法为秦始皇寻觅仙药,以始皇贪于权势、专用刑罚为由,相约逃亡。
始皇闻讯,下令穷究。
被认为犯禁,受到株连的儒生四百多人皆被活埋于咸阳。
”配合整段文字,编者安排了一幅历史遗迹照片,看上去是一个隆起的小土丘,照片正下方有简短注释,说:
“图三十一焚书坑儒遗址”。
显然,编者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
“秦始皇曾下令在这里焚书,又下令在这里活埋犯禁的四百多名儒生。
”但是,这个遗址在什么地方,编者根据什么资料说它是秦始皇既焚书又坑儒的遗址,书中全无交待。
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地点,这种意见是笔者前所未闻的新观点。
笔者急忙到图书馆寻找材料进行核查,结果,发现由张传玺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一节“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中也配有一幅历史遗迹照片,跟《中国通史图说.三·秦汉》书中的“焚书坑儒遗址”照片,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可是,《中华文明史》书上的照片说明是“陕西渭南秦焚书灰堆遗址”。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都像《文物秦汉史》书上所说的那样:
“在今陕西渭南湭水东岸土丘上残存有灰堆遗迹,据说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地方。
”却没有一条资料说秦始皇曾在此处坑杀儒生。
以历史文物、历史遗迹照片印证历史,增强可信度,是《中国通史图说》的编辑本意,可是该书编者明明知道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事,却故意把它们混淆在一起,又不敢标明他们所谓“焚书坑儒遗址”的具体地点──陕西渭南,从而加大了对读者的误导,与编书的本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编者存心指鹿为马,伪造遗址,忽悠广大读者。
这实在缺乏历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从上述的这些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绝大部分史学工作者对司马迁《史记?
秦始皇本纪》上所讲的秦始皇坑儒故事是信以为真的,对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上所讲的秦始皇坑儒故事实际是心存怀疑的,所以都不愿意直接引用它。
可是,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地下一番苦功夫去考证,辨别其真伪,所以才出现回避卫宏所讲坑儒故事的普遍现象。
这正是史学界浮躁的一种具体表现。
至于那些故意混淆两个坑儒故事,伪造法证据,忽悠广大读者的史学工作者,就更等而下之了。
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中说:
“考证为史学方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
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
”这是入木三分的高论,真可谓一语破的,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史学界重视史观阐述,轻视史料考证的弊病,而这种弊病的存在,正是造成史学界浮华的重要原因。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课题的研究中,浮华的弊病表现在研究者对有关史料的真伪关注很少,而对如何认识、评价这一事件的“史观”问题,则争论不休。
因为考证史料的真伪,除了需要综合运用各种传统史学方法外,还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如考古学、文字学、金石学、地理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等,非要下一番苦功夫、笨功夫不可!
它不如认识、评价事件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见解来得容易。
像秦始皇坑杀的对象,究竟是儒生呢,还是术士呢?
该称“坑儒”,还是该称“杀术士”?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明代学者于慎行提出来的。
他在《读史漫录》中说:
“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
方士侯生、卢生相与讥议始皇,始皇闻之,怒日: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
’于是使御史按问诸生在咸阳者,传相告引,得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夫以二方士故,而坑诸生数百人,其说不可知。
彼所谓诸生者,皆卢生之徒也,坑之诚不为过;其诵法孔子者,与方士何与?
而尽坑之!
世不核其实,以坑杀儒士,彼卢生岂儒士邪?
”这段议论对秦始皇“坑儒”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
其要点是,所谓“坑儒”之事,系由两位方士欺骗、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使御史按问诸生,这里的“诸生”都是“卢生之徒”,即方士;方士装神弄鬼,以求仙寻药为名,欺骗秦始皇,赚取钱财爵位,“坑之诚不为过”;这件事跟儒生无关。
于氏的见解不无道理,对后世颇有影响,不断有人发挥其说。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六收有梁启超的《战国载记》,其中《纪秦并六国章第六》写道:
“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
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
……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汉武帝时,方士少翁、栾大先后以招引神仙的方术迷惑皇帝,骗取赏赐,前者被封为文成将军,后者被封为五利将军。
梁启超认为,秦始皇所坑杀的人,百分之九十是跟汉武帝时文成、五利一样的方士,依照法律是该杀的。
这跟于慎行的看法,同出一辙。
梁氏更一步指出:
秦始皇的坑杀之举,可以扫荡社会恶劣的风气,惩处残害百姓的蠹虫,功劳大于罪过。
张分田著的《秦始皇传》第十四章第四节标题就是“‘焚书’与‘坑术士’”,其中写道:
“‘坑儒’的提法不够准确,应该称之为‘坑术士’”,并认为“‘坑术士’是专橫暴虐的君主政治下正常统治行为。
”
然而,反对这种意见的人相当多。
目前大部分中国通史著作都讲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些专著还特意驳斥秦始皇“坑术士”说。
如安作璋、孟祥才著的《秦始皇帝大传》第八章第二节标题就是“焚书坑儒”,其中写道:
于慎行“对‘坑儒’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司马迁《史记》对‘坑儒’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如此重大的事件在西汉初年必然广为流传,不少知情者也能够证实事件的真相。
司马迁的父辈是秦汉之际的人,他完全有条件与此事件的知情者接触,很难想象他会把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作为信史传给儿子。
”(笔者注:
此说不正确。
秦亡于公元前207年,司马迁生年有两说:
一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见《太史公自序》张守节“正义”;另一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见《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
司马迁出生时已经距离秦亡62年或72年了。
那时候,司马迁的父亲不可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说“司马迁父辈是秦汉之际的人,他完全有条件与此事件知情者接触”,断难成立。
)再如郭志坤著的《秦始皇大传》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坑儒的恶果》专列一目,讨论“被坑者是方士还是儒生?
”作者认为,“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方士和儒生皆有,更多的是儒生。
”作者举出三条根据,最有力量的一条根据是“扶苏向秦始皇的进谏”,说:
“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据此,作者认为:
“照扶苏讲话的含义,秦始皇所要坑杀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
”为增加这一结论的分量,作者援引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一段话作说明:
“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者而是方士,我自己在以前也曾这样说过。
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过细读清楚。
”
秦始皇究竟坑杀的是儒生还是术士?
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直至现今。
2009年4月25日,《北京青年报》刊登王立群先生的文章,题目观点鲜明:
《“坑儒”应为“坑术士”》。
次年6月,臧嵘先生在《邯郸学院学报》发表长文,题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儒生保卫文化的斗争》,坚持秦始皇“坑儒”说,驳斥“坑术士”说。
如何评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疑是这个研究课题中的重头戏。
传统观点都将“焚书”和“坑儒”视为暴政、虐政,予以谴责。
在这个大同的前提下,小异是存在的。
这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梁启超在《战国载记》中说:
“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
坑儒之事……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
……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若夫焚书则不然。
其本意全在愚民。
而其法令施行,徧及全国。
当战国之末,正学术思想磅礴勃兴之时,乃忽以政府专制威力,夺民众研学之自由,夭阏文化,莫此为甚,而其祸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