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一支烟男版.docx
《请给我一支烟男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请给我一支烟男版.docx(8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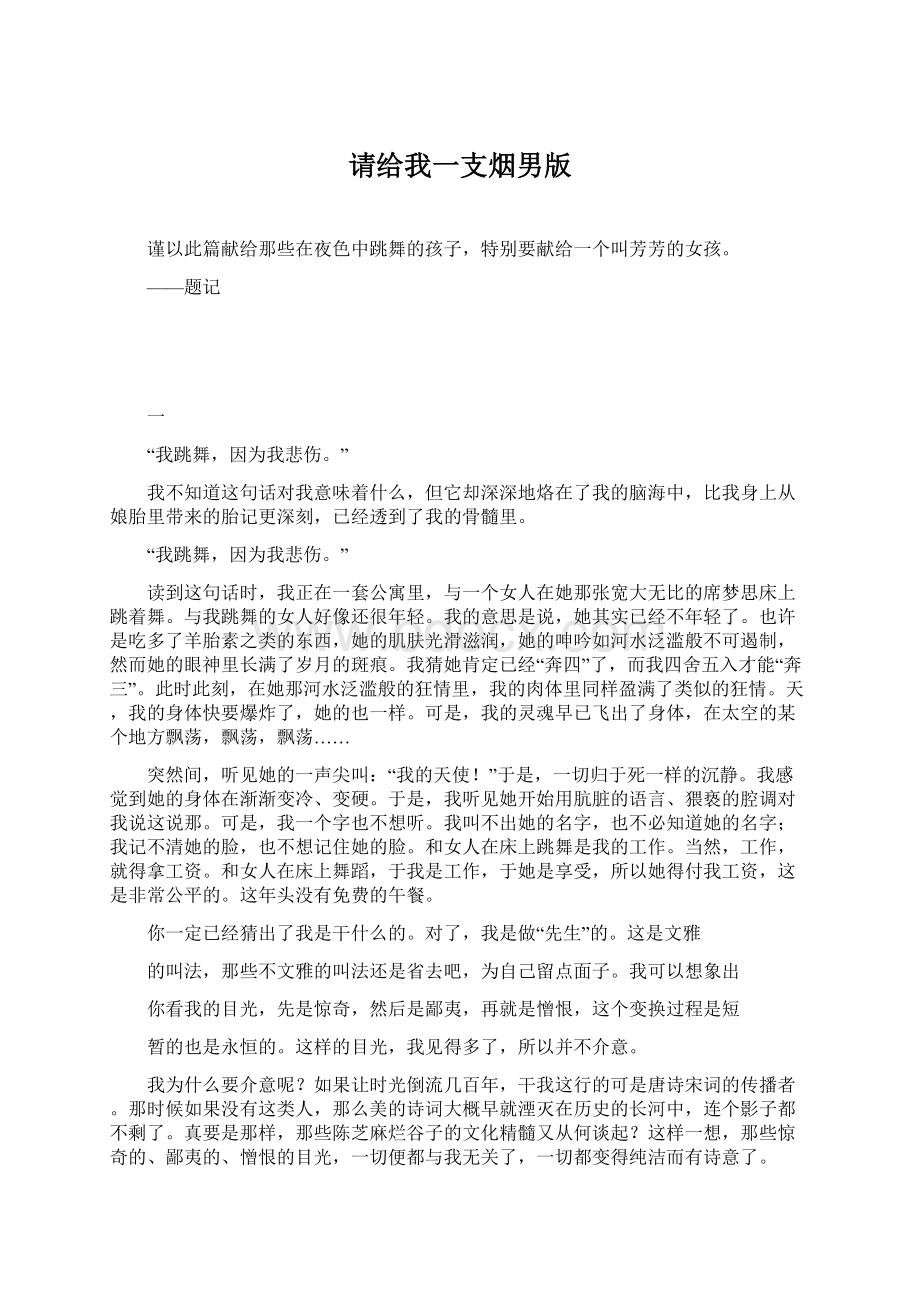
请给我一支烟男版
谨以此篇献给那些在夜色中跳舞的孩子,特别要献给一个叫芳芳的女孩。
——题记
一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
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但它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中,比我身上从娘胎里带来的胎记更深刻,已经透到了我的骨髓里。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
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在一套公寓里,与一个女人在她那张宽大无比的席梦思床上跳着舞。
与我跳舞的女人好像还很年轻。
我的意思是说,她其实已经不年轻了。
也许是吃多了羊胎素之类的东西,她的肌肤光滑滋润,她的呻吟如河水泛滥般不可遏制,然而她的眼神里长满了岁月的斑痕。
我猜她肯定已经“奔四”了,而我四舍五入才能“奔三”。
此时此刻,在她那河水泛滥般的狂情里,我的肉体里同样盈满了类似的狂情。
天,我的身体快要爆炸了,她的也一样。
可是,我的灵魂早已飞出了身体,在太空的某个地方飘荡,飘荡,飘荡……
突然间,听见她的一声尖叫:
“我的天使!
”于是,一切归于死一样的沉静。
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渐渐变冷、变硬。
于是,我听见她开始用肮脏的语言、猥亵的腔调对我说这说那。
可是,我一个字也不想听。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也不必知道她的名字;我记不清她的脸,也不想记住她的脸。
和女人在床上跳舞是我的工作。
当然,工作,就得拿工资。
和女人在床上舞蹈,于我是工作,于她是享受,所以她得付我工资,这是非常公平的。
这年头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一定已经猜出了我是干什么的。
对了,我是做“先生”的。
这是文雅
的叫法,那些不文雅的叫法还是省去吧,为自己留点面子。
我可以想象出
你看我的目光,先是惊奇,然后是鄙夷,再就是憎恨,这个变换过程是短
暂的也是永恒的。
这样的目光,我见得多了,所以并不介意。
我为什么要介意呢?
如果让时光倒流几百年,干我这行的可是唐诗宋词的传播者。
那时候如果没有这类人,那么美的诗词大概早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个影子都不剩了。
真要是那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文化精髓又从何谈起?
这样一想,那些惊奇的、鄙夷的、憎恨的目光,一切便都与我无关了,一切都变得纯洁而有诗意了。
刚出道那会儿,我曾经接了一个客人。
记得我曾承诺她会飘飘欲仙。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让她兴奋起来并获得了高峰体验。
事后,她告诉我,她已十几年没有性高潮了。
我用面纸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我真想向世界大声宣布:
我,欧阳剑,一个从事最古老最卑贱职业的人,拯救了一个女人,唤醒了一个女人的生命。
尽管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那么低贱,那么卑微,那么龌龊,但是我的价值与他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次我没有收她的钱。
以后,我每每遇上这种可怜的女人,都是免费服务。
在每一次的免费中,无法挥去的羞耻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胜利者的骄傲。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又变回了自己,一个有血有肉的自己。
我承认自己是戴着面具走在阳光下,走在人群中,但这并不代表我是虚伪的。
这世上,哪个人不是戴着面具活着?
有一回我无意之中打开电视,画面上是一个威严的男人在作报告。
一看见这张脸,就觉得眼熟。
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搜索这张脸的信息。
终于想起来,这张脸曾经出现在我的小兄弟小姐妹们经常出入的夜总会,在那里,这张脸为了一个“小姐”与一个男人争风吃醋,大动干戈,风度扫地。
我看着画面里这张看起来道
貌岸然的威严的脸,听着他传教士布道般的慷慨陈词,我狂笑起来,笑得那张脸在我的眼里扭曲成粪坑里蠕动着的蛆,让人恶心想吐。
我和他都有两张脸,都只会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情景之中摘下面具,展现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是平等的,如同经过坟墓,所有的人都同样站在上帝面前。
当然,面具戴久了,就会觉得闷气,得摘下来透透气,这种摘是主动的,而不是像电视上那张威严的脸被动地摘。
主动摘,是为了完完全全地面对一个人,这个人是我想看到的,这个人曾经那么想感化我。
一个秋日的下午,天很高很蓝,秋阳在水中洗过了,很明澈。
我的那位大学校友张辉映,我只叫他阿辉,他现在的职业是吃公家饭的小官吏。
他从良知讲到了道德,从道德讲到了法律,试图让我迷途知返。
但在我看来,他讲的那些,与其说是在教育感化我,不如说是在卖弄自己的博学。
这么多年了,他的这种喜欢卖弄学识的脾性一点也没变。
在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话后,我告诉他,这些话还是说给他的下属听吧。
其实就是他的下属听了,也不过当作是逢场作戏,而且是一场极其无聊的戏,戏散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何况对于一个已经上了“山”下了“海”的人?
我回敬他的是这样一句话:
最卑贱的妓女往往是最圣洁的贞女。
他听了,只是淡然一笑,然后沉默了,看上去像在思考和回味我说的这句话。
这句话根本不是我的知识产权,是某本书上写的。
其实,他是从不回味和思考别人的话的。
他的习惯是,每每在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候,喜欢用模棱两可的沉默来应对,这就是他油滑的一面。
他在官场上是不是这样?
但我宁愿把他的沉默权当是默认。
后来他问我老了怎么办。
我说,到了做不动的那天,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拿去出版,不愁卖不掉。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总喜欢偷窥别人的私生活,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其实心里想得都快发疯了。
他们太需要偷窃别人的隐私来给平淡无味的生活添加调味剂了。
我把我的隐私写出来,不畅销才奇了怪了。
其实,我比谁都明白,这一行根本不可能干到老,干个三年五载后,就是心里想干,自己的身体也会说对不起了,因为那时“老二”将不再昂挺,从外到内都成了阳痿者。
一想到自己可能彻头彻尾地阳痿,我的心里便涌出空旷的苍凉来,仿佛看见自己猥琐地倚着墙晒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内心呼喊着自己的“命根子”。
但此刻,我别无选择,我无能为力。
从那个陌生女人的公寓里出来,正是清晨,太阳刚刚从夜色里探出头来。
差点忘了告诉你,不陪客人用早餐是我们的行规。
走在行人稀少的路上,睡意像三月的小雨密密地细细地轻轻地绵绵地缓缓而至,我赶紧戴上墨镜。
那睡意在墨镜阴郁的色彩里悄然退出。
清晨的阳光是没有出尽的汗,一点也不爽利,暧昧的。
透过墨镜,我看见了马路两旁蓬头垢面的法国梧桐,看见了空中密织如网的电线,看见了偶然飞过的一群家养的鸽子,看见了这座城市灰蒙蒙的天空。
凡夫俗子们从我的身旁走过,行色匆匆。
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凡夫俗子,是因为他们排斥与他们的眼光、与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们的行为艺术不同的人。
他们讲究共性,害怕个性。
他们以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总是以卫道者的姿态指责别人是错误的。
其实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是最俗陋的瓷器,是最经不起诱惑的亚当和夏娃。
他们害怕打破固有的平衡而达到新的平衡。
如果让我在凡夫俗子和行尸走肉之间选择,我宁愿做行尸走肉,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讨厌在阳光中看到的这一切,那是因为我讨厌阳光。
这阳光,总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情景。
那时我在阳光里打着瞌睡,那束阳光是从一个小窗户射进来的。
那扇小窗被铁栅栏分成了六块。
窗外是高得几乎要压下来的墙,上面的电网如蜘蛛网那么规则而密匝。
阳光翻过高墙,再越过枯草和青草混杂着的草丛,又爬上泛着青灰色的光的冰冷的墙,再穿越一道走廊,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跃到那扇被分成六块的小窗上,照射进屋内,最终射在了我的身上。
我之所以在阳光里打着瞌睡,是因为我的身体正接受一个男人的玩弄。
那一时刻我的身体和思维都是麻木的,唯有睡眠才能让我知道自己还存在着。
但那时我像一个被驯服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一切,我需要以自己的身体换取优越的“宫里”生活,那时我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我吃不起20元一盘的青椒肉片,吃不起15元一盘的麻辣豆腐,也吃不起10元一块的走油肉,我只能吃刷锅水般的免费菜和带着异味的免费米饭或馒头。
而那个人却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我所需要的饭菜的费用,于是我顺从了他。
从他那里我明白了两个道理:
一贫如洗是一种罪!
男人的美丽同样是本钱!
想起那一幕幕,我就会悲伤。
但是,这种悲伤是伴着喜悦的,因为它让我知道了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起码还有自己的身体和漂亮的面孔,那本身就是赖以生存的本钱。
于我,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
我与陌生女人在床上跳舞时,虽然没有任何悲伤,但是这句话勾起了我心灵深处的那种悲伤。
这一时刻,我把喜悦给了肉体,而把悲伤给了灵魂。
但是我没有泪。
我从来就不知道眼泪是个什么东西。
二
我没有眼泪,那是因为我不怕疼痛。
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烈火中永生》,那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受刑的场面。
同学们看了都在说共产党员的意志如何坚强,有的人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长大后,要做江姐、许云峰那样的共产党员。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正我没这样想。
我想到的是:
他们受刑的时候难道不疼吗?
我偷了养父的香烟,点上,然后把燃着的那头按在我的大腿上,疼,钻心地疼,我还闻见了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
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闭着眼睛,想象着自己是电影中的某一个地下工作者,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岿然不动。
这样经历了记不清的次数之后,一切跟肉体相关的疼都不过是被养在身体上的虱子咬了一口,轻描淡写,雁过无声。
在“宫”里头,电棍、殴打、鸡奸等等给我的疼痛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对疼痛的感觉是麻木的。
我曾经试图寻找自己对于疼痛麻木的根源。
在大学里,我确实在这一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
有一段时间,我不去上课,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到理论上的说法。
很遗憾,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并不失望,因为找不到理论,反而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身世是造成我不怕疼痛、不会流泪的根本所在。
让我告诉你吧,我是一个私生子。
我的养父从没有向我隐瞒过这一点。
我觉得养父是个很真实的人,他没有用美丽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这让我有了很强的承受能力。
每当他喝了酒之后,就会骂我是“婊子养的野种”。
对于婊子和野种这两个在凡夫俗子们看来带有侮辱性的词,我早就习以为常了,我从没有觉得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好,它们只能说明我与别人的不同。
我确实与别人不同。
念中学时,因为打架和早恋,转了三次学校。
没有人对我抱有希望,老师说我是人渣,不可救药。
但问题是,我居然考上了大学。
一位对我恨之入骨的老师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时,竟发出这样的惊呼:
“上帝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
”亏他还是个无神论者,居然也会用“上帝”这个词。
不过,这是一句多么可爱的感叹,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有“香港脚”的人喜欢挖自己的脚丫子一样。
养父虽然骂我是野种,仿佛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但我以为,他还是以我为自豪的。
要不,他不会在我考上大学那会儿请了两桌酒,这可花掉了他半年的工资。
我想,与其说他是在祝贺,不如说是在炫耀,或者说是在向凡夫俗子们反击。
养父是在我“坐宫”的时候去世的。
是那个曾经想感化我的张辉映帮我操办了丧事。
在我“坐宫”的时候,养父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也没流一滴眼泪。
我对前来探监的张辉映说:
“现在一切都解脱了。
阿辉,我告诉你呀,我不是他亲生的。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生子,是只浑身爬满虱子的野狗。
”我这是第一次向一个外人坦白自己的身世。
阿辉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大概他以为,我肯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而胡言乱语,便说了一气安慰我的话。
其实对于“坐宫”我从来就不在乎,“坐宫”就“坐宫”呗,读不了大学就读不了大学,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对着阿辉笑了笑,说:
“我真的是个私生子,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我只知道她与老爸本来是在一个剧团唱戏的,跟一个唱小生的生下了我,然后就抛下我,跟那个唱小生的跑了。
老爸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毁了,连她的照片我也没见过。
”阿辉的眼里突然有一星泪光在闪动,我知道他在滋生文学的感动,这种感动随着文字的形成,就会烟消云散的。
阿辉把两只手都贴在玻璃上,我的手也贴了上去,我们都没有说话。
但探监的时间到了,他说:
“我会常来看你的。
”不知为什么,我背过身走向牢房的那一刻,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
管教厉声问我笑什么,我说浑身痒得难受,管教便给了我一个耳光,说是替我杀杀痒,可我笑得更厉害了。
因为笑不出眼泪,管教说我在装疯卖傻。
那天我吃了管教五个耳光,脸都红肿了,却感觉不到疼。
我一直认为,担当改造别人的角色的人,大抵都有施虐的倾向,而被改造者又都有受虐的潜意识,否则就达不到平衡。
达不到平衡的人群,还能存在吗?
教官的耳光与我的笑声,就是达到平衡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我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那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出乎意料地思念我的养父。
当捧着饭碗时,我想起了养父做的狮子头,还有油炸臭豆腐,还有他每晚咪酒时散发的酒香。
当管教们教训我的时候,我想起了养父给我的耳光,耳边响起他的骂声:
野种!
跟那婊子一样的野种!
当夜晚降临,牢友们花钱去看电视,我一个人蹲在牢房里,透过小窗对着苍茫的夜色发呆,我又想起了养父,想起了他唱的戏。
在“坐宫”的日子里,每一个失眠的夜晚,我都能听见一种鬼鬼祟祟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同牢房的那几个小瘪三躲在被子里手淫。
在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里,这种声音就像春夜里猫的叫春声,很能催生春情。
可是我几乎丧失了性的欲望,我讨厌那样的声音就如讨厌人们在吃饭时讨论着大便。
这时,养父的唱戏声就会很清晰地飞进我的耳朵里。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养父的唱戏声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那样的氛围里出现,甚至连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吐字、每一次换气,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眼前老是晃动着养父的那件戏袍。
其实,此时我听到的唱词和看到的戏袍都是毫不相干的。
我听到的往往是养父在《甘露寺》里扮乔玄的一段唱,唱词里说的是乔玄劝说孙权和吴国太不要杀刘备的事,听养父说这是马连良最著名的唱段,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晓得马连良是谁,我只晓得京剧里有个男扮女装的梅兰芳。
唱戏声渐渐消失了,可是养父演戏时穿的那身戏袍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戏袍可不是乔玄穿的,而是西楚霸王项羽穿的。
听养父的那些戏友说,养父演《霸王别姬》很拿手,演虞姬的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当时在小县城里是有名的美人儿。
他们说我笑起来时像她,我说我又不是女人。
现在想想,我那位母亲的眼睛一定生得很妩媚,专勾男人的魂的,没准儿养父就是被这双眼睛勾住的。
她的眼睛一定是生在了我的脸上,要不,他们怎么说我笑起来像她呢?
这种眼睛生在女人的脸上是妩媚,要是生在男人脸上就是淫荡了。
有时我讨厌这双眼睛,它让我看起来像个坏人,可它却是我养活自己的本钱。
男人喜欢妩媚的女人,女人喜欢淫荡的男人。
这是生活告诉我的。
其实我看到的那件戏袍早在我14岁的时候就被养父亲手烧掉了。
至今我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烧掉它。
烧了就烧了,为什么还要把烧成的灰埋了?
我是在养父烧戏袍的那天,发现养父老的。
那天,我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无所事事地打着瞌睡,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锣鼓声和京胡声,我知道养父和一帮票友又在树荫下面折腾开了。
他们的京剧于我真的是毫无意义,他们唱来唱去,我怎么着都觉得是一个调子,有时一个字得拖很长时间,听着都嫌烦。
可养父他们就是那么乐此不疲,除了下雨下雪,天天都这么折腾,有时在树荫下,有时在公园里,有时在巷子的某个天井里。
听街坊邻居说,养父先前在小城里唱戏名气挺牛,《霸王别姬》、《铡美案》是他的拿手戏,特别是在《甘露寺》中,他由花脸反串了一把老生,更是轰动一时。
后来,剧团解散了,他又没多少文化,只好到工厂当了工人。
那边京胡声传来,养父就唱了起来,没唱几句,声音陡地一变,嗓子仿佛被什么划了一下,接着那边就鸦雀无声,后来京胡又拉开了,还是那调,养父唱的还是那几句,一到先前卡壳的地方便又卡住了。
我知道他的嗓子倒了,这意味着他以后再不能唱了。
这样反复了好多次后,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养父朝家这边走来,低垂着头,步履有点蹒跚,好像生了病似的。
我愕然发现养父的双鬓已经斑白,养父老了呀!
我奔下楼去,上前扶住他。
他用力一把推开我:
“野种,给我闪开!
”我说:
“你骂什么人?
好心没好报。
”他瞪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就骂你这个婊子养的野种!
”我说:
“没老野种,哪有小野种!
”他滔滔不绝地骂着进了家门。
一进家门就从箱底翻出那件绣着龙的戏袍,抱在怀里,脸埋在戏袍里,呜呜地哭起来。
我懒得去劝慰他,由着他在那儿独自流泪好了,自己拿了本书和一包香烟到阳台上去享受阳光。
那时候,我喜欢阳光。
我不知道养父是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的,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冲到我面前,一把夺走我手中的香烟,朝楼下的天井里扔去。
那大半包香烟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全都散落出来,落在地上横七竖八,像鼻涕虫爬过后留下的痕迹,杂乱无章,却是千丝万缕地连着的。
养父说:
“老子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可不是让你这么不学好的!
”我说:
“反正我是野种,学不学好跟你没关系!
”养父忽然软了下来,说什么以后再也不会骂我野种了,并拿出钱让我去给他买猪头肉和啤酒。
养父脾气暴躁,但有他的优点,那就是说话算话,像个爷们。
我们这里的男人与江南和上海的男人很相似,像爷们的少,像娘们的多,大多是些“母男人”。
打这以后,他还真的没骂过我野种,我和他安安稳稳地过了一段日子。
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校和人打架,被学生家长告到家里来,他又开骂了,只是这次把“野种”改成了“孽种”。
我一直以为养父就是“诚信”的代名词,否则,我早就离开他,流浪去了。
我到巷子头上称了一斤猪头肉,买了一打啤酒。
那天晚上,养父就着猪头肉、臭豆腐干,还有中午剩下的一些蔬菜,开始还是一瓶酒分三至四次喝完,到最后三瓶时,就是一仰脖子,咕咚咕咚,那硕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游动着,不换一口气,一瓶酒就这么下去了,一打啤酒和一斤猪头肉一扫而光。
我知道养父的酒量很大,可从没看见他喝得这么猛。
看着他喝酒,我就想,倒嗓对他的打击难道就那么大?
唱戏对他就那么重要?
喝光一打啤酒,养父的脸色一点没变,但话少了不少,眼里有些伤感的东西。
后来,他站起身来,到里屋把那件戏袍拿了出来,披在身上。
我愕然发现,在夜晚的灯光下,它是那么熠熠生辉,上面的那条用金丝线绣的金龙呼之欲出。
如果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它一定是金碧辉煌的,但这种金碧辉煌又是傲视一切的,穿上它的人也就有了一种霸气。
它绝对是一件精品!
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养父叹着气从身上扒下了它,然后来到天井里,点上了火。
我惊叫:
“别烧!
”养父没有理我,只是用火钳拨弄着它,火便更旺了。
火光映出养父的脸和头颅,脸上的皱纹像水波纹似的流动,头发是灰白的,没有一丝生机。
这一瞬间,我意识到养父已经很老了。
火熄灭了,养父完全沉在了黑暗中,他蹲在那堆灰前,一动不动,四周非常静,静得叫人想喊出来。
突然间,我听见他像在舞台上唱戏那样长叫一声,然后就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把地上的灰用手一捧一捧地捧进一只小布袋里,然后出了家门。
我跟着他,来到他跟戏友们经常聚会的那棵银杏树下。
只见他在地上挖了个坑,把那个装了灰的布袋埋了进去。
树下一片黑暗,从人家屋里窜出来的几星灯光,只是加重了这黑的颜色。
现在我每每回想起这一幕,就会贸然想起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的一句话: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养父并没有成就某种事业,但他依然那么英勇,那么卑贱。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孩子,一个介于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孩子,一个在夜色中跳舞的孩子。
三
我现在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编外先生”。
当我决定入这一行的时候,“爹地”李老大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做编内的还是做编外的。
李老大就是我“坐宫”时的牢头,那时他是我的“丈夫”。
他现在是我们这些先生的“爹地”。
他开了一家“夏娃河”酒吧,那是我们这些“先生”在这座城市里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我问他,编外和编内有什么不同。
他说,编外得靠自己的本事找生意,而编内则有他的保护,但要听他的管教。
听到“管教”这个词,我就感冒。
从学校到监狱,我受够了各色人种的管教,我怕了,厌了。
我要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于是,我选择了编外。
李老大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语重心长地看了看我,说我虽然是编外的,但他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护我,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喜欢我的,在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他是唯一帮助我的人。
问题是,我对他从来就没有兴趣。
“坐宫”的日子已经过去,我要做一个独来独往、无拘无束的“编外先生”。
但这段时间我无法做生意,因为这座城市正在“刮台风”。
据说,这是一个记者挑起的事端。
这位记者在南下的火车上,听见两位四川妹子在议论这座城市“小姐”的生意如何如何好做,便在这座城市下了车。
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遍这里所有的歌舞厅、酒吧,还有这里的长江街和润河街,回去写了份内参,说这里的色情业已泛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后来这里的“台风”就“刮”起来了。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记者是最无聊最没骨气的一群,他们只会反映事物的表象,而没有勇气揭示表象后面的本质。
就拿那位记者来说吧,他只说出这座城市的色情业如何如何泛滥,并没有去调查为什么会泛滥。
白痴也知道,任何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存在。
我可以告诉你,玩弄我们这些“小姐”和“先生”的,大多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钱有势有社会地位,他们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和虚荣心一掷千金,却舍不得为慈善事业拿出一分钱。
对于这样一群生活在阳光下的正人君子,大多数记者所做的只能是敬而远之,有的还做出种种令人作呕的谄媚之态。
而对我们这些“小姐”和“先生”却是横眉冷对,义愤填膺,仿佛我们是罪恶的根源。
明眼人都明白,正是因为有钱有势有地位的嫖客群的存在,才有了我们这些“小姐”、“先生”的存在,这叫相辅相成。
这世界就是在相辅相成、相生相克中达到了平衡,世界因平衡而存在。
虽然正在“刮台风”,但我没有像其他的“小姐”、“先生”那样,从银行里取了款,逃到家乡去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卷土重来。
我只是换了一个手机黑号,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家对我而言,已成了一个空虚的名词。
养父去世后,那点私房钱全部用来偿还家里欠下的债务了。
等我出狱,我已是一无所有,到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只要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行。
“刮台风”的日子,对我而言是吉日。
我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坐下来,舔一舔自己身上的伤口,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进行修理。
充足的睡眠,丰富的营养,还有健身房里的锻炼,已让我的体力和机能得到充分的恢复。
接下来的,就是无所事事。
我早就什么书都不看了,因为我不再相信书上说的一切,那上面全都是在放屁。
不可否认,我虽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在学校我读了许多书,不比一些教我的老师读得少,就是在“坐宫”的时候,我还在读书。
我曾让张辉映从外面捎进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书捎进来的时候,阿辉做了技术处理。
因为那两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
“在美国被封禁了数十年之久的成人小说。
被西方文学史称之为巅顶之作的反叛文学。
”“成人”和“反叛”这两个词,对凡夫俗子们具有强大的魔力,一方面他们渴望读到它,读他们想象中的性描写,他们用身体进行阅读,一边读一边分泌着荷尔蒙;另一方面,在所有的公共场合振振有词,把它贬得一钱不值。
想到这两个词,就看到了他们的目光,那是尘埃浮动的阳光里被唾液和体液污染过的钻石的光芒。
把这样的书带进了“宫”里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等待我的将是罪加一等。
一开始阿辉是怎么也不肯的,探监结束的时候还对我咬牙切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再次来探监的时候,他给我带来了两本政治家文集之类的书。
我说:
“给我上政治课呀?
”阿辉说:
“我还不是希望你早点出来。
”阿辉走的时候,手指在那两本书上轻轻点了点,给了我一个很怪异的表情,我就知道那书里有文章的。
打开一看,果然,这两本书的外壳下裹着《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亏阿辉想得出来,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计,将这两类毫无共通之处的书做得这样浑然天成。
我捧着书,抑制不住地笑出来。
我真是爱死他了!
爱死他了!
如果我是女人,就做他一辈子的玩物,不要任何的名分;如果他也有牢头李老大的那种需求,我会义无反顾地把第一次那种撕裂心肺般的疼痛献给他,而我绝不会有一丁点的心痛。
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爱读书了吧,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只是那两本书,现在我能记住的只有其中的一句话:
得到面包比吃面包更重要。
这句话说出了活着的真谛。
看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不管有着怎样的性别,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有着怎样的经济基础,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得到面包的方式。
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不再读书,是因为一件事。
我出狱后,在一家网吧找了份差事,那是我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熟人帮的忙。
那时的网吧还不像现在这样多。
到我工作的那个网吧上网的大多是些大学生。
有一天,那个网吧的10台电脑的内存和硬盘一夜之间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