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docx
《读书心得《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读书心得《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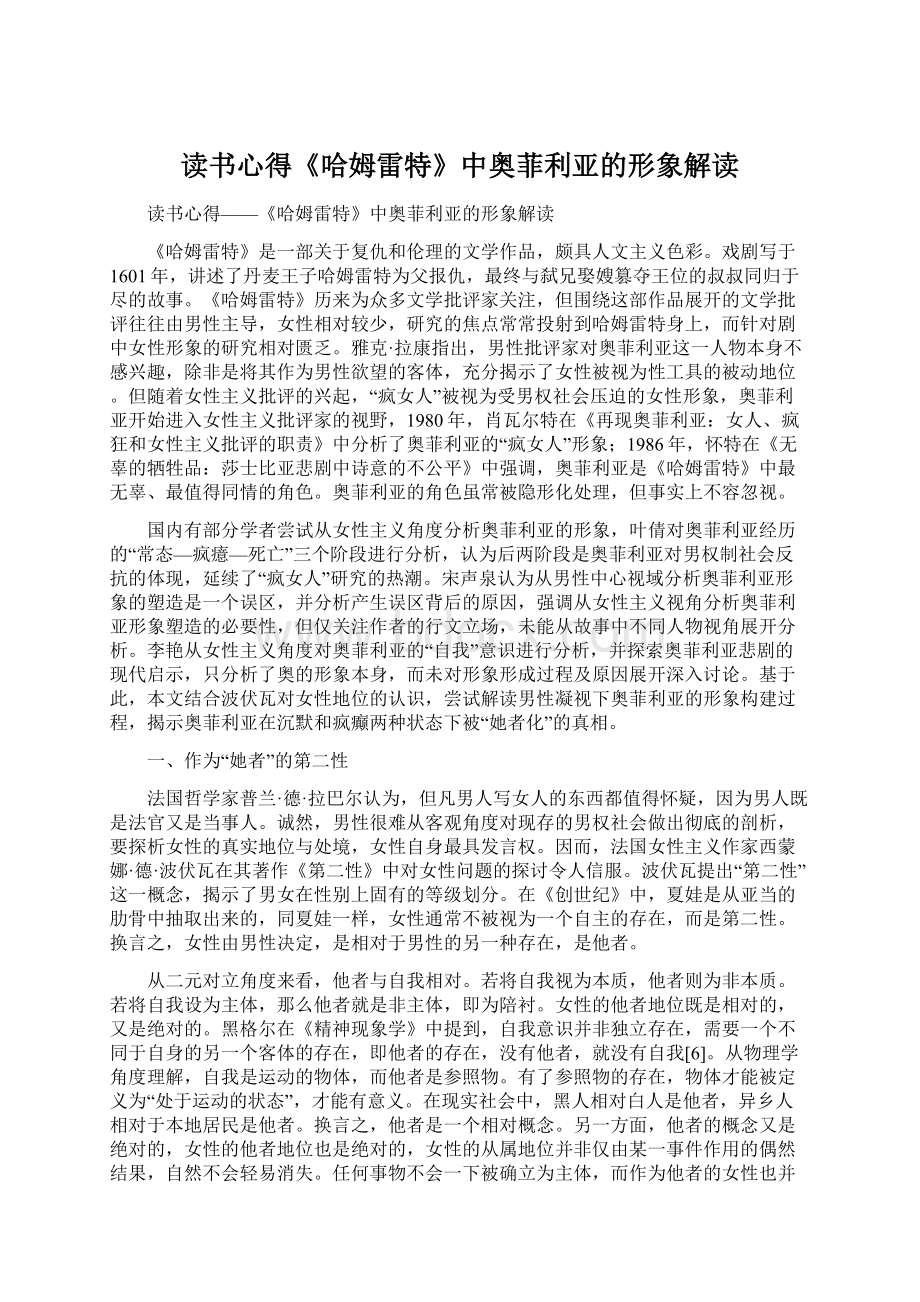
读书心得《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
读书心得——《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
《哈姆雷特》是一部关于复仇和伦理的文学作品,颇具人文主义色彩。
戏剧写于1601年,讲述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最终与弑兄娶嫂篡夺王位的叔叔同归于尽的故事。
《哈姆雷特》历来为众多文学批评家关注,但围绕这部作品展开的文学批评往往由男性主导,女性相对较少,研究的焦点常常投射到哈姆雷特身上,而针对剧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相对匮乏。
雅克·拉康指出,男性批评家对奥菲利亚这一人物本身不感兴趣,除非是将其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充分揭示了女性被视为性工具的被动地位。
但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疯女人”被视为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形象,奥菲利亚开始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视野,1980年,肖瓦尔特在《再现奥菲利亚:
女人、疯狂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职责》中分析了奥菲利亚的“疯女人”形象;1986年,怀特在《无辜的牺牲品:
莎士比亚悲剧中诗意的不公平》中强调,奥菲利亚是《哈姆雷特》中最无辜、最值得同情的角色。
奥菲利亚的角色虽常被隐形化处理,但事实上不容忽视。
国内有部分学者尝试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奥菲利亚的形象,叶倩对奥菲利亚经历的“常态—疯癔—死亡”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后两阶段是奥菲利亚对男权制社会反抗的体现,延续了“疯女人”研究的热潮。
宋声泉认为从男性中心视域分析奥菲利亚形象的塑造是一个误区,并分析产生误区背后的原因,强调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奥菲利亚形象塑造的必要性,但仅关注作者的行文立场,未能从故事中不同人物视角展开分析。
李艳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奥菲利亚的“自我”意识进行分析,并探索奥菲利亚悲剧的现代启示,只分析了奥的形象本身,而未对形象形成过程及原因展开深入讨论。
基于此,本文结合波伏瓦对女性地位的认识,尝试解读男性凝视下奥菲利亚的形象构建过程,揭示奥菲利亚在沉默和疯癫两种状态下被“她者化”的真相。
一、作为“她者”的第二性
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认为,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
诚然,男性很难从客观角度对现存的男权社会做出彻底的剖析,要探析女性的真实地位与处境,女性自身最具发言权。
因而,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令人信服。
波伏瓦提出“第二性”这一概念,揭示了男女在性别上固有的等级划分。
在《创世纪》中,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中抽取出来的,同夏娃一样,女性通常不被视为一个自主的存在,而是第二性。
换言之,女性由男性决定,是相对于男性的另一种存在,是他者。
从二元对立角度来看,他者与自我相对。
若将自我视为本质,他者则为非本质。
若将自我设为主体,那么他者就是非主体,即为陪衬。
女性的他者地位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到,自我意识并非独立存在,需要一个不同于自身的另一个客体的存在,即他者的存在,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6]。
从物理学角度理解,自我是运动的物体,而他者是参照物。
有了参照物的存在,物体才能被定义为“处于运动的状态”,才能有意义。
在现实社会中,黑人相对白人是他者,异乡人相对于本地居民是他者。
换言之,他者是一个相对概念。
另一方面,他者的概念又是绝对的,女性的他者地位也是绝对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并非仅由某一事件作用的偶然结果,自然不会轻易消失。
任何事物不会一下被确立为主体,而作为他者的女性也并非是自我界定为他者的。
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而相继“被成为”他者的。
追溯历史可知,男性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继而女性成为一种附属,长期在男性的统治之下,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女性对于男性而言,是性伙伴,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是性欲对象,是他者,通过女性,男人寻找自己。
存在主义观点认为,人在自由选择中不断构建本质,有了本质才有主体性,因而自由是主体性的基础。
相比男性而言,女性往往是不自由的,女性在男性眼中是性的客体,是可交易的商品,是可支配的财产。
这种根深蒂固的划分使得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局面,她们很难自我确定为主体。
久而久之,女性的他者地位成为一种普遍认知,深深扎根,最后被内化接受,让人毫无察觉。
作为第二性,女性不只是“他者”,更是“她者”。
二、男性凝视下的奥菲利亚
视觉既是一种生物本能,也参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视觉投射方法,凝视常常携带着权利运作。
凝视者占据主体地位,有权“看”处于被动地位的被凝视者。
观者通过实施“看”的特权确立地位,向被观者施压,被观者承受压力的同时不断内化观者灌输的价值判断,进而自我物化。
《哈姆雷特》中,男性角色较多,但与奥菲利亚联系较紧密的有:
其爱——哈姆雷特、其父——波洛涅斯、其兄——雷欧提斯。
除此之外,其塑造者莎士比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波洛涅斯及雷欧提斯即为享有特权的观者,而奥菲利亚则长期被裹挟在男性凝视下,难以摆脱被控制、被利用的命运。
(一)莎士比亚凝视下的奥菲利亚
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常常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仙女”型,另一种是“巫女”型。
前一种女性常具有天真柔弱、纯洁善良、美丽温柔的特点,而后一种则表现出凶狠毒辣、淫荡邪恶、自私蛮横的一面。
两种形象分化为两极,要么完美化,要么妖魔化。
爱莲娜·肖沃尔特称这种做法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或“对女性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
奥菲利亚在《哈姆雷特》的两种形象则恰巧符合两大类型:
戏剧伊始,奥菲利亚的形象呈“仙女型”,与兄长对话时,她天真可爱,与父亲交谈时,她乖巧温顺,在哈姆雷特的描述中,她美丽善良;遭遇变故后,奥菲利亚以疯癫的形象示人,言行举止轻佻叛逆,与之前判若两人,转变为“巫女型”。
依照肖沃尔特的说法,莎士比亚对奥菲利亚形象的塑造则属“文学虐待”。
此外,莎士比亚创造的奥菲利亚具有一定模式化,远不如其笔下性格丰富的男性角色,这种创作手法看似未对女性产生压制,实则束缚了女性性格的多元化发展,这反映了潜藏在莎士比亚内心深处的男权意识。
父权文化系统是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前提,父权社会背景下派生的文化价值系统常以维护父权制为目的。
莎士比亚在其创作中包含着“厌女”成分,因而其笔下的情节安排大都表现着男性主宰、女性服从、男性优越、女性低劣的倾向,这一公式化的写作范式绝非偶然,而是男性权力支配的文学痕迹。
《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将奥菲利亚设定为人物关系的纽带,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她激起哈姆雷特与波洛涅斯间的矛盾,也刺激雷欧提斯实施复仇行动,她的爱情让波洛涅斯对哈姆雷特的试探成为可能,她的软弱和不坚定是哈姆雷特迷茫延宕的原因之一,她的疯癫与死亡坚定了雷欧提斯不顾一切复仇的决心。
然而,在整部作品中,如此重要的奥菲利亚自始至终只出现了七次,这使她成为不在场的“她者”。
除了作为情节联结点以外,奥菲利亚还充当了哈姆雷特的镜像。
拉康认为奥菲利亚是以客体身份存在的,仅仅是哈姆雷特的陪衬[10]。
奥菲利亚身上展示的是哈姆雷特阴柔的一面,两个人物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情节的发展却截然不同,二者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加深了戏剧的悲剧性。
两人都因父亲的告诫而进退维谷,两人的父亲都因“不明原因”离世,两人都孤独、迷惑、痛苦,且都有被背叛的感受。
最突出的相似点在于两人都被定义为“疯癫”,不同的是,哈姆雷特的“疯癫”是伪装出来的,带有目的性,而奥菲利亚的“疯癫”则是受到现实压迫下的真实反映。
虽然给两人设定了相似的经历,但莎士比亚终究忘不了维护男性英勇的形象,他赋予了哈姆雷特冲破束缚,奋起反抗的勇气和智慧,而将柔弱卑微的牢笼套住了奥菲利亚。
(二)哈姆雷特凝视下的奥菲利亚
在男权主义社会中,女性注定是屈从的、被占有的、被利用的,她们的形象始终是通过男性的意识塑造的[5]100。
在哈姆雷特的凝视下,奥菲利亚的形象经历了变化和发展,但始终摆脱不了被物化的悲剧。
对于哈姆雷特而言,奥菲利亚有四个“物”的形象:
宝物、玩物、厌物和弃物。
哈姆雷特一开始将奥菲利亚视作人间珍宝,他在情书中极力抒发对奥菲利亚的爱慕之情,称她为至爱。
出于“装疯”的需要,哈姆雷特利用奥菲利亚,将她当作玩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玩弄感情,为的是传递出他已经发疯的假象,掩盖他真正的动机。
母亲的改嫁和奥菲利亚在爱情里的软弱让哈姆雷特产生“厌女”心理,他在第二幕第二场中称“人不能使我欢喜,不能,女人也不能”[11],由此表述可知,哈姆雷特将“女人”与“人”区分开来,暗示哈姆雷特将奥菲利亚异化为“物”,刻画了她“厌物”的形象。
波伏瓦[5]109认为,女人完全被归入了东西的行列,而男人力图用他征服和拥有的东西来装饰自己的尊严。
奥菲利亚下葬时,哈姆雷特向雷欧提斯证明自己的爱,但“爱”(loved)的时态限定在过去,表明了爱的期限。
即使是“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也终究落得被丢弃的下场,可见此阶段的奥菲利亚已然成为哈姆雷特自证清白的凭证物,是被遗忘在时光隧道里的弃物。
(三)波洛涅斯眼中的奥菲利亚
父权制下,女性属男性的财产,首先这份财产的物主是她的父亲;通过婚姻,他把她转让给她的丈夫[5]110。
对于波洛涅斯而言,奥菲利亚是一份私有财产,因而他要求财产“保值”,甚至是“增值”。
得知女儿与王子有来往时,波洛涅斯对女儿冷嘲热讽,贬低奥菲利亚所珍视的爱情,认为奥菲利亚无知愚昧,要求女儿自重以“保值”。
他告诫奥菲利亚,“把自己的价值抬高一些”[11]57,拒绝哈姆雷特,以“增值”。
在严格的父系制下,父亲对少女有一切权力,他可以在女孩出生时决定女儿的生死,例如阿拉伯人的文化里存在女孩一出生便被遗弃的大量例子。
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合法地进行群居生活,要受到严格的贞操管束。
除此之外,作为财产的女儿又是可以任由父亲支配的,父亲可以按照意愿控制女儿的行为。
旧约《圣经》里,弗耶将女儿作为祭祀品献给了神[12]。
同样地,波洛涅斯干涉女儿的感情,把女儿当作试探他人的工具,这样的干涉、利用行为在父权制下的西方社会乃至中国古代社会俯拾皆是。
波洛涅斯在开场时否定奥菲利亚与哈姆雷特的爱情,禁止女儿与哈姆雷特来往,却因想在国王、王后面前立功而将女儿作为“诱饵”,企图探究哈姆雷特“发疯”的原因。
从父女二人相处的过程来看,波洛涅斯自始至终没有真切考虑过奥菲利亚的内心感受,他曾用冷言冷语扑灭这个天真少女对爱情的渴望,让女儿承受爱而不能的悲痛,继而又利用女儿的爱情为自己谋求利益,任由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施加语言暴力。
哈姆雷特戏谑地称波洛涅斯为“鱼贩子”(fishmonger),在俚语中,“鱼贩子”一词有“妓院老板”之意,哈姆雷特选用这一词汇,既讽刺了波洛涅斯利用女儿作诱饵的举动,同时揭露了奥菲利亚作为被交换物品的卑微地位。
(四)雷欧提斯眼中的奥菲利亚
女人的第一监护人是他的父亲,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由父系的亲属完成这个职权[5]110。
雷欧提斯是奥菲利亚的兄长,是奥菲利亚的另一个监护人。
雷欧提斯将妹妹视作天使一般的女孩,从他对奥菲利亚的呵护与关切中可窥见其内心对于女性的期待与训诫。
雷欧提斯希望奥菲利亚温柔顺从,反复向奥菲利亚强调贞洁对女性的重要性。
他提醒奥菲利亚要守住“贞洁的宝藏”,认为“一个顶规矩的姑娘只要对着月亮显示了她的美丽,便算是极度放肆了”[11]51。
雷欧提斯眼中闪烁的对奥菲利亚的期盼正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凝视。
自古以来,贞洁是女性绕不开的话题。
西方文化里,贞洁具有宗教意义。
在中国文化里,从一而终、坚贞不渝的女性被视为纯正高洁的典范,贞节牌坊成为女性的殊荣;不遵从贞洁规训的女性则被视为十恶不赦,承受社会的指责与相应的惩罚。
贞洁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单向度标准,而这一标准对于男性则失去限制性,这种不对等的双向标准深度刻画了男女地位的不对称性。
男性将女性看作私有财产,并要求女性保持童贞,丈夫希望妻子原封未动,归己所有,因为确定财产属于自己的最稳妥方式是阻止他人享用它[5]218。
无人涉足的新土地对探险者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因为这种征服独一无二、史无前例,有无法想象的新鲜感。
同样地,男性将女性的身体看作是一个被动的、可以征服的物体,他要在占有前确保自己是开拓者,以确认自己的物主身份。
三、奥菲利亚的“她者”形象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下,奥菲利亚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是非主体的“她者”,也是被物化的“她者”。
正如父母给新生儿取名时会寄予期望,作家在给作品中人物取名时往往有设定角色的目的。
奥菲利亚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意为“帮助者、救济者”[13],对于莎士比亚而言,奥菲利亚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辅助角色,他是男性的镜子、工具和财产,她被男性训诫、控制,又被男性利用,她的“她者”形象未曾变化。
面对不被父兄认可的爱情,她无力反抗,选择了沉默、屈服和顺从,甘作被物化的“她者”。
面临亲人和爱人离去的双重打击,她打破沉默,在疯癫中自由发声,看似找回了话语权,然而,疯癫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状态,疯癫状态下人的话语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因而发疯的奥菲利亚踏入的是另一种边缘化地带。
(一)不说话的“她者”形象——物体
福柯认为,话语是被建构的,权力参与了话语的建构过程,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
占据统治地位的主体掌握着话语权,而处于“她者”地位的非主体则很难享有话语权。
男权制要求女性保持沉默,认为沉默是女性的高雅举动,顺从是女性的一种美德。
奥菲利亚的“她者”形象在男性话语中得以塑造,她宛如一个柔软的面团,被动地任人揉捏,她的顺从和让步让男性的塑造行为显得合乎自然,也使得她的主动权磨灭殆尽。
奥菲利亚本对爱情充满幻想和向往,却在父亲和兄长的话语压迫下,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丧失主体性。
她听从父兄的教诲,放弃爱情,配合父亲的指令,佯装看书,成为父亲和国王刺探哈姆雷特秘密的工具,她内心的声音渐渐减弱,她的感受完全被忽略。
尽管她也曾为爱辩驳,但在强势的父权制文化下,她含糊而不坚定的言辞实在微不足道。
面对恋人哈姆雷特的冷言恶语,她伤心欲绝,却无法将内心的真实感情传达出来,只能默默忍受语言暴力。
在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看来,若女性活在男性话语体系中,且总是向处在对立面的男性求助,她特有的精神会被消灭,她的声音会减弱直至湮灭。
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做的就是打破秩序,扭转局面,奥菲利亚选择打破秩序,在一种自由且无罪的疯癫状态中发出内心的真实声音。
(二)说话的“她者”形象——疯癫
尼采认为,长期被禁锢在秩序与规训之下的人会忧郁狂乱,若找不到发泄渠道,唯一的选择是在自身寻找出口,正如人在被逼入绝境之后往往选择向死而生。
奥菲利亚在男性话语控制下生活,失去了言说的权利,也失去了爱情。
当父亲去世,兄长远游,恋人离去后,围绕在她周围的声音散去,她开始打破沉默,“疯癫”成为她的出口。
根据福柯的观点,疯癫既是一种医学上的病理现象,又是文明进程中的社会产物,是文明时代理性压制非理性的结果[17]。
理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对道德的约束及对群体的要求。
疯癫超越了社会秩序,是一种无序的精神状态,因而被视作“理性的他者”。
奥菲利亚生活的环境里,父权制对女性的要求构建了理性,而这种理性让她窒息,使她不得不在非理性中寻找喘息的空间,她需要在疯癫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发出声音,找回主体性。
仔细品味奥菲利亚发疯后零碎的言语和她吟唱的民谣,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与哀怨。
她一共唱了四首歌,第一首的主题是死亡与埋藏,第二首歌主题为诱惑与背叛,后两首是挽歌,既唱给父亲,又唱给自己。
四首歌曲主题不同,却无一不饱含着女性对社会的控诉、抗议与哀痛。
借助疯癫状态下的话语和歌声,奥菲利亚刺穿了理性的覆盖层,诉说了真相,吐露了心声,主体意识得以唤醒。
可悲的是,奥菲利亚所处的疯癫状态是另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她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她的话语没有倾听者,人们只知道她疯了,且认为“疯言疯语”毫无意义。
奥菲利亚极力挣脱男权束缚,却始终被压于制度之下,她最后的发声也被贴上“无意义”的标签埋进一抔黄土,没能摆脱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她者”躯壳。
四、结语
在父权制凝视下,奥菲利亚演绎了温柔顺从的天使形象,丧失话语权,陷入“她者”的沼泽。
当现实的打击唤醒她内心的思想时,她极力挣扎,疯癫解救了她。
本以为疯癫之下可得以喘息,无奈疯癫是一种异化的状态,是另一种“她者”境地。
通过对父权制凝视下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可以窥见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下非主体、非本质的从属地位。
这种被边缘化或被“她者化”的过程不是偶然形成的,权利与话语在施力,秩序与规训在发挥作用。
莎士比亚借助“疯癫”的力量,为奥菲利亚争取一口喘息的机会,让其自由发声,这是作者对女性的援救,也是无奈之选。
现实生活中,疯癫不应是女性发声的唯一路径,女性需捍卫自身权利,敢于突破父权制对女性的限制和规训,让内心的声音被听到。
而只有颠覆男权中心的社会制度,女性才能从附属地位中逃离,从“她者”的藩篱中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