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再纪念李燕涛向死而生怀念吾师邓正来.docx
《三年再纪念李燕涛向死而生怀念吾师邓正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年再纪念李燕涛向死而生怀念吾师邓正来.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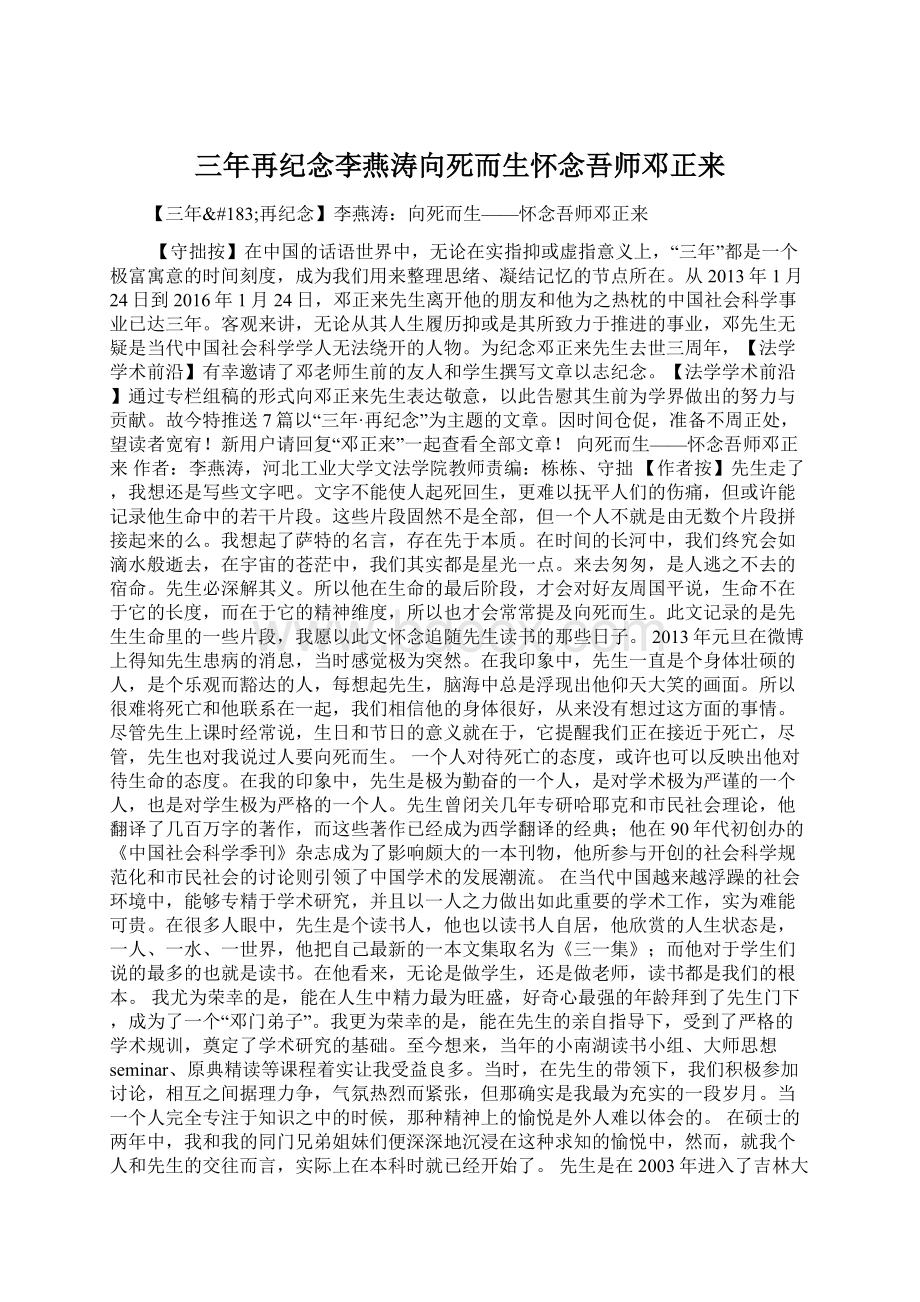
三年再纪念李燕涛向死而生怀念吾师邓正来
【三年·再纪念】李燕涛:
向死而生——怀念吾师邓正来
【守拙按】在中国的话语世界中,无论在实指抑或虚指意义上,“三年”都是一个极富寓意的时间刻度,成为我们用来整理思绪、凝结记忆的节点所在。
从2013年1月24日到2016年1月24日,邓正来先生离开他的朋友和他为之热枕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已达三年。
客观来讲,无论从其人生履历抑或是其所致力于推进的事业,邓先生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人无法绕开的人物。
为纪念邓正来先生去世三周年,【法学学术前沿】有幸邀请了邓老师生前的友人和学生撰写文章以志纪念。
【法学学术前沿】通过专栏组稿的形式向邓正来先生表达敬意,以此告慰其生前为学界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故今特推送7篇以“三年·再纪念”为主题的文章。
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周正处,望读者宽宥!
新用户请回复“邓正来”一起查看全部文章!
向死而生——怀念吾师邓正来作者:
李燕涛,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师责编:
栋栋、守拙【作者按】先生走了,我想还是写些文字吧。
文字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更难以抚平人们的伤痛,但或许能记录他生命中的若干片段。
这些片段固然不是全部,但一个人不就是由无数个片段拼接起来的么。
我想起了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
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终究会如滴水般逝去,在宇宙的苍茫中,我们其实都是星光一点。
来去匆匆,是人逃之不去的宿命。
先生必深解其义。
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才会对好友周国平说,生命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精神维度,所以也才会常常提及向死而生。
此文记录的是先生生命里的一些片段,我愿以此文怀念追随先生读书的那些日子。
2013年元旦在微博上得知先生患病的消息,当时感觉极为突然。
在我印象中,先生一直是个身体壮硕的人,是个乐观而豁达的人,每想起先生,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他仰天大笑的画面。
所以很难将死亡和他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信他的身体很好,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尽管先生上课时经常说,生日和节日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我们正在接近于死亡,尽管,先生也对我说过人要向死而生。
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或许也可以反映出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是极为勤奋的一个人,是对学术极为严谨的一个人,也是对学生极为严格的一个人。
先生曾闭关几年专研哈耶克和市民社会理论,他翻译了几百万字的著作,而这些著作已经成为西学翻译的经典;他在90年代初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杂志成为了影响颇大的一本刊物,他所参与开创的社会科学规范化和市民社会的讨论则引领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潮流。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浮躁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专精于学术研究,并且以一人之力做出如此重要的学术工作,实为难能可贵。
在很多人眼中,先生是个读书人,他也以读书人自居,他欣赏的人生状态是,一人、一水、一世界,他把自己最新的一本文集取名为《三一集》;而他对于学生们说的最多的也就是读书。
在他看来,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做老师,读书都是我们的根本。
我尤为荣幸的是,能在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好奇心最强的年龄拜到了先生门下,成为了一个“邓门弟子”。
我更为荣幸的是,能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规训,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
至今想来,当年的小南湖读书小组、大师思想seminar、原典精读等课程着实让我受益良多。
当时,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积极参加讨论,相互之间据理力争,气氛热烈而紧张,但那确实是我最为充实的一段岁月。
当一个人完全专注于知识之中的时候,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在硕士的两年中,我和我的同门兄弟姐妹们便深深地沉浸在这种求知的愉悦中,然而,就我个人和先生的交往而言,实际上在本科时就已经开始了。
先生是在2003年进入了吉林大学法学院任教,那时他已经开始给研究生上课。
当时我正读大一,此前在阅读一些法学书籍的时候,我经常会在书的注释中发现“邓正来”三个字。
这三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尤其是他所翻译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和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
后来当我无意中得知法学院新来了个教授,上课方式挺特别,而且也叫邓正来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经常出现在书籍注释中的那个名字。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通过博登海默或哈耶克而认识了邓正来。
先生对此也很诧异,为何一本在国外并不出名的著作,在国内的引用率如此之高。
或许,这也说明了我国法学的基础是何其之弱。
然而,这位邓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长什么样,脾气如何,我一无所知,直到2003年先生加盟吉林大学并做了一场就职学术演讲。
当时在经信报告厅,我记得那天能容纳几百人的大报告厅都坐满了,深受法学院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张文显老师也参加了那天的报告会。
在邓老师讲话之前,张文显老师让他的博士生念了一篇文章,这是张老师自己写的一篇介绍邓正来先生的文章,文章热情洋溢,介绍了邓正来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贡献。
这也让在场的人更加好奇,这位即将就任法学院教授的人会说写什么,他可是一下子越过了讲师和副教授,直接升任了吉大法学院的教授。
邓正来先生的演讲一下子就把很多人都镇住了,先生声音洪厚,中气十足,气场强大,他不仅讲了对于当下学术现状的看法,而且,也讲了对于今后工作的安排。
我记得他说要用8年的时间厘清休谟到哈耶克的学术理路,再用8年的时间厘清康德到罗尔斯的学术理路,然后,再用5年的时间厘清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的学术理路,进而在他60岁的时候,就可以构想出一个知识体系。
先生后来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他要在60岁之后写个东西,作为对自己一生的交代,不知道这是不是指当时演讲时所构想的内容。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不能看到这部著作了,这真是莫大的遗憾!
我记得他说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对西方著作进行表面化理解的现象,鉴于此,他有志于在吉林大学培养100多名博士,使得吉大成为研究西方思想家重镇。
当时,我听了极为震动,倒不是震动于先生的宏伟计划,而是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我在想一个人一年至多能带3-5个博士,那也得20年才能培养100名博士.......在演讲的结尾,先生用了八个字来结束,“宏大目标,点滴努力”,这也是我在后来多次听到的八个字。
此后,我便有意识地关注了邓正来,并搜寻和先生有关的信息。
我方才知道,他翻译了很多的著作,写了很多文章,还创办过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他研究哈耶克,同时也研究市民社会,他的名字更是和当代中国的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阅读先生的文章,我发现先生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他很多难懂的句子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理性而深刻的看问题的方式。
不仅如此,我还溜进了先生的课堂,得以当面感受先生上课时的情形。
那是在2005年4月的某天,我进入了先生在吉大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律思想者学园”的课堂。
我发现他的课堂里坐满了人,由于去的晚,只能在门口找个位置。
那天,先生正带着学生们读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的道路》,一句一句分析,读的非常仔细。
有时会为一个词语的含义而讨论很长时间,直到对这个词语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
这种学术上的认真对我震动很大。
大四准备考研,我最终决定报考本校的法理学专业,这很大程度上和先生来吉大有很大关系。
有次,我在课堂上问先生,如何成为他的学生。
先生回答说,要爱读书、能吃苦、英语好、不论贫富高矮美丑男女即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我继续去法律思想者学园蹭研究生的课,也继续读先生的书,在考研的时候也决定了考先生的研究生。
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我如愿以偿通过了研究生考试,我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先生,他勉励我继续努力。
某天,同级的杨晓畅找到了我,让我做师门的作业,并参加师门的活动。
这时,我意识到,邓先生已经收我了,当时感到非常高兴。
终于,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成为了邓正来先生的弟子。
很快,我便融入到了一个新的集体中,在这个集体中,我发现大家的关系比较简单,我找到了某种归属感。
在这个被人称作“邓门”的集体中,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起聚餐,一起活动。
在进入邓门的第一次聚餐中,先生便让其他人告诉了我师门的几条纪律:
1、不准以任何名义给老师、师母和嘟儿送礼;2、不准和其他师门的同学闹矛盾;3、不准学术抄袭。
后来又加了一条,当有人对老师和邓门进行批评的时候,不许进行回应。
在后来的几年中,这几条纪律被不断提起,每年都有新的同学加入邓门,每个弟子进入邓门首先被告知的便是这几条纪律。
它们像一条红线,成为了所有弟子的行为准则。
有段时间,先生在外讲学经常会提到他的师门,提及师门的特殊之处。
大量的阅读任务、不同的读书小组、每周的集中锻炼、师门知识上的团结、散步学派.......实际上,在很多人眼中,“邓门”其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像邓老师特立独行的性格一样,邓门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某些“不合时宜”之处。
师门内部经常性的集体活动,难免会给人以搞小圈子的感觉。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与本科时候的无拘无束相比,硕士两年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先生的严格让我有些惧怕,我想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我记得有次某个师兄新婚没几天,先生即问及他怎么还没有回来,后来,那师兄没几天便回学校上课了。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害怕先生来长春。
先生一来,我们便要紧张一周,先生上完课后,我们便会感到暂时的轻松。
但是,不可否认,在先生的这种严格督促下,我们也确实读了些书。
对于师门的这种特殊性,我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后来随着逐渐深入其中,也逐渐意识到了。
有次先生来长春,上完课后,先生像往常一样请师门弟子吃饭。
我正好和先生坐在一张桌上,席间,无意中聊到了这个话题。
我问先生,在整个大环境都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样能行吗,是不是有些独特了。
我清晰地记得先生的回答,先生大笑了一下,而后顿下很认真地说,“那就让它孤独地存在吧”,言谈中略显无奈。
先生的意思或许是,他无法改变整个环境,但可以从自身做起,不盲从甚至对抗整个学术界的浮躁。
在我眼中,这既是一种抗议,更是一种实验。
若干年后,当南方科技大学的教育改革实践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朱清时校长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有次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学生问朱校长的情形。
他也像当年的我一样,满带疑惑地问朱校长,现在的情形能坚持多久。
实际上,这样的提问中,既有疑惑,又充满了期待。
邓师门的独特性实际上体现了先生对于教育的理解,也是他对于现行学术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
邓先生对于现行的学术体制多有批判,但批判不等于否定,我想先生是在以自己的努力进行一种学术教育的尝试,他更多地是想进行一种教育改良。
既然无法改变整个学术体制,也无法改变整个学术界的风气,那他至少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基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学生们进行严格的学术“规训”,至少能够带领他的学生们研读经典。
“那就让它孤独地存在吧”,虽然先生为人豁达豪爽,交友甚多,但是我想,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邓先生是孤独的。
这种孤独的产生并不是出于先生本人的格格不入,而是由于当下学术体制中存在太多不尽如意的因素。
当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先生却以及的个人努力与之对抗,并尝试进行些许改变。
其实,先生对待事情是极其认真的。
但是,在我辈看来,这种改变何其之难。
教育和科研制度是整个国家制度的重要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大环境的改变,学术环境能够改善么?
有次,在三教六阶,先生回吉大演讲。
有学生提问,“您对未来中国的学术前景怎么看?
”“一片大好!
”先生回答。
其实,先生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吉大任教的这几年,先生雷打不动,每个月都会来吉大集中授课。
长春冬天很冷,奇怪的是,先生很多次来的时候,总会遇到降温天气,有人戏言,先生一来,天气就不好了。
有次,先生来长春,又遇到了大幅度降温,突然感冒了。
我们考虑到继续上课不利于他身体好转,师门便选代表便告知先生说大家已经集体商量后,决定不上课了。
这次“罢课”事件引起了先生的勃然大怒,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而且写了个文章讨论这个事情。
就我这两年的感受而言,做先生的学生,实际上是很辛苦的。
每次上课前,我们都需要做充分的准备,都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
我们每两周都会向先生交一次读书报告,而且还要仔细地阅读下次课要讨论的文献。
即便如此,每次上课时,我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某个错误被先生批评。
先生批评学生的时候非常之严厉,有师门同学就曾当面被批哭过。
先生其实是在用他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他或许在想,我能做到的,你们比我年轻,也应该能做到。
在他的严厉中,其实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后来,先生患了喉癌,虽然治好了,但或许和这几年的奔波操劳有关。
然而先生一直来就非常强调身体的重要性,他多次嘱咐我们要锻炼身体。
为此,他和师母给个月给我们几百块钱,专门作为师门的锻炼经费。
起初大家对参加锻炼的积极性并不高,先生每次来都督促大家。
后来,我负责了组织大家体育锻炼,才理解了先生的用意,他不仅是想让大家都有个好的身体,也是想利用锻炼的机会,让大家平常多多交流,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
平时上课或通信的过程中,先生谈论最多的便是读书,在他看来,读书是老师和学生的根本所在。
不仅如此,我们在他的课堂上都接受了某种学术规训。
通过课堂上对我们的观察,他也会结合我们每个人的兴趣,为我们确定研究的方向。
邓门的学生大都都会跟据自己的兴趣和老师的意见选定一个人物作为研究对象。
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这种人物的思想研究其实并不受欢迎。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学科,人们大都强调学术研究要和中国有关,要能解决实践问题。
其实,不仅其他人有这样的看法,而且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研究中国很重要,但是了解西方也很重要,但是如何取舍呢?
先生后来对我们说过他的用意,他说并不是要我们都成为某个人物的研究专家,而是在我们都缺乏学术训练的情况下,让我们以一个人物的思想研究为契机,能够了解一流的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
研究一个人物,首先便需要阅读大家的一手文献,而且要借助于好的研究文献,这样,在阅读西方文献的基础上,便可以从中学习研究的方法。
人物研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训练方法。
当然,他也强调过,并不能因此而忽视研究大家思想的意义。
实际上,先生在那时就已经关注了研究中国的问题。
他曾组织了一个“中国研究小组”,成员们通过邮件的形式定期交流对于和中国有关的问题的看法,进行学术上的讨论。
参加的人都是年长我的师兄师姐们,从中,我受益很多。
我仍然记得当时先生让我参加这个小组时的情形,某天,他把我叫到中心的办公室,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他想建立一个学派,想让我参加这个小组的讨论。
我当时听了很意外,我说建立一个学派需要很多因素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有研究纲领,研究群体等等。
先生说,你先别管这些,先参加讨论再说。
后来先生在复旦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倡导“重新发现中国”,这和当时那个讨论小组不无关系。
或许,当时先生就在思考中国研究的相关问题了。
在我看来,先生是极其勤于思考的一个人,他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先生常臧否人物,直言不讳,在当前盛行互相吹捧的学术界,先生确实有些不合潮流。
然而先生却并不赞同我们那样做,他让我们去踏踏实实的读书,而不要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
他教导我们做学问不要着急,要“慢慢来”,好的学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的。
他教导我们说学问要想做的深刻,需要抓住以下几点,要让学问和自己的生命相关,要深入问题的前提进行反思,要假设其他人都是聪明的,这样你才能想得更多。
他教导我们说,翻译其实需要有“比慢”的功夫,也需要有“较真”的本领,太着急了翻译不好。
他以他自己为例,他说他翻译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前前后后翻译修改了很多遍,有时为了一个词语,需要斟酌很多天。
先生身上有股强大的气场,听他讲话,很容易被其感染。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他的看法常常有与众不同的新意。
他常能指出你的不足,并给出他自己的观点。
余虹先生逝世后不久,先生有次回长春,在师门的会议上,大家讨论起了这个事情。
对于余虹先生自杀这个事情,甘师兄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行为,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是用死亡和现实进行抗争。
对此,先生则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并非一种勇敢的行为,是没有其他办法之后的一种表现,并不值得提倡和赞扬。
他认为人应该活着,并勇于和现实抗争。
当时,我并不赞同先生的看法,现在我却理解他了。
这其实很符合他的性格,先生是个不屈服于现实的人,也是个极为自信的人。
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并不把死亡当做对于现实的抗争方式。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对于死亡的看法,尽管在此之前,我就听先生说过,人应该向死而生。
那是硕士毕业的时候,我面临着人生的选择。
我跟先生说我想考博,想考北大的宪法,先生说你还是考吉大吧。
我又说未来还是很不确定,先生说,你应该学会“向死而生”。
后来,先生去了复旦,和先生的联系便比过去少了,见面的机会也并不多。
先生在复旦高研院的事业蒸蒸日上,我也非常高兴,我想先生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尽管如此,先生说的“向死而生”四个字却被我深深记在心里。
向死而生,实际上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命题。
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人生智慧,一种面对世界的生命姿态。
这是一种豁达而从容的胸怀、一种积极而乐观的心态,一种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绝不屈服的精神。
许纪霖先生在微博中说,即使在罹患重疾住院期间,先生还是“象一位勇士一样斗志昂扬”。
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勇士,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他经常跟我们说人要有大气象,只有具有大气象才能成就大事业;他也经常跟我们说要“参透”人生。
在我看来,他说的这些很抽象,对于缺乏充分的人生阅历的人来说,至少现在,是很难做到的。
这或许是他这些年来历经风浪之后的人生体悟吧。
如今,先生走了,走的很匆忙,甚至没留下一句话。
他还有很多构想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然而先生并未走远,先生的那些著作依然存在,先生独立的品格依然存在,先生留下的那些教导依然存在,这不正是先生所期望的精神维度么?
我相信,先生留下的这些东西必定会使后人铭记。
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