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docx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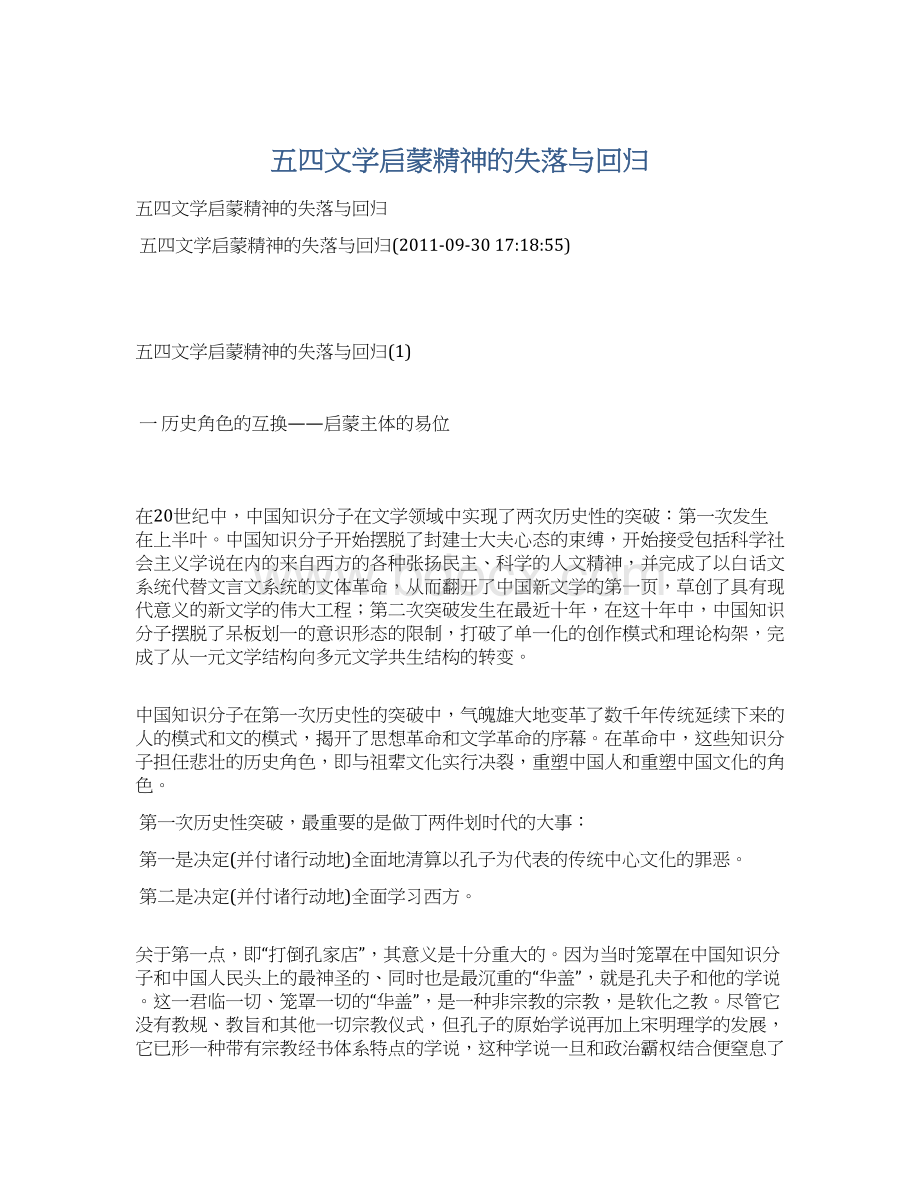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2011-09-3017:
18:
55)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1)
一历史角色的互换——启蒙主体的易位
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突破:
第一次发生在上半叶。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了封建士大夫心态的束缚,开始接受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来自西方的各种张扬民主、科学的人文精神,并完成了以白话文系统代替文言文系统的文体革命,从而翻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草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的伟大工程;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最近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呆板划一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打破了单一化的创作模式和理论构架,完成了从一元文学结构向多元文学共生结构的转变。
中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中,气魄雄大地变革了数千年传统延续下来的人的模式和文的模式,揭开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序幕。
在革命中,这些知识分子担任悲壮的历史角色,即与祖辈文化实行决裂,重塑中国人和重塑中国文化的角色。
第一次历史性突破,最重要的是做丁两件划时代的大事:
第一是决定(并付诸行动地)全面地清算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中心文化的罪恶。
第二是决定(并付诸行动地)全面学习西方。
关于第一点,即“打倒孔家店”,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因为当时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头上的最神圣的、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华盖”,就是孔夫子和他的学说。
这一君临一切、笼罩一切的“华盖”,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是软化之教。
尽管它没有教规、教旨和其他一切宗教仪式,但孔子的原始学说再加上宋明理学的发展,它已形一种带有宗教经书体系特点的学说,这种学说一旦和政治霸权结合便窒息了中国社会的生命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在一千年前出现了盛唐气象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民族精神不断萎缩,人民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
而中国社会停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布圣人死了,对于中国人的命运关系极大,它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存在方式。
原来中国人是按照孔子规定的方式而思维而存在的,现在规定主体死了,中国人开始了一个自我规定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时代。
这正如郁达夫所说的:
“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如果没有宣布圣人已死并由此带来的巨大转换,中国人至今还可能在礼治秩序的黑暗中徘徊。
决定全面学习西方的意义也是极端重要的。
这种决定,不是一时激愤的选择,也不是人为的、几个先锋派角色的心血来潮,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十字路口上的一次集体性的抉择。
当时无论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还是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主流派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是向西方学习。
在这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并不情愿学习西方,不愿放下“天朝——中央大国”的架子接受西方文化。
在“五四”之前,从李贽开始,已有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尽了一切努力,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拯救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机制,但是,这种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某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放弃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找武器以挽救中国文化的空想,开始从西方学说这一异质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的药方,但也仅仅是各自从防御性或从策略性的问题考虑出发,择取一端,并且不得不披上古圣人的合理外衣(如康有为)。
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继续在自己的祖辈文化体系内部徘徊,企图从中发掘救国药方纯属自欺欺人;而仅从某一渠道、某一层面半遮半掩地学习西方,即既顾全祖宗面子又要故国新生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素质上全面学习西方才有出路。
于是,他们决定从传统的铁屋子里走出来,从雷峰塔的压迫下走出来,直面西方文化。
决定摧毁孔家店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激烈的新文学运动,其主将有四个人:
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
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陈独秀:
突破文学的精神模式,提倡科学与民主,正式举起文学革命之旗;
胡适:
突破文学的语言模式(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变文学观念和草创新诗形式;
鲁迅、周作人:
突破文学的主题模式和叙述模式,建立小说散文新形式(改造国民性和创造人的文学)。
这四位文学革命主将以及稍后产生的杰出作家郭沫若、冰心、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共同推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学革命。
他们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共同担任着历史改造者和启蒙者的角色。
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主体,知识分子在启蒙者的历史角色中,一方面启蒙他人,另一方面又肯定自身。
即肯定自身乃是新世纪的自我,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下再是黏附于皇上朝廷或某种政治结构的士大夫人格。
因此,“五四”又是知识分子肯定自我和张扬个性、突出个性的时代。
这种肯定的根本点,是抛弃封建士大夫的历史角色和封建士大夫的文化精神,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基本思路——“代圣贤立言”的思路,从而改变文化上的附庸性格。
这种性格,使知识分子丧失其精神主体性的地位,而在实际上成为文化奴隶。
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再造文化性格的革命命运动。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呼吁新青年完成六大抉择: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而最要紧的是第一点:
第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陈独秀这篇文章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独立宣言。
它宣布,中国知识分子将开始为自立、自强、自由而奋斗,将告别文化奴隶的时代并以独立的人格去塑造新的时代。
由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因此,当时作家的文化心态都比较热烈、积极、奔放,都充满信心地肯定自我的精神价值,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发光体。
当时鲁迅宣布: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郭沫若宣布:
“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鲜的星球。
”在这之前,胡适宣布: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
他们都确认自己就是太阳,自己就是炬火,他们不再借助外在的光明来照亮自己的道路,而是依靠自身的光明去展示新的人生和新的文学。
他们不是绕着他物转动的物体,而是自强自立的个体。
他们的个性燃烧起来了。
他们发现了自身的光热,自身的力量,并认为真正有力量的是个人,是强大的、不随波逐流、不黏附于他物之上的生命个体。
因此,他们当时普遍地推崇易卜生和尼采。
这两位西方的思想家共同的特点就是确认独立的个人是最有力量的人。
他们主张以个人强大的意志去抗争悲剧性的环境,敢于重估一切价值,敢于肯定自己独立的人格,哪怕因此被绝大多数的“庸众”视为“国民公敌”也在所不惜。
他们呼唤强大的个人,即使被社会视为“狂人”、“疯子”也不放弃信念。
以这种亢奋的独异的思想进行自我肯定,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第一次伟大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不仅确认自己是发光体,而且确认自己可以照耀别人,可以唤醒别人,因此,他们的创作皆奉行“启蒙主义”。
他们的启蒙,主要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对于人的内在精神、内在尊严的启迪,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证伪,是对科学、民主等现代人生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的张扬。
鲁迅在1933年所作的《自选集·自序》中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确实是着意要毁坏那个延续几千年的铁屋子,以唤起正在屋子里沉睡的同胞。
鲁迅写了《阿Q正传》、《故乡》等小说,小说中的阿Q、闰土都是沉睡着的悲惨的、麻木的灵魂。
他们对自己的不幸未能自知,对自己的“不争”更是毫无觉悟,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的死魂灵。
要唤醒这种死魂灵,没有大声呐喊式的启蒙是不可能的。
阿Q们的灵魂与现代人的文化意识相去太远了,与整个新的时代精神完全隔膜了。
除了鲁迅,当时流行的问题小说、社会剧和乡土小说,直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品都在致力于思想启蒙。
“五四”作家和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者,在各个方面确实发挥了先锋作用。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
“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又说: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
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之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是人们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这种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不久就逐步地被淡化、被削弱乃至被否定,以致发生历史角色的互换,即作为先觉者和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反而变成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原来被“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的农民则变成改造主体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主体。
在这种历史互换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启蒙精神和自我意识便一步一步地丧失。
40年代之后,类似《阿Q正传》那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农民的愚昧、落后的具有强大启蒙力量的作品几乎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赵树理那种讴歌农民的作品。
试图保持“五四”作品的基本思路,继续让知识分子在生活中维持主体性地位的作品,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942年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受到批判就是典型的一例。
这一批判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地位的文学时代在一个历史阶段上已经终结。
《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到延安后,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
她满腔热情,试图把较为现代的护理方法搬到医院中,为了照顾好产妇、婴儿,为了她们的一点需要,她常常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争执。
生活那么呆板,环境那么落后,一切都使她感到彷徨和不安。
但是,她不断地自我克服,努力工作。
然而,即便如此,她仍然遭到种种非议,有人说她太热心、太浪漫,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等。
她成了一个怪人,一个异类。
她试图改造落后的医疗环境但反而被环境所窒息。
这篇小说,为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请命,希望能够尊重和理解知识分子。
这种思路是“五四”文学思路的一种延伸。
但它和陆萍的良好愿望一样,可悲地受到嘲弄和批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训:
话》发表之后,不仅《在医院中》这种作品在解放区已经销声匿迹,而且直接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也见不到了,即使出现某些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人物,其身份也是干部或下乡干部。
例如韦君宜的《三个朋友》,其中的知识分子也已半是干部半是知识分子了,而且小说的思路与“五四”已有质的变化——知识分子开始自我贬抑了。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个知识分子,她有三个朋友,一个是纯正的农民(刘金宽);一个是下乡的知识分子干部(罗干);一个是开明绅士(黄宗谷)。
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中,“我”终于分别认识了这三个阶级的代表人物。
开明绅士是“两面国”的人,不可靠;知识分子罗干说话喜欢绕弯子,不坦率;只有刘金宽淳厚、勇敢、讲义气。
因此,知识分子的“我”终于在三个朋友中选择了一个堪为朋友的刘金宽为朋友。
小说最后说:
“现在你自然懂得了,我所说的良师益友是谁——和刘金宽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
你们外边人老爱过分称赞我们这些摇摇笔杆的解放区人,说我们‘百炼成钢’了,其实,你听我说了还不知道?
我们还不是照样有这么多往昔的依恋、寂寞、梦幻,真丢人,常常分不清谁是自己的朋友,糊里糊涂忘掉了自己的脚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