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docx
《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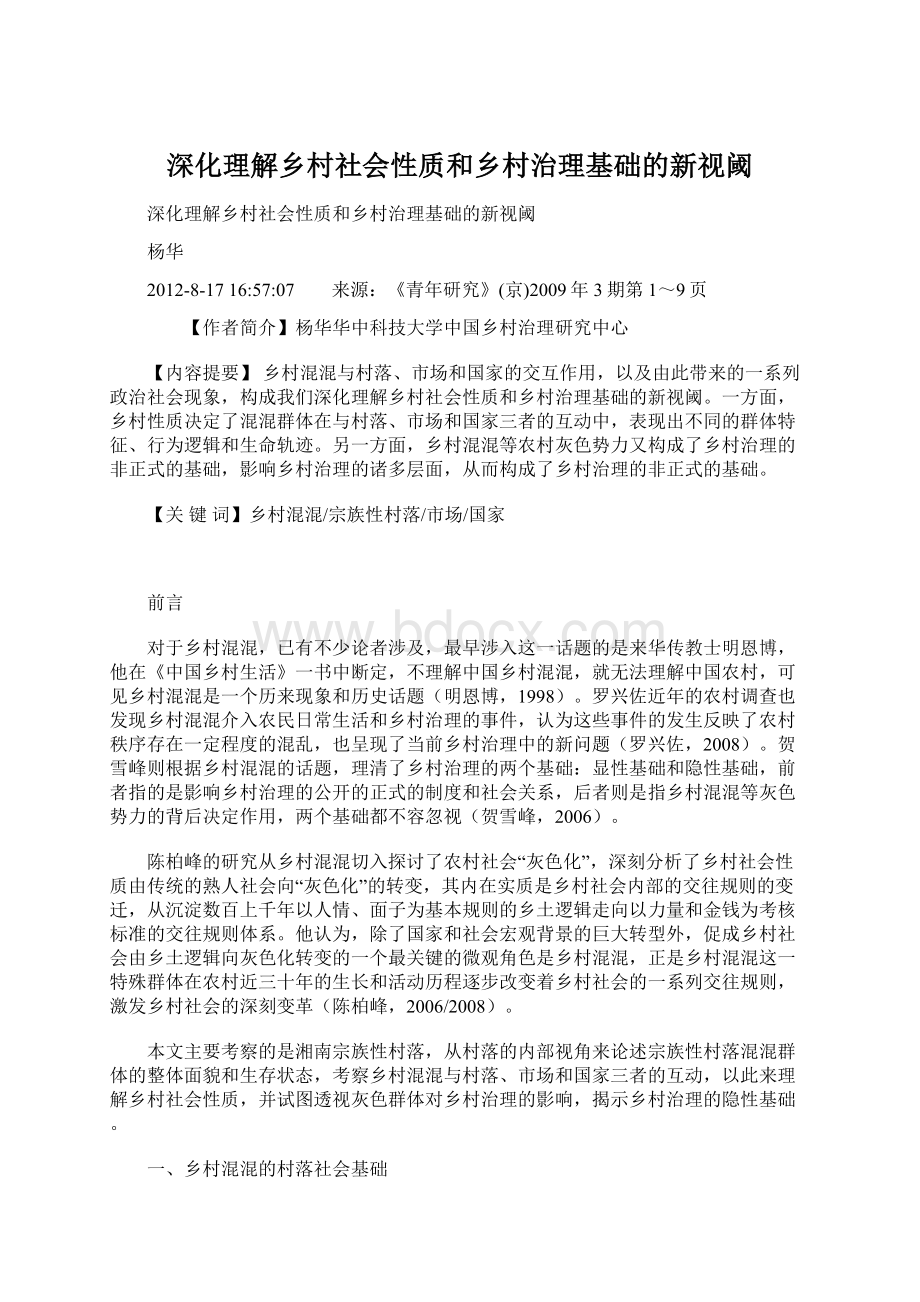
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杨华
2012-8-1716:
57:
07 来源:
《青年研究》(京)2009年3期第1~9页
【作者简介】杨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
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关键词】乡村混混/宗族性村落/市场/国家
前言
对于乡村混混,已有不少论者涉及,最早涉入这一话题的是来华传教士明恩博,他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断定,不理解中国乡村混混,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可见乡村混混是一个历来现象和历史话题(明恩博,1998)。
罗兴佐近年的农村调查也发现乡村混混介入农民日常生活和乡村治理的事件,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农村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也呈现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新问题(罗兴佐,2008)。
贺雪峰则根据乡村混混的话题,理清了乡村治理的两个基础:
显性基础和隐性基础,前者指的是影响乡村治理的公开的正式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后者则是指乡村混混等灰色势力的背后决定作用,两个基础都不容忽视(贺雪峰,2006)。
陈柏峰的研究从乡村混混切入探讨了农村社会“灰色化”,深刻分析了乡村社会性质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灰色化”的转变,其内在实质是乡村社会内部的交往规则的变迁,从沉淀数百上千年以人情、面子为基本规则的乡土逻辑走向以力量和金钱为考核标准的交往规则体系。
他认为,除了国家和社会宏观背景的巨大转型外,促成乡村社会由乡土逻辑向灰色化转变的一个最关键的微观角色是乡村混混,正是乡村混混这一特殊群体在农村近三十年的生长和活动历程逐步改变着乡村社会的一系列交往规则,激发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陈柏峰,2006/2008)。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湘南宗族性村落,从村落的内部视角来论述宗族性村落混混群体的整体面貌和生存状态,考察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以此来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并试图透视灰色群体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揭示乡村治理的隐性基础。
一、乡村混混的村落社会基础
(一)宗族的复兴与村落的性质
湘南地区的村落,总体而言是宗族性质的,每一个姓氏占据一个或多个村落而聚居,形成较为紧密的生活、生产以及交往社区。
除了特殊的历史原因,比如高级合作社时期的村落被整合成少数小姓和大姓杂居之外,一般每个村落都是一个姓氏,即宗族。
在宗族性村落内,建国前30年,原来比较强大的宗族组织、庞大的族产以及宗族族谱遭到摧毁,宗族活动一度被迫停止,但改革开放后,湘南绝大部分的村落都恢复了以前的宗族形式,宗族观念也逐渐增强。
随着1980年代分田单干、大队解体,许多宗族村落便趁势形成了自己的宗族组织,自称为“自然村领导班子”,由五个干部组成:
自然村村长、副村长、会计、出纳和监管员。
自然村有自己的林产,原来分配到村民小组的部分林地没有完全分到各户,而是由自然村收归、纳入到自己的账上,并且每个自然村都还有个风水宝地——“后垅山”,这块地方是宗族的信仰和风水所在,一直以来就属于自然村。
因此,这两块林产就相当于宗族性村落的“族产”。
“自然村领导班子”负责自然村内的事务,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调解宗族内部矛盾,以及协调宗族之间的事项等。
这个领导班子并不与行政村的领导班子重合,即使在一个自然村内部,各小组组长也不兼任宗族内的职务,它的主要职责是传达上面的文件和精神。
所以行政村的许多事务都被“自然村领导班子”分割——除了计划生育工作外,其他的事都被自然村包干。
行政村领导干部不任自然村的干部,但两个班子协调得很好,行政村只对自然村进行指导、给予支持,“自然村领导班子”中的优秀分子很可能是行政村领导的主要候任人,而行政村的干部退休后也可进入“自然村领导班子”。
在由一个大宗族村落和其他小宗族村落组成的行政村中,村领导一般由大姓村民担任,小姓挂个虚职,而有时候,“自然村领导班子”在竞选中很可能集体接任行政村班子。
除了宗族组织已全面复兴外,宗族仪式、观念也有不同程度的再现和恢复。
宗族祠堂在集体时代并没有被人为地拆除,而是挪为他用,比如人民公社时的集体食堂,老人过世也依然还在里面举行仪式,但宗族祖先牌位被移开销毁,祠堂里不再允许举行除“过老人”外的其他大型宗族活动(如拜祖、祭祀),族谱也基本上被当时的红色干部强行销毁,祭拜共同祖宗的同姓村落也不再来往。
而集体解散之后,这些过去被认为是旧的事务又重现在宗族的生活和信仰当中,大型的宗族族谱修复活动在跨区域(乡镇、县市)范围内进行,原先亲自烧毁老族谱的领导在七老八十之后又开始担当续谱的组织、动员和领导工作,绝大部分宗祠在最近十年内全面重建、翻修、扩充,虽没有再摆牌位,宗祠里的大型仪式、集会活动有很多也恢复举行,人们依然像以往那样虔诚、热情。
同姓之内的“家”与“门”也重新建立起了联系,比如湘南大陈家湾是个拥有两千多人的大自然村,而隔壁乡镇的小陈家湾则是祖上从大陈家搬出去的,只有三四百人,前者为老“家”,后者为选“门”,前尊后卑。
每年大年初二,小陈家都会派五六十人到大陈家来拜会“老家”的祖宗和“娘舅”,大陈家由“自然村领导班子”负责接待,召集族老同客人座谈、会餐,一起祭祀共同的祖宗。
而快到大年十五的时候,大陈家的“自然村领导班子”也会率一个上百号人的团队前往小陈家回拜。
通过这样的活动和仪式,增强了宗族内部的联系和感情纽带,人们的“家门”观念得到重新认受,宗族情感越来越浓烈。
因此,在湘南宗族性村落,人们对本宗族的认同和“屋里人”的观念十分的强烈,宗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人们的村落“历史感”和“当地感”(杨华,2009),人们对待宗族成员和“外人”有着两套不同的法则和规范,对“屋里人”做事说话都要有分寸,不能超过一个度,而一旦越过了就等于是把对方当“外人”对待了,这在村落里谁也没有这个权力。
村落还有很强的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完全可以在村落里获得生活的意义,在外工作的人对村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们构成村治意义上的“第三种力量”(罗兴佐,2002),这些人对村落的主动支持成为村落建设、治理的重要资源。
同时在一个完整的宗族村落社区内,人们的道德感和社区舆论还很强,人们对他人的评价还很在意,时刻注意自己在村落里的形象,要为家庭和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交往环境。
传统面子观在村落里还占着重要的地位,“养崽、起屋和讨媳妇”依然是人们“一世人生”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面子,人们会为生男孩子而想尽一切办法,只要没有特殊的障碍,就可以一直生下去。
以宗族观念和宗族认同为支撑的村民合作与一致行动容易达成,农民生活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不高,金钱化、利益化的诱惑在许多时候并不会出现很明显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在村民中产生不好的结果。
人们传统的“熟人逻辑”和新近嵌入村落的“市场逻辑”在不同的生活、生产领域较劲、斗争,最终的结果是前者以其相对较强的力量战胜后者,进一步确立为村落的主导思维和行动逻辑。
(二)乡村混混与宗族性村落的价值生产
在宗族组织部分恢复其能力和功能,宗族观念依然占据着人们内心世界的湘南村落,乡村混混的生活面貌、生存状态必然不同于村落本身已经原子化、社会关联度很低的荆门等地农村的同类群体,也殊异于以小亲族、户族为行动单位的鲁西南、关中地区。
由于宗族的普遍存在,湘南乡村混混的活动范围被排除出村落,流落到乡镇所在地、集市、“闹子坪”上,而镇上的混混则进不了村落。
湘南的混混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惯偷,是村落里的“三只手”,另一类是在镇上“打遛”的混混。
由于严格的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职业惯偷在当地村落并不多,整体的治安环境很好,村落比较平静。
也很少听说有人家的比较值钱的东西如耕牛、肉猪和农耕机械被偷。
一般情况下,把农具放在田地里,并没有人拿走,普通人家的大门基本不上锁。
但我们调查的湘南水村杨姓宗族的三个村落里,也有一个死不悔改的惯偷。
这个惯偷已经成了名,人们一般把他的名字和“强盗”连在一起叫,但他的主要盗窃区域不在村落里,而是周边的乡镇。
村落里最不耻偷盗的年轻人,认为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得有声有色,就是不能去搞偷偷摸摸。
这个“强盗”的生活面向是外在的,一两年都回不了一趟家,他的价值不在村落里,所以对他而言,在村落里的声誉并不重要,同时他之于村落,是被排除掉的人,也不影响村落的价值生产能力,因此他所受到的约束并不大。
但是相反的,如果是个离不开村落、要在村落里终了此生的人,那么他的价值所在、生命意义等一切重要的方面都与人们对他的印象和评价相关,也就是说村落其他的人掌握着他的命运,他若要在村落里顺顺畅畅地过一辈子,而不受到来自村民的指责和舆论围攻,他就得遵守村落的一切规矩和共识。
其中一个共识是不打村落和宗族内部的主意,不偷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的,完全可以好言相借。
因此人们可以原谅偷盗外地人东西的子弟,却绝不可能宽容监守自盗的子孙。
案例1水村历史上唯一一例年轻男子自杀的个案,是因为在湾里偷盗被发现后自杀。
曾路明,男,三十岁左右,在湾里偷牛,被湾里人抓到,“不好意思,过不下去”,吃药而亡。
事后人们对他的死很冷淡,说:
“不好意思,过不下去就吃药死了。
”也就是说人们对这个年轻人的死并不惋惜,而且很清楚地知道他在村落里已经“过不下去”了,为什么呢?
因为“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就是一个人在村落里已丢尽了脸面,没有脸面和勇气再在村落里活下去了。
在村落里,脸面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与个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要想在村落里“过得下去”,就必须挣得足够的面子,而一个完全没有面子的人硬撑着活在村落里,则是“死要面子”,会更没面子,就算活着,人们也全然不会赋予他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生活在村落传统价值观和面子观里的人们都懂得他们的行为如何才是得当的,什么样的行为会遭受什么样的后果,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细账,对应着村落共识与惩罚。
在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压力下面,每个人都得掂量自己的一言一行。
其他混混群体也不敢在宗族性村落内部“混”,他们混在镇上,被唤做“打溜的”。
在村落里,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与“混”相反的一副面孔,他们遵守村落里的道德、规范和共识,既尊老爱幼,又懂得村落的文明礼貌,尽管有些吊儿郎当,但仍不失为好孩子的形象。
重要的是,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体现一个宗族的力量和气势,一伙二三十岁的年轻后生聚集到一起,就是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在经常发生宗族之间矛盾和械斗的湘南宗族性村落,他们永远是斗争的中坚,冲锋陷阵在最前头。
因为这些年轻人一般冲动而没有顾虑,而其他的宗族成员尽管在这些重要场合必须出现,却总希望用和谈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这些在外地混的人虽然易冲动,却也会听从宗族领导班子的话,适可而止。
也就是说,对于宗族而言,他们在与其他宗族的利益、资源(土地、矿藏、森林、水利等)和面子的争夺战中,需要这些“混”的子弟张目壮胆扩大声势,以争取自己宗族利益、面子的最大化,从而使宗族更加团结、内聚,且这些在镇上混的年轻子弟并不扰乱村落的生活秩序,对村落内部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构成威胁,他们在镇上混,尽管可能影响宗族在外地的声誉,但也起到了声势和力量外溢的效果,使其他宗族村落一听到该宗族的声名就有畏惧感,这对宗族在区域(乡镇)占据更有力的地位(如市场条件)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而对于混混自身而言,宗族的声名和气势是他们“混”的内在基础,宗族大,在当地有力量且远近闻名,混混也就有底气,混得有声有色,而小宗族的混混则必须依托大宗族的混混才能混得开,否则也混得不如意,要受其他混混的气。
因此,混混对村落宗族事务也颇为关心,事事为宗族出头效力。
宗族矛盾为混混在村落里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为宗族抛头颅洒热血的混混会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在村落里带来极高的声誉。
案例2在湘粤边界传统上就经常有分属两省份的不同宗族为着历史的仇恨和当下的利益而发生宗族械斗,1999年的时候,水村临近的一个村落与广东某村落发生矛盾,广东村落宗族破坏湖南的省级公路、高压电线,因而构成犯罪,有数个出头较狠的混混被判刑入狱。
2005年七八月份这些人被释放出来,整个村落为他们接风洗尘,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大宴宾客,并且请了水村的一套“八音班”助兴。
在村民的眼里,这些被判刑的人就是宗族的英雄,他们为宗族而不是个人的利害入狱,理应受到宗族的厚待和嘉奖。
混混为宗族办事不遗余力,从中获得了不菲的受益,不仅在声誉上获得了宗族的认可,而且他们在宗族里的形象和地位也建立起来了,从而在宗族价值系统里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着村落价值和意义的生产职能,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和风范。
因为村落价值的生产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事关村落面子、利益和命运的关键时刻。
那些在关键时刻为宗族利益而奋斗的成员,彰显了宗族的价值和意义,而那些畏畏缩缩的成员,则是宗族的耻辱,这些人在村落里不会有面子,其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得不到村落的认可。
(三)乡村混混的话语建构与转换
在针对村落价值生产和意义创造的道德层面上,就有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冲突问题。
我们把宗族间争斗(或械斗)中兴头、不要命的人称为混混,而国家正式法律也对这些行为和人加以规范与否定,但在村落宗族的话语系统里,“打遛的”与村落(宗族)英雄是完全可以置换,乃至合一。
在平时是“打遛的”,在街面上成群结伙控制市场,敲诈勒索,靠拳头吃饭,但到了村落宗族内部,其身份便可很快转变成宗族的护卫者,村落价值与意义、面子和利益的集中体现者。
这种角色之所以转换很快,与村落的“公私”观念相关,村落或宗族相对于国家、社会这个大的“公”而言,它是彻底的“私”,但相对于其麾下的成员来说,宗族是绝对的大“公”,个人是小私。
当私人在街面上混时,它违背的是社会大公的道德准则或法律规则,并不涉及到宗族“公”上,因此宗族可以把这些子弟称为“打遛的”,虽然有道德上的责备意味,却并无过分的谴责之意。
而当宗族里的个人为宗族事务而与社会大公作对时,破坏的是社会大公,维护的则是宗族的私,而这对个人而言确是“公”的,因此角色就此转变过来,在宗族“公”的层面上(相对于社会而言是私),社会话语中的“打遛的”、“混混”就成了英雄人物。
个人在社会大公和宗族(村落)“公”两者中选择了后者。
也就是说,外来的国家话语和地方话语是不对称的,人们生活在这两种话语中,必然会产生话语的冲突与对立,而两者的较量结果是地方话语战胜国家的话语,宗族掌握了话语权。
二、宗族、乡村混混与基层市场交互作用
在湘南一带,一般几个村落共享一个初级市场。
以前没有设立集市的乡镇近年逐渐都有了自己的“闹子”,有特定的“闹子坪”,于是在“闹子坪”及附近就形成了一个初级市场,而且“闹子坪”多设在乡镇所在的村落。
乡镇各地的农民集中到这里买卖东西,或者从农村把货物运到闹子,再由闹子集中运输到次级市场,或者由次级市场把农民所需要的货物运到闹子坪,再通过赶“闹子”把货物转到农民手中。
因此从表面上看,农村集镇的“闹子”是再自由不过的市场,人们可以把东西弄到这里来出卖,也可以到此地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买卖自由,通货畅通。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层繁华、自由的表象,把视阈从经济学转到社会学、人类学,通过参与式的观察,就会发现“自由”背后极其复杂的东西,这为我们探讨农村“自由”市场的内在机理以及市场与其他现象(如宗族)的关系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一)基层市场中的宗族
“闹子坪”的建立,为“闹子坪”所在地和周边村庄落的农民创造了极好的市场机会,激发了人们的盈利欲望——谁都想在这里占块地,分杯羹,抢占黄金地段,占领市场制高点。
因此,资本的投入既密集又活跃。
但是在市场形成过程中以及正常运营以后,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资本,而是宗族势力。
市场为宗族之间的斗争提供了又一个竞技场。
在这个场域内,谁的力量最雄厚,谁就能捕获绝对的市场空间和机遇,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在竞争中失败的宗族,则被驱逐出主要的市场位置,只能在一些利润狭小的领域做买卖。
我们以湘南“白沙闹子”为例来说明宗族以及宗族里的混混是如何对主要市场进行操控的。
“白沙闹子”,逢五逢十赶闹子。
“闹子坪”周边两三公里以内有数个村落,有陈家、刘家、李家、罗家、邓家等几个较大的宗族,其中又以陈家为最大,人口多达两千余人。
陈家和刘家都离市场比较近,刘家就在市场边上,有一段市场还延伸到了村落里,而陈家的主村落离市场有两公里路程,但其田地却靠近市场,因而开辟市场之后,陈家人都在市场边大量修建房屋,开设门面。
因此市场的主要争夺者是陈家和刘家。
陈刘两大宗族有宿仇,至今互不通婚。
两大宗族的老村落只有一江之隔,双方经常为利益和小事发生争斗,两姓各自在江上修了数座桥,但都因仇恨被对方毁掉,最后由乡政府出面修建,方能平安通行。
由于陈家比刘家的人口多、势力大,在市场资源的争夺战中陈家占了上风,基本上占掉了全部市场的四分之三,刘家只拥有延伸至其村落的一小段市场。
市场两旁的门面、摊位(包括衣裤区、杂货区、鞋袜区、饮食区、音像区)都被陈家人给垄断着,或租给人家做买卖,或自己当老板。
并且,每一个市场品种基本上都固定了人数和产品数量,形成了一个稳固、封闭的利益集团,禁止他人进入。
比如白沙“闹子坪”逢闹子的时候会有近十五六家猪肉摊子,半数以上(十三家)是由陈家人摆的,而且每家在逢闹子时都是半个摊位做生意,另半边闲着,因为摊位的固定,多年来不曾有人插进来,这些猪肉老板都达成了默契,只做一半的生意,让每一个人都有生意做。
事实上,每个猪肉摊位都有固定的客源,即在市场上买肉的人都是熟客,不会挑拣摊位,也不会砍价杀价。
每个摊位上的猪肉价格都一致的,即使有差别也不会相差太大,所以(陌生顾客)选摊、讲价往往行不通,而只有到了下午,价格才会有所松动。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利益集团是“车主”团体,这个集团的掌控者也非陈家莫属,所有的载客中巴都属于陈家人或他们的亲戚。
白沙共有五辆载客中巴,其中只有一辆是开往县城,其余的开往附近乡镇。
并不是因为去县城的人少,没有客源,每天真正去县城的要比到其他乡镇的顾客多出几倍。
一辆车一条路线,要赶往县城的人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得来“闹子坪”挤车,许多人搭不上车,怨声载道,都希望能再添一辆到县城的车。
没有搭上车的只有搭前往其他乡镇的中巴再转车,既要多花钱,又浪费时间,还辗转劳累。
这便是陈家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二十年来这个局面从未变动,车辆数目没增加,车辆路线不变更,中巴大小未改变。
在客源相同或增加的情况下五辆车分流客源,去往县城的车要为其他车辆留足客源量,而乘客的福利和权利就没法去考虑。
猪肉摊位、车辆牌位和其他的大市场以及盈利较大的产品买卖都被陈家垄断,其他人只有和陈家扯上关系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如到县城的中巴有段时间就归属于陈家的一位外地女婿。
陈家已经在白沙“闹子坪”上形成了一个既得分利集团,他们不仅能够占领主要市场,还能控制市场(包括准入、价格、品种、数量、秩序等),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二)宗族基础、混混渗透与市场秩序
陈家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宗族支撑,使其有底气,敢于做,而他们之所以能做成,则完全是因为陈家宗族里的混混在市场上游荡。
一般而言,宗族力量既可以是静态的表述,体现在它的气势上,也可以是动态的过程,这就需要有载体。
也就是说,宗族势力的表达需要由宗族里的某些群体展示出来,比如“自然村领导班子”的强悍有力,不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又如普通村民能够精诚团结;互助互爱,而宗族内的混混的凝聚、霸道、不怕死的气概也常常被认为是宗族力量的体现。
正如上文所言,村落不是混迹的合适场所,因此不同村落的混混都到集镇上来混,而宗族力量强大的陈家混混势力最为庞大,他们的背后还跟着许多小宗族的或远地方的混混。
在集镇上,不同混混群体因各自宗族势力的强弱而有等级分化。
陈家的混混等级最高,人数最多,队伍最庞大,在市场上也最嚣张,刘家的混混次之,也有个很强的队伍。
其他地方的混混依靠这两大宗族的混混而在市场上混世求生存,他们是大混混群体的跟班和打手,而大混混则会罩着他们,帮他们出气。
这样,很可能两个小宗族的混混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因为他们各自所依靠的“东家”介入进来,形成大混混群体之间的斗争,最终演变为两大宗族的矛盾,从而需要通过宗族之间的协商解决。
而在混混群体内部,也分等级,在街面上有大笔财产、店面、摊位的混混是混得最好的,他们往往是混混里头的老大,陈家就有一个在市场上拥有上百万资产的混混,此人理所当然地是陈家混混的老大。
次一级的混混要么有财富在市场上,但不够气势,要么在村落里拥有不少兄弟或堂兄弟、“屋里人”。
处在最底一层的一般什么也没有,只能跟着他人混,他们一般在市场上对陌生人(故意)生出事端,实施敲诈勒索,以此满足自己的生活消费。
因此,混混群体的分层源于各自背后的宗族力量,但最终可表现为职业上的分层,有职业的就是在市场上开店面、摆摊位、摩托出租、中巴老板等,而没职业的则跟在这些有职业的背后,保护他们或驱赶他人,为自己的“东家”办事。
混混群体除了保证自己在市场上获得利益之外,还是族人的保护伞,为他们开辟市场、保护他们的正常运营、控制市场规模等。
如果归属大宗族里的人在市场受到“不公正”对待,只要联系本宗族的混混群体,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而基本上是不计报酬的。
只有在给其他小宗族混混“摆平”某些事上,才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陈家宗族控制了白沙“闹子坪”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俨然整个市场就是陈家人的,因而陈家在市场上营业可以抗拒缴纳市场税,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得维持市场治安、调解市场纠纷,这部分工作也由陈家混混集团承担,他们成了市场上的执法者。
因此每到赶“闹子”的时候,陈家混混成群结队地聚合在一起,在一个市场的棚架下摆桌子聚众赌博,市场上一发生矛盾纠纷,他们就立马行动,这样不仅能够维持市场平静,还可以从中捞上一把。
由于集镇上宗族混混的精诚团结,市县的混混就下不来,下来了也是“死鱼”一条。
案例3在四五年前,白沙“闹子坪”每逢闹子,就有30多张桌子摆在一个大型的棚架下聚众赌博,摆桌子的人即这张桌子的庄家。
只要是陈家的混混,财力比较雄厚、势力比较大、行事比较凶狠,都可以到市场上摆桌子设赌。
这样的赌桌是不上缴市场税的。
从2005年开始结束这种“战国”的场面,不再各自为政,而是由六大“股东”垄断了市场上的赌场,其他人不得随意摆桌子设赌。
谁想摆桌子设赌坐庄,须请示“股东大会”,交纳两百块钱方可设赌,由股东大会保证每张桌子的安全。
股东大会的龙头老大就是陈家在“闹子坪”最大的混混,人称陈老大。
他兄弟多,家族势力大,由小混混一直混到陈家的大混混,拥有数百万资产,在市场上办了几个工厂(鞭炮厂及其他店面),几年前被乡政府推选为“企业办主任”,负责乡镇企业管理。
因此此人白道、灰道通吃。
由这位陈主任召集另外五位人士入股,这五人中有一位是乡中心小学教务处主任,同时也是陈家的女婿,其余皆为没有正式职业的陈家大混混。
这些人每人凑5000元,合成三万元本金,每次派一位股东出面坐庄(唯小学老师不便出面),以打牌赌博为生。
于是围绕着赌局形成了一大批寄生者:
股东、小庄、赌博者、放高利贷者、“治安人员”等。
(三)混混介入市场造成宗族吸纳市场的假象
综上所述,混混之所以能在市场上横行无忌、控制买卖,完全是仰仗宗族的势力,如果宗族一旦在市场中退场(比如衰弱),混混群体就会面临解体、重组;而宗族则依靠族内的混混为自己打拼天下,捞得好处,显示实力,假如族内混混在市场上被清扫,宗族就无法再控制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就会崩溃瓦解。
这是一种相辅相生的局面,一方离开了另一方都会受到损失。
就是说,当市场经济冲击传统的宗族,在巨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