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docx
《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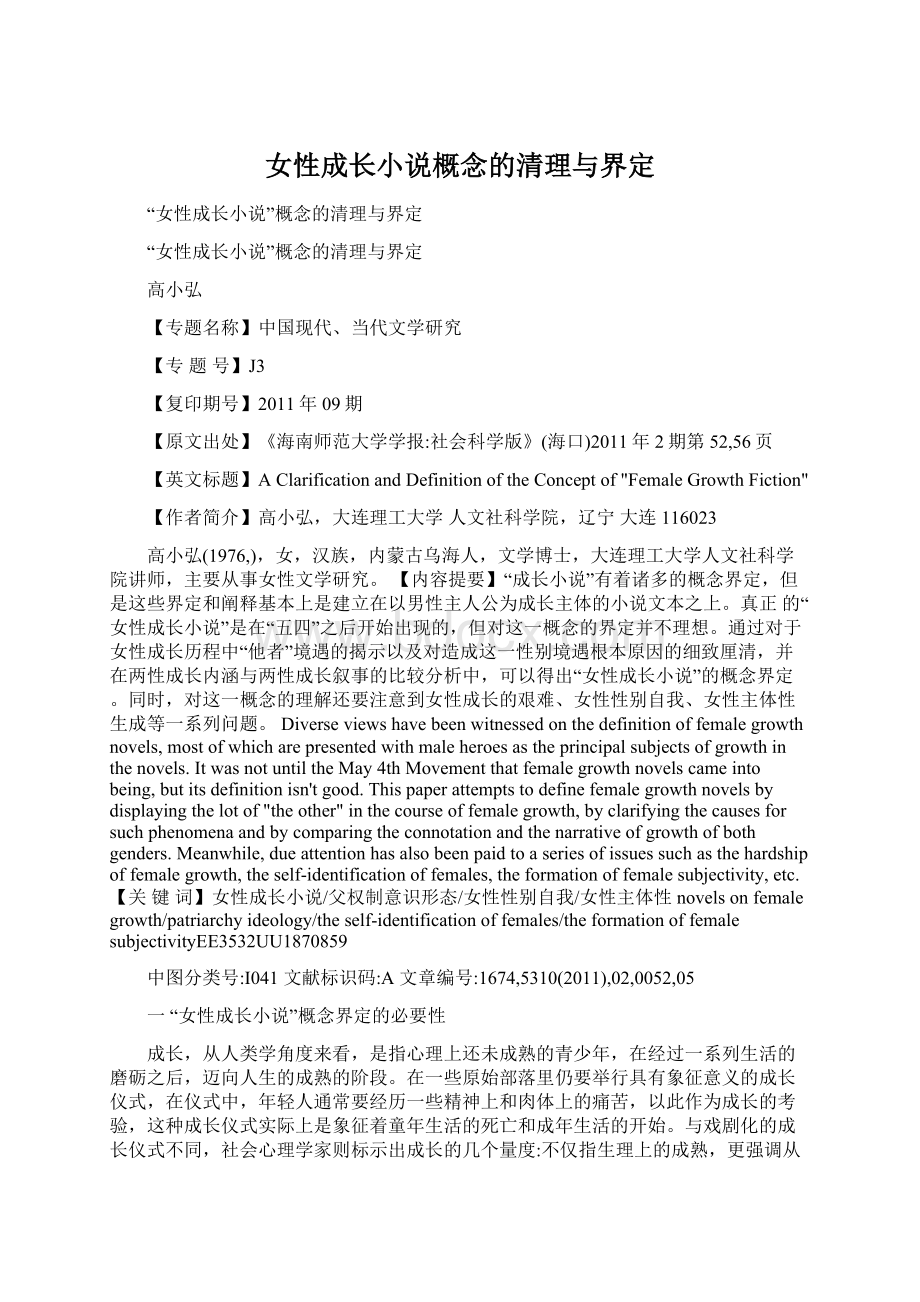
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
“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
“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
高小弘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3
【复印期号】2011年09期
【原文出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海口)2011年2期第52,56页
【英文标题】AClarificationandDefinitionoftheConceptof"FemaleGrowthFiction"
【作者简介】高小弘,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高小弘(1976,),女,汉族,内蒙古乌海人,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成长小说”有着诸多的概念界定,但是这些界定和阐释基本上是建立在以男性主人公为成长主体的小说文本之上。
真正的“女性成长小说”是在“五四”之后开始出现的,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不理想。
通过对于女性成长历程中“他者”境遇的揭示以及对造成这一性别境遇根本原因的细致厘清,并在两性成长内涵与两性成长叙事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得出“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
同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还要注意到女性成长的艰难、女性性别自我、女性主体性生成等一系列问题。
Diverseviewshavebeenwitnessedonthedefinitionoffemalegrowthnovels,mostofwhicharepresentedwithmaleheroesastheprincipalsubjectsofgrowthinthenovels.ItwasnotuntiltheMay4thMovementthatfemalegrowthnovelscameintobeing,butitsdefinitionisn'tgood.Thispaperattemptstodefinefemalegrowthnovelsbydisplayingthelotof"theother"inthecourseoffemalegrowth,byclarifyingthecausesforsuchphenomenaandbycomparingtheconnotationandthenarrativeofgrowthofbothgenders.Meanwhile,dueattentionhasalsobeenpaidtoaseriesofissuessuchasthehardshipoffemalegrowth,theself-identificationoffemales,theformationoffemalesubjectivity,etc.【关键词】女性成长小说/父权制意识形态/女性性别自我/女性主体性novelsonfemalegrowth/patriarchyideology/theself-identificationoffemales/theformationoffemalesubjectivityEE3532UU1870859
中图分类号:
I0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5310(2011),02,0052,05
一“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界定的必要性
成长,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是指心理上还未成熟的青少年,在经过一系列生活的磨砺之后,迈向人生的成熟的阶段。
在一些原始部落里仍要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成长仪式,在仪式中,年轻人通常要经历一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此作为成长的考验,这种成长仪式实际上是象征着童年生活的死亡和成年生活的开始。
与戏剧化的成长仪式不同,社会心理学家则标示出成长的几个量度:
不仅指生理上的成熟,更强调从儿童阶段到成人阶段的社会身份的转变,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认同以及理性思维能力的获得。
作为人类个体重要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文化现象,成长必然会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对象。
这首先是因为成长本身就意味着童年与成年交界的空白地带,意味着困惑与渴望相伴、恐慌与顿悟并行的心路历程,这一充满悖论与张力的人生阶段为创作开拓了意味深长的审美空间;其次,走向成长的青少年往往在初次面对充满欺诈与暴力的社会人生时不知所措,以往儿童时代所秉持的那种纯真和美好无法应对丑恶的现实人生,要想顺利实现社会化的成熟过程,就必须捐弃童年时代的率真,因此,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失乐园”的文化象喻,而其中所体现的成熟与异化如影随形的生存困境,形成人类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永恒探询;再次,成长总是以个体为其承担者,在自我与社会的融合与冲突中确立自我个性,寻找具有主体性价值的自我文化身份,这本身就体现了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和确证,对于生命意义的自觉追求。
可见,“成长”本身丰富的文化意蕴决定了它成为一个反映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文学母题,特别是在长于表现广阔现实生活和精深心理体验的小说体裁中,有关成长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并形成了“成长小说”这一独特的文类。
作为一种按文学主题特征进行分类的小说类型,“成长小说”的创作传统悠久,数量巨大且影响深远,但对其审美范围的界定,学界却很难达成共识。
具有代表性的界定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所作的系统阐述:
“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
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
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
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
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的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
”[1]另一个具有理论代表性的说法来自莫迪凯?
马科斯,他将众多成长小说的定义作了深入的归纳分析后,指出对“成长小说”中关键词“成长”的界定一般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将成长视为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逐步增长的过程;二是把成长解释为一种认知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在我国理论界,对于成长小说有代表性的理论论述有以下几种:
一是基于“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基本观念,认为成长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
[2]二是通过归纳中国成长小说的文本特征试图把握成长小说的内涵,这几个特征分别为:
小说的主人公是性格尚未定型、成熟的青少年;主人公与生活于其间的人和环境的关系,有教育与被教育明确的施受关系;主人公的文化成长得到确定而充分的表现,而文化成长的关键词是“改变”;在成长小说的行动元结构中成长通常是构成小说的基本物质材料,并得到连续显现而保持足够的叙事维度。
[3]三是强调成长小说文本中必须出现“主人公迈出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并在分析美国文学中公认的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归纳了几个特征:
强调成长小说内容中须具有亲历性的特征,认为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构成了成长小说模式化的叙述结构,即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并将主人公获得对社会、人生和自我的重新认识看作主人公在经历生活磨难之后的成长结果,并进一步强调这种认识必须是“明确而切肤的感受”。
[4]
毫无疑问,以上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和阐释,基本是建立在以男性主人公为成长主体的小说文本之上,男性的主体成长被默
认为人的主体成长,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脉里,那些能同构文化原型模式、负载丰富文化意蕴、形成古老文学母题的成长文本,实际上就是男性成长小说。
这一文化现象也印证了父权制社会中所谓人的主体即专指男性主体的特点,而居于从属边缘地位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注定由于主体性的缺席而喑哑无声。
女性所处的文化位置决定了文化长河中女性成长故事的无名和匮乏状态,而男性成长故事中的大部分女性形象也无法逃脱男性对于女性文化想象的窠臼:
承载男性审美和情欲理想的天使或圣女以及道德堕落构成罪恶渊薮的妖魔或荡妇,前者因貌美在男性成长故事中与其他宝物一样成为迷人的客体,不仅构成男性成长的叙事基本动力,而且还可以作为男性经历考验后的绝妙奖赏并标示男性的成熟;后者因貌美或谗言成为男性成长过程中陷阱或诱惑的化身,作为一种危险的成长考验潜伏在男性成长的路途上。
女性这种两极化修辞以及在男性成长舞台上的功能设置无疑是为了衬托男性这个成长主体,而女性的真正存在及生命成长却在关于男性成长的形形色色的阐释中被封闭在文化视觉的盲区中。
在中国文化史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照亮了几千年黑暗、喑哑和隐秘的女性文化世界,以人的觉醒促发了女性性别的觉醒,使初步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开始以一种来自女性生命体验的语言进行自我言说和言说自我,而这就意味着女性成长小说真正破茧而出,真正从文化无意识的混沌与黑暗中浮出历史地表。
事实上,女性成长小说也在不断的发展深入中,推动20世纪女性写作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
基于此,把“女性成长小说”当作一种文类提出并对其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定就非常必要了。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女性成长小说”这一提法虽经常被人使用,但更多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较为严格的理论清理和概念界定,学界较为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认为女性成长小说“主旨在于全面展示女性主体的成长过程”。
[5]这一提法看似无懈可击,但事实上,由于“主体”在思想史领域里存在着过于复杂的涵义,比如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的“主体”就是对康德以来人文主义“主体”的反驳,女性主义到底强调的是哪个“主体”,这个概念并没有做出理论说明,即便这一概念全盘接受的是人文主义的主体观,那么后现代的思想成果要不要或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也未见有清晰的论述,因此,用这样一个涵义本来就模糊不清的术语作概念界定的关键词,得出的结论自然暧昧不清了。
另一种公认的提法是对女性成长小说中“成长”进行理论阐释,认为“这个成长,是双重指向的成长,一方面指创作主体/女作家在这一时期思想和艺术不断深入、成熟的发展经历,一方面指作为创作对象的时代——社会——家庭——男人——人等诸事项与众生相的发展变化”。
[6]这一界定看起来也义正辞严,但由于“成长”的内涵和外延过于宽大,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从而失去了特有的理论针对性。
理论界对“女性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认识的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这一文类的研究,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整个女性文学的认识,因此对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的理论界定将是十分必要的。
二“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
“女性成长小说”毫无疑问属于成长小说这一大的范畴,它首先具有成长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从幼稚走向成熟,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必然要经历文化心理转变等,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女性成长小说”又有着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它得以确立的根本,也是极需要清理与明晰的关键所在。
从本质上讲,“女性成长小说”独异特征的核心即是“女性”这一性别前提所内含的性别特质,而“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7]因此,“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
”[7]704也就是说,女性现实生存构成的性别境遇应当具有一种本源性的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女性成长的路径选择和命运结局。
因此,只有在深刻探究女性性别境遇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其他派生出的女性性别成长的各种文化命题才有可能被理解和认知,也才可能真正找到“女性成长小说”的独特性所在。
女性成长历程中的性别境遇,正如波伏娃所言:
“她是附庸的人,是同主要者(the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inessential)。
他是主体(theSubject),是绝对(the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Other)。
”[7]11而所谓的“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
”[7]5女性这种“他者”的性别境遇是在男性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中被强制性给定的。
由于没有相对照的“他者”,就根本无法树立“此者”,因此女性并不是在将自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男性“此者”,而是男性在把自身确立为“此者”的过程中将女性树立为“他者”。
而且男性“此者”与女性“他者”之间的关系,缺乏一种可能平等转换的相互性,男性被树立为唯一的主要者,女性只能顺从地接受这种带有“纯粹他性”的“他者”境遇。
事实上,任何一个生存的个体都不愿丧失自我主观意志,任凭他人或环境来摆弄自我的命运,因此,造成女性“他者”性别境遇的根本原因可以直接溯源到人类早期的社会文化结构。
历史地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8]这一历史演变造成了一种带有性别统治色彩的社会关系,并进而产生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根据康奈尔的说法,“在任何不平等的结构中都会形成一定的利益,结果必然会造就一些不同的集团,通过维持或改变这种结构,这些集团得到或失去利益。
一个男性统治女性的性别结构不可避免地形成防卫性的男性利益集团和求变性的女性利益集团。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它与男人们作为个体是爱女性还是恨女性或者说是相信女性是平等的还是卑劣的无关,它也与女性目前是否追求变化无关。
”[9]为了维护男性性别统治的社会结构,“防卫性”的男性利益集团逐渐生发出一种以男性中心观念为核心原则的父权制意识形态,这种父权制意识形态最终成为男性维护自己利益的最重要的工具与手段,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套简单静止的观念,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和重构的动态过程。
具体而言,父权制意识形态借助习俗观念、家庭与社会教育甚至宗教,给两性生理上自然而任意的身体构造赋予差别和等级意义,在臣属阶级(女性群体)那里生产出一种既代表男性利益,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却又看起来非常客观化的社会标准,这一标准不仅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接受进而内化成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的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数千年男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
这一标准的具体表现就是社会对于男女两性在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方面的限制和规定。
如果说性别气质“指的是沿固定不变的路线形成人格,而这一切的基础,又是实施统治的这一性的需要和价值观;被用做准绳的,是这一性的成员崇尚的品质和较方便地在从属的那一性的成员身上发现的品质”,[10]那么,就女性而言,“女性气质并不是指女人的自然状态,它只是赋予‘WOMEN’这一符号以历史可变性的意识形态意义,而这一意义是被男性社会群体为其自身所构建出来的,他们借助制造一个虚幻的他者来缔造出自我的身份和假想的优越性。
”[11]也就是说,男性主动、智慧、有力量与女性被动、无知、温顺等性别气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父权制意识形态“有意”建构的文化产物。
与性别气质相依存且相互补充的是性别角色,它要求两性分别符合一整套互相协调行为、姿态和态度的规范。
在父权制社会,分配给女性的只是趋向于生物体验水准上的有限的角色,而把所有能够被描述为真正人的而非动物的活动都保留给了男性。
社会所分配的性别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首先鼓励建立符合角色职能的两性气质,而性别气质的习得也与性别角色规范的充分内化有关。
这种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的循环论证,将社会普遍观念围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沼泽里,而男性中心观念则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文化惯例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同。
但是作为“求变性”的女性利益集团并不总是甘于屈服,而是不断地滋生对于自身臣属性地位的不满意识,父权制意识形态
就需要不断地再生产来巩固和维护性别统治关系,这种再生产的实现主要是施用两种策略将女性压回到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的强塑中去。
首先,启动一种文化监视体系,使女性置身于“性别化的集体匿名凝视”中,这一凝视内含了一系列父权制社会中有关女性道德和行为的评价模式,通过敦促女性实践父权制意识形态标准来行使性别权力。
当女性被迫面对这无处不在的“男性主体凝视”时,她就被降低为“被看的客体”,成为一个时时要“纠错”以使“凝视”主体满意的客体。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一伴随整个女性成长过程的“凝视”中,女性逐渐开始“自我监视、自我审查”,自觉在潜意识和人格中植入了一个以男性立场存在的“虚幻的主体”,并以男性的眼光“凝视”并审查自我的身体、语言、姿势等日常生活表现。
而女性精神内部出现的这种自我分离倾向,致使女性“自为”存在在文化监视系统的凝视下溃散了,沦落为父权文化秩序中一个“他者”。
其次,在全社会范围内生产一种双重道德伦理范式和双重道德标准,即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主张的两种基本道德:
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
在主人(男性)的道德里,善的意思是做世界的统治者,恶的意思是被压制、被镇压或被踩在脚下。
而奴隶(女性)的道德正是主人道德标准的极端对立面:
谦卑和被动等特点被视为奴隶的美德,而决断、能动等特点被看作奴隶(女性)的恶习。
一旦女性的真实自我不自觉地越过了这一道德默许的界限,道德律令的审查便使之有羞耻、焦虑、负罪等感觉。
久而久之,女性便逐渐产生出对权力意志的消极态度,害怕冲突、挑战,满足于平庸。
这一强大而虚伪的双重道德律令,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将女性彻底固定在“他者”的地位上。
女性“他者”的性别境遇决定了女性的成长与男性的成长迥然相异。
表面看来,女性的成长虽与男性一样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作为男性成长起点的幼稚主要是意味着对自己社会角色的混沌,而成熟则是男性气质的最终获得,以及男性对于父权制意识形态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男性知识分子有可能拒绝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但始终避免不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侵蚀)而女性的“他者”境遇却导致了相反的成长逻辑,女性的幼稚除了指代童年时期的懵懂之外,主要是指女性对于父权制强塑下的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的全面认同和贯彻,而女性的成熟则是对父权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疏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女性的成长之路。
正是两性成长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两性成长叙事的根本差异。
从大多数文本的实际情况来看,男性成长小说的叙事内容由于应和了父权制文化惯例,更容易获得叙事权威。
而女性成长小说所描述的那种偏离父权文化常规的女性成长真相,却常因逾越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和挑战公众的日常观念,而时时面临被审视、被质疑甚至被否定的困境。
另外,就叙事效果而言,由于浸淫着男权观念的常规语言系统基本不会与男性写作者思想情感倾向发生根本抵牾,因此,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整体风格会呈现出明晰的一致性。
而女性写作者则会时常陷入了两种话语类型的窘境中:
一种是支持性别统治的话语倾向,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表达;另一种是坚持女性真实体验的反性别统治话语倾向,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反抗和消解。
这种语言窘境直接会产生出一种认同与质疑、抵抗与服从杂糅的创作心理,因此,女性成长叙事的审美效果就呈现出晦暗不清、枝蔓丛生的特点,而这种叙事效果本身也隐喻了女性成长历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
通过以上对于女性成长历程中“他者”境遇的揭示以及对造成这一性别境遇根本原因的细致厘清,并在两性成长内涵与两性成长叙事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将得出“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
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
三关于“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几点说明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概念的提出与界定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恰恰相反,它是相对的、有一定限度的——一个再完备的概念都会有它的缺陷与不足。
因此,有必要在对“女性成长小说”这一概念界定后再补充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以使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趋于完整明晰。
首先要说明的是女性成长的困厄,即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追求精神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保持真实自我与完成自我实现是极其困难的。
这主要是因为父权制文化意识总是以强有力的主体姿态破除女性保存自我的壁垒,将女性排挤至客体和边缘的位置,并强塑了以“被动”和“服从”为基本品质的女性的“自我概念”。
这种人为建构和系统灌输的“自我概念”,损害了女性原初的、积极的自我力量,泯灭了其追求自我同一、精神自由和完善自我人格的意识,使其无法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全部可能性。
更为严重的是,正如波伏娃所言:
“和每个个体肯定其主观存在的道德冲动一起出现的,还有一种诱惑,使其放弃自由,变成一个物。
”[7]17这种诱惑就是完全认同自我的客体地位,甘愿成为他人意志的造物。
而个体无法拒绝这种诱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生存方式“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由于不具备确定的资源,由于认为把她与男人相连接的纽带虽不可缺少却是和相互性无关的,由于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
”[7]17这样一来,女性所谓“真实的自我”有时不过是压抑女性主体力量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同谋者。
在这个意义上,跋涉于成长之途的女性不时地沉浸于两种意愿的冲突和两种自我的区分当中,内心也不时被两种意识纠扯着:
或者被动服从父权意识强塑的女性气质与女性角色,从而可以回避主体性生存带来的艰辛与苦痛;或者主动抵制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有力强塑,但需要承担主体性生存全部的坎坷与挫折。
女性成长的脚步就仿佛在这两条价值指向“背道而驰”的成长之路上游移不定,最终导致了女性自我人格的破碎与分裂,神经官能症和精神抑郁症也就成为女性特有的成长症候。
其次,女性成长历程中所要建构的“性别自我”,包括“性别身份”和“成为自我”两重涵义。
性别身份,是人的首要身份,是人们在成长历程中首先获得的身份,因此它最具永久性,意义最深远。
而个体的性别身份并不仅仅是其自然性别的产物,更是在某种支配性观念(如男性中心观念)的隐形作用下,在社会文化中不断建构而成的。
性别身份认同的核心,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某些现象与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联系起来的性别认知,这种开始于童年时代的性别认知会贯穿整个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生成的过程。
对女性而言,这种性别认知恰恰是父权制意识形态长期作用的结果,它决定了女性的性别身份既是与生俱来、不可脱卸的自然身份,更是一个被铭刻了屈辱和压抑的文化身份。
因此,女性成长既要尊重性别身份所带有的独属于女性的特有的自然标识,同时也要充分地辨识性别身份的社会性对于女性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的“个人”所带来的全部的阻碍性,这样女性才能将做女人与做个人统一起来“成为自我”,才能成为一个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个人”。
“性别自我”这一提法不仅将价值目标界定为“女性个人”,而且也充分考虑到性别身份的社会性给这一成长目标带来的艰难。
最后,“主体性生成”作为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界定的关键词,无疑需要重点说明。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明确指出:
“每个打算为自己生存辩护的人,都会认为他的生存含有一种不明确的需求,即超越自我、参与自己所选择的设计的需求。
”[7]25也就是说,每个生存的个体都具有通过开拓或设计自我命运,从而超越自我有限存在的主体性要求,而女性也会本能地选择做一个根据自我主观意志、能动地实现自我超越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
然而父权社会中强加给女性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有力束缚,使女性无法获得一种主体性力量以实现自我设计与自我超越,也就无法获得自我实现与自我价值。
因此,“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ego)’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
者。
”[7]25在这种戏剧化的处境中,女性被